犹怜人间草木青
2023-11-15徐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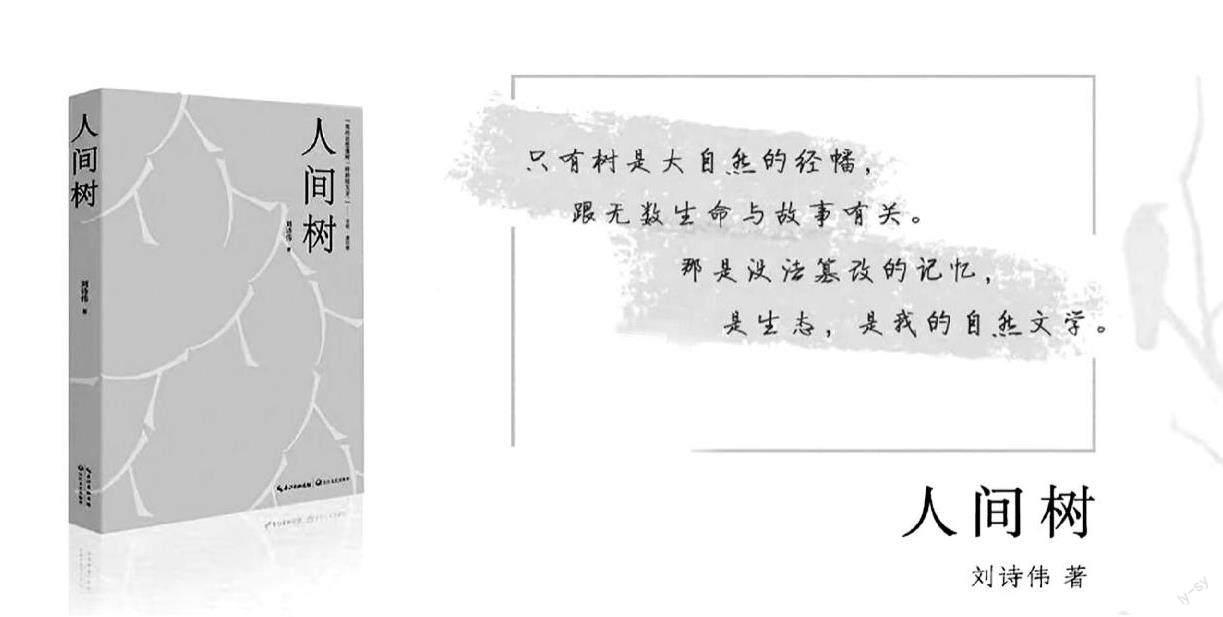
刘诗伟是文学界公认的一位优秀小说作家。读了他的散文集新作《人间树》之后,我禁不住要感叹:他的散文才华被他的小说给遮蔽了!或者也如前辈作家汪曾祺所言,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首先都得把散文写好,如果连一篇散文都写不好,遑论能写好其他。
《人间树》里自始至终写到了一个既是地理概念又有类似福克纳笔下的文学意义上的“邮票大小的故乡”——兜斗湾。这是江汉平原上、通顺河大堤下的一个小小村湾。村边的一棵大柳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鹊巢,一对喜鹊常年站在树冠和高枝上喳喳鸣叫。湾子里任何一家的风雨、悲喜,甚至是人来客去,也都是全村公共的风雨、悲喜与人来客去。
兜斗湾是作者童年和少年时奔跑与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和心灵的“故园”,与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约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凤凰之于沈从文,白鹿原之于陈忠实,高密之于莫言,枫杨树之于苏童,没有什么两样。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到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我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刘诗伟对兜斗湾的一草一木、妇孺老少和人情世故的熟悉程度,比曼德尔施塔姆有过之而无不及。福克纳说自己那个像邮票大小的故乡,“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人间树》里写到的那些人与事,如果一一展开来写成小说,显然也足够作者写上一辈子的。兜斗湾是江汉平原上的一口深井,值得作者继续深挖下去。
《人间树》除了两章短小的序跋,全书收入15篇长散文,最长的可能已经超过3万字,近乎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全书分为“乡亲们”“上辈人”和“我自己”三辑。但人事的交错、代际的延续里,都离不开兜斗湾的阴晴圆缺与光风霁月。所以,《人间树》不同于一般的散文结集的是,它是一个互为关联、比较完整的叙事整体。“我”的成长、回望与反思,贯穿全书。与其说这是一部散文集,不如说它是一部“村庄史”和“村庄传”更为准确。书中的每一篇章,都是作者为自己的乡村和乡亲写下的“志”与“传”,是乡村风雨志,也是乡野心灵史。
磨菜刀的王大猴,劁猪的郭胖子,驼背老爹,还有剃头佬、老木匠、道魁叔、水亭叔、务善老爹、亦疯亦痴的奇人胡贤木……这些乡里人物,都装在作者的心底里,记忆都保留得清清楚楚。记得老作家孙犁曾略带自嘲但也不无自信地说过,自己“好写女人”。毫无疑问,与描写劁猪的、剃头的、磨菜刀的这等人物相比,刘诗伟跟孙犁一样,也是“好写女人”,更擅长刻画女性之美。于是我们看到,在他的笔下,出现了莲婶、麻婶、杨枝阿姨、缺嘴婆,还有祖母、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外婆、母亲、姑姑、儿时的玩伴小女孩等众多的、性格各异的乡村女性形象。所以,读着诗伟的这部作品,我还有另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他的家乡江汉平原和兜斗湾子,真应该庆幸和感谢,能拥有这样一个悉心洞察她、感受她和热爱她的儿子,并且他还能够怀着“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一般宽厚的心胸,用自己温情的笔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当然,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庆幸,拥有一位这么好、这么接地气的作家。
人间草木,乡村伦理,大地道德,在《人间树》里呈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几乎写遍了生长在江汉平原上的常见的树木家族:柳树、桑树、苦楝、白杨、刺槐、山楂、银杏、木子树等等。这些姿形不同、年轮各异的普通的树木,也一一对应和象征着书中诸多普通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比如缺嘴婆的柳树,莲婶的苦楝,麻婶的枣树,祖母的桃树,祖父的刺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从作者对这些人间草木的仰望与顾怜之间,也不难感受到一片温润的散文文心,那就是前辈诗人所赞许的“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片文心,或许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无关,但一定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伦理、大地道德息息相通。因为描述得当,作者的是非观点也就自在其中了。文以载道,托物言志,从来就是中国散文的传统与正脉。《人间树》接续和流淌的正是散文的正脉。
常言道:君子关注眼前事,真佛只说家常话。好的散文作家,一定也会倾心关注当下现实,并且力避和摒弃虚浮的抒情,返璞歸真,以“说家常话”为美。我自己写散文,几十年写下来,回头一看才发现,竟然也是一个从追慕华丽到回归平实的过程。青年时代激情澎湃,写了很多语言华丽、感情上“浓得化不开”的抒情散文;后来渐渐认识到这种文风的浮夸与矫情,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文笔平实质朴的才是好散文。诗伟的散文,不求宏大,却人情练达,甚至能在乡俗俚语之中别开生面,闪耀出文学的光芒。平原上的底层小人物的声音,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幽怨与悲苦,不再仅仅具有个人色彩,而成为一种唤起人类共有的经历与记忆的东西,成为一种具有普遍和永恒意味的文学的内容。这样的细节和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比如他写村头的大柳树和喜鹊巢:“我差不多每天看见它冠顶的鹊巢,认得那两只在枝头蹦跳的喜鹊。”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乡村孩子的记忆。“早春时节,它们喳喳、喳喳地鸣叫,声调平和,节奏明快,那是通报戗剪子磨菜刀的王大猴即将进入兜斗湾。”谐谑的回忆里有温情的乡愁。当然,兜斗湾不是世外桃源。哪一段家庭悲欢和个人经历,不是与国家命运、时代风雨休戚相关?“冬天来了,大雪覆盖平原。柳树白了,树冠上的鹊巢变成白白的一团,只有站在白鹊巢上的两只乌鸦继续黑暗着。有时,它们得意地哇了一声,不是特别恐怖,日子勉强太平;然而,一旦它们真格儿‘哇——哇嚎叫,便狰狞无阻,声音所到之处,天空霎时黑了下来。”我们这代人都是经历过这样的严冬的,从这样的细节里,焉能辨认不出那个时代的样子?怎能听不到大时代里真实的风声与雨声?
他写自己少年时背着小小行囊,离家去毛嘴求学,祖母站在台坡口,用手搭着额头,满怀期待地观望着远处的情景;写自己有时放学回家,独自站在河堤,望着纷纷扬扬的黄叶,隐约听见沙哑的蝉鸣声,黄狗乌子跑过来舔着他的手,这时候,少年的脸上闪着无声的泪光……“你看见老老少少的人挑着箩筐,扛着扫帚,纷纷从湾子里出来,急切地赶往杨树林……那不是去打扫大地,是要扫积树叶,把它挑回家当柴火。”这样的情景,不就是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吗?作者笔下的乡愁有美丽的与温暖的,但也不乏苦涩、冷冽与沉重。那是那个年代整个江汉平原的苦涩、冷冽与沉重。作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往往能于雨丝风片里写出时代的风声雨声,展现出时代风雨和世态冷暖中的普通劳动者的生存智慧与生活信念。
《那些叫作杨树的柳树》的结尾写道,有一天,作者沿着村路回到兜斗湾,半道上迎面遇见一位衰老的老人,“使劲想了一阵,陡然惊呼:哦,你是道魁叔”。这是作者从小就熟识的一位乡亲。接下去是这样两句对话:“您老没去女儿家?”道魁叔摇摇头:“湾里还有一个跟我一辈的人没死。”作者又问:“下游湾子的椅子赔完了吗?”这里说的是一件遥远的往事。道魁叔竖起两根手指:“还差两把。”散文到此,戛然而止。看似轻描淡写的文字里,包含着何其沉郁的乡愁。让我不禁想到海子的诗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将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毫无疑问,《人间树》是近年来湖北乃至中国散文界的一个重要收获,相信会被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关注。它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散文集,但书中不少篇章也可作小说观。因为作者本来就是小说家,善于用丰饶而真切的细节描写支撑起韵味悠长的叙事,也擅长在散文的笔调里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平原人家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现实日常的拥纳与挚爱,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坚韧、温暖与生生不息。
现在很多作家喜欢把“人民性”“人民立场”挂在嘴边,这很好,总比无视人民性与人民立场要好。什么是人民性?散文家普里什文有一段话,我曾借来表达自己对“人民性”和“人民立场”的理解:“在我的奋斗中,最能够使我显得突出的,就是我的‘人民性,是我对祖国母亲的语言和对乡土大地的感情。我像草一样,在大地上出生,也像草一样,在大地上开花。人们把我收割下来,马吃掉我,而春天一到,我又会一片青葱。夏天,快到收割的时候,我又开花了。”诗伟和兜斗湾的关系,以及他在散文里呈现出来的姿态、立场与草木般朴素的感情,也是一位作家对“人民性”和“人民立场”的最好的诠释。
徐鲁 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第十届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届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现任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 王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