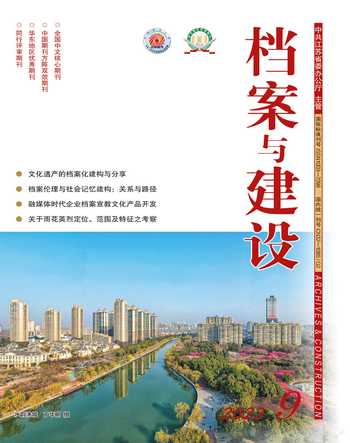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关系与路径
2023-11-12聂云霞陈彦慧
聂云霞 陈彦慧
摘 要:档案是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档案伦理作为规范档案主体行为的道德准则,可为社会记忆的合理建构提供内在指引。结合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基本概念,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档案伦理对社会记忆建构起正向促进作用的同时,社会记忆建构活动也在不断充实档案伦理内容。基于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内涵及二者间的关系,文章从档案主体、正义、技术与法理四个伦理维度出发探索社会记忆的建构路径。
关键词:档案伦理;社会记忆;建构路径
分类号:G270
Archival Ethics and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and Path
Nie Yunxia1,2 Chen Yanhui3
( 1.College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0; 2.Archival Undertak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3.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
Abstract: Archive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As a moral code that regulates the behavior of archival subjects, archival ethics can provide conceptual guidance for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Combin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archival ethics and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archival ethic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and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re constantly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archival ethic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archival ethics and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social memory from the four ethical dimensions, namely archival subjects, justice, technology and jurisprudence.
Keywords: Archival Ethics; Social Memory; Construction Path
在社会记忆理论中,人民是社会记忆建构的主体。档案作为最直接的原始记录,是人民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形态和承载体。一般来说,依托档案建构或参与建构的社会记忆更为真实、可靠。然而,毕竟档案的形成主体是“人”,其在形成、管理、利用等过程中凡涉及“人”的因素,必然也逃避不了伦理问题。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档案各主体间的关系愈加错综复杂,数智技术赋能档案资源的形成、保管、开发和利用等全生命周期。在此背景下,社会记忆的承载媒介、生成主体、建构形式等均发生新变化,原有的档案伦理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新发展、新要求。
學界关于档案伦理的研究虽然一直未曾“断链”,但将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进行直接关联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研究中以档案与社会记忆为主题,潜在涉及档案伦理内容的成果较为常见。如特里·库克认为档案工作者不能只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而应充当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不忽视社会个人和群体的记录[1];聂云霞等主张转变档案机构作为记忆管控的单一主体,重构一个拥有更多元话语权主体的社会记忆管控模式[2]。反观以档案伦理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则较少论及社会记忆内容,而是较多围绕档案伦理本身的建构与实现等方面展开讨论。[3-4]
总体看来,现有研究中关于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的专题研究成果较少,且既有成果的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本文拟从两者的内涵阐释出发,辨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档案主体、正义、技术与法理四个伦理维度出发探讨社会记忆的建构路径。
1 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基本认知
目前学界对“档案伦理”和“社会记忆”的认知尚无统一定论。为更好辨识和厘清本文所阐释的对象,重新梳理两者的基本内涵十分必要。
1.1 档案伦理
伦理学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道德活动与道德行为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5]黑格尔认为伦理是现实的或活的善[6],泡尔生也认为伦理可指示人们做出何等行为,养成何等品性,而后达于至善[7]。可见,伦理在相互关系中产生,其实质是实现行为个体的自我规约。档案伦理作为伦理学在档案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其可视为档案主体在参与各类档案活动中用以规范自身行为、处理各种关系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
档案伦理主要涉及主体、客体和中介三者。其中档案伦理主体是档案伦理的践行者,主要包括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档案工作者、博物馆、图书馆、科研院所及社会公众等文化机构与个体;档案伦理客体是档案伦理主体作用的对象,指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档案;档案伦理中介则是联结档案伦理主体正向作用于档案伦理客体的隐形桥梁,具体可指约束自身行为的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等。
档案伦理通过规约档案主体行为,留存真实、可靠的档案记录,满足公众对于档案资源的多样化需求,服务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建构要求,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经验指导。
1.2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中首次明确提出集体记忆概念,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8]。起初,哈布瓦赫这一开创性研究并未引起学界过多关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领域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升温,保罗·康纳顿、哈拉尔德·韦尔策等学者在继承和发展哈布瓦赫集體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记忆理论。其中,哈拉尔德·韦尔策认为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9]。孙德忠则将社会记忆定义为“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存储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10]。
关于建构,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将建构视为一种带有创造意味的发现、发明,以及一个发生与发展的过程。[11]丁华东认为建构是一个涵盖“昔日重现”的全过程,包含存储、提取、选择、排列、组合、解释(诠释) 、改造、叙述、表达、传播等复杂且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的“动作”[12]。
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社会记忆建构可简要理解为社会群体根据特定要求和情境,对过去获取的经验和知识进行选择性提取、加工和创造的过程,其实质是社会群体对历史、文化与知识等的重新理解、诠释和认同。
2 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的关系
档案伦理中所蕴含的“善”的价值取向,能够通过植根档案主体内心的方式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于无形中促使主体在是非曲直中保持清醒,并自觉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换言之,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以档案为关键联结点,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影响。档案伦理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正向的促进作用,社会记忆建构活动的开展也为丰富档案伦理内容提供实践支撑。
2.1 档案伦理正向促进社会记忆建构
档案伦理以其附着于档案主体的内在约束力,间接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了更为真实可靠、涉及多元主体、体现正义内涵的记忆内容。
(1)确保记忆可靠,留存真实记忆
档案不是事后撰写的,而是自然的“人为之物”,因而可视为原生态记忆或本源性记忆。[13]由德国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的记忆遗忘规律可知,人的大脑所能记忆的内容是有限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内容会逐渐地被遗忘。一般情况下,档案形成者出于职业操守和伦理底线,能对所发生事件照实具录,最大限度避免记录内容的失实、歪曲。在此基础上,档案工作者出于维护历史真实面貌的需要,对档案材料进行收集、甄选,并对其真伪进行鉴别,进一步确保了留存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此,人们通过留存的文字、图片、书信和历史物件等,能够实现最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记忆与活动画面的重构。
(2)关注多元主体,拓宽记忆范围
档案承载的社会记忆是带有一定主观性和选择性的历史记忆。特里·库克指出:档案与文件在历史认知、集体记忆、国家认同的塑造与定向中施行着权力,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作为个体、团体与社会的自我。[14]可见,当档案主体过多受控于国家权力时,便会表现出官方记忆占主导、公众记忆遭忽略的失衡态势。在档案伦理规约下,档案工作者将客观公正的选留态度内化于心,一视同仁地收集与保留具有重要价值的官方档案与民间档案。档案馆亦出于档为民用的工作理念,在馆藏资源建设中自觉扩大主体视野,主动将社会流动人口、失业人群等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形成的社会记忆纳入档案收集范围。
(3)维护完整记忆,凸显社会正义
档案缺失很大程度上会对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的完整度和历史价值造成影响,这对于建构完整的社会记忆十分不利。[15]在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海纳事件中,为防止公众公开指控昆士兰州青少年和儿童机构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行为,档案工作者违背档案职业伦理,同意内阁销毁由诺埃尔·海纳牵头调查的所有记录。[16]这一举动损害了记忆的完整性,亦有违社会公平正义。在档案正义伦理的感召下,档案工作者能够避免沦为非正义的“爪牙”,勇于抵制社会记忆建构中重要记录的恶意删除和遗忘行为。如面对日本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残忍事实的删除、掩盖与粉饰,档案工作者积极充当社会正义的捍卫者,通过收集有关档案文献或采集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档案,能够最大程度还原被蓄意抹去的历史原貌。
2.2 社会记忆建构充实档案伦理内容
数智时代,社会记忆各方面要素的变化对社会记忆建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档案伦理内容在延续其稳定性内涵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充实。
(1)多主体协同建构:档案治理伦理
长期以来,受传统档案管理思维影响,社会记忆建构的主体和对象多来源于执政党或国家政权机关。当下档案理论和实践正经历从“国家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模式”(“社会范例”)的重要转变[17],档案事业发展维度更加多元。随着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档案治理活动中,参与式档案治理模式渐趋成型。但一方面是多元主体参与档案治理的责任与义务有待进一步明晰;另一方面是档案治理体系仍在建设中,尤其是档案治理法律法规尚待建立健全。因此,治理实践中涌现的各种问题亟须从伦理层面给予回应。
(2)新形态融入建构:档案数据伦理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并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格式的文档、图片、网页、聊天记录及音视频等,是社会记忆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然而,这一时期人们交往呈现出的间接性、虚拟性、匿名性特征,很容易让部分人在道德情感上错位,做出违背道德伦理的失范行为。[18]如档案数据在采集、使用、传播等过程中,出现被恶意加工、利用、泄露等问题。尤其是当前数据鸿沟造成的数据壁垒,严重削弱了档案用户对于自身数据隐私的控制权,但现有隐私保护法律还未能对隐私范围作出明确划分。[19]档案数据作为社会记忆的新形态,其在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新的伦理问题不容忽视。
(3)新技术助力建构:档案修复伦理
档案受载体特性及外在因素影响发生的劣变、病害等,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社会记忆建构的完整性。面对数智技术在档案修复领域的深度运用,传统档案修复技术中存在的局限性得以缓解。海量纸质档案、照片档案、音视频档案在数智技术的修复下重新回归公众视野,进一步巩固了社会记忆建构的基石。但由此产生的伦理问题同样不可小觑,如目前破损照片档案数字化修复具备完美“移花接木”的特点,然则缺少相关规范制度的保障,易造成修复后照片档案失真等情况。[20]在缺乏强制性约束的前提下,运用数智技术从事档案修复实践的档案修复人员需借助一定的伦理准则进行自我“规训”,以最大限度地确保修复后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
3 档案伦理视域下社会记忆建构的主体和原则
从哲学角度看,主体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组织、机构和个人。无论是研究档案伦理,还是建构社会记忆,最终都需要基于主体来实现。从档案伦理视域考量社会记忆建构主体及其应遵守的原则,有助于在社会记忆建构活动中把握方向、明晰责任。
3.1 档案伦理视域下社会记忆建构的主体
数智时代,社会记忆生成环境日益复杂,以官方为主导的记忆形式逐渐发生转变,社会记忆建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具体表现在社会公众能够在政务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进行意见反馈与互动,也可通过参与众包项目上传档案资源、讲述个人故事。除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等主体外,其他机构及社会公众也纷纷参与。
档案主管部门和档案馆是社会记忆建构的引导者。其在发挥自身职能的同时,鼓励其他主体参与建构社会记忆并为其提供有效途径。
档案工作者是社会记忆建构的加工者。在档案编研工作中,档案工作者筛选、整合、凝练、重组档案材料的过程,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且由于档案的各个工作环节无不渗透着档案工作者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因而档案工作者所从事的档案管理工作,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记忆建构行为。
其他机构及社会公众是社会记忆建构的参与者。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是开展记忆资源建设与开发活动的重要主体。如首都图书馆发起的“北京记忆”、中国科学院牵头的“数字敦煌”项目等,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再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公众是社会记忆建构最广泛的参与力量,日益丰富的媒体书写工具为其描摹个体记忆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持,这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了极为充实的素材支持。
在社会记忆建构活动中,建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关键要素。档案伦理视域下社会记忆建构的主体、对象、原则与档案伦理主体、客体、中介相对应,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关系密切。社会记忆建构主体以建构原则为指引作用于建构对象,以此完成一系列社会记忆建构行为。
3.2 档案伦理视域下社会记忆建构的原则
原则是行动的基础,明确社会记忆建构的原则有助于为建构主体提供行为指引。基于档案伦理建构社会记忆应确保记忆素材的真实可靠,保证各主体在合法范围内平等参与社会记忆建构,并要求其自觉约束自身建构行为。
(1)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是首要原则,具体指各主体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应尊重记忆内容的真实性,准确客观地生成相关记录。公众作为社会记忆生产的主力军,应自觉将记忆的真实性置于首位,保证所分享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符合事实真相。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的加工过程中,亦应摒弃主观臆断,确保生成内容有理可依、有据可循,对于模糊不清、存有争议的信息,应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辨其真伪,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最为真实可靠的内容支持。
(2)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指社会记忆建构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不得以“自由”之名突破法律底线。由于现有法律法规为社会记忆建构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社会记忆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均受法律保护。相应地,档案主管部门应引导其他机构及社会个体主动对照法律规定约束自身行为,不得损害、侵犯他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档案工作者担负“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重要使命,须自觉抵制不良诱惑,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工作职责。
(3)平等性原则
平等性原则主要表现为多元主体的记忆表达与建构需求均能受到重视,并享有平等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权利。社会记忆是无数个体记忆的融合交汇,任何个体记忆碎片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社会记忆的不完整。以往社会记忆以“体制内”机构生成的记忆为主,平等性原则未能得到充分贯彻。而今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手段和渠道愈加丰富,档案部门应将普通公众及社会弱势群体等形成的“体制外”记忆合理纳入社会记忆建构中。
(4)自律性原则
自律性原则要求社会记忆建构主体保持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自觉抵制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建构行为。档案工作者应不遗余力将归档的记忆信息留存好,避免做出利用职务之便篡改、泄露机密信息等有违职业操守之举。鉴于公众在社交媒体中缺乏明确的辨识度,而数智环境中的记忆书写、内容传播拥有较大自由度之间的矛盾,参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个体应以更高的自律水平约束自身行为,避免捏造虚假信息、非法传播不实信息。
4 档案伦理视域下的社会记忆建构路径
档案伦理与社会记忆建构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档案伦理一方面可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发挥正向促进或规约作用,另一方面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不断涵养自身发展。鉴于档案伦理建构社会记忆的实质是利用符合社会认知的道德觀念指引社会记忆的形成与重构,因此主要可从主体、正义、技术、法理四个伦理维度探讨社会记忆的建构路径。
4.1 坚持人民至上,关注多元叙事主体
社会记忆之所以能够超越个体记忆的局限性且在个体内心扎根,源于社会记忆派生出的建立在人民之上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个体记忆鲜活、具体、直观,其形成主体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也在社会框架中重构记忆。因此,社会记忆建构必然离不开、也不能缺失个体性的表达。
数智时代,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个体叙事呈现出极大的延展性特征。普通公众得以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多元媒体书写个体记忆、表达个人观点,社会记忆的个性化、民主化特征愈加凸显。基于社会叙事主体的转变以及档案服务人民的本质要求,档案工作者对于档案的选留既要兼顾能引发共鸣、体现强大群体凝聚力的重大记忆项目,如脱贫攻坚记忆、北京奥运记忆等;又要关注看似于现实“无用”的“潜在记忆”,如普通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日常、就某一事件发表的观点等。各级各类档案馆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库,可进一步基于人民视角留存记忆,对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状态的记忆承载媒介进行收集。如普通市民镜头中关于城市人、景、事变迁的图片、影像,民间档案收藏者手中积攒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旧物件等。[21]针对目前档案资源结构不平衡,无法充分体现公民视角的现状,档案部门可鼓励非官方建档,即倡导个人、家庭、社群基于身份认同、记忆传承等目的开展建档活动。如上海市奉贤区档案局携手各镇、街道、社区、开发区档案工作人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已成功助力131户家庭建立家庭档案。[22]
4.2 融入正义内核,强化社会记忆认同
辩证地看,档案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价值会因利用者立场不同而呈现双面性。其可成为证明真相、遏制谎言与歪曲事实的正义工具,亦可作为政权机构开展专制镇压、挑起非正义争端的有力武器。正义是民主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和基础性准则。档案所承载的正义向度的社会记忆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对体现非正义的记忆内容,可将其转化为支持社会正义的“反面教材”。
档案不仅是精英历史叙事的官方来源,而且对恢复沉默的声音及支撑大众民间叙事意义重大。档案记载中出现的“空白”或致使某一群体“失忆”,并不符合社会正义的本质要求。档案工作者应自觉将正义内核融入档案工作各环节,正确处理档案在塑造官方记忆与人民记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大限度地留存真实记忆。面对非正义行为,馆藏机构可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档案资源优势,收集整理有关档案凭证予以还击,为社会记忆建构添上正义的一笔。如2015年10月9日,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歷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等机构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联合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23]档案主管部门在档案治理过程中也应体现社会正义的要求,保证社会公众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档案治理,主动将弱势、边缘群体的合理档案诉求纳入考虑范围。档案馆在提供档案利用服务时应做到客观公正,无差别对待各类档案利用个体,确保所有个体平等享有利用已开放档案的权利。譬如,进一步完善档案网站利用模块,为视力障碍者开设无障碍阅览室等。
4.3 依托数智技术,赋能社会记忆建构
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广泛运用,为社会记忆的数字化建构提供了便利。就技术本体而言,其是没有思想、没有立场的,但技术一旦被人使用就具有了思想,代表了立场。因此,数智技术必须在一定的档案伦理规约下才能正向助益社会记忆建构。
就兼顾建构主体的多元性而言,可通过借助数智技术搭建社会记忆集成平台,为公众唤醒过往记忆、建构当下记忆提供精细化、智能化的档案数据检索服务,并为其参与建构社会记忆开设专门版块。如“上海记忆”项目采用语义网、关联数据、知识图谱等数智技术搭建的数字人文服务平台,设立了“众包平台”模块支持用户贡献内容,兼顾了社会记忆展演与公众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需要。[24]区块链技术在保证参与主体平等性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档案部门可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等技术特性,搭建档案资源协同治理平台,创新档案资源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社会记忆的内容;或通过与运营商、第三方等部门进行合作,运用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建立社交媒体档案信息智能交互系统,收集各类社交媒体信息,并利用以ChatGPT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对有效数据进行提取和归档,以实现社会记忆的全面留存。社会个体亦可在伦理限度内合理利用数智技术参与社会记忆建构,如“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项目,通过采用现代数字技术以“全要素数字化+‘全息’”呈现高迁古村的真实面貌,使得逝去的乡土记忆再换新颜。[25]
4.4 促进法理相融,提供双层记忆保障
古今中外,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道德与法制往往相伴相生,共同作用于治理实践主体。数智时代,档案伦理视域下的社会记忆建构实践也应坚持道德规范与法律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通过法律法规“硬”规定和道德规范“软”约束双管齐下,营造良好的档案伦理环境,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法律、伦理双重保障。
在“软”约束方面,对于参与档案治理的个体,应引导其以合乎道义的伦理准则调控自身行为,自觉将伦理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硬”规定方面,则须通过填补法律法规空白、细化已有法律条例等方式,实现对档案伦理主体行为的制约。如档案修复工作需要法律层面的规范,但当前已有法律法规与各地档案工作条例中对于“档案修复”几乎全无提及,无法用标准严格的流程与规范来考察衡量档案工作者开展的档案修复工作。[26]鉴于此,未来应在当前已有档案修复行业推荐性、指导性标准的基础上,就档案修复工作的质量评价、责任追究等问题建立强制性的档案法规制度。同时也应将数据立法纳入制度建设框架,数据档案作为社会记忆在数智时代的新形态,其未经授权访问、被破坏、篡改和非法使用等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对数据条款进行细化,明确违背数据利用规则主体的惩罚形式。关于社会主体参与档案治理,《档案法》(2020年修订版)笼统指出“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但对于社会主体如何参与,以及在参与档案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理等未能作出明确规定。为此,应尽快出台具体条例或办法在法律层面对治理主体行为予以规制,为社会记忆的合法、合规建构提供法律保障。
5 结 语
社会记忆的建构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无数个体记忆特性与共性的选择性剥离。数智时代,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强化,个体记忆与档案记录的真实性对于社会记忆建构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更需要科学的档案伦理加以引导和规约。档案主管部门、档案馆、档案工作者等档案伦理主体在建构社会记忆过程中应当关注更为多元的叙事主体,将正义理念融入社会共同记忆的塑造中,合理使用数智技术,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为社会记忆建构营造良好的档案伦理环境,推动社会记忆全面、真实而有序地生成、重构和再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档案法》背景下综合档案馆文化功能及其实现研究”(项目编号:21BTQ08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2]聂云霞,陈烟然.解构与重构:论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J].档案与建设,2021(4):22-25,46.
[3]杨光.道德结构理论视角下档案职业伦理的缺失与建构[J].档案学通讯,2017(3):84-88.
[4]曹玉.档案管理责任伦理认知及其实现机制[J].档案学研究,2020(1):46-51.
[5]张善城.伦理学基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3.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87.
[7]泡尔生.伦理学原理[M].蔡元培,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3.
[8]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9]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10]孙德忠.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J].哲学动态,2003(3):17-21.
[11]李伯聪.选择与建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4,21.
[12]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
[13]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2.
[14]SCHWARTZ J M,COOK T.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Archival science,2002,2(1-2):1-19.
[15]王晓晓,施秋璐.档案对建构社会记忆的作用与影响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9(2):36-42.
[16]JIMERSON R.Archives for all: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The American Archivist,2007,70(2):252-281.
[17]张斌,徐拥军.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J].中国档案,2008(9):8-10.
[18]张建梅.基于信息伦理视域的档案从业者职业素质培养[J].档案学研究,2011(1):79-81.
[19]张东华,尹泷杰,卢俊.数据伦理视角下档案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2):97-101.
[20]齐文台,荆涛,李嵋,等.破损照片档案数字修复的应用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9(5):120-126.
[21]聂勇浩,熊健怡.建构“全民记忆”——“城市记忆工程”中的社会参与[J].档案学研究,2016(1):91-95.
[22]上海奉贤区开展2022年度家庭建档活动[EB/ OL]. [2023-04-05].http://www.zgdazxw.com.cn/ news/2022-09/06/content_336566.htm.
[23]11組档案见证南京大屠杀:从中国记忆上升为人类记忆[EB/OL].[2025-05-29].https://baijiahao.baidu. com/s id=1752109072200967342&wfr=spider&for=pc.
[24]夏翠娟.构建数智时代社会记忆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理论与实践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5):86-102.
[25]冯惠玲,梁继红,马林青.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研究——以高迁古村为例[J].中国档案,2019(5):74-75.
[26]张志惠.我国档案修复伦理规范构建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7(5):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