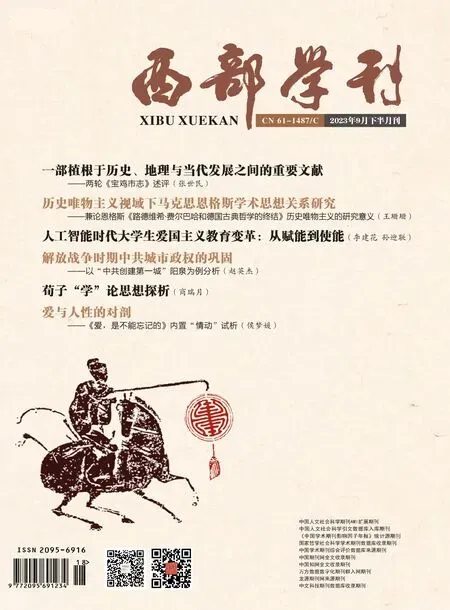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研究
——兼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意义
2023-11-06王珊珊
王珊珊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石家庄 050000)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起初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科学的“历史观”称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恩格斯正式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学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向很多,争论也特别多,尤其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整理与阐释,奠定了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正统解释模式的形成。为了打破苏联的正统唯物史观解释模式,很多学者从文本考证、义理阐释,以及结合现实等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解构与重构。很多学者之所以反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一方面认为这种模式扼杀了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模式大都来自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这也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形成了对立论、一致论、差异论。
一、西方马克思学的“马恩对立论”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便承担起了阐释马克思哲学的任务,并对马克思的思想有所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很多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自我发明”,因此在欧洲各民主党的内部就开始出现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不一致”的声音,甚至发展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是“对立”的说法。恩格斯在世的时候还能对这些“分裂”声音进行有力的驳斥和回击。但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这些声音难以得到遏制,很快就发展成了“马恩对立”的理论思潮。
“马恩对立论”在其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形成了三次浪潮。
伯恩斯坦和康拉德·施密特于1897年掀起了“马恩对立论”的第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1914年。伯恩斯坦质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一种神学,甚至直言恩格斯是一个非上帝信仰的“教徒”。伯恩斯坦对恩格斯非常犀利的责难,在当时受到了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人坚决有力的反驳,直到1916年第二国际破产之前,恩格斯的思想仍是处于无法撼动的地位。“马恩对立论”的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卢卡奇在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责恩格斯“对……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中心地位了。”[1]卢卡奇等人掀起的“马恩对立”第二次浪潮在整个学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西方马克思学”为首的学者掀起了马恩对立的第三次浪潮,他们标榜着要还原一个“科学客观”的马克思,实际干着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勾当”,进而发表了一系列“马恩对立”的著作。“马恩对立论”的三次浪潮,对恩格斯的非难与攻击,其目的不仅在于分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分裂出“两个马克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进行猛烈的斥责,无非就是想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和人道主义化。
二、国内学界反对“马恩对立”的“一致论”和“差异论”
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发展至今,也历经了三个历史阶段。
(一)介绍翻译西方马克思的“对立论”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工作,学界翻译了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与介绍,虽然开拓了当时国内学者的视野,但对其理论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分析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界思想涌动的时代,当时大部分学习面临的是如何定性的问题,所以在根本的研究立场上坚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观点,所以根本没有能力对“马恩对立”论的观点去进行深一层的批判和反驳。
(二)独立著书反驳“对立论”的“一致论”阶段
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著作,如1990年出版的陈先达的《被肢解的马克思》、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其铨《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等。这一期间,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多,其基本立场就是反驳“马恩对立论”,从而坚持恩格斯和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陈先达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正是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一般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揭示和马克思晚年对具体意义上的多样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辩证统一体的全貌。”[2]
(三)深入反思“一致论”的“差异论”阶段
21世纪发展至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国内学者除了有一部分坚持马恩思想关系的绝对一致论外,有一部分学者提出了“差异论”,论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在差异基础上坚持马恩关系的一致性。
第一场争论围绕俞吾金的差异分析法展开,俞吾金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在于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本体和人的问题,而恩格斯强调的是自然、认识和思辨的问题。第二场争论主要源于何中华对马恩关系“分工说”和“情境说”的质疑,恩格斯将马克思称为两人思想合作的“第一小提琴手”,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但何中华认为这种比喻,并不能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之间的思想差别。对于何中华的这种观点,杨楹、周世兴则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理解为根本性的差异无疑是一种谬见,“有必要予以澄清,”[3]所以第二次争论在当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对《费尔巴哈论》研究历程的影响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的源起文本,自发表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研究阶段。(1)西方马克思学者坚持“马恩对立论”前提下对《费尔巴哈论》的“贬低论”研究;(2)苏联、国内早期学者维护“马恩一致论”前提下对《费尔巴哈论》的“肯定论”研究;(3)国内当代学者在提出“马恩差异论”中对《费尔巴哈论》的“反思性”研究。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费尔巴哈论》的研究中对恩格斯的理论基本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这与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贬低恩格斯的“马恩对立”思潮分不开。然而到了20世纪末以后,由于“马恩对立”这一思潮开始有所缓解,那些坚持“马恩对立”的学者态度趋于“相对温和”,在对《费尔巴哈论》的研究中也改变了之前的极端态度。比如,戴维·麦克莱伦在《恩格斯传》中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思想之间存在差异,但也强调了恩格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中独有的历史贡献[4]。西方学者研究《费尔巴哈论》主要目的是从中寻找“马恩对立”的文本依据。
后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著作传到中国,国内学者经过“西马”思潮影响后,开始对早期坚持的马恩绝对一致论进行反思。当前学者虽然也是在反驳“对立论”的过程中论述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一致性,但与早期学者不同的是,不再坚信苏联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范式就是“绝对真理”,在这质疑与解构的过程中形成了“超越论”“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新的理解范式,尤其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范式可以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独有的“发明”。中国当代学者无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一块整钢”的立场还是坚持马恩关系差异论的立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解范式作出了积极并且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从上述《费尔巴哈论》的文本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在对苏联“一致论”研究范式的反思中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立论”的批判中构建起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这无疑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费尔巴哈论》对马恩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他和马克思思想关系进行了特别的说明:“我不能否认,……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所以这个理论用他(马克思)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5]因此,《费尔巴哈论》自诞生起就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这一问题所纠缠。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笔者简单思考如下。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研究的文本回归
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是最能代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主要侧重的是关于人的问题,探讨人的本质、人的异化以及人的发展等问题,所以依据马克思早期著作,很多人将马克思解读为人本主义者,并产生了“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两种分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中晚期,主要侧重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必然性。
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过去我们为了捍卫这一正统解释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块整钢”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是绝对一致的。但事实证明,这种简单定性划分立场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尤其是国内学界在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洗礼,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不再是原来的简单化一,而是深入文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重新阐释。当今我们只有展开艰苦细致的文本研究,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统一之处,建立起一个新的、综合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能够回答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统一之处: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结合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而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恩格斯,无论是早期恩格斯与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唯物史观文本,还是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整理,都说明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统一之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要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关系问题,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文本研究,尤其是对两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研究。安启念认为,当下最有可能解决“马恩对立”这一困扰整个马克思主义学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是中国学者,“开展深入细致的文本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6]《费尔巴哈论》不仅是马恩思想关系争论的缘起文本,同样也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经典文本,所以研究《费尔巴哈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费尔巴哈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较少,当然这也与“马恩对立”这一问题的争论分不开。
五、结束语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虽是一篇回应性质的文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篇幅不长的著作有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必须立足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进一步打通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一系列文本。通过这样的研究,核心阐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脉相承性,这一研究工作无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