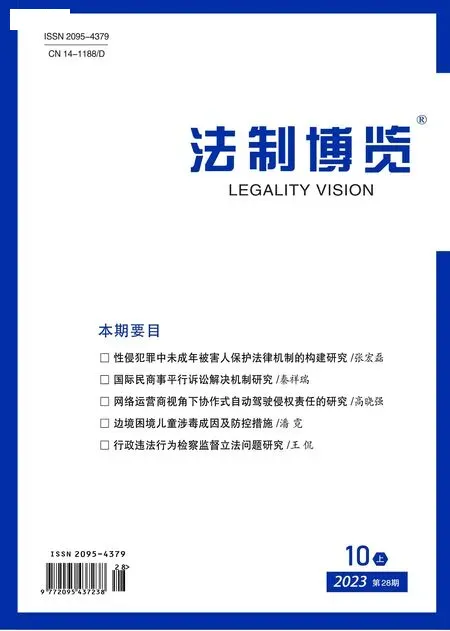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类推为“出售”出入境证件行为罪刑法定的挑战
2023-10-31刘海明
刘海明
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一、骗取入境证件刑法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包含六个罪名,其中在第三百一十九条规定了骗取出境证件罪,而并没有将骗取“入”境证件行为规定为犯罪。骗取“入”境证件行为受到规制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出入境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弄虚作假骗取签证、停留居留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的,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境和入境的人员数量剧增,随之带来的就是对出入境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外国人非法居留、非法入境、非法就业的情况突显,需要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对于立法者未将骗取“入”境证件规定为犯罪系因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对外开放刚刚起步、经济相对落后,大量的国人有出境劳务输出、经贸往来的需求,骗取“出”境证件的行为大量存在,需要依据《刑法》予以规制和打击,反观外国人入境数量较少,骗取“入”境证件的现象更是极少,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普遍发生在国外(入境人员本国),不必要以犯罪方式予以打击。
随着国家社会形势的变化,将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已成必要,2019 年科技部部长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公布:2018 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33.6 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笔者切身感觉到了身边东欧的白色人种和非洲的黑色人种越来越多,而这些居留于我国境内的外国人,并不都具有合法居留身份,骗取居留许可的行为大量存在,而随着国际往来的越发开放,骗取“入’境证件需求亦将急剧上升,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要么进行行政处罚,但力度较轻放纵了这种行为;要么为了打击需要,易类推适用其他相近的《刑法》条文,最常见的就是类推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二、有偿的出具虚假材料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不能被评价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笔者发现部分地区公布的裁判文书中将骗取“入”境证件行为类推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罪,故对于两者之间需要进行比较以厘清各自保护的法益。笔者按照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顺序对“出售”“骗取”进行解释,具体内容如下:
(一)文义解释
对于“出售”一词大致描述为“将商品以货币的交换形式卖出去。”进一步讲,“出售”应当系所有权(权益)与货币的交换。这种交换应当不包括出售本属于买受人所有的物品,否则会出现逻辑上的错误。如出售房屋给其所有权人、出售车辆给其所有权人、出售证件给其所有权人。为了区分行为界限,2017 年公安部印发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行为名称及其认定》(以下简称《行为名称认定》),其中第二十三条用列举的方式将出售、出租、出借作为非法提供证件的行为方式,按照通常理解其中并不包括有权机构核发的真实出入境证件。
“骗取”一词笔者认为与其他骗取类犯罪(如骗取贷款罪)具有一致性,即虚构事实(提供虚假材料),相对人(出入境管理部门)基于认识错误而交付。对于骗取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行为名称认定》第六条也明确了骗取行为的特征为:编造事由、身份信息、相关证明材料取得护照之外的出入境证件。
以《行为名称认定》为依据,将出售和骗取两种行为可以进行准确的区分。
(二)体系解释
1.厘清提供伪造、变造和出售之间关系。《刑法》第三百二十条“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或者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伪造、变造、出售在同一条文中予以规定,笔者认为三者所侵害的法益具有同一性。三种行为共同特点包括:一是三种行为均侵犯了出入境管理部门制作核发出入境证件的专属权力;二是三种行为可能导致出入境人员持有“假”的证件,成功出入境,这里的假并非指证件是假的,而是特指证件与出入境人员实际身份不符;三是选择性罪名均具有关联性,可以是提供伪造、变造成品证件,也可以出售给他人证件由购买人进行伪造、变造。提供伪造、变造证件可以系无偿的,而出售证件系有偿的。
2.厘清是否只要收取费用就是“出售”。2000年3 月,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立案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骗取出境证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为重大案件:(一)违法所得10 万~20 万元的”;2012 年12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三百二十条情节严重的标准之一为:“非法收取费用30 万元以上的”。两部文件均提到骗取出境证件也存在收取费用情形。通过体系比较,收取费用并非出售出入境证件所独有,故不能以是否收取费用来界定出售行为。
3.厘清骗取出境证件行为与出售出入境证件行为侵害法益异同。《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将骗取“出”境证件作为犯罪处理。骗取行为系虚构出入境事由、提供虚假材料,使出入境管理部门陷入认识错误,交付“真”出境证件,骗取的出境证件对于实际出境人员系“真”的,只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侵犯了管理秩序,使出入境管理部门陷入错误的认识,造成“不应当发而发”的结果。出售出入境证件系持有了或真或假的证件将其出售给了需要出入境的人员,这种真或假的证件之于需要出入境人员系“假”的,所侵犯的是出入境管理部门专有的审批许可权,造成“应当审而未审”的结果。
因骗取出境证件经过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查的一道关卡,对出入境证件的管理能够起到一定防御作用,而出售出入境证件绕过了出入境管理部门审查,对出入境证件管理没有任何防御作用,骗取的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低于出售行为,所以能够印证出售出入境证件的刑罚重于骗取出境证件,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4.厘清骗取出入境证件与出售出入境证件的处罚。笔者通过对比,《出入境管理法》第七十三条,骗取出入境证件、出售出入境证件进行行政处罚,而《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骗取“出”境证件为刑事犯罪,骗取“入”境证件无规定。《刑法》第三百二十条出售出入境证件为刑事处罚。通过对比,现行法律体系尤其是《出入境管理法》已经明确区分了骗取出入境证件和出售出入境证件行为,《刑法》亦应根据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进行分类,骗取入境证件是单独的行为不能类推为出售出入境证件行为。
(三)立法目的解释
骗取出境证件罪、倒卖出入境证件罪系1994年被规定为犯罪,依据199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草案说明》)第二条解释了当时因劳务输出、旅游、对外经贸往来的需要,弄虚作假骗取“出”境证件非法“出”境的情况严重,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类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有惩处的必要。不难发现《草案说明》都是针对“出”境证件相关犯罪行为予以打击,这亦符合当时出境需求多于入境需求的国情。
《草案说明》第三条解释了出现了专门伪造、变造、倒卖“出”境证件犯罪活动,如按照现有《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伪造证件罪的规定处刑过轻,故将伪造、变造、倒卖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现行《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系由199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中的“伪造、变造、倒卖”变化而来。系伪造证件罪的特别法,所打击的系出入境领域的提供“假”证行为。
笔者查阅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该说明全面阐述了1997 年《刑法》修订的过程,但其中并未对1994 年“倒卖出入境证件”变为“出售出入境证件”予以说明,笔者认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仅系将“倒卖”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词语更新为法律用语“出售”。
(四)假设
假设《刑法》将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其跟骗取出境行为应当具有同一的法益侵害性,应当规定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条中。那么有偿提供虚假材料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毫无疑问将按照本条予以处罚,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因现在立法缺陷,如果以《刑法》第三百二十条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定罪处罚,即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立法缺陷导致法律适用变化,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为了打击而适用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刑罚尺度远比骗取入境证件罪(假定存在)的刑罚尺度要大。这将是一种悖论,为了打击的需要,未规定犯罪导致的结果比规定为犯罪导致的结果还要严重。
综上,现行《刑法》第三百二十条“出售出入境证件”的立法目的就是打击“倒卖出入境证件”,应当对该条文中“出售”一词含义进行限缩解释,即收购他人出入境证件再出售给他人的行为,证件之于使用人系“假”证。不能将有偿帮助他人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类推适用出售出入境证件罪予以处罚。
(五)司法解释及案例
1.刑事审判参考案例
“张某利出售出入境证件案”——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1]法院认为:“张某利所出售的是商务邀请函,不属于出入境证件。商务邀请函是办理商务入境签证需要的文件之一,但不是唯一文件。商务邀请函也不属于入境时海关必须查验的材料。”该案例的论证一言以蔽之地指出了,其出售的“标的”系办理入境证件如本案中签证的前置材料,不能将出售虚假材料行为变相认为出售出入境证件本身。
2.相关司法解释存在欠缺
2022 年6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第二条第六项明确,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出”境证件犯罪,偷越提供虚假证明等帮助行为的,可认定为骗取出境证件罪共犯。该条司法解释系特别提示条款,其仅能解决骗取出境证件共犯问题,而骗取入境行为仍然无法在法律层面予以评价。笔者认为这样规定符合罪刑法定,亦符合司法解释的定位——司法解释不能代替和超越法律。
三、罪刑法定禁止类推原则面临的挑战
(一)一线检察官法官呼吁立法
早在2018 年,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检察院卢山检察官就在其《建议增设骗取入境证件罪》[2]一文中提出:“不宜把提供虚假材料为他人办理入境证件的行为定性为出售出入境证件,笔者认为应设立骗取入境证件罪”。以上可以看出司法第一线的检察官同样认为骗取入境证件的行为应当在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二)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灵魂
1997 年《刑法》按照现代法治司法理念,在《刑法》第三条将“罪刑法定”原则予以明确,坚决禁止类推。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的概念遥相呼应,即犯罪必须同时满足危害社会、触犯刑法的两个条件;而在《刑法》分则中明确了哪些行为触犯刑法,从而正确适用法律,以达到打击犯罪和尊重保障人权并重的目的。
(三)罪刑法定原则需要司法化予以实现
司法机关为了打击犯罪的需要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大量外国人涌入中国、滞留在中国,应运而生的“中介”或其他单位从事有偿提供虚假材料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客观上确实扰乱了出入境的管理秩序,但由于立法空白,不能因为打击犯罪需要而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这会极大伤害到国家整体的法治建设进程,破坏《刑法》的正确实施,不利于人权保障。
(四)罪刑法定、禁止类推原则所面临的挑战
“有偿帮助外国人骗取入境证件”的案件已经有部分进入了司法程序,有的予以刑事立案、逮捕,有的法院已经评价为犯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这种类推适用法律的现象有抬头的迹象。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帮助立法者、司法者及全体法律人,准确厘清骗取入境证件与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区别,正确适用法律,同时呼吁立法机关增设“骗取入境证件罪”,彻底解决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秩序犯罪现实需要与尊重和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