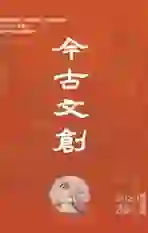琦君散文的诗性探析
2023-10-27郑近近
【摘要】琦君是一个极具悲悯情怀的作家。她的散文风格正如她所热爱的古典文学崇尚的诗风那般讲究温柔敦厚,而古典文学的功底和深受宗教文化的滋养使得她的作品致力于挖掘庸常生活中美的凝驻,她热衷于用作品传递温情和诗意,尽管有时候诗意的弥漫是以牺牲思想内涵的深刻换来的,本文将从唯美化意象、诗词化语言、儿童式视角三个角度来探析琦君在散文诗性美学上的执着建构。
【关键词】诗性;意象;语言;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6-004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6.013
琦君“爱的哲学”深刻影响她的文学观,她崇尚以自然之笔写真实之情,讲究落笔要疏淡,抒情要浓厚。琦君“爱的哲学”不仅与家庭环境和教育有关,也与她从小在浙江温州长大有关,温州从古至今都是宗教气息特别浓郁的地区之一,不管是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根植,还是近代传教士在温州建立了许许多多教堂,不同宗教文化在这里汇聚,琦君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她的一些亲近的老师都是佛教徒,而与她关系特别好的一些邻居又是基督徒,从小在宗教文化浓郁且多元的环境中成长势必影响她看待世界的眼光。而文学历来和宗教难分难解,无论是佛道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逍遥”美学增注诗意,还是西方文学从基督教提供的超验想象中挖掘灵感,很多宗教经典本身就自带诗意,这些都反映出宗教文化自身建构的诗性带给文学灵感的滋养。诗性,不仅是创作主体以审美的形式在文本中的抒情表达,也是个体对于人类灵性中趋同于神性的认同和体现,琦君作为一名忠诚的佛教徒,始终以爱和怜悯的眼光来打量被她描绘的世界,使她的文学世界充满诗性。
一、散文意象的唯美化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说道:“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之矿藏。”[1]意象不仅是解读诗歌的密码,应用到散文这一更灵活多变的文学样式中,从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的挖掘,到创作本身对意象的构造、剪裁和处理这一过程,不仅是创作主体自身审美观念和兴趣爱好的体现,也是其心灵情感的独特艺术表达。
琦君的散文以诗意著称,首先便在于其散文中充斥着众多唯美化的意象,且意象的摘取与中国古典文学一脉相承。王弼曾站在哲学思辨的高度将言象意三者的派生关系固定下来,刘勰将意象拓伸到美学的范畴,意象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审美晋身,正如袁行霈在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指出,物象在变成意象的过程,需要经过审美遴选和情感晕染两道程序的加工。[2]
琦君散文中的许多自然意象和器物意象,无不带有作者本人的委婉心曲,并且极具审美意蕴的意象更是在文本中构筑了诗意的世界。《下雨天,真好》中,作者以“雨”为线索回忆起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文本中不时出现的是雨水滴下来的动态描写,听到雨水滴到瓦背上,“我”感受到的是安心,因为可以窝在母亲暖和的臂弯里,听到雨水滴在法国梧桐树叶上,“我”感受到的则是怀念母亲的惆怅,听到雨水滴在琉璃瓦上,“我”涌现出的則是对过去生活回忆的满足。同样的意象在不同场景中随着作者情绪流转而意蕴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作者总是试图对出现的任一微小意象进行诗意叠加,或是直接从古典诗词中化境入文,如当“我”坐在父亲的书桌上听雨时,此刻是檀香冉冉,“院子里风竹萧疏”,极具诗境。
琦君散文的诗性不仅得益于所择取意象本身的唯美,更重要的是她在处理人物意象时,总是力图在自己的散文世界中构筑人性的童话。她着意于人类灵魂世界中趋同于神性一面的审美展现,对人性之恶常常点到为止,甚至不愿触及,努力展现人类真正的美与善,不同于其小说创作。白先勇曾在其评论文章中以《橘子红了》为例,来阐述弥漫在琦君小说背后人性之恶的暧昧表达。但在琦君的散文中很难发现类似深刻的刻画,有学者认为琦君的散文具有小说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以小说人物来要求琦君散文中的人物意象,则散文中的人物则要扁平化得多,以创作主体本人回忆和情感的浸染将其美化、净化、纯化,正是人物意象的这种简单化和纯净化使得情感抒发比较纯粹,散文更加诗意盎然。
琦君自己认为对于散文人物意象的刻画应该“融入小说的立体感”,但在她具体创作中,较为完美彰显了她这一理念色彩的则是“二妈”的形象刻画。在《髻》中,父亲带回来的“二妈”美丽摩登,在《我爱纸盒》中,二妈一出场则是毁坏了阿荣伯给“我”做的纸盒,并禁止“我”从废纸篓中拣出纸盒,她在这里呈现出的是冷酷、严厉、专横且践踏孩子童心的形象,但是在《“代书”岁月》中,尖酸摩登的二妈又展现了她温婉柔情且自尊的一面,起初“我”对于二妈让“我”给她代写书信觉得困惑,因为在“我”印象中她是知书识字的,后来得知每当“我”把书信写好她也不会立刻寄出,而是在夜深人静中在书房中将“我”写的信仔细重抄一遍,原来是因为她有很多字不会写,须得“我”打个草稿,“二妈”的形象在这里极为鲜活与可爱,既有对丈夫的柔情似水、深情若海,又有在晚辈面前维持自尊的执着。
但是,在琦君最爱刻画的“母亲”形象中,则并未展现出如“二妈”形象如此丰富的书写。一方面确实因为作者自身对“母爱”的情感体验是泛化的,母亲无私的爱、关怀带来的诗意和温暖并没有多少独特性,母亲的温婉良淑、贤惠持家也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书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琦君本身致力于构筑自己的纯真世界,母亲是这个纯真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每当可以对母亲真实复杂的心理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和刻画时,作者立马就用母亲的温柔、慈爱、怜悯来进行消解了,这既是文学创作自觉的艺术美化,同时也是情感回忆不自觉的筛选,正是琦君自觉或不自觉的简单化处理构筑了散文的诗性。
二、散文语言的诗词化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真正的散文是充满着诗意的,就像苹果包含着果汁一样。”[3]散文整体诗意的氤氲离不开文字之间的排列组合,正如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之盛发展到词之兴,固有韵律局限更深一层的思想和情感表达,词格式的错落有致、长短不一为更精微的情绪抒发争取了空间。
琦君精通诗词创作,在她的散文中也处处体现了句子之间长短错落有致和收放自如。在《西湖忆旧》中,描写母校之江大学风光中:“在山上,凝眸远望,江上雾氛未散,水天云树,一片迷蒙。”“少顷,雾氛散开,江面闪着万道金光”[4],两句话中,二字、三字、四字等短句与长句互相穿插,排列起来玲珑有致,明显有着辞赋的痕迹,甚至短短几句的环境刻画可以说脱胎于苏轼的《赤壁赋》。
在《桂花雨》中,作者回忆儿时和母亲一起摇桂花时写道:“我们边走边摇,桂花飘落如雨,地上不见泥土,铺满桂花,踩在花上软绵绵的,心中有点儿不忍。”[5]在这句话当中,共有六个分句,五六分句中,作者精炼语言省去人称代词,从桂花本身的飘落动态透过“踩”这一触觉上升到内心的动态流转,其中一二分句又有对称之美,正如王鼎钧称琦君的文字是诗化和词化的精妙结合。
琦君对文字的精细揉捏,不仅体现在她对具体句式的穿插与排布上,也体现在她特别善于从古典文学中寻觅资源和灵感。在文中,处处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古诗句使其散文氤氲诗意。无论是人物对话语言,或是俗语俚语,她都尽可能将其进行诗化加工,首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琦君文风所弥漫的诗意:灯景旧情怀、母心似天空、千里怀人月在峰、青灯有味似儿时、三更有梦书当枕……每当琦君描绘父亲的时候,总会穿插许多诗词来烘托父亲的志趣和性格,就连描写母亲的吟诵时,也会刻意进行诗化,在《桂花卤·桂花茶》中,当母亲品尝桂花茶時也总是不自觉吟唱“桂花茶,补我心,我心清时万事兴。万事兴,虔心拜佛一卷经”[6]。父亲接受的是系统良好的教育,并且于古文颇有造诣,他的生活充满着诗情画意不足为奇,但母亲是个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旧式女子,竟然也能随口吟唱一些较为押韵的打油诗,这不仅体现作者在进行散文创作时着力进行独特的美学建构,也反映出作者在诗性表达中着意于使日常生活审美化。通过语言的雅化对日常琐碎进行处理,给予庸常的生活无限诗情。
琦君非常善于将古典诗词语言与口语白话进行揉化衔接,使得散文语言既温婉典雅又通俗自然。在《灯下琐谈》“雨之恋”中,由张潮的《幽梦影》提及的清明之雨联系到人生的风雨,极为自然妥帖地化用辛弃疾之词“可惜流年,忧愁风雨”,将典雅的诗词语言揉进了白话中,传达出面对人生风雨也应从容和享受的豁达情怀。而情感的诗化和所用的古典诗词化语言分不开,琦君特别善于在其散文中即兴抒情,但她的抒情不矫揉造作,正是语言的诗词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情感的泛滥,正如《西风消息》中,由西风萧条联想到欧阳修、杜甫、姜夔,由深秋之景想到了人生的秋冬和老年,读到外子从海外寄来的一片红叶,本来无限怅惘,但感情斗转急变,最后全部浓缩释放于苏东坡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中。白话语言抒情的自然化与古典语言抒情的典雅化,在她的散文中达到力与美的平衡,不仅使散文中诸多庸常琐碎的描写折射出诗意浪漫的光辉,而且情感的悲悯、爱怜、追忆和欢愉得到甜而不腻、哀而不伤的彰显,语言诗词化带来的凝练与在文本中营造的空白,使得散文情感的表达更加丰富。
三、散文视角的儿童化
叙事视角的儿童化也是琦君散文一个典型的特征,同时,儿童化的视角也是其散文散发诗性的因素之一。首先,叙事视角的儿童化可以使作者更好地处理那些让其感觉需要避讳的内容,作者的怀旧散文大多采用儿童式叙事视角,当作者在打开记忆库攫取素材时,她更乐意展现的是生活的欢愉与美好,但散文虚构空间的有限与对真实性的要求,又使得作者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丑恶与黑暗,而儿童化的叙事视角正好可以帮助作者避免在文中直接性地批评和判断,作者更习惯用儿童的思维模式来直接和本原地呈现生活,既保证了散文的真实性,同时又使其散文不丧失诗意和温情。
在《髻》中,作者以儿童视角来叙述对姨娘美貌的惊叹,母亲拒绝佩戴姨娘赠送的翡翠耳环,把姨娘赠送的头油也高高地放起来,作者只是以“大概母亲舍不得吧”这样的孩童口吻来加以阐释,这不仅可以避免对父亲抛弃母亲、对婚姻不忠做出评判,其实也避免对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做更深一层的刻画,这一方面是因为儿童的视阈本就不允许作者进行这种阐释,另一方面,批判也并非作者的本意,在琦君心里,悲悯要比批判重要得多。作者只是通过描写母亲把姨娘送的东西收起来这种细节,但却深刻表达了母亲的悲哀和痛苦,对于母亲来说,尽管她很善良,但这些东西的出现不得不提醒自己被丈夫遗弃的悲剧命运。
同时,正是儿童视角造成的叙事视阈的有限性使得文本留下很多空白,而这些空白不仅造成感情的慰藉,同时也提供了丰富阐释的空间,而这恰恰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被琦君应用到散文创作中,使得散文具有丰富且蕴藉的诗性。
在《碎了的水晶盘》一文中,是以儿童视角“我”来记录水晶盘破碎的故事。三叔公从国外带回一个外国妻子,不仅在“我”家那小小山乡引起哗然一片,更是遭到家里母亲和表姐的强烈反对,“我”那来自巴西的三叔婆被迫逃到“我”家来落脚,在她日复一日地无效等待中,“我”认定了三叔公是个自私懦弱的人,但文本最精彩之处在于当“我”按照三叔婆的嘱托把她的水晶盘交给三叔公却被他后娶的妻子摔得粉碎时,三叔公的反应是拾起那些碎片,不仅用原来的布包裹上,又拿出自己的手帕再包一层递给了“我”,“手帕”在中国文化中蕴意相思,但因为叙事视角的局限,“我”与三叔公并未有多少接触,“我”对他真实心理一无所知,在“我”表面认定他是一个胆小薄情的负心男子的背后,他的挣扎痛苦与无奈却透过他包裹破碎的水晶盘所用的“手帕”隐隐传递出来,从而使文本解读更加丰富。
作者在进行儿童视角叙述时,需要用儿童的眼光和心灵来审视和聆听所看到的世界,而儿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对万物本身鲜活的生命感受使得他们总是用“万物有灵”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这种灵动鲜活的视角使得他们将万般事物纯净化,从而添加诗意。在《儿时不再》中,“我”趴在地上看蚂蚁,当“我”觉得冷的时候也担忧蚂蚁觉得冷,过新年时会让“我”想到蜈蚣妈妈要给它的孩子做那么多双鞋,从而深深同情蜈蚣妈妈如此辛苦,并感叹生了一堆儿女真是辛苦,字里行间流淌着儿童特有的稚气与天真,但是读后却只会让人动容,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琦君所建构的童真世界中被消解,收获的只有美、纯净和温暖,尽管它不深刻,却情挚脉脉。
但在琦君有些作品中,作者可能太过执着于诗性与温情的建构,将本来可以写得更有思想力度的作品为了诗意而削弱深度。
在《妈妈的小脚中》,作为孩童的“我”自然是无法理解母亲裹小脚的痛苦。当母亲摇摇晃晃手提装着饲料的木桶走路时,让“我”觉得只是好玩从而模仿母亲走路的姿态,并且也学着母亲揉着脚后跟喊着疼,从儿童的视角来看,自然不能体会裹脚这一封建陋习的残酷带给母亲的伤害。生于传统观念中女子命运的痛苦透过孩子的眼眸来看,她们的苦痛只是好玩和有趣。这种前后巨大的讽刺和张力透过儿童视角来叙述,其实可以写得很深刻。但是,琦君执着于刻画母亲慈爱怜悯的形象,描写她对于自己的痛苦的反应也只是“笑眯眯”的。在其他许多篇章也是,母亲的出现永远像裹挟着希望的暖阳,只有在涉及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母亲的难过、自责、懊悔等消极情绪才将母亲从圣化的神坛拉下来。尽管对母亲的刻画足够细腻和深情,但有时候并不让人觉得真实。
四、结语
琦君始终以“爱”作为看待一切苦难的透视镜,不管多么悲伤和沉痛的题材,在琦君笔下经过柔情的过滤往往都会具有诗性。她的散文不追求歇斯底里,只讲究中和之美,沉重的悲哀经过诗意的节制而余韵悠长。它不够现实,不够有力度,甚至也并不深刻,但它是一个童话的存在,是琦君用她宗教式的温柔和慈悲,选择美化的意象,巧借诗词化的语言,用灵澈的孩童目光构筑的一个温情的世界。不仅是琦君用以涤荡现实污浊的桃花源,它的诗性也使读者返回到亚当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之前的伊甸园,带给人返璞归真的畅想。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
[3]佘树森.散文创作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琦君.琦君散文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12.
[5]琦君.桂花雨[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
[6]琦君.琦君散文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郑近近,女,安徽淮南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