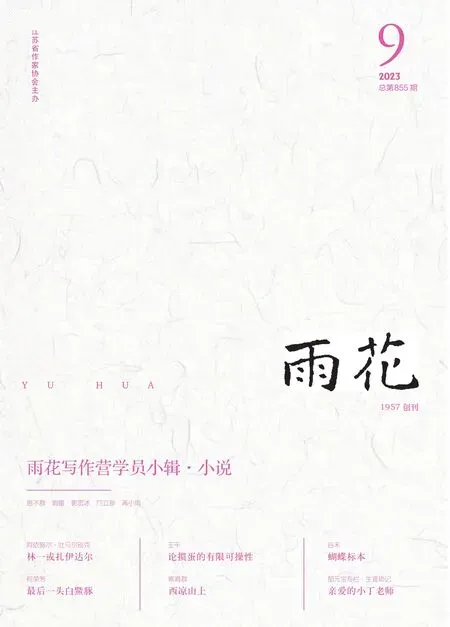某在斯
2023-10-22思不群
思不群
第一封信
傅廉:
今天下午,一只鸟儿会飞进你的房间,落在窗前的书桌上,抬起它栗色的小眼睛看着你,但不说话。现在它就在你的面前,就在你手中,微微发热。它是从我的房间里飞去的,经过整整一夜,我在房间里孵出了这只鸟,并让它迅速长大。它学会了自己开窗,但还不能说话,所以我只能自己来说,写出这封信,送到你的面前。
你一定会惊讶。但每一个收信人都不是偶然被选中的。昨天傍晚,我从家里的花店偷偷跑出去,跑到五月广场和阿娟会合。我和她每隔几天就要碰个面,吹着风,两个人嘻嘻哈哈地说一通。你知道女孩子的身体瘦小,装不下多少东西,总是需要定期往外丢掉一些,否则就太沉了。当我们聊天时,那些语言在空中来回往复,就像两个相互扔棒子的杂技演员,你扔我接,我扔你接,准确而热烈。这项表演在外人看来平淡无奇,其中的乐趣只有我俩知道。昨天也是如此。我俩旁若无人地聊着,忽然之间,广场上的人群一阵惊呼,我俩不由扭头看去,只见广场边缘处由一幢幢建筑物堆出的群山万壑之上,是鱼阵般排布的晚霞,彤云与金辉相互交织、相互间隔。而下边的城市和广场上满是夜色,仿佛晚霞云阵投下的影子。就在那时,从逐渐黯淡的余晖中,闪出一道白亮的光带,从半空中垂下来,一直落到地上。光带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瘦削的小伙子,他的白衬衫有点胆怯似的贴着身子,一双眼睛黑亮又迷茫。他在广场上走动的轨迹牵引着我的目光,好像他身上的光亮仍未消失,但只射向我一个人。
阿娟看了我一眼,抿着嘴笑了,然后推推我,示意我走过去。我打掉她的手,坐着没有动,只是用眼睛系住那个小伙子,不让他跑掉。他走到哪,我的目光就转移到哪。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那些影子都化入了暗夜之中,而那件白衬衫仍然亮着,在广场上像一盏移动的落地灯,漫无目的地从喷泉边到杂货店,从中心雕塑到旋转回廊,它迟迟无法离开,被一根线牵住。有一刻,他径直朝我走过来,但走到半路,似乎是受到某种暗示又停住了,向这边张望着,然后突然转身,张开双手,他的翅膀越来越大,在一阵风起的时候,遽然飞走了。
他飞到哪里去了呢?他是否知道在他走了之后,那个手中握着线的人还坚持又坐了很久,而风筝或者蝴蝶却已经不见了。甚至连阿娟也走了。当有人走来搭讪:“姑娘,你等的人就在你面前。”我回他:“我等的是一只白蝴蝶。”那个人摇摇头走了。在夜幕降临的广场上等一只蝴蝶,是可疑的,甚至像是某种病症。但那个有药的人是否会来?
你是否会来?昨天晚上,我一直有种幻觉,傍晚并未过去,那道晚霞从未退去,一直挂在天边,就在我的窗前,那么亮,那么炫丽,其中有白蝴蝶的蹁跹,我走到哪,那道霞光就投到哪。于是我有了平生第一个白夜。它一直照着,一直照到我的心里,像白夜一样亮堂。二十年来,我还从未像这样看清过自己,所以我写下了这封信,孵出了这只鸟儿,希望它能穿过我的白夜,飞向你的黑夜,让你更清晰地读出它。
你是不是叫傅廉?也许我搞错了。这个名字几乎是跟随着那道白练一起到来的,也许这是我给你取的名字,我权且这样叫你吧。
阿巧
3 月5 日
第二封信
傅廉:
写完第一封信,我有点后悔,我是不是太唐突了,就这样给从未认识的人写信,我们比大街上偶然被风吹到一起的两片树叶还要陌生。你是否曾认为这是某个无聊的女孩恶意的捉弄?但两片偶然相遇的树叶也许会有相类的纹理、相近的色泽,甚至是相同的卷曲弧度,当又一阵风来,它们会一起朝着某个角度跑去。
我写这封信来,是想告诉你,我是在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下开始给你写信的。那股冲动不可遏止,就像火山喷发,它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它要喷涌。在第一封信里我还遗漏了一点——其实,可能还有更多,因为一个人突然之间被赠予诸多宝物之时,她总是不自觉地抱紧,不想把它泄露出去,每次只透露一点点——那就是,那天傍晚,当那片垂天之云彩落到地上,我感觉它就像一道闪电,而我就是那个被闪电击中之人。这道闪电从此储存在我的身体里,像一道白色的影子,舞动、飞翔,我度过的第一个无眠之夜不过是被闪电击中的后遗症罢了。被电之后,身体器官甚至全部细胞都像死了一样,停止了运转,只有那道闪电在五脏六腑间游动、穿行,带起闪耀的电火花,闪落在身体里,像一些似断似续的微梦,清早起来,我用手捧着,捡拾了不少。
这几天我和往常一样在花店里帮忙,拆开包装、剪枝、插花、包扎,为顾客提出建议,外出给那些陌生的名字送花,顺带接受他们收到花时的惊喜。这是我喜欢的工作。花是美的,买花的人也是美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脸上都有绿影荡漾,像一座移动的山林。他们在各类花中间走动,站立,欣赏,就像他们年幼时,在树丛中穿行、奔跑、嬉戏,一朵花就是一个人开了又败、败了再开的童年,它凝固成了美。
昨天傍晚,我带着几枝百合花走出花店,来到五月广场,在那里待了半个多小时。我没有约阿娟,一个人在长椅上静静坐着。人们来来往往,但我的眼睛却有一种特殊功能,将他们一一清除,所以在我看来,那里空空一片,就像在电脑的画布上执行了一键删除操作,而那本应出现的画中人却始终没有现身。回到家,我把百合插在花瓶里,摆在桌上。一枝已经开了,长长的花瓣向四方披拂,如舞女将头后仰着以手触地;两枝未开,花苞紧紧裹着,像包裹着一个美丽的秘密。我觉得我就像这些百合花,两种都像。
你在干什么呢?你是一个公司职员、小学教师,或是一个店主、自由职业者,甚至艺术家?更或者集所有这些职业于一身?我经常想,当一道闪电落入生活中,当他乘坐公共汽车,吃着早餐,眼望着街头;当他加班写一份企划书,几个小时顾不上喝水,只能舔一舔嘴唇;当他独自漫步在夜晚的街头,突然闻到一阵花香,这道闪电会如何变形,如何展现自己的色彩和内部结构。
很期待。
阿巧
3 月10 日
第三封信
傅廉:
写完第二封信,我发现它同样愚蠢可笑。我总是这样,做错一件事,想立即弥补但接着又错。如果一直错下去,我总会绕回来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收到前面两封信后有何感想。你读了吗?读完后是把它们扔在一边一笑置之,还是骂一声无聊,然后将它们撕成碎片?我猜想很有可能是后者。没关系,那些碎片会像鸟儿一样飞上天,鸣叫着相互寻找,相互召唤,然后又会重新拼接在一起,重新变得完整,这就是我写给你的第三封信。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窗外清洁工正手握扫帚在清扫小区路面。他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双手一上一下交叉握紧大大的笤帚,使它贴紧地面,然后双手一起用力,在身体左侧,从落叶和灰尘中抡出一个半圆。但风总与他做对,马上又将一大半落叶吹了回去,将半圆变成了扇形。这些天来,我也是这样在内心清理自己,这份工作同样艰难,前进几步,又后退更多步。你有没有发现我的信写得颠三倒四?但我还嫌它不够乱呢。要是用一枝笔实时记录我的每一刻的心理变化,那才叫有味。但那也可能会吓着你。
阿娟昨天到我家来了,并在我的房间里待了一个晚上。我们关紧房门,聊一会儿就哧哧笑,头跟头都碰到了一起,像两只小松鼠,哧哧声就像剥栗子。妈妈听到我们的笑声,不时会笑着骂一句:“两个傻丫头!”有时会给我们送点水果或者点心进来,等她一出去,我们又把门关紧。
阿娟问我你有没有回信。阿娟真是不懂,你怎么会回信呢?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对吧?而且也不应该期待你回信。写信这件事就是这样,你写下了一段文字,送出一部分自己,像是割下一块血肉,把它寄出去,就结束了。当你连续写,割下的血肉越来越多,最后你就把整个的自己都交了出去。那时,你已经做完了这件事,成功地把自己转移了出去,现在你只要想象着对方读了没有,读了之后会作何感想,那就是馈赠,那就是回音。你想着他把那一块血肉拿在手上,手足无措,你就放心了。写信就是这样,就是偷偷转移自己的一种办法。
所以,你看,这封信变成了一个预告。
阿巧
3 月17 日
第四封信
傅廉:
你好。
我要和妈妈一起出门了,但我忽然想要给你写封信,这封信非写不可,否则把它一直背在身上,就太累了。我马上就要出门了,所以只能简单写几句。
有一种说法,如果你在傍晚散步时,跟着晚霞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就会穿过黑夜,到达白天,就像是穿过一个时光隧道。晚霞在半空中照耀着,如同一件披在身上的衣裳。这些天来,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穿过了一个长长的隧道,我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通上了电。
是你开启开关了吗?
阿巧
3 月27 日
第五封信
傅廉:
你好。
今天上午,刚吃完饭,阿娟就打电话来,提醒我别忘了今天是我们外出郊游的日子。我们这些朋友有一个惯例,每过两个月就相约一起到城郊的桃湖边游玩。我们骑着自行车沿湖边巡行,唱着歌,风吹起衣襟和头发,但却带不走它们。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一行人散落四处,彼此散漫地聊着天,常常是没聊几句就没来由地大笑起来。但今天我跟阿娟说我有事,不去了。阿娟就说要到我家来找我,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你来也没用,我继续说。不过,我没想到阿娟还带了阿娈一起来了。阿娈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很可爱,力气大,她俩一到我家,啥也不说,就拉着我往外走。但是刚走了几步,走到门口,她们不得不停住了,就像她们的衣服被什么挂住了,再也无法向前。她俩扭过头来,笑着唬了我一眼,双手使上了劲,特别是阿娈,屁股往外撅着,很像某个舞蹈动作。但是无论她们怎么用力,我仍然纹丝不动,连我自己都有点奇怪,我好像被什么给吸住了。我就像门套那一块被砍伐、削平的木头重新长出的新枝,牢牢地立在原地,她俩也对此惊奇不已。
但最后这根新枝还是被阿娟摘下了,她把我移栽到了桃湖边,还让大家来看。虽然最终熬不过阿娟的威逼利诱还是去了,但我在姐妹们中间真的就像一根树枝。我骑车总是落在后面,唱出的歌只有呜呜声,躺在草地上时,我成功地脱离了她们,一个人飞到百米之上,与白云为伴,独自游荡。当她们喊我时,我的回答要从半空中慢慢降落下来,不仅要延迟半分钟,而且总是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阿娟气坏了,她爬起来,走到我跟前,用力拉起我,说道:“你不想跟我们玩,你还是回去吧!”她只是开玩笑地轻轻推了我一把,我就高高飞起,瞬间闪回了家里,就好像我今天从没离开,一直就坐在房间里。现在,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给你写信。从第一封信开始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我的姐妹们一定发现了我的异常之处,甚至可以命名为神迹。虽然我参加集会更少了,但还是能发现她们交换眼神时,有些陌生的东西一闪而过。
她们最没想到的是,我竟然能瞬间飞行了。我也没想到。
阿巧
4 月10 日
第六封信
傅廉:
你好。
今天这封信,主要是讲述一个梦。昨晚临睡前,外面下着雨,我靠在床上翻读着一本书,不料一会儿就睡着了,而且做了个梦,梦见了你。其实,在梦中我并没有看见你的脸,但是我非常确定,那就是你。背景是在荒野中,树影、山岭像粗粗的炭笔画,你在一条山路上飞快地走着,你肯定已经走了好一会儿了,不时用手抹一下额头。树影像融化了的黑雪,一会掉下来一点,掉到地上,就变成了一条蛇,它们在你的脚上缠绕着。你不管它们,只是迈步向前快走。走过一个小坡,你停下来,四处张望,有时还扒开树丛,把脸埋进去。你站住,仿佛思考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来,回头朝反方向走去。这时,你才发现,在你走过之后的几分钟里,小路已经完全被淹没,消失不见了。草丛迅速长高,杂以灌木和野花,直抵你的胸口。你茫然地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呼吸急促起来,眼窝缩紧,焦灼在眼里闪烁。你想要跑动,但两只脚被杂草牵绊着,跌跌撞撞的,你用手拨开灌木枝桠与乱草,艰难地向前走着。脚下的迷魂阵搅动热血和气息,不断上升,最后汇集到你的眼睛里。这时,你的眼睛已经像两只燃烧的灯笼,要烧穿这一片荒野,它热切、期待,想要穿过重重迷障,找到什么,但这跋涉让你只能喘着粗气,难以前行,最后倒在地上,双眼瞪着天空,嘴里喃喃低语。我就这样一直看着,但这时我忍不住了,着急地对你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但你听不到,没有任何反应。你还在找着,甚至气急败坏地将一片杂草踩踏成平毯,把其中的灌木丛全部拔起,但你仍然一无所获。不一会儿,从你的脚下又长出高高低低的乱草来,它们越长越高,淹没了你的双腿、胸脯、脑袋,与周边的荒野完全融为一体。你仰面朝天躺了下去,看见天空中一颗星星闪耀着缓缓飞过,你不禁微笑起来,你的寻找之旅结束了,我的梦也到此为止,后面就进入了真正的睡眠。
阿巧
4 月20 日
第七封信
傅廉:
你好。
让我不得不感叹的是,你拥有什么样的沉默啊,像花岗石一样,像大海一样,极端坚定而又极度广大。我能理解,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沉默就越是坚定,仿佛有一种下沉的力,在底部将它稳住,稳稳端坐,像菩萨一样。菩萨永不开口,他始终保持沉默,但他的承诺却是永恒的,最稳固的,我妈妈常常这样说。虽然他不开口,但求告人代他做出了承诺,所以这是一条自己通往自己的路,那么什么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想象的,这就是祈祷的秘密。
现在让我着迷的,是一个黑洞,一个深渊。小时候,我和小伙伴经常往一个很深的山洞里扔石子、瓦片,当它们落到山洞底部或最终击打到水面时,返回的清脆之声在山中回荡。而现在这个山洞进一步加深了,扔下去石子却听不到回声,就像石子在深渊里融化了,全部变成了黑色的液体,沉在底部。我读过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叫《取悦一个影子》,写的是与沉默的对话。作者写下这篇文章之时,对话者已经去世多年,作者试图用这篇文章将他召唤回来,但召唤回来的只是一个影子,他无声、缄默。于是,文字中回荡的只有作者的深切告白。那影子沉默地站在深渊之中,始终不言不语。
面向深渊中的影子的告白,是多么美妙啊。我也有一个深渊,我也有一个影子。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像黑色的石子,我仿佛还站在童年的山洞旁,一直扔着石子,而深渊从未被垫高。
你喜欢我的游戏吗?
阿巧
5 月1 日
第八封信
傅廉:
昨天晚上,我看了会儿电视,但越看越觉得电视剧索然无味,那些人物动作呆板、神情虚假,甚至比不上街头杂耍艺人的表演。于是我关掉电视,转而去研究几种最新的插花,但那些线描的花瓣总是像鲜花掉落下来,影响我的心情。最后我决定还是读一会儿书,找个故事消遣一下。
我读的是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教长的黑面纱》:从某一天起,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胡波牧师在脸上戴了一层黑面纱,把他的五官几乎都遮住了,只把嘴露在外面,而且即使是在做礼拜和布道时,他也从不摘下来。这道黑面纱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原本和蔼可亲的脸孔如今变成了一个黑洞,让人无法看透、无法猜测的深潭。当你和他聊天、向他倾诉时,你不知道他对于你所说的一切持什么态度,也无从判断从他嘴里说出的话是否是违心之言。人们在他面前坐立不安,像是面对着最后的审判一般。人们纷纷请胡波牧师摘下面纱,恢复他以前的面目,但都没有成功。胡波牧师异常固执,甚至让人感觉他是有意如此。故事读到这里,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既为人们着急,也很想知道胡波牧师到底长什么样。我最终忍不住将手伸进书本,揭开了他的面纱。啊,正是那熟悉的脸,你的脸,一张什么都没有,但却如此熟悉、如此确定的脸。
于是我赶紧上床躺下,关掉灯光,闭上眼睛,马上睡觉,因为我知道只有在梦中,才能将脸上的空白填充出来,才能看清你的脸。
阿巧
5 月12 日
第九封信
傅廉:
今天是周末,我不用去花店,我和阿娟、阿娈等几个朋友一起去爬山。太阳山就在郊外,我们开一辆车,每个人背着双肩包。这座山我们经常来,站在上面可以望见大半个城市。尽管已经是五月下旬,但今年的节气似乎推迟了,温度并不高,风儿吹动树叶,哗哗作响,像有人在倾听什么;吹动我们的长发,发丝在眼前反复缭绕,像荡秋千;吹动山中庙宇,铁铃发出清脆的叮当之声,如同召唤。我们一路向上,一路聊天、嬉笑,阿娈还唱着歌,将四野都激荡起来,花草树木不停地抖动、摇摆。走了一会,我渐渐落在了后面,阿娟停下来等我,拉着我向前快走几步。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又慢下来了。阿娟说道:“你是故意要等谁吗?这么慢吞吞的。”确实,我以前走得比她们都快,但今天我感觉我的背包特别重,里面不只有一瓶矿泉水、一包饼干和一包纸巾,而是装着一个人,而且还在不断地将他的分量加上去。事实就是如此,从一出门到开始爬山,我一直背负着他,即使是在斜坡上,我也从未将他放下,我决心就这样背着他,一直到达山顶。其实他带来的还不仅仅是重负,他还使山上的风景都改变了。以前我们只想一口气爬到山顶,畅快地呼吸,远眺山脚下的城镇、村庄,河流和公路。而今天,我感觉在每一棵树后面,在每一丛花草后面,都有值得留意的东西,就是那仅供歇息的半山亭也是刚刚飞回来,翅膀尚未收起,还在向着远方张望。而草树密布,泉水忽左忽右,这些惯常的风景,实则是心底的幻象,是心中荆棘丛生和耽思欲渴的心灵布景。山顶上的巨石,再不要形容它状若莲花,那只不过是我将一直背负的他卸下来,放在了山顶。从我身体上下来,他长大了,坐在那儿,以一身稳住了晃动的世界。
看着那块石头,我忽然想起了西绪弗斯,他会不会来到这里,加入我们,将石头反复滚下来,再推上去?
阿巧
5 月21 日
第十封信
傅廉:
已经三个月了,我用了整整一百天仍然没能将你创造出来,没能召唤你诞生,只能让你活在纸上,活在我的思虑中。你仍然是无形的,不可捉摸,就像三月的那天傍晚,你从晚霞中下来,又随着晚霞而去。你只在夜里,在黑暗中,才与我在一起。你像黑夜一样沉默,从不作声,从不现身,我的爱情仿佛是对深渊的爱情。也许我这个梦有点长,从遇见那道闪电开始,我就一直在做梦,甚至还编造了一个名字。有人说:所有的情书都是荒谬的,但至少所有的爱都值得珍藏。不能将你召唤出来,进入现实,这是我的失败,不是爱情的失败。爱情会转移到另一女孩身上,继续它的神秘创造。
现在,我将熄了灯,静静地坐在黑暗中,至少在那里,仿佛我们又在一起。
阿巧
6 月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