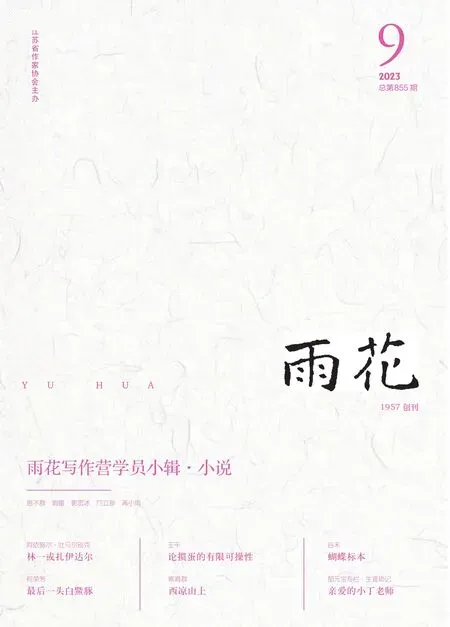亲爱的小丁老师
2023-10-22郜元宝
郜元宝
小学四年级一结束,我们的学校生活立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本村的两位“鬼头”“建平你”和“小虎子”不得不离开学校,成为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与此同时,两个生产大队合办的“完小”因生源猛增,必须一分为二。严厉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章老师留在原来的“完小”,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同学们则转入另一所新建的“完小”,小丁老师荣任校长,同时兼任五年级班主任及语文老师。
小丁老师是我们那条夹江上游“老观嘴公社”的高中毕业生,他以本地知青身份来我们“完小”代课,一直没有轮岗到别处。在严厉的章老师做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很少有机会跟隔壁班教语文的小丁老师打交道,只是经常看到他在操场的单杠上玩“引体向上”“双臂大回环”等高难度动作,令我们这群男生羡慕不已。直到换了学校,我们跟小丁老师才渐渐熟悉起来。
小丁老师唇红齿白,身材健美,肌肉发达,相当帅气——当然也很严厉,比如学生们说话行事有甚不妥,他脸色一黑,就蛮怕人的。
自从做了新“完小”的校长兼五年级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小丁老师已经完全跟我们打成一片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与其说他严厉,不如说他是在彼此亲近的基础上对学生提出“高标准、严要求”,把我们当作成熟的少年看待。他的严厉或严格,乃是关系融洽的师生之间应有的严肃认真,包含着友情的温馨。这就和始终跟我们保持距离的初级小学陈老师、旧“完小”章老师的严厉,大不相同。
学校的风气也很快转变。随着“建平你”和“小虎子”的辍学,也因为小丁老师的深度介入,以往学生内部“鬼头”与“小鬼”间的等级结构几乎荡然无存。我和“学庆你”虽说追随小丁老师来到本大队新建的“完小”,属于年龄最大的元老级学生,却根本没有野心与兴趣补“建平你”“小虎子”的空缺,继续当“鬼头”,而是一有空就去小丁老师的单身宿舍。
小丁老师的个人魅力如此之大,我们给他做小跟班,比当“鬼头”有意思多了。
新“完小”很简陋,五间教室一字排开,朝南一个小操场,这就是学校的全部设施。
几位年长的民办教师一放学便巴不得赶紧回家。他们除了教学任务,家里还有做不完的农活。只有小丁老师一人驻校。学校处于草创阶段,生产大队偶尔抽调农民过来,帮助学校在四周挖掘引水沟渠,以防下雨天水漫金山。其他事务,比如购买树苗、给操场四周搞点绿化、布置教室里的黑板桌椅、给小丁老师搬家等,就都交给我们这些“高年级”同学。大家手脚并用,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丝毫不觉得疲劳,反而十分欢畅,很有成就感。
小丁老师担任小学校长,虽能独当一面,也需要培养和依靠几位学生骨干。何况他还是单身,教学之余,也要一群男生作伴,一起散步、游泳、玩单杆。我游泳技术的提高,还有一点单杠上的基本功,全赖小丁老师手把手的耐心指导。
他还经常邀请我和“学庆你”晚上去他宿舍秉烛夜谈。小丁老师的宿舍就在学校东头那间最大的教室隔壁,一床、一桌、一椅、一个脸盆架子,此外别无长物,但因为只是十几平方米的一个小房间,仍然挤挤挨挨,并无“家徒四壁”之感。
小丁老师爱干净,宿舍窗明几净,一切井然有序。床铺尤其讲究,不像乡下人家,衣裳被服胡乱堆在一起,而是衣裳归衣裳,被服归被服,叠得整整齐齐。床上靠墙整整齐齐码着他爱看的书籍,床下是一只装着换洗衣服以及其他日用品的木箱。床沿留出足够的空间,客人们可以看到小丁老师从家里带来的整洁漂亮的床单。
说到小丁老师床上那些书籍,至今仍是一个迷。除了正式的课本,小丁老师并不鼓励我们看“闲书”。我和“学庆你”登堂入室,每天追随其左右,却从来不曾想过要向小丁老师借书看。也许是我们那时玩性太重,尚未养成阅读的习惯,也可能是小丁老师觉得他那些书籍并不适合我们,总之他从未向我们展示床边那一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藏书。日常放在窗前办公桌上的总是雷打不动的一本《夺印》。这本书小丁老师自己不怎么看,只在炒菜时偶尔用来做垫子,放一下烧热的铁锅,免得烫坏办公桌上的油漆。这也是我们格外喜欢小丁老师的原因。作为教师,他并不喜欢将“学习”二字整天挂在嘴边,也从未拿“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程门立雪”之类的故事激励我们好好读书。仿佛每天只要放学铃声一响,“学习”“读书”这件“正事”就告一段落。剩下的时间,该干啥干啥。
他会给我们讲故事,吹一阵口琴,再教我们唱几首歌。单杠玩累了,就去田间地头到处走走,“呼吸新鲜空气”。
五年级下半学期,全村通电,教室里大放光芒,我们的夜晚活动因此增加了新项目,就是将几张课桌拼成一副乒乓球台。小丁老师很快就教会了我和“学庆你”打乒乓,而一旦打起乒乓,我们简直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就在我读五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父亲终于回到久违的教学岗位。虽然只是民办教师,但年近花甲的他并不看重名利,全身心投入了自1958年起便中断的教学活动。小丁老师过去并没做过父亲的学生,但他和别的年轻老师一样,始终尊称父亲为“郜老”,请他做教导主任,负责一至五年级语文。但父亲很认真,坚持要从一年级开始“跟班”上课。因此,重返教学岗位的父亲和我虽然有半年时间同在一所小学,然而已经读到五年级的我始终无缘听到自己的父亲讲课。
这样也好,我可以继续无拘无束地跟着小丁老师,享受“学习”之外的各种赏心乐事。
大队后来又选拔了两位上海女知青来学校做代课教师。
她们合住一室,就在小丁老师隔壁稍大的一个房间。我们吃了晚饭去学校,或者放学之后直接留在学校跟他们三位老师一起做饭聚餐的机会,从此就更多了。
乡下那时古风犹存,男人从不下厨房。但小丁老师和两位上海女教师完全不管这些。一到周末,他们就在一起做饭,忙得热火朝天,我和“学庆你”则打下手。
他们的伙食自然比一般村民好很多。单是“炒蛋”,就让我们两个乡下男孩大开眼界。我们从来不会炒蛋,顶多做一碗薄如稀粥的清炖鸡蛋,全家人补充一下营养。但他们居然将四五个鸡蛋打在一起,直接用洋葱煎炒!
这样势必就得经常向村民买鸡蛋。有一次我陪其中一位上海女教师去一位农妇家买鸡蛋,整整一篮子才五块钱。当上海女教师拿出一张十块的人民币时,那位农妇惊呆了,“我怎么找得出啊!”结果说好十块钱就先放在她家,下次来时,再拿一篮子鸡蛋!
直至模模糊糊发现小丁老师跟两位上海女教师陷入了“三角恋”,我和“学庆你”仍旧继续当灯泡。所幸两只灯泡亮度有限,基本看不懂他们的关系究竟有何微妙。就这样,替他们跑跑腿去供销社买茶点“开茶话会”,或者夜里陪他们在乡间小路散步,数天上繁星,闻远近犬吠,还是愉快胜任的。
以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如此近距离接触老师。现在小丁老师和两位上海女教师凡事都找我们商量,顿时让我们感到长大了不少,再也不是被晾在一边或任谁都可以呼来唤去的小屁孩喽。
然而且慢,乡下少年真要改变小屁孩的形象,谈何容易!至少还需要一条穿在里面的短裤。这就又要说到我告别开裆裤之后的一件羞惭之事了。
那是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上海女教师中长得比较俏丽的那位在学校旁边的水塘洗衣服,不慎将新买的“香皂”掉落水中。小丁老师命我下去捞。我不假思索,脱个精光,勇敢地潜入水中,很快摸到了香皂。
当我得意洋洋爬上岸来,将香皂交给那位上海女教师时,她满脸春风地对我说:“谢谢谢谢,看让你打光腚了!”
我在另一篇散文中讲述了小丁老师和这两位上海女知青之间微妙的三角恋,这里不再重复。这份恋情昙花一现,并未结出任何果实。1977 年夏天,我们小学毕业,预备上初中,两位上海女教师赶上知青回城的潮流,也要回上海老家了。只有小丁老师还继续坚守在这座简陋的乡村“完小”。
惜别之际,我和“学庆你”每人获得了两位上海女知青共同赠送的礼物:塑料封面上印着“向科学进军”五个烫金大字的笔记本。尽管我们后来的职业都与“科学”无关,但我们都忘不了那个小小的笔记本所包含的美好的祝福。
小丁老师并没有送我们什么赠品,而是邀请我和“学庆你”去他老家(隔壁的“老观公社”)去“度假”。那也是一个临江的小村庄,还有一个与村庄相对的小小的“江心洲”。我和“学庆你”跟着小丁老师,在那里足足玩了一个夏天。要记叙那年夏天我们所经历的故事,就得另写一篇文章了。
没想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小丁老师。只是回乡探亲时,偶尔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信息。小丁老师不久也离开了那所“完小”,转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学。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后,他结了婚,也离开了教学岗位,改行做起乡镇的行政工作。因为能力突出,屡获擢升,最后官至副县级。目前已退居二线,正安享荣休后的生活。
去年12 月底,我正“阳”着,躺在床上发呆,忽然接到小丁老师的电话。原来他从“学庆你”那里获知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们互道平安,也简单通报了别后数十载各自的生活。他说自己不用微信,因此也就没法视频。电话中他的声音依然很年轻,我眼前彷佛又浮现出当年他跟我们促膝谈心、月下散步、拼起课桌打乒乓、教我们游泳和玩单杆时亲切的面容和矫健的身影。
在我心目中,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1977 年那个依依难舍的盛夏。
你好,亲爱的小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