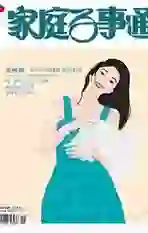儿时豆香
2023-10-19黎强
黎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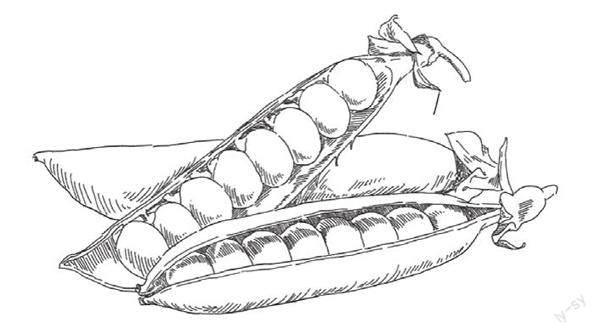
小时候的家常豆香,莫过于在豆子收割季节的烧烤豆荚香、母亲亲手做的水豆豉香、用新割的豆子推的井水嫩豆花香和父亲下酒的炒黄豆香,它们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飘着别样的香。
翻过老家屋后的土坡,穿过茂密的青?林,眼前就出现一大片长势喜人的黄豆田。只见黄豆叶子已由青幽幽的绿色渐变为黄绿色,荚果肥大饱满,稍弯下垂,仿佛整片田都飘着黄豆的清香。再经过几天的艳阳天,就到了收割黄豆的时候。收割豆子的季节,也是童趣盎然的季节。在田里,娃儿们的游戏就是将拾捡的豆荚装进小荷包里,装得鼓鼓囊囊的。拾捡得多的娃儿,小脸上挂着几分得意。娃儿们拾捡的豆荚,会细心地数了又数,再交给灶膛前的大人们,埋进柴火堆里。不一会儿,就听见噼噼啪啪的豆荚爆响。之后掏出来,掸去柴灰,要回自己先前数清了的豆荚数量,放进小荷包里,一溜烟跑去屋后的草垛下,剥开豆荚,摇头晃脑地吃着焦香的青黄豆。
勤俭持家的母亲每年都要亲手用黄豆制作水豆豉,满满的一大瓦坛,能吃上好几个月。凉拌菜也好,热炒菜也罢,加上一勺水豆豉,红红的,满是辣香、姜香、豆香,既好看,又下饭。
母亲把老家带来的青黄豆一股脑儿倒在大簸箕里面后,就开始手把手教我选择黄豆:把干瘪、虫蛀的豆子挑选出来,并不舍弃,留着炒油酥黄豆,给父亲下酒。父亲也不挑剔,吃得津津有味。偶尔吃到一颗苦涩霉臭的,也只是呸呸几下,再抿一口老白干,又自得其乐地吃着。母亲做的水豆豉炒牛皮菜,是我吃过的佳肴。母亲见娃儿争抢着,自己连筷子都不动,看娃儿们吃得风卷残云似的,眼睛里湿漉漉的。
用老家屋后的老井水推豆花吃,是父亲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还特别叮嘱,要今年新割的豆子。父亲每次回到老家,第一天晚上,就去屋后提来一大桶井水,把青黄豆泡上。第二天,父亲不让别人掺和,把昨晚泡好的豆子沥好,盛在一個大筲箕里,去井边打来井水,将豆子洗净,再沥干。尔后,我跟在父亲身后,到老井边,见父亲很有仪式感地用土瓢一瓢一瓢地舀起井水,嘴里自言自语念叨着:“这井水好呀,这井水好呀,这井水养了好几代人了哟,从没有干涸过。”然后,让仨兄弟轮流喝几口土瓢里的井水。那井水甜丝丝、凉津津,真叫一个舒服安逸。
席间,父亲抿着老酒,吃着老井水推的嫩豆花,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落座者说:“老家是啥哟?老家就是这些老石磨、老井水再加上新黄豆、新海椒、新鲜菜。”父亲说着,仿佛没有新黄豆老井水,老家的根就不在了一样似的。
还有一种豆香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深刻。父亲爱酒。但那时好酒是凭票供应的,父亲搞不到好酒喝,便经常去他朋友开的中医院,只为搞一瓶专治跌打损伤的名叫“五加皮”的药酒。回到家,让母亲弄点炒黄豆下酒。出锅的炒黄豆端上桌子,香气袭人。父亲拿来几个小碟子,把大部分炒黄豆分给了眼绿绿的娃儿们,自己留下少许,就着“五加皮”。
父亲喝得有些微醺了,却自顾自地念叨着“门对门,盅对盅,碗轿对烟囱”之类的。当时,我不懂,渐渐长大之后才明白,其实父亲念叨的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的贤文句子。我想,这是父亲在品味黄豆香时,不知不觉地给我的文化启蒙,或许有意,也或许无心。
家常豆香,最是难忘……
编辑|廖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