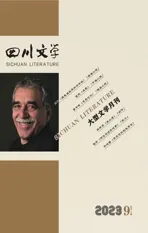呷尔及其附近
2023-10-15李存刚
□文/李存刚
高处的呷尔新村
谁也不知道一条陌生的道路通往哪里。
尤其是这条路还修在半山腰,朝向高处,并且有一段曲里拐弯的巷道似的起始,你就更加说不清,前方等着你的将会是什么了。2022年1月7日黄昏,当我从九龙县民族医院的住处出来,沿着医院门前的乡间公路散步的时候,就看到了好几条这样的路口。我本来是要去九龙县城的,但又一次没能经受住可以理解的所有初访者必然会有的好奇心的驱使,在又一条差不多同样的路口摆在眼前时,我的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拐进了巷道似的道路。后来,我特意站在路边一户人家门前,看了看紧闭的大门上钉着的门牌号码,才知道我们意外闯入的这个地方和我们工作的医院同属于呷尔新村。
开始的一段路还与途经医院门前的乡间公路垂直,碎石和着水泥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但还算得上宽阔——差不多可供小汽车单向通行,走在上面,足底有一种被人抚按的快慰。忽左忽右拐过几个弯之后,就有一堵石墙赫然挡在眼前。我以为走上的是一条断头路。在内地,我在好些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路。走近了才知道,路在墙根下折向拐了个弯,变成了仅可供人行走的石梯步,一条羊肠小道。
羊肠小道没几步便又折回来,继续维持着朝向高处的基本走向。沿着两旁的人家院子石头砌成的墙根,继续折过几个弯之后,一条差不多与途经医院门前的乡间公路并行的道路豁然横在眼前。因为是第一次来,尚不知道这条道叫什么名字,也许本身就是一条无名路。因为修在比途经医院门前的乡间公路更高的山腰上,除了隔不远就突出一小块平地,大约是为了会车专门拓出来的,其余路段只能供小车单向通行。
后来我知道,如果时间回退十年或者更久一点,这里还只有稀稀拉拉的三五户人家,房屋远不像现在这样密集,无名路和后来立起来的房屋的地基上还种满了洋芋、玉米、蒜苗、白菜,以及比现在多得多的核桃树、花椒树。后来立起来的那些房屋的主人来自五十多公里的三垭、小金等乡镇,他们一来,便在呷尔村地界上聚集成了一个新的村子,就叫呷尔新村。可惜十多年前我还没有机会像今天这样出现在村子里,我只能通过本地同事和朋友口中的只言片语,凭借想象,勾勒出一幅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当时图景。
不过这样也好。正好让我在一栋栋房屋穿行时,保有足够充足的好奇心,而我看到(房屋有新有旧,有一些是水泥楼房,更多的房顶盖着红色或者青色的瓦片,房顶上袅绕着或浓或淡的炊烟)、听到(我尚未完全学会的一种口音浓重的语言——彝语,半生不熟的汉话,鸡鸭牛羊此起彼伏的叫声)、闻见(不知哪家刚刚出锅的腊肉、鸡肉、牛肉扑鼻的香气,若隐若现的牛粪、猪屎、鸡鸭屎、羊粪的味道)的一切,分明让我感觉闯入了一种似曾相识而又全然陌生的生活里。这是一种已然老旧不堪的生活气息,它属于呷尔新村不太久远的过去,也来自呷尔新村的现在。在我踏上曲里拐弯的巷道似的路口,沿着一堵堵水泥砖头或者石头垒就的墙根,从东一棵西一株的核桃树、花椒树下经过时,我就恍惚间生出了这样的感觉。尽管已经置身其间,一切都近在咫尺,似乎又都很遥远。
三两步冲上去,站在无名路上,气喘吁吁间回望来路。高高低低的房屋之间,一堵堵更低些的石墙若隐若现,东一棵西一棵擎在空中的树,只看得到树枝,看不见树根,仿佛那些树就是浮在那里的。也看不见刚刚涉足走过的羊肠小道,谁都知道它当然是在的,我来或不来,它一直就在那里,随时供需要的人穿行而过,仿如人体里的侧支循环——如果把医院门前的乡间公路和我此刻所在的无名路看作两根大血管,我刚刚走过的羊肠小道就是连接在它们之间的若干根小小的交通分支中的一条。当然,作为一条通路,它存在的意义并不单单是让我看见。
眼前的无名路是一段绵长的斜坡。道路另一侧是同样一户挨一户的人家,几乎家家都是二层小楼,房前都筑起了小院,都有高大的院门与无名路相连,院门四周是水泥砖块垒成的围墙。可惜我似乎来得不是时候,家家户户的院门都紧闭着,只看到几个小孩在路边的水泥空地上玩耍,否则,我很可能就会把这里当成又一座空村了。
正继续朝向斜坡高处走,一扇大红色的院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门框里钻出一位中年男子。我在惊异中站定,中年男子却若无其事地从左手臂上提起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抓着衣领接连抖动了几下。看到我,中年男子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似乎是在对没注意到我的出现表示歉意。中年男子身后的院墙上写着一行字:“不要乱丢垃圾”。字是红色油漆写就的,大约是写下的时间太久之故,字迹是明显地变淡了,但定睛细看,准确认出还不是什么难事。“不”字上端的一横起自第二块水泥砖块的下沿,往后的“要乱丢垃”似乎一直在试图挣脱,却被一股不知哪里来的力量束缚住了,到了“圾”字,终于彻底地脱离了第二块水泥砖块,那行字因此看起来就变得有些杂乱,感觉不像是标语,倒像是谁家孩子调皮的涂鸦。我的目光越过水泥砖块垒成的围墙,看见中年男子家的阁楼。阁楼的木栏杆前种了一排海棠花,花树上擎着一朵朵粉红色的花瓣,瑟瑟寒风中,看起来那么弱不禁风,不知道它们将在哪一场寒风中黯然凋落。
正和中年男子说着话,就看到一些身着“察尔瓦”的男人和身着“百褶裙”的女子,三三两两地从无名路两侧的房屋里或者小巷似的道路出来,在我前方不远,不约而同地朝着斜坡高处走去。他们都不说话,只管默然地向前走着,然后越过斜坡最高处,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禁不住问中年男子:“他们这是怎么了?”
中年男子又是无声一笑:“做道场呗。”
道场,就是为逝者举行的送行仪式。中年男子告诉我,那些“察尔瓦”和“百褶裙”送走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彝族老人。仪式从昨天下午老人去世后就开始了,仪式还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三点。这样,逝去的人就会顺利地升到天堂。
等我也走到斜坡最高处时,我听到了喧哗声。斜坡那边有一处洼地,洼地上辟出的一块长方形台地上聚满了“察尔瓦”和“百褶裙”。走在我前面的那些,有的已经加入聚集的人群,未到达的那些也正步履匆匆地往前赶。台地上拉了电线,挂着几盏大灯。离天黑分明还有些时间,那些灯似乎是早就亮起来了的,在这个冬日的黄昏,仿如一颗颗小小的太阳。我听到的喧哗声就来自那块“灯火通明”的台地。在两块山脊之间的低洼处,像茫茫大海上安然耸立的一座小岛。
站在无名路上,我的目光被台地上的灯光和喧哗声牵引着,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紧跟着身前的“察尔瓦”和“百褶裙”向前走去。没走几步,我便收住了脚步。因为我不敢肯定,我如此贸然地闯入,是否会惊扰到他们?乃至惊扰到老人已然迈向天堂的步履?
渐渐适应九龙的海拔后,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和医院里的几位同事一起外出散步,目标是和来这里之前一样的,每天至少完成一万步,每次不少于半小时。冬日的高原难得有一场雨,这倒也在无意间成全了我。但在2022年1月7日那个黄昏之后,我就再没走进过医院门前的乡间公路旁那些巷道似的路口,再没去过医院背后更高处的呷尔新村。
我承认我是有些害怕自己一旦走近,就会触景生情地想起那位在我到来之前刚刚仙逝的老人,甚或遇见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我无缘得见那位老人的音容笑貌,但我总感觉自己认识他。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降生,也有人离去,活着的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目标要去完成,而离去的人在离去的那一刻,就已定格成了永恒。
石头多的地方
沿248国道去冕宁方向,南行近九十公里便开始进山。
山口放着一根横杆,所有进出的人和车子必须在横杆前停下。我的车窗还没完全摇下,路边的阴影里便冒出一个男子,小跑着来到车窗前,问我们去哪里、去干什么,然后指着路边的水泥墙上张贴的两张二维码图片,要我们扫码,登记个人信息。先是场所码,然后是防火码。我们来的地方属“低风险区”,到九龙已逾半月,场所码当然是绿色的。接着扫防火码,微信弹出一个公众号,关注过后对话框里弹出一个小框,最左边是一个手枪样端着的手,往右指着一行字:“点我,开始进山登记!”我是坐在驾驶室里进行扫码登记的,看见小框里手枪样端着的手,还没看清后面的字,男子便从我手里抢过手机,接连在屏幕上戳了两下。接过男子还回来的手机,我还没回过神来,男子已跑到车头前,伸手抬起了拦在我们车前的横杆。从对流程的熟悉和具体操作可以看出,男子应该是个驻守山口的老手。
尽管有防火码上的“进山”提醒,我还是想象不出我们即将进去的是什么样的山。来之前,曾听本地朋友这样说起朵洛:工作靠酒,出门靠走,治安靠狗。说的当然是进山的公路筑通以前的情形。朵洛是一个彝族乡,彝族汉子喜欢喝酒天下皆知,因此到朵洛工作或者办事,喝酒差不多是一项必备的技能;地处高山,又不通公路,外来者也就只能靠脚步来丈量进出的距离,而朵洛人呢,即便是在公路筑通以后,上山干活也基本是步行,因为公路并不能通往所有的山巅和谷地。据说,就是如今公路筑通了,进出的山间小道上依然时常有人出没,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公路就被落石、塌方给阻断了;也因为地处高山,难得有生人到来,真有生人出现在村子里,可能不会被朵洛人发现,这时候就轮到狗们大显身手了——对经常进山寻找猎物的狗来说,看家,可是它们必须首先具备的本领。
我在《四川省九龙县地名手册》里看到,朵洛是一个藏语地名,意为石头多。我们的车子穿过山口的人家,开始的一段路沿着谷地的溪流上坡,没多远便是一个回头弯,弯道的尽头卧着一堆乱石,乱石间,一眼山泉汩汩地淌着甘冽的泉水。我们的车子刚停稳,便听见一阵响亮的喇叭声,每一声都在山谷间回响,抬起头望着往右拐向高处的道路,只望见一处高高的山崖,很长时间不见汽车。对面也是高高的山崖,山体上裸露大大小小的石头,由于距离的缘故,看不清石块到底有多大,只能看到支出来的“头”。等我们洗过手,又捧起甘冽的山泉水喝过之后坐上车子,便见右侧的公路上轰隆隆驶来一辆越野车。车上只有司机一个人,会车之际,司机又一次摁响了喇叭,我赶紧也摁了一次,这是我学习驾驶技术时,那个跑了多年货车后来改当起驾校师傅的老司机告诉我的行车礼仪,开始驾车以后,我一直谨记师傅的话,并认真遵照执行。
往右拐出不远,道路便开始沿着山崖蛇形起来,路面也陡然变窄,只容得下一辆车单向通行。那道路显然是在山崖上硬生生开凿出来的,高处悬着岩石,里面一侧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就是路面上也不时堆积着碎石,外面一侧自然就是悬崖了,有多高不知道,因为不敢看也无暇看。现在时兴减肥,有些肥胖的女士为了所谓的美感,拼命地勒腰束胸。我后来在山崖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那道路的走形差不多等同于一个超级胖子长时间勒腰束胸后留在身体上的凹痕,区别只在于,一个是为了所谓的美感,一个是为了方便通往之地的人们出行。
我握着方向盘,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的道路,把车速放到最慢,生怕一不小心就吻上路边哪块面目狰狞的岩石,或者经不住路面成堆碎石的挑逗,即便不会腾空而起(当然不是欢腾),也可能因为车身的摆动,轰隆一下侧翻到路边的悬崖下。正紧张间,又一次听到山间传来急促的喇叭声,不由得更加小心翼翼地紧握着方向盘,没多远便见一辆越野车迎面驶来,竟和我们一样是川T车牌的。心头霎时生出一种意外的亲切之感,但转瞬就被迫在眉睫的问题取代了:怎么办?对方大约也看到了我们的车牌,但对方很可能是这条道上跑过不止一次的“熟手”,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开始将车子往后倒了。对方一动,我也跟着动起来。尽管路面逼仄且多弯,但对方倒车的速度竟比我前进还快,很快便在一处专供会车的开阔地停了下来。会车的时候,我特地踩下刹车、摁响喇叭,并且探出头,冲对方说了声谢谢。一个脸膛黝黑的中年男子坐在驾驶室里,从开着的车窗里扭过头,冲我微笑着摆了摆手。
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就在打退堂鼓。我们在山口问过一位正在地里下种的大姐,说是到我们要去的朵洛卫生院还需要半个小时。可没想到开始的这段路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听说过道路不好走,但没想到会如此险峻。会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一下那块开阔地,据我目测的结果,要在那里掉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再说,同事胡开宾作为医院指派的疫苗接种保障人员,已经坐另一辆车先行去了朵洛,为了兑现昨晚许下的陪同他去朵洛的诺言,我们已经开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实在不想半途而废。这也是我多年的职业习惯使然,作为医务工作者,任何时候,一旦为患者制定了治疗计划,就会不折不扣地执行。移换到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言出必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到做到”……这些古老的人生信条。
会过车后便是一个回头弯,道路折返,驾驶座因此换到了靠外一侧。经过刚才的一段路,现在又坐到了相对远离山崖的位子,又无暇看一眼车身外的悬崖,无法亲眼见到悬崖之悬,紧张的心绪不觉间放松了许多。大部分路段装了防护栏,不知什么时候被高处的飞石砸中,或者说不定就是某次车祸过后的遗迹,有一段防护栏差不多完全掉脱下来了,一头连着最后一根竖桩,另一头绳索似的掉落在路边的悬崖上,不知道掉有多长,留下几根光溜溜的竖桩歪歪斜斜地立在路边。我本已放松的心重又紧张起来。终于,在越过一堆碎石过后,我看到了溪流,前方是一座大山,看不清也无法想象通往高处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但毕竟离开了山崖,心里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在溪边停下车,掏出一根烟。这样的时刻,再没有比抽烟更适合的了。点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竟像帕金森患者那样止不住地发抖。我抽着烟,同事骆正霞又一次拨打起了胡开宾的电话。昨晚,胡开宾接到参与疫苗接种保障工作的通知时,我们就自告奋勇地决定随他一起来朵洛。我们三个人,同时受医院指派,以“医疗支援”的名义从几百公里之外赶到这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也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当医生,干一个医生该干的活儿;但是,我们毕竟是受医院指派前来的,事实上也就代表了医院(不只是医疗技术)。来之前我们是医院的一分子,来到高原了我们仍然是医院的一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临时性的缩微“医院”。我们没有理由不守护好这个由我们三个人组成的小小集体。这是我们理应奉为圭臬的集体主义。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是骆正霞第七次,也可能在第八次拨打胡开宾的电话,结果不是“无法接通”,就是“不在服务区”。我心头刚刚重燃起来的打道回府念头于是在手里的烟头之前彻底熄灭了。我征求骆正霞的意见,她也觉得我们必须往前走。
往前走的路全是上坡。起先一段沿着溪流弯曲蛇行,没多远便是一个接一个的回头弯。路面依然逼仄,感觉却和山崖路段明显不同。明晃晃的阳光透过车窗映照进车厢里,路两侧的坡地里种满了核桃树、花椒树,树下的土地难得看见一棵草,有几块地里似乎下种得更早些,黄灿灿土块间长满了幼小的玉米苗、洋芋苗。因为地处高山,光照充足,洋芋、玉米、核桃、花椒便成了朵洛的主要出产。阳光普照下的核桃树、花椒树、玉米苗、洋芋苗取代了悬崖和巨石,撞入眼帘,映在心间,就显出亮堂,滋生出愉悦。
朵洛乡政府就建在核桃树掩映的山坡上,乡政府旁边就是学校和乡卫生院,远远看去,像一个被世人遗忘在山间的微型村子。在如此陡峭的山坡,建村只能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我们在路边的一块树荫下见到胡开宾时,他正在和身旁的几个人交流着什么,大约都是医疗机构的同行,在讨论接下来的预防接种工作。我们像失散多年的亲人那般冲向胡开宾,他似乎没想到我们真会出现,见到我们,明显地愣了一下,然后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回程。尽管已经想到过这一趟的不易,但在车子驶到山崖下时,我们还是着实被惊住了。我们的车子越过小溪进入山崖,便见前方不远的悬崖上不断有石块在掉落,砸在路面、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嘚嘚、咚咚、当当地响个不停。看路面,有一堆被碾成一座小山峰似的碎石,想来就是由若干次这样的飞石堆积而成的;看高处,一块张牙舞爪的巨大岩石,正无声地冒着浓浓的烟尘,那些落石就是从那里掉落下来的。这时候起了风,扭动的烟尘里,那块巨大的岩石似乎也随时可能落下来。我迟疑了一下,下定决心踩下了油门,我们的车子于是轰隆着,向前冲了出去,一直冲过整个山崖,在胸腔里咚咚狂跳中在山崖下的那个拐弯停住。
那块悬着的巨石终于没在我们经过时掉落下来。
但在我心里,乃至此刻在回忆里又一次重温起从山崖下逃也似的经过的时候,它分明已经轰然落下,砸中了我大脑中某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尽管不至于瘫软如泥(否则我那时候怎么可能驾着车顺利经过那块飞石滚滚的山崖),但心惊肉跳却是真真切切的。真是后怕呀。满脑子都是“如果……”已然变成现实后的恐怖场景,仿佛自己果真就躺在了那块巨石下面,越想越觉得可怕。
行驶到山崖下的那个拐弯时,我再次停下了车,捧起路边的山泉水洗了一把冷水脸,然后抬起眼,打量我们刚刚经过的山崖。我想如果日后有人向我问起朵洛,我一定会告诉他,这里,真是一个石头多的地方。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每一个去过朵洛的人,所获得的感受定然是不同的。
就在准备重新上路的时候,接到医院马院长发来的信息,要我们赶紧返回,语气恳切而又严厉。就在刚才,同事将我们战战兢兢路过山崖时拍摄的短视频发在了微信朋友圈,没想第一时间便被马院长看到了。后来得知,以前,就有和我们一样从内地赴藏区工作的同行开车外出时发生了意外,一整车的人全部遇难。看来我们这趟出行,着实让马院长担心了。
也就因为此,除开我工作生活的县城(呷尔镇)和途经的汤古、乌拉溪,朵洛成了我在九龙期间唯一到过的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