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人生》到电影《人生》:悲剧主题的淡化与消解
2023-10-12杨蕊
杨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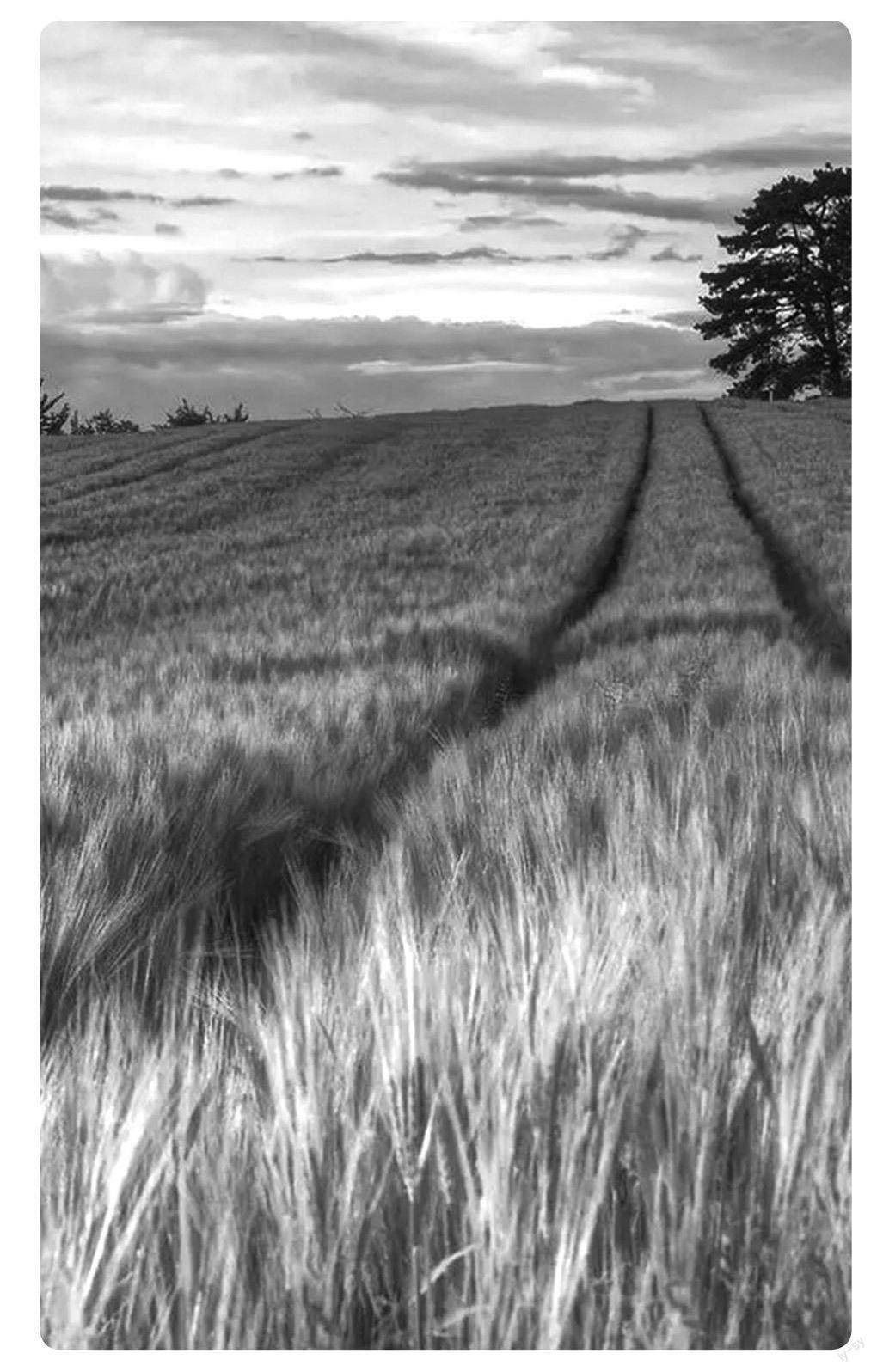

路遥的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一年后,路遥根据小说版《人生》创作电影剧本。电影《人生》在著名导演吴天明的执导下于1984年上映。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在创作时间上仅仅相差两年的时间,但从细节的重新编织、情节的增删乃至电影独特的镜头语言上,能让我们看出路遥创作中的心态变化与其所受到的时代影响。着眼于小说、电影中分别对围绕在主人公高加林身边的两位女性角色刘巧珍、黄亚萍的人物刻画,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电影对小说悲剧主题的消解与淡化。
一、以女性人物描摹建构宿命性社会悲剧
小说《人生》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主人公高加林在以回到土地、离开土地又重返土地为主要脉络的人生中,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产生了情愫。围绕高加林的事业、爱情两条线,《人生》集中体现出时代背景下农村青年的困境与悲剧命运。其中,爱情线与事业线缠绕交错。作品通过对与高加林有着恋爱关系的两位女性角色的塑造,建构并深化了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宿命性色彩。
(一)淳朴而善良的农村女孩儿刘巧珍
刘巧珍是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塑造出的一个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
刘巧珍有着直白表达内心所爱与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气,她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在日常生活里展现出农村人民勤劳、能干的优秀特质,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是男性的理想择偶对象。而这样一位在我们传统的主流价值观中趋于完美的女性形象,却遭受了爱情失败的打击,其根本原因在于爱情主体双方在知识层面的巨大落差。刘巧珍成长道路上的遗憾便是她从未受过教育,因此,她内心深处对有文化的、有思想的人有着别样的欣赏与看重。但作为农民的刘巧珍的感情是清醒而又克制的,她素来知道自己只是个不识字的姑娘,纵使外表美丽,也无法受到来自当时的高水平知识分子高加林的另眼相看。因此,她在高加林失去教师身份,迫不得已回到农村重返农民身份后,才向其倾吐自己的内心想法。而当高加林在马占胜的安排下成为记者后,刘巧珍即使心怀哀戚,仍坦然接受了自己被高加林抛弃的事实,并随后以极强的同理心回馈再度陷入落魄状况的高加林,在展现出高度的人文光辉的同时,建构起属于刘巧珍的爱恋的悲壮结局。
路遥在倾尽笔墨树立起淳朴善良的刘巧珍形象的同时,也通过这段不合时宜的爱情,为主人公高加林的人生奠定了悲剧性的情感基调。刘巧珍和高加林的爱情中,并没有绝对错误的一方,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不曾受到教育的刘巧珍爱上有文化、有才华的高加林是内心情感的真实驱动;到城市工作的高加林难耐刘巧珍与自己的文化差距,选择结束与她的感情,这是客观现实的理性驱动。但命运的阴差阳错使高加林再度失去了城市的记者工作,再度回归乡村的高加林不复拥有体贴善良的刘巧珍,那些他曾拥有过的爱情温存与事业辉煌在一刹那都离他而去。高加林对更好工作、更广阔未来的追求,其实是每个人内心对向善向好的本能渴求,高加林对刘巧珍的抛弃固然有着不负责任、有失考量之处,但在此过程中,他本人也经历了巨大的苦痛。因此,于情于理,这场发生在高加林和刘巧珍之间的爱情悲剧具有一定的宿命性。路遥竭尽笔力用心塑造臻于完美的女性形象—刘巧珍,能够造就高加林在前后人生里的巨大对比,令这场爱情悲剧更显造化弄人。
(二)灵动却利己的城市女孩儿黄亚萍
黄亚萍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现代新女性”代表。
黄亚萍成长于城市,具有优渥的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她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作为独生女,她备受瞩目,学识渊博,涉猎广泛而具有灵气。出色的出身导致黄亚萍具有极高眼界与极远追求,同时也造就了黄亚萍清高自傲、利己自私的个性。
黄亚萍有过两段情感经历,其一与张克南,其二与高加林。两段感情中,黄亚萍都展现出其现实到近乎自私利己的爱情观念。张克南一直全心全意给予黄亚萍自己真挚的感情。黄亚萍虽在日久生情的影响下接受了张克南的爱情,但是在高加林重返城市后,她立刻投入高加林的怀抱。高加林身上有着黄亚萍所爱的才气和志气,但她還是不会选择当农民的高加林,这才有了高加林来到城市后二人的爱情,也解释了为什么当高加林遭受举报,黄亚萍便自然与之分离。黄亚萍的利己主义爱情观念不仅指导其行动,更在对话中直接展现。高加林于踌躇中告知黄亚萍自己与刘巧珍的关系,黄亚萍听后,这样说道:“这简直是一种自我毁灭!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又有满身的才能,怎么能和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结婚?我真不理解你当时是怎样想的!”黄亚萍无法接受高加林与一个农村妇女结婚,这也体现出她重现实、轻感情的利己主义爱情观。这一爱情观直接导致了黄亚萍与高加林的爱情终结,纵使从现实上看,城市与农村的爱情本就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但黄亚萍的行动举止让高加林在事业遭受剧烈打击的同时,情感上也失去了唯一的寄托,这对当时的高加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黄亚萍不仅在有关爱情的选择方面趋于利己,更在日常相处中展现出“浪漫”包裹下的任性实质:二人共骑一辆自行车行驶在县城的街道,故意引人注目;黄亚萍为了所谓“即兴的浪漫”,硬生生地将高加林从会议中拉走去寻找并没有弄丢的小刀。爱情中的情侣固然需要一些彰显情感、增进感情的互动,但绝不是如此影响彼此、影响他人的活动。小说中的高加林在失去刘巧珍后却进入这样一段令人有些无奈的爱情,这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读者对高加林抛弃刘巧珍的不满,展现出一种高加林生活并不美满的直观感受,刻画了高加林悲剧人生的无奈感。
二、以人物细节篇幅增删消解人物悲剧性
电影《人生》上映于1984年,即小说出版后的两年后。《人生》的作者与编剧皆为路遥,电影在对小说的大面积还原下,也在细节部分作出许多修改与增删,两种媒介形式下的《人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互文性。相较于小说,电影对刘巧珍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细节刻画,更在两个小时的电影画面中反复出场;与此同时,电影减少了小说中黄亚萍和高加林的相处场景,从而减少对黄亚萍的个性描摹。二者结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个性表达,从而消解了高加林身上的悲剧性,减少作品传达的社会生活的无奈感与宿命性。
(一)刘巧珍:反复出场与趋于完美
相较于小说作品,电影增加了幾段小说中未曾出现过的以刘巧珍为中心的情节,增加的人物情节使刘巧珍这一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也消解了高加林波折人生中的悲剧性色彩。
电影中,刘巧珍已经改口称呼高加林的母亲为“妈”,这便说明刘巧珍与高加林的感情已经一定意义上得到了长辈的认可,称呼的更替更加展现出二人关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电影增加了刘巧珍与高加林母亲的互动,加重了高加林为了城市生活而抛弃刘巧珍这一行为的罪恶性。通过这一细节,高加林从“被迫”失去刘巧珍这一伴侣的值得同情的人,转变为抛弃与自己共克艰难生活的伴侣的负心汉。从情感上,高加林将不被观影者所理解,并因此消解其悲剧性。
正如前文所述,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之根源或许在于双方在知识水平、文化程度方面的鸿沟。小说里,刘巧珍并没有于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在电影中,路遥设置了刘巧珍向妹妹请教识字的情节,从而可以看出刘巧珍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和高加林之间存在的隐患,并试图解决。刘巧珍的主动学习使这一本就善良美好的人物形象更加趋向于完美,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高加林的抛弃显得更加绝情。在二人告别的情节中,刘巧珍兴高采烈地向高加林展示自己在纸上密密麻麻写下的“高加林”,但是高加林还是在这时候扫兴地、无情地提出了分手。路遥通过前后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展现这一冲突,使观影者对爱得热烈却遭受背叛的刘巧珍产生深深的同情,而相应地也便不会给予高加林面临的为难处境过多的理解与共情。
此外,影片中用长达八分钟的镜头细致地刻画刘巧珍与马栓婚礼的场景。在这一场景中,锣鼓喧天,一派热闹景象,展现出了陕北特色民俗风貌的美学价值。这一场景的设置更通过“以乐景衬哀情”的手法,用宏大、热闹、喜庆的结婚场景,烘托出刘巧珍内心的苦痛和哀伤,通过艺术性表达极大地强化了刘巧珍爱情的悲剧意义,与此同时消解了高加林悲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二)黄亚萍:形象淡化与特征隐匿
在小说《人生》中,黄亚萍是重要程度仅次于刘巧珍的女性形象,而电影对黄亚萍形象的描述呈现出大面积的删减,导致人物塑造相对单薄,人物个性被隐匿。路遥在电影《人生》中大面积删去对黄亚萍的个性塑造以及她和高加林的互动,小说中原本能够表现黄亚萍利己、自私而又任性的情节设置在电影中都被一一略去。小说中黄亚萍和高加林在类似的文化审美与人生追求方面达成高度共鸣,但电影中对黄亚萍的描述仅仅保留她几次来到高加林的办公室向其表示自己对他所撰写的新闻稿的仰慕之意的情节,从电影视角上看,黄亚萍同高加林的情感基础变得薄弱,二人之间感情产生得非常突兀。观影者不免对这段情感的真挚程度感到疑惑和犹豫,并且有理由怀疑高加林接受黄亚萍的仰慕是为了借力获得更好的就业机遇与事业平台。以先入为主的想法为先导,高加林最终失去这份记者的工作这一遭遇的悲剧性便被合理消解。
电影有意识地减少对黄亚萍的细节刻画,尤其删去能够体现她任性的重点事件,删去的内容中包括她为了所谓“即兴的浪漫”,硬生生地将高加林从会议中拉走去寻找并没有弄丢的小刀等。情节上的缩减在令黄亚萍成为电影的非核心角色的同时,无形中使高加林成为观众目光的聚焦点,成为爱情里的“过错方”:他带着“利用”的目的答应黄亚萍的告白,在这段感情中又时而对刘巧珍念念不忘。黄亚萍人物形象的改变导致高加林的人物形象转向不负责任、功利虚伪,并以此消解高加林所面临人生困境的悲剧色彩。
三、从多维视角分析小说和电影差异之成因
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的创作仅仅相差两年时间,且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同为路遥,“同一作家对同一事件不同形式的表现,且在电影忠实于小说的创作原则支配下,电影和小说也就不能简单地被界定为两部作品,而应该被视为一部作品的两种形式”(张连义《叙事策略与“事件”的跨文本传播—以〈人生〉小说和电影的互文性解读为例》)。因此,小说和电影之间呈现出互补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小说和电影的区别,我们能够从中追溯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与主观因素。
(一)时代与社会的两次回应
总体而言,无论是小说《人生》的创作,还是电影《人生》的改编,其传递的内容、表达的中心题旨,都是路遥对社会现实的投射与反映。
小说《人生》回答了“潘晓来信”事件中的核心问题。“潘晓来信”发生于1980年5月,当时,一位署名潘晓的年轻人撰写的信件被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随后便引发了长达半年多的讨论。在来信中,潘晓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迷茫感受。《人生》中,以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确立为主要脉络,但是作品的另一条主线在于农村青年的出路问题。因此,《人生》被称作“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讨论的后续事件”。爱情作为人生中同事业一样重要且影响道路选择的因素,也经小说化被写入作品内,由此生成刘巧珍与黄亚萍两位性格、出身迥异的女性形象。
然而,从作品发表后的读者反响来看,小说中对高加林的命运设置引发了部分读者的不满。阅读期待的偏差影响了小说的社会舆论,让小说对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进退两难:高加林接纳了突如而来的特权待遇,即使有很多的无奈之处,他本性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应该使他成为小说所塑造的令人感到同情且在社会悲剧影响下失去未来的人物形象。纵使路遥在谈到《人生》的电影改编时表示电影将把“小说的题旨应较完整地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作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早晨从中午开始》)。但是,在这类社会压力的迫使下,在事实上,路遥扭转了电影叙述的笔锋,将讲述重心落脚在爱情这一单线上,并通过前文分析的种种方式,利用女性形象的改编,间接性隐藏高加林命运中的社会悲剧性,有意识地对之采取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批判态度。
(二)创作者内心的真实展现
作者对作品人物的主观偏向性,将直接影响塑造人物时的具体表达。
路遥在塑造《人生》中的人物时,毫不吝啬自己对刘巧珍的偏爱,他以文中德顺老汉之口热烈地赞美刘巧珍为“金子一样的人”。路遥本人出身贫困的农民家庭,受家庭环境和成长因素影响,在提及刘巧珍和德顺爷爷时他表示,“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是永远宝贵的”(《关于〈人生〉的对话》),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直接影响其在塑造刘巧珍形象时带有很强烈的倾向性,而他对现代文明的内在抗拒也导致他在塑造黄亚萍时具有一定成见。作家的个人因素极大地影响作品人物的刻画与塑造,这一倾向性在电影中表达得更为透彻。
小说《人生》是路遥一人的创作果实,但是电影《人生》受其媒介形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成为多位合作者的共同杰作。在《人生》的改编中,导演吴天明对作品情节也起到了极大的干预作用。吴天明出生于陕西咸阳,在中学时期便确立了自己从事电影工作的未来志向。吴天明家境相对优渥,看待事物的眼界也比较前沿,他和路遥的成长环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他提出应该对黄亚萍的相关情节进行改写与删除,这是为了“对小说存在的一些不足作些弥补,使它更合理更朴素些,符合生活的真实”(吴祥锦《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访〈人生〉导演吴天明》),他认为高加林和黄亚萍“应该有不融洽的地方,但分寸把握上过了些,过了会让人感到失真”(吴祥锦《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访〈人生〉导演吴天明》)。如前文所述,电影删去了展现黄亚萍利己、任性的情节,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吴天明对知识分子阶级的保护和偏袒。另外,小说中的刘巧珍未能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局面,但在吴天明看来,“这对一个现代农村姑娘来说,我们觉得欠完善,所以增加了巧珍识字的细节”(吴祥锦《小说“人生”与电影“人生”—访〈人生〉导演吴天明》)。然而,吴天明对农民的真实生活现状了解甚少,刘巧珍是否会主动用学习知识的方式补足自己的短板,这一点我们依然不得而知。而阴差阳错的是,吴天明在主观影响下对《人生》的改编,使社会悲剧不再是作品最为突出的主题,作品的悲剧性在这里得到消解。
总体而言,作品《人生》由小说走向电影,在改编与调整中,我们得以窥見时代特征,更能够以作品的细节揣摩出作者的内心世界。电影《人生》着力通过女性形象的再塑造,微调作品故事情节,一定程度上消解和淡化了作品的悲剧主旨,展现出当时的时代特性与作者的主观感受。小说《人生》和电影《人生》在各自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能够以相互对照、互相对比的形式为读者带来更多的感悟与体验,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与史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