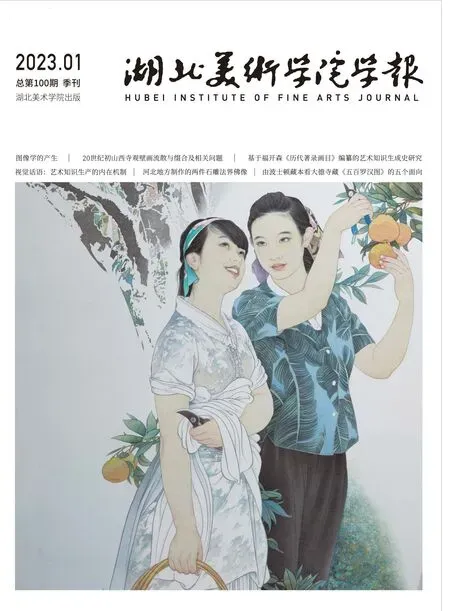民国女性艺术展的叙事探索:以“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20世纪前半期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为例
2023-10-11房桦何香凝美术馆
房桦 | 何香凝美术馆
“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作为何香凝美术馆“20 世纪女性艺术”系列研究计划的开篇,它针对如何重新运用“何香凝”这个艺术符号,在“女性艺术”的定位上展开叙述,力求突破长期以来以时间为轴线的叙事模式,以讲故事的姿态为策展体系建设作出尝试。本文以该展览为例,从空间叙事模式的角度探讨展览叙事转向对突破策展困境及策展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女性艺术运动”的个案与图景:主题新探、史事编织及叙事转向
1.主题-场景:女权思想与女性艺术
何香凝(1878——1972)一生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作为政要人物、画家、社会活动家,其人生堪称20 世纪中国现代进程的缩影。由于人物的政治性与革命性,以往研究甚少从“女性”的角度解读何氏及其艺术,甚至去“女性化”,隐去何香凝的“女性身份”。而何香凝作为女性个体,历经留日、革命、弃职等与国家命运交互的个体经验,以及她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努力,作为革命遗孀在弃职前后的思想变化等,体现了何香凝从“夫人”向以画为生、自足于社会的“女画家”的角色转型。何香凝个案涉及女性思想、女性角色转化、女性艺业与谋生等一系列“女性问题”,其人生运际也反映了女性个体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成为我们探究20 世纪中国艺术语境中“女性问题”的新视角。
何香凝1924 年在广州国民党“一大”倡议发起第一个中国“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广州掀起了首届“三八”节庆祝大会及游行。中国妇女运动在广东逐渐开展起来,此后迅速向全国推广。1926 年何氏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代理部长时提出“国民革命是妇女唯一的生路”[1],使之成为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锋。1928 年“四一二”政变后,何香凝由广州移居上海,身体力行为中国女性发声,切实为女性立足社会做出表率。在个人革命事业与跨文化交流互为交织的同时,何香凝的艺术实践也展现出对传统艺术的现代探索,何香凝在艺术和妇运领域之间自由跨界。1930 年代寓居上海期间,她充分运用个人文化声望,调动上海妇运力量,率领女性工作者为抗战救国筹办画展,召集全国各地女性画者加入,向社会公开展示作品并义卖。在开放、多元的上海,女性公开办展成为拓展女画者社交空间的有效途径。
1934 年中国女子书画会创建于上海,成为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性美术社团。此时距何香凝倡议争取女子权益已历10 年。上海艺坛活跃着以何香凝为领衔的女性国画家群体,及从事现代艺术研究的女性洋画家们。她们均成长于中国女性运动的盛期,一面是传统国粹的承袭,另一面是跨文化的交流融合,还有一面是传统绘画的现代探索。由此,民国女性画家群体分三个类型:献身社会的革命女性;继承传统书画的新闺秀;致力西画研究的新女性。她们在结构类型、艺术主张、社会活动、女性创作等方面,为我们观察民国“女性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样本。我们也从其历史情境中,重新审思“女性”在现代艺术进程中的价值。
2.故事-角色:史料新探与史事编织
博物馆界对现代叙事学的兴趣在新千年以后渐成热潮,将“故事”视为展览叙事转向的基本态度,展览故事很大程度扮演了以故事包装道理的作用,故事在观点塑造和表达上的能量是博物馆界拥抱叙事的原因[2]。展览以“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为题展开叙述,在不同“场景”下,民国女画家各自艺术与生活的“事件”存在着大量的交叠。通过多个故事的引入,原本单薄而空洞的时序性叙事结构将被层次丰富的事件所填充,改变了传统的单线叙事模式。故而,梳理和组织民国女画家的作品及文献、女性成长与女性言论,编织历史事件,遴选经典案例,重视事件之间的编排和结构,建立一个足以诠释主题的叙事模式尤为重要。
围绕民国“女性艺术运动”主题,本次展览的研究对象从民国女画家的三种类型入手,首先以何香凝为代表的革命女画家群体,其次是中国女子书画会为代表的国画创作群体,其三为致力于西画研究的洋画家群体。这个分类一方面呈现了女性艺术群体在艺术实践上的不同侧面和特点,另一方面从文化史的维度来看,她们摆脱对家庭的依从,谋职于社会,这个女性群体便凝聚出关于“艺业与职业”的共同话题。由此,展览从女性与社会、时代与艺术、生活与才情多个维度观察和解析研究对象,以主题-并置结构的空间叙事呈现一场“图景式”的民国女性艺术运动。作品、文献、史料的调研、收集与解读,便是编织“故事”的基础。
关于中国古代女性艺术的研究,自20 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就明清女性艺术著述不断,2000 年以后国内学界对女性艺术的研究,又为进一步系统深入的女性专题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民国女性艺术运动及个案研究也渐成热门选题。近十年来,先后有安徽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馆、上海画院、程十发美术馆、常州画院、吴青霞纪念馆等,基于藏品优势策划了不少优秀的民国女性艺术展,为客观展现女画家的艺术面貌作出了学术引导。如2020年上海画院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复原”了民国女画家的创作实践[3]。媒体对民国女画家的史事与故事曝光率也较高。如何进行创新策划是此次展览的挑战之一。
经作品调研所知:一、民国时期,女画家受艺术市场的影响,创作上虽继承传统却难有新意,故作品遴选上存在局限;二、民国时期的作品多分散收藏于不同机构,因经费限制,运输、商借存在困难;三、现流通于艺术市场或私人收藏的民国作品存在甄别上的风险;四、女画家在新中国之后作品留存虽较多,但晚年作品的艺术语言、题材已呈现特定的时代特征,难以贴近民国时期的创作情状。
结合作品调研及经费条件,将民国女画家名单厘定为(第一组)何香凝、郁风;(第二组)冯文凤、顾飞、李秋君、陈小翠、周錬霞、吴青霞、陆小曼;(第三组)方君璧、杨荫芳、关紫兰12 人。展品包括书画、信札、民国报刊、出版物、档案、视频等,出自何香凝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深圳博物馆、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浙江省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6家机构。藏品出处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与展览主题及研究对象的历史活动轨迹相吻合。由此也说明,艺术遗存体现了地方文化的保护意识及其历史沿革与累积。
3.藏品之外:文献与文献作品化
文献是除藏品叙事之外重要的视觉图像,它对阐释特定时代、人物的艺术创作及历史情景等社会性因素提供丰富的信息。由于藏品散落等原因,展览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加强对文献的梳理,作为弥补原作“缺席”的必要方式,更是组织故事层次的基础。藏品与文献共同构成展览空间中具有叙事能力的“物”,它们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而展览叙事为这些“物”制造特定的语境,将“物”与背后的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建立了逻辑关系。展览叙事对藏品与文献的运用,并为空间叙事引入丰富的子元素,充实展览主题,达到组建脉络,编织故事,丰富叙事结构的目的,也是考验策展人对视觉材料的组织和表达。而策展人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者。
为达成以何香凝为原点,以中国女子书画会为切面,以同时代洋画家为延展的策展思路的贯联,利用文献与作品组成对话关系,将文本阐释转化为视觉叙述是此次展览叙事模式的主要处理方式——以文献与原作为组合,12 位民国女画家构成12 组图像关系,围绕主题作并置叙事的形态。每一位女画家以原作展示艺术本体的同时,文献为其发声。在展陈设计上让文献作品化,结合原作形成有机、互动的关系。这一策展形式,突破了以往以藏品为优势的展览形态,也弥补了展览中因个别代表作的“缺席”造成的断点和空白,规避千展一面的陈设习惯,为策展挑战之二。
例一,展览首先以何香凝为原点,文献展陈建立在对何香凝早期留日史事和留日时期作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日本女子美术大学的授权,展出了何香凝学籍档案、同时代毕业于该校的女学生名单的影印件。1982 年日本学者石井洋子整理发表的清末民初留日的中国女学生名单,显示了何香凝在东京不同学校之间入学、转学、退学的接续情况。这些重要文献的收集和陈列,呈现了何香凝早期如何接受现代艺术教育的过程,突出了女性接受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并为清末女性留学问题提供了案例。何氏现存最早的作品,正是完成于她留日期间。三件1910 年创作的虎图与前述的文献构成一个完整组合,充分表明何氏作为同盟会会员以革命者的姿态对拯救没落王朝的想象。起源于日本的虎画,此时已成为清末文人圈中流行的新的收藏对象。因新题材、新画法,何氏的虎画被视为“新派美术”的成果,流通于清庭政务人员之间的日常馈赠和人情交谊。“何香凝”作为一个视窗,为观者进入20 世纪之初察看现代女性思想的启蒙、东亚现代女性职业教育的发端、中日文化互动与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代表性的女性个案。
例二,中国女性艺术于1920 年代普遍得到社会的认可,从事中西绘画研究的女画家频频亮相于大众刊物和流行画报。1934 年中国女子书画会成立之时,妇女界刊物《妇女月报》及女性读者为主的《上海画报》《礼拜六》《良友》等流行刊物对该团体予以了关注,媒体报道络绎不绝。媒介对女性话题的大量传播,一方面得益于女性权益的提升及社交空间的拓展,一方面则是媒介为女性的自我表达提供了一个空间。诗词、散文等绘画以外的女性书写是女画家们日常的思想交流。如顾飞《我与绘画》、陈小翠《画余随笔》、陆小曼《泰戈尔在我家》、方君璧《我的中国画改良观》等,透露出文艺女性的日常互动和社交。展览通过大量收集、梳理媒体刊发的书信、日记等文献,在女性的绘画与书写、艺术与日常之间构建了一个可“读”的视觉文本。
例三,郁风与方君璧、杨荫芳、关紫兰等均是致力研究西画的女画家,她又与何香凝同属于“革命女画家”的一列。前者以“革命者”自诩,是抗战宣传的骁将,后者出身于革命,是以妇运和艺术为革命服务的领袖。1937 年郁风撰写的《记何香凝》是最早对何氏女性思想及其行动展开个人解读的文章,她代表着一代青年女性对何香凝倡导的女性解放与救国的认可,并追随“革命者”的独立精神,投身到“男人的行列”,离开家庭奔赴前线。郁风最出色的反映个人觉醒的两件自画像作品《风》(刊物剪报,1935 年)及《朝阳》(京都国立博物馆藏,1935——1937 年),精准地体现当时的女性思想和行动力。展览以大量照片与民国报刊文献,辅助呈现郁风与何香凝这两位“革命女性”的历史交织。前文提到,遴选女画家时首先将何香凝、郁风归为“革命女画家”一组,但在实际展示结构上,以何香凝为开篇,以郁风收尾,两位带着“革命”烙印的女性在展览中首尾呼应,再度回应到何香凝在广州发起女权思想与郁风在上海发扬女性艺术的对照上。中间的女性案例则在20 世纪女性艺术运动的时序上发展、交替,彼此切换、递进。
二、史事陈情与艺术叙事的交织:主题-并置叙事在展示路径上的体现
展览以12 位女画家串联呈现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女性兼容传统与现代、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运动图景。根据展厅空间格局,从三个篇章共同解读民国女性艺术缘起于广州、发展于上海的叙事脉络。
第一章“国之觉醒 女性独立”,以一部女性“成长史”的形态呈现1910 年代至1940 年代何香凝留日习艺、艺术转型、妇运救亡的三段经历。清末智识青年为了寻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也唤醒了沉睡的中国女性。为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求学、就职便是一条摆脱依从的女性独立之路。这一章从1903 年何香凝留学开始,开启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独立与求学的篇章,展示何香凝辗转于日本女子大学校和女子美术学校,入学、退学、再入学、毕业的情况。围绕何氏留学史实,以日本女子美术大学藏1909 年“何香凝学籍表”及《外国人卒业生国别一览》的“何香凝页”再现何氏接受现代艺术教育的诸多细节。它提示观众注意学籍表上呈示的何香凝家世背景、清政府留学鼓励政策、师从日本名师田中赖璋等信息。这一部分为学界了解何氏留学与革命、海外生活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展览以明治时期女子美术大学的教学场景图、何香凝夫妇与孙中山在日本“帝政取消一笑会”的历史图片,以及何香凝1937 年《自传初稿》所述的旅日生活、学习与革命,提供清晰明确的物料读本。最具代表性的是1910 年何香凝三件虎图的并置展出,直观反映其留日时期的绘画水平。主题作品有深圳博物馆藏《虎啸图》、何香凝美术馆藏《虎》以及1963 年《何香凝诗画集》首页作品图像《虎》,首次以组合形式展出,点明主题。
何香凝的个体经历与独立思想,铸就了她对新派艺术的探索和追膜,产生了有别于同时代闺阁秀媛的题材意识。因此,展陈逻辑上顺应何氏留日归国后创作的连贯性,将她广州时期与上海时期的画业,分出左右两个展区予以对照。“广州时期”陈列何氏早期代表作品《狮》《菊》原作。难得一见的是,何氏1910 年的《山水》画页与1914 年的《马》原作,分别与日本赖山阳史迹资料馆藏《田中赖璋和他的门徒》画册中同时期田中的代表作品《山水》《墨马》两两比较,清晰呈现两者的师承关系及画风继承。
“上海时期”则以何氏1928 年《山水》原作和一则《怡如庐中何香凝广征画品》剪报共同牵出何香凝从广州移居上海之后的艺术实践,重点带出何香凝西行状游前后两档重要展事:1929 年旅欧之前途经南洋举办“新加坡华侨筹助仲恺农工学校书画展览会”,1931 年欧游回国在上海举办“抗战救亡义卖画展”。当时《新加坡画报》《上海画报》对两档展事作连载报道。8 张何香凝在菲律宾、马尼拉,回国游轮上的生活照片与刊物文献一同再现了这段何香凝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行旅时光。在她出游至归途的这个时期,国内相继出版了第一、第二部珂罗版的《何香凝画辑》,收录何氏1910 年代至1930年初约20 年间的作品。新加坡学者姚梦桐在《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中重申了何香凝南洋之行与南洋画展对新加坡战前美术发展的时代意义。这一批文献也为学者研究何香凝西行提供了重要史料。
在这个展区中,重点呈现何香凝1929 年参加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美展,1935 年参加第二届中国女子书画会的展览,并将何氏的原作与参展作品的图像进行比对。这个阶段是何香凝创作的高峰,她最拿手的是山水画,虎图次之,梅菊一类产量最丰,也是售卖最好的作品,如她在1934 年《梅》所款题:“沽酒莫愁阿堵物,石头城下卖梅花。”何香凝以画为业的现实光景,还从民国记者的一系列采访报道中得到印证。其中一件特别的展品,上海鲁迅纪念馆藏1937 年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委员会给何香凝开出的“伍拾圆 捐款收据”。另外展柜内还有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藏1944 年何香凝写给女儿廖梦醒的两封家书,悉数交代卖画款的分配。这些原始文献为说明何香凝于民国中后期依赖画业收入支持生活和社交,提供了充分的物料读本。
何香凝1924 年在广州引领妇女运动,直至1927 年正式当选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她这年任职的肖像与报道被放大置于展区的重要位置。女性运动和平权思想起源于广州,发展壮大则在上海。与大幅肖像配合的材料是1926——1947 年间广州、上海两地报刊中何香凝署名发表的演说及文章。其中14份具有先锋思想的报告材料,以剪报的形式呈现何香凝引领于时代的女性思想与实际行动。展览也让何香凝自己发声。何香凝作《我们的目标》激励全国女子参与抗战救亡时说:“国权丧尽的时节,我们尚有什么女权可争,现在我们唯一要争的是救亡权。”[4]以其原话植入展墙,点明主题精神。该展区最后以曹国智1947 年出版的《何香凝先生与中国妇女运动》,就何香凝民国时期妇女工作进行总结和评述。又以何香凝女性思想研究专家蔡瑞燕的访谈视频辅助解读。
第二展厅一改前厅深灰色的沉重色调,以明媚、雅致的淡青色作为第二章“海纳百川 异彩纷呈”的主色调,象征上海的包容、多元。“上海”作为一个场域概念,既承接着第一章何香凝1930 年代寓居上海的日常生活和妇运事业的时代环境,又预示着创立于上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成员的生活环境。展厅以民国黄浦江景观照片为界,合理实现区位内容的逻辑转换。第二展厅开篇以1932 年俞逸芬《画苑闺秀谭》剪报图像作引,承上是评述1931 年何香凝组织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上的女画家群体日益壮大,渐成艺界新潮流,启下便是女画家与中国女子书画会各类展事报道材料。顺接以老照片的设计,再现1934 年中国女子书画会首届展览开幕,会员合影的场景,引导观者进入了上海女画家的故事集。
中国女子书画会是沪上女画家自发创立的美术社团,标志着女画家主体意识的整体觉醒。1935 年《妇女月报》记:“中国女子书画会,是由一般爱好艺术的妇女们组织而成。听说她们唯一的目的是研究书画,预备将来替艺术界放一道异彩。”[5]展墙上植入的这句话点明了中国女子书画会的艺术定位和价值取向。也在这一年何香凝加入画会,参加第二届画会特展。虽是创设于上海本地的画会,但随着社会接纳度的提升,女性会员遍及全国,4 年间最高峰近200 人。在以男性为主体的艺坛,女画者逐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每年举办画展是女画者艺术发言权的一种象征。画会的艺术水平和组织性,也是其他地域社团难以比拟的。这一章聚焦在画会创社会员冯文凤、顾飞、李秋君、陈小翠、吴青霞、周錬霞、陆小曼的作品和文献,以群像形式呈现1920 年代至1960 年代女画家的“艺业与职业”。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多地女子艺术培育逐渐发展壮大,女性接受画艺的培育并以此为职业已不罕见。其中部分以艺术为职业的女性获得艺界认可。如冯文凤,出身优渥,承继家学,13 岁对客书屏,16 岁在香港开办女子艺术学校,自任校长和教授,移居上海后再办女子艺术学校。书法、水彩、图样设计等多个艺术科目由冯氏负责传教。多年从事艺术教育的经验令其得以担任中国女子书画会首任会长。展览中陈列出冯氏的两份教学讲义《水彩家的水彩箱》《图画放缩机构造法》,与广东美术馆藏隶书对联拓片共同展出。
顾飞,为黄宾虹女弟子,展览中以顾飞散文《我与绘画》自述在艺术道路上从懵懂到顿悟,从自学到拜师,从对自我天赋的悦纳,到弃职学艺,以画为业。浙江省博物馆藏黄宾虹晚年寄赠顾飞的《论画长札》,将自己对山水画的见解和品评悉数传授顾飞,是对她的认可和珍视。配合这件长札展出的是顾飞致黄宾虹的两封信札。有别于画理的探讨,信中尽是顾飞悉心为尊师操办画展事宜、装裱确认、售画情况及款项交办的日常沟通。顾飞追求绘画缘起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平淡、天真的山水画创作理念承袭于黄宾虹,日常当中也饱含着对尊师的恭敬。
李秋君,家庭优越之余,日常也忙碌于画会会务及妇运工作。如1936 年《画家李秋君女士访问记》所见,李秋君不仅负责主持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务、每年一届书画会展事的筹备、会员联络与会费收缴等,李秋君与何香凝的结识始于1930 年代初寒之友社成员于右任的介绍,此后李秋君成了何香凝妇女事业的忠实追随者,协助何香凝操办妇女抗战慰劳会。何香凝美术馆藏1954 年何香凝、李秋君等人合作的《青山红树》,款题记述了1930 年代何、李等沪上画家的亲密交往。
吴青霞,1928 年自常州移居上海,开业授徒,以职业画师自居,花卉、翎毛、山水、人物无不精妙。刘海粟称其为“常州女将军”。展览以若干上海旧报刊刊登的山水画、仕女图像、采访等文献,配合上海中国画院收藏的《芭蕉仕女》《芦雁》,展现吴青霞早年积极谋生于上海的职业女画家形象。生前采访视频和画册图录补充体现了吴青霞对画业与生活的个人理解。
民国女画家不绝于国画创作这一面,诗词、歌赋、散文不逊于画艺。如陈小翠和周錬霞,一个以戏剧创作为主业,一个以诗词创作为主业,在各自的文学研究上成绩斐然。展览将此两位女作者置于同个展区,从文献的途径反映彼此诗歌酬唱及日常交谊。展区以周錬霞为界,将其散文、诗词文献置于第二、三展厅转折处的展墙,将陈小翠与周錬霞、陆小曼的友人关系作为展区内容转换的衔接。
陆小曼的故事顺着周錬霞而来,置于第三展厅的第一个展区。“不可不看的风景”是刘海粟对陆小曼的评语,也是这个展区的题名。陆小曼是民国大众刊物的宠儿,戏剧、绘画、诗词、文学、翻译使她被奉为时代的偶像。至今仍在民国刊物上留存着大量关于陆氏的图像和报道。该展区首先以浙江省博物馆藏1931 年《设色山水长卷》和上海中国画院藏1961 年《黄山清凉台》展现陆氏山水画的师承与造诣。前者因大量文化名人的题跋以及胡适与贺天健的不同艺术观点的对话而使这件技法拙稚的山水长卷颇负盛名。经过30 年画艺磨炼,陆小曼晚期的画风已非常接近其师贺天健。
1926 年陆小曼与徐志摩定居上海。在她学习绘画之前,她热爱昆曲,活跃于专业舞台,青衣、老生、小生的多个扮相剧照刊发在1926 年至1930 年间的《上海画报》。1927 年8 月3 日的《上海画报》显示,陆小曼曾作为“上海妇女慰劳会”剧艺大会的骨干演员,在8 月5 日这天将与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思凡》《汾河湾》《少奶奶的扇子》三部剧目。该展区将陆氏8 幅剧照图像集中展示,又将时人对陆、徐二人戏剧功力的辛辣评价植于墙体,表现出民国大众文化的娱乐氛围和文人互为戏谑、调侃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民国时尚偶像与流行文化的一个侧面表现,也是陆小曼“不可不看的风景”之一。
徐志摩逝世后,编辑出版徐志摩的书稿、日记成了陆小曼的日常寄托,因此有了《序志摩日记》等忆述文章和出版物。还有《泰戈尔在我家》《中秋杂感》等散文,均是陆小曼寄托怀想又不失风雅趣味的写作。除了编辑出版的收入之外,画业也是陆小曼主要的生活来源。因此民国报刊上常有陆小曼的画展报道、山水作品和销售广告。“陆小曼”即是民国流行文化的偶像及符号,也是流播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女性形象。民国刊物为满足大众对名媛生活的想象和追捧,将其塑造为有别于日常的一道“风景”。1934 年徐悲鸿作炭笔素描《速写陆小曼像》,则让观者看到了一个写实的,卸去了媒体包装的女性形象。
第三章“欧风东渐 度越古人”聚焦于1920 年至1970 年间现代新女性的艺术探索,展现了方君璧、杨荫芳、关紫兰、郁风四位独立探寻艺术道路和追求自我表达的女画家。留学巴黎的方君璧,留学日本的杨荫芳、关紫兰的油画、素描作品均出自广东美术馆。她们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行至广州,分别与广东画家高剑父、高奇峰、丁衍庸等人展开艺术交流,杨荫芳为方人定妻子,期间往返于广州和东京。作品呈现出她们对现代艺术与本土文化符号结合的创新性。广州、上海分别是现代女性意识萌芽最早及发展最快的地方,是现代中国得风气之先的重镇。该展区将具有海外艺术教育经历和国际视野的新女性交集于“广州”,她们该时期的创作及艺术观,已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广东现代艺术探索的风潮。同时,上海的《东方画报》《中华月报》《艺风》《良友》等杂志也频繁刊发她们的作品、展览活动和艺术评论。
展览最后以“革命女画家 致敬何香凝”为题再次强调女性精神在整个20 世纪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中的独特价值。故事再次从广州切换到上海。郁风1937 年文章《记何香凝先生》及“何香凝速写”记录她在上海所见所知的何香凝,开启她与何香凝的历史交织。展览以历史照片、著述、书题等实物文献铺陈郁风父女与何氏母子在1930 年代的革命交谊。探讨20 世纪女性艺术时,郁风也是一个具代表性的案例,她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艺术女学生到左翼女青年,再到革命女报人所经历的角色转换,以及她坚持以贫苦女性为对象作艺术观察和纪实创作,宣传女性的自救与救亡,作为自身对女权思想的人生实践。郁风、何香凝两位革命女画家的个体交织,伴随着20 世纪中国女性艺术运动的发展。
三、从时间线到故事线:展览叙事转向与权威化解
1979 年“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以时间为轴线,展出何香凝1910 年至1965 年期间创作的92 件精品,呈现了何香凝革命与艺术互为交融的一生。展览由中国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是何香凝1972 年逝世后第一次回顾展,由时任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郁风主持。展览调用了画作、诗词、历史照片等素材,将何香凝的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以视觉的形式作出合理的注解。郁风在《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随笔》一文回顾了展览的内容和形态,作品按时间序列铺陈,何香凝的诗词穿插其间[6]。其女性书写饱含着一位革命者的愤慨激昂,又隐含着个体身份的更迭。从廖仲恺妻子、孙中山日本时期的女管家、留日女学生、鬻艺救国女画家、仲恺农工学校女董事、训子杀敌革命母亲等,各阶段身份的转变伴随着艺术家创作风格、题材及内容的更新。可以说,展览试图通过艺术家身份更迭的提示,在其艺术实践历程中串联起的这位画家的艺术革命史。
上世纪80 年代初及90 年代末,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何香凝美术馆分别在广州、深圳开馆。原“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的展品分别拆解存放。诗词、书信等文献由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收藏,以家族史形态展示。何香凝的画作、照片保存于何香凝美术馆。原“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中的故事性被抽离,展览叙事分化。馆主照片精选后集中在独立展厅按时序排列,表现馆主“社会活动家”的一面;绘画作品按“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展品清单所列,演变为“何香凝艺术精品陈列”的常设展,讲述馆主“画家”的另一面。陈设上,两者各自独立。整体来看,两者合并构成何香凝“集社会活动家与艺术家于一身的伟大女性”的历史定位。
“何香凝艺术精品陈列”的生成,依据原“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的展品清单而来,以文物为主导,按照作品创作先后依次摆放。虽可被解读出一些叙事性,但缺乏展现作品被创作产生的动因和原生性的背景。作品的逻辑关联主要在于它们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分期。观看的次序遵循作品艺术风格发展的客观性,但展览自身的诠释受到制约,观者对展览的释读也受限于时间的维度。
以时间轴线作为展览的架构,是观者较为熟悉的一种阅览习惯。作品的秩序感,使展览具备了一定的叙事性。观众对时序的直观体验,容易从内容中获得解析,也无需调用过多的知识储备。久而久之,在这套“程式化”的视觉逻辑的培养下,经验性解读形成一套固化的叙事系统。单一叙事进而衍变为叙事的权威,这是因叙事的单一以及解读的固化共同制约,造成了展览叙事的困境。
近十年,“讲故事”被引进到展览策划并广泛运用,是一种有助于展览增加故事性并调动观众情绪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传播策略,还是一种以观众体验为出发点的策划目标。博物馆界纷纷将“讲故事”作为展览叙事转向,加以推崇。有选择性的叙事策划虽是策展人的个性化表达,它仍需建立在材料与主题、主题与价值之间的客观性,作为以传播为主导的艺术性处理。“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便将叙事作为展览建构的方式,在“女性艺术”主题下,12 个“故事”游走在广州、上海两地,在1910——1940 年代、1920——1960 年代、1920——1970 年代三个交叠的时段中推进。展览将丰富的子叙事按组织结构纳入,建立主题-并置结构的叙事方式,各子叙事彼此独立又围绕主题进行。通过材料选编和秩序建构的叙事化安排,展览的可读性及整体的连贯性在主题之下获得了统一。
原作、手稿、档案等藏品和文献的信息,如何在“故事”所营建的时空场景中,再现一个令观者得以“进入”又贴近历史的空间。首先,从策展人的思路出发,通过文献材料的编织,引导观者去“见证”不同时空场景下的个案(即女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其次,在建构叙事性展览的过程中,利用访谈、纪录片等影像素材为观者提供一个第三方视角,以他者陈述事件并予以解析,观者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对材料加以转化,形成新的认知。再次,借用女艺术家自己的语录,以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作旁白式的解说。通过植入展墙的形式在浏览过程中予以观者视觉提示。原作、档案、影像、语录等展品都是讲述这些“故事”的历史物证,它们共同为展览发声。
叙事转向拓展了“故事”在展览中的复杂性。前文提到1979 年“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叙事中隐含主线(书画创作与革命人生)与辅线(诗词书写与女性身份)的交叠,以作品时间序列建构的“故事”,也隐含着叙事者(郁风)个人的立场和视角。当辅线被剥离之后,仅剩作品的铺陈,便造成了叙事者在展览中的“失语”。单一叙事的展览限制了第三方对“事件”的解释权,形成了叙事的权威与解读的固化,进而限制他者的介入与阐释。那么,将“故事”置入情景和空间,引入叙事者,为“故事”带来不同角度的解读,以突破叙事困境。而叙事者是多变的,它可以是策展人的思维框架,也可以是切合历史真相的档案材料,更可以是某事件的集体发声。
在“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女性艺术运动图景”的案例中,通过“故事”在不同场景和时空中的推进以及多重叙事者的切换,展览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被解读的可能性。观众也在接收不同信息的同时,建构着自己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