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自然与人文之间漂移的地理学家
2023-10-08唐小兵
唐小兵
阿伦特曾经说过,一个有教养的心灵应该是懂得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而这样的人她也常常称为人文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理学家段义孚以其构建的地理世界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彰显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人文主义者形象。在这个人文主义者形象之外,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世界主义和自然维度的变量。段义孚先生去年过世,我才从一些零星的纪念文章中知晓这位人文地理学奠基人的生命片段,偶然购买了他的两种代表作《恋地情结》和《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在教学和研究之余,尤其是在旅途中或地铁上,我经常随身携带其中一种翻阅,常常啧啧惊叹于这种面向自然、历史、文学和自我的地理写作的开阔与深邃,进而改变了我对于地理学家只会将所有的自然世界作为一种冷冰冰的存在客观分析的刻板印象,原来地理学也可以是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关切和真切的生命体验的学科。这种既拥抱自然世界,又无限返回人文世界的地理学作品,对于我这样一个游荡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地带,同时又经常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畅想自然生活的读书人,无疑是一种很有治愈感和启示性的文本。

打开段义孚的作品,就像同时在打开这个将黑暗与光明、崇高与卑下、动荡与静谧等融为一体的自然世界。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仿若在与古往今来的哲人围炉谈话。段义孚就像一位克制、内敛而博学的领读人,带领我们去读解自然、历史、文学与人性的奥秘。段义孚的作品具有一种迷人甚至让人迷幻的光泽,这种光泽既来自理性的剖析,又来自情感的代入,这就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必须同时打开头脑和心灵,以前者去追随分析的进路,而以后者去感受作者的生命体验,进而获得一种深刻的共情。这在我多年的阅读生活中,无疑是一种极为新鲜的体验,他的书似乎从任何一部分进入都不会让你觉得跳宕或脱裂,在任何一部分停顿也不会让你觉得突兀或残缺,甚至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沈从文先生以前讲过所谓“抽象的抒情”,我们也经常见到那种泛滥无归的抒情或者莫名其妙的呐喊式抒情,而段义孚对待自然世界的抒情态度,是一种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抒情。这种抒情是有格调和内涵的,更是有着充分的知识考古和野外考察依据的,所以是一种扎根大地又仰望星空的抒情。比如,他曾经独创性地提出“恋地情结”的概念,这对于安土重迁而又经常将自我安顿在乡愁之中的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很容易引发高度情感共鸣的。段义孚如是诠释:“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也许人类对環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美感可以是从一幅美景中获得的短暂快乐,也可以是从稍纵即逝但豁然显现的美之中获得的强烈愉悦。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抒情源于审美,我甚至可以笃定地认为段义孚是一个审美主义的地理学家。他在回顾《恋地情结》《美好人生》和《穿越诡异与雄奇》三种著作时特别提及了审美的若隐若现及其赋予的内在意义:“唯美主义和审美里都包含着‘感受的意思。去感受等于去生活,由此可以变得充满生机活力。感受能化为生命,反之亦然,若将感知消灭,生命必然沦为残丝断魂。而化为生命的过程始终是深刻的,它源于对世界的审美,以及渴望增添美的冲动。当美好的词语化为深刻的思想,美丽的装束变为建筑的艺术,当这些事物统统加起来成为人类的文化时,难道它们不正一往无前地朝着那更兼收并蓄、更易于理解的生命形态跃进吗?”(《我是谁?》,志丞、刘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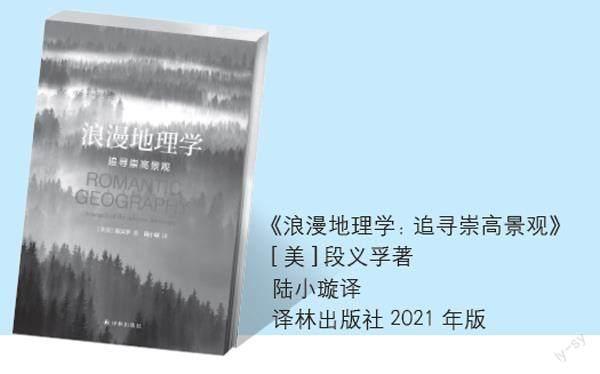
段义孚在《浪漫地理学》这本代表作中就对于自然豁然显现的美进行了细腻而深刻的描摹,他对于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习焉不察或者感到恐惧的自然景观的深描,让我们突然有了一种抽离世俗而又重返自然的“灵魂的震颤”之感。按照古希腊的说法,哲学源于惊异,而我们在阅读段义孚的作品时,也可以认为他的人文地理学同样也是源于对于自然、历史、文化和自我的惊异。段义孚就像一个游离于整个世界,却仍然心系故园且永葆赤子之心的人,让我们感觉到一种天真和浪漫。他所有的环境书写中都弥漫着或者渗透着人文主义的向度,因此这是一种有着人的观察、感受和体验的地理学,更奇妙的是,他对于涉及这些自然环境的来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或者托马斯·曼、华兹华斯等大师级的作品中的相关叙述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可以无缝对接地展开论述而又不让读者觉得是一种炫耀,他的态度与其说是夸耀的,不如说是克制、内敛和谦卑的。段义孚构建了一个人文地理学的小宇宙来安顿自我的身心,但这个小宇宙同时也是对外敞开的,我更愿意将他的作品视同对被抛掷在这个失序的世界的每一个人的一种诚挚的邀请。他在《浪漫地理学》中对于山、海、森林、沙漠、冰等自然存在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这些诠释既让我们心存惊异,同时又让我们有一种瞬间被治愈的安顿感。比如他从对山的诠释延伸出对高和低的独特理解:“‘高确实暗示着智慧和精神,而‘低则暗示着身体与物质。然而,一种相反的理解同样是可行的,比如‘高可以暗示一种即将经历衰落的孱弱与冗杂,而‘低则可以暗示健康与活力。”
段义孚在热带雨林和沙漠之间的喜憎理由也让人莞尔:“我现在比以前更清楚沙漠对我而言为何会有如此魅力了,不仅仅是因为它清晰的轮廓和方向感,还在于它的荒芜,它的空缺,能让我把性爱、生命与死亡这些元素从生命中暂时抹除。相反,热带雨林有令人感到窒息的生长、繁衍和挣扎,腐烂的气息逼人心魄,它带着辛辣的性欲渗进了我的意识里。”在讲述人类对于原始森林的态度时,段义孚在梳理了森林的历史变迁和人类对森林的态度之变化后,很敏锐地捕捉到了中西文明对于原始世界的不同态度:“中国人一度向往‘黄金时代,那便是其将往昔浪漫化的方式。在道教的影响下,那些在强大而辉煌的帝国供职的儒家朝臣,开始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转而寻求回归朴素的生活。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怀旧也很少包括对未开化或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他们并不钦羡野蛮人身上那种动物性的活力和野性的优雅。欧洲的作家和艺术家却有所不同。他们已然厌倦了那种与叮当的茶杯声和白色的遮阳伞相伴的生活,而渴求那种存在于原始人身上的生命活力。”(《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

空间与地方是段义孚学术写作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他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经验空间、空间能力、建筑空间、神话空间等,也讨论了人类对于故乡和地方的依赖感是何以产生的,进而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如何以及应该如何理解空间和地方。书里充满了各种隽永的金句,比如“对时间的意识影响了对空间的意识”“物体可以让时间停泊”“在有目的性的活动中,空间和时间逐渐以思索性和积极性的自我为中心”等。可见在段义孚的笔下,空间和地方不再仅仅是一个物理性或地理性的存在,而成为主体性弥散的空间,是召回乡愁和投注未来性的记忆储存之所,是一代代的人类在新的探索与怀旧之间沉潜往返的中间物。任何对于地方和空间的亵渎乃至摧毁,也就成了对于个人的自主性、完整性和尊严的冒犯。因此,这个地方在段义孚的思虑和想象之中,“包含着对城镇更广泛的实质,甚至比邻里、家园和房屋都蕴含着更广泛而丰富的内涵”。而空间更是“意味着移动、行动、自由、潜力和未来,还意味着生命和对复苏的感知。它是一种知觉(aesthesia)。之所以我能在人的身上感受到一份悠然自得和轻松愉快,是因为我总能发现人类在移动和空间上所取得的经验,这也就是所谓的‘生活”。

这种跨文化的洞察力和对于熟悉事物的重新陌生化能力来自段义孚广阔的阅读和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生命体验。我终于可以抵达撰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了,即阅读最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段义孚短小精悍而又言近旨远的自传《我是谁?》引发的感触和思考。在我这二十多年读过的上百种回忆录中,段义孚的这本薄薄的自传是最为独具一格的,它不是作者对于亲历和参与事件的记录(段多次强调他的记性不好,对于很多青少年往事的记述依赖于他的兄弟姐妹的补充信息),也不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更不是一个在北美学术界扬名立万的人文地理学之父的“创业史”(我马上就想到了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迥异的风格)。他的这本自传涉及的“事情”极少,言说的“心灵”和“情感”极多,却并不因此让人觉得腻烦和琐碎;他面对自我心灵的无情解剖和真诚探索,尤其是如何走向自我救赎的地理学之路的重构,深深地触动每一位读者。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度过。我读过段义孚的自传之后,却在寻思这种过度反省的人生究竟是如何度过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早就意识到自我的性别取向在人类社会中属于少数边缘甚至是异类的华人,他如何处理自我的生命在高度角色化的家庭、家族和族群文化中的安置?段义孚对于自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妙的解释:从年少时候的公共性到成年之后的私人性(“我的人生是从童年的公共世界迈向了成年的私人世界。所以我的成长经历就像从宇宙走向了炉台一般,而不是反过来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战争和动荡,以及后来随外交官父亲的全球漂移,客观地造成了他的成长史与外部世界是深度衔接的,少年时代的段义孚在私人生活里能够窥见和感知世界的涌入,尤其在父母安排的款待各路名流的家宴之中;而在成年之后,因为个性的内敛和性别意识的困扰,他将身体和心灵更多地安放在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单身状态之中,更投放到自然和文化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世界缩小到了学术界的一个小角落里。尽管思想的视野不断扩大,但我认识的人只是那些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里取得世界级成就的人”(《我是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段义孚是一个面向自然的世界主义者,他对于这个地球上各种自然生态的观察、感受和书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知世界;但与此同时,他对于私人生活那些极为珍贵的片段、细节和场景倍感珍惜,比如他对母亲的深深依恋:“在我看来,她不谙世故,尽管她尽职尽责地参与了我父亲的外交和政治活动。她不像父亲那样喜欢公共场合,更喜欢远离聚光灯,热爱生活里那些简单素朴的事情,比如给孩子买衣服和鞋子,买下午茶,买圣诞树和装饰品之类。”(《我是谁?》)
段义孚在自传第一章就提及了写作的切入点:“我是一名中产阶级的华裔,但一生都单身,因此不得不游离于华人的圈子之外;我还是一个地理学家,但在这個学科里也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同于大多数地理学家,我的景观是‘内在的(inscaps),更多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景观。”从这本自传来看,段义孚是一个矛盾体,他推崇有道德勇气和敢于表达自我观点,以及强健明朗的人格,而他自认为是一个躲在阴影之处冷静客观地自我剖析的人,就像近代文化史上的吴宓和夏济安一样,他所认同、思慕的自我与事实上清晰意识到的自我存在明显的鸿沟。在根本上无法接纳自己就会产生严峻的身份认同危机,早慧的段义孚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我一直纠结于内心的个体情结—与他人的分离。它时常让我活在骄傲与痛苦相互冲突的情感狭缝里。‘我是谁?这个问题,成了我如何才能被社会认可的根本问题。”承认的焦虑像幽灵一样撕扯着他敏感的心灵,尤其是性别取向给他带来的困扰:“它使我无法履行传宗接代的任务。单身是我的命运。在尚无文字的社会或在由亲缘关系维系的社会里,一直单身的状况是遭人憎恶的。剩男剩女会被视为怪胎,还有可能被当作巫医、神棍来对待。”这种恐惧和负疚交错的情感,也长久地影响着段义孚的自我认同和生命处境,也正因为此,段义孚一直对于弱者、边缘者和无助者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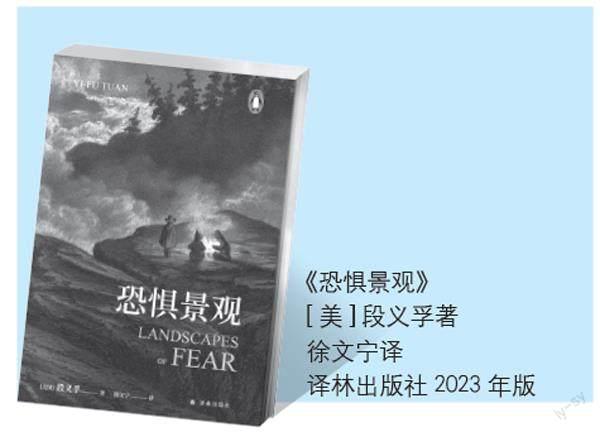
不过,他最终找到了地理学,实现了自我救赎。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如此写道:“在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不以权力和声望为基础的世界,并渴求真的有那么一个实体的小圆孔,能让我们洞见另一个世界的现实。”人文地理学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体的小圆孔”,他在阐释找到地理学之后的亢奋和犹疑时如此写道:“如果离开了宇宙,或准确地说,离开了和谐自然和人类极致成就所带来的喜悦,我的人生将变得悲惨,活不下去。所以,地理学拯救了我。我可以自然而然地看见外面世界的严酷和丑陋,就像窥见我自己内心世界里的混乱无序一样。我甚至相信,自己的悲惨,自己无法改变的社会次等身份,以及外人对我的接纳,都得以让我洞察人类的悲惨,特别是那些零散破碎的少数群体里的悲惨景况。但是,我却不愿久待在那些阴影里—包括自己内心的阴影和世界的阴影。而我是否又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是否太过分沉溺于宇宙之美了?我是一个逃避主义者吗?我是否常把自己放在了一束光里,去表达人性中那些可能是最乐观的一面,并提醒周围总在关注事物阴暗面的饱学之士们:这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美与善的事物?其实我并不知道,又有谁知道呢?”将原本可能饱受折磨甚至噬咬的孤独生命活成了一束光,段义孚把自己作为方法,把人文地理学作为桥梁,以这种回忆录的形式展现了个体的精神生命是如何实现自我突围的。他对历史学的认同,也让我这个从事历史研究的读者深感喜悦,地理学主要是处理空间的学问,他却渗透进了时间的维度,而历史学是处理时间的学问,所以才强调要行万里路。段义孚是将空间时间化(依托自然景观进入历史和文本的脉络)、将时间空间化的大师级学者,在时空纵横交错的十字架上,他实现了自我的灵魂救赎。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几乎所有中国读书人的梦幻,青壮年时代的段义孚因为家庭和学术的原因早已实现,他正是在这样一个人文之旅中构建了他的人文地理学的王国(尽管他看上去总是像有点忧郁乃至孤独的小王子),这也是他对这个处于至暗时刻的世界最好的馈赠。他也在这部像心灵史一样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对待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漂移的历史”,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段义孚的地理学写作为何转向内在具有关键的引导意义:“在五十岁的时候,我体内的机理肯定发生过一次变化。从那时起,大地上的壮观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高耸入云的大厦等,都无法再激起我的兴奋感了,它们变成了我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我的兴趣点也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进入中老年期,那种想要四处旅行、看大千世界的冲动消失了,因为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世界,尽管不是全部,但我可以问:再去更多的地方意义何在呢?难道我真的需要去看看月光下的泰姬陵或朝霞里的喜馬拉雅山吗?没有这些经历,我的人生就不完整了?进入中老年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这样的美包括上方的天堂和地上的人类个体,而不再是那些中间尺度的可爱事物—社会、景观和地方了。”正因为此,段义孚的精神生活得以扩展开来,自我审视让他更加明白自己是谁,而审视外界则让他越发认清了外部现实的本质,他成了他所期待的“精神生活的历史学家”,最终地理与历史在他的身体和灵魂里实现了人文主义的汇合和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