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
2023-10-08王震中
王震中
古史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学派。在古史辨中,一百年前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四个打破”最具理论特色。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反思古史辨派,我认为它有贡献亦有局限。当我们反思古史辨派的贡献和局限的时候,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理念也会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一、顾颉刚“层累说”和“四个打破”的提出及其影响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简称“层累说”)的观点是1923年在胡适主办的《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名称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所以取名《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是因为之前顾颉刚与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先生通过书信来往而讨论经书辨伪问题,1923年,胡适请顾颉刚给他主办的《读书杂志》写稿,顾颉刚因给钱玄同的信寄出两月而未得回音,就把他寄给钱玄同的信中论古史的一段抄出,并加上按语,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也想借此逼一逼钱玄同给他回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说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60页。。
顾颉刚说他在整理《诗经》《尚书》《论语》里的古史传说时,“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着看,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閟宫》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典》的‘禹拜稷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2页。。
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还写道:
至于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第63页。
此文刊出后,先是钱玄同在《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发表了长篇回信,认为顾颉刚关于古史的意见“精当绝伦”,并谈到许多六经的真相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他不同意顾颉刚所说的对禹的推测,因为《说文》中从“禸”的字,甲骨文、金文中均不从“禸”,如“禽”“兽”“萬”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也”之“禸”字,大概是汉人据讹文而杜撰的字。接着,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在《读书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读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针对顾颉刚提出的“东周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推知的”观点,他也以《诗经》为文献依据,大量引用《诗经》中的《长发》《閟宫》诸篇驳斥顾颉刚对禹的解释,认为在《诗经》里禹丝毫不带神秘意味,对于顾颉刚关于禹从何而来的推测,刘掞藜认为是想入非非任意编造附会。其对顾颉刚关于《尧典》在《论语》之后等观点,也进行了辩驳。《读书杂志》第十一期上还发表了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的文章。胡文也对顾颉刚进行了质疑。
针对刘、胡二人的批评,顾颉刚又写了长篇文章《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第十二至十六期上。在该文中,顾颉刚论述了禹的天神性、禹与夏的关系、禹的来源、尧舜禹的关系,以及后稷非舜臣、文王非纣臣等问题,还提出了“四个打破”的问题。
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必须打破四项传统观念: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认为“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认为“《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兽与神混的,如秦文公梦见了一条黄蛇,就作祠祭白帝”等等,举不胜举。所以,这种史“决不是信史”。“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这就“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9-102页。。
这“四个打破”可以说是“层累说”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这“四个打破”才能更明确地说明中国古史之层累地造成说。
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轰动学术界,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1926年,顾颉刚以《古史辨》为书名,把学术界自1923年以来有关古史和辨伪讨论的论文编辑在一起出版。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开始,至1941年止,十五年间先后出版了七册,发表论文三百五十余篇,对古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讨论,古史辨派成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学术思潮。胡适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即发表评论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5)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3页。郭沫若在1929年评价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4页。。
王汎森评价说:古史辨运动“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最大意义是使得过去凝固了的上古史系统从解榫处解散开来,使得各各上古史事之间确不可变的关系松脱了,也使得传统史学的视野、方法及目标有了改变,资料与资料之间有全新的关系。故即使不完全相信他们所留下的结论,但至少在传统古史系谱中,已经没有任何人或事可以安稳地被视为当然,而都有遭遇到怀疑或改写的可能”。“综括地说,这个运动使得史学家们能有用自由的眼光去看待上古史的机会”(7)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295-296页。。
西方史学界对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潮也是广泛称赞,如美国史学家施奈德说:“顾的反传统主义乃革命的一部分,他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同样地也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贡献。”(8)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二、“层累说”和“四个打破说”贡献与局限相交织
今日我们重新思考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既感到它对摧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旧古史体系有积极的一面,又感到事情并非顾先生考虑的那么单纯。
顾先生对“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之辨,其方法论是从古书辨古史,即从古书成书年代的先后来推论古史形成的过程,因此他得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是“层累说”的关键,他由此不相信“三皇五帝”古史系统,有其自洽的一面。但是,三皇五帝系统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历史文化背景是什么,顾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然而却很有深究的必要。
(一)“三皇”形成过程的反思与“三皇”所代表的时代
“三皇”有不同的组合,这些不同组合确实如顾颉刚先生所言出现在秦以后。但是,被组合在三皇中的一个个具体人物(或可称为“上古诸帝”)及其事迹却出现在战国时期。也就是说,组合的三皇与被组合到三皇里的一个个上古诸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出现在秦汉以来,而后者出现在战国诸子的论述之中,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加以区分。
作为泛称的“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以及《庄子》和《吕氏春秋》等书。《周礼·春官宗伯》云:“外史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9)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7页。《庄子·外篇》中的《天运篇》说:“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10)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7-168页。《吕氏春秋》的《禁塞篇》曰:“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11)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141页。《吕氏春秋》的《贵公篇》《用众篇》《孝行篇》中也都提到“三皇五帝”,但都如《禁塞篇》所言,只作泛称。三皇五帝到底指谁,上引《周礼》《庄子》《吕氏春秋》并未指实,而秦汉以来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却有多种组合模式,情况甚为复杂。
关于三皇,根据我的统计,秦汉以来的三皇至少有七种组合模式:(1)天地人三皇说(《尚书大传》);(2)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春秋元命苞》);(3)燧皇、伏羲、女娲为三皇(《春秋命历序》);(4)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白虎通·德论》,另《礼含文嘉》排列为“宓戏、燧人、神农”);(5)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通鉴外记》);(6)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礼稽命征》、孔安国《尚书传序》、皇甫谧《帝王世纪》);(7)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白虎通·德论》)(12)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页。。
以上七种说法中,第一种“天地人”三皇说,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1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2页。这里的泰与大同音,大字像人形,故有学者提出泰为大之音借,大为人形之讹(14)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44页;翁独健:《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跋》,《古史辨》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9页。。与“天地人三皇说”相关的是“天地人三才说”。《古今注》载“程雅问董仲舒曰:‘自古何谓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15)崔豹撰,牟华林校笺:《〈古今注〉校笺》,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201页。。“三才”指“天、地、人”。《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16)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75页。通观中华思想文化史,“天地人”三皇说是一种哲学式的构思,它与由人组成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不属一类。
七种三皇说的另外六种,究竟以哪三人为三皇,说法各异。对此,诚如东汉末年的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所言:“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17)王符:《潜夫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王符这段话所透露的无可奈何与无所适从,是当时人们构筑三皇古史系统时的实情。
作为学术反思,我认为顾先生“层累说”提出组合的“三皇”出现在秦汉以来的文献是有贡献的。但是,三皇各种组合中的一个个“人物”(或可称为“上古诸帝”,或可称为“三皇式‘人物’”)却出现在战国时期,在诸子中时有表述,并非从秦汉才开始叠加上去的。此外,对于某些三皇式“人物”,我们可以把他们作为历史进步的时代性符号或时代性名词来对待(18)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第12页。。
我这样说的理由有二:其一,周秦时人在说到上古诸帝时,有时将他们作并列处理,但也有很多地方是把他们作为一种历史的推移和递进来讲的。如《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说: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19)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40页。
《庄子·缮性篇》: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20)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180页。
《商君书·更法篇》: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21)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页。
《风俗通义》:
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五霸黜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22)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22页。
《淮南子·氾论训》:
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23)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8页。
桓谭《新论》:
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24)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页。
可见,在战国时期人们所论的古史系统中,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以至于三王、五伯的这种排列,表达了一种历史递进关系。这种历史递进关系属于战国时期人们的一种历史观。我们今天在重建上古史时,对战国诸子有关我国上古历史的这种统括和划分,对这些古史传说所反映的历史阶段,当然应该是在辨析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学、人类学资料而加以利用。

例如《韩非子·五蠹》说: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25)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73页。
《庄子·盗趾》:
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26)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357-358页。
《易传·系辞下》: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卷,神而话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27)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21-627页。
在上述战国诸子对远古社会的种种推测与描述中,有巢氏不在三皇之列,但在《韩非子》和《庄子》等书中,显然是把他作为人类初期阶段的代表来对待的。此时人类混迹于禽兽之中,为规避野兽的伤害,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暮栖木上”(28)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第673页;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357页。。从这一角度来看,把有巢氏划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只是,作为人类初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在由猿转变为人之后,考古发现的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居住在洞穴之中的,人类在居于洞穴之前,是否有一个阶段是普遍居住在树上,现在还不能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实际上也很难印证。而考古学所发现的诸如河姆渡那样的干栏式房屋建筑遗址,其时代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离旧石器时代早期有百万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庄子等人在说“有巢氏之民”时,很可能是参照了当时“南越巢居,北朔穴居”的民俗,而把它安排在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初期,在今天尚无法确知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是否普遍地居住在树上的情况下,笔者不主张用“有巢氏”来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特征的概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误导。

燧人氏传说的文化特征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约在距今5万年至12000年前这一范围内。在笔者看来,燧人氏实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这一文化特征的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
伏羲的文化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民以猎”(29)尸佼著,汪继培辑,朱海雷撰:《尸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4页。,“作结绳而为罟,以田以鱼”(30)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24页。,“取牺牲以供庖厨”(31)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2页。;二是“制以俪皮嫁娶之礼”(32)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第63页。;三是“始作八卦”(33)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22页。。“教民以猎”可视为高级狩猎,而“以佃以渔”则属于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过渡;“制嫁娶”可以看作由“原始群婚”开始进入氏族社会的“族外婚”;“始作八卦”则说明已出现原始、朴素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所以,伏羲氏代表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年代约为距今1.5万年到1万年间。

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是否为真实的人物,我赞成徐旭生先生的说法。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就现在所能得到的材料去研讨,我们可以推断神农与有巢、燧人为同类,是战国时的思想家从社会进步的阶段而想出来的指示时代的名词。至于伏羲、女娲却同太皞、蚩尤为一类,是另一集团的传说中的英雄,他们的真实人格也许可以存在,也许并不存在。”(3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98页。
我们说“神农”是一个“指示时代的名词”或“文化符号”,也与我国史前农业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分布范围甚广,以及神农氏既可代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农业起源又可代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耜耕农业有关。


(二)五帝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
“层累说”和“四个打破”,也涉及五帝:一是认为五帝等诸帝都是神而不是人,这涉及所谓古史由神变为人的“人化”问题;一是认为五帝等谱系不是一系而是虚构的。古史神话的“人化”的说法,我认为是片面的,问题很多,对此我们后面再具体讨论;对《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所列五帝之间血缘谱系仅止于否定而不进一步深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破而未立”或者说是“破有余而力不足”。
关于五帝,也有不同的组合。一类是按照四时、五行、五方位横向排列的组合,一类是按照血缘的纵向排列的组合。按照四时、五行、五方位横向排列的组合的五帝,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等,如《淮南子·天文训》说:“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皞,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38)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第28页。对于这种以五行相配的五帝组合模式,有学者说它是战国秦汉时的“学者为落实五帝说的编造”,并认为“神学上的五帝说为人间的五帝说提供了理论依据”(39)叶林生:《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3、65页。。
其实按照四时、五方位横向排列组合的五帝,是把上古的诸帝按五行的五方位作了横向上的分布组合,因而是先有上古诸帝的存在而后才有与四时五行相配合的五帝。然而,这种五方帝的组合模式却可透露出组成五帝的上古诸帝原本有可能不属于一个地域族系,他们当来自不同的地域族团。
按照血缘纵向排列的组合的五帝,有三种组合:(1)《易传》《大戴礼记·五帝德》《国语》《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2)孔安国《尚书序》以少皞、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3)郑玄注《中侯敕省图》,“以伏牺、女娲、神农三代为三皇,以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六代为五帝”(40)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0页。。关于六人而称为五帝,郑玄的解释是:“德合五帝座星者称帝,则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实六人而称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4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第440页。这样的解释实属牵强附会。
诸种不同组合五帝的出现,包括列有六人而称为五帝的情况说明:第一,应当是先有“三皇五帝”这样“三”“五”概念的存在,而后出现用不同的古帝去填充它;第二,“五帝”与远古诸帝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五帝”可视为远古诸帝的代表或概括,因而应当把对“五帝”的研究置于远古诸帝的整体研究之中。
关于按照血缘谱系排列组成的五帝,表述最完整的是《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按照《五帝本纪》中的排列顺序,黄帝为五帝之首,其余四帝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儿子,即黄帝之孙。帝喾的父亲叫蟜极,蟜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与颛顼的父亲昌意都是黄帝的儿子,所以,帝喾是颛顼的侄辈,黄帝的曾孙。尧又是帝喾的儿子。而舜则是颛顼的六世孙。这一组合模式表达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现出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二是按照司马迁所述五帝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祖孙关系。笔者认为《五帝本纪》中五帝在历史舞台上称雄先后的时间顺序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认为黄帝与其他四帝即五帝之间在血统血缘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有疑问的。
从姓族来看,黄帝族有十二姓,以姬姓为主(42)《国语·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参见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53-354页。;颛顼和帝喾不知何姓,“颛顼祝融”属于一个集团,祝融有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都不在黄帝十二姓之列;帝舜姚姓,也不在黄帝十二姓之列,而且孟子还说舜是“东夷之人”(43)《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参见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7页。;只有帝尧祁姓,在黄帝十二姓之中。上古的姓与姓族表现的是血缘关系,由此我认为在司马迁所说的五帝中,只有黄帝与帝尧属于同一族系,而其他三帝与黄帝在血缘族系上不是一系。为此,我曾将五帝所表现出的先后时代关系称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实”,而将其一脉相承的血缘谱系称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44)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第14页。。
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文化星罗棋布,新石器文化遗址数以万计,创造这些新石器文化的氏族部落部族林立,即使后来组合成几个大的部族集团,各大族团之间起初也是互不统属,根本不可能是万古一系。司马迁等人把原本属于不同部族或族团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族属描写成一系的做法,因而需要予以纠正。
但是,当我们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把五帝之间说成是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中有虞氏和夏后氏等都以黄帝为其远祖的说法,例如《国语·鲁语上》说:“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45)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168-169页。从《国语·鲁语》和《礼记·祭法》看,黄帝与颛顼、尧、舜是有祖先关系的;周人禘喾,周人与黄帝都是姬姓,这样帝喾与黄帝也就有了血缘关系,由此而言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不就都有血缘关系了吗?也有学者把五帝之间的血缘关系称为“拟血缘关系”。《国语》和《礼记》都是战国时期成书的,那么,战国时期的人为何要把原本不属于同一姓族诸帝描述为同一血缘系统,并都以黄帝为远祖而进行祭祀呢?我认为这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融合的结果:当时华夏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强烈,已越过了自在民族,早已成为自觉民族(46)实际上,从西周开始,华夏民族就已进入自觉民族的发展阶段。关于由华夏民族由夏商时期的“自在民族”发展为周以后的“自觉民族”的过程,参见王震中:《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第190页。,需要一个民族标识,姬姓的黄帝族与姬姓的周人乃属同一族系(47)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第8页。,这样,华夏民族共推黄帝为自己的始祖就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和时代需求。黄帝之外的其他四帝虽说多数不与黄帝族为同一姓族而无血缘关系,但他们在五帝时代就先后成为华夏集团的组成部分,并从夏代开始融合为华夏民族一员,所以从战国到汉代采用“拟血缘关系”把他们组合成为一系是不难理解的。当时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原本代表不同的部族,他们先后来到中原或活动于中原地区,之后又融合而形成华夏民族;在融合的过程中,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称雄有先有后,《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排列,就透露出称雄的先后。《国语》和《礼记》的作者以及司马迁正是鉴于华夏民族的组成和融合情况,才给出了五帝在血缘上出于同一族系的记述,这主要是因为战国秦汉时期并没有今日的民族学概念,只得按照传统做法把民族融合表达为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并用祭祀谱系表现出来。若从华夏民族形成过程来看,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或因其先后来到中原或因其原本就在中原,最后都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在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他们都同属于华夏民族成员,只是有一个形成过程而不是自古一系而已。为此,我认为古史辨派在摧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系统时“破有余而立不足”,而把五帝之关系与华夏民族起源和形成过程相联系,才会“有破有立”。由此,我们鉴于五帝属于不同姓族而否定他们为一系,而又提出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五帝乃极重要源头。这一点较顾先生“层累说”和“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也属于重建上古史的一种考虑。
(三)关于“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的反思
顾先生“四个打破”中的“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确有建树,但也需要辩证地对待。如本文第一节所引,顾先生认为,“《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诚如顾先生所言,战国时期希望统一的愿望是强烈的。《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48)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页。这里的“一”就是“统一”。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战乱时期的人们对安宁统一的渴望。战国时的各国特别是战国七雄属于独立的国家,然而在各国独立的现实社会基础上却产生出统一的思想观念。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分析这一现象,战国时的统一思想若不能以战国社会现实中各国是独立的为基础的话,那么除了人民厌恶战争之外,战国之前的夏商西周的国家形态结构——三代社会政治,就成为战国时统一思想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大一统的思想和地理格局是由大一统的政治决定的,按照我的考察,中国历史上的“一统”有三个层次、三种形式:(一)秦汉至明清中央集权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二)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的“一统”观念;(三)五帝时代中原地区族邦联盟机制下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一统”观念。
地理格局是与国家政治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顾先生说的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是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这也是史学界的共识。对于夏商西周三代的地理和王朝结构,百年来的学术研究,其认识是逐渐清晰的。关于夏商西周的国家形态结构,传统的观点有两种。这里以商朝为例,第一种观点认为,“商王国是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的大国”,“商王对诸侯如同对王室的臣僚一样……诸侯政权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在实质上,就是后世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一种初期形态”(49)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原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6、169页;又收入杨升南:《甲骨文商史丛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48、51页。;或者说商朝是确立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50)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第二种意见认为商朝时期并不存在真正的中央权力,而把商代看作一个由许多“平等的”方国组成的联盟(51)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4页。,或者称之为“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52)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页。。
在上述两种观点之外,我在近年提出:包括商朝在内的夏商周三代都属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只是其发展的程度,商代强于夏代,周代又强于商代(53)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文史哲》2010年第1期,第91页;《商代都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6、485、486页;《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36-440、471-485。。在夏代,其复合制国家的特征主要是由夏王乃“天下共主”来体现的;到了商代,除了商王取代夏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外,其复合制国家结构主要由“内服”和“外服”制构成;到了周代,周王又取代商而为“天下共主”,其复合制国家结构则通过大规模的分封和分封制而达到了鼎盛,被分封的诸侯邦国属于“外服”系统,周王直接统辖的王邦则属于“内服”系统。换言之,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就像复合函数的函数套函数那样,处于“外服”系统的各个诸侯邦国是王朝内的“国中之国”;处于“内服”系统的王邦即王国,属于王朝内国中之国的“国上之国”,是王权的依靠和基础,而“内外服”即整个王朝又是一体的(54)王震中:《夏代“复合型”国家形态简论》,第91页;《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38页;《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13年,第436-440、471-485页。。这样的一体性,构成了另外一层次的“大一统”即我们一般所说的“一统”或“统一”。
夏商周三代王朝“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其一体性即在一统王权支配下的王朝国家的一统性,也可由国土观念和结构得以说明。在国土观念方面,用《诗经·小雅·北山》里的话来讲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5)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天子的大臣詹桓伯也说过类似的话:西部岐山和山西一带的“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东部齐鲁之地的“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南方的“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北部的“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49-1450页。。
战国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源自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这样的政治,而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则有族邦联盟。当时,一方面是邦国林立,史称“万邦”;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又结成了族邦联盟。五帝时代史称“万邦”,其政治格局是邦国林立与中原族邦联盟并存。在族邦联盟机制下,产生出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一统”观念,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说的帝尧能“协和万邦”,《礼记·礼运》所说尧舜禹时“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
可见,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乃至明清,伴随着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先后产生了三种背景指向的“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一统王权支配下的一统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识(57)王震中:《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光明日报》2019年6月10日“史学版”;《“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海南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第8页。。顾先生“四个打破”中“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固然有其建树的一面,但我们也不应以此为满足,还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即联系夏商周三代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结构和五帝时代族邦联盟的情形来追索战国“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
(四)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以及“神化”和“人化”问题
顾先生“四个打破”中的“古史人化”的问题,指的是他认为古史传说人物都是神而不是人,都是由神而“人化”为人。对古史辨派来说这是他们的最大建树,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古史辨派最主要的局限。
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固然呈现出许多神性,但并不能以此就说明他们是神而不是人。古史传说人物所具有的神性,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因为远古人的思维具有两重性——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的统一体(58)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一书强调原始人的思维不属于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原逻辑”的神秘的“互渗律”思维。笔者认为,原始人的思维固然有“原逻辑”的“互渗律”思维的一面,但它也有逻辑思维的一面,而且这二者可以统一在一个人的脑海里,也统一在他们的活动中,统一在他们的宗教崇拜中。参见拙作《论原始思维的两重性: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的交叉重叠》,待刊。,其中的原逻辑思维的机制是神秘主义的“互渗律”(5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1页。,在原逻辑的互渗思维机制下,原始人对自己死去的祖先或活着的酋长、英雄人物赋予神力和神性,是必然的;其二是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神名本是可以同一的,这样,从人名的角度看他是人,而从图腾名和神名的角度看呈现出的就是神。
对于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笔者在《炎黄学概论》(60)李俊、王震中主编:《炎黄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7-43页。一书中已有谈及,这里仅就黄帝以及顾先生特别举出的大禹为例,来回答古史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并进而分析所谓“由神到人”的古史“人化”问题。
关于黄帝,黄帝名号的由来就涉及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黄帝名轩辕,又称为有熊。黄帝、轩辕、有熊的名号是如何来的?这里我们先从“黄帝”一名说起。《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6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页。。《论衡·验符篇》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62)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6页。这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土德”来解释黄帝名号的来源。中国古代五行最盛行的时期是战国,从战国到秦汉,“五德始终说”政治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和王充用土德来解释黄帝名号的由来,是不难理解的。但黄帝及其所在的时代远在远古,此时还没有五行的说法,所以黄帝因土德之瑞得名不足为据。
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例如,《庄子·齐物论》:“是皇帝之所听荧也。”(63)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30页。《经典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64)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4页。又《庄子·至乐篇》曰:“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皇帝之道。”(65)王先谦集解,方勇校点:《庄子》,第174页。《吕氏春秋·贵公》:“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66)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9页。毕沅校曰:“‘黄帝’刘本(明刘如宠本)作‘皇帝’,黄、皇古通用。”(67)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19页。《易传·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68)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第627页。《风俗通义·音声篇》作“皇帝”(69)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267页。。可见黄帝与皇帝通用的例子甚多。而在《尚书·吕刑》中“黄帝”乃皇天上帝:“蚩尤惟始作乱……上帝监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皇帝清问下民。”(7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四),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2009页。依据这些文献中黄帝与皇帝通用的例子,当年古史辨派主张黄帝是神而不是人(71)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黄帝与皇帝及上帝》,《古史辨》第七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7页。。但也有许多先秦文献说黄帝是人,例如《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72)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355-3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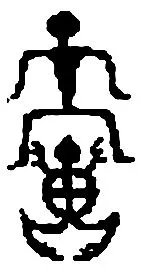
黄帝又号称有熊氏,有熊一名也来自黄帝族的图腾名。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77)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第5页。又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78)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第8页。也许有学者认为《帝王世纪》是西晋时期的书,不足为据。但是《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了以兽为名的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罴、貔、貅、豹、虎(79)《史记》,第4页;孔广森撰,王丰先点校:《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9页。。这六支以图腾为名号的军队以熊为首领,“有熊”是这些图腾的概括或代表,可见《帝王世纪》说“黄帝有熊氏”(80)皇甫谧等著,陆吉等校:《帝王世纪 世本 逸周书 古本竹书纪年》,第5页。是有依据的。有熊氏也可以在青铜器上找到其族徽铭文。邹衡提出“天兽”族徽(图一 1~6),即在“天”字图形之下铸有各种兽类图形的铭文,他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率领以熊图腾为首的六支军队与炎帝作战的史实,认为这些天兽类族徽是与黄帝有联系的,(8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13页。即青铜器铭文中的天兽类族徽是由黄帝族中以兽为图腾转化而来的。

1 2图二 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的蛙纹(1.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 2.甘肃师赵村遗址出土)
黄帝号称轩辕氏,又称有熊氏;既以天为图腾,也以青蛙(天黾)和熊罴貔虎等(天兽)为图腾。究其原因,是因为“黄帝”也代表一个族团。如《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82)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353-354页。二十五宗、十二姓显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而属于一个部族。在这个部族中,有的首领以天为图腾,有的首领以天黾(青蛙)为图腾,有的首领以天兽(有熊等)为图腾。我曾提出氏族图腾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的,这些图腾还可以进而转化为部族宗神(83)王震中:《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页。,黄帝族与周人乃一个族系,周王称天子(即天的儿子),以天为至上神,也是由此而来的(84)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第8页。。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
总括上述,关于黄帝名号,从文献看有“黄帝”“轩辕”“有熊”;从族徽的视角看,有“天”“天黾”“天兽”等。在“天”“天黾”“天兽”之中,“天”是共同的;在“黄帝”“轩辕”“有熊”之中,“黄帝”是共同的。从这两个方面的共同性出发,我认为,对于黄帝族而言,“天”是总名,“天黾”和“天兽”可以包括在“天”之下,这和春秋战国以来“黄帝”(既是皇天上帝即天帝,亦是作为人的人文初祖,还是春秋战国华夏民族的标识)是总名,“轩辕氏”和“有熊氏”是其别名一样。这一认识是把各方面的材料和现象融会贯通的结果,黄帝名号的由来及其意义由此也就清晰起来了。

关于图腾崇拜及其与祖先崇拜之关系,近年来笔者有新的研究。对于图腾是如何起源发生的,众说纷纭,这是图腾研究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图腾崇拜起源于远古时期的人们在不了解性交与怀孕有何关系的情况下,女性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也是对本族来源的一种解释。在由猿转变为人、进入人类社会之后的旧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繁衍都是由妇女怀孕生育实现的,但是关于性交与生育的关系,即男性在生育方面的作用,人类最初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其最初只是在本能上有性交方面的生理要求和感情冲动,而并不知道这类行为所带来的怀孕的结果。甚至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制度尚未出现或处于萌芽的时候,人类也还是不具备关于性交与怀孕关系方面的知识,或者说女性怀孕生育被认为与男子无关。这一方面是男女性交这一受孕行为与怀胎的象征(初次明显的胎动等)距离太远;另一方面,当时尚处于“群婚”,性交关系十分随便,而且性交未必皆生子,因此认为性交与怀孕生子没有关系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人类的思维和求知欲又促使他们力图对怀孕生育现象做出自认为合乎道理的解释。在当时那种“原逻辑”的“互渗思维”机制的作用下(即世界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相互转化的)(90)笔者认为原始思维具有两重性,即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交叉重叠在一起。其中的“原逻辑思维”的机制则是“互渗律”,即世界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相互转化的。,女性很自然地会将母体胎儿明显的胎动与当时所看见、所接触或所吃的东西联系起来,构成原始人的因果推理,从而认为怀孕和生育是这一动植物进入母体的结果。这也就是商族的祖先契被认为是简狄吞玄鸟卵因孕而生、周族的祖先后稷被认为是姜嫄踩巨人足迹因孕而生(91)《诗经》和《史记》中有关商族男始祖和周族男始祖诞生的神话故事,既是图腾崇拜方面的材料,也是祖先崇拜方面的材料。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图腾崇拜发生在前,祖先崇拜发生在后,而后来出现的祖先崇拜是可以把先头出现的图腾崇拜包括在内的。这就使得我们既可以把《诗经》《史记》记载的始祖诞生神话故事用来研究图腾崇拜,又可以用来研究祖先崇拜。,以及澳大利亚阿兰达人(Aranda)认为怀孕与性交及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图腾祖先的神灵进入母体的结果”的缘由(92)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成都: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第27页。。
如果我们承认图腾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的话,那么,最初的图腾就只能是个人图腾,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说的氏族图腾(氏族集体的图腾),即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这是因为:第一,女性怀孕和生育都是个体行为,她们对自己怀孕生育的解释也都是具体的,涉及的也都是一个个的个人,其产生的图腾当然是个人图腾;第二,当时还没有出现氏族,也没有所谓氏族制度,因而不可能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的出现已属图腾转型。
所谓图腾的转型,其一指的是由发生于旧石器时代、氏族制之前的个人的图腾转变为氏族社会及其之后的图腾,也就是说当社会进入氏族制之后,原有的图腾崇拜为了适应氏族制度的需要,所做的相应的转型演变。这种转型演变呈现出三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变为氏族集体图腾;第二种形态是转型为氏族名称、徽号、标识、族徽铭文等,并转变为保护神;第三种形态是在祖先崇拜中包含有图腾崇拜,即图腾崇拜发生在前,祖先崇拜发生在其后,但后出的祖先崇拜是可以包含之前的图腾崇拜的,这就使得祖先“感生神话”既可以作为祖先崇拜的材料来使用,亦可以作为图腾崇拜的材料来使用。
图腾转型的第一种形态是在原有的个人图腾的基础上出现了与氏族集体相联系的氏族图腾。我们从澳大利亚阿兰达人中大量的个人图腾与一小部分氏族集体图腾相并存现象,以及在我国远古社会作为想象中的全氏族部落共同的女祖先与图腾交感受孕的神话也即应运而生的现象,可以推知许多氏族图腾应该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的。因为在氏族内那些个人图腾每每会因其个人的死去而被人遗忘,只有那些为本氏族做过贡献的英雄的图腾,特别是氏族酋长的图腾才会在其死后依然被人们所传颂,一代一代地口耳相传,并成为该氏族代表性图腾,氏族图腾就是由这样一些个人图腾转化而来。
图腾转型的第二种形态是图腾演变为氏族名称、徽号、标识、族徽铭文等,并转变为保护神。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某一动植物,对早期以此为图腾的某一氏族团体来说,尚具有图腾祖先的含义,依旧同氏族徽号、标志、氏族团体相联系,但作为其保护神的另一重要作用,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随着这一氏族部落在本部族集团中地位的上升,渊源于这一氏族部落的图腾保护神,将会升华为本部族集团的保护神,其他氏族部落将会自觉地引之为崇拜物,从而呈现出一种所谓“时代风尚”。不过,这种崇拜对别的氏族部落来说,不是作为“图腾祖先”对待的,而是取其保护神的意义。久而久之,这一崇拜物就具有维系本部族集团团结的功能,成为这一部族集团在整体上区别于其他部族或部落集团的标志物。当氏族组织本身在形式和结构上有进一步的转型或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之中时,并且文明和铸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易于用青铜器铭文来表现族氏徽号时,图腾名称就转变成了族徽铭文,即族氏的族徽铭文渊源于氏族图腾名称。
大禹和夏部族的情况就是如此。“禹”字构形为蛇形龙,即因为蛇形龙是禹的图腾,也即禹的名称来源于他的图腾名,并非禹就是动物;而禹乃夏的君王,禹的图腾转化为夏部族图腾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列子·黄帝篇》说“夏后氏,蛇身人面”(93)严北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第69页。。夏为姒姓,姒字也是蛇形龙,姒姓族的夏以蛇形龙为图腾是由禹的图腾转化而来的。《国语·郑语》说姒姓的“褒人之神化为二龙”(94)韦昭注,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502页。,也说明夏人以龙为其最高图腾,蛇形龙是夏族的宗神。由此我们说“禹”这样的人名与“夏禹”这样的带有族属意味的名称,以及夏的图腾神乃至宗神之名完全同一,这是我们解决包括夏禹在内的古史人物究竟是神还是人这样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的结论是:夏禹是人,而他之所以称为禹是以其图腾名称呼的,这一图腾神还上升为夏部族的宗神(95)从考古学上看,笔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后期王都,而二里头出土了包括绿松石蛇形龙在内的许多蛇形龙。笔者认为,在没有本朝文字记载本朝史事的情况下,作为二里头遗址一种重要的文化特质——对于蛇形龙的崇拜,与文献记载相联系之后,这一文化特质所说明的问题,其价值就会大大提升,完全可以作为二里头是夏代王都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参见王震中:《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76页。。
当然,提出禹为神的观点,并非仅仅依据禹字的构形,还与大禹治水传说夹杂着许多神话成分有关。例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96)程俊英:《诗经译注》,第361页。《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97)程俊英:《诗经译注》,第493页。《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98)程俊英:《诗经译注》,第434页。这些大山河川也都是禹开垦疏浚的。《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99)程俊英:《诗经译注》,第565页。《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100)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535页。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101)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第538页。这些传说虽然反映了大禹作为族邦联盟的盟主,他所领导的治水范围却并非限于自己邦国所在地,而是遍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但是传说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话,诸如以“身执耒锸”这样的工具,而竟能做出“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河”之类非当时人力所能为的治水功绩,当然显示出其神力和神性。这就属于古史传说中神话与历史相交融、相混杂的问题。
大禹在治水中表现出的那么多神性与远古先民对自己部族酋长、部族英雄和祖先不断加以神化有关。而之所以被神化,主要是远古先民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与后人不同。原始思维是“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两重性的交叉混合,这种交叉混合可以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也可以体现在原始人的活动和作品中。在这样的思维机制中,上古时期的人似乎不借助于神话就不可思想。在“原逻辑”思维的神秘主义作用下,那些强有力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英雄,在其活的时候就可能被视为具有神力或神性,成为半人半神者,其死后变为部族神,其神性被不断地加以强化,并在部族中或部族间广泛流传,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文献化过程中,有的经历的是由神到人的所谓“人化”过程,也有的经历的是由人到神或半人半神的所谓“神化”过程,有的甚至是“人化”与“神化”交织在一起,亦即经历了:远古时是活着的部落酋长(是人但具有神力、神性,乃至被视为半人半神者)——死后为部落或部族神——在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又被历史化、人化为人或具有神力的人。也就是说,从远古开始,在先民们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中所谓“神化”与“人化”就交织在一起,从远古到春秋战国,英雄的祖先经历了由人到神,人神混合,再由神到人等演化过程。可见所谓“古史人化”或“神化”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由神到人的现象是有的,但并非仅仅是由神到人。这也就使得古史传说呈现出的是“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102)杨向奎:《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第44页。,笔者称之为古史传说中有“实”亦有“虚”,“实”指的是历史或历史的素地,“虚”指的就是神话(103)王震中:《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第14页。。而古史辨派则把这些人物一概作为神和神的“人化”来对待,这当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局限,对于重建中国上古史是没有帮助的。
(五)古史人物名号的沿袭性问题
在说到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时,还需要回答为何这些传说人物活的时间那么长,一个“五帝时代”或“炎黄时代”何以可跨越千年乃至二千年?这里也涉及古史传说诸人物的时代区分。不能回答这类问题,也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古史传说人物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
关于古史传说诸人物的时代区分,笔者认为,所谓黄帝时代、颛顼时代、尧舜禹时代或其他什么时代,是指黄帝族、颛顼族、唐尧族、虞舜族或其他什么族的称雄时期。因为作为古老的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存续的时间是相当长久的,而它留在先民们的记忆中的年代每每是其称雄阶段,在其称雄之前或衰落之后,该族实际上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不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已。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五帝谱系中,黄帝族称雄时间较早,因而黄帝也被视为“人文初祖”,继而是颛顼族、帝喾族称雄,最后是尧、舜称雄,大禹属于过渡期人物——他的前半段属于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时期,后半段则向夏朝过渡。
每个传说人物所在的族群都有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其间的每一个传说人物及其神话传说都有其“时间深度”。所谓神话传说的“时间深度”,指的是在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中,每每把不同时期的一连串的神话传说挤压在一起,成为一个神话传说。对此,张光直先生做过一个很好的论述:任何的神话都有极大的“时间深度”,在其付诸记载以前,总是先经历很久时间的口传。每一个神话,都多少保存一些其所经历的每一个时间单位及每一个文化社会环境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文化社会环境,一个神话故事不免要变化一次;但文籍中的神话并非一连串的经历过变化的许多神话,而仍是一个神话;在其形式或内容中,这许多的变迁都挤压在一起,成为完整的一体(10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256页。。
由于古史传说人物所代表的族群都有相当长久的存续的时间以及神话传说所具有的“时间深度”,这使得古史人物名号及其族群名号具有了沿袭性,这种沿袭性也体现在考古发现的图案纹样等图腾艺术的演变痕迹上。
有些古史人物在文献中是跨越时代存在的,属于古史人物名号沿袭性的显例。例如善射的后羿,《淮南子·本经训》说唐尧的时候,十日并出,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狶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105)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第80页。。《山海经》的《海外南经》和《大荒南经》也讲到“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杀之”(106)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第325页、第467页。的故事。这是用神话故事来讲述当时诸部族间的斗争。在这里,羿与唐尧是同一时代的人物。然而,《竹书纪年》和《左传》襄公四年却有“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10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27页。的记载,这是说后羿是夏代太康时的人。后羿跨越了唐尧、虞舜、大禹、夏启、太康五代。
再如皋陶,依据《论语》《墨子》以及《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皋陶和虞舜、大禹属于同时代的人。《尚书·尧典》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10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一),第201页。《尚书·皋陶谟》中记录有皋陶与禹的对话,《史记·五帝本纪》也是把皋陶和虞舜、大禹放在一起进行叙述。皋陶是舜和禹时掌管刑罚之官。在《论语·颜渊》中有“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109)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墨子·所染》篇说:“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110)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第16页。因而在传统的史学中,皋陶是与尧舜禹同一时代的人物;《史记·夏本纪》明确说皋陶卒于夏禹之时。然而,在清华简《厚父》篇中,咎繇(皋陶)乃夏启时卿事。因此,清华简《厚父》篇的整理者说这“颠覆了过去咎繇卒于夏禹时的说法”(111)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第83页。。其实,皋陶原本也属于一个沿袭性人名,既有尧舜禹时期的皋陶,也有夏启时的皋陶。
在中国上古史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沿袭性称号,是因为从远古时代起,氏族部落酋长之名与氏族部落之名可以同名。这也是一种上古族名与人名可以相同的现象。作为一个酋长或邦君,其寿命是很有限的,而作为一个氏族部落或部族其前后存在的时间是很长的,完全可以跨越不同的时代。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古史人物名号具有沿袭性。
(六)古史辨派的贡献与局限之小结
古史辨派的兴起也被称为是一场史学革命,今日反思之,应该说它既有贡献亦有局限。其贡献,概括地讲有这几个方面:第一,“层累说”和“四个打破”在总体上动摇了传统的古史体系,为建立实证史学的新体系做了尝试。第二,古史辨派推动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特别是以确认成书年代为基本内容的古籍整理。徐旭生是反对古史辨派的,但是,1960年他评价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和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11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1页。。第三,顾颉刚和他的古史辨派推动了对以《禹贡》为首的上古历史地理的深入研究。第四,古史辨派强调审查史料,去伪求真,是史学研究的必备条件。第五,古史辨派促进了学术界对考古学的重视。学术研究有破有立,古史辨派破掉了旧的史学体系,在建立新的史学体系时光靠文献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转向对考古学的重视。诚然,考古也不是万能的,考古学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多种学科的整合并从多个思维向度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古史辨派有建树亦有局限,其局限性最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疑古过度”的问题,主要是把一些属于先秦古籍写定的时间说成是秦汉以后,如《周礼》一书顾颉刚先生认为它成书于汉代,而现在一般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包含有西周的许多素材。第二,古史辨派提出古史传说人物都是神而不是人,顾先生的“层累说”已提出这一问题,“四个打破”中的“古史人化”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这是把古书中描写为具有神性的人物等同于就是神灵,其实这二者是有区别的。第三,就是古史辨派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破有余而立不足”,需要我们“有破有立”地重建中国上古史。
三、在多学科整合中重建中国上古史
(一)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提出
“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倡导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之后,在学术界“信古、疑古、释古”三种范式和态势并行之时,古史研究的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就有这样的提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我国台湾的古史学界也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大陆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呼吁更是越来越多。
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一般的提法是“三重证据法”。所谓“三重证据法”是指用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民族学)三个方面的证据来证明一些历史问题。三重证据法的前身是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原意是说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文献资料相互进行印证。尽管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也是考古物的一种,但它与考古学毕竟不是一个概念,而后来人们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乃至“三重证据法”中的那一重证据已由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扩展为考古学,也就是说,它既包括出土物中的文字资料,亦包括非文字资料。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两种文字资料之间的直接印证,具有证明的直接性,而后来所谓二重和三重证据法中的考古学资料往往并不含有文字资料(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其证明就有间接性的问题。这种证明的间接性是由考古学的特性决定的,对此我们后文再作进一步说明。
“三重证据法”,把人类学(包括民族学)看作其中一重证据。但在我看来,在这里人类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证据,而只是一个参照系。除了以人类学的资料为参照外,人类学还有一重价值是可以提供一种理论思维和理论模式,并由此把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学科连接在了一起。总之,“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概念,有时有用,有时又略感有缺陷,由此笔者转向使用“整合”这一概念。
(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将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三者相结合来重建中国上古史,也是对三者的整合;随着科技考古愈来愈多地深入到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整合就不仅是三者的整合,而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整合。多学科整合时就需要清楚地知道多学科中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局限,也就是说,每个学科各有其长处,但也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1.考古学的优势与劣势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测年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等等知识和手段对人类活动的方式和文化乃至社会的变迁等做出符合上古实际的分析和解释。所以,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是客观的,但对这些材料的阐释却不可避免地夹杂有主观的因素,阐释的高明与否也与阐释者的知识结构及其智慧密不可分。
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包括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文化学的等等理论。因此,这里还存在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笔者曾说:“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113)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503页。对此,李学勤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觉得这说得很对,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形成,归根到底是一个理论问题。对这样重大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说有真正的成果。”(114)李学勤:《序》,《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2页。
关于考古学的局限性,正如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在其《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所指出的:“研究史前和上古历史的科学,一般都是面对地下发现的断壁残垣、各种艺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那些永不变质的陶制品。从这些物件中,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底下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纸张——,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早期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不能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正如早期人类的宗教、还有那——不论以这种或是那种方式——对人来说是命中注定摆脱不掉的国家、以及人的语言这些现象一样,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来。”(115)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赵蓉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绪论”第2页。罗曼·赫尔佐克所说的不能直接从地下挖出社会的制度、宗教、国家等,并不是说对它们就不可以研究。事实上,今天的考古学在调动各种手段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后,可以提出有关上古社会的制度、宗教、国家等问题的解释,当然解释的观点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总之,有些学术问题是考古学能够解决的,有些是它不能解决的。尽管如此,作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框架性材料,我们还需以考古学为基础,因为它毕竟是当时的人遗留给我们的直接材料。
2.上古史学的优势与劣势
中国上古史的范畴,包括国际学术界曾提出的“史前时期”“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和“历史时期”的一部分这样三个时期。所谓“原史时期”,西方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紧接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其时间段被界定在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渡阶段。例如,中国的夏代历史,至今尚未发现像甲骨文、金文那样用本朝文字记录有关本朝史实的情形,《史记·夏本纪》是用周代以后的文献记载的材料来叙述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夏代历史的性质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论,尚属于“原史”的范畴(116)笔者认为夏代应该有成系统的文字,只是没有发现,也特别难以发现。因为像书写甲骨文、金文的甲骨和青铜器都不是用于书写的正常材质,上古用于书写的正常材质应该是竹简木牍之类,但这些材料埋在地下,在北方的环境下,一般是难以保存的,因而也特别难以发现。这样就造成目前只能把夏代视为“原史时期”。。
从文献的角度讲,史前和原史都属于古史传说的历史时代。谓之古史传说,是因为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的,这些内容后来用文字表现出来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看,必然是有“实”有“虚”,虚实相混(117)王震中:《古史传说的“虚”与“实”》,《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三皇五帝传说与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第14页。。对于古史传说中的“实”,尹达先生称之为“史实素地”(118)尹达:《衷心的愿望——为〈史前研究〉的创刊而作》,《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第5页。。古史传说所含有的史实素地,或者表现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浓缩性、神话性说明,或者表现为对远古社会的合理推测和想象,或者是把族团与族团之间的衍生、繁衍、分化表现为“某某生某某”式的父亲、儿子、孙子相传相生关系。古史传说中也含有许多纯粹属于神话的成分,其中有的属于古人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想象和解释,有的则属于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例如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就是古人用神话来解释人类的起源。再如,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19)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1989年,第27页。这个传说,一方面意在表明共工氏与颛顼氏有过激烈的称霸之争,并以共工的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地貌和许多江河都流向东南的河流走向。所以,古史传说是一种历史与神话的交融,用杨向奎先生的话讲,就是“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120)杨向奎:《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第44页。。对古史体系中虚妄的部分和荒诞不经的神话,我们当然需要去伪存真,对其伪尽可能地予以剥离。现在对古史传说进行虚实分析时,有的做法是借用考古发掘的成果,也即能被考古学所证实的古史传说,就归于史实。然而,所谓“被考古学所证实”,不能拘泥于某一遗址是否就是某一传说人物的遗留。迄今为止,凡是说某个遗址就是古史传说中的某个人物的遗址,很难得到学术界认可;而说某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是某个传说人物所代表的那个族群或部落集团的某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倒是有可能的,但也需要从时空和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予以论证。所以,探寻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对应,远距离、大体上的对应才是较为合理的。古史传说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在时代特征或时代背景上能与考古学上的时代相一致,就应该说这样的传说包含有史实素地及合理内核。可见,对于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的分析和剥离,是需要的,但其成效也是相对的。所以,古史传说中的实与虚,在与考古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时,要做辩证分析,还要以研究者对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都有系统的梳理、分析和研究为基础,而不能简单地比附,乱点“鸳鸯谱”。
上述关于古史传说中的“虚”与“实”及“去伪存真”的问题,就是上古史学历史文献的特点与局限性的问题。当然,古史传说性质的历史文献只是上古史学的一个方面而已。对作为与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的历史学来说,以重建上古史为目的的历史学理论是重要的,它也起着把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及人类学连接起来的纽带作用。
3.人类学的优势与劣势
在上古史的重建中,人类学就其材料而言有所谓“活化石”的意义,它弥补了考古学资料只见物而不见活生生的人的局限,然而“活化石”的意义也是有限的。人类学材料、民族志材料为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某些原始的状态,这对我们了解已经逝去的远古社会是有帮助的。但是,现存的这些原始的土著民族,他们自己至少也有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他们近代以来的生存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与远古是有差异的,有的甚至差异很大,特别是与中国远古时代的差异更大。因此,就材料而言,人类学所提供的这些原始民族的材料和社会现象,其原始性也是相对的;它们有参照意义,但不能说是直接证据。
人类学的另一个价值是它的理论建树和理论模式,特别是其理论被当作解释人类早期社会演化的便利工具。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通过对那些鲜活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类型、社会制度、社会习俗、思想观念和原始宗教崇拜等具体事例的研究建构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真实性基础。但是,人类学理论并非没有假说的成分。
第二,塞维斯把生产的地区分工与再分配机制作为酋邦兴起的模式也属于一个假说。依据这一模式,酋邦的兴起于某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即由于环境资源的不同,不同的村落之间出现生产的地区分工和交换的需求,从而产生相关的协调活动和再分配机制。如果酋邦只产生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之中,那么大部分属于自给自足的聚落群或社区,就无法由部落发展为酋邦,酋邦也就不具有普遍意义。塞维斯的“再分配机制”这一假说只可视为对酋邦兴起原因的一种探讨。不赞成他这一说法的学者,在面对酋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酋邦演进过程的动力等课题时,都提出过自己的新说,诸如人口增长压力说、战争说、对集体化生产活动的管理与对贵重物品的控制说等等。应该说这些新说也含有假说的成分,也属于假说的范畴。理论需要联系实际,这些假说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这既是理论创新的魅力所在,也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塞维斯不承认酋邦社会里存在弗里德在其“社会分层理论”(122)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185.中所说的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分层,这是塞维斯独特的学术观点,也是其酋邦理论的一个局限。在塞维斯的酋邦概念中,酋邦社会的不平等只是由血缘身份地位造成的,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酋邦只是酋邦社会的初级阶段,并非所有酋邦皆是如此。在史前社会中,虽说是先有血缘性的身份地位的分等,后有经济性的社会分层,而且也有从军事的宗教的社会职能和职务中产生出贵族和统治者的情况,即社会分层有起源于政治途径的情形,但这不等于说在原始社会末期没有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在这方面,同样属于主张酋邦理论的厄尔和约翰逊就与塞维斯完全不同。厄尔和约翰逊认为酋邦与此前简单社会最为重要区别就在于分层,在于社会成员掌握生产资料权力的差异,这当然是占有重要经济资源权力不平等的一种制度,也就是说,在厄尔和约翰逊看来,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分层并非在酋邦社会之后,而是始于酋邦社会之中。笔者认为厄尔和约翰逊主张酋邦有社会分层的观点,以及厄尔把酋邦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做法,都属于对酋邦理论的发展。
第四,酋邦概念和定义的极不统一,也可以视为酋邦理论的局限。例如,奥博格将酋邦定义为在一个最高酋长管辖下由次一级酋长控制的、以一种政治等级从属关系组织起来的多聚落的部落社会。塞维斯把酋邦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123)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5页。。“斯图尔特将酋邦定义为由许多小型聚落聚合而成的一个较大的政治单位,他进而将酋邦分为军事型和神权型两种。……弗兰纳利认为酋邦是社会不平等世袭的开始,自此社会中不同血统是有等级的。不管个人的能力如何,其地位的高贵和低贱与生俱来。血统和地位也与财产的拥有相联系……弗兰纳利认为,酋邦从考古学上辨认的诀窍是看是否有高等级的幼童和婴儿墓葬,可以说明权力和地位的世袭。……皮布尔斯同意酋邦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体制,贵族和酋长具有实施控制的权力,这种权力多少依赖神权来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卡内罗赞同酋邦是一种超聚落的政治结构,将它定义为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由多聚落或多社群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124)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第141-143页。厄尔把酋邦划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认为酋邦是一种区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社会结构由一个酋长集中控制的等级构成”(125)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第146页。。“克里斯廷森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区别在于部落社会与国家社会,酋邦只是部落社会的一种变体,或者说,酋邦是社会组织的一种部落形式。”(126)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4-295页。
欧美学者对酋邦有种种定义,其根源在于酋邦类型的多样性。酋邦类型的多样性,是由于原始社会后期或由史前向国家的转变时期不平等现象和形式本身就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是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平等的多样性使得学者们对酋邦的定义和特征的归纳存在着许多差异。如果我们一定要将那些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即从刚刚脱离原始部落的较为平等的状态一直到非常接近国家的复杂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都冠名以酋邦的话,就只能牺牲丰富性和具体性而上升到抽象性,将酋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早期酋邦或简单酋邦的特征是血缘身份与政治分级相结合的一种不平等的原始社会类型;晚期酋邦或复杂酋邦则是已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层的原始社会类型。张光直曾说:“酋邦的主要特征是其政治分级和亲属制度的结合。”(127)张光直、陈星灿:《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第36页。在这里,我们对酋邦主要特征的概括与张光直的概括是一致的,也兼用了厄尔用“简单酋邦”与“复杂酋邦”来表示酋邦社会中不平等的发展程度和酋邦演进中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样的认识。
4.科技考古的优势与局限
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是考古学长足进步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测年技术,可以解决考古遗址的年代问题;用科学技术可以测定分析出遗址的生态环境,从而解决人地关系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问题;用古DNA分析技术可以从血缘上检测出聚落遗址究竟属于母系还是父系等问题;用锶同位素技术可以检测出遗址内人与动物迁徙移动等问题;用碳和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研究人和动物的食物组成等问题;用铅同位素可以检测出金属冶炼中铜等矿石的来源等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属于科技考古的优势。那么,科技考古有没有局限性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标本采样是有严格要求的,若在采样中让标本受到了污染,测试出的结果当然是有误的。其次,用古DNA测定某一聚落遗址的血缘究竟是母系还是父系是有用的,但用古DNA来测定某一区域或早期国家是否已脱离血缘关系而进入地缘关系则是困难的,需要对该地域内数量相当多的成批的人骨标本进行测定,而且这些人骨标本与都邑、村邑、居邑或房屋群的居住关系必须是清晰的,否则很难说明问题。

问题一,所谓“系列拟合”,就是把已经测定的系列数据所呈现的时间范围人为地加以压缩。我们知道,被拟合的系列数据之间,最理想的条件是所采集的标本属于同一遗址内具有上下地层叠压关系的测年标本,只有这样的标本,其系列数据之间才具有确实无疑的前后年代关系。用这种具有确实无疑的前后年代关系的系列数据来压缩拟合,其拟合的结果才会较为可靠。然而,在后一种拟合中,即“新砦、二里头第一至五期的拟合”中,新砦期的数据与二里头第一期的数据是两个不同的遗址的数据,二者之间先后关系的排序只是根据它们文化分期之间的年代关系,而并非依据同一遗址内的直接地层关系,所以其拟合的条件不是最理想的。

由此可见,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科技考古等都有自己的特殊优势以及局限,都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整合才成为必要,才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整合可以发挥各自的特殊优势,也可以弥补彼此的缺陷。对此,我称之为“互补互益”,并提出“以考古学材料为骨架,以文献材料为血肉,以人类学材料为参照,来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134)王震中:《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绪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页。。这是一种从资料的个性特征上整合三者优势来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考虑。
(三)多学科整合中的主体性与多个思维向度的学术创新性
我们在上古史研究中究竟如何整合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科技考古?我认为,这种整合并非拼盘式的综合或凑合,它应该是围绕某一课题或问题,以某一学科为主去整合相关学科,整合要为创造性思考服务,多学科要体现多个思维向度,共同构建和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多学科整合中首先涉及的是以谁为主的问题,即多学科整合中的主体性问题。对此,我曾提出要以聚落形态学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135)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第55页。。之所以这样做,与当时这一课题的主题、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所依靠的主要材料的特点有关系。
我们说历史学既是实证性的亦是解释性的。研究上古史,特别是研究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这一时段的上古史,材料的基础是考古学材料。在考古学中,聚落考古学研究的是聚落内的社会关系以及聚落与聚落之间的社会关系,故而通过对聚落形态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其社会形态、社会类型的发展变化,也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就决定了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结合为研究上古时代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的主体对象,而人类学在这里虽然可以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作为“活化石”的参照,但它在这里毕竟是为解释上古史服务的。所以我提出“以聚落形态学和社会形态为主,去整合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主要是从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整体上着眼的。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三者的整合主体性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此外,尉迟寺聚落遗址的复杂化程度低于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相关遗址,如果我们说观象授时的“火正”的出现是一种社会分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论:一是社会职务的分工早于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即它并非以社会的不平等为前提;二是这样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开始的分化,可以促进该聚落和聚落群沿着社会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社会阶层和阶级产生的途径之一。
蒙城尉迟寺的例子告诉我们,考古学与人类学相整合而产生的新的学术观点、学术见解,就像人类学理论服务于历史学上的解释需求一样,考古学对解释的需求也可以通过人类学理论的引入而获得启发。
以上我们从方法论视角探讨了多学科整合以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课题。至于本文所论“古史辨的贡献和局限与上古史的重建”,我觉得它们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古史辨派以打破旧史学体系为主,破有余而立不足,但毕竟先“破”然后才能“立”;我们无论是在古史辨派贡献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还是通过对其局限的反思而向前迈出一步,都是在走向重建中国上古史。上古史的重建,我认为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多学科并在诸多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和突破,二是做出理论创新,三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长期任务,其成果更多地呈现为阶段性和时期性,因而也是相对的,特别是随着考古新发现而产生的新学问,以及对古代文献和古文字资料进行新解读而做出的新学问,都会使得我们始终处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