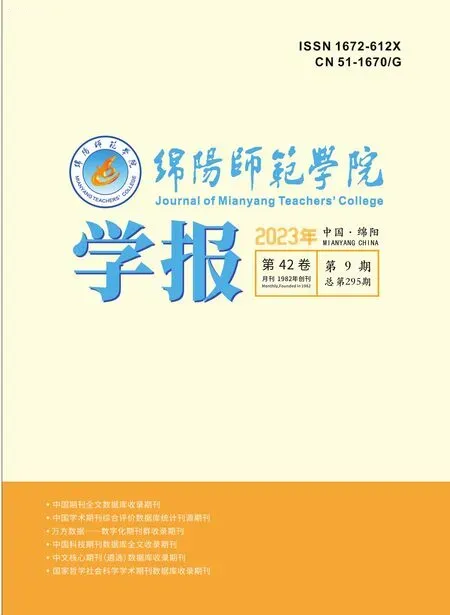互文视域下唐代壁画诗与敦煌壁画之研究
2023-10-08徐小洁
徐小洁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一、问题的提出
诗歌与绘画,其本质意义上都是一种符号,一种媒介。从符号学角度看,诗歌语言与绘画语言之间存在着“互文性”现象。“互文性”是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文本生成的一种重要理论。“互文性”理论最早由法国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其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中正式提出。她认为:“文本意味着文本间的置换,具有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相互交会和中和。”[1]51文本与文本之间具有互相参照、映射的关联性。克里斯蒂娃还提出了“意素”的概念,将狭义的语言文本扩展到广义的文本(文化)中,她指出不同文本的描述需要置于广义的文本(文化)之中,某种特定的文本系统与其吸收到自身空间中的陈述语(句段)或是发送到外部其他文本(符号实践)中的陈述语(句段)之间的交会被称作意素。意素承载了“具体化”了的互文功能,借此在互文性中研究文本,在社会和历史中思考文本[1]51-52。
意素的提出,明确了文本之间“具体化”的互文功能,这是一种动态的功能,“赋予文本以历史、社会坐标”,将文本置于社会和历史的广义文本框架中进行思考与解读,很显然,文本的阐释空间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从孤立封闭的状态转而走向开放与丰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启迪:文学艺术的研究应该置于广义的文本(文化)中,形成一种开放性、超越类型局限性的研究结构。
百余年的敦煌研究,所形成的敦煌学已是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广阔性,研究结构的开放性,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厚重、宽广与辉煌。敦煌石窟计有550多窟,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清,绵延1600多年[2]1。史苇湘在《汗尘迷净土 梦幻寄丹青——论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一文中指出,盛唐正是佛教发展的盛期,天下佛寺无不崇楼丽阁、宝塔林立,峻宇复殿、焕若神宫。然而经过千百年岁月不断的兵燹干戈、江山易代,许多宏伟的寺院、著名画家的绘塑,早已荡然无存。唯独敦煌莫高窟却能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八十一个盛唐石窟,大约保留了盛唐丹青近四百壁,约占莫高窟壁画总数的六分之一。这些珍贵的壁画艺术,至今尚金碧耀眼、粉墨逼人,一派盛唐气象[3]1-2。敦煌壁画尤其是唐代壁画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内容极为丰富,成为唐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艺术卷》中以敦煌壁画为主题的论文非常突出,很多论文从唐代的角度进行绘画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交叉性研究,阴法鲁《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一文,将唐诗与敦煌壁画的唐代舞蹈相对照,如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李端《胡腾儿》诗“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人在地毡上跳舞,这和壁画上相同[2]104。这类表现音乐、绘画、舞蹈、建筑等艺术形式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比比皆是,如刘禹锡《观柘枝舞》:“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绮墀。神飙猎红蕖,龙烛映金枝。垂带覆纤腰,安钿当妩眉。翘袖中繁鼓,倾眸溯华榱。燕秦有旧曲,淮南多冶词。欲见倾城处,君看赴节时。”[4]3984《全唐诗》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编成,康熙作《御制〈全唐诗〉序》,对唐代诗歌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
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縠率,治器之就规矩焉。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宴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虽穷达殊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厘为九百卷。于是唐三百年诗人之菁华,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4]1。
唐诗繁荣与唐人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创作诗歌有更密切的关系。葛晓音指出初唐文人在交游方面对于诗赋也有迫切的需要,《全唐文》和《全唐诗》记载了初唐文人大量宴集和送别的序文及诗歌[5]77-78。这不仅是初唐诗歌的创作景观,迨至盛唐,诗赋作为精神交往的工具与载体,始终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正如《全唐诗序》所概括的“一举而托之于诗”的创作盛况,是唐诗繁荣的基本条件。正如李白诗歌所表现出的情志特点,尤其是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等多种类型的诗歌,与全唐诗“而又堂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宴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的创作风貌,形成鲜明的映照。
本文拟以唐代壁画诗与敦煌唐代壁画为具体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全唐诗》中的壁画诗及相关的山水诗等,抽绎出能够与敦煌唐代壁画形成映照互鉴的要素,从现实题材与艺术情境的角度去研究壁画的主题思想、物象特征等,着重讨论以李白诗歌为典范的唐代壁画诗以及敦煌盛唐壁画中的佛寺题材,力图探究唐代壁画诗与敦煌唐代壁画之间的互文性研究价值。
二、唐代壁画与壁画诗
唐代绘画,至开元、天宝之际,名家辈出,灿若星辰,可谓极人文之盛况。唐代壁画艺术亦盛极一时,“或饰于道院,或见于佛寺,或饰于石室及其他建筑物,虽多没灭,不可得见,其可见者,如敦煌石室壁画,细致富丽,至可宝贵也。”[6]18《宣和画谱》记载的唐代擅长壁画丹青的画家首推吴道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请道子画鬼神于天宫寺,资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缞服,用军装缠结,驰马舞剑,激昂顿挫,雄杰奇伟,观者数千百人,无不骇栗。而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气以壮画思,落笔风生,为天下壮观。故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皆以技进乎道;而张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则草书入神;道子之于画,亦若是而已[7]19。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列名画家吴道子为“神品上”,仅一人。朱景玄赞其壁画:“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又按《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壁、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背为妙,但施笔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彩绘。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一笔而成。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8]56-57唐代绘画史上擅长壁画的著名画家还有与吴道子同时代的杨庭光,善写释氏像与经变相,旁工杂画山水等,皆极其妙,时谓颇有吴生体。卢楞伽学画于吴道子,尤喜作经变相。乾元初尝于大圣慈寺画行道僧,又尝画庄严寺三门,窃自比道玄总持壁。范琼善画人物、道释、鬼神,咸通中,于圣兴寺大殿画东北方天王并大悲像,名动一时。更为传奇的是孙位光启中,画应天寺东壁,画成,矛戟森严,鼓吹戛击,若有声在缥缈间。至于鹰犬驰突,云龙出没,千状万态,势若飞动,非笔精墨妙,情高格逸,岂能与于此耶?这些记载于《宣和画谱》的唐代大画家的事迹,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壁画艺术水平之高超,同时也可以看到壁画作品分布之广泛,尤以道观寺院的宗教壁画为突出。唐代壁画的施用之地,不限于佛寺道院,即宫殿祠堂第宅之间,亦往往有之,惟施于寺院中者为多数耳[6]123。这些壁画大多已遭湮没,难以睹其盛况,所幸古代画论典籍多有载录,可藉此仿佛而想像之。
(一)唐代壁画诗
唐代极为丰富的壁画作品为唐诗创作提供了灵感与素材,产生了以壁画为题材的壁画诗。郑午昌论中国绘画史,提出艺术为人类之艺术,不能以地方自局。绘画虽小道,更不能独自产生长进,必受其他文艺政教之孕育与促成[6]3。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把唐代绘画列入“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所谓“宗教化时期”,是指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历六朝而迄唐宋,印度绘画,时随佛教以俱来,国画受其影响及陶熔,顿放异采。天龙宝迹,地狱变相,凡寺壁塔院,遍绘庄严灿烂之印度艺术化之佛画。所谓“文学化时期”,是指唐代绘画,已讲用笔墨,尚气韵;王维画中有诗,艺林播为美谈。自是而五代、而宋、而元,益加讲研,写生写意,主神主妙,逸笔草草,名曰文人画[6]4-5。郑午昌对中国绘画史的分期具有融合性、互文性的审美特点,将宗教、绘画、文学等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突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渗透性,极具见地。唐代绘画的宗教化与文学化,以敦煌唐代壁画最富典范性;唐代诗歌的宗教化与绘画性,亦是不刊之论。如李白的题画诗,从题材上看,所题有故事画,有佛像画,有人物肖像画,有山水画,有鸟兽画等。从画的质地上来看,有壁画,有屏风画,有挂画等。从画的种类上来看,有五彩图画,有金银泥画,有水墨画等[9]。检索《全唐诗》,据不完全统计,诗题有“壁画”二字的共计20余首(详见表1):

表1 《全唐诗》中“壁画”诗统计表
这些壁画诗的作者包括李白、杜甫、岑参、高适等唐代著名诗人,所歌咏的壁画题材多以山水为主,如孙逖《奉和李右相中书壁画山水》、李颀《李兵曹壁画山水各赋得桂水帆》、刘长卿《会稽王处士草堂壁画衡霍诸山》、李白《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钱起《题礼上人壁画山水》、皇甫冉《酬包评事壁画山水见寄》《刘方平壁画山》、王季友《观于舍人壁画山水》、卢纶《达奚中丞东斋壁画山水各赋一物得树杪悬泉送长安赵元阳少府》、羊士谔《台中遇直晨览萧侍御壁画山水》等。唐代寺院壁画的题材多山水画,赵声良《从敦煌壁画看唐代青绿山水》认为,由于长安、洛阳等城市的唐代寺院消失殆尽,寺院壁画中的山水画难以见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了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10]。其他壁画诗以具体物象为歌咏对象,主要有佛像、鹤、马、云、松、竹等。除表1中所列唐诗外,言及壁画的唐代诗歌尚有很多。如陈子昂《咏主人壁上画鹤寄乔主簿崔著作》诗云:“古壁仙人画,丹青尚有文。独舞纷如雪,孤飞暧似云。自矜彩色重,宁忆故池群。江海联翩翼,长鸣谁复闻。”[4]902孙逖《宿云门寺阁》:“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画壁馀鸿雁,纱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4]1193唐代壁画生动表现了直观可感的物象之美。
还有一类壁画诗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如包佶《观壁画九想图》:“一世荣枯无异同,百年哀乐又归空。夜阑鸟鹊相争处,林下真僧在定中。”[4]2144包佶,字幼正,天宝六年及进士第,累官谏议大夫,坐善元载贬岭南。迁刑部侍郎,改秘书监,封丹阳郡公。诗题所云“九想”,虽未具体描写佛教九种具体观想,但其“归空”思想显然是佛教的。王志鹏在《简论敦煌写卷中组诗、长诗的佛教特征》一文中指出,敦煌P.3892和S.6631卷分别保存有两种《九想观诗》各九首,一组为每首七言四句,另一组每首为五言十二句,诗歌内容分别对初生(或婴孩)、童子、盛年、衰老、病苦(或病患)、死、胞胀(或膨胀)、坏烂、白骨等人生阶段和死后腐化的各个过程进行歌咏[11]。敦煌诗集残卷有数首九想诗,其中斯六六三一《九想观诗一本》有《九相观序》:“普劝有识,归心解脱之门;凭此胜因,同证涅槃之路。诗陈九相,列在后文。”[12]902-904上博四八(41379)《九想观一卷并序》序云:“世人每思九想观,即知变太化来非。识姓(性)了心须觉悟,从生至死缀成词。”[12]932-934这都表明了诗歌宗旨在于宣扬劝人归心解脱的佛教思想,可与包佶诗相佐证。此外刘长卿《狱中见壁画佛》:“不谓衔冤处,而能窥大悲。独栖丛棘下,还见雨花时。地狭青莲小,城高白日迟。幸亲方便力,犹畏毒龙欺。”[4]1512卢纶《题嘉祥殿南溪印禅师壁画影堂》:“双展参差锡杖斜,衲衣交膝对天花。瞻容悟问修持劫,似指前溪无数沙。”[4]3165这都体现了鲜明的佛教色彩。敦煌诗集残卷也有一些壁画诗,如宋之问《咏省壁画鹤》亦见于斯五五五唐诗丛钞,题作《咏壁上画鹤》,诗云“画作双山鹤,昂藏仙气多。似飞还不去,应是恋恩波”[12]512,与《全唐诗》有异。
(二)李白壁画诗
唐人常称壁画为“粉图”,朱金城先生指出“粉图”一词用于唐代诗歌,似陈子昂为最早。陈子昂有《山水粉图》诗:“山图之白云兮,若巫山之高丘。纷群翠之鸿溶,又似蓬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爱云山以幽求。”[4]898但以李白诗文为多见,如《金陵名僧頵公粉图慈亲赞》《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志公画赞》《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观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图》《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壁画苍鹰赞》等。“粉图”“粉壁”“壁画”是李白壁画诗常用的词汇,李白壁画诗是唐代壁画诗当之无愧的艺术经典。唐代的壁画诗,以李白《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最具创造性与艺术性。李白《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诗云:
高堂粉壁图蓬瀛,烛前一见沧洲清。洪波汹涌山峥嵘,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岚气灭,谓逢山阴晴后雪。回溪碧流寂无喧,又如秦人月下窥花源。了然不觉清心魂,只将叠嶂鸣秋猿。与君对此欢未歇,放歌行吟达明发。却顾海客扬云帆,便欲因之向溟渤[13]1045-1048。
以古注本为主体的李白诗歌经典阐释系统,极大地丰富了李诗学的“意义空间”。传世注本中明代朱谏《李诗选注》对李白诗歌内容的串讲富有特色。朱谏(1462—1541),字君佐,号荡南,浙江乐清人,明孝宗弘治丙辰(1496)登进士第。李白《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朱谏按语如下:
按烛照山水壁之画,最难形容。李白乃能曲尽其妙,始终宛转;体物象景,意极亲切,辞宏丽而气敷畅。想于宴会之时,灯下引杯,顷刻而就,不假于沉吟潜思之力,有若风云之变现,转睫异态,真天材也①。
山水壁画由具体物象构成,李白因景赋诗,融景、情、志于一诗,情由境生,辞随意转,“有若风云之变现,转睫异态”,画里画外,情境交融,甚至粉壁空白之处,也因诗人的错觉而幻象顿生“光中乍喜岚气灭,谓逢山阴晴后雪”。在审美的眼光中,素壁之光亦可成晴后之雪,这纯然是幻象,却为诗意平添了一份美感,可见诗人的情思飞动达到了极致。正如苏轼《论文》所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14]591苏轼说的是为文之法,用在此处,也突出了“随物赋形”的艺术特征。诗人的情思随着山水景物的变换而变换,如朱谏所云“体物象景,意极亲切”。另一首《当涂赵少府粉图山水歌》表现的绘画内容更加丰富繁盛,“随物赋形”的特点更为突出。朱谏注云:
按白之题画,咏山则以峨眉、罗浮、赤城、苍梧、三山等言之;咏水则以南溟、洞庭、潇湘、三江等言之,终以羽仙、武陵之事归之主者。云烟、草木、舟帆、泉鸟,杂然布置,情思流动,辞气激扬。初看若无统纪,细玩则界限分明,有如韩信用兵而多多益善也。
朱谏指出了李白山水题画诗的特征,常以真山真水、名山大川言之,从大处落笔,气势极其宏阔;又于细处点染,用心勾描云烟、草木、舟帆、泉鸟等画中物象,以形容画中岩谷景物之精妙处,着意表现“山水之真”。这非常符合李白的绘画观念,其《金陵名僧頵公粉图慈亲赞》所云“粉为造化,笔写天真”[13]4173,与李白诗贵“清真”“自然”的美学观点高度一致。
壁画是李白诗文的重要题材,除诗歌外,还有一类文体比较突出,就是“赞”,上文已言及《金陵名僧頵公粉图慈亲赞》《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等作品。以具体物象为表现内容的“赞”主要有《壁画苍鹰赞》《方城张少公庭画师猛赞》《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壁画苍鹰赞》是一篇苍鹰壁画上的题辞,先对画面上苍鹰的凶猛之状做了生动的描绘和比喻,接着又从观众的惊愕反应来突出此画的艺术魅力。题下注“讥主人”。赞云“突兀枯树,傍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秋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銛剑戟,手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11]4182。其中“未悟丹青之所为”非常生动地表现了壁画上苍鹰呼之欲出的形象特征。另一首《方城张少公庭画师猛赞》以方城张少公厅壁狮子图像为主题,所谓“师猛”,指凶猛的狮子。赞云:“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掣蹲胡以震怒,谓有夏之嶤杌。永观厥容,神骇不歇。”[13]4184诗人描绘了一幅雄姿英发、势若破壁而出的猛狮图,其逼真处不止在外形,更在其精神与气势。王伯敏《李白杜甫论画诗散记》指出:“‘狮猛’的气势,正是在于它的‘震怒’之中。常言‘狮吼以惊谷’,何况生动地画出它的‘震怒’,其‘神骇’的异状,当可想而知。”[13]4186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幅猛禽壁画并不在宗教场所,而是绘于家宅厅壁。苍鹰、狮子这类猛禽形象反映了主人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寄托,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反映了一种刚健勇猛的大唐气象。另一种唐代壁画习见的禽鸟“鹤”,则表现出缥缈出尘、超然物外的审美趣味。李白《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云:
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倘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13]4203。
这是一幅仙鹤画图赞,生动描绘了图中仙鹤的体貌神态。关于壁画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有的根据《宣和画谱》所载薛稷遇李白的故事,认为这幅仙鹤图是薛稷所作;有的考证史实,认为不一定是薛少府所画。朱景玄曾记载“神品下七人”的薛稷遇李白一事:“薛稷,天后朝位至宰辅,文章学术,名冠时流。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画踪如阎立本,今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曾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相留,请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佛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秀,曹张之匹也。二迹之妙,李翰林题赞见在。”[8]22-23杜甫有《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一诗,题下注“稷,汾阴人,工书画。官至太子少保,封晋国公。以太平公主乱,坐知谋赐死”,诗云: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4]2321。
据《宣和画谱》所载,薛稷以画鹤著称。昔李杜以文章妙天下,而李太白有稷之画赞,杜子美有稷之《鹤诗》,皆传于世。稷在睿宗朝,历官至太子少保,封晋国公[7]163。杜甫《观薛稷少保书画壁》后一首即是《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题下注“稷尤善画鹤,屏风六扉鹤样自稷始”。诗云:“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4]2321-2322画中鹤与诗中鹤俨然一致,不仅描摹鹤的外在神态,更着重表现鹤之“真骨”。所谓“鹤样”,当如此。此类壁画诗往往物象鲜明,或描摹物态,或寄寓情思,与自然风物联系紧密。金乡薛少府厅壁画的作者难以考证,厅壁上的仙鹤图早已荡然无存,所幸诗仙李白以绝妙诗笔描摹入画,诗中有画,象在其中,赋予读者以审美想象空间。同时,诗画互证,唐代大量的壁画诗文也给壁画观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参照。
三、唐代壁画诗与敦煌盛唐壁画的佛寺题材
唐代图画,无论人物山水花鸟及其他杂画,往往图之寺院,与宗教有关。就大体而言,此种图画,终不若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制作之伟大富丽[6]108。杨炯《游废观》诗云:“青幛倚丹田,荒凉数百年。独知小山桂,尚识大罗天。药败金炉火,苔昏玉女泉。岁时无壁画,朝夕有阶烟。花柳三春节,江山四望悬。悠然出尘网,从此狎神仙。”[4]617张说《灉湖山寺》:“楚老游山寺,提携观画壁。扬袂指辟支,睩眄相斗阋。险哉透撞儿,千金赌一掷。成败身自受,傍人那叹息。”[4]929崔国辅《宿法华寺》:“松雨时复滴,寺门清且凉。此心竟谁证,回憩支公床。壁画感灵迹,龛经传异香。独游寄象外,忽忽归南昌。”[4]1199崔国辅,吴郡人,开元中,应县令举,授许昌令。皇甫曾《赠鉴上人》:“律仪传教诱,僧腊老烟霄。树色依禅诵,泉声入寂寥。宝龛经末劫,画壁见南朝。深竹风开合,寒潭月动摇。息心归静理,爱道坐中宵。更欲寻真去,乘船过海潮。”[4]2185皇甫曾,字孝常,天宝十二载登进士第,历侍御史,坐事徙舒州司马、阳翟令,诗名与兄皇甫冉相上下。这些壁画诗多与寺院相关,或感慨世事变迁,或描绘壁画图景,皆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唐代壁画诗的题材丰富,包含寺观、山水、人物、场景等,其中佛寺题材是唐代诗歌内容极为突出的部分。《全唐诗》的佛寺题材,仅统计诗名就非常丰富,唐代寺院成为诗人歌咏的重要对象。这些佛寺题材的诗歌所涉及的寺院有名刹古寺,有普通寺院,遍及天下,蔚为大观。诸如长安慈恩寺、杭州天竺寺、灵隐寺、开元寺、润州金山寺、甘露寺、慈和寺、鹤林寺、杭州孤山寺、苏州灵岩寺、楞伽寺、思益寺、虎丘寺、南陵隐静寺、扬州法云寺、宣州开元寺、庐山东林寺、岳麓道林寺、长沙开元寺、元门寺、鄂州头陀寺、徐州延福寺、天台国清寺、金陵栖霞寺、歙州兴唐寺、凤翔天柱寺、梓州牛头寺、巴陵开元寺、九华化城寺、泾县水西寺、襄阳凤林寺等,据不完全统计,仅诗题含有寺名的诗歌就有1 400余首。唐代寺院在历史烟尘中消失殆尽,其建筑体制、环境、风貌等端赖文学艺术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诗是无声画,画是无声诗,诗歌作品以文字为媒介,绘画艺术以造型为载体,直观与想象相结合,心灵世界与图像世界互融通,以佛寺为题材的唐代诗歌所展现的艺术情境,敦煌唐代壁画所绘制的佛国世界,彼此映照互鉴。如西安寺西方佛,杜甫诗所谓“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6]119者也。李白诗文中所描绘的“八功德水,波动青莲之池;七宝香花,光映黄金之地。清风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乐,咸疑动作”[9]的西方净土变相,如今在敦煌石窟的唐代壁画中尚可以看到。这种诗画的彼此参照可以视为艺术桥梁,共同通向唐代社会历史环境,为敦煌壁画研究与唐代诗歌研究提供比较真实可靠的依据。

我闻金天之西,日没之所,去中华十万亿刹,有极乐世界焉。彼国之佛,身长六十万亿恒沙由旬,眉间白毫,向右宛转如五须弥山,目光清白若四海水。端坐说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树,栏楯弥覆,罗网周张。砗磲琉璃,为楼殿之饰;颇黎玛瑙,耀阶砌之荣。皆诸佛所证,无虚言者。
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盖冯翊郡秦夫人奉为亡夫湖州刺史韦公之所建也。……誓舍珍物,搆求名工,图金创瑞,绘银设像。
八法功德,波动青莲之池;七宝香花,光映黄金之地。清风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乐,咸疑动作。
赞曰:
向西日没处,遥瞻大悲颜。目净四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称极乐。珠网珍宝树,天花散香阁。图画了在眼,愿托彼道场。以此功德海,冥祐为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风扫轻霜。庶观无量寿,长愿玉毫光[15]1324-1328。
《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是李白晚年在湖州应原湖州韦刺史夫人之请,为超度其亡夫而绘制的一幅净土变相画所作的赞文。金银泥画,是用有金银粉末制成的颜料所作之画,金碧辉煌[13]4190。所谓“变相”,在唐代是和“变文”相当相应的佛教名词。徐调孚说:“在唐代,差不多没有一个庙宇的墙壁上不绘着‘变相’;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没有一个庙宇里不讲唱着‘变文’的。再就内容说,据现在我们所知,两者相同的非常众多。所以‘变相’和‘变文’,实际是那时佛教宣传的两种不同方式。”[16]67王伯敏指出了李白《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的创作背景,在唐代,由于净土宗在佛教中影响大,所以在寺院、石窟中画西方净土变相的特别多。敦煌的莫高窟中,唐代的壁画《西方净土变》几乎比比皆是。相传唐代的名僧善导法师居长安,在他的主持下,抄写了弥陀经十万卷,绘制了净土变相数百壁。李白所赞颂的这壁净土变,可能就在当时长安的某寺院中[17]33。李白的这篇赞充分反映了唐代净土宗的影响以及西方净土变相壁画的丰富意蕴,与光彩夺目的敦煌净土变壁画辉映互鉴。
李白诗歌古注本中,以清代王琦笺注此赞文最为详尽。王琦注引《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法苑珠林》《南齐书》《释氏要览》《大阿弥陀经》《佛报恩经》等佛经与史书,为赞文内容做了详细注脚。李白所赞的这铺《西方净土变》,以阿弥陀佛本尊为中心,有山水、楼殿、装饰,呈现出一个华丽庄严、气象万千的极乐世界。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相是根据《阿弥陀佛经》或《观无量寿佛经》的内容来画的,从环境到人物都非常具体。王琦引《佛说阿弥陀经》来佐证赞中描绘的极乐世界:“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黎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黎、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彼佛国土常作天乐。”[15]1325李白所描绘的佛像,王琦注引《观无量寿经》:“无量寿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陀恒河沙由旬,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如五须弥山。佛眼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15]1326李白赞生动反映了佛经中的极乐世界,也真实地表现出唐代净土变相画的绘画特征,尤其是题目中的“金银泥画”,独具特色。这幅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秦夫人极为珍视,“誓舍珍物,搆求名工,图金创瑞,绘银设像”,力求完美呈现极乐世界。关于金银泥画的材质,王琦注云:“图金创瑞者,泥金为质地,而以为创始。绘银设像者,以银代彩色而绘成形像。”[15]1327王伯敏认为,这与敦煌莫高窟现存唐画西方净土变在色彩处理上是不一样的[17]36。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西方净土经变如奇葩绽放,光彩夺目。据统计,仅莫高窟一处就有观无量寿经变78铺、无量寿经变和阿弥陀经变共37铺。唐代壁画诗丰富的佛寺题材与诗歌情境,也为敦煌盛唐壁画研究提供了诸多视角。
四、余论
中国传统的诗与画有着天然的亲近感,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具有诗画互证的可行性。诗歌语言与绘画语言都是文本的构成要素,同时作为独立的文化符号又具有自身特定的意义与内涵。尤其是唐代壁画诗,以文字描摹画面,赋予了写实与想象的双重空间;而敦煌唐代壁画,以绘画的物质材料与艺术结构来展现佛寺等现实生活场景,同样也赋予了写实与想象的双重空间。
艺术作品的“物象”是一种特殊的具象化了的文本形式,一种诗性语言,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浸透着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与想象。诗歌文本中的物象,特指由具体名物构成的语象,是提示和唤起具体心理表象的文字符号。唐代诗歌中的名物极其丰富,不仅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具体名物为主体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也反映出唐代政治、社会与生活的种种细节,成为诗史互证的重要载体。敦煌壁画中大至宗教、音乐、舞蹈、世俗生活等场景,小至器具、服饰、妆容、纹样等物象,都是唐代诗歌重要的审美主题与表现元素,共同构成丰富的审美融合视域。将这两种艺术形式置于唐代社会历史的广义文本框架下给予考察与研究,显然存在比较大的研究空间与学术价值。
注释:
① 本文所引朱谏注语皆出自:[唐]李白(撰),[明]朱谏选注,李诗选注[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1572)朱守行刻本。为避繁琐,恕不一一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