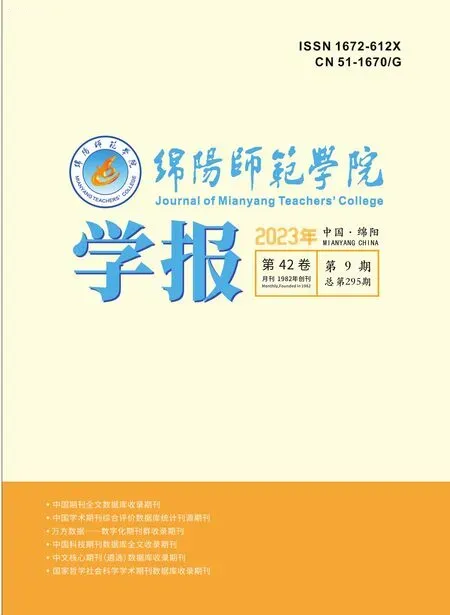纪昀与洪亮吉流放新疆诗歌书写之比
2023-11-17迟晶元
迟晶元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考察有清一代,在发往新疆并留下相关诗作的流人中,乾嘉两朝人数最多,而纪昀与洪亮吉同有四库背景的知名文人恰在其列。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馆开,纪昀被任命为总纂官,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勘阅事宜。同年安徽省于太平府设局,搜集遗书,当时在朱筠幕府的洪亮吉总司其事,主持征集眷写之事,后乾隆四十四年(1779),洪亮吉入京参与四库馆校书。关于纪昀与洪亮吉的交往,洪亮吉在贵州学政期间作有《续怀人诗十二首》,其中《纪尚书昀》回忆道:“只我最饶知己感,下春官第枉高轩。”[1]809诗注言:“先生主甲辰会试,余试卷最为所赏,欲首擢之,为监试御史所阻而止……彻棘后又枉道过访。”[1]809吕谱对此事也有记载:
先生年三十九岁。正月十八日,抵都门。三月,应礼部会试。……总裁蔡文恭公及纪公昀奇赏之。纪公尤撃节五策,必欲置第一。时内监试丰润郑侍御瀓以得卷迟,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纪公坚持不允,因为相与忿詈不可解。总裁胡公高望调停其事,遂置不录。纪公于卷末赋《惜春词》寄意。出闱,即先诣寓斋相访焉[1]2337。
可见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会试中,纪昀对洪亮吉的赏识与知遇之恩。及洪亮吉入翰林,与纪昀常相过从,交往甚密[2]144。二人于京师时情谊匪浅,又因缘巧合于不同时间被流放新疆。
乾隆三十三年(1768),纪昀姻亲卢见曾涉扬州两淮盐运使司亏空盐银税案,纪昀瞻顾亲情,为卢家擅行通信,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任为秘书官,助佐军务。乾隆三十六年初(1771)获释返京。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犯言直谏,流放伊犁,“初派督催处行走,后又改册房”[1]1211,在戍所未达百日即赦回。对纪昀与洪亮吉两位著名的乾嘉文人来说,流放新疆无疑是其人生的重大挫折,可如此经历又帮助他们拓宽了写作题材,丰富了文学创作。新疆,古称西域,清代以前,由于很少有人亲自到达,中原人士对新疆的印象在“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3]1691等诗句的不断强化下,形成了固定看法,即新疆是遥远神秘的不毛之地,荒凉苦寒,有去无回。但随着清廷统一天山南北,迁入大量人口对其进行开发,新疆的面貌已大有改变。当纪昀与洪亮吉以流人身份亲自踏上新疆这片土地时,他们一方面抱怨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叹命运多舛,另一方面又惊叹新疆的雄奇山水,歌咏风光;一方面感慨自身境遇的变化,悲凉寂寞难以排遣,另一方面又欣喜新疆生活的繁荣幸福,赞颂朝廷功绩。如此复杂纠结的情感充斥心头,二人感物吟志,用同而不同的书写内容丰富了乾嘉新疆文学图景。
一、自然风光之书写
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自序道:“今亲履边塞,纂缀见闻,将欲俾寰海外内咸知圣天子威德郅隆,开辟绝徼。龙沙葱雪,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无极。”[4]1即纪昀是感于新疆的巨大变化,为了称赞乾隆的十全武功,歌颂清廷的鼎盛而创作《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这一百六十首七言绝句分为风土、典制、民俗、物产、游览、神异六部分,读来就像一本介绍乌鲁木齐的科普书,明快畅达又面面俱到。
与纪昀系统的内容分类不同,洪亮吉的新疆诗歌是其赴戍、在戍、赦归过程中的实时记载,收录于《万里荷戈集》和《百日赐环集》中,从《八月二十七日请室中,始闻遣戌伊犁之命,出狱纪恩二首》算起到《凉州城南与天山放别歌》共一百三十三首。这一百多首诗歌连在一起,宛如一部详细的个人旅游日记,记录了洪亮吉沿途所见所想,既描写了雄奇的自然风光,也展现了旅途艰辛,既反映了新疆的风土人情,也含蓄记录了自我的情绪心态。
刘勰在探讨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时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5]695自然景象是文思之奥府,是文学创作之源泉,会对个体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感发作用。以此观之,当奇异的新疆自然风光投射在纪昀与洪亮吉心中时,二人怀着不同的情感与审美情趣,展现出同且不同的书写特点。洪亮吉的戍途所见所感,“万古飞难尽,天山雪与沙。怪风生窟穴,战地绝蓬麻”(《安西道中》)[6]82,“狂风飞牛羊,往往集空谷。三更寒雾重,马足植如木”(《安西至格子墩道中纪事》)[6]84,新疆环境与中原环境相差极大,多极端恶劣天气,且洪亮吉赴戍时正值秋冬之际,低温暴雪连续不断,代步的马已四蹄僵直,行动艰难。荒寒的大漠中,更有狂风可将牛羊吹上天空,“北风排南山,山足亦微动”(《肋巴泉夜起冒雪行》)[6]101,甚至连山脚也已微微动摇,虽有夸张色彩,但也是在实写戍途艰辛。“北风吹雪入鬼门,风定雪已埋全村”(《三台阻雪》)[6]118,交通受阻也是常有的现象,被迫困在原地不能前进的诗人“无卧具,无食物,冷坐一宵”[6]62,如同在鬼门关徘徊。更有命悬一线之时,“车箱压马马压人,马足只向人头伸。身经窜逐死非枉,只惜同行仆无妄”(《覆车行》)[6]100,车马翻覆,险些丧命,自己本是流放之人也不算枉死,但可惜僮仆却遭此无妄之灾。戍途漫漫,艰险万分,洪亮吉不能不生出浓郁的死亡意识,恐自己有去无回,死于流放途中。
虽说风雪苦寒逼人,但洪亮吉诗中更多的是对奇特自然风光的歌咏。在清代新疆诗人的笔下,天山是不可不赞的一道壮丽风景,高俊雄奇的天山不仅给诗人带来了视觉冲击,也带来了心灵的震颤和美的陌生化享受。洪亮吉出关后的第一首诗感叹“却出长城万余里,东西南北尽天山”(《出关作》)[6]80。洪亮吉半生游览,中原和西南的名山大川都曾尽收眼底,但他依旧被绵亘东南西北的天山所震撼,同巍峨险阔的天山相比,五岳都已变得渺小了。在《天山歌》中,洪亮吉更是铺采摛文,浓墨重彩地绘出天山种种奇观:
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穷冬棱棱朔风裂,雪复包山没山骨。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濛万年雪。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青松岗头鼠陆梁,一一竟欲餐天光。沿林弱雉飞不起,经月饱啖松花香。人行山口雪没踪,山腹久已藏春风。始知灵境迥然异,气候顿与三霄通。我谓长城不须筑,此险天教限沙漠。山南山北尔许长,瀚海黄河兹起伏。他时逐客倘得还,置冢亦象祁连山。控弦纵逊票骑霍,投笔或似扶风班。别家近已忘年载,日出沧溟倘家在。连峰偶一望东南,云气濛濛生腹背。九州我昔历险夷,五岳顶上都标题。南条北条等闲尔,太乙太室输此奇。君不见奇钟塞外天奚取,风力吹人猛飞举。一峰缺处补一云,人欲出山云不许[6]87。
全诗构思奇特,极近夸张之能,首四句就将天山之大之雄表现得淋漓尽致。随后又从不同方面描绘出天山种种奇观,千古不化的积雪,如玉般的绿石、奔腾的飞瀑、奇妙精灵的生物,甚至在这神奇的冰雪世界里,竟还藏有春风,如此灵境应当是与天上的仙界相通吧!接下来诗人的思绪跳荡开来,由对雄山胜景的描写转为抒怀言志,联想到开边破敌的霍去病、投笔从戎的班超以及阿史那社尔等古代名将,借以表达自己的报国热情。虽然现实中自己被贬边塞,离家久远,但此刻在诗人胸中升起的感情却不是悲苦和惆怅,而是对边疆雄山的由衷赞美、振奋激动之情。正如星汉所言:“洪亮吉感受到了天山的脉搏,天山也给他的诗作增添了豪迈瑰丽的气韵。”[7]322无怪乎洪亮吉后于《松树塘万松歌》中挥笔:“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6]93在奇异景观的触动下,诗人纵情狂呼,将生死置之度外,尽显其乐观好强、豪放不羁。还有“一峰西来塞官路,峰顶一峰复回互。人疲马懒亦少休,云外飞桥落无数。山坳路古盘如线,却向林梢瞰遥甸。一片伊吾晓日华,黄金世界空中现”[6]90(《进南山口》),山岭叠叠,路亦曲折,但当登顶极望时,彩霞满天,灿然美好如一片黄金世界。洪亮吉移步换形,写尽了南山即天山东段的灵奇风光。
同样,纪昀也记录了一些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如狂风,“城南风穴近山坳,一片涛声万木梢。相约春来牢盖屋,夜深时卷数重茅,”[4]21(《风土其十九》)“惊飙相戒避三泉,人马轻如一叶旋,”[4]21(《风土其二十》)既直接描写风力之大可卷走屋顶、人马,又突出了大风来临前的声音,渲染恐怖氛围,还有干旱多沙、冰雪崎岖等等。但较之洪亮吉,纪昀没有注重突出出塞之苦,更多的是展现新疆自然风光的秀美,在给家人的信中,他认为遣戍所见的风景“反多雅趣”[8]20。例如同是写雪,洪亮吉记述的是令人生畏的严寒暴雪,纪昀却是出于欣赏、喜爱的情感而描绘神奇的雪景。如“流云潭沱雨廉纤,长夏高斋坐卷帘。放眼青山三十里,已经雪压万峰尖。”[4]8(《风土其四》)城内夏日炎热,但山中依旧长寒,细雨绵绵过后,诗人卷帘遥望,在逶迤绵延的青山映衬下,峰尖的皑皑白雪令人赏心悦目。又如“万家烟火暖云蒸,销尽天山太古冰,”[4]7(《风土其三》)原本万古难消的天山冰雪现在由于气温逐渐升高而渐渐融化,侧面反映了新疆人口的不断增多,烟火繁盛。纪昀笔下还有饶有趣味的新疆水景,“雪地冰天水自流,溶溶直泻苇湖头。残冬曾到唐时垒,两派清波绿似油,”[4]9(《风土其六》)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河水不冻,依旧流淌不息。“白道飞流似建瓴,陡陀不碍浪花鸣。游人未到萧关外,谁信山泉解倒行,”[4]10(《风土其七》)流水逆行的奇景在这里也可一睹为快。以及“乱山倒影碧沉沉,十里龙湫万丈深”[4]13(《风土其十》)的天池,“界破山光一片青,温暾流水碧泠泠”(《风土其十一》)[4]13的水磨沟温泉等游览胜地。总体来看,纪昀是以观赏游览的心态来书写新疆的自然景观,突出再现其美好可爱,富有情趣的一面。洪亮吉则是情随景移,捕捉新疆自然环境或艰险或壮美的特点,结合自己的奇情奇思进行艺术化的再现。
二、物产经济之书写
与中原地理环境大为不同的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其中有许多是中原地区稀缺或是不曾见过的。随着乾隆统一天山南北,重视开发经营,新疆已不复当年的落后荒凉,而是生产、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纪昀注意到了这些并记录在《乌鲁木齐杂诗》的物产部分。这些丰富独特的地方物产,既能体现地方特色,也有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
首先是种类繁多的瓜果菜蔬。深处亚洲内陆,光热充足的新疆素有“瓜果之乡”的美誉,自古盛产甜瓜、葡萄、苹果、桑葚、枣、桃等瓜果。恰如纪昀称赞的“种出东陵子母瓜,伊州佳种莫相夸。凉争冰雪甜争蜜,消得温暾顾渚茶”[4]73,(《物产其五》)“甘瓜别种碧团栾,错作花门小笠看。午梦初回微渴后,嚼来真似水晶寒”(《物产其六》)[4]74,品种多样的甜瓜甘甜如蜜,其清凉爽口使人回味无穷。特有蔬菜品种味道也是一绝,如清爽甘脆的黄芽菜“旋绕黄芽叶叶齐,登盘春菜脆玻璃”(《物产其七》)[4]75,纪昀称赞其味道口感可与家乡的徐水萝卜相媲美。其次是因独特的地理环境而孕育的独特生物品种,像是“昌吉新鱼”“凯渡河鱼”这些风味不减江南的水禽、“年年珍重进彤围”的稀珍野鸡、“风味盛黄羊”的野骡,芨芨草、梭梭、红柳,玛努香、阿魏等药材植物。生产经济的发达自然也带动了贸易的繁荣。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乾隆年间,扼北疆之咽喉的乌鲁木齐成为了新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新疆内外的各种产品都在此汇聚,“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谁知只重中原味,榛栗楂梨价最高”[4]73,(《物产其四》)物以稀为贵,吐鲁番商人挑担卖果,最受欢迎的水果不是苹婆、杏或蒲桃这些本地特产水果,却是中原运来的榛栗楂梨。还有《物产其九》谈到的万里之外运来的橘子和黄柑,这些来之不易的中原水果,只有当地的“有力者”才能购得。
新疆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乌鲁木齐地区目前已探明近三十种矿藏,其中就包括《物产》中提到的铁、金、硝、云母、煤等,例如“温泉东畔火荧荧,扑面山风铁气腥”[4]84(《物产其十九》)一诗,此中描绘的炼铁景象在嘉庆年间的《乌鲁木齐政略》《乌鲁木齐事宜》里也有记载,“以迪化城北热水泉地方产有铁矿”[9]72,“查铁厂一处坐落迪化州东北八十里,山内设炉子五座”[9]139,这些都可印证新疆矿产资源的丰富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也侧面体现了纪昀诗歌的写实求真。
洪亮吉也有涉及新疆物产经济的诗歌,主要集中在《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但因与当地交流时间过短,洪亮吉没有象纪昀一样详细地进行分类描述,而是多选择将这些物产化为诗歌中的意象群,借以烘托气氛,营构意境。如“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6]127(《伊犁纪事诗其十二》),“游蜂蛱蝶竞寻芳,花事初红菜甲黄”[6]129(《伊犁纪事诗其十七》)。春风乍暖,百花盛开,鸟儿觅食,游蜂戏蝶,一幅欢腾热闹的新疆春景图跃然纸上。又如“鹁鸪啼处却东风,宛与江南气候同。杏子乍青桑椹紫,家家树上有黄童”[6]134(《伊犁纪事诗其二十七》),“山沟六月晓霞蒸,百果皆从宴上升”[6]137(《伊犁纪事诗其三十四》),虽然伊犁地处偏远,但到了入夏时节,这里却同江南气候一样安适愉快,生机盎然,既有美味可口的杏子、桑椹、甜瓜等百果成熟,又有馋嘴的孩子爬上果树戏耍,童趣十足。所写之景皆含欢悦之情,景情浑然一体。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边境少数民族的商贸活动逐渐开展起来,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伊犁是中原与哈萨克、布鲁特等归附清廷部族的主要交易点,洪亮吉就描绘了这种边境贸易的盛况,“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6]124(《伊犁纪事诗其六》),自注言:“布鲁特每年驱牛羊及哈拉明镜等物至惠远城互市。”布鲁特是清朝时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他们每年三到九月会带来大量马牛羊和皮革等来交易换取粮食、布匹、丝绸、茶叶或者其他日用必需品,这时的集市人山人海,堵得水泄不通。还有《自乌兰乌素至安济海,雪皆盈丈,十余日不见寸土,因纵笔作》云:“群驱羊马作互市,从此番回悉衣被”[6]112,都反映了清朝乾嘉时期边境贸易的繁荣。
在物产经济书写方面,纪昀与洪亮吉新疆诗歌中最不容忽视的是对屯垦戍边的记述。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后,为了巩固新疆统治,实行了旨在“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开发经营方针,如此大规模、有计划的屯垦活动不仅为戍边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维护了边疆稳定,也毫无疑问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洪亮吉在《四十里井讯》中写道:
四十里井间,只有十家住。十家汲井过,并向麦畦注。麦肥如野菽,饱食耐征戍。耕余了无事,间或插桑苎。遂令半里间,夹屋无杂树。南山团作障,三面塞去路。时有归墟人,穿云白如鹭[6]161。
“四十里井”是地名,在今阜康县城东一百三十五里,设有塘汛。诗人用平实自如的语调,叙述了四十里井及滋泥泉子一带屯垦耕种的日常片段。在人烟稀少、适宜耕作的四十里井,麦苗如同野菽一样茂盛地生长着,屯民们在耕种麦苗之余,也会栽种桑树与苎麻。在这恬静的环境中,偶有归墟之人,远看仿佛穿过云层的白鹭,静中有动,愈显田园风光的自然悠闲。全诗语言通俗浅显,让人觉得如叙家常,亲切淳朴,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而与洪亮吉相比,纪昀作为较早描写新疆屯垦戍边题材的著名文人,他饱含热情,客观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屯田的制度与规模,丰富全面的歌咏连同其自注可视为一部“清代前期的屯田史”[10]55。例如《风土其二十四》和《物产其十四》:
秋禾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三十四屯如绣错,何劳转粟上青天[4]25
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4]80
两首诗以热情洋溢之笔,共同勾勒出屯田的热闹丰收画面。秋禾春麦,波浪翻涌,良田相属,稻米飘香,乌鲁木齐辖地的三十四个兵屯,远瞰如同华丽的锦绣一般交错铺展在大地上,其生产的粮食充足,已不需再从中原千辛万苦地转运;原籍甘肃高台的北郊屯田民户们辛勤劳作,年年丰收,米质优良颇似吴杭的稻米,这是何等喜人的景象!
此外纪昀在《典制》和《民俗》中也提及了屯垦的管理制度,再现了屯户们不同的生活状态。像是“藁砧不拟赋刀环,岁岁携家出玉关。海燕双栖春梦稳,何人重唱望夫山”(《典制其七》)[4]32,记录兵屯官兵们举家团聚,安心边疆,不必忍受分别之苦;“鸡栅牛栏映草庐,人家各逐水田居。豆棚闲话如相过,曲港平桥半里余”(《民俗其十八》)[4]51,以清新闲适的笔调描写了民屯“一家村”的田园生活。兵屯和民屯的屯民安居乐业,而犯屯的遣犯们却是叫苦不迭。纪昀于诗中记载了一种名叫钻天啸的鸟,“山鸟一声天半落,却来相唤把锄犁”[4]109(《物产其五十》),此鸟四更便引吭而鸣,睡意朦胧的遣犯听到上工的信号,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拿起锄、犁开始新一天的劳作。遣犯是屯民中“政治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生活最苦的一个阶层或群体”[11]97,其从事的劳动之繁重,开发边疆的艰辛不言而喻。
得益于合理的屯垦政策以及屯民的辛苦劳作与不懈努力,清朝新疆的开发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新面目。富饶的物产和繁盛的经济贸易让纪昀与洪亮吉笔下的新疆不再是令人色变的荒凉贫瘠之地,而是秀美宜居、温馨热闹的繁荣之地。置身于“一统极盛”时代背景的纪昀与洪亮吉,自然而然地以真切体验和审美表达抒发了对新疆繁荣昌盛的赞美,对国家民族统一的自豪感。
三、文化风俗之书写
在以往的新疆诗歌中,新疆的文化风俗总是以一种异域的、神秘的面目出现,但在清代乾嘉诗人笔下,新疆文化风俗的面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是纯粹的他者文化,而是让人感觉熟悉,甚至是认同。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在中原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清时期的新疆文化与中原文化正在相互融合,多元的文化风俗在新疆共存繁荣。例如纪昀《典制其四》《典制其五》《物产其六十七》中提到的八蜡祠、痘神祠、露筋祠。这三种祠庙本是中原信仰习俗,随着中原居民的不断迁入,新疆本土人民受其影响,当发生田鼠、天花和花蚊之害时,便会修建祠庙并虔诚祭祀,可见两地信仰风俗的渐渐统一。新疆的饮食风俗同样也在逐渐发生改变。“酒果新年对客陈,鹅黄寒具荐烧春。近来渐解中原味,浮盏牢丸一色匀”[4]56(《民俗其二十四》),年节时,热情好客的新疆人民除了用馓子和烧酒招待客人外,还会依照中原做法制作一些粉团糕饼。“蒲桃法酒莫重陈,小勺鹅黄一色匀。携得江南风味到,夏家新酿洞庭春”[4]70(《物产其一》),以江南的绍兴法酿新疆葡萄酒,酒质可与江南的洞庭春相媲美,这种生产方法与口味的创新丰富了新疆的饮食生活。
教育文化风俗方面,“芹春新染子衿青,处处多开问字亭。玉帐人闲金柝静,衙官部曲亦横经”[4]64(《民俗其三十三》),新疆社会原来都以卒伍为正途,开始兴办教育后,社会风气逐渐转变,处处是书院学堂,弦歌相闻,书声琅琅。娱乐文化风俗也见融合趋势,“玉笛银筝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4]133(《游览其九》),纪昀在诗后自注:“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清代是戏曲,特别是地方戏迅速发展和日渐繁荣的重要阶段,而伴随着中原移民的足迹,优伶歌童、各类剧种也随之而来。除京剧的广受欢迎以外,杂剧、昆曲、楚调、越剧等也同样在新疆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些戏曲艺术在新疆的传播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原移民的思乡之情,在这种类似于中原的文化氛围中,移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新疆戏曲的熏陶,慢慢产生了认同感,促进了新疆与中原艺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下面这首最能体现两地文化交融:
地近山南估客多,偷来番曲演鸯哥。谁将红豆传新拍,记取摩诃兜勒歌。[4]130(《游览其六》)
“估客”即商贾,指从中原来新疆的商人,鸯哥本是维吾尔族妇女之意,此处指歌女。这些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在春社时诙谐风趣地扮为新疆歌女,为大家演唱一种新“番曲”,这首改编再创的歌曲,歌词来源于“红豆”代指的汉族情歌,乐曲则是取自新疆笳曲“摩诃兜勒歌”。纪昀独具慧眼,将镜头锁定在春社节庆时的一群商人身上,他们兴高采烈,自娱自乐,颇具创意地将两地艺术巧妙融合,用维吾尔流行曲调演唱汉族情歌,乐声柔美,独具特色。整首诗纯用白描,娓娓道来,一幅栩栩如生、有声有色的风俗画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当时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节庆时,这样的文化交流则更为明显,儿童玩耍的竹马灯、猜灯谜、舞狮表演等中原的传统风俗娱乐活动风靡新疆,深受大家喜爱。而沉浸在如此热闹喜庆的氛围中的纪昀也跃跃欲试,“迷离不解春灯谜,一笑中朝旧讲官”[4]128(《游览其三》),可没想到新疆的灯谜内容怪奇俚俗,连这位博学多才的翰林院学士也被难住。
与纪昀相比,洪亮吉诗歌中关于新疆文化风俗的内容记载较少,主要是因为洪亮吉在新疆的时间很短,他无法去深切感受,偶尔谈及也只能是简单描绘。且由于自身流放的哀愁,哪怕是节庆日的文化活动,其诗中刻画的景象也总是有些萧条。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二十八日,洪亮吉跋涉了四个多月后抵达巴里坤,“年残风亦暴,客至裹重帷,灯火集一城,宵惊烛光绿”。[6]95(《廿八日抵巴里坤》)年关将至,风雪益加暴虐,全城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春,原本温馨热闹的一切在洪亮吉的眼中却都发出了诡异的绿色,客观的景象因注入了诗人的情绪与意识而笼罩在阴郁的氛围里。吕谱记载,洪亮吉直言上谏后,“始以原稿示长子饴孙,告以当弃官待罪”[1]2345,自知此次上书凶多吉少,流放伊犁更是九死一生。虽然途中面对气魄非凡的新疆奇景时,洪亮吉暂时抛下过遣戍的阴影,但在本应与家人团圆的除夕之日,苦闷之感再度袭来。“世缘应已尽,梦亦不还家”,“他日能归骨,从亲傍水涯”[6]97(《除夕夜坐》),世缘已尽,生还渺茫,洪亮吉只盼望死后的尸骸能回乡安葬在祖宗亲人的身边,孤独哀愁的情思浓重至极。另一首作于除夕夜的诗《除夕巴里坤客帐祀先》,记载逆旅主人在除夕时为客人专门准备了祭祀先祖的场所。“烛借穹庐火,牲求牧泽羊。荒寒一瓯雪,聊抵奠椒浆”[6]96,命运变幻无常,洪亮吉怀着难解的人生哀愁,在荒寒的边疆完成了对祖先的祭祀。“殊方都喜说新年,板屋斜欹彩胜偏。一事暂教乡思缓,家家门巷有秋千”,[6]98(《镇西元日》)嘉庆五年(1800)正月初一,新春新岁,于边城度过了孤单寂寥的除夕夜的洪亮吉,思乡之情浓郁难以抑制,是什么能让诗人的乡思得以暂缓?原来是房屋装饰的彩胜和门巷处的秋千这些家乡常见之物。巴里坤为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从洪亮吉笔下除夕祭祀祖先的场所与物品、春天的彩胜和秋千,可发现巴里坤虽然地处边隅,却早已有了中原文化的印记。
嘉庆五年(1800)五月一日,洪亮吉接到赦回谕旨,百日赐环轰动朝野。赦归途中,洪亮吉遇到了一场神秘的祭祀,“森森女娲庙,客户竞私祭”“黯黯神烛昏,脂车作行计”,[6]180(《度赤金峡》)客户是指外地来此谋生的人,他们一边在悄悄地祭祀,一边在给车轴膏油,而对女娲的神话崇拜显然是中原特色。这场夜晚中的祭祀,烛影昏暗,气氛略显阴森鬼魅。正所谓“一切景语即情语”[12]34,纪昀笔下的民俗活动场景总是热闹欢乐的,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洪亮吉则由于自身难以排遣的悲愁,营造了疏离、凄凉的氛围,甚至扩大了民俗祭祀的某些特征,色调更为阴暗。
四、创作情感之异同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我们就必须要认真考察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可以这么说,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是产生艺术品、艺术家的根本,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3]2换言之,作家的创作总会受“精神气候”,即一定社会政治环境、文学思潮等的制约与影响。乾嘉时期,禁书、文字狱等高压文化专制手段令广大文人噤若寒蝉,不断压抑自身情感。又清廷规定,废员至戍所,由当地官府严加监督、管束。废员在戍所若能奋勉行走,切实效力,就有可能赦回或起用;若在戍所怨望不满,赋闲吟咏,怠于公事,一经地方官员奏闻,则罪上加罪,不仅回籍无望,且要严加责惩[14]38。由此,流放新疆的纪昀与洪亮吉谨言慎行,“余谪乌鲁木齐,凡二载,鞅掌簿书,未遑吟咏”[4]1,“余自经忧患后,夙有戒心,断除笔墨已久”[6]253,“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月,不敢涉笔……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6]65。二人自称无意文字,实际上却并没有停止诗歌创作,而是将诗歌书写重点放在了吟咏自然风光与记录人文风俗上,抒发诸多歌咏风光与国家统一的积极情感。但生存状态的骤然改变与流人身份的不自由令纪昀与洪亮吉始终怀有苦闷情绪,内心世界的冲突令二人流放新疆诗歌交织着多重情感,从而赋予了诗歌独特的韵味。
大量客观写实的描摹令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堪称“无我之作”[7]414。这种“无我”的创作除与纪昀主张“温柔敦厚”的含蓄诗教有关外,也因为纪昀深知此次流放无性命之虞,他心怀东归希望,由此能自如化解流放的凄怆酸楚,保持平和心态。与之对比,洪亮吉的诗歌书写折射出的情感强度较为浓烈。因他是“大不敬”罪,当斩立决,后死里逃生,流放伊犁,期满赦归的可能性很小,而在戍所时,伊犁将军保宁又对他严加管束,心理压力巨大,时常担忧朝不保夕。壮美雄奇的新疆风光可帮助洪亮吉开阔心胸,一展豪情,然绝望痛楚一直难以挥去。直到特旨释归,“此生不料能归骨,万死无言只叩头”[6]150,(《将发伊犁留别诸同人》)诗人深感“命轻恩重”,频频感泣君恩。纵观洪亮吉流放新疆的诗歌书写内容,虽以风土纪行为主,但依旧可以在其中发现他的情感历程。
关于清诗面对的写作困境,“内容的日常化和艺术的平庸化已成为诗歌最突出的现象,诗歌所表现的日常感觉经验也日益陈旧老化”[15]130,流放新疆是纪昀与洪亮吉人生中的重大挫折,但于文学创作而言,新疆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象帮助他们拓展诗料,打破了日常经验的写作困境。正如张维屏在《听松庐诗话》中评洪亮吉言:“及登上第,持使节,所为诗转逊前。至万里荷戈,身历奇险,又复奇气喷溢,信乎山川能助人也。”[15]6789洪亮吉将被流放的情感体验和对新疆的独特感知寄寓在诗歌创作中,“不平则鸣”的情感内涵与异域奇景交织,其诗歌创作也得以焕发生机。同样,《乌鲁木齐杂诗》在纪昀的大量应酬唱和之作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五、结语
共处相同思想文化背景的纪昀与洪亮吉,一前一后流放新疆,本怀着巨大的感恨与忧虑,但当亲眼目睹新疆独特的风土人情后,他们怀着惊讶与好奇,用全面多彩的笔调描绘了不同于前代的新疆风光,以往的新疆荒凉苦寒,“风土断人肠”[3]2037,现在却是“宛与江南气候同”[6]134,一片繁荣安乐的景象。然由于流放经历与情感的相异,二人在共同的内容书写上有着同而不同的表现,同是写山水风光,纪昀重景观之秀美,洪亮吉重风光之壮美;同是描绘物产,纪昀展现得更全面,更写实;同是记录文化,洪亮吉表现得更低落,更疏离。具体书写的差异恰恰从不同方面补充了乾嘉新疆文学图景。目前学术界关于纪昀流放新疆诗歌的研究,角度多样,成果丰厚,关于洪亮吉流放新疆诗歌的研究数量较少,仍有拓展空间。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既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二人的流放新疆诗歌创作,亦可略窥彼时新疆流人诗歌书写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