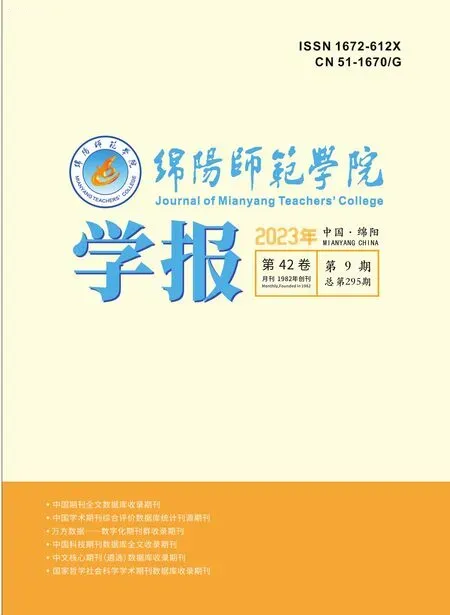身体参与下的艺术意境及意境审美
2023-11-17吴雨临
吴雨临
(四川音乐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四川成都 610021)
意境是极具东方色彩的审美范畴,尤其在中国艺术领域,意境美学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昭示,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思考和民族审美创造。艺术意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意与境和谐、韵味久长的审美特征受到了中国艺术、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1],在明清时期正式成为一种美学范畴后被广泛运用于诗文歌赋、诗词绘画的审美阐述中,成为品鉴中国艺术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美学既不局限于狭隘的诗词与绘画等艺术领域,也不局限于自然美的问题,其本质上是一种凭据直觉力的知觉,遍及于整体性的经验世界[2]132。中国艺术对于意境之美的探索不仅体现在对哲学、玄学、佛学的理解思考,也体现在对“物与我皆无尽也”和“得其环中”的融入性体验追求,所以对艺术意境的品鉴与体验也可以看作是人与世界的具身性交流。见境起情首先需“见”,虚实相生首先要体会到“实”,意与境和谐首先基于实际存在的“境”。人通过视、听、味、嗅、触等各种知觉系统感受到了意境,再经由自己的审美知识和能力进行体会,进而才能品到激荡悠长的美之韵味。
一、艺术意境审美与审美方式
如何体会和感受意境是艺术意境审美的基本问题之一。意境的概念最初生发于佛教中的“境”,“境”也有“境界”之意。佛学把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认识感官称为“六根”。“六根”能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其对应的视、听、嗅、味、触、思维的感官功能称为“六尘”,而“六尘”与外界对象接触产生的六种认识结果称“六境”[3]。“六境”意为六种境界,因代表着人身体具身参与的“六根”而得以生发。唐代诗人王昌龄将适用于诗词的意境也分为了“物境”“情境”“意境”三个层面,其对于“意境”的阐述是:“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4]172-173此外对意境的理解还通常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与“气”结合,或将人对于意境的体悟归于身体肤觉的先行感受。
然而不管是佛学的“六境”,还是王昌龄对于意境的阐述,抑或是人们对“气”的理解以及通过身体肤觉获得的体验,这些不同领域和群体对意境的解释都提到了人的身体。佛教的“六境”是人通过身体器官感知认知世界的结果;王昌龄对于意境的阐述虽然还较为模糊,但也提及了意与境是相互交织,进入人的心理活动而获得的审美体验和意味;哲学上的“气”是人类身体的展现,它在礼乐文化中通过礼仪艺术地展示了一种流动、蕴藉、连绵的状态[5]。美学思想史表明,我们不能仅以“视觉”“听觉”等来限定审美活动以及美学研究范围[6],所以身体为研究艺术意境审美指出了另一个方向,即身体美学。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第十章“身体美学:一个学科建议”中提议建设身体美学学科,此后身体美学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身体美学让美学重新回到知觉、意识、情感这类核心问题上来,这些问题也体现在美学一词的词根含义“感知”(aesthetic)与其常见反义词“麻木”(apathetic)的对比上[2]3。这表明在艺术意境审美活动中不止可以将视角放在难以表述的神秘经验上,还能将身体哲学也作为一种美学,通过人的实在身体与身体感知来体验理解艺术意境。
虽然身体美学由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但对于身体的思考在历史上早已展开。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与普罗泰戈拉的“认识万物的尺度”都意指人要将注意力从自然界转向自身,梅洛-庞蒂也将身体做了“客观身体”与具有认识能力的“现象身体”的区分[7]76。身体是人认识世界的第一途径,其不仅是搭载我们意识的载体,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和储存经验的记忆宫殿,面对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知识内容亦能通过最直接的身体接触来进行区分和理解。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音乐是一些个体,即一些我们不能在其中把表达与被表达者区分开来的存在——它们的意义只有通过直接的接触才是可以理解,而且它们不用离开其时空位置就能够传播其含义[8]215-216。实践基于客观实在的身体,在艺术意境和意境审美中,无论是欣赏艺术作品、品味艺术意境的观众,还是需要创作艺术作品的艺术家,都需要通过身体的观察和实际动作来具身参与,才能进而切身体会和感知到艺术中的意境。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便可以谈论艺术意境中身体的问题。
二、艺术意境中的身体
人不可能凭空进行审美活动。艺术意境的生成或寄托首先需要艺术环境的存在,该环境可以是诗词歌赋等艺术作品,也可以是山川景色等自然景象,不同内容在组成环境之余还会形成互为主客体的环境场。当艺术作品以客体姿态作为艺术活动中的观赏对象时,主体就是存在于该审美空间中进行着审美活动的人的身体,是身体作为纽带将人与审美环境及艺术意境联系在一起。赵之昂说:“意境的审美空间所基于的是人类身体——肤觉的空间扩展和充盈,而这一空间扩展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9]由此看来,除了作为环境中的主客体外,人的肉身也同样可以看作一对主客体——作为自我的主体身体和作为环境中以感受者形式出现的镜像客体。
作为自我的主体身体是人本身,人对于意境的体验首先来源于身体本身,究其原因是人的身体提供了这种视角——其坐标原点或起点[2]97。“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来”不仅能体现出诗人身体所处的空间方位,也能在阅读时带给我们扑面而来的感受。也就是说意境审美是通过身体的知觉,如视、听、味、触、嗅等先唤醒我们的意识,进而在具身感知到的现实基础上通过知觉经验调动我们的情绪,最后达到情景意识统一和谐、带给我们审美体验。李白在《夜宿山寺》中写道,“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10]1470。诗句不仅描绘出了楼的状态,更暗示了身体在审美空间下如何自然伸展,体现诗人作为主体看到、并登上寺楼后引发的对身体空间扩展的表达。在峻峭挺拔、高耸入云的寺楼上诗人欣赏到了灿烂星汉、伸手就能摘到星星;为了进一步描写楼高,诗人甚至不敢大声说话,唯恐声音惊醒了天上的仙人。在身体作为知觉主体具身参与的前提下诗人才能有如此观察与联想,寥寥二十字就将楼高夜静和浪漫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文化讲究的“天人合一”“身心合一”,也无不揭示着人在生活生存和精神发展中身体的重要性和对身心灵肉达到浑然一体境界的精神追求。
而作为镜像客体的身体则是审美环境的接收对象。身体对环境的感知先由环境中的运动传达到人,再经由人的主观能动转变为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身体作为艺术意境中的“外来客体”接受了意境的显现,但这并非意味着人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只能僵硬无为地被动接受审美环境的变化。以视觉和人的观察为例,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提到“视觉在观看形状时完完全全是一种积极的活动”“在观看事物时,我们是在主动地捕捉它们”[11]39。人在艺术意境中从感官知觉的体验到唤醒情感意识的过程其实都是一种将身体融入环境的融入性审美过程。“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是审美意境中情景交融的体现,秋色进入视野、秋风吹拂皮肤,让诗人知觉到了秋之颓唐,引发了诗人的重重心事,而心事重重又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诗人感到所见之景更加秋意浓重。身体除了接受环境带来的变化和捕捉正在变化的环境外,还能主动参与进审美的场所,构成艺术意境中的客体之一。“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李白同月与影的歌舞即为自我的身体融入以夜色、月亮与酒造就的审美场,诗人不仅感受着审美意境,也造就丰富着意境环境的内容,在这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之意境中达到了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与和谐。由于人对艺术意境有了高度的审美体验,所以即便审美过程告一段落,人仍能感受到意犹未尽、韵味久长。审美过程不仅会形成审美经验,还会丰富过往的审美体验,最终会提高人的审美水平。“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是诗人对于意境审美结束后的回味,即使“醉后各分散”,这一份审美意境和体验仍然永存于心与记忆之中。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身体在审美环境中作为主体还是客体并非固定不变的。当人沉浸在艺术环境中时,身体及其所经历的感受、启示、领悟并非以机械式的固定顺序出现,也有可能是一种存在着乱序或同时生发可能性的“双重感觉”。这种“双重感觉”在梅洛-庞蒂看来类似于“左右手相互按压”,这种按压涉及的并不是人同时体验到的两种感觉——就像我们知觉到两个并置的客体那样,而是两只手可以在此轮换“触摸者”和“被触摸者”功能的含混构造[12]。对于意境审美来说,主客体交换意味着选择不同的视角、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瞥见不同景象。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描述了自己江上漂泊的感受:“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10]1318在此意境环境中,苏轼的身体作为纵舟而游的主体,能通过身体感受到的移动和视线环境的变化、切身感知自己纵舟在浩渺江面上越过;而当他作为江景中的客体与扁舟合二为一时,又任由江水荡涤推送他与小舟,通过小舟的动态变化体会到了浩淼飘然,仿佛乘风飞行进入仙境的感受与审美环境。
除了审美环境外,人在进行艺术意境审美时还需要审美经验。体会艺术意境的方式不止有品鉴审美场中寄托了意境表达的客观物质,还能够通过人在审美过程中引发重现的内隐记忆与当下个人体悟交织。审美经验介于神秘经验与科学知识之间[7],同审美环境一样影响着人进行艺术意境审美的能力。作为一种经验,其必然先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但身处艺术环境中的人如何体会到无形的意境,又为什么能沉浸融入审美环境之中,其审美经验又如何自然而然被唤起?这种被情景和现实影响而调动起的意境体验其实源于潜藏在人身体中的内隐记忆。
三、身体内隐记忆与艺术意境审美
隐性记忆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界定为不需要在意识或有意回忆的情况下,个体的经验自动对当前任务产生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记忆,通常指无意识下使用出来的记忆[12]203。隐性记忆来源于人的身体,是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内隐记忆,甚至可以体现为身体记忆和肌肉记忆。意境体验并不能凭空从人的本心生发、不单是因外界刺激而产生的荷尔蒙、也不依赖于特定的身体器官,而是多种条件认识综合的结果。内隐记忆不仅能帮助审美者进行意境审美,还能在艺术家描绘、营造意境时提供经验记忆和灵感。这里的身体记忆并非单一地指肌肉记忆或技巧的熟练度,也指内化于艺术家内心用以串联各种思想和表达方式的隐性记忆。有时,身体认知所形成的隐性记忆还表现在隐喻上,如“推敲”本是肢体动作,但在语言中常被隐喻为琢磨、思考,诗词绘画中的隐喻更不胜枚举。诗词绘画中的意境大多由现有的“境”进入飘渺的“意”,在这里境为环境,意则多是抽象的隐喻内容,如在惜别时出现的柳,在思乡时(“天涯共此时”)的月。对这些隐喻内容抽丝剥茧,我们可以发现原型基本来源于社会生活与身体认识,是一种内隐化的身体经验。作为记忆内容的经验不能直接显像于我们审美时的真实环境,所以发觉这些隐喻的内容的途径之一即是我们身体在相似环境下的再次活动。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是中国艺术意境审美中虚实相生的表现。诗人看见“实”的月亮,唤醒了对日夜交替这一现象的记忆,无需刻意推理就能知道残夜必将迎来破晓。这一隐性记忆经由诗人内化于心的审美水平和学识文化,进一步联想到对时光“虚”的思考。实在眼前,虚在意念,中国文化中的“和”在此表现为诗人融入了环境与意识共同构建的和谐审美场,在这一虚一实中诗人不仅体会到了通俗意义的美景,还在和谐的审美中调动了身体,让自身意念与环境统一共鸣,最后从身体体验升华到了审美体验和哲理思考。苏轼“胸有成竹”的审美学说从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画家通过对于画竹这一动作的不断重复得到了技巧层面的纯熟,即使不观察真实的竹子也能轻松地画出来;而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胸有成竹”吸收了佛道哲学的心性思想,意在强化心作为官能之主宰所秉有的包藏万有、创生万物之潜能[13],这里“强化心的潜能”实际就是内化于心的各种生活经验与审美记忆,即“审美底蕴”,它们融会贯通后往往能产生出比单个记忆更强的审美能力,这与格式塔心理学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说法异曲同工。
作为观赏者,感受艺术意境的能力同样来源于身体记忆和审美经验。“意境”审美较之一般的意象审美和艺术创造,更具有人生感和历史感,更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味[14]。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表达的悲情怆然就源于被自然景色引发显现的过往知识和个人经历。可以理解为诗人领悟到的“环境之意”是对“境”做了初步审美活动,但最终目的是用以抒发个人情怀之“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除了表达现实场景中前后无人外,实则在暗喻过往明君已逝,自己无法在他们麾下一展抱负,也无法得知后世是否还会有明君出现的愤慨。诗人生不逢时,在这一前一后中化作了一个静止的点,本就显得空虚,再加上目光所及之处一片苍茫,更加觉得一腔抱负在天地之间无处寄托。此时诗人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倾向于悲观,故天地辽阔无法引发豁达情绪,只令诗人无可奈何、无聊迷茫,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于后世品诗者来说,能够理解陈子昂为何怆然的人必定对古往今来历史浮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必然在生活中也有过怀才不遇、迷茫未来的相似经历,被唤醒的过往记忆或许还能够进一步激发后世品诗者的爱国情怀和人生抱负。在这里,人们对诗词品鉴的意境审美过程就体现为我们所说的“共情”。
在此不由令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满江红·点火樱桃》:“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15]2陈子昂前后瞻望,辛弃疾远眺遥望;陈子昂看见了天地悠悠,辛弃疾看见了山峦交错;陈子昂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看不见施展一腔抱负的可能性,而辛弃疾面对国破家亡,望不见家在何处,寻不到自己的归处。一诗一词朝代不同、因缘各异,但其中流露出了相同的孤独茫然、愤懑悲伤和渴望报国的情感。一个印象没有能力唤醒其他印象,只有以它首先被包括在过去经验(它在那里与它要唤醒的那些印象碰巧共存)的视角中为条件,它才能唤醒其他印象[8]42。耄耋老人与初生孩童、王公贵族与流浪者,在观看同一事物时体会到的内涵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知识内涵、生活需求各个方面都有区别,所以毛宣国说,对于“意境”审美来说,人生感和历史感的生成是非常重要的[14]61。
虽然诗词中诗人抒发胸臆大多先以身体为起点,赏诗者对诗句的品味大多以内隐记忆为体验源头,但中国艺术的意境并不局限于诗词美学之中。中国整体的艺术体系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视觉艺术,都包含了艺术意境与意境审美。艺术意境的呈现方式是丰富的,对于意境的体验认知也是多种环境因素与个人综合素质感知的统合,所以意境审美还可以以人的身体实践形式展开。梅洛-庞蒂说:“作为运动能力或知觉能力的系统,我们的身体不是‘我思’的对象:它是走向其平衡的一组被亲历的含义。”[8]218身体下的意境审美过程不仅使意境造就的审美场可体验化,也为艺术意境研究找到了更贴合人本身的审美途径。从身体美学理解艺术意境能更细微地体会到意境之源与意境之美,所以从身体角度出发的艺术意境审美特征也可以理解为:情景交融是身体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场所体现,虚实相生是对身体记忆及内隐记忆的唤醒,意与境的和谐是人的经历情感与审美环境场所的共鸣,韵味久长是对身体内隐记忆的下一次铺垫。对艺术作品与艺术意境的分析体悟是意与境施于人的身体、经由人的意识处理、再生发而出的人的新的体验。时间是不可逆的,所以即便相似的审美环境引起了内隐记忆的共鸣,眼前看见的与体会到的“实”也必然不是当初的“实”。“实”在这一刻达成了“虚”的转向,这一转向并非两级的瞬间转变,而更像交融汇合后的分流,所以人在虚实转向和虚实结合中能将旧的经验与新的体验结合,体会到新的艺术意境之美、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这即是艺术意境与人灵魂身体的循环感知。此外,“眼见为实”的客观实在除了肉眼看到事物景象外,还有因触景生情引发内隐记忆而达到情感共鸣的人本身,此时人也为“实”,身体在作为使意境显现的工具载体之外也是环境中的客体之一,在这种主客体的转换中人能体会到“虚实相生”的玄妙。
身体美学不仅为艺术创作和艺术审美提供了人生理方面的指导和解释,同样也为人本身提供了自我意义。身处意境营造出的审美场所中,获得审美体验的不仅是人的身体本身、其内隐记忆同样被增加了新的内容。意境打破了身体与知觉的平衡,也重组了新的平衡。在这种起伏不定的平衡变化中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又如何认识自己?所以在身体下的意境审美中,作为主体的人可以从更具身的层面理解和体会意境之美,在与其他客体互为镜像的审美场中进一步看见看不见的自己,这些体验经历最终会再回归到人主体本身,并经由艺术认识更多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