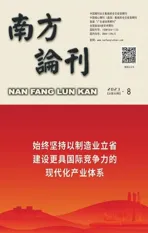“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2023-10-08邱雨诗
邱雨诗
(南开大学 天津 300350)
“主义”是一个外来词汇,据历史学家王汎森考证,该词最早应是从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引入,近代中国常用“主义”来表达思潮、思想、观念、主张、方法、世界观等。细察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历程不难发现,“主义”一词从一个普通外来词汇,逐渐“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等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及生活世界中的形形色色,轻轻罩上一层纱,或染上一缕颜色。”[1]并随着国情局势逐渐成为能够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大力量。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一次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久不衰,恰恰在于它的实践性与人民性,而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看,任何新思想的引入往往为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所最先接受,这似乎与最广大群众和客观社会现实发生了断裂,这种矛盾迫切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突破现实的迷雾,走出书斋,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缘起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封建传统价值体系在西方列强一次次侵华中摇摇欲坠,封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出现危机。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大众对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新的转变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作为胡适实用主义思想重要来源的杜威博士开始了他的两年访华宣讲之旅,他的主张迎合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日趋激进的社会氛围。以上种种都在无形中酝酿着近代中国一场不同凡响的思想碰撞。
(一)传统文化价值的危机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近代以儒学为思想支撑的传统文化,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百家争鸣的发端、独尊儒术的确立到宋明理学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实现了与政治形态的完美融合。事实上,看似繁荣的文化价值体系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形成了内部的危机。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催生一大批有为青年的觉醒,他们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中华民族腐朽落后的根源是封建传统文化的结论,传统文化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呼唤着一种适应时代转换与突破的新模式,当社会层面的种种矛盾都最终反映在文化层面上时,突破束缚构建新文化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
二十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众多报刊社团的宣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马克思主义最初也只是作为其中一种社会思潮被引入中国的,当时归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流派繁多,正如时人潘公展所说:“报章杂志底下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2]事实上,此阵营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连以王揖唐为代表的臭名昭著的安福系反动政团都要借社会主义的名号来假装时髦。这时的青年面对形形色色的新思潮,还未能够辨明究竟哪些利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不知该接受哪种主义,往往忽略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仅限纸上的空谈。
(二)俄国十月革命认识的转变与杜威实用主义的盛行
当十月革命这一讯息通过西方媒体辗转发行在中国人的报刊《民国日报》上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人了解十月革命的开端。而此时的中国报刊报道国外新闻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媒体,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初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是片面甚至多以负面为主的,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思想渐变过程。
最早向十月革命表示欢迎的中国人除了李大钊,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代表。当李大钊、罗家伦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今日世界之新潮》等文章中表达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歌颂时,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对Bolshevism有了好感。十月革命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外交后,资本主义的野心最终打破了国民们的幻想,而此时的新俄国突然宣布废除与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新俄国产生了好感与好奇。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开始大量传入中国,信仰自由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宣传推介“实用主义”(pragmatism)学说,杜威主义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介绍人当属蔡元培和黄炎培,“1912 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时,他把‘实利主义’教育列为教育宗旨之一……”[3]黄炎培在此后也开始了推介“杜威实用主义”,“大约在1913 年8 月,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4]他在文章《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里说:“‘实用主义’今俨然成为吾国教育上一名词矣。”[5]经过蔡、黄二位学者宣介,“实用主义”开始在国内知识界引起反响。五四运动前夜,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开始了他的两年访华之旅,在这两年里他走遍河北、浙江、广东等十一省,作了许多针对中国国情和社会问题的演讲,酝酿了一场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热潮。
二、“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影响
这场论战持续时间不长,参与人数不多,但不同学派从正侧面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影响和点化,达到了多层面形成合力助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效果,在理论方面辨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为广泛有效科学的传播。
(一)引导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径
其一,这场论争发生在思想活跃的五四前后,胡适以其实验主义派的高度敏锐度较早感知到了当时学界空谈各种“好听的主义”而忽略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考察的弊病。胡适的几篇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其实并不反对谈主义,而是反对文人学者在引入各种外来主义时非但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反而不加甄别、一味滥用的做法,呼吁知识分子在引入“主义”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考虑与中国现实国情的结合。
其二,从影响来看,胡适创造性的呼吁的确引起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鸣与重视,他们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吸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重视对具体实际问题的考察。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下简称《再论》)中表达了今后对实际问题重视的决心:“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6]论战过后,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走出书斋,在研究宣传学理的同时,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持以辩证态度。
其三,“问题与主义”之争使先进知识分子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树立了问题与主义并重的观念,从辩证法的角度处理这一对关系,达到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和谐发展,“不脱离实际问题去抽象地谈论主义,也不离开主义而陷入问题丛中迷失方向。”[7]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就已经初步形成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8]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以现实问题为土壤扎根的,现实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源泉,在马恩生活的年代,无论是著作的创作还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现,都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进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实现的。
(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
首先,“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双方对科学主义的倡导与弘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营造了有利的气氛。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被许多知识分子接受,随后进行传播,除了理论适应了中国的现实国情需要,具备解剖复杂社会现象从而全面把握整体脉络的功能,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科学的世界观——“唯物史观”出发去把握客观规律、解决现实问题。无论是胡适还是李大钊,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价值体系出发从而对科学产生信仰和追求,使得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会因其科学性而产生好感,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环境。
其次,在论争中冒牌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受到批判,知识分子初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它们的界限,对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产生积极意义。在《再论》中李大钊做了一个比喻,将混杂在社会主义中的各种冒牌主义比作“杂草毒草”,他表示,不能因为掺杂了这些就把善良的花草一并收拾了,正是由于论争中双方对冒牌主义的批判,使人们在今后接触到各种新思潮的同时具备了独立思考、辨别真伪的能力,推动先进分子进一步思考究竟何种主义利于中国。
最后,在论争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意识到了系统全面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开始集中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理论上还未成熟,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没有全面理解,但是已经开始了运用理论进行考察。经过这场论争,李大钊的理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再论》中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表明了他开始了运用理论武器的尝试。此外,他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6 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学说以及劳动价值说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新阶段。正是借着这场在知识界引起轰动的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澄清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空前扩大。
(三)帮助大批进步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新道路
一方面,论战之前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与其他社会思潮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一大批先进分子正是在论战的影响下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蜕变,陈独秀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陈独秀在1920 年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并不出众,可当他在复刊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政治》一文时,就已经明确把自己规定为个共产主义者,并采取行动迅速与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划清了界限,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分析社会现实的尝试。石川祯浩认为:“对陈独秀来说,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9]无论早期先进分子最早接受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理论之中找到行动的工具,此后,李、陈纷纷开始了投入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组建党的早期组织,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尝试,在李、陈的影响以及新思潮的洗礼下,以蔡和森、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进步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另一方面,论争前寄希望于通过文学艺术等方式达到潜移默化改造社会的社团和报刊纷纷转向从事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造的研究活动。“尤其青年学生逐渐分清了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的界线,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常常被看作受‘问题与主义’之争影响的典型”[10],又如1919 年底在天津等地兴起的先进知识分子工读互助主义的活动,即新村实验的尝试。据统计,这一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非常活跃,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介绍马列主义、翻译马恩著作以及河上肇的解读文章数量空前绝后,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入门》等。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论战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纷纷成立,青年们经过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涌现出来了,自此,知识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起来。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示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聚焦到“问题与主义”之争,不难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影响全国的论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个大考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面对挑战与质疑中发展壮大的,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一)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打好意识形态阵地战
“思想理论只有借助一定的话语体系才能得以表达和传播。”[11]从现实层面而言,能否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最关键的目标之一。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占据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而明确的任务,这一过程也与党的伟大实践历程密不可分。
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认识,阐释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需要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彻底革命来改变现实。回望百年波澜历程,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既注重意识形态体系的建构与传播,又不忘在社会实践中发展好维护好,因为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紧密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2]。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因此任何时候都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打好意识形态阵地战,科学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规律,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朝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二)持续推进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人才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培养一大批坚定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并通过他们在不同领域进行大众化且有组织性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支持和拥护。
论战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作用,利用论战的效能向社会大众宣传,能够在传播中引导先进分子走出各种社会思潮的思想迷雾,增强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于培养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人才队伍日益重视,不断加大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力度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因此,当前要充分发挥高校马院的重要功能,既要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功能,又要旗帜鲜明抵制错误思潮的误导,引导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总之,在传播人才需求方面,既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理论创新的需要,又要有适应互联网及其技术设备而形成的多模式传播样态,造就一支面向国内海外的高素质理论传播人才队伍。致力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3]
(三)坚持问题导向,勇敢应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挑战
坚持问题导向,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各个奋斗时期的概括凝练。
马恩在创立发展马克思主义初期就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意识出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形成阶段,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进行反驳。在面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偏颇主义一方,而是坚持以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4]突出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在总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在实践探索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创新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15]当前面对互联网环境下各种“反马”“非马”错误思潮的传播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不回避,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调查、充分了解后,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传播。
四、结语
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百年风雨历程,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而这场发生在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引起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空前关注,至今仍给后人深刻的思想启示。五四先贤们对“问题与主义”所持有的辩证统一的态度,达到一个超脱历史语境的高度。当后人摒弃形而上学的即偏颇一方的思维方式,以开放自由的心态再来聚焦这次论争的核心时,会发现这场争辩已实现了思想论争的批驳功能和阐释功能。
大批知识分子在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局势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又经过深刻的理性论争,对社会上种种思潮和主义进行筛选辨别,马克思主义成为越来越多青年的信仰。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面回应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与点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占据早期意识形态阵地,在开放自由的氛围内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青年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赓续马克思主义伟大精神,弘扬传播真理的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