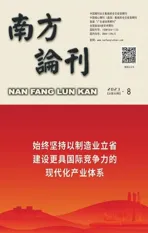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
2023-10-08高正星
高正星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从“以俄为师”“以苏为鉴”到“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再到“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理论创新成果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崛起,也代表着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重新占据重要的地位,以深厚的文明底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超越。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以及马克思主义新文明观的指引下成功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规范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之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之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中华文明为民族底色,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灵魂和旗帜,实现自我革命的过程。
(一)文明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
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中华文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文明属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深厚的文明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性文明转型的强大精神动力[2]。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到两汉经学,再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华文明以其兼容并蓄、协和万邦的文明特性而延绵不绝,其中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大一统”等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精神特质。其一,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的“民为贵”、贾谊的“无民不为本”皆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性的重要方法论。其二,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绿色生态思想。“仁民而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生态智慧,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秉持这样的绿色承诺中,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明之路。其三,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中华民族虽历经朝代更迭,但其文明并未中断,并且在数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形成了强调“和谐”“大同”的“大一统”观念,成为我国开展大国外交的文化基因。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成果,承载着中国人民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根基。
(二)文明之魂:马克思主义新文明观的理论指引
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霸权特征,构建了主张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更加符合人类美好追求的共产主义文明观。黑格尔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殊意志经常得到调和与一致的最好的办法,得出“现代战争的进行方式是人道的”这一结论[3]。马克思从根本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存在论,他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马克思认为,必须以新型社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在保存和发展生产力成果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此为指导,在实践中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霸权逻辑,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超越。
马克思晚年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他认为现代文明的霸权表现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掠夺和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两个方面。其一,关于工人异化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多次强调人类最终会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谴责了以资本运动为主导的西方社会对人的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人的生存危机等问题。其二,关于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殖民掠夺的问题。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提出,强调资本主义不是现代化的唯一选择,为东方落后国家建立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侵略东方社会的伪善性时指出,当资产阶级文明输出到殖民地时,其“极端伪善和他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5]。东方落后国家在接受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同时,也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来对抗西方的现代性,马克思新文明观在与实践相结合中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新文明观的指导下,我们党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不等于西方现代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因而中国不可能完全依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标准和方式进行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中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传统文明的超越。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探求历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百余年的探索历程中,始终伴随着现代性文明的转型与超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超越。
(一)文明蒙尘中探求:从因循守旧到开始向西方学习
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国逐步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伴随着“天下”之中国变为“世界”之中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逐步式微,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面对民族和文明的双重践踏,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
在被动地进行早期现代化追求中,改良派发动的东西文化比较,开创了近代中国东西文化比较的先河。在比较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落后根源,探索前进道路,提出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等主张,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先觉者最初的思想历程。虽然无论是洋务阶级的“中体西用”,还是维新派的“破旧立新”,作为效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尝试,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但是从谭嗣同的《仁学》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再到梁启超《新民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现代性自觉凸显,开始突破和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认识到中国未来之命运不能仅仅停留在“中西体用”之争,不能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的阶段,而是如何改造国民与社会,改造中国与世界以及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性中华文明。
(二)文明自觉中学习:从“以俄为师”“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
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寻现代化方案经历诸多“主义”的考验和失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生机,成为引领中华文明自觉发展的“灯塔”。中国由此开始转向“以俄为师”和“以苏为鉴”的现代化探索之中。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逐步开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辛探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社会文明建设。而后,无论是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还是解放区的整风运动,都真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社会主义文明也由此诞生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着如何成为一个有着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境遇。在1954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7]。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明确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也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引。随后,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文明自觉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步呈现出来。从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向苏联学习,到独立自主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自觉发展。
(三)文明互鉴中进步:借鉴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明再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文明的理解更加深刻,在如何对待现代文明的问题上,邓小平认为,应该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8]的时代背景出发,强调要重新认识西方文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9]。事实上,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正是这种差异性,促使不同的文明相互借鉴,彼此融合。从西汉丝绸之路的开辟到遣唐使来华,从马可波罗来华到郑和下西洋,不同文明相互借鉴的历史事实都展现出来文明的差异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因此,应当积极借鉴有益于本国现代化发展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邓小平始终倡导解放思想、大胆借鉴,强调用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建立了属于东方社会的文明话语体系和实践指导原则,中华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得以发展。当然,大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有益成果,并不是对西方文明全盘吸收。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存在的各种文化鱼龙混杂,其中有很多对我国国民产生巨大吸引力的落后文化。吸收什么样的国外文化,排斥什么样的国外文化,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因此,邓小平始终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要抵制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文明崛起中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超越
新文明形态的开启,意味着要实现对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文明形态的扬弃与超越[10]。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三个文明建设”“四个文明建设”,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来统一部署与落实。从邓小平提出的“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再到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现从“两个文明”到“四个文明”的跨越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孕育而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五个文明”全面发展,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框架基本确定。
人类文明新形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旨归[11]。就其本质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就其内涵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追求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单维度文明;就其目标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解放”为目标,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目标的西方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成就的高度概括,也标志着人类文明新路的诞生,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
百余年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中华文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超越了以资本为逻辑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文明的革故鼎新,破解了西方中心论,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的文明价值意蕴。
(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中华文明引向现代,实现了中华文明的革故鼎新。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文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因清王朝的闭关锁国,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致使中国一直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而后又在近代遭遇文明重创,亟需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12]。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性相遇,促进了二者的双向互动和深度融合。一方面,内蕴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现代性要素,突破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瓶颈,将其带入现代形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生。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发展的土壤,使其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成为可能。总而言之,在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将中国现实国情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相融通,坚持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激发了文明的内在活力,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再生发展。
(二)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破解西方文明中心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回归人本逻辑的价值追求,实现了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重大破解。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同民族创造的文明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尊重和包容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保持人类文明繁荣延续的重要前提,相互借鉴先进的文明成果是保持文明生命力的重要保障。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建立起现代霸权思维,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处于支配地位。相比于资本主义“文明中心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启的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存在质的区别,不是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文明,而是倡导“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文明观。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实践中,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都倡导文明的和谐共生,有效破解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狭隘弊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范围内的共享性文明,不是只限于民族内部的地方性文明,超越了西方社会主导的文明优越论。文明的普遍性意味着其在价值理念上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在表达自身文明经验的同时,也在为人类发展思考一种新的努力方向。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某种意义上的反思与实践,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的范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文明类型的选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为其走向现代文明提供了新的选择。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呈现的价值体系,为分析解决世界性难题,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崛起的文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