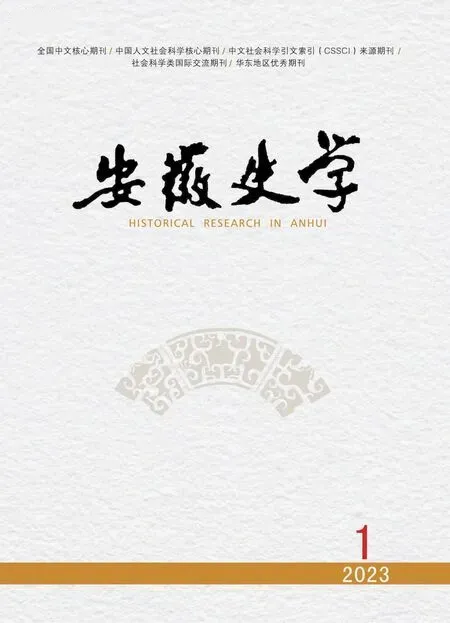皇明异典:明代军籍豁除考论
2023-10-07黄谋军
黄谋军
(赣南师范大学 王阳明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户籍制度是传统社会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也是历代国家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在实践过程中极大地形塑了社会的阶层体系、流动模式、职业结构和生活样态。(1)赵方杜:《户籍制度嬗变中的社会管理蕴意》,《理论月刊》2013年第8期。明初,朱元璋告谕天下“许各以原报抄籍”,将全国人户分为军、民、匠、灶等籍,并规定人户以籍为定,不许妄变版籍。(2)万历《明会典》卷19《户部六·户口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页。其中军籍是保障军户制度及卫所军源的重要措施,为保证军役的世代延续,“军法必世继,继绝以嫡,嫡绝以支,支绝以同姓,不奉上诏旨,不得邃自免”(3)岳正:《送张鸣玉诗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32,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页。,“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4)⑦《明史》卷92《兵志四·清理军伍》,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58页。学界关于明代严格管理军籍有较为普遍的认识,但对军籍豁除方面的研究,多散见于相关论著中,或略带提及,或高度点明要旨,对明代军籍豁除的类型、军籍豁除中的利弊权衡与情感表达以及明朝后期军役的经济化实践与军籍难除的祖制因循等问题尚缺乏专题性研究。(5)陈宝良:《明代社会流动性初探》,《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张金奎:《军户与社会变动》,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7页;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85页;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以期有助于明代户籍制度的研究,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军籍豁除中的特赦与常例
明朝建立后,天下人民“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以定”。(6)《明宣宗实录》卷69,宣德五年八月乙未,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校印本,第1629页。在民、军、匠、灶等诸多户籍类别中,“盖终明世,于军籍最严”(7)⑦《明史》卷92《兵志四·清理军伍》,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58页。,军户想要脱免和改变军籍身份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亦可见到一些军籍改为民籍、官籍或其他户籍的事例。(8)黄谋军:《明代官籍再探》,《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张金奎曾指出,明代的配户当差制度非常僵化,户籍世代不能改变,这在大原则上是正确的,但配户当差的僵化实际上只停留在制度层面,对其实际运行状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9)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第285页。
揆诸史籍,明代军户非法摆脱军籍军役束缚的手段众多,如洪武、永乐年间,“有畏避军役诡作民籍者,有因诡籍而分析二三户者,有见在卫所当军,洪武以来黄册上报作民,以图分户脱死者。造作军籍并无卫所行拘者有之,人不见在捏作死绝回申者有之,随母改嫁冒作别姓而避军亦有之。”(10)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0页。有应继壮丁怕充军役故自伤残者(11)陈九德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卷17《兵部四·为条例事》,《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甚至有实行自宫,希除军籍者等。(12)《明仁宗实录》卷3上,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癸卯,第89页;《明英宗实录》卷208,景泰二年九月壬戌,第4483页。但为保持兵源军力,明朝统治者一再重申,禁止军籍人户妄变版籍。笔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改变军户军籍的现象。大体而言,主要分为特赦与常例两大类。
(一)军籍的特赦
关于明代军户军籍的特赦,人数有众有寡,事由不一,且终明一代,不曾停止,而前中期尤甚,兹列几类如下:
因孝行突出而特赦军籍。明朝推崇儒家文化,践行以孝治天下。明太祖曾指出:“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人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13)《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壬戌,第963页。这种孝道思想在户籍管理中也有所体现。如洪武八年,“除应天卫卒李彦才籍。彦才,潼川遂宁人,尝从元将万户卜花征北,与其子添禄相失,已而彦才归附为应天卫卒,几二十年矣。而添禄以有司荐,任澧州石门税课司副使,访求累年,始知父母所在,奏乞给侍。上怜之,命除其父军籍,俾就其子禄养。”(14)《明太祖实录》卷99,洪武八年四月庚寅,第1679页。李彦才因其子添禄的孝行,得到朱元璋的垂怜,得以豁除军籍。又如明人程通,尝上书太祖,乞除其祖戍籍,辞极恳切。高皇怜之,叹“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家军籍。(15)《明史》卷143《程通传》,第4056页;姜清:《姜氏秘史》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66—767页。此外,洪武十八年,“旌表蓟州遵化县张拾孝行……诏旌表其门曰孝子,仍蠲其军役。”(16)《明太祖实录》卷173,洪武十八年五月乙卯,第2642页。二十七年,又“诏免孝子郝安童军役”。(17)《明太祖实录》卷233,洪武二十七年五月辛丑,第3399页。这一先例也为继任诸帝多所效仿。永乐十三年,“举人郭鲁,自陈父履尝为栾城县儒学教谕,以所教无中科者谪戍云南,愿代其役,辞甚恳切。上悯之,命削履军籍,复教谕职”;(18)《明太宗实录》卷163,永乐十三年四月辛卯,第1848页。正统元年,英宗以“子能盖父之愆”,“免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户内军役”。(19)《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庚辰,第285页。
因特殊功绩而特赦军籍。在明代,军籍军役的非时恩霍,时常被纳入皇帝奖赏体系之中。统治者通过对有特殊功绩大臣军籍军役的豁除,笼络统治阶层内部的各派力量。如明人徐琦,先世钱塘人,其祖谪戍宁夏,遂为军户。勤奋力学,登科入仕,历任右通政、南京兵部右侍郎等职。宣德八年,徐琦在处理安南贡赋问题上明敏有断,“帝悦,命落琦戍籍,宴赍甚厚”。(20)《明史》卷158《徐琦传》,第4316页。永乐辛卯进士邝埜,正统改元时,升为兵部左侍郎,“时西鄙有警,尚书王骥出征,埜独任其事,英宗嘉其才。荆湘民多隶戎伍,埜家亦与焉。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宠。”(21)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83《湖广郴州府·邝埜》,《续修四库全书》第5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成化年间,累官礼部尚书、太子少保的刘岌“音吐鸿畅,甚为宪宗所眷”,“自陈世为戎籍,敕兵部除其籍”。(22)《明武宗实录》卷4,弘治十八年八月戊午,第127页。同时,刘岌还乞求豁除其从弟、太医院医士刘崟军籍,也获得宪宗批准。(23)《明宪宗实录》卷255,成化二十年八月庚辰,第4313页。但从徐琦的“帝悦,命落琦戍籍”,邝埜的“特除其籍,以示宠”,刘岌的“甚为宪宗所眷”可以看出,明代帝王对于军籍的豁除,常端凭自身喜好、需求而决定,未有制式之程序与标准。
因已任官,无人补役而特赦军籍。如宣德七年,行在兵部尚书许廓上奏:“武昌推官姜謩诉其祖充五开卫军,已死,其父老病,户无余丁。今五开数取謩补役,援洪武中例,乞除免。今复勘是实,未敢擅除。上曰:太祖皇帝于生员有成,尚不忍弃,况謩为官,岂止一卒之用。其除之,俾修职自效。”(24)《明宣宗实录》卷88,宣德七年三月戊辰,第2028页。又如景泰四年,光禄寺少卿陈诚奏:“臣本山东靖海卫军籍,见今缺役,止臣一身,无人可代,乞恩开豁”,获得允准。(25)《明英宗实录》卷233,景泰四年九月辛未,第5094页。成化年间,若正户已升官,贴户则无需补役。十二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杨峻建议,“今天下卫所,有三户垛充军役,其正户已升官,仍勾贴户补伍者,乞与分豁”,兵部准行。(26)《明宪宗实录》卷153,成化十二年五月丁巳,第2792页。从上述也可看出,军户若走向仕途,很大程度上则无须再补军役。
除以上几类,明代特赦军籍的例子还有很多,事由不一。如连婚宗室(27)《明宣宗实录》卷90,宣德七年五月丁亥,第2069页。,承担皇陵户等特殊劳役(28)《明英宗实录》卷61,正统四年十一月己未,第1162页。,也可被特赦军籍军役。另外,据《明实录》统计,正统、景泰时期关于文职奏蠲军伍的记载较为频繁,尤其是景泰时期。如景泰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四年,南京工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来;五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邹来学等文臣都上奏乞除户下军伍,且获得批准。(29)《明英宗实录》卷206,景泰二年七月己酉,第4421页;卷231,景泰四年七月戊寅,第5060—5061页;卷241,景泰五年五月庚午,第5258页。但这些例子,并未给出豁除军籍的具体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代宗为拉拢大臣以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措施。但当英宗复位时,立即推翻景泰时期的做法,文职系景泰间蠲伍者,依旧勾补。(30)《明英宗实录》卷277,天顺元年四月庚子,第5905页。
(二)军籍豁除中的常例
除上述事由不一的军籍特赦外,在明代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供遵循的军籍豁除常例,“军籍清勾,自宣德正统以来屡有勘详开豁之例”。(31)《明神宗实录》卷438,万历三十五年九月乙巳,第8300页。现兹列几类如下:
丁尽户绝者。当所勾军士丁尽户绝时,则允许开豁军籍。洪武二十六年,辽东开元卫军士马名广上言五事,其中之一即建议“兵老死而营无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补之劳”,太祖从之。(32)《明太祖实录》卷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未,第3299页。宣德四年,行在兵部进勾军条例,其中一条为“自今所勾军士,如有丁尽户绝……遣人同有司官吏、里老人等,挨勘至再三无勾,保结申报,军卫有司各仍造册……通以无勾缘由转缴兵部,以凭开豁。”(33)《明宣宗实录》卷57,宣德四年八月癸未,第1357页。宣德六年、正统二年这一条例再次得到重申。(34)《明宣宗实录》卷81,宣德六年七月癸酉,第1877页;《明英宗实录》卷34,正统二年九月癸卯,第663页。正统十三年,因清勾不力,挨无姓名籍贯者尤多,为防奸弊,有司回申次数由三次直接上升为十次。(35)《明英宗实录》卷17,正统十三年九月戊子,第3274—3275页。万历年间,军户丁尽户绝,循例除豁依然得到践行,且有司结勘回申次数降为五次。(36)《明神宗实录》卷6,隆庆六年十月辛巳,第245页。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诸多军户亦借此条例非法脱籍。如正德七年,巡按直隶御史何沾反映,“洪武初年以来,有一父所生二三子或四五子,父子各立一籍……后父为事充军或犯法典刑全家发卫者,止尽随户人丁补当,后因逃故等项就作丁尽户绝开豁”(37)霍冀:《军政条例类考》卷5《题为申明旧例以裨军政事》,《续修四库全书》第852册,第85页。,此类推脱之弊,不可胜数。
生员应起解者,经考试有成效,准许开伍卒业。明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把笼络、选拔人才视为王朝安危治乱的关键,将举贤任才,视为治国之本。这种人才观在军户子弟中也同样适用。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曾与兵部尚书沈溍展开“一力士”与“一贤材”的讨论,最终以“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难”为由,豁除潮州府学生陈质军籍,遣归进学。(38)《明太祖实录》卷199,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第2988页。又于二十九年,以法律形式规定:“生员应起解者,送翰林院考试。成效者,开伍,发回读书;不成者,照旧补役。”(39)万历《明会典》卷154《勾补·凡开伍免勾》,第788页。这一事例为后继者所继承。宣德四年,浙江上虞县李志道,充楚雄卫军,死而无继,正有孙宗侃已赴乡试中式,而卫所追补军役不已。“兵部尚书张本请依洪武中石坚事例,豁除其军籍,俾读书会试以自效”,宣宗从之。(40)《明宣宗实录》卷53,宣德四年四月己卯,第1269—1270页。同年八月,行在兵部将这一事例纳入勾军条例。(41)《明宣宗实录》卷57,宣德四年八月癸未,第1357页。其后,生员沈律、张珩等“俱蒙列圣体念贤才,考试作养,底于有成。其后多繇科目,布列仕途,为国効用”。(42)⑦叶盛:《叶文庄公奏议·西垣奏草》卷8《题为申明祖宗成宪事》,《续修四库全书》第475册,第303、304页。
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特例。如正统十三年,有生员翟麟援引前例,希除军籍,但“蒙发补役,不曾考试”。景泰初年,亦有“江西吉安府生员郭源,奏乞照依太祖高皇帝旨意并《军政条例》考试”,但兵部“因查翟麟事例,拟奏定夺,蒙令补当军役”。(43)⑦叶盛:《叶文庄公奏议·西垣奏草》卷8《题为申明祖宗成宪事》,《续修四库全书》第475册,第303、304页。但正德所修《明会典》已将这一条例收入(44)正德《明会典》卷124《兵部十九·事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0页。,说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贯彻落实。
二、明代军籍豁除中的利弊权衡与情感表达
明代军籍身份虽整体上给军户家庭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在各种利弊权衡下,并非所有军户都渴望豁除军籍。如洪武时期吏部尚书翟善,“明于经术,奏对合帝意”,皇帝欲除其军籍,遭到拒绝,善曰:“戍卒宜增,岂可以臣破例。帝益以为贤。”(45)《明史》卷138《翟善传》,第3965页。翟善以军国大事为重,认为戍卒宜增,不可破例,将保留军籍身份视为顾全大局、为皇帝分忧的表现。这一记载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从史书书写角度来看,似乎带有某种忠君观念的宣传。另外,河南商丘侯氏军户家族,在万历年间取得“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佳绩。当族人侯恂官至兵部侍郎时,曾提议设法脱去家族的军籍,其父侯执蒲则拒绝其议,理由是“人尽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独以为辱,如吾祖宗何?”最终并没有解除军籍。(46)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5《太常公家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1册,第496页。这一事例,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侯氏军户家族的家国情怀。同时,侯执蒲的这一做法被雍正《河南通志》《侯氏家乘》等广泛记载与流传,并在乡里传为美谈。(47)雍正《河南通志》卷58《人物二·归德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7册,第432页;商丘《侯氏家乘》卷1《载籍·河南人物通志》,转引自李永菊:《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对明代河南归德沈氏家族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于军籍士子而言,读书科举、登科入仕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地位,有时还可豁免家族军籍,彻底摆脱军役。但在国家军役面前,仍有以忠孝为先而辍学服役者。如太学生赵孝先,家为军户,其父当袭替军役,但因年老,赵孝先愿辍学服军役。爱孝先者认为:“旦夕当为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请,上未必不许也,而何急自代为哉?”惜才者则认为:“国家地尽四海,执干弋、职战守者如林,而少者岂一兵乎?而使孝先为之。”(48)②方孝孺:《送太学赵孝先从军诗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9,第66页。反映出当时社会一定程度上已形成通过科举登科入仕豁除军籍的认识和愿望。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不能“苟为荣辱计而忘大义”,在大是大非面前应以大局为重,“知亲之不可遗,禄位之不可苟”,而子则为孝,而臣则为忠。赵孝先辍学服军役,即属此类。(49)②方孝孺:《送太学赵孝先从军诗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9,第66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军户拒绝豁除军籍或并非急迫豁除军籍,除了明面上的忠君观念、家国情怀外,背后或有更深层次的利益考量。
世之人一隶戎籍,子孙往往贻累于无穷,“一人当军,全家受害,较之民户,苦诚过倍”(50)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2《酌议军余丁差以苏疲累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2册,第637页。,能够得以豁除军役军籍,实乃天恩异典,受惠者因此多感恩戴德。如国子监生程通,于洪武二十三年上表乞除其祖伍籍,并在撰文中提到:“荷太祖高皇帝可其奏,特赐恩诏,释放还乡,俾得以终其老于牗下,至今铭刻,莫可为报”(51)程通撰、程长等辑:《贞白遗稿》卷2《送陈士深还莆田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735页。,表达出对皇帝豁除其祖军籍的感激之情。又如内阁大臣杨士奇,曾乞求仁宗豁除其继父罗氏家族之军籍,罗氏兄弟子侄得以优游田里,并表达出对仁宗的感激之情,“旷古所无之典也”。(52)金幼孜:《书杨少傅陈情题本副录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8,第145页。
另外,嘉靖时期官至礼部尚书、内阁首辅的夏言亦出身军户,关于其家族军户的由来与最终的豁免,在夏言所作《闻讲书院先公祠安神告文》有所说明。其祖上因触禁,编隶军籍,因遭洪灾而家道中落。其父夏鼎荷戈执经,发解京闱,晚登进士之后,夏氏乃昌。(53)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8《闻讲书院先公祠安神告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第123页。至夏言登科入仕后,因“见应役丁笃疾,京卫及江西俱无次丁”,于嘉靖十一年“乞除其家府军左卫军籍”,获得世宗恩准。(54)《明世宗实录》卷143,嘉靖十一年十月甲午,第3336页。可见其军籍之豁除,虽有无丁补役的实情,但也与夏言官任礼部尚书紧密相关。对豁免军籍的天恩异典,夏言感戴而泣,遂作“蒙恩免除军伍开立官籍感恩志喜泣下成章二首”:
百年板籍脱戎行,此日君恩讵可忘。御笔亲题除豁字,玉音嘉答谢陈章。簪缨门户从今重,雨露松楸倍有光。传与云仍思报称,祗将忠孝作肝肠。
白头老祖从军日,弱冠先君解卫年。家世艰危忧坠地,圣恩广大赖同天。甲科名纪三朝录,仕版官登八座联。积德从来如种获,独思庭训倍潸然。(55)夏言:《桂洲诗集》卷15《蒙恩免除军伍开立官籍感恩志喜泣下成章二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339册,第295—296页。
从这两首诗,可见军籍身份对于夏言家族的影响。其父弱冠解卫,家世艰危,开豁军伍之后,“簪缨门户从今重,雨露松楸倍有光”,虽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基本能反映当时军户家族的实际情形。以上事例,亦可从侧面反映明代军籍豁免之难。
三、明代军役的经济化实践与军籍难除的祖制因循
上文所述只局限于个体军户的军籍豁除,明后期也逐渐出现了以银代役,甚至从法制上废除军籍制度的倡议与呼声。明中期以后,各地卫所均出现军士逃亡、正军失额现象,为替补由正军逃亡留下的空缺和承担诸多杂差,明政府大量佥派军户余丁应役,以致“军余几成正军”。(56)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如成化十三年,规定“各处清军御史严督都司卫所,将各官舍余尽数查出造册,送赴清审存留,帮军分拨差操”。(57)霍冀:《军政条例类考》卷1《军卫条例·军余查拨差操》,《续修四库全书》第852册,第19—20页。为解决这一问题,明政府将州县民政系统中的徭役编派制度逐渐引入到卫所管理之中。如正德六年,“先是都御史许进巡抚大同,议各卫所空闲舍余,照民间均徭例,每丁岁出银四钱,以给公需,上下便之。后为瑾所革,至是镇巡官以请,乃复之”。(58)《明武宗实录》卷71,正德六年正月乙亥,第1571页。说明正德时期,均徭法在大同等边镇卫所已有所实施。《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也收录了一份万历五至九年名为《辽东各卫所边堡官军下余丁舍丁等纳银名册》的残缺档案(59)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上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74页。,显示出明代辽东地区亦已实行均徭法。从这份舍人余丁的纳银名册可以看出,均徭审编后,差役以一定的工价银两为准,舍余也按三等九则派役,分别缴纳不等的代役银。但由于编审人员的枉法受贿,卫所均瑶法在实际的审编、佥派过程中出现均徭对象混乱、徭役负担不均等弊端。正德元年十一月,巡抚顺天等府都御史柳应辰也明确指出这一弊端:“顺天、永平二府并各卫所差役不均,审户虽有三等九则之名,而上则常巧于规免论差,虽有出银、出力之异而下户不免于银差,且有司均徭当出于人丁,近年兼征地亩;军卫均徭当出于余丁,近年兼派正军,奸弊难稽,民穷财尽。”(60)《明武宗实录》卷19,正德元年十一月乙酉,第561—562页。
为了改变卫所军户等编审和均徭对象的混乱不堪,明代君臣开始在部分卫所实施一条鞭法。关于卫所引入一条鞭法的研究,于志嘉和张金奎等学者主要依据万历十四年钦差巡抚江西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陈有年所上《酌议军余丁差以苏疲累事疏》,探讨了一条鞭法在南昌卫推行的原因、过程及方案。(61)参见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99页;张金奎:《军户与社会变动》,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441—445页。经巡抚陈有年等层层会议,认为“军卫条鞭之法,诚为革弊苏困之方”,建议将南昌卫城屯余丁比照郧阳、滇南事例,“悉照民户见(现)行条鞭,征银雇募”。(62)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2《酌议军余丁差以苏疲累事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52册,第634页。此法于万历十四年十二月丙戌获准实行。(63)《明神宗实录》卷181,万历十四年十二月丙戌,第3386页。均徭法和军卫条鞭法在卫所中的推行,不仅有利于减轻卫所军户的徭役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军官对军户的剥削压迫。但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均徭法及军卫条鞭法的推广仅限于余丁杂役,而正军军役则未能实现以银代役。
明代为保证军役的世代延续,严格管控军籍户口,还建有收军册、清勾册等各类详细户口册。(64)万历《明会典》卷155《兵部三十八·军政二·册单》,第796页。但由于实际操作层面无比复杂,军士逃亡现象严重,清勾替补十分艰难,军力日渐消耗。面对这一局面,朝中有识之士对军户制度提出改革建议。如嘉靖三十年正月,户科给事中何光裕奉诏清理陵卫军士,指出“各卫逃亡军士,州县之清解虽多,而伍籍之空虚益甚者,以风土之不同,人情若于羁旅故耳”,建议“广收土著之众,使自为守,而令各处应解补者出装银助之”,提出应解补者出“装银”而广收土著应役。但兵部以“招募军士应募者少,得用亦难,招得游食之民,复与解来户丁何异”为由,拒绝这一建议。(65)《明世宗实录》卷369,嘉靖三十年正月丙申,第6596—6598页。又如万历三年十一月,工科给事中徐贞明提出将军役仿照班匠事例,以银代役。(66)徐贞明:《亟修水利以预储蓄酌议军班以停勾补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398,第4307—4308页。时任郧阳巡抚王世贞表示赞同,并言有四便。(67)《明史》卷92《兵志四·清理军伍》,第2257页。但兵部以“祖宗定为兵制与班匠不同”等,拒绝其议。(68)《明神宗实录》卷44,万历三年十一月己酉,第994页。万历十一年七月,巡按直隶御史徐鸣鹤在条陈边务时指出“清勾之令,縻饷无益”,建议“令军籍人户,征军装银三两六钱,类解各边别募”,但兵部以“清勾之法乃祖宗定制,应照旧”为由予以拒绝。(69)《明神宗实录》卷139,万历十一年七月己亥,第2594页。
到崇祯末年,明朝统治者依然固守祖制,不知变通,依旧严格控制军籍人口。如崇祯十七年,户部尚书倪元璐为增加财政收入,建议“免军籍为民籍”,允许军籍人户通过缴纳银两,免其勾补,改为民籍,通过“以银代役”的方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崇祯皇帝却以“军籍原属祖制,岂可议更”为由,断然拒绝。(70)倪元璐:《倪文贞集》卷11《请免军籍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第311—312页。
上述可知,明朝后期,朝中有识之士不断建议和督促政府改革军籍军役制度,甚至有人提议仿照班匠制度,在军役实践中实行以银代役。但明朝统治者碍于祖制成宪,又因军籍制度兹事体大,更多地秉持“补偏救弊,尚有可以持循;因噎废食,恐遂不可救药”之思想,最终阻碍了法制上军籍的废除。直至清朝顺治二年,清世祖颁布诏令,才正式废除明代的户籍制度,即“前明之例,民以籍分,故有官籍、民籍、军籍,医、匠、驿、灶籍,皆世其业,以应差役,至是除之。”(71)《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21《职役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2册,第444页。
结 论
明初实行的军户世袭制度是传统社会皇帝对百姓人身强制的根本大法之一,有利于国家强化社会控制,稳定军役来源。但明朝统治者对出身军户但孝行突出、有上进心的才干之士以及有特殊功绩的大臣等抱有极大的同情心,逐渐形成了皇帝意志下的非时恩霍与一定程度上可供遵循的豁除常例,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人治”社会下户籍政策实践的宽容与弹性。
明代军籍身份虽整体上给军户家庭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在忠孝观念、家国情怀或更深层次的利弊权衡下,并非所有的军户都急迫渴望豁除军籍身份,而是部分选择了坚守。军户在允准豁除军籍之后,也对统治者的天恩异典表达出极大的感激之情,凸显出明代军籍豁免之难。明中后期,在部分卫所余丁杂役中先后实行均徭法和条鞭法,显示出朝中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利用经济力量处理军政问题,但未能实现向正军军役的推广。明朝政府碍于祖制成宪,又因军籍制度兹事体大,更多地秉持“补偏救弊”之方,最终阻碍了法制上军籍的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