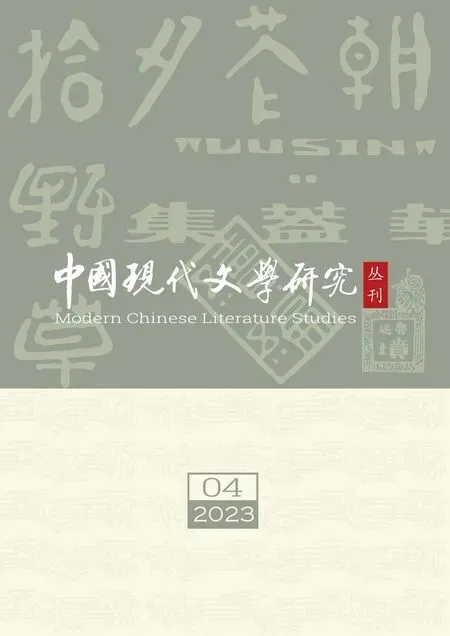鲁迅引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考
——兼论珂勒惠支版画在中日间的传播
2023-10-06秦刚
秦 刚
内容提要:鲁迅从日文刊物《新兴艺术》上读到永田一修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美术的形势》一文,这成为他关注珂勒惠支的契机。鲁迅随即通过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搜集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德国版画家的画集,并在介绍木刻《牺牲》和撰写《〈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时,参照并引用了永田一修的文章。鲁迅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通过赠送与代销两种路径传入日本,这也是日本普罗美术沉寂后仅有的珂勒惠支作品的输入,为战后日本民众版画的复兴存留了火种,鲁迅因此成为日本战后版画运动的精神导师。
鲁迅是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引入中国的先驱者,珂勒惠支的艺术对于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影响至深。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已有学者点明“珂勒惠支也是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①熊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突进的艺术与革命意识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2010年3月,艺美基金会联合珂勒惠支美术馆在北京举办《珂勒惠支和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展》时,组织美术界、鲁研界专家专门对“凯绥·珂勒惠支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整理与回顾。但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策划与所撰文章都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鲁迅在何时发现了凯绥·珂勒惠支?该展览及所刊图录对此均未涉及,而是将1930年7月15日徐诗荃从德国寄来五种珂氏画集作为《珂勒惠支在中国年表》的起点。①《凯绥·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艺美基金会2010年版,第112页。可是,徐诗荃所寄画集显然是受鲁迅之托的代购之举。那么,鲁迅究竟从何时开始关注这位德国女性版画家?其最初的认识又来自何处?这个问题涉及鲁迅发现珂勒惠支的具体路径,关乎对珂勒惠支进入中国的追根溯源,对此国内学界尚未作出独立的考论。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珂勒惠支的艺术在1928年初就被介绍到日本,因此鲁迅经由日文出版物与其邂逅的可能性极大。迄今被采信较多的观点,便认为鲁迅看到了在日本首度介绍珂氏的日文文章,本文将对此作出辨析。对凯绥·珂勒惠支的发现,无疑得益于鲁迅对日本美术出版物的高度关注,是他竭力借鉴世界普罗艺术、“从别国窃得火来”的主观意识使然。在此过程中,从内山书店购入的日文书刊成为鲁迅了解德国左翼版画的窗口。数年之后,法西斯主义高压下的日本普罗美术全面式微,鲁迅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以下简称《版画选集》)还传入日本,成为在战后破土发芽的版画运动的一粒种子。
本文将论证永田一修的美术评论《全世界无产阶级美术的形势》(「世界に於ける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情勢」,以下简称《形势》)是鲁迅阅读并发现珂勒惠支的源头,验证该文对鲁迅搜集珂氏版画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并进而分析鲁迅在评论珂勒惠支时如何汲取和引用了永田一修的论述。日本左翼美术评论家永田一修在国内尚无介绍,但同时期鲁迅的阅读与其多有交集,对永田一修的重视也体现出鲁迅积极摄取左翼美术资源的取向。最后,本文还将探寻鲁迅的珂勒惠支摄取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勾绘出鲁迅作为“中间物”的珂勒惠支版画艺术在中日间传布的断代史。
一 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相遇
鲁迅究竟从何时开始了解和关注珂勒惠支?迄今为止较为集中的说法将这一时间确定在1928年,其依据多来源于《鲁迅与木刻》一书中奈良和夫的说法。仅近年发表的论文中持此说者便有周耀卿《故宫博物院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玻璃底片来源考》②周耀卿:《故宫博物院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玻璃底片来源考》,《故宫学刊》2015年第2期。、高秀川《珂勒惠支的中国行旅与左翼文学》等,后者文中写道“根据内山嘉吉和奈良和夫的著述,鲁迅最有可能在日本杂志《中央美术》1928年1月号中了解到凯绥·珂勒惠支”①高秀川:《珂勒惠支的中国行旅与左翼文学》,《山西师大学报》2016年第2期。。然而奈良和夫又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仔细斟酌便会发现其推论过程并不严谨。
1928年1月号的《中央美术》刊发了正在柏林学习戏剧的千田是也寄来的题为《凯绥·珂勒惠支 Kaethe Kollwitz》的专稿,这是珂勒惠支首次被介绍到日本。1927年7月8日珂勒惠支六十岁生日之际,柏林各报纸竞相刊发祝贺报道,千田是也参考各种德文资料后撰写此文,发表时配有珂勒惠支的十幅素描、版画及木刻作品的图片。奈良和夫依据1924年4月15日鲁迅日记中“上午钱稻孙来,见借《中央美術》四本”②《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一句,认为鲁迅借给钱稻孙的《中央美术》和刊发了千田文章的《中央美术》(中央美术社出版)应该是同一种杂志。仅根据这一条线索便认定鲁迅必定阅读了千田是也的文章,进而判断说“鲁迅可能是由于这篇文字的介绍,发现这位女版画家的”③内山嘉吉、奈良和夫:《鲁迅与木刻》,韩宗琦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这一推测的漏洞显而易见,鲁迅即便在1924年阅读过《中央美术》,也无法据此推断四年后也必定读过1928年1月号的该刊。1928年鲁迅已定居上海,在现存的鲁迅书账和藏书目录中查不到《中央美术》,鲁迅也从未言及千田是也的文章,更找不出能证明他必定阅读过该文的证据。相反,鲁迅的珂氏认知必不会来自千田文章的证据却能找出不少。《〈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以下简称《序目》)中对画家生平的说明出现两处舛误,即谓其父亲做过“木匠”(实为石匠),谓其“大儿子”(实为次子)死于战场④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486页。鲁迅的误会可能源自《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中的史沫特莱撰写、茅盾译《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一文。,这些细微之处在千田文章中都有过准确叙述,鲁迅如若读过当能避免这样的误会。
能够确定鲁迅最早阅读的有关珂勒惠支的文献,其实是永田一修撰写的《形势》,这篇文章发表在1930年5月1日发行的《新兴艺术》第七、八合并号上。同年5月25日鲁迅在内山书店购入了此期《新兴艺术》⑤《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并立即阅读了此文。在此前后的两三个月间鲁迅先后购买了《柳濑正梦画集》《无产阶级艺术教程》《为了无产阶级美术》等多种左翼美术类的日文原版书籍,①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227~230页。在这样的阅读倾向下关注该文可谓顺理成章。日本学者东家友子在《鲁迅与德国版画》②東家友子:「魯迅とドイツ版画——メッフェルト、コルヴィッツの作品紹介をめぐって」,『アジア遊学』第168号,2013年11月。一文中,就关注到鲁迅对此文的阅读,指出鲁迅对梅斐尔德的了解即始于此文。在近出《珂勒惠支美术在中日两国的首次接受》③Tomoko Toya,First Reception of Käthe Kollwitz art in Japan and China,邵大箴、范迪安、朱青生主编:《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鲁迅与凯绥·珂勒惠支》④東家友子:「魯迅とケーテ·コルヴィッツ——日本プロレタリア美術運動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学』第269号,2022年5月。两文中也都有论及,后者更是细读了鲁迅对该文章的接受。但东家友子的论文以铺陈和分析为主,并未以纠正既有的误说和考辨探源为目的。为此,本文将运用史料排比与文字对勘,以论证和验明永田一修的文章才是鲁迅发现珂勒惠支的真正源头。
《全世界无产阶级美术的形势》全文两万多字,分七章论述了苏俄、德国、匈牙利、墨西哥、美国与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日本普罗美术的现状。在第三章《德国无产阶级美术》中,作者将德国普罗美术的发展分为“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否定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以及“现代德国的年轻无产阶级画家”的三个阶段,然后用“海因里希·齐勒与凯绥·珂勒惠支”“乔治·格罗斯与奥托·迪克斯”“年青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画家”三节评述了各时期的代表者,这其中就包括了鲁迅后来称之为“新的战斗的作家”⑤鲁迅:《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页。的三位版画家,即凯绥·珂勒惠支、乔治·格罗斯和卡尔·梅斐尔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文末附有三幅插图,能确定其中两幅是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一幅是创作于1925年的素描《儿童肖像》(洛特·纳格尔)(Kinderkopf[Lotte Nagel]),另一幅是创作于1923年的木刻版画《幸存者》(Die Überlebenden)。后者下方有画家的亲笔签名。这两幅插图很可能是鲁迅亲见的最早的珂氏作品。通过此文既能了解由版画和素描所代表的德国普罗美术创作的总体现状,还能对珂勒惠支在德国现代画坛的地位有所认知。而且文后所附珂氏画作,能够借此获得对其画风的直观认识,这对于了解一位画家是极为必要的。鲁迅阅读此文时,其作者永田一修已在东京被捕,对此容后文再述。
以鲁迅购入该期《新兴艺术》的1930年5月25日为一个时间节点,便能发现他对珂勒惠支的画集及原拓版画的收集都在此之后。据日记可知,5月28日、31日,6月11日、22日,鲁迅都曾给留学德国的徐诗荃写信,其中很可能表达了托其代购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画集之意,6月10日“托柔石往德华银行汇寄诗荃买书款三百马克”①《鲁迅全集》第16卷,第200、204、258页。即足可为证。7月15日“收诗荃所寄Käthe Kollwitz画集五种、George Grosz画集一种”②《鲁迅全集》第16卷,第200、204、258页。,其中五种珂勒惠支画集为《凯绥·珂勒惠支画帖》(Käthe Kollwitz Mappe,1927)、《呐喊声起》(Ein Rufertönt,1927)、《母与子》(Mutter Und Kind,1928)、《织工反抗、农民战争、战争》(Ein Weberaufstand,Bauernkrieg,Kri-eg,1930)、《凯绥·珂勒惠支画集》(Das Käthe Kollwitz-Werk,1930)③参见《鲁迅全集》第17卷“书刊注释·注释条目〔西文〕”。。
1931年4月7日鲁迅又托史沫特莱给珂勒惠支汇去一百马克求购版画,5月24日、7月24日分两次共收到二十二幅珂勒惠支的版画原拓。鲁迅将有画家签名的组画《织工反抗》一套与一幅铜版画在同年8月20日赠送给内山嘉吉,作为对他在暑期木刻讲习会讲授木刻的感谢。同年6月23日,又“得诗荃所寄Daumier及Käthe Kollwitz画选各一贴,十六及十二枚”④《鲁迅全集》第16卷,第200、204、258页。,这次买到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帖》是1927年慕尼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同题画帖的新版⑤参见黄乔生《鲁迅外文藏书提要(二则)》,《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翌年10月15日,鲁迅将其赠送给了篠崎医院儿科医师坪井芳治。
上述鲁迅搜求珂勒惠支画集及原拓的时间次序,已足以反映出永田一修论文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另有一条辅助线索,即永田一修在文中将插画家齐勒与珂勒惠支并列评述,而鲁迅于6月30日“收诗荃所寄《德国近时版画家》一本、《Für-Alle》一本”⑥《鲁迅全集》第16卷,第202、213页。,后者即齐勒的画集《为了大众》;9月23日“晚收诗荃所寄关于文艺书籍五本”⑦《鲁迅全集》第16卷,第202、213页。中还有齐勒的画册《街头的孩子》(Kinder der Strasse)。这条辅助线同样可以佐证,鲁迅以永田评论为指南,有目标地求购德国左翼画家的画集。加之此后数年间他多次引用这篇评论,因此可以确定该文即为鲁迅发现珂勒惠支的源头。
二 鲁迅对永田一修的转引
永田一修对珂勒惠支的评述见于《形势》第三章第二节,作者评价她为“德国无产阶级绘画之母”,对齐勒则称“德国无产阶级绘画之父”。在对一年前刚过世的后者作了简要介绍后,他将话题转向前者,直接引用了霍善斯坦因著、川口浩译《现代艺术中的社会性要素》的一段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论述。这段关于珂勒惠支的评述虽不过千字左右,但鲁迅在介绍木刻《牺牲》以及为《版画选集》撰写《序目》时,都参照和摄取了这段文字。
鲁迅为纪念牺牲的柔石选取木刻《牺牲》刊发在《北斗》创刊号的扉页,在为其撰写的说明中就珂勒惠支的创作作了如下介绍:
最有名的是四种连续画。《牺牲》即木刻《战争》七幅中之一,刻一母亲含悲献她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时正值欧洲大战,她的两个幼子都死在战线上。
然而她的画不仅是“悲哀”和“愤怒”,到晚年时,已从悲剧的,英雄的,暗淡的形式化蜕了。①鲁迅:《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鲁迅全集》第8卷,第350页。
木刻《牺牲》中母亲悲哀地献出爱子的画面,与珂勒惠支年仅18岁的次子彼得在比利时阵亡的经历相关。但指其“两个幼子”死于战场则属误会,这能证明鲁迅没有读过千田是也的文章,因为该文中有“她的次子在弗兰兑伦战线‘光荣战死’”的具体叙述。②千田是也:「ケエテ·コルヰッツ」,『中央美術』1928年1月号。引文为笔者译。关于珂氏晚年画风变化,“到晚年时,已从悲剧的,英雄的,暗淡的形式化蜕了”一句其实来自于永田一修。永田评论说珂勒惠支创作的原动力是“悲惨的生活”和对剥削者的“愤怒”,“当她迈入老龄后,便从初期受到的蒙克的影响,以及延至中期的悲剧式或英雄式的阴沉形式中摆脱出来了”③永田一脩:「世界に於ける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情勢」,『新興美術』第7、8合并号,1930年5月。本文对该文的引文均为笔者译。。这一句在时隔五年之后,鲁迅在《序目》中再度援引。
1935年春,鲁迅将选出的珂勒惠支的铜版画、石版画二十余幅邮寄至北平故宫博物馆印刷所,用珂罗版复制印刷。1936年1月11日郑振铎带来印成的版画,在补印文字后,鲁迅抱病为版画加入衬纸、封面,亲自编排成册,7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以线装方式装订完成。鲁迅邀请了与珂勒惠支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为画集作序,他自己则撰写了一篇长文《序目》。
《序目》在介绍了画家的生平后,通过引述霍普德曼、罗曼·罗兰、亚斐那留斯、霍善斯坦因、永田一修共五人的评论来概述珂氏的创作成就。前三者的引用均来自迪尔编《织工反抗、农民战争、战争》和亚斐那留斯编《凯绥·珂勒惠支画帖》①黄乔生:《“略参己见”:鲁迅文章中的“作”、“译”混杂现象——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但对后二人的引用未标明具体出处,研究者也尚未查清引文来源。现在可以确定对霍善斯坦因和永田一修的转引文字,均出自永田一修的《形势》一文,这篇文章也是鲁迅撰写《序目》时参照的唯一日文资料。《序目》提及霍善斯坦因之评的文字为:
霍善斯坦因(Wilhelm.Hausenstein)批评她中期的作品,以为虽然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暴力的恐吓,但在根本上,是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形式也出于颇激的纠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的形相。②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第6卷,第488页。
必须承认,这是一句略为费解的表述,珂勒惠支中期作品里“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以及“暴力的恐吓”究竟为何意?通过对比《形势》原文,可以发现鲁迅的转引对原文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理解偏差。为方便对比,先将永田一修的这段原文翻译如下:
霍善斯坦因在《现代艺术中的社会性要素》(川口浩译)中,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有如下的评论。“如果人们去看凯绥·珂勒惠支那富于鼓动性的、有男性气质的铜版画,以及斯坦伦(Alexandre.Steinlen)的虽有些许的工团主义者的威风但却是真正意义上革命的、激情的罢工宣传画,就能体会到这些作品与更为深层和鲜活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而且这些作品的形式是从更为激烈的挣扎之中诞生出来的。事物本身的生命力赋予其形式更强劲、更本源的紧张感。事物的生命力也为画笔的笔触增加了力度,在此,形成了比克兰(Walter.Crane)——英国社会主义画风的画家(永田)——更准确地捕捉到事物形态的艺术形式。”①永田一脩:「世界に於ける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情勢」。
原文的这部分文字是将珂勒惠支的版画与瑞士画家亚历山大·斯坦伦(Alexandre Steinlen,1859—1923)的罢工宣传画放在一起讨论,而鲁迅忽略并跳过了斯坦伦(日文原文为“スタンラン”)的名字,还把“工团主义者的威风”(日文原文为“サンヂカリスト的な空威張り”)误解为“暴力的恐吓”,并将其作为对珂勒惠支作品的描述来处理,误译了原文内容。最后“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的形相”一句,则是对原文末句评价珂勒惠支及斯坦伦的绘画形式的扼要转述。霍善斯坦因以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考察现代艺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在《霍善斯坦因论》中曾对其大为赞誉。上述对珂勒惠支的评论出自《现代艺术中的社会性要素》一文,收录于《现代造型艺术》(Die Bildende Kunst der Gegenwart,1923)一书。川口浩在编译霍善斯坦因的评论文集《造型艺术社会学》时将其收入其中。《造型艺术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第六册,于1929年11月8日由丛文阁出版发行;11月14日鲁迅即从内山书店购入该书。②《鲁迅全集》第16卷,第159页。奈良和夫注意到鲁迅藏有此书,误以为鲁迅的引用来于此。③内山嘉吉、奈良和夫:《鲁迅与木刻》,韩宗琦译,第194页。但实际情况是,《新兴艺术》所载永田之文才是引用的真正出处。
鲁迅在转述时对霍氏评论作了大幅度的缩略,但对永田一修的补充评论则作了较为周详的引用和转述。
永田一修并取她的后来之作,以这批评为不足,他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和里培尔曼(Max.Liebermann)不同,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来画下层世界的;她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她照目前的感觉,——永田一修说——描写着黑土的大众。她不将样式来范围现象。时而见得悲剧,时而见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无论她怎样阴郁,怎样悲哀,却决不是非革命。她没有忘却变革现社会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脱离了悲剧的,或者英雄的,阴暗的形式。”①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第6卷,第488页。
上述鲁迅的转引基本上忠实于原文,此处译成“里培尔曼”(Max Liebermann)的画家,是珂勒惠支的早期创作深受其影响的画家马克思·利伯曼,永田原文中将其注明为“资产阶级画家”。但鲁迅并未采用这一标签式的分类。通过和原文对比,能发现《序目》的“她照目前的感觉”一句中的“目前”,其实是“眼前所见”(日文原文为“目の前”)的“目前”,而非指时间意义的当下。这句话在永田文章里的表述为:“他对于眼前的黑土地上的大众,如同所见的那样做出感性式描写。她没有将样式生硬地套在现象之上。”鲁迅所说的“她不将样式来范围现象”,即是对此文后半句的直译。而此后的直接引文的翻译则十分准确,永田原文的大意为:“她的作品有时是悲剧式的,有时是英雄化的。可是无论她怎样阴沉,怎样悲剧式,却决不是非革命的。她从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化改造的可能性的思考。而且她迈入老龄后,便从初期受到的蒙克的影响,以及延至中期的悲剧式或英雄式的阴沉形式中摆脱出来了。”②永田一脩:「世界に於ける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情勢」。
通过文字对勘还可以发现鲁迅的一个不易察觉的处理。那就是把“将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化改造的可能性”(原文为“ブルジョア社會の革命的克服の可能性”)简化为“变革现社会的可能”,从而略去了“资产阶级”一词。同时还把“无产阶级的世界”(原文为“プロレタリアの世界”)翻译为“下层世界”,同样避开了“无产阶级”一词。这些被略去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表示阶级划分的词汇,在《序目》的通篇自始至终未见使用。这似乎证明鲁迅试图将珂勒惠支的版画成就定位于更为宽泛的艺术范畴,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这些词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鲁迅所转述的永田之论并非完全来自永田一修的独立论述,将这段文字和千田是也《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对比可知,其大部分内容是从后者摘取和提炼而来的。例如指出珂勒惠支不同于从题材趣味出发去描写普罗世界的利伯曼,她是为悲惨的生活所动而不得不用画作表达的一处,基本是摘取而来的。“可是无论她怎样阴沉,怎样悲剧式,却决不是非革命的”一句,两篇文章的表述高度相同。“她从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化改造的可能性的思考”也是对千田文章的“她从没有失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化改造的可能性的信仰”一句略有词语替换的照搬。只有最后指出珂勒惠支年老之后从“悲剧式或英雄式的阴沉形式中摆脱出来”是永田一修本人的结论。这也再次证明,鲁迅不可能读过千田是也的文章;否则必定会参考该文,而不会从永田一修的文章里大段转引。仅就对于珂勒惠支的介绍而言,千田文章的内容更为详细而充实。《形势》的珂氏评论主要来自对霍善斯坦因的引用以及对千田是也文章的摘选。这也证明在永田一修撰写此文时,千田是也的文章依然是他能参考的关于珂氏的仅有的日文文献。
三 鲁迅对日本普罗美术的汲取
从鲁迅初读《形势》到撰写《序目》时引用参照,时间跨度有五年零八个月。这足以证明《形势》一文在他眼中的重要性。鲁迅对梅斐尔德的最初了解也始于此文,前文所述东家友子的论文对此已有考论。①東家友子:「魯迅とドイツ版画——メッフェルト、コルヴィッツの作品紹介をめぐって」,『アジア遊学』第168号,2013年11月。而鲁迅对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s)的介绍,亦有部分内容源自于此,尚未有人披露。
继《北斗》创刊号刊出木刻《牺牲》之后,鲁迅在1931年10月20日发行的《北斗》第二期扉页上刊用了里维拉的壁画《贫人之夜》,这也是里维拉的作品在中国的首次介绍。1930年4月30日鲁迅收到徐诗荃寄来的书中,就有德文版《迭戈·里维拉画集》②《鲁迅全集》第16卷,第228页。。在为《贫人之夜》撰写说明时,鲁迅参照了《形势》第五章“墨西哥革命与美术”中“革命画家迭戈·里维拉”一节,该节介绍“迭戈·里维拉是革命化墨西哥的无产阶级画家的代表者”,并选用了里维拉为劳动会馆创作的壁画《砂糖工场》(1922年作)为插图。而鲁迅对《贫人之夜》的说明中,末尾的“理惠拉以为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因此也可知倘还在倾向沙龙(Salon)绘画,正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①鲁迅:《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说明》,《鲁迅全集》第8卷,第356页。一节,就是翻译自永田的文章。因为鲁迅没有明言这段文字出自翻译,最末句“因此也可知倘还在倾向沙龙(Salon)绘画,正是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很容易被理解为鲁迅自己的判断。最早关注了鲁迅对里维拉介绍的丁景唐,就误以为是“鲁迅先生把它称之为‘现代艺术中的最坏的倾向’”②丁景唐:《鲁迅与里维拉》,王观泉编:《鲁迅和里维拉》,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原载《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实际上,此句只是如实翻译了永田文章转述的里维拉本人的艺术观点。
《新兴艺术》所刊《形势》一文多次成为鲁迅介绍外国普罗美术的源文本,通过鲁迅的汲取与转译汇入中国左翼美术的话语资源。永田一修曾是日本普罗美术评论的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名画家,他于1928年创作的油画《读〈真理报〉的藏原惟人》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日本普罗美术人物画的杰作。
永田一修1903年出生于福冈县门司市,1922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进入藤岛武二教室学习,同年作品便入选第四届帝国美术院展。在学期间与同学大月源二共同参加前卫美术运动,作品曾入选未来派美术协会展。1927年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不久后加入劳农艺术家联盟下属的剧团前卫座,此期间在劳艺会议上结识了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劳艺分裂后,永田一修所在的美术部组成前卫艺术同盟,藏原惟人、村山知义等都名列其中,永田任美术部负责人。1928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与前卫艺术同盟结成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以下简称“纳普”),其机关刊物《战旗》创刊号封面为永田设计。藏原惟人主导的以介绍苏俄及世界普罗文艺为目的的国际文化研究所于1928年10月创立后,永田一修参与机关刊物《国际文化》的编辑、撰稿、封面设计。1930年5月20日,永田在东京家中被警官持枪包围,带至府中拘留所。同日,一批“纳普”领导骨干因参与日共的运动募资被检举拘留,这一事件被称为“5·20事件”,同日被拘留的还有三木清、佐野硕、冈本唐贵、村山知义等人。鲁迅于5月25日购入《新兴文艺》第七、八合并号,这意味着当鲁迅读到永田一修的文章时,永田其实已被拘留。他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期执行五年,狱中“转向”后于1931年2月末获释,但仍长期受到监视。1941年他进入东京日日新闻社(后成为每日新闻社)摄影部,直至1958年退休。后以制作鱼拓知名,并成为钓鱼史研究家。他得知了鲁迅对其文章的引用,在1983年撰写的《自传》中曾写道“我为能得到鲁迅的关注而感到荣幸”①永田一脩:「自伝」,『追悼永田一修』,鳥海書房1989年版,第41页。关于永田一修生平还参照了山口泰二著『変動期の画家』(美術運動史研究会2015年版)等资料。。1988年4月9日永田一修去世,享年84岁。其代表著作有《无产阶级绘画论》(天人社1930年版)、《鱼拓》(艺美出版社1960年版)、《杜米埃/库尔贝/梵高现实主义的黎明》(新日本出版社1976年版)等。
除《形势》之外,在鲁迅的阅读中还能找到其他与永田一修相交集的线索。例如,鲁迅藏有三册永田参与编辑的杂志《国际文化》②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第3集,1959年版,第91页。,其中1928年12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号中,刊有永田一修、小川信一共同撰写的关于第九届帝国美术展的报告。永田的油画作品《读〈真理报〉的藏原惟人》曾在1928年11月开幕的首届普罗美术大展展出,后收入日本无产阶级美术家同盟编《日本无产阶级美术集》(内外社1931年版)。1931年8月6日鲁迅购入了这本画集③《鲁迅全集》第16卷,第264页。。鲁迅一直高度关注藏原惟人翻译的各种苏俄文艺理论及文艺作品,这一时期他正在为《毁灭》的译稿做最后校对,其翻译所使用的底本就是藏原惟人所译的日译本。可以推断鲁迅翻阅画集时必定会留意到这幅肖像画。巧合的是《读〈真理报〉的藏原惟人》所画的,正是1928年夏季正在专心翻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时的藏原惟人④永田一脩:「自伝」,『追悼永田一脩』,第38页。。
因鲁迅在《序目》与致鹿地亘的信中都提到永田一修,《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十四卷都对永田其人做了注释,但两则释文均有舛误。两则释文中的“永田一修(1903—1927)”的卒年标注错误,应为“1988”年。第六卷“永田一修”注释中有“这里所引他的话,见《无产阶级艺术论》(1930年出版)”⑤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496页。一句,此处的书名应当指的是《无产阶级绘画论》。《无产阶级绘画论》是在永田在《形势》的基础上扩写而成,1930年5月28日由天人社出版。但鲁迅未收藏此书,《序目》中的引用亦非出自此书。全集第十四卷的“永田”注释,称“鲁迅所引他的文章,即《世界现代无产阶级美术的趋势》,载《新兴文艺》第七、八号合刊”①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标题中的“现代”二字并不见于原标题,应当删去。
鲁迅通过永田一修与珂勒惠支相遇,是以阅读同时期日本左翼美术文献为路径的。在1930年的购书和阅读中,《新兴艺术》是鲁迅尤为瞩目的刊物之一。1930年1月6日“往内山书店杂志部买《新興芸術》四本”②《鲁迅全集》第16卷,第177、186、197页。,3月3日“午后往内山书店杂志部买《新興芸術》五、六合本一本”③《鲁迅全集》第16卷,第177、186、197页。,5月25日“买《新興芸術》(二之七及八)一本”④《鲁迅全集》第16卷,第177、186、197页。,至此购齐了该刊的全部六册发行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中,共有七册《新兴艺术》,其中刊载《形势》的七、八合并号现藏两册。⑤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第3集,第94页。《新兴艺术》是1929年10月创刊的综合性艺术评论杂志,由艺文书院发行,编辑兼发行人为田中房次郎。该刊发行至第七、八合并号后停刊,共发行六期。实际负责编辑的核心人物是坂垣鹰穗,即鲁迅翻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一书的作者。其他编辑人员还有岩崎昶、坂仓准三、吉川静雄等。该刊编辑风格前卫,理论性强,尤为注重对欧洲现代派艺术的介绍,涵盖电影、建筑、美术、戏剧、雕塑、美学理论等众多领域。
源于《新兴艺术》阅读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鲁迅将第一、二号连载的岩崎昶的评论《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翻译成中文,改题为《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补充了《附记》后在1930年3月1日发行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这成为鲁迅译介的左翼电影理论的重要文献。《新兴艺术》的刊名之“新兴艺术”,所指的是更为广义的现代派艺术、前卫艺术以及现代大众艺术。普罗艺术虽包含其中,但在全部六期中的文章数量并不多,而岩崎昶和永田一修的评论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新兴艺术》的众多评论中鲁迅尤为重视这两篇左翼艺术评论,这也反映出他在阅读和摄取上的取向。
四 珂勒惠支版画在日本
前文考证了鲁迅在收藏和介绍珂勒惠支版画过程中如何汲取和借鉴永田一修的文章,厘清了珂氏版画引入中国的一个关键环节。本章将对鲁迅编印的《版画选集》在日本的传布展开探微与钩沉,以鲁迅引入的珂氏版画再反向影响日本的实例,将珂勒惠支艺术在中日之间往返传布的文化行旅勾绘完整。
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版画选集》仅印制一百零三部,但鲁迅却制定了使其在海外流通的计划,他为该书撰写的牌记显示,“四十本为赠送本”“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①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牌记》,《鲁迅全集》第8卷,第524页。三种流通方式的册数分布亦十分明确。在中国出售的部分由“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代售”。那么,“三十本在外国”销售的地点又在哪里?笔者认为,应该是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于1935年10月创设于东京祖师谷的内山书店。诸多线索证明,《版画选集》印成后通过赠送和海外代销的两种路径传入日本。
鲁迅日记记载了1936年8月1日,鲁迅赠该书给须藤五百三;8月31日,还托内山完造寄给在柏林的武者小路实笃一部,托其转赠给珂勒惠支。②《鲁迅全集》第16卷,第615、618页。此外鲁迅还赠送给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一部,此事鲁迅日记虽未记载,但鹿地亘曾有回忆。他与池田幸子在8月中旬前后登门拜访鲁迅时特意为此道谢,鲁迅又以一部《海上述林》相赠,还拿出珂勒惠支的原拓版画请其欣赏。③鹿地亘:『魯迅評伝』,日本民主主義文化連盟1948年版,第64~66页。鹿地亘夫妇通过这次拜访拉近了和鲁迅的距离,他们在向日本传递鲁迅的珂勒惠支摄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内山完造的斡旋,当时已决定由胡风协助鹿地亘编选和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由日本改造社出版。鹿地亘想将《版画选集》的《序目》收入其中,鲁迅看过选篇后写信表示不收也可,“记得在日本已有更详细的介绍了。不过倘已译好,收进去亦可。其中引用永田氏的原文,登在《新兴艺术》上,现将该杂志一并送上”④鲁迅:《360906致鹿地亘》,《鲁迅全集》第14卷,第393页。。“在日本已有更详细的介绍”即指永田一修的文章,鲁迅将刊有此文的《新兴艺术》也随信寄去,鹿地亘也理应阅读了永田文章。因鲁迅病逝,《鲁迅杂感选集》的翻译计划扩展成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后者虽未收入《序目》译文,但鲁迅对珂勒惠支的喜爱依然经由鹿地亘等人介绍到日本媒体。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改造社发行的文艺刊物《改造》和《文艺》分别推出的鲁迅追悼特辑,都以图文结合的方式介绍了鲁迅去世前的版画活动。
1936年12月号《改造》的“悼惜鲁迅”特辑,以鹿地亘翻译的《写于深夜里》开篇,文章的首节即为“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鲁迅回顾了为纪念柔石把珂勒惠支木刻“介绍进中国来”的五年前的往事。译文中配有鲁迅与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文字说明为“10月8日(去世前11日)在上海第二届民国木刻展览会和青年木刻家谈话中的鲁迅氏”。特辑第二篇文章为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追忆》,文中述及“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中的一大艺术运动,便是黑与白的版画”,进而介绍了鲁迅热心收藏各国版画,主导木刻讲习会,这成为“今日风靡全中国的版画艺术的发端”。①内山完造:「魯迅先生追憶」,『改造』1936年12月号。1936年12月号《文艺》“追悼鲁迅”特辑,首篇是池田幸子的《最后之日的鲁迅》,文中讲述了鲁迅在去世的前两天登门造访时的情形。鲁迅为他们带来《中流》和英文期刊《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各一本,然后拿出两部《版画选集》放在桌上说:“请把这些送给日本的朋友。”②池田幸子:「最後の日の魯迅」,『文藝』1936年12月号。鲁迅带来的《中国呼声》应为第1卷第6期,刊发了《写于深夜里》的英译文,而《中流》应为第1卷第2期,所刊随笔《死》从为印制珂氏画集邀请史沫特莱做序之事写起。而《文艺》特辑刊发的两篇鲁迅文章的译文,首篇便是池田幸子翻译的《死》。鲁迅在最后一次出门做客时推荐的两篇文章,都与珂勒惠支相关,也均被鹿地夫妇译成日文,收入悼念鲁迅的期刊专辑。
池田幸子述及鲁迅请其转赠日本友人的两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鹿地夫妇都未交代其去向,但其中的一部很可能寄赠给了中野重治。这是因为中野重治曾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承认:“鲁迅将他在死亡逐渐临近之际编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安排人为我寄到日本一部。”③中野重治:「魯迅について」,『中野重治全集』第20巻,筑摩書房1977年版,第634页。这本版画选集为中野重治生前珍藏,原书留存至今,上有鲁迅手书编号“三十六”。④竹内栄美子:『批評精神のかたち 中野重治·武田泰淳』,イー·ディー·アイ2005年版,第146页。
前文论及东京内山书店应该是出售过该画集的唯一的海外书店,能作此推断,是因为青年版画家上野诚当年就是从该处购入了《版画选集》。他通过东京美术学校教授版画的平塚运一结识了曾接受过鲁迅指导的中国留学生刘岘,并在其推荐下前往已迁入神田一桥的内山书店购入一部,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受到珂勒惠支的现实主义风格影响至深。①上野遒編:『上野誠全版画集』,形象社1981年版,第215页。东京内山书店于1937年3月从祖师谷搬到神田一桥,由此可推测上野诚购书的时间当在此后。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刘岘在即将回国之际,上野诚将其创作的二十多幅木刻作品赠送给刘岘,其中包括了揭露日军杀害中国东北民众的木刻作品。②刘岘:《版画先驱刘岘文辑》,兰考县刘岘纪念馆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9年版,第10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野诚成为推动日本木刻运动的重要人物,鼎力支援中国木刻在日本举办流动展,热心促进中日版画交流。
在鲁迅编印画选之际,身在德国的珂勒惠支已陷入“只能守着沉默”的被禁止创作和发声的境地。纳粹上台后疯狂镇压左翼艺术,1932年她被迫离开艺术学院,1935年起被禁止参加所有展览,1936年因莫斯科发行的报纸刊载了一篇对她的采访文章,随即受到盖世太保的审问和威胁。鲁迅对她的境遇显然知情,所以在《序目》中说,“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③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第6卷,第486页。。而日本国内的普罗美术也早已在法西斯政权剿杀之下归于沉寂,因此,自1935年起的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凯绥·珂勒惠支的声音从德国传递到日本。④新海覚雄:『ケーテ·コルヴィッツ——その時代·人·芸術』,八月書房1950年版,第39页。也就是说,鲁迅编印的《版画选集》在这十年间成为日本仅有的珂勒惠支艺术的传入途径。《改造》和《文艺》对鲁迅引入珂氏版画的宣传,无形中构成了对珂勒惠支本人及德日两国被压制的左翼美术的特殊方式的声援。这一时期,内山嘉吉一直珍藏着鲁迅签名赠予的珂勒惠支的组画《织工反抗》和一幅铜版画。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躲避空袭,他将这些版画和鲁迅书信全部疏散到东京目黑区,但在日本战败三个月前,版画和书信全部毁于美军的轰炸。⑤内山嘉吉、奈良和夫:《鲁迅与木刻》,韩宗琦译,第12页。
战后日本版画运动,是在抗战期及抗战胜利后中国木刻所取得成就的启示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1947年2月19日,中日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木刻展览会”在银座三越百货店开幕,在为期十天的展出期间,中日文化研究所在神田骏河台文化学院讲堂举办了“中国的民主艺术”系列讲座,其中包括鹿地亘主讲的《关于中国人民的文化》、土方定一主讲的《中国木刻与美术革命》等。①島田政雄:『四十年目の証言』,窓の会1990年版,第59、60页。曾担任过日共领导的无产阶级美术同盟书记的铃木贤二在参观“中国木刻展览会”后深受触动,旋即与大田耕士、饭野农夫也等人组建了“刻画会”,倡导为人民大众的版画艺术。中日文化研究所的理事长菊池三郎决意“让鲁迅开启的新木刻运动之火在日本点燃”②島田政雄:『四十年目の証言』,窓の会1990年版,第59、60页。,在鲁迅逝世十一周年之际在茨城县大字町举办了名为“全日本新木刻会议”的木刻节,铃木贤二、小野忠重、内山嘉吉、饭野农夫也、菊池三郎等参加了讲授和指导。经过这一系列活动的举办,“日本版画运动协会”于1949年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战后日本版画运动的新纪元。
参加过普罗美术运动的小野忠重的早期木刻作品,曾收入鲁迅所藏《日本无产阶级美术集》中。1932年他在日文杂志《古东多万》上看到了对《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的转载和宣传 ,从作家佐藤春夫处购入这本木刻集。③秦刚:《〈古东多万〉转载〈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始末——佐藤春夫主编杂志的鲁迅推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6期。他曾向内山嘉吉数次借出鲁迅所赠的《织工反抗》④内山嘉吉、奈良和夫:《鲁迅与木刻》,韩宗琦译,第51页。,还在1944年出版的《支那版画丛考》一书中首次系统介绍了鲁迅指导的木刻普及活动,其中也提及鲁迅编选的珂勒惠支版画集⑤小野忠重:『支那版画叢考』,双林社1944年版,第187~204页。。1947年7月小野忠重在东京主持了“中日版画恳谈会”,邀请李平凡作了题为《中国木刻的人民性格与发展》的报告。⑥李平凡:《版画沧桑——李平凡版画60年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5页。他后来成为著名版画史研究家,多次撰文回顾鲁迅推动新兴木刻的业绩。1956年岩波书店出版全13卷的《鲁迅选集》时,小野忠重从中国木刻作品中为各卷书函封面选用了配图,并撰写了作品解说。
战后在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担任会长的李平凡在回忆录中介绍,出任该会顾问的乡土玩具收藏家尾崎清次由衷敬仰鲁迅,曾珍藏过包括《引玉集》《版画选集》在内的鲁迅编印的版画集。⑦李平凡:《版画沧桑——李平凡版画60年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5页。“刻画会”及“日本版画运动协会”主要会员之一的大田耕士以鲁迅为榜样,立志于版画教育事业,创设了日本教育版画协会,独立承担了《版画》杂志的编辑、印刷与发行工作,得到日本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儿童版画教育团体的支持,被称为“教育版画之父”①中條秀憲:「『教育版画』の形成と教育観について」の研究概論——太田耕士にみる版画教育と人間形成」,『日本美術教育研究論集』48号,2015年。。内山嘉吉在《鲁迅与木刻》一书中写道,“大田氏是根据鲁迅的这种精神,努力使版画这种教育手段用到孩子身上去”。“中国木刻精神即体现在版画上的鲁迅精神,就是这样渗透在日本教育之中的。”②内山嘉吉、奈良和夫:《鲁迅与木刻》,韩宗琦译,第47页。大田耕士的女儿大田朱美进入东映动画公司从事动画制作,大田朱美的丈夫便是让日本动画艺术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的宫崎骏。
战后木刻复兴之际的1947年至1950年,“中国木刻热”推动者之一的中日文化研究所在日本各地举办过三百次不同规模的中国木刻展③李平凡:《版画沧桑——李平凡版画60年回忆录》,第33页。,内山嘉吉也多次提供收藏和保存的中国木刻作品。日本学者友常勉在《从中国木刻到版画——战后日本的民众版画运动·序说》一文中论及,日本战后民众版画运动的特点,就是以“日本版画运动协会”为中心组织开展大量的展览会。④友常勉:「中国木刻から版画へ——戦後日本の民衆版画運動·序説」,『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80号,2010年7月。如是特点显然借鉴和继承了鲁迅在内山完造的协助下举办德国作家版画展、德俄版画展览的历史经验。
虽然千田是也最早将珂勒惠支介绍到日本,但日本出版首部珂氏作品集,已是1950年印行的新海觉雄著《凯绥·珂勒惠支——时代·人·艺术》(八月书房)一书。新海觉雄在写于1949年的序言中提及“鲁迅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为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绘画带来巨大影响”⑤新海覚雄:『ケーテ·コルヴィッツ——その時代·人·芸術』,第2页。。归根结底,鲁迅是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东方民族引入凯绥·珂勒惠支艺术的真正的取火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木刻版画之父,也被日本战后版画运动奉为精神导师。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在亚洲的流布过程中,鲁迅担当了作为“中间物”的无比重要的传播链中的一环。
结语
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鲁迅邀请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举办暑期木刻讲习会,这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标志性起点。但从时间脉络上看,木刻讲习会也可以认为是引入珂勒惠支的关键性的步骤与环节。鲁迅将珂勒惠支的签名版画作为答谢赠给内山嘉吉,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味。鲁迅对凯绥·珂勒惠支的介绍和传布,自始至终,每一环节,都属于跨语际、跨文化性质的开拓性的文化实践。
2018年初春,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名为《刻在黑暗上的光——亚洲的木刻运动 1930年代至2010年代》的极具创意的专题展览。这次展览将木刻诠释为与民众运动相联动的“媒介”,梳理了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到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新加坡,80年代的韩国,直至21世纪的印度尼西亚等地相继发生的“木刻运动”的历程与相关性。①黒田雷児、五十嵐理奈編集:『闇に刻む光 アジアの木版画運動 1930S-2020S』、福岡アジア美術館2018年。这次专题展直观呈现出木刻实际上成为20世纪亚洲各国不同时期的民众运动中共通的艺术式样,同时也有力昭示出,鲁迅将珂勒惠支的版画引入中国,是“亚洲的木刻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原点。这次展览给出的启示是,有必要以亚洲美术史、世界美术史的视域去审视和把握鲁迅对珂勒惠支的引进和汲取;鲁迅对珂氏艺术价值的挖掘之于20世纪亚洲美术史的意义,有待于在视域转换中不断发现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