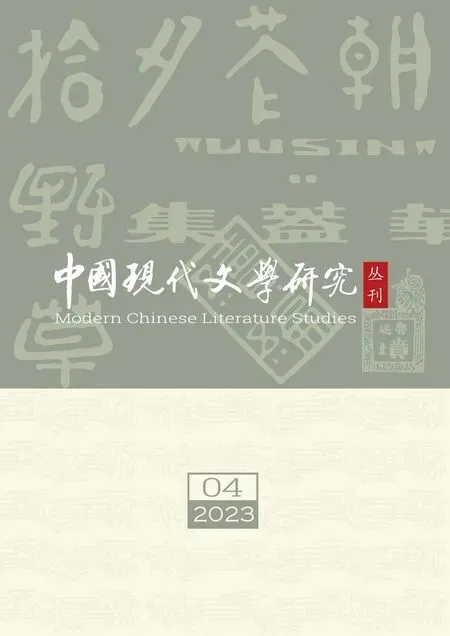否定的诗艺与待形成的主体※
——郭沫若《前茅》时期诗歌初探
2023-10-06孙慈姗
孙慈姗
内容提要:编定于1928年1月的诗集《前茅》收录了郭沫若1921年至1924年创作的部分具有革命色彩的诗歌。长期以来,由于其艺术性的“粗疏”与政治呐喊的“空泛”,这部诗集并不被批评者看重。然而总体观之,《前茅》时期的创作在郭沫若“诗人人格”的养成以及文学、政治理念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必要对这部诗集及其周边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探究。本文拟从文本特征入手,分析《前茅》中大量出现的“否定”性的思维与表达方式,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读与对诗人这一时期生活境况、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察,呈现《前茅》对“自然”“艺术”“自我”的否定背后诗人文学观念与政治意识的变迁,并试图以此为个案揭示浪漫派文学-政治主体生成的艰难过程,以及某种纠结辩驳、尚待形成的主体状态所蕴含的丰富可能。
1928年正月,蛰居上海准备东渡日本的郭沫若编定了他一生中第四部白话诗集《前茅》。这部诗集收录了郭沫若创作于1921年至1924年的部分诗作。在经历大革命的洗礼后,郭沫若以整理旧作的方式对自身进行着“清算”,并从“五六年前的喊叫”中辨识出些许走向革命的前兆。①见郭沫若1928年1月11日为《前茅》集题写的序诗:“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这可以说是革命时代的前茅。/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声音,/这是我五六年前的喊叫。/在当时是应者寥寥,/还听着许多冷落的嘲笑。/但我现在可以大胆的宣言,/我的友人是已经不少。”见郭沫若《前茅》,创造出版社1928年版。
尽管《前茅》所收诗歌与革命事业似有直接关联,然而无论郭沫若本人还是同时代批评者似乎都对这部诗集不甚看重。郭沫若自认为“《前茅》并不高妙,只有点历史的意义”①郭沫若1928年2月19日日记,见郭沫若《离沪之前》,《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页。,钱杏邨则将《前茅》与《女神》进行比较,认为在《前茅》里诗人“发现了他自己应该走的路,发现了人类的真正的敌对的方向”,然而《女神》“究竟是可以代表时代的,比《前茅》更加伟大而重要”。②钱杏邨:《诗人郭沫若》,见王训昭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90页。蒲风从诗集的整体精神风貌入手,指出《前茅》虽则“热烈地喊着革命”,却多是些“空的呐喊”,其中还夹杂了些许“伤感”的痕迹。③蒲风:《论郭沫若的诗》,《中国诗坛》(广州)第1卷第4期,1937年11月15日。同样地,穆木天也从《前茅》中发现了“1922年末之后”在诗人身上出现的“新要素”:“以先生主张Inspiration的诗人,现在要求文艺的社会性了。”因此,《前茅》中的诗作虽于形式上少有新的发展,但“如果拿着去做Ideologie的研究,是很有趣的”④穆木天:《郭沫若的诗歌》,《文学》(上海1933)第8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然而即便在意识形态(“Ideologie”)层面,评论者们亦多将其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的热情”与冲动。⑤楼栖:《论郭沫若的诗》,见王训昭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第247页。总之就艺术创新性与“时代精神”的建构而言,《前茅》似乎远不及塑造了郭沫若诗人形象的《女神》,而若从思想水平方面进行考量,左翼评论家又往往认为《前茅》中的“喊叫”并不代表着对革命的真正认识,这种空泛而粗疏的热情形态进而被视作诗人个体认知水平局限性的产物。
或许是基于此种已然定型的论调,后世研究也几乎忽略了郭沫若的这部诗集。而随着对《女神》时期诗歌艺术与诗人精神气质不断深入的探究,新诗史上的郭沫若形象似乎也逐渐定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立体而丰富的形象背后,仍有一些未被充分注意却较为关键的因素等待发掘。而暂时抛却前人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等尺度为《前茅》框定的位置,以另一种观照思路重审这部诗集中的作品,或可发现以往诗人形象的塑造中被遮蔽的部分,同时对文艺创作与时代精神之关系做出新的认知。
这样的观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就诗集中所收诗歌的创作年代来看,《前茅》时期(1921—1924,其中大部分诗作创作于1922年底至1923年中期)在郭沫若“诗人人格”①李长之曾以郭沫若为“诗人的性格”的代表,见李长之《现代中国新诗坛的厄运》,《晨报·文艺》1937年2月8日。而近年的学界研究也着重挖掘了“诗人”人格与精神气质对于郭沫若的本根性意味。姜涛以《女神》时期作品为核心探讨了郭沫若诗人人格的形成过程(姜涛:《解剖室中的人格想象:对郭沫若早期诗人形象的扩展性考察(初稿)》,《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刘奎则在针对抗战时期郭沫若文学活动的研究中强调了诗人身份对于郭沫若的特殊意义,这不仅由于他一生都未摆脱“诗人”之名,更在于“浪漫派诗人的思维、想象方式对他现代主体生成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对他此后革命、政治实践的内在影响”(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的发展以及文学理念的转变历程中实则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从表面上看,这段时期依靠“直觉、情调、想象”的诗歌书写模式似乎不再唯一,在对时代文化氛围的感知中,郭沫若开始寻求创作方法的新变。与此同时,已然成家而尚未立业的他这时也逐渐走出诗的王国而迈入现实社会,其间的种种遭际在诗人敏感神经的捕捉下化为不无“革命”色彩的喊叫,也潜在体现为从“Inspiration”向“Ideologie”的诗学观念的转变。如果认为郭沫若的身份及其文学创作存在着诗人/革命者、文学/政治、主观/客观、浪漫/写实等元素之间的递进或突变,那么正如论者们所注意到的那样,《前茅》时期乃是一个“转变的集中点”②楼栖:《论郭沫若的诗》,见王训昭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第248页。,一个可被识别的过渡阶段。而倘若有意突破这样二元对立的思路,强调郭沫若生命历程与文学风格的一元性,将诗人心态与作品风格的几番变化解释为同一主体状态在不同条件下不同侧面的凸显③刘奎在《诗人革命家》中引卡尔·曼海姆的论述——“在特定的案例中知识分子把其以前的身份融合在他们自己的新的组织关系中”,从而将郭沫若看起来不断改变的身份释为“他主体的不同面向在某个时段的凸显”。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第23页。,那么也有必要通过对相关文本的细读进一步探求,这般“表面上(或传记意义上的)的灵活转徙”④王璞:《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新诗评论》2014年第4期。是否总是如此游刃有余,而“当这种转换过程过于流畅,那个转换的‘主体’是否具有内在的主体性”⑤姜涛:《解剖室中的人格想象:对郭沫若早期诗人形象的扩展性考察(初稿)》,《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一
在《凤凰涅槃》《天狗》《晨安》等《女神》时期的作品中,某种具有世界视野的时代精神往往通过“我是……”“我要……”“我想……”等肯定性表达被强力召唤。有别于此,在《前茅》集和同时期其他诗文作品里,否定的句式、语气伴随着“告别”的意识屡屡出现,这样的否定不但指向对外界的破坏与反抗,更带有自我质疑、自我清算的意味,从而连带着犹疑的精神与切身的痛苦感。在最为显见的层面,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呈现出“女神”一般崇高浪漫的诗人形象在此刻遭逢的困境。
在具体文本中,“否定”的矛头首先指向自然,这个在浪漫主义文学观与“我-万物-神”一体的泛神论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前茅》中对自然的质疑,以及对“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的理想生存状态的弃绝也往往被视为诗集中最具“革命性”的成分,因为这样的反思乃是从洞穿“自然之美”的阶级性开始的:
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
那小鸟儿们的歌笑。
啊,我愿意有一把刀,
我要割断你们的头脑。
……
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
你只是在谄媚富豪!
我从前对你的赞美,
我如今要一笔勾消。①郭沫若:《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见郭沫若《前茅》,第19页。
“自然”只在“富儿们”的花园里展现其美是诗人将他原先的赞美“一笔勾消”的原因,而一种朦胧的“暴动”意识似乎也在此生成。这般决然的喊叫并不仅基于某种简单的怨愤。更进一步,诗人对“自然”的否定也缘于其身份想象和观察视角的变化。在早期诗作中,“自然”或为整个地球甚至宇宙的代指,或以广袤的松原、神秘的星空、波澜壮阔的海洋等形象示人。与之相对的是其在某个具体社会空间中存在属性的不甚鲜明。然而在成长经历中,诗人身份意识的逐渐明晰使得其笔下的“自然”生长出“神性”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属性。在这一过程里,首先出现的或许并不是自然的阶级性,而是其民族性。
身为异国学子,祖国的自然风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客居他乡的诗人的精神慰藉,也是其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的重要支撑。在1923年留学毕业即将回国之时,郭沫若的《留别日本》以一系列“自然”风物为喻凸显“祖国”的优越性,与之对比的是日本这座“新式的文明监狱”:
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山虽是荆棘满途,
可是那儿有清洁的山茶可煎。
那儿有任鸟飞的青空,
那儿有任鱼游的江湖,
那儿的牢狱是虽有如无。①郭沫若:《留别日本》,《孤军》第1卷第8、9期合刊,1923年5月9日。
然而在收入《前茅》时,作者对这一节诗进行了较大改动。“青空”“江湖”等意象被置换为“铁槌”“镰刀”,由是具备了“自然”风物所很难具有的革命属性与行动力量。可以看出在《前茅》的成集过程中,对“自然”的否定伴随着诗人对诗作的不断修改、对革命者身份的逐渐自觉而越发明显。
回到《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一诗或许可以认为,这类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诗人以相对简单的“贫富不均”概念指认了“自然之美”的阶级性并由此生长出原始的革命意志,更在于通过这样的书写,诗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呈现为浪漫主义世界观中“主体(自我)和客体(宇宙)相互认同、相互转化”②王璞:《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新诗评论》2014年第4期。混融无间的样貌,而是“自然”以“具备阶级性的风景”等形式成为“我”所要认知、剖析的对象。主客体的区隔与前者对后者的分析姿态开始瓦解“人-自然-神”的一体性,而这条纽带一旦松动,对自然的质疑与否定也就可能通向对具备神性的崇高自我位置的反思。循此可以发现,在《前茅》同时期的诗文作品中,一方面对自然的某种审美余绪尚且保留①这种审美感觉造成了一批风格清丽柔美的诗歌,大都收入《星空》诗文集,如《静夜》(1922)、《雨后》(1921)、《天上的街市》(1921)等。,另一方面诗人的观察视角与自我形象亦发生了普遍变化,从穿着“白羽衣”独立于天地之间的人神变为在地面仰望天宇的凡人。在《怆恼的葡萄》中,“我”洞察着自然的诸般矛盾,并最终以凡间诗人的身份向自然告别:
矛盾万端的自然,
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
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
将为我今日后酿酒的葡萄。②郭沫若:《怆恼的葡萄》,《中华新报·创造日》1922年7月23日。
与这样的宣言相呼应,《前茅》中的确出现了观照和介入人世间的“我”的身影。《上海的清晨》《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等诗作就直接表现了“我”对所在社会空间种种不合理现象的体察与对惨苦之人的同情。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同情不仅是人道主义式的关怀,也代表着阶级意识③汪晖在《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中谈到阶级概念在20世纪滋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动员,“第一种促成在身份、财产权甚至生产资料的掌握上并不隶属于无产阶级的成员成为该阶级的马前卒或战士,如农民或出身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主体甚至领袖;第二种动员将阶级出身设定为僵固不变的制度标记和衡量敌我的标准”(《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以此划分标准,则中国革命进程显然更多地采取了第一种动员形式。这也使得郭沫若等诗人可以通过“ideologie”的转变获得先进的阶级身份,而这种转变往往要通过文学作品来宣示。这种文学表达所承载的阶级身份认知或误认与革命实践的复杂作用关系还值得进一步发掘。的觉醒,在对底层劳动者“兄弟”“朋友”的称呼与“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④郭沫若:《上海的清晨》,《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的感受中,“我”的阶级身份已逐渐明晰。这种身份指认进而帮助诗人确立了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并进一步影响了他对文学艺术本身的认知。
二
与创作风格变化息息相关的是这一时期诗人生活状况的改变,这也影响着他对“人世间”的具体观感:孩子的接连降生为小家庭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与繁重的家务。而随着年级的增长,郭沫若的医科学业也渐次进入艰难阶段。在专业学习之外,他的文学兴味依然浓厚,诸多作品的发表与在国内引发的轰动效应也让他看到了在文坛立足的希望并努力寻找着同道中人。自1921年4月起,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中日之间来回奔波,其结果是创造社的成立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的相继发行,这一系列举动也使得郭沫若与国内文学界、出版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对于而立之年的诗人,家庭、学业与事业上的种种境遇都可化为其“转型”的某种内在因由。
在1932年写就的自传《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较为细致地回溯了这一段生活经历与心态变迁。考虑到这部自传的创作时间和动因①根据郭沫若的叙述他此前已对自传这种文体的价值有所怀疑,而促使他撰写《创造十年》的直接原因是鲁迅在《上海文艺一瞥》中对创造社的讽刺性描述(见《创造十年·发端》)。因此这部自传具有较强烈的为创造社之事业“正名”的意识。,自然不能将其视为作者十年前处境与心境的完全再现,但根据这些记述亦可大致钩沉出1921~1924年郭沫若的基本生活、社交状况及创造社的起落兴衰对诗人创作态度的影响。
回顾自身的创作道路时郭沫若认为,1919年至1920年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一个爆发期与文坛交际、报刊出版有很大关系——在这期间,与郭沫若多有书信往来的宗白华担任着《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编辑。宗白华颇为欣赏郭沫若的诗作,并以他在大自然与解剖室间洞察“宇宙意志底真相”的姿态为理想诗人人格的代表。②见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叶集》,亚东书局1929年版,第23页。在这般偏爱中,郭沫若寄去的诗稿宗白华“无有不登”,甚至“《学灯》的半面也有整登着我的诗的时候”。精神与物质双方面的鼓励刺激着郭沫若诗情的高涨:
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场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9页。
这段描述中,除去“生了热病”“战颤”这般身体性因素在诗歌创作机制中的凸显,“工场”与“生产”的修辞也颇值得关注。这里并置着两种“创造”状态:本能的、不受控制的甚至病态的身体力量的发泄,和机械的、批量化的、技术化的工场作业,而后者与市场(“销路”)的关系尤为重要。事实证明销路的保障的确刺激了郭沫若的诗歌生产,而“1920年的四五月间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从此也就消涸了”②郭沫若:《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78~79页。。《女神》中的作品多产生于这段“爆发期”。而在创造社成立前后,郭沫若一方面需要为自己谋求养家糊口的职业,另一方面也着意与友人们一同开辟属于自己的文学团体及相应的文学生产与流通渠道。
这个过程并不顺利。郭沫若和成仿吾回国后首先投靠了泰东书局。应该说对于创造社的成立与几种刊物的相继发行,泰东书局不无功劳。但在郭沫若的描述中自己与泰东基本构成一种“主奴”关系。由于没有正式的聘用合约,泰东书局并不能按时提供工资,稿酬也时有拖欠。为养家和筹集办刊经费计郭沫若屡屡跑去泰东“十块五块地要”,这在他看来自然是一种耻辱。与留学时期拥有政府的资助相比,郭沫若此时的经济情况更加困窘③徐志摩在日记中记载了1923年10月到郭沫若家做客的情形:“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毕语……”见《徐志摩全集·日记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其文学创作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物质”上的因素。与此同时,同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过节和论战似乎更让郭沫若等人体会到文坛的复杂与既有势力的“压迫”,这些也一并促成了创造社同人对自身位置与“反抗者”身份的想象。④详见刘纳《“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刘纳:《创造社与泰东书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经济上的窘境、对书局和作家间“主奴关系”的体会与对自己“弱者”身份的确认①这是创造社同人在与文学研究会等群体论战时采取的一贯姿态。成仿吾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中宣称“我们才是真的弱者,并且也很甘心是这样”(《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9月10日)。或许使诗人在想象中与城市底层劳动者分享了共同的际遇与情感,于是遂有了《上海的清晨》等诗作对工人“兄弟们”的召唤。但更多时候,《前茅》中出现的“朋友”所指显然还是郭沫若身边的文学家们。如《励失业的友人》提及“到那首阳山的路程也正好携着手儿同走!”②郭沫若:《励失业的友人》,《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27日。大约便与郭沫若和郁达夫待业在家,“以民厚里为首阳山”、自比“孤竹君之二子”的经历有关。而结合诗作末尾“我们到兵间去吧!我们到民间去吧!”的呼唤,则《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的“朋友”也多半指“亭子间”中的作家。由对这些期待读者的召唤入手,《前茅》时期诗作进一步通向了对既有文艺创作机制的反思。在《力的追求者》前两节,诗人以否定的姿态对“力”的对立面——“美”的艺术取向进行告别:
别了,低回的情趣!
别要再来缠绕我白热的心曦!
你个可怜的扑灯蛾,
你当得立地烧死!
别了,虚无的幻美!
别要再来私扣我铁石的心扉!
你个可怜的卖笑娘,
请去嫁给商人去者!③郭沫若:《力的追求者》,《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这番“告别”的语句反向对应着“到兵间去!到民间去!”的正面呼求。在这里,“艺术”自身的合法性还未被完全取消,需要转变的只是艺术的风格与诗人的心智。而在《前茅》集中,更为激烈决绝的姿态体现在诗人对文学艺术本身的否定中。
《黑魆魆的文字窟中》便表达了这样彻底的否定。这首诗聚焦于印刷工业与文学作品间的关系:
朋友说:没有一点价值的书
值不得排字的工人如此受苦!
著作家哟,你们要知道这句话的精神,
请到排字房里去坐个二三十分!
黑魆魆的文字窟中
一群苍白的黑影蠕动,
都是些十二三四的年轻兄弟!
他们的脸色就像那黑铅印在白纸。
这儿的确莫有诗,
的确莫有值得诗人留恋的美,
有的是——的确是“死”!①郭沫若:《黑魆魆的文字窟中》,《创造周报》第6号,1923年6月16日。
在这里,“诗人”发现了“排字工”的存在,因而对艺术的价值产生了质疑。问题不在于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使艺术品逐渐丧失了“灵晕”,而在于一旦将文学创作由神秘、“高贵”的内部活动还原为外部世界物质性的社会生产过程,呈现出写作-印刷-出版发行等环节的相互关系,似乎就必然觉察到文学生产-消费领域里同样存在着的某种权力等级和剥削机制。对此种剥削关系的犀利洞察使这首诗将诗人视为导致排字工中毒而死的直接“凶手”。“诗”与“死”的同构性再次出现,但这已非颓废唯美的“近世情调”的渲染,而是在“灵感”变为印刷文字的过程中真实存在的悲剧。白纸黑字与工人脸色的意象重叠不无震撼效果——似乎在印刷厂里,无论文学“形式”怎样新颖、“情感”怎样真挚,都不过是为囚禁、杀害工人的“文字窟”添砖加瓦罢了。若如伊藤虎丸所言,创造社成员普遍具有日本大正青年的“感性消费型”人格,而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的生存发展又让他们把握了在“消费生活之中的生产契机”②伊藤虎丸:《创造社和日本文学》,见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那么至少在这样的诗作里,诗人已然确定了文学并不外在于社会生产的事实。这或许是使他们的文学艺术具备“生产性”的关键因素。
在理性认知层面,郭沫若不会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导致排字工惨境的直接原因,而这般对“诗与死”关系的指涉其实是对“灵感”“情绪”“自我”之于文学写作的自足性的否定,或许还包含着对依赖印刷工业生存的现代文学/文学家之改造世界能力的质疑:如果这类文学作品(包括“我这首不成其为诗的诗”)只能促成工人的早死,那它的意义何在?诗作结尾依然是类似“到民间去”的呼喊,但这仍然无法落实为“我”真正的行动轨迹,而是代表了诗人在否定“诗”的价值后主动走向“死”的激烈告别姿态。通过将文学创作置于社会生产结构之中诗人或已朦胧意识到,文学的新生不仅意味着语言形式或情感内涵的创造,更需在根本上与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革相互牵动。
有趣的是,尽管《前茅》收录的一些诗作中存在着对诗人自矜自怜姿态的批判与嘲讽,但在这一时期,促使郭沫若一度质疑文学价值甚至企图告别“文学家”身份的其实还多是一种对自身“弱者”地位的伤怀与自恃。郭沫若1924年写就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部曲》及同题材短篇小说便在这种“自怨自艾”情绪的鼓动下宣称“悲多汶哟,歌德哟,你们莫用怒视着我,我总不是你们艺术的国度里的居民,我再不挂着你们的羊头卖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们告别,我是要永远同你们告别”①郭沫若 :《十字架》,《创造周报》第47号,1924年4月5日。。事实上,1924年郭沫若再度赴日后的确有过告别文学转而研究生理学的想法。这种“怨”的情绪在《前茅》中多有出现,无怪乎评论者在革命的“热情”之外,更多地捕捉到了诗集中以个人“经验”为背景的“悲哀分子”。②洪为法:《评郭沫若〈女神〉以后的诗》,见《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第230页。
三
《前茅》中热情与幽怨、社会关怀与自我怜惜并存的情形也许是“浪漫”精神之双面性的典型表现。如卡尔·施米特所概括的那样,“浪漫有时是力与能,有时是病弱和被撕裂,是maladie du siècle(世纪病)”③卡尔·施米特 :《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在追求“力”,告别“低回”“幻美”的同时,浪漫诗人的作品总还是不免被“病弱”和“撕裂”感缠绕。如何从既有情绪框架中挣脱,形成真正具备生产性的“喊叫”,在“否定”中生长出“肯定”的因素,无疑还将经过一番探索。而在《前茅》中已然能够发现以“肯定”形式出现的呐喊及其萌生过程。
如上所言,《励失业的友人》《朋友们怆聚在囚牢中》的呼喊针对的多半是在亭子间度着卖文生涯的作家,是这群人共同的“怆恼”情绪的释放,而最后“到民间去”的呼吁也是在召唤一种行动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行动力的获得似乎需要以彻底否定现存的感受与表达机制为前提,这就是《力的追求者》第三节所“喊”出的最为出人意料的告别:
别了,否定的精神!
别了,纤巧的花针!
我要左手拿着《可兰经》,
右手拿着剑刀一柄!①郭沫若:《力的追求者》,《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对“花针”的告别如果仍可视为在“美”与“力”、弱与强之间的取舍,那么对“否定的精神”的告别则以一种悖论性的姿态宣示着思想与行动间必然存在的抵牾及甘愿舍前而取后的抉择。表面上看,否定精神与革命精神具备同源性,而《前茅》对自然、社会、艺术及崇高自我的否定性理解也被视为其革命意识生长的前提。然而在这里,诗人更担心的是耽溺于对内外部世界无限的犹疑、反思、否定的循环并以此作成文学的材料(《怆恼的葡萄》)会进一步延滞行动的展开——无限的否定将破坏一切同一原则,而决断的做出与行动的发生却必须依赖某种同一性。因此,似乎只有抛却这样的否定机制,个体才具备参与历史发展的能动性,而自我的崇高性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获得——在否定了“否定”之后,“我”最终定格为先知与开拓者的形象,这或许也承载着诗人对革命主体的最初想象。
而在另外一些“叫喊”中,发出喊声的“我”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被召唤的主体——“我们”的浮现。如在“呐喊”色彩最为强烈的《孤军行》中,“我们”也最为密集地出现,试看最后一节:
进!进!进!
世如有无衣的男儿,
我们有戈矛赠你。
我们愿携手同行,
向着那魔群猛进!
进!进!进!
愁城中的人们哟,
请替我们喊叫三声!①郭沫若:《孤军行》,《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15日,1928年编入前茅时改题为《前进曲》。
在短促有力的“进!进!进!”的重复之间,“我们”、“人们”乃至“你”其实都可看作广义上的“我们”在不同位置的反复出现,这是一个尚未被确切命名却被赋予了巨大能量的“人群”,与之相对应的是亦无具体所指的“魔群”。在这些诗作里,“我们”取代了“我”成为新的与日月并肩的崇高主体(“逐暗净魔的太阳”),浪漫主义式的主体想象也在这样的新人称中复现。
上述诗作已呈现出诗人这一时期对社会改造途径的初步认知,而郭沫若日后回忆,“我对于政治问题发生了一些关心的,是在这个时候”②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01页。。需要探问的是,《前茅》中呐喊的“空泛”是否完全缘于诗人认知水平的局限,是否是将政治宣传安插进文学作品的必然后果,还是另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从中作用。
检视这些诗歌的发表媒介与导致诗人对政治问题“发生关心”的直接原因或可为上述问题寻找思路。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提到与“孤军派”成员的接触是其文学政治化转型的一个起点。这里的“孤军派”指的是《孤军》杂志的主要编辑和作者群体,郭沫若与他们多有交往,而《孤军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等篇目都刊登在《孤军》杂志中。郭沫若创作与《孤军》杂志的联系一方面说明了人际关系对作家转型的影响①此方面研究参见陈俐《郭沫若政治转向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探微》,《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3期。,另一方面也再次呈现出文学生产、政治运作与商业出版在都市文化语境中相互作用、彼此依存的方式。
就政治倾向而言,“孤军派”一般被认为是主张国家主义的团体,然而其内部成员的思想与行动轨迹亦多有不同。按照郭沫若的理解,他们的主张以恢复“约法”为中心,是与“好人政府”和“劳农革命”鼎足分立的社会改造思路。在当时郭沫若似乎更倾向于革命,但他对政治经济学出身的友人们的观点亦未加置喙,并同意参加例会和为《孤军》提供稿件。这样的合作是互利的,诗人需要表达的渠道与进一步认识社会、了解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途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刊物也看重郭沫若在新诗坛上的位置与文学才能为其带来的更为广阔的市场。因此对于具体政治主张上的隔阂双方似乎均有体察却选择了暂时搁置,毕竟发出充满“热情”与“正义感”的喊叫是他们最为核心的共同诉求。②“孤军派”成员对与郭沫若合作的观点可参看何公敢《忆〈孤军〉》,《福建文学史料》1986年第13辑。如学者所言,“在对现实世界的最初的‘文学性’感受中,他们是可以沟通的”③李怡:《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在郭沫若后来的分析里,当时无论恢复约法、好人政府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似乎都还携带着比较强烈的“文学性”的感受方式(郭沫若以“唯心”概括之)而缺乏深入社会肌理的考察和完备周密的理论体系。。然而在具体表达层面,郭沫若亦不得不考虑到杂志主办者的政治主张。收入《前茅》的某些篇目是为《孤军》的特别专号而写,类似于命题作文,如《孤军行》便被作为杂志创刊的宣言,《留别日本》则刊登在针对“二十一条”国耻的“五九纪念”专号。这种情况下,语义的含混与呐喊的空泛或许也是题目要求与主张分歧下具备调和色彩的产物。而《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则刊登于“推倒军阀”专号,诗歌在结尾处明确给出了祛除“毒菌”(军阀)的办法,并预言了中国在20世纪革命中的重要位置:
已往的美与法——是十八世纪的两大革命,
新兴的俄与中——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华人权大革命哟!
……
你们把人权恢复了之后,世界统一的使命,永远平和的使命,
要望你们二十世纪的两个新星双肩并举!
郭沫若以俄式革命恢复“人权”乃至“统一世界”的主张显然与强调裁兵约法的《孤军》同人有所不同。是以在这首诗刊登之时,编者以附注的形式申明了对此诗的理解:“郭沫若先生所谓革命单指扑灭军阀而言,非调约法也可抛弃,读者切勿‘以辞害意’!”①《孤军》第4、5期合刊,1923年1月1日。
与《孤军》的合作促使郭沫若的政治意识进一步生长,但生长的结果无疑会导致与友人分歧的加剧。从人际关系来看郭沫若与几位“孤军派”成员始终维持了不错的情谊,而在合作渠道上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人却在寻找着其他的可能。时机对他们而言或许有利——文学与政治合流已然成为一种时髦趋势,创造社的名声也让许多追求知名度与发行量的社团报刊主动递出橄榄枝。1923年创造社与《中华新报》合作编辑了日刊《创造日》,《前茅》中收录的《怆恼的葡萄》就曾在《创造日》发表。虽然意识到《中华新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其政治主张与创造社同人亦多有出入,但考虑到日刊所能带来的影响力,郭沫若等人还是以“不沾染他们的政治色彩”为自我安慰同意了合作的要求。1924年,太平洋社提出与创造社合办《创造周报》,分为政治与文艺两个模块,分别由在北京的太平洋社和在上海的创造社负责。郭沫若等人同样不喜太平洋社的政治色彩,但在郭沫若赴日后,合作仍然达成,两社合作的结果是《现代评论》的诞生。
关于为何在不接受对方政治主张之时仍要维持合作,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给出了说法:“把方向转换到政治方面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要求”,而“我们却没有转换的能力”。②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63页。这“转换能力”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同人此时都还未形成独立系统的社会发展观念与政治主张,其对“革命”“阶级斗争”等概念的理解亦未超出“反抗精神”“创造力”等文学的范畴。另一方面,创造社主要成员的社会身份决定了这一社团终究只是依附于都市报刊与出版业的文学团体,尚不足以具备真正的政治能动性。与“孤军派”、《中华新报》乃至太平洋社的几番合作真正令郭沫若感到失望的不是“文艺”最终成为“政论”的附属品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64页。,而是在缺乏独立明确且具备一定理论支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判断力、群体行动力时——换言之,当自身不具备“转换能力”时,“文学”感性的呐喊就只得为各种政治理念、政治团体所利用,而丧失了深度生长的空间。在文学与政治间建立勾连的尝试与几次不甚愉快的合作无疑为诗人接下来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四
除去直接激烈的呐喊,某种较为隐曲的思索与表达形式亦在《前茅》中有所出现。古事与古体的回归就为这种表达提供了载体。
相比于胡适在新旧诗体之间曾做出的决绝判断,郭沫若似乎始终不曾反对旧体诗创作并且不掩藏自己对这种诗艺的谙熟。旧体诗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在《前茅》时期,这似乎是他探索诗歌技艺、重释传统思想甚至审视自身、表达心曲的较为重要的文学形式。自《女神》时期开始,郭沫若的新诗、诗剧中就常有古事古体出现。1923年泰东书局出版了他翻译《诗经》中部分作品的《卷耳集》,这些译稿曾相继在《创造日》发表。《前茅》中亦收录了两篇与古事古体相关的诗作:《暴虎辞》与《哀时古调九首》。前者创作时间较早,是计划中历史剧《苏武与李陵》的楔子。而后者以“古调”叙写心境,以“古事”影射今事,或许更能呈现出诗人彼时的生活与情感状态。
这一组古调同样发表于《孤军》杂志,诗意多暧昧难解。多年后诗人在《创造十年》中逐一解释了诗作的针对对象,它们囊括了对军界、政界、教育界等多方面形势的观感,其中某些时局批判在当时语境下大约只能以隐晦之语出之,如《古调》第六首“孙悟空,齐天圣,/十万八千里,只消一翻身。/才闻专使拜曹公,/又见三桂哭清庭”等句,便是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联络曹锟、张作霖等军阀势力的不满。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自身处境的描绘。根据郭沫若的解释,《哀时古调九首》中的前两首就是他个人状态的呈现: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
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
人贱不如铜。
一碗饭,五羊皮,
养活淮阴侯,
买死百里奚。
伯夷叔齐首阳山,
不合时宜该饿死。
四支,五微,
秋高马正肥。①郭沫若:《哀时古调九首》,见郭沫若《前茅》,第49~50页。
前一首的关键在于作诗时的身体感受。彼时郭沫若为了创作《孤竹君之二子》立意绝食体验伯夷叔齐挨饿的情形,结果却得了这几首诗。“嵇康抚琴”指的是好友陶晶孙在楼上弹奏钢琴,琴声正伴着郭沫若饥肠辘辘的节奏,也与“一东,二冬”的韵脚相似。第二首则明确提到伯夷叔齐,此处所指还是郭沫若等人与泰东书局“类似友情的主奴关系”。似乎与泰东的情分牵绊着他们不能另择明主,“善于自行解嘲”的诗人于是自比为伯夷叔齐的“高洁”。②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14页。当故意挨饿寻找创作灵感的举动加之以“人贱不如铜”的感慨、古韵糅合着西洋乐器的“风雅”、首阳山上的上古隐士对应着现代作家与出版机构间的尴尬关系并以小调的形式掺杂书写,这样的诗作也就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反讽色彩。在这里,内与外、身与心、个人与国家等因素叠合缠绕,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否定与质疑,从中可见写作主体纠结忧郁而又企图从中解脱的心态。第九首古调以“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耨!”作结,似乎也有从否定中生长出肯定力量的态势,而在为此诗作注时,郭沫若将诗中的自我形象描绘为“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这似乎又为革命式的呐喊平添了几分自嘲意味。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14、219页。可以继续追问的是,在苦闷的心绪、变革的意念与玩味自己情思的余闲之中,一个新的“文学-政治主体”是否可能产生。
关于深具浪漫精神的文学家能否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主体,卡尔·施米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施米特的分析基于对浪漫派“主体化的机缘论”的发现,即浪漫的主体倾向于把整个世界当作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由此,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在浪漫派的视野中都“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并成为某种抒情体验。而从这种“审美的自负扩张”中生长出的消泯了分歧与决断的“政治活力”终究只是幻象。归根结底,“一切政治能动性——不管其内容是纯粹的征服技巧、政治权力的要求或扩张,或是建立在法律或道德决断上——都与浪漫派的审美本质相冲突”。当浪漫的“有创造性的人”终究不能成为政治上的“能动者”,其在历史大潮中就成了某种悖论性存在——施米特以德国的浪漫派“先是把大革命浪漫化,然后又把得势的复辟势力浪漫化”为例说明这种浪漫精神一贯的依附性。最终,“一切浪漫现象都是受非浪漫力量的控制”,而那个坚持“自我”的崇高属性,“昂首超然于各种限制与决断之上的人,变成了异己势力和异己决断的臣仆”。②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20~21、198~201页。施米特的判断似乎正印证着人们对郭沫若一生经历的认知抑或某种偏见,而对于探究中国“浪漫派”的生命历程,重思浪漫与现实、文学与政治、诗人与革命家的关系而言,施米特所提出的问题——政治能动性与审美本质的冲突——无疑是严峻而深刻的。如果承认“审美的自负扩张”与“政治活力”不可混为一谈,而又看到“浪漫”的主体的确曾主动参与塑造着政治变革与历史发展历程而非总是被动臣服于“异己势力”,那么从个体经验出发探究审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也许是可行的路径。具体到郭沫若而言或可探讨的是,自《前茅》时期以来,徘徊于“人生的歧路”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第267页。尚待形成的主体究竟通过某种“否定”的诗艺实践着怎样的自我扬弃。
在这里,“自我”的位置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的第一期,郭沫若以《创造者》与《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两首诗宣示着创造事业与从事创造的主体——“我”的巨大能量:
海上起着涟漪,
天无一点织云,
初升的旭日
照入我的诗心,
秋风吹,
吹着亭前的月桂。
枝枝摇曳,
好像在向我笑微微。
吹,吹,秋风!
挥,挥,我的笔锋!
我知道神会到了,
我要努力创造!.
作《吠陀》的印度古诗人哟!
作《神曲》的但丁哟!
作《失乐园》的米尔顿哟!
作《浮士德悲剧》的歌德哟!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孤高,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苦恼,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狂欢,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光耀。
……
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
我要高赞这开辟洪荒的大我。①郭沫若:《创造者》,《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1922年3月15日。
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
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
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②郭沫若:《创世工程之第七日》,《创造周报》第1期,1923年5月13日。
“秋风”与“笔锋”的共振暗示着创造事业得之于自然的伟力,而在创造世界同时重造自我的宏愿则将文学创作者提升至造物主的神圣位置。在社团刊物面世之际,对“开辟洪荒的大我”的高赞无疑是向外界展示这一新兴团体在“创造”方面的高度自信。然而如上所述,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伴随着对自身既有自然观、艺术观的否定,诗人的“自我”也逐渐遭受着质疑。这般对“我”的矛盾姿态在郭沫若的文论中亦有所体现。在《批评与梦》中,郭沫若提出文学批评要充分体察创作者“心的活动”并申明自己的创作态度:“我不愿当个那么样的通人,我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像留音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③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1923年7月1日。“言为心声”的认知确保了自我之于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留音机”在这里则作为理想创作状态的对立面出现。这样的认识与表述方式在随后几年中不断发生着微妙的调整。在1925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讲演中,“无我”与“大我”的关系被再度提出:
德国哲学家萧本华(Schopenhauer)说,天才即是纯粹的客观性(Reine.Objectivitat),所谓纯粹的客观性,便是把小我忘掉,溶合于大宇宙之中,即是没我。——即是没有丝毫的功利心……艺术的精神就是这无我。④郭沫若:《生活的艺术化——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时事新报·艺术》第98期,1925年5月12日。
这里的“无我”似乎更偏重于“无功利心”。但与此同时,对一己身心感受——所谓饥寒与情感——的忘却与超越也是达成“艺术”之“纯粹客观”精神的关键。而在强调以“无我”的方式完成“大我”,以将作家“削弱成服务于更高法则的一种客观工具性”的方式使其获得“作为主体、行动者和立法者的地位”①见詹姆斯·钱德勒对雪莱《西风歌》的讨论,转引自王璞:《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新诗评论》2014年第4期。之时,不可讳言“自我”的某些方面的确需要被抛弃。这不仅指自我情感的直接表达(“饥则啼、寒则号”),更是自我在感知外部世界时一系列相对定型的审美、玩味或反思、批判机制,也即所谓“否定的精神,纤巧的花针”②程凯在分析新文学知识分子对“留声机”问题的言说时认为:“‘留声机’意味着不经过‘自我’消化或反思的机械认同和传达。而且,‘自我’不单是反思性的理解机制也是反思性的传达机制,如果取消后者,简单地书写个人经验也不过充当‘自己的留声机’。”见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这样的抛弃与告别诚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却也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世界之于浪漫主体的“机缘”关系——世界在此已非能被整合进“有创造性的人”固有审美抒情机制的材料,或是“我”神奇笔锋下的产物,而是需要个体以赤裸裸的姿态去投入的客观存在。应该说在“小我”通向不同形态的“大我”的链条中,自我的重要性始终不曾被完全取消,而自我否定意识所赋予自我的开放性、流动性,也是其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不断生长出新的力量的关键。
对自我之伟力与局限、自我与世界复杂关系的体认或许最终通向了文学与政治之关联以及文学-政治主体的生成问题。如果将这里的“政治”具体理解为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革命实践,则对自然、艺术、自我等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中的反复认知便是文学“政治化”(文学与革命发生结合)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前茅》时期,“艺术”与“革命”的同构基本体现在二者情绪(“热情”)与历史目的(“美化社会”)的相通性中。③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9日。而在此之后,当诗人通过研读社会科学理论而获得了“理性的背光”与“维系着生命的梦想”④郭沫若 :《创造十年续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205页。,并逐渐介入具体的社会调查与革命政治实践,他对二者关系的认知也经历着持续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文学”精神中生长出真正的“政治”动能不仅需要自我-社会-全人类这条“感应神经”的敏锐,还需要科学知识、社会参与、思想指导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许,在郭沫若这里浪漫诗人的气质最终作为某种本源性的因素保留了下来,融合到了他的革命者身份中,但至少如《前茅》时期这样喊叫与自嘲、肯定与否定并存的状态表明他在文学与政治间的转徙过程并非十分平顺,所谓“文学-政治主体”,也并非某种既定的概念范畴或身份想象,而更宜理解为对“转换能力”的自觉追求,以及在这两个场域间往复穿梭,建构具体、动态关联的持续努力。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前茅》时期诗作呈现出的纠结辩驳、尚未形成的主体状态所蕴含的可能性有待于在后续历史发展轨迹中逐渐展开。推而广之,这一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也不断为文学对政治的主动参与、深层互动和独特把握开辟着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