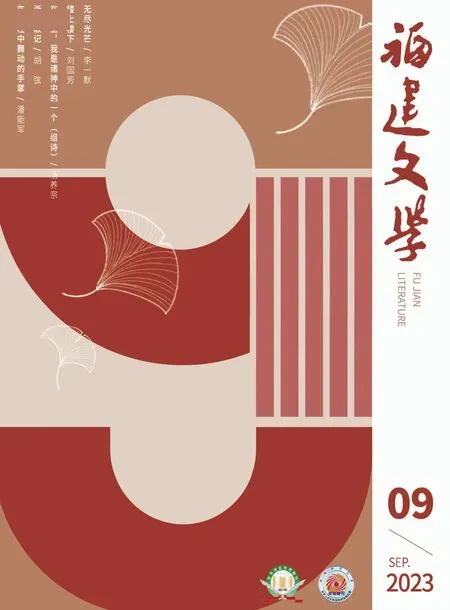西街小吃店
2023-10-03柯翰杰
柯翰杰
推荐人语
陈培浩(著名评论家,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青年作家柯翰杰的小说《西街小吃店》很有特色,很有嚼劲,也很有意味,值得推荐。
《西街小吃店》属于校园文学题材,但又不完全是。校园生活几乎没有涉及,重点在学校外面这条西街上。作者写人状物,栩栩如生,很善于赋予人物独特的个性,比如麻辣烫店女老板的唠叨、沙县小吃店老板的沉默、面线糊店老板的自得其乐。写作上的写实并非认领,而是创造。你必须把人物从脑海中清晰而且精确地创造出来。好作家写作时,人物个性在头脑里一定是分明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A 很难说出B 的话,反之亦然,这是个性使然。但很多初学写作的人,笔下人物说出来的话,让人要么觉得违和,要么觉得模糊。柯翰杰的语言造型能力很强,写出来惟妙惟肖,让人觉得像,觉得就该是这样。这是写作能力的一种天然表现。
《西街小吃店》写到麻辣烫店女老板时,我以为小说会变着法子写同一个人,那就有点像《祝福》了。但作家必须打破读者的期待,他更换了好几个对象。虽然写了好几个人,但是这些对象的人生和命运依然是清晰的。每个人都是其命运之树长出的果实。他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长成什么样。于是,你忍不住想:麻辣烫店女老板的儿子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让麻辣烫店女老板变成一个对顾客的感受毫不在意的人?又是什么使沙县小吃店老板变得那么沉默,用一个“嗯”字就完成了与社会的大部分交道?
最终,你会发现:《西街小吃店》不是校园小说,也不是世情小说,而是沉思的青春小说。小说写那么多人,归根结底还是写一个青年——“我”对人生选择的迷惘。多年前,面线糊店老板读完大学,仍旧子承父业,他是知道自己的幸福何在的。而“我”呢,被生活推回到曾经学习的地方,成为一名计算机教师。西街已经物是人非,但生活中很多东西又似亘古不变。在这无所不在的剧变中,为什么学校里权力的规矩仍旧坚挺?这大概是很使作者感慨的,也是《西街小吃店》很有意味之处。
李世成(青年小说家,著有小说集《月亮今天亮了吗》,曾获“台积电文学赏”):
柯翰杰的《西街小吃店》,是一篇充满意趣的小说。从学校地理位置“东/西街”到结识三家小食店谈起,一种淡淡的忧伤,贯穿始终。同时还要一本正经“搞笑”,少年人的青春皆是“梗”,读来想笑但不忍笑。麻辣烫店女人、沙县小吃店只说“嗯”的老板、面线糊店青年……躲藏,离群,理想,每一个可供臆想和虚构的形象与符号,都被青春时期的“我”给用心打发过了。
偷偷在外进食,自我娱乐和享乐,假想中与学校规约“对抗”,穿上校服和脱下校服的心境……是无所事事也好,不解忧愁也罢,年少时失去了什么没人说得清。正如作者讲述的故事,你说他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还是给读者来一场自黑的长时脱口秀?这都不重要。
回到文本,柯翰杰的叙事能抓住人的地方,在于选材和视角有别于常见的青春叙事,与一些言及青春势必追悔的版本不同,他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坦直承认“失去”和让幻象存活的版本。没有不舍,没有追认。
作为00后作者,柯翰杰对时光与事物的感知,新鲜且倔强。
2012 年,我还在上中学,学校那时刚刚完成翻新。崭新的教学楼宏伟的校门,校门外流着一条自西向东的街——西街。为什么要叫西街不叫东街?沿街行走无所事事时,我常思考这个问题,明明是向东的啊。不知是哪一天我才顿悟,或许是店面都重重压在西边这头,越往东,离学校越远。
这未必是一个正确答案,可事实证明,很多商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学校刚完成整修后便限制学生的出行——放学后,在校生只能吃校内食堂,走读生只比他们多一个选项,即回家吃饭。真可恶,学校把店面租给了饭店,用人流骗得了高昂的租金,却连被选择的机会都不愿给他们。
校方给出的理由很多,学生在校内更容易管控,校内的食物也更便宜,更安全。大家心知肚明的理由也不少,校内的伙食并不丰盛,若是大家都到外面吃饭,校内的三座大食堂便难以运转。即便如此,翻新伊始时,仍有不少的学生趁保安不注意溜出学校,可学校派出教导沿街巡视后,便少了很多以身试法的人。西街显而易见地冷清了下来,汉堡王、拉面馆、福鼎肉片……原先花花绿绿的商铺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闭,仍旧坚挺着的,只有几所以打包售卖为主要营业渠道的店铺,大多是小吃店。
我不知道那些租在东边的店家是否苦恼过,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离西边较远,外加需要拐弯,这些店家很难被巡视的教导察觉,在那个外卖还不发达的年代,它们反而存活了下来。在西边开张起千篇一律的便利店和文具店时,关东煮、奶茶店、蚵仔煎……五花八门的店家仍活跃于东边。路过那些零星的饭馆时,我甚至觉得,这条街道早就应该改路名换招牌,“东街”远比“西街”合适。
当然,大多数人不会关心这个问题,甚至会忘掉西街的名字——自从学校禁止外出政策开始落实后,去西街的学生便寥寥无几。“还会拿着走读生的电子资料一个个问呢。”几乎所有人都就此放弃,不过,我是个例外。触犯校规我也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我只是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虽然是走读生,但回去并没有人给我做饭。另一方面,校内食堂动辄排上二三十分钟的长队实在难熬,反倒西街店家更高效,光顾西街就此成为最佳选择。我记得很清楚,由于口感挑剔的缘故,我最常光顾的店家最后只剩三家——麻辣烫店,沙县小吃店,还有坐落在沙县小吃店和麻辣烫店中间的面线糊店。
起先,我最常光顾的是麻辣烫店——它是三家店中最靠近学校的一家,做东西最快,也最先进入我的视野。麻辣烫店店名我早已忘了,它的味道太过普通,可麻辣烫的店家我至今仍有印象。那是一个很瘦的女人,瘦得双腮尖削,嘴唇却很厚,吊着尖嗓,讲起话来滔滔不绝。麻辣烫的做法并不复杂,先选食材,后拌香油料酒一类作料,若是手脚麻利,一份麻辣烫五分钟就能完成。
若单从时间上看,麻辣烫女人的手脚并不拖沓。可不同于其他店家的地方在于,别的店家选食、搅拌用时四六开,她却通常是二八开,甚至一九开——其中的八和九,她通常用来和顾客聊天。店里的味道很大,夏天没有空调,一开口更容易被呛得满口热辣。可女人似乎习惯了这一切,自顾自滔滔不绝,也从未察觉到顾客的不自在。
“我表姐家的儿子都考上大学了,我啊……”麻辣烫女人经常说这些,左邻右舍,自家家常。内容不新鲜,却也不讨人烦,可这些数不尽的话题足以让她打发掉大中午的顾客——她认为她需要打发。很显然,并不是所有顾客都买她的账,在她发出“我要是能这样也就放心了”之类的感慨时,“嗯”一声回应,点头表示赞许,就算尽了仁义道德。大部分顾客都只当她是柜台内的演说家,一个孤芳自赏,不求掌声,永远打不破第四堵墙的演说家。
说着说着,麻辣烫也就拌好了。“给。”她厚实的嘴唇终于合上,多数客人通常接过后便转身离开。每天饭店里来来往往的客人不多也不少,白T 恤黑衬衫、高矮胖瘦、男女老少都有,等待的时间大抵相同,来去的动作也千篇一律。由于很难归纳出顾客的特点,有时我甚至会忘记这是一家开在学校旁边的小吃店。
“你知道吗?我儿子啊……”由于太频繁来的缘故,她的主要故事我都耳熟能详。她总是一边拌着酱料一边告诉我,她的儿子在上中学,以前成绩还行,可不知为什么,自从升入初二后迷上了电脑游戏,成绩也一落千丈。“孩子大了,我又忙,管是管不了哦,说想当电竞选手,一说他就冲我发火,随他去吧……”她经常这样感慨,我时不时接上一声“嗯”。
来了有几回后我才知道,这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点。或许是她儿子的故事说腻了,她才说起其他的故事。“你知道吗?他爸啊……”他爸爸是卖衣服的,没赚几个钱,却整天游手好闲。“你说,他这样当爸,带出来的儿子能好到哪去啊?”不知是哪一天,我终于听到,又或者说是注意到这句话,前后两件事终于关联了起来。接着她又开始了感慨,“管是管不了哦,一说他就冲我发火,随他去吧……”
“嗯。”我说。这次答话倒是带了几分真诚。头一回听到故事的第二章,尽管语调、神情、叹息声同之前很相似,可毕竟是一个新故事,我跟着接上一声淡淡的叹息——除了饭钱,她也值得这样的回报。
我并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若日子能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未必会抛弃麻辣店。可不知是哪一天,她开始注意到,或是开始表明注意到了我胸口的校服标志。
“啊,你是一中这边的学生啊。”她指了指我的胸口,神情有几分讶异。
“是啊。”在回答她的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家开在学校旁边的小吃店。
“能在一中读书,是真的好。我儿子就不像你们呀……”她感慨道,又连篇说了一大堆,我只得尴尬地笑笑。
她接着又问:“你在这边读几年级啊?”
“高……”高二。我刚想开口,可又打住了话头。虽然我每次在这儿打包完就匆匆离开,可每天中午出校的人不多,加之学校随机抽查,并不排除学校拿着我的电子照片询问店家的可能。头一个字已经开口,实话实说肯定不行,若是说高一,她的孩子也读高一,会不会因此进一步追问?如果说高三,她会不会反问,一中高三的学生还有心思出来瞎逛?情急之下,我随口回答说:“高中。”
她应该不会继续追问吧,我天真地认为。就在我急匆匆转身准备离开时,她居然更大声地问我:“高中啊,到底是高几啊……”“就是高中啦。”我说。她似乎没察觉到我的不快,竟然自顾自更大声了起来:“我儿子也是高中呀,现在读高一,你……”
“我高三,改天再聊吧。”我没顾及她接下来还说了什么,便转身匆匆离去,走,快点走,身后的声音顷刻就消失了。一直到家门口我都没回头。平静下来后,我才意识到,早在我匆匆离去的那瞬间,我就暗下决心,再不去那家麻辣烫店了。
从那天起,我必须在剩下的店家中做选择。除去昂贵的火锅店,胃口不适的川菜店,只剩下沙县小吃店和面线糊店两家。我并不想在过多的店家里留下足迹,可就在我还来不及选择时,一件更棘手的事情摆在了眼前。
麻辣烫店坐落在沙县小吃店和面线糊店前头。这也意味着,不论我要去它们中的哪一家,都得先路过麻辣烫店。每天来来回回,哪怕我刻意回避,也总觉得麻辣烫女人在直勾勾看着我,后脖颈热得发烫。有那么一刻,我也替她感到委屈。她并没有做错什么,随口一问就失去了我。可我抛弃她也没有错,我没有义务被她拥有。我跟她的故事,就是一个麻辣烫女人和一个高中生常客的故事;一个爱讲自己故事的女人和一个爱答“嗯”的高中生常客的故事;这个高中生在被探听身份后,再也不光顾麻辣烫的故事。若是其他人问起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就此了结。
想到这,我决定坦坦荡荡地经过麻辣烫店。第一天,第二天……一直到不光顾成为常态的某一天,我深吸了口气,充满期待但又紧张地转头,以为会撞上她的眼神,但并没有,她仍自顾自大声讲着她的故事,她的邻居、表姐、儿子、丈夫……或许还有其他人,但都与我无关了。她也在回避我吗?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没有义务被她拥有。
为了防止相似的纠结再次发生,我决定选择那家靠后的沙县小吃店。如若以后决定抛弃掉它,便不会再有类似的尴尬。尽管沙县小吃店离学校更远,但远也有远的好处——它藏在拐角更深处,几乎要和学校脱节的地方。一般的巡视,不会将其考虑在内,用更远的路上更多的保险,这样的买卖在当时的我看来很划算。
抱着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我来到沙县小吃店。沙县小吃店老板和麻辣烫女人可以说是大相径庭,麻辣烫女人一进门就会招呼,可我进沙县小吃店足足一分多钟,他仍自顾自看着手机,若不是他抬过头,不止一次抬了头,我甚至会怀疑他没感知到我的存在。
“老板?”
“嗯?”
嗯?我不知道怎么答话。我们足足对视了三秒,三秒的尴尬,或许只是我一个人的尴尬,我决定开口。
“要一份拌面,一份扁食。”
“嗯。”
“我要打包。”
“嗯。”
“不要一次性筷子和汤勺。”
“嗯。”
刚进店不到三分钟,我就知道这家店始终空荡荡的原因。老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相貌的优缺点一并遮了去,面上也总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时间像风和阳光一样在店里凝固了,从头到尾,他只会说一句话,话里只有一个字。
“钱放在柜台上了。十块。”
“嗯。”
那时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一个个“嗯”字,让我对沙县小吃店有了莫名的好感。这种好感甚至让我想要留在沙县小吃店内堂食——拌面必须即刻搅拌,打包带走,时间一久便结成团,难以下咽,而这里的位置、这里的人都绝对安全。从麻辣烫店到面线糊店要不了两分钟,面线糊店到沙县小吃店却快要四分钟,我这样的年轻人都走得气喘吁吁,更何况肥头大耳的教导处主任。哪怕在这边堂食,也不见得比在麻辣烫打包不安全。
因此,在连续打包快一个星期后,我终于下定决心留在沙县小吃店就餐。“我在这里吃就行。”我告诉老板。“嗯。”他反应的速度,回答的语音语调,仍和之前我问他任何问题那样没有差别,仿佛琴键正中的中央C,不论你怎么按,它都统一得毫无特点。我更放心了。
“嗯。”我也说。
不知是哪天,我忽然意识到,很多关系颠倒过来了。在麻辣烫店里,我是一个只会说“嗯”的人,可在沙县小吃店,只会说“嗯”的人不是我,反而是老板。一切的一切,都同之前有了反转,我了解麻辣烫女人的一切,她的邻居、儿子、表姐、丈夫……但她最多知道我是学生。可沙县小吃店老板对我的了解,甚至比我对他的了解还要多。他知道我每天十二点路过这,喜欢吃扁食拌面,扁食不喜欢加香菜,拌面的酱汁喜欢稀一点。他知道我喜欢用汤勺吃拌面,吃一次大约十五分钟,不喜欢放辣酱醋盐。若是他留心观察,他还会发现我是个左撇子,离店时往哪走,我的衣服、裤子、鞋子、书包……所有关于学生的一切,都暴露在这家沙县小吃店内。店里通常只有我一个人,他要注意到我并不难。
可他对于我来说呢?我从第一天来,就知道他是一个沙县小吃店老板,一个穿一身白衣服,面无表情,只会说“嗯”的老板。除此之外,我再也搜索不到其他信息——每次他做扁食拌面,都会走到里间,有时三分钟,有时八分钟,很不固定。他低下头看手机时,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不管是手机还是人。有一次我好奇他究竟在看什么,便把脖子伸了过去,只看到一片漆黑。你刚刚在玩什么?我很想这么问。“手机不错嘛。”“嗯。”只是回答的间隔稍微长了点,这让我很纳闷。
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安静得像个好学生,我只能这样归纳。因为学校不允许学生带手机,每次到沙县小吃店时,我总是一边吃,一边想,如果有一天,教导主任来到这问话,他怎么回答呢?面对着一张张走读生的照片,他会把我供出来吗?“有学生来过这里吃吗?”“嗯。”他点点头。教导主任拿出他的电子显示器,一张张划,“看到过吗?”他摇摇头。“看到过吗?”他又摇摇头。“看到过吗?”“嗯。”他点点头。显示器上显示的,正是我,一个十七岁高中生面无表情的证件照。
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突然在我心中萌发了。我忽然意识到,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先前那种走出校门踏入沙县小吃店,不用吃两素一荤,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愉悦感不见了。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晋江市民的愉悦感不见了。麻辣烫女人接触的学生多,或许知道学校查岗的事,可沙县小吃店的老板似乎对此一无所知,一旦被查问,他一定很快就会把我供出来,一定。教导主任是我的科任老师,他完全可以进一步确认。“他一般十二点后到这边。”“嗯。”“他是个左撇子。”“嗯。”“他背蓝色书包,穿蓝色回力运动鞋。”“嗯。”我突然有种被扒光衣服后紧张的羞耻感。想到这,我忽然意识到来沙县小吃店吃东西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事情一旦发生,再低的概率,也会成为百分之一百。
要选择其他店家吗?那只会让我更危险。我并非没有考虑过回到麻辣烫店,可想到她可能会开口说,“你怎么那么久没来了?”“可以跟我儿子一起吃啊。”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帮我一个忙可以吗?”犹豫好久,我才决定尝试给他打预防针。
“嗯?”
“是这样的……”我开始给他详细地介绍学校的戒严政策,我每讲一阵,他就点点头,连“嗯”都很少说。
“所以,你能帮我个忙吗?”我说了不知多久,累得气喘吁吁。
“嗯。”
“以后要是教导主任问起我的时候,你就说没有,没有见过我。”
“教导主任?”他突然瞪大了眼睛,像是有生之年头一次学会说除“嗯”以外的话,“你不就是教导主任吗?”
“我是学生啊。”我突然有点生气,“你就看不出我是学生吗?”
“嗯。”他顿了顿,才答复。
一种莫名的怒火突然从我胸中燃起,霎时间,我忘了先前我跟他说那么多学校政策的目的。我忍不住跟他说,我每天中午都来这边,十二点左右,总是点扁食和拌面。我吃扁食不喜欢加香菜,拌面的酱汁喜欢稀一点。过去每天都说一遍的话,今天在一遍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遍。我每说一句,他就“嗯”一回。
“清楚了吗?”
“嗯。”他点了点头。
“我都来了那么多遍了。”
“嗯。”
“你就一点都不知道吗?”
“嗯。”这次回答的间隔稍微长了一点。我突然有点哭笑不得,问他为什么不清楚。他像是想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说,每天不同的点都有穿白衣服的人来这边。中午,下午,晚上……他坐在柜台里,只能看到他们的白衣服,统一的裤子看不到,更不会去打量胸口的学校标志。
他并不认得我,更不知道我是学生,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意思。
“所以如果教导主任来这边的话,”他终于主动开口,“我就把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说给他听吗?”
时间又一次凝固了。整个沙县小吃店安静了三秒,三秒的尴尬。对视的发起人从我变成了他。我忽然觉得自己真是太愚蠢了,硬生生把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变成了最危险、最像学校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他完全不了解不是更好吗?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但世上没有后悔药,我只好跟他说:“别,千万别。你就当我刚刚这些话全都没说过,甚至完全没来过这儿就行。”
“嗯。”
那也是我听他说的最后一次“嗯”。他已经知道我了,我只能放弃他。但或许他不久后就会将我彻底遗忘,他和麻辣烫女人不同,哪怕还知道,我也无须愧疚或紧张。只是我没想到,就在我离开后不久,那家沙县小吃店就关门大吉,成为西街东边最先倒闭的一家店。这也在情理之中,我所有的担忧也就此一扫而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就这样,面线糊店成为我最后的唯一的选择。面线糊店的老板很年轻,至少看上去比我要年轻,如果不是他自己提及,我甚至会一直以为,他是个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的面线糊青年。
“我以前也认真读书,高考五百多分,考上了大学。”他笑了笑,“找了很多工作,还是觉得跟爸爸做面线糊最快乐。”
是在很久以后,我才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的。那时的我还间歇性信奉着学校讲堂里“清晨六点的天很黑,但六百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的集体式咆哮,并没把这句话放心上,但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就有一种莫名的愉悦感。做面线糊最快乐了。我知道的,我不在一中,不在学校食堂,而是在学校外的一家面线糊店。
我必须承认,面线糊青年给我的感觉最舒适。他不会像麻辣烫女人那样张着厚唇自顾自说个不停,也不会像沙县小吃店老板那样一言不发。我们都不是说“嗯”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像个刚进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没有老领导架子,很容易就跟学生打成一片。尽管我在面线糊店驻足的时间并不长,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要加什么?”“醋肉,卤蛋,火腿……”他的动作很利索,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利索,这跟麻辣烫女人那种利索得过于急切的神情很不相同。他一样一样加,分量刚刚好,“多给你夹点肉,下午上课有精神,听课才不闷。”多打了两勺,很恰如其分的,“闷了也没事,下次过来我再给你添。”
我们总是这样恰如其分地讲着跟学校有关的话。“一下课就来你这了。”“那下次别等到下课咯。”“作业真的太多了。”“没关系,学什么就忘什么,哪怕忘不掉,也没啥用。”“你上中学的时候有想过以后会做面线糊吗?”“有啊,当然有啊。”
他是认真的吗?我瞪大了眼睛。
“我从小就吃我爸的面线糊,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一直开面线糊店。”他言辞笃定,我也无言以对。
事实上,做面线糊也没什么不好。就像后来兴起的外卖小哥、滴滴司机、顺丰快递……很多人风吹日晒里求得的生计并不比写字楼里的人差。当然,那时的我体会不到这些,但也没想过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最近一次在学校听到“理想”这个词,是在一堂计算机课上。计算机的科任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全省最好的学校。第一堂课,他就把自己的毕业院校名方方正正写在黑板上。“同学们,一定要有理想,要做个有理想的人……”他高举双手张大嘴巴,又是一个厚厚的嘴唇。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麻辣烫女人,“哎,别像我这样只当个计算机老师,技能科目一点地位都没有。应该当程序员的,没办法咯,随他去吧……”
我很怀疑,班上除我以外的同学都没在听讲。若不是因为那只厚唇,我也不会多听那么几句话。下一秒,我决定把头藏在电脑后面,做一个像沙县小吃店老板那样的人。机房的电脑总是这样,连不上外网,也没有端游。百无聊赖之际,我只好打开了从小学到中学在机房里玩了无数次的金山打字游戏。
打字速度和学习成绩往往不成正比,我深信这个道理。生死时速中,警察永远追不上我玩的小偷。关卡不断升级,警察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也不断加快步伐,小偷的躲藏点,也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玩着玩着,我的脑海中莫名涌现出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警察抓捕逃犯,逃犯伪装成了高中生,活动在学校附近的社区。他经常光顾三家小吃店——麻辣烫店、沙县小吃店和面线糊店。每天中午他都去三家中的一家,警察也去,但两人的时间点总能错开。万般无奈下,警察只得对店家们进行直接询问。有哪些常客?麻辣烫店女人说,有个高三的学生,不喜欢吃辣,每天大概十二点来。沙县小吃店老板说,店里没有来过学生,倒是常来一个教导主任——他说自己来过很多次,喜欢扁食和拌面。面线糊店青年说,很多学生一下课就到他店里,有个很常来的,说将来想开面线糊店。警察被绕晕了,他不知道这个逃犯本身就是个高中生,等会儿一下课就会离开机房,前往面线糊店。
“那你以后想干什么呢?”面线糊店的老板问我,我一边拎着面线糊,一边说:“也想开面线糊店。”
我笑了,他也笑了。我看着他笑,莫名地想把麻辣烫女人和沙县小吃店老板的面孔都替换成面线糊青年。明明去面线糊店的次数最少,我却觉得,这是我最常光顾的一家。我甚至希望计算机科任老师能来逛逛西街,进一趟面线糊店。
不过,去得最少并不是我的本意。就在选择面线糊店后不久,我和教导主任就在那碰了面——我们前后脚进了店,只差不到一分钟。和计算机课的结局一样,有理想的老师锁定了电脑,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警察逼近一动不动的小偷。
“你是不是经常来这边?”教导主任问我,我尴尬地笑了笑。“也给我来一份吧。”他对面线糊青年说。
“嗯。”青年和沙县小吃店老板开始了一样的答话。
那一瞬间,我真希望他能去沙县小吃店,跟没表情的老板碰个面。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怎么就来了这边?没有选择麻辣烫店,也没有选择沙县小吃店,还就在这个点跟我撞了头。真倒霉。可出乎我意料的是,教导主任没有骂我凶我,左撇子,蓝书包,回力鞋……他也一个词没提。他甚至邀请我坐到桌旁,跟他共进午餐。
“学校有规定,你不知道吗?”
我低下头,不说话,看见自己胸口的校徽,后脖颈烫烫的。他在看我,和麻辣烫女人一样在看着我。胡闹!以后出去必须跟我报备!我会跟你爸妈说的……各种各样的台词、凶神恶煞的表情在脑海中飞驰而过。几秒钟后,我却听见他说:“这次就先不追究你了。但下次,不要再让我看见。”
什么?
什么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下次注意点。”
我真的没听错。接下来,他缓缓说出学校出台规定的原因。除了食物安全外,学校并不希望有学生中午或傍晚在校外喝酒赌博聚众玩闹,没规定前,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严厉惩罚也往往只是针对这些人。“再好的学生,一出学校就容易分心。”或许最后这句才是重点。我也跟他说出光顾这些店家的缘由,回家没有人给我做饭,食堂又得排很久的队,思来想去,我才选择了它们。
“理解。”只扔下这两个字,往后的记忆便一片空白。
可那时的心情我却记忆犹新。明明说的是实话,我却有些心虚。明明没有受到惩罚,可我却莫名地有种失落感。教导主任告诉我,除了他,可能还有其他老师会巡视。如果还要光顾这些店家,打包吃饭可以换下校服,不然就是铁证当前,巧舌难辩。“影响很不好。”他最后总结。我抬起头微笑,想表示感谢,可却看见一张没有表情的面孔,以为自己走进了沙县小吃店。
“去吧。”存档清空,警察就这样放走了逃犯。
从那天起,警察抓捕逃犯的故事就结束了。我忽然想起来,那天计算机课上的游戏并没有结束,而是强制退出界面——一种没有结束的结束。麻辣烫店、沙县小吃店、面线糊店再也没有了非此即彼的理由,我不会再抛弃,也再不会被拥有。时间一久,我甚至会怀疑那段记忆的真实性。麻辣烫女人很少再讲她的故事了,偶尔别人问起,她也只是说一句,“也就那样吧。”麻辣烫工时似乎也从二八开转为四六开——如果我有手机,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掐着秒表看。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她,最近过得如何?儿子还沉迷游戏吗?父亲还打牌喝酒吗?“嗯。”第一个问题她这么回答。“嗯。”第二个问题她仍然这么回答。我成了麻辣烫女人,她成了沙县小吃店老板。
更蹊跷的是,好像从那天起,沙县小吃店就消失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倒闭了,可再一次经过那儿的时候,沙县小吃店的招牌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洗剪吹的店牌。“同学,你头发长了,得赶紧剪剪呐。”她喊着,“快进来啊。”我半推半就地应了声“嗯”。她成了麻辣烫女人,我成了沙县小吃店老板。
一直到毕业,我都再没绕远路经过洗剪吹——记忆中沙县小吃店出现的位置。而面线糊青年居然也换了面孔——他满脸皱纹,鬓角银白,每一个转身都有岁月的痕迹。点菜时,我们也只是很机械地来回。“要加什么?”“醋肉,卤蛋,火腿……”他的动作仍旧娴熟,有条不紊,可很少再讲其他的话。我又一次忍不住发问:“这家店,一直是你一个人在开吗?”
“当然。”他愣了愣,这么回答我。
“可是之前……”我想问先前面线糊青年的事,可又觉得太过荒唐,便没继续发问。
“现在也只有老头子会开这种店,年轻人读了书,还做这个干吗。”他拎起塑料袋帮我打包,没有再讲其他的话。
我真的按教导主任的吩咐,每次点菜都换下校服。可把校服换掉,却感觉我更像在学校里,先前的愉悦感再也回不来了。再后来,学习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店家我也不去了,中午和傍晚,我都买来学校便利店的面包,教室内就能解决一日三餐。西街的记忆渐行渐远,我开始和其他人一样忘却它的名字。它是叫东街,还是叫西街?或许叫西街,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东南西北,都与我无关了。百日誓师那天,大家高喊着目标分数、理想院校。“清晨六点的天很黑,但六百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所有人都在咆哮,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登时狰狞了起来。可爸妈问起将来想干什么时,我却说,开面线糊店。
很显然,他们不会遵从我的意愿。“年轻人读了书做这个干吗。”他们也这么说。爸爸说做程序员赚钱,妈妈说当老师稳定,思来想去,最后我的高考志愿表便填了师范院校的计算机专业。
等我上大学后,外卖行业已开始蓬勃发展。在北方的冬天里,我划着手机,找麻辣烫、沙县小吃店,但找不到南方的面线糊店。一边敲作业,一边吃麻辣烫、沙县小吃,我却常常想起面线糊青年说的话,“做面线糊最快乐了。”“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一直开面线糊店。”“你在说什么?”我身边的同学问。“嗯,没什么。”我又把头藏了起来,拉平嘴角,开始做沙县小吃店老板。
可事实上,我并没有成为面线糊青年,更没有成为沙县小吃店老板或是麻辣烫女人。程序员的收入很高,但工作时间长,职业寿命短,选择这条路的同学终究是少数。在父母和老师的建议下,我和很多人都去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有的人留在了北方,而我,选择回家乡工作,一毕业就回到母校,成为一名计算机老师。
“你以前也是一中的学生吧?”开学时学校分配工作,领导问我话。
“嗯。”我回答。
“那你对以前西街的规定应该熟悉咯。”
“嗯。”我又回答。
即便如此,他仍旧把戒严政策说了一回。说得很详细,就好比六年前,我在那家不知是否存在过的沙县小吃店里跟老板解释的那样,住宿生要严惩,走读生要严查……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带着听过很多很多遍但又像是头一回听的感觉。
“清楚了吗?”
“嗯。”
我又一次来到了西街。已经是2018 年,东边也兴起了无数的食品店。花花绿绿的商铺多米诺骨牌般一家接一家立着,我一间间经过,终于来到东边。时至今日,面线糊店也消失了,麻辣烫店还幸存着——但不知道是不是先前那家。麻辣烫店店主是一个年轻的男生,和我年纪相仿。我很想上前问他,这里一直是麻辣烫店吗?附近之前卖面线糊吗?麻辣烫女人呢?但我没这么做,不问,就不会得到否定的答案。
因此,我带着麻辣烫来到了机房,给高二年级学生上计算机第一课。我没有写毕业院校,也没讲理想,只是打开电脑,说面线糊真好吃,底下的同学都笑出了声。
“老师,你吃的是麻辣烫啊。”
“是吗?”我看了看,“嗯。”好像是这样。
但也没什么差别。开学第一课,思来想去,我决定分享高中时学计算机的故事,计算机课上警察抓小偷的故事。一切的一切,都得从西街讲起:“2012 年,我还在上中学,学校那时刚刚完成翻新。崭新的教学楼宏伟的校门,校门外流着一条自西向东的街——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