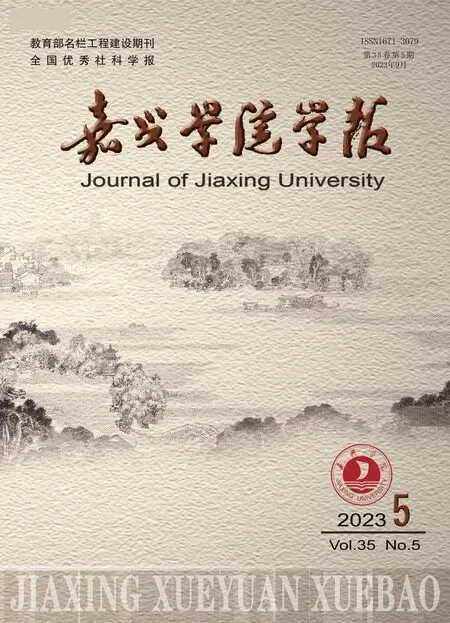民俗艺术视角下的嘉兴婚育礼俗图像研究
2023-09-28郭友南
郭友南
(嘉兴学院 设计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婚育图像长期应用于生命礼俗活动中,其生成逻辑源自人们对生命的执着与眷恋。冠昏丧祭是古代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中都要举行的仪式,溯源实为民间风俗,后来贵族制礼,于是在节文上等而上之。钱穆先生解释礼俗关系言:“俗乃是由礼脱变而来,礼亦由俗规定而成,二者还是一个源流,只其表现有不同而已。”[1]其中礼是为着适应政治统治需要而诞生,具有极强的宗法和象征指向。而俗则是基于生活中得到传习的、无意识的继承和发展。在“礼”与“俗”结合互动的实践中,其谱系颇为丰富,汇聚历史、天文、民俗、神话中的诸多物象,兼具普遍性、合理性、应用性、仪式性和审美性。嘉兴自古就是文化聚集勃兴之地,在社会经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婚育图像仍是人生礼俗中不可缺少的艺术样式。婚育图像作为一种人生礼俗极具生命力的民间传统美术类型,其文化的选择与艺术价值是根植于以生命、情爱、繁衍等为主体的民俗文化沃壤之中。就其价值而言,婚育图像不仅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民俗、社会和文化等综合价值也非常突出。以嘉兴婚育图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其历史发展脉络为基础,从婚育图像的外在艺术表征入手对其进行由表及里的民俗内涵剖析,对于认识嘉兴传统礼俗文化、探析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理解人们婚育观念具有重要价值。
一、生命思维与信崇生成
婚姻与生育是个体生命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个人生活、族群和社会发展都无法回避。
先民凭借观察、经验和联想对自然界中的物事、现象及其因果关系进行整理和分析,做出评判以及感悟,唤醒自身深处的潜意识,激发自我意义和生命意识,生命思维中渗透着神奇的逻辑力量。
(一)外物感应
激发先民两性致爱习俗的物类、现象较为广泛和复杂。原始社会的先民有着比现代人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在他们的世界里,有着现代人所忽略的细节且有不同的解读,特别是物我相类之处尤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联想,有果必有因的思维模式得到确立。两性相吸、两情相悦是动物本能使然,在族群社会中更关注两性结合后的生育繁衍。到了宗法社会,女人存在的意义即种族传递繁衍,一个女人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将会遭到丈夫的诅咒和祖先的谴责。宗法社会规定或要求就是法律甚至高于法律。在这种环境包裹下的女性,生育能力成为种族意志也是个人意志,但凡和生育有关联的种种都成为爱恋、结合、生命的催化剂。
1.果实
《诗·召南·摽有梅》中鲜活地描绘出未婚青年在三月三集体聚集以寻觅异性伴侣的生活情景,为后人揭示了其中所寓之意。闻一多曾说:“女以果实为求偶之媒介,掷人果实,即寓贻人嗣胤之意,故女欲事人者,即以果实掷之其人,以表诚也。”[2]如果说投果相赠是女性爱慕之情的表露,那么,男性视角则是以多籽的“椒”为欣赏对象。闻一多:“椒聊喻多子,欣妇人之宜子也。”[3]“椒”即花椒,结实聚生成房状;形态类似后世传入中国的葡萄。诗经作品《椒聊》形容其盛多子外形肥硕,芬香浓烈,四处弥漫。当时女子以丰硕为美,暗示自己不仅貌美,且能生育众多子嗣。
2.玉石
考古学界用新旧石器来划定历史阶段,经历300万年的石器是人类最早的人工物。距今7000年前的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中,朴素、精致、小巧的各式石器已经成为墓主人最为重要的随葬品,可见玉石在族群中的地位已经摆脱了实用物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想象中的“人化”和“对象化”,显露出宗教、艺术、哲学等的萌芽。《山海经》中曰“状如鹑卵”的帝台之石可令人“服之不蛊”。[4]与卵形相似的石头让先民将其与生殖力联系起来,卵生与石生合一生殖观念的形成为先秦时期的卵生神话和石崇拜奠定了基础。我国北方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生育食蛋和投石乞子的风俗,民间男女老少佩玉的风尚依旧。
3.桑
蚕由卵而虫,虫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又生虫,其周而复始的生命轮回着实令先民惊奇。桑树生命力旺盛,枝叶发达,可翳人于下,桑葚饱腹,桑叶喂蚕,特别是桑葚累累,被古人视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桑、桑树、桑林给先民带来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如图1所示,以桑象征女阴,实行崇拜。如《离骚》《九歌》《山海经》中将扶桑称为联通冥界、尘世和天堂的媒介,在后世诗文、祭祀、器物、纹样等载体中占比最多。

图1 桑林图 汉代像砖拓片
(二)物我相类
上古族群有识鸟兽之语的记载,鸟兽语言至今仍然神秘。皋陶鸟喙、闻牛鸣而知、伯益知禽兽等虽有神话传说之嫌,但人伦事象的联想却露端倪。匹鸟栖则交颈、昆虫飞鸣生物、两鱼以口相交、雄雌发情交尾等情景不免刺激了朴素先民的性情。“牝牡相诱谓之风”,[5]风在先民原始思维中蕴含生物创世观念,鸟虫因风化育在先民心目中是最具灵性的生殖现象。《周南·螽斯》中的文字完全是夫妻欢愉、子嗣昌盛的生动场景。如此就能洞察到上古先民意识中虫鸟禽兽与风及其万物兴育。明代兴建紫禁城内,螽斯门与百子门相对,民间新房常置办有蟋蟀纹样的器物,即是对这一意象的信崇。
二、婚育图像的意象构成系统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合卺的出现,与之对应的婚育图像也走过了一段漫长且辉煌的历程。婚育图像的各个意象元素又非独立存在,彼此间是相互映射、关联兼融以及协同作用的系统。作为超系统——婚育风俗的文化氛围,子系统皆有其在民俗寓意、象征或指代中的定位。因此,婚育图像是经历系统表达与象征性思维相结合的文化产物。
(一)婚育图像中的人物谱系
依据历史脉络,婚育图像系统中的人物谱系有三种:一是来源于神话传说中开启人类创始、具有原初意义的生命之神,如图2女娲、伏羲等,被视为婚育图像的“母题”之所在;二是带有虚幻色彩的仙话人物,单独出现能够表达致孕祈子寓意的人物,如送子观音(图3)、送子娘娘、张仙、牛郎织女、许仙等,都是基于民间在生命信仰基础上的加工创造;三是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的仙骨人物,如和合二仙(图4)、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独占鳌头、指日高升等,他们虽为传说中的人物,但有亦真亦幻的色彩,贴近民众心理,情感朴素,构成了婚育图像中有信仰色彩、栩栩如生、仙凡混杂的人物谱系图。

图2 伏羲女娲(汉画像)

图3 送子观音(宋 瓷质)

图4 和合二仙(1)嘉兴龙凤花烛中的制作模具。(作者拍摄)
(二)婚育图像中的动物意象
“动物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所依靠的,对于人来说就是神。”[5]婚育图像中,很多动物意象正是迎合了人们祝愿两性致爱、致孕祈生的心理信崇交汇而成的。在婚育图像系统中,动物意象符号可分为兽类、鸟类、水族类和其他类。
1.兽类
麒麟预示孔子降生,图5为嘉兴龙凤花烛制作模具——麒麟送子。狮子在民间有避邪纳吉、预卜洪灾、彰显权贵寓意,体现了人们对太平祥和的美好期盼。鹿性柔和顺从、喜群居,鹿每胎一仔且孕十月,与人的孕期最为接近,受到先民关注而产生联想。《仪礼·士冠礼》中记载,成年加冠仪式中有给年轻人加鹿皮冠,意在表明其性成熟已可以婚育。古时,青年男女在野外邂逅,如将猎物——鹿作为礼物相送,是对婚育的象征与祈求,古人婚礼纳采所用的鹿皮,亦是象征性成熟与婚育意愿。松鼠与葡萄组合,鼠在民间尊为“子神”“财神”,葡萄多籽,有多子多福之意。
2.鸟虫类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男女主人公殉情后化为蝴蝶,成为追求自由与爱情的象征;雅俗共赏,寓意明确;鸽子一旦配对就感情专一,形影不离,寓意纯洁、专一的美满婚姻;民间女性通常绣以鸳鸯图案作为定情信物,寓意夫妻和谐白头偕老。螃蟹、鸭与科举仕途有关:“鸭”与“甲”谐音;蟹有甲,一蟹“一甲”即状元;仙鹤“一品鸟”之称寓意仕途顺畅,官位显赫。蝉与祥云图像为“一名如意”,是对子孙学业有成的预祝。蝈蝈(官)与菊花(居)组合,为“官居一品”。蝙蝠(福)和古钱(前)组合,寓福在眼前。鸡在民间有生命力和生殖力的象征,鸡鸣日出,万物复苏,生命开始;金鸡为阳性,铜钱则代表女性,二者结合寓意男欢女爱,多子多孙。锦鸡意为锦上添花,小鸡五只意为五子登科。古时婚仪“六礼”,有五次用雁为礼,因其终身一侣,天涯共飞;思乡重情,冬去春来等美誉为贽见之礼。蟾蜍在古人眼里是月亮的象征,其表面上的疙瘩像一叠叠钱币,传说是会吐金钱的神兽,三足蟾蜍也因“刘海戏金蟾”成为吉祥和财富的象征。
(二)婚育图像中的植物意象
在婚育图像的发展和演变中,文人创作得到了充分体现。早期婚育图像中葫芦、莲藕、南瓜等具有信仰性质的主流题材,随着文人画的兴起,带有清新脱俗元素的梅、兰、竹、菊融入,使得婚育图像的格调和品位得以提升。
在植物题材中,果蔬类图案多集中在佛手、桃、石榴、葫芦等;在花草类图案中有莲花、万年青、月季、海棠、玉兰、杏花、萱草等。两类图案并非孤立显现,而是根据题材,迎合格调,主次登场,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1.果蔬类
佛手的“佛”谐音“福”,与桃、石榴同时出镜视为“三多”,寓意多福、多寿、多子,如图6所示。百籽葫芦、金瓜生籽、榴结百籽比喻落地生根的“籽”,代“子”,表示生命繁衍不息。葫芦藤蔓交错,蔓长而多子。婚育图像中常把缠枝和藤蔓作为辅助出现,二者都洋溢着勃勃生机的生命力,为子孙昌盛之意。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石榴裙”“拜倒在石榴裙下”可见国人赋予石榴红火、情爱、多子、团聚等美好寓意。《九世同居图》由9只鹌鹑和几组盛开的菊花组合而成,取菊谐音“居”,9只鹌鹑来喻意“九世”,鹌鹑与“安”谐音,寓意安详的人伦盛况。莲子、莲藕等纹样常进行组合,称为“因荷(何)而得藕(偶);有杏(幸)不须梅(媒)”,如图7所示。还有荔枝、桂圆、核桃(同元,科举全中)、白菜(清白)、柿子等。
2.花草类
牡丹被誉为“花中贵裔”。牡丹花与雄鸡鸣啼同框(“鸣”与“命”谐音,“长鸣”即“长命”)的寓意是“长命富贵”;牡丹与白头翁的组合构成“富贵白头”的祝愿。月季,又名“长春花”“金盏花”,花开四季,跟海棠花、玉兰花组合寓意万代长春。在后两者中取“玉”“棠”,谐音“玉堂”,宋以后玉堂即翰林院,泛指书香门第,寓意后人科举高中。玉兰树映射“玉树临风”,是古人对洒脱才华出众男子的赞誉。
旧时女性往往以物传情,隐晦表达爱慕。“竹子”的谐音“祝子”,表达虚心、有节、宁折不弯,岁寒时节仍有青苍之色的自然品性,以迎合士人阶层的审美倾向。萱草是带有鲜明性别特征的植物,《录异记》曰:“妇人带宜男草,生儿。”[7]还有忘忧之意,其性具有安神的药物疗效。水仙的民俗应用名中有“仙”字,常见的水仙、万年青、奇石、牡丹组合图像表示神仙相助之意。此外,杏花(科举顺利)、芦苇(科举及第)、水草、芍药、茶花、万年青(万年好运)也都代表不同的祝福寓意。
三、嘉兴婚育礼俗图像
自古以来,嘉兴即南北文化交汇中农业文明的发达地区,明清时期,嘉兴手工纺织进入了全盛时期,盛泽、濮院生产的纺绸畅销海内外。江南(六府一州之地)的三百余个城镇,代表了我国明清城镇发展的最高水平。魏塘镇、濮院镇、王江泾镇、西塘镇、梅里镇和新塍镇皆属嘉兴,其经济繁荣、文风昌盛,以嘉禾平原城镇为歌咏对象的组诗——《鸳鸯湖棹歌》可以确证。长期富饶稳定的社会环境给人带来的闲暇以及外来望族迁入的本土化融合,为嘉兴的地域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契机,具有嘉兴地域文化特色婚育礼俗图像的生成与完善自然不会缺失。
(一)嘉兴婚育礼俗图像特质
嘉兴婚育图像基于地域环境与人文积淀,表现为阴柔宽厚、儒雅精致的总基调,呈现“精、细、雅、洁”的艺术特色,是自然人文长期绵延与演变的结果。“精”即精致,与黄河流域表现出来的大气、粗犷、拙朴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嘉兴作为江南腹地具备水乡、蚕乡、精耕、温润、烟雨等自然特色和阴柔气质,体现在器物上则是构图精致、巧妙,工艺制作细腻,用料考究,进而形成了精致唯美的艺术呈现。“细”即细巧,体现在嘉兴婚育图像中玲珑、娇小、温润、小巧、亲切、巧思的女性形象中,与马家浜文化遗存器物风格具有“异质同构”的审美倾向。“雅”即儒雅,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腹地,嘉兴婚育图像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和体验功能的实现,需要文化修养的浸润与滋养。嘉兴婚育图像在崇文重教、孝友传家、清德勤俭的族群文化环境下呈现出儒雅气质。“洁”为简洁,与传统皇家御用图像奢华、繁琐、矫饰的风格迥异,嘉兴婚育图像具有较强的民间性特征,表现为理性、通俗、参与、日常、仪式,体现出务实精进、干净利落、质朴无华的地域文化特质。嘉兴婚育图像的民间性,为其社会性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作为一种“嵌入式”艺术形式,在建筑装饰、瓷器图案、家具设计、服饰织物、节庆商品等不同载体中得以显现,是性别文化的组成部分。嘉兴婚育图像能够致力于变革与调节男人跟女人的意识和冲动,通过这些男人和女人改变世界。如图8,2020年在嘉兴地区婚礼中实存的龙凤花烛(曹海荣拍摄),其中几乎囊括了婚育图像相关要素且使用嘉兴语言进行表述。
(二)嘉兴婚育礼俗图像题材
基于中国婚育图像母题与主题的绵延与变异视角,可以初步判断,婚育礼俗图像缺少民族特点正是其最大的特点,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共性和不易被环境改变的韧性,蕴含了人类文化普世和久远价值。但是作为地域性的表述,折射出地域性对性别文化的解读,对中国“生生”哲学的独特理解和地域性话语。
嘉兴婚育图像包含瑞兽、鸟禽、虫草、花卉、水族、树木、食物、人物、风景与文字、纹样、器物等题材。图像形式包括立体、平面、浮雕等。图像组织形式以连续纹样、适形纹样和单独纹样为主。嘉兴婚育礼俗图像以系统形式出现,子系统如建筑装饰、生活起居、日用木器、女工用具、文房物件等,几乎囊括了婚后新人生活所用器物的方方面面;工艺手法涉及木工、金工、漆工、雕工、窑工、女工等多个工种,蔚为壮观。仅生活起居中的服饰品就有滚、镶、贴、连缀、印染、刺绣、织锦等工艺手法。
表1是对嘉兴婚育图像题材、组织形式和工艺手法的调研统计。

表1 嘉兴婚育礼俗图像的题材和内容
(三)嘉兴婚育礼俗图像意涵
1.阴柔宽厚
嘉兴传统氏族中女性在家族中发挥重要作用,女子能积极学习文化艺术,转化为优良母教,助推家庭教育。潘光旦在其代表作《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着重论述望族人才辈出与迁移、婚姻、教育有密切关系。在嘉兴婚育图像中凸显女性在自我意识表达中对情爱隐喻诉说以及自我价值与能力的展示非知性女性不可为,即表现出能够找到自己中意人选,且能展示自我独特的才华高度与审美格调。作为陪嫁物品配饰中表现尤为厚重,如发禄袋、荷包、扇袋、钱褡、名片袋等,是女性传情的重要载体。用“因何得偶”“玉树临风”“芳思春华”“一甲一名”等表达少女爱慕之情以及对心上人仕途期盼,借双蝶、白头翁、鸳鸯、竹、梅、兰花等图像表达对婚姻美好的向往。嘉兴女性以针代笔巧妙规划、布局,无论是在图案象征、制作工艺方面,还是体现诗情画意方面,都展示出女性技艺和文采。
2.护生纳吉
生命延续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家族兴旺的根基。民间将生育比喻成香火绵延,视为人伦头等大事。嘉兴婚育图像可以概括为祈子、护生和纳吉三类,虽与其他地域有一致的主题考量,却有自己的文化解读与图像话语。祈子即以佛手、石榴、金瓜、葫芦等多籽主题图像表现对多子多孙的期盼;护生即对子孙呵护,以仙鹤松树即鹤寿松龄表达对长寿高龄的祝愿,以菊花、竹子与梅花表达后世人格有节、科举高中,用玉兰花和海棠花寓意玉堂;纳吉以“宜子孙大吉祥”、“富贵亦寿考”、“一路福星”、盘长纹、牡丹等题材表达对富贵吉祥的祝愿。借助月季、万年青、竹子表现长青(长寿)、节节高的寓意,也表现淡泊、清高、正直的人格追求。
3.崇文重教
嘉兴民间素有崇文传统和家学衍递的社会氛围,新生命的降临到家族精神和文脉延续是一个生命升华的历练过程,或许是经历明清五个半世纪的文化浸泡、家族荫庇和婚姻考量,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已经成为嘉兴望族文化中的普遍现象。正是这种风气,才孕育出茅盾、王国维、丰子恺、朱生豪等文化大家。婚姻图像由兰花和桂花纹样组合称为兰桂齐芳,比喻后人为官清廉,为人端正,不忘劝谏;莲藕、荷花寓意一品清廉;蝉、水仙花等象征高洁品质。在器物纹样中有笔、笙、元宝、如意等。胪唱先声、金殿唱题、常占春色、蕊榜题名、一品当朝等作为文字纹样,鼓励或倡导用崇文重教来实现人生理想,彰显蒙以养正的人文思想观念。
四、余言
嘉兴婚育礼俗图像是一个动态演变的系统,且具有自身独特的性别文化、表述途径与传播场域。未来既要重视基础研究中婚育图像生成以及意象构成系统、嘉兴地域特点的婚育礼俗图像,还要考量现代自媒体流量以及当代设计思潮对传统婚育礼俗图像所带来的机遇。如何将传统嘉兴婚育礼俗图像与当代传媒相融合,还原其应有的生活地位,特别是在生命礼俗节点发挥其精神层面作用,作为当下婚育文化可选择和参照的范式,或许是设计人的时代课题,也是该课题研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