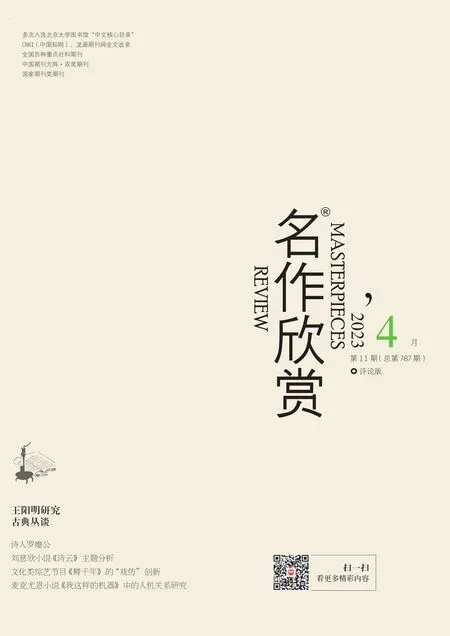鲁迅小说中的“坏孩子”形象探究
2023-09-28马千惠香港城市大学香港999077
⊙马千惠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999077]
一、绪论
儿童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笔墨不多,但正是这些描写孩子的“只言片语”,使得作品有了更复杂丰富的意义。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这些孩子形象独特鲜明,甚至一反儿童的“常态”。可见,是其形象本身具有重大内涵与象征性,鲁迅才会将其反复而多样地呈现在小说中。
具体而言,在社会病态、人性丑恶的背景之下,“孩子”形象不再是大众认知的天真烂漫,而是呈现出异化的特征,鲁迅洞察到了病态社会下这些孩子的异化状态。一直以来,学界大致将小说中的“孩子”形象分为三类:一是病孩子,如《明天》中因庸医而死去的宝儿,《药》里得了肺痨而听信迷信吃人血馒头的华小栓;二是丑恶残忍的“熊孩子”:《孤独者》中粗鄙野蛮的大良二良、《在酒楼上》中“简直像个鬼”的阿顺;三是依然质朴纯良的好孩子:如《故乡》中的少年闰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单纯的“我”。其中,学界对于“好孩子”形象有较为普遍的阐述:其代表了鲁迅所要回忆的“乌托邦”和美好精神的寄托,但目前对于坏儿童形象作具体分析的情况较少见。因此,本文以鲁迅小说中“坏孩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坏孩子”类型,并阐述其各自成人化行为的原因。目前,对于坏儿童形象的多数研究都还停留于解读鲁迅对旧社会封建伦理的批判以及对此提出的现代伦理观念等层面,忽略了鲁迅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孩子为什么“坏”的原因。因此,本文结合鲁迅其他文章中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来看鲁迅小说中的“坏孩子”形象塑造以及“救救孩子”“解放孩子”的心路历程,以此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时期鲁迅的思考和认识。
二、鲁迅笔下的“坏孩子”形象
儿童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看似存在感不强,但其实寥寥几笔之间时常充斥着复杂深刻的内涵。无论是孩子的内在本性,还是其外在形象,鲁迅都在作品中有所呈现。唯有将二者结合分析,才能更好地领悟鲁迅小说中儿童形象的意义。
(一)由《孤独者》引发的孩子本性论
在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和“我”针对孩子的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魏连殳重视子的程度超越了孩子的祖母:“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①而在“我”看来,孩子是吵闹的象征。而面对孩子的态度,魏连殳和作为孩子家长的祖母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将其视为“中国唯一之希望”,后者则忽视孩子的身心,甚至将前者的担心视作笑柄。在魏连殳看来,中国的唯一希望,是孩子本性为善与天真。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儿童的身心从出生就被社会环境所荼毒。最终,魏连殳被大良二良抛弃、无视的惨淡结局为这次论辩画上无形的句号。
以孔乙己、魏连殳等这类受社会排挤的知识分子为例,可以看出孩子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受成年人影响而形成的:《孔乙己》里,所有人都将孔乙己视为笑话消遣,因此“我”也可以跟着笑;《孤独者》中大良二良对魏连殳的态度随着房东、祖母的变化而变化。可见,是成年人(即社会环境)的态度影响了孩子。而对于孩子本性是好是坏的答案,实际上在“我”与魏连殳的讨论中有所体现,最终“我”劝慰魏连殳道:孩子是环境教坏的。可见,孩子的本性并非鲁迅想要表达的重点,关注的重点应该是“酒店的人们”“房东祖母”等成年人形象。为什么孩子被环境教坏,以及如何“救救孩子”才是关键。
鲁迅认为,旧社会的家长只会生,不会教,因而孙子、儿子、父亲,一代代角色转换,也都只是在社会中乱转。只有“人”之父,不仅生,还要教育,才能将孩子培养成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孤独者》里无论是“环境教坏论”还是“种子坏根苗论”,其实都不是准确的答案。从鲁迅的杂文中可以看出,正确教育孩子才是必要的问题。然而,若社会上出现了真正重视孩子的人,结局会是怎样?鲁迅在《孤独者》中给出了答案:孩子祖母将魏连殳为三良的红斑痧急得脸发黑气传作笑柄,形容魏连殳是“他先前怕孩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可见,家长不关心孩子的身体,甚至认为重视孩子是失去“长者尊严”的行为。这些都是鲁迅对当时社会中关于孩子生养、教育的错误观念的洞察。
在明确孩子本性论的意义后,对于鲁迅笔下孩子的“坏”就能从更加直接的角度去理解。孩子具体是如何坏的、变坏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有可解救的办法,这些问题其实在鲁迅作品中都有清晰的呈现。
(二)“坏孩子”形象分析
1.残忍的行刑者
首先,鲁迅笔下的坏孩子在外貌上就丑恶可怕。比如《在酒楼上》“阿昭长得全不像她姐姐,简直像一个鬼”②,《孤独者》里“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的可以”③。鲁迅用“简直像一个鬼”“丑得可以”来形容孩子,不仅与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的普遍描写相悖,甚至是离奇的。
坏孩子不仅外貌丑恶,言行举止也凶残可怖:《长明灯》里孩子们在跑闹时:“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吧!’”④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颓败线的颤动》里:“最小的一个正玩着一片干芦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仿佛一柄钢刀,大声说道:‘杀!’”⑤鲁迅重复了三次这样的场景,《孤独者》里:“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很不能走……”足以见出,鲁迅赋予这个动作极其深刻的象征意义。看似依然是孩子玩闹嬉笑的动作,但读来却没有天真美好的感觉。他们或是拿着芦叶指着人说:杀!或者比作枪:吧!动作语气干脆残忍,俨然是成人化的开枪行刑之态,可见其受社会影响之深。巧合的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所写的信中说自己吐血失眠。据《本草纲目》记载,芦叶恰好有治疗吐血的作用。然而,这一治疗魏连殳的药早在先前就被用作杀掉他的“武器”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孩子的“坏”在鲁迅看来是悲哀而近乎绝望的存在。社会环境是病态的,人们是冷酷自私的。因此,刻画孩子模仿成人姿态无异于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现象:孩童的顽皮吵闹与成人世界的杀戮结合了,作品中“樱桃似得小嘴”“笑吟吟”等形容与开枪的动作交织,反而令读者感到别扭不适,原本应该天真无邪的儿童形象,在潜移默化中与病态的成长环境相融了。
对于这样的野孩子,鲁迅在《随感录·二十五》中专门叙述了其形成的原因:“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⑥可见成为凶恶的野孩子与物质水平无关,最根本的原因是长辈的完全性地放养和对管教的疏略。“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⑦鲁迅的这个观点,正好与他的小说《孤独者》中祖母让自己的孙子们“下跪、装狗叫”等行为相呼应。没有把“孩子”当人看,就是没有教导他们立人的思想,没有同他们有“人与人”的交流。“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再一次强调家庭、社会的影响对孩子是非常大的。一方面,鲁迅借由病态社会下孩子的异化抨击旧社会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旧社会缺乏正确的生养观,错误的价值观使得孩子成了“恶的种子”。
2.麻木、冷漠的看客
冷漠麻木的旁观者形象在鲁迅小说里几乎是所有坏孩子的共同特征。在人性冷漠的“看”这一层面上,孩子的表现完全与成年人一致:《孔乙己》中“我”面对孔乙己的悲惨境遇始终抱以冷漠嘲笑的态度。“我”的年龄至多不过十几岁,却能面对他人痛苦之境时产生如此冷漠的内心活动,其过早世俗的迹象可见一斑。同样的“儿童看客”在《示众》中有着更加直接的展现。警察押送犯人,人们纷纷涌上前来,在这个混乱的过程中,鲁迅写到了三个小孩看客:胖孩子、小学生、老妈子怀里抱着的小孩。胖孩子就像是胖大汉的“缩影”,他在被胖大汉扇了一记耳光后不懂反抗,如同小鼠一样仓皇;小学生在人丛中四处飞奔穿梭,在围观的世界里无目的地撺动;老妈子怀里的小孩最年幼,然而早早地就在老妈子的引导下当起了看罪犯的看客:“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⑧有学者认为从象征意义来看,胖孩子、小学生、小孩其实代表了未来的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和新生命,小说分别体现了他们殊途同归的未来:成为冷漠的看客。然而,无论何种身份,都深陷于冷漠无情的“看与被看”中,渗透着的其实是鲁迅洞察社会病态下儿童深受毒害的现象。他在《上海的儿童》里表明,不管是娇生惯养还是漠视、打骂,都是家长以权威者的身份把儿童客体化、他者化。值得注意的是,孩子不仅是“看客”,也是“被看”的存在。在被漠视或者打骂下成长的孩子,他们怯懦麻木的性格在面对逆境时只会更加顺从,由此被禁锢于终生“被看”的命运。
看与被看,其实都是家庭、社会无形之中对孩子的引导,身处于病态的成长环境,幼者的“恶”更加说了“救救孩子”的艰难。同时,也更说明“救救孩子”本质上不是要从孩子入手,而是整个病态社会。此外,救救孩子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孩子本身为善。这一点其实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有所体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⑨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被看的孩子或许还可以被拯救,已经学会了看的孩子,或许已经彻底无药可救了。
3.不受尊重、被忽视的生命
打骂、约束孩子的情节在鲁迅小说中随处可见,无论是压迫目的还是无心之失,这都是一件平常之事。在《孔乙己》里,“我”作为童工,在店内受到的约束其实非常大,平日里“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叫人活泼不得——”⑩《示众》里胖大汉误扇了胖孩子的脸颊,然而他却恶狠狠地反问:“什么?”更奇怪的是,被打的孩子按着脸颊像小鼠子一般仓皇逃走。胖大汉没有丝毫歉意,胖孩子对于被打也似乎习以为常,不懂申辩反抗。“打耳光”的情节在《弟兄》中也有类似描写;家长在梦里梦见比平常大了三四倍的手掌向儿子脸上一掌批过去。《孤独者》中,魏连殳对孩子的关爱在孩子祖母看来却是怕孩子,认为这是“低声下气”的表现。可见,摆出足够的权威才是一个“老子”该有的样子。“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装狗叫”和“磕头乞求”是有失人格和尊严的行为,然而这些行为在祖母看来却是有趣的,这一对比鲜明地指出旧社会封建思想对父权的重视以及对孩子人格培养的忽视甚至扭曲。
在《立论》里,对新生儿的祝福,大家说道:“‘这孩子将来发财的’于是得到一番感谢,‘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于是收回几句恭维;‘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⑪孩子在刚出生时就被套上了虚荣的枷锁。鲁迅的态度则是一阵敷衍:“啊呀!阿唷!哈哈!”让人们沉溺于自己想要的答案作罢。此外,人们的祝福都是围绕着金钱、权力,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鲁迅在《孤独者》里其实有所暗示,当提及亲戚想把儿子过继给自己,魏连殳认为其实亲戚们是要过继自己的一间寒石破屋。有孩子就意味着可以占有房子。换言之,人们认为生孩子的意义在于继承财产,仅此而已。
事实上,无论是野孩子还是看客孩子,社会都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这不仅说明孩子的人格被忽视,其实也是孩子之所以成为“看客”与“行刑者”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救救孩子”出自《狂人日记》的结尾:“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小说直到最后,鲁迅才将前文的“吃人的人”替换为“吃人的孩子”,可见这里的孩子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儿童。再看救救孩子后的省略号,让“救救孩子”这句话更多了无力和绝望之感。但他没有停留在无言的悲哀中,在《随感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中,鲁迅针对封建思想所导致的问题提出了几个方法:删除旧账、婚姻恋爱自由、转变父辈思想。鲁迅所批判的是整个中国传统封建生养孩子的态度:家长自视为权威者,孩子始终是被压制与忽视的对象。因此,鲁迅破除了封建家庭中“父母有恩于子女”的观点,提出了与传统“长者为本位”完全相反的现代伦理观念——“以幼者为本位”,以“爱”取代“恩”,颠覆了传统伦理观念。虽然知道了救救孩子的办法,但是旧思想的长者们自然是不肯轻易解放的,过程必然艰难困苦,无法平和。所以愿意平和的鲁迅也不得不说,现在还不能解答。
①②③④⑤⑧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第31页,第92页,第68页,第210页,第74页。
⑥⑦⑨⑩⑪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第311页,第454页,第457页,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