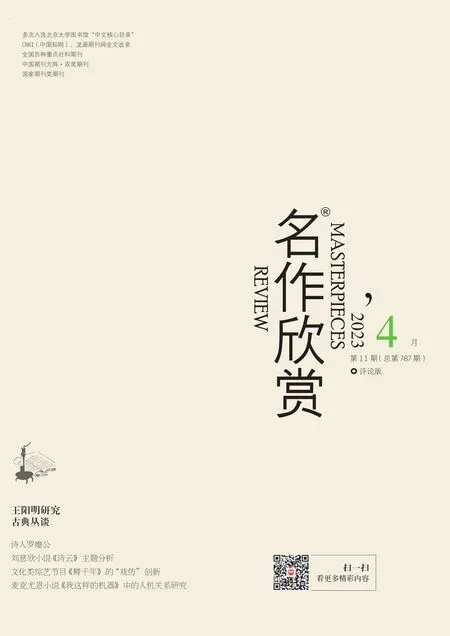清谈玉露繁,心怀天下难
——论《鹤林玉露》的社会书写
2023-09-28张天宇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010022
⊙张天宇[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 010022]
一、《鹤林玉露》中的社会现实书写
笔记的叙事抒情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虚饰伪装,均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历。①罗大经也在 《鹤林玉露》甲编自序中说道:“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②这透露出该书的写作是面对社会现实时的因时而论、有感而发,其中确有不少关于社会现实方面的描写。《鹤林玉露》中的社会现实书写,共有下层百姓的困苦、统治阶级的奢靡、社会道德的衰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五部分。
(一)下层百姓的困苦
《鹤林玉露》对社会现实方面的反映,表现最为突出的应当是下层百姓生活的困苦。当时的百姓要面对官府的重重盘剥,《鹤林玉露》论及百姓要缴纳的赋税有“头子钱”“经总钱”“丁钱”等,还有苗、盐等实物。例如乙编卷一“经总钱”条所记载的“经总钱”,经过多年发展,已经益之又益,成为地方百姓生存的一大难事:
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中,王师讨之。命陈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夫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倣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之初,尝诏罢之。军兴,议者再请施行,色目寖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③
除了官府的重税,下层百姓还要面临富户的欺压,沦为富户家中的奴仆: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呜呼,悲夫!④
最后的结果就是罗大经在丙编卷六“方寸地”条说到的“有无立锥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
(二)统治阶级的奢靡
当下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统治阶级却在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他们建造豪华的宫殿,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过着奢靡的生活。《鹤林玉露》揭示统治阶级生活奢靡角度最为巧妙的,是丙编卷六的“缕葱丝”条:
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⑤
一个士大夫在京城买了一个小妾,小妾自称是蔡京蔡太师府上包子厨中人。一天,士大夫让这个小妾做包子,小妾做不出来。既然是包子厨中人,按照常理应该会做包子。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小妾只是在包子厨中缕葱丝的。既有包子厨,便也应有水饺厨、面条厨;既有缕葱丝者,便也应有切生姜者、剥蒜头者。可想而知,如此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不知这蔡太师府上该有多少厨师、杂役。想必不仅是罗大经会“慨然兴怀”,一众读者也会被这奢靡的程度惊讶到。上流社会的腐败堕落、奢淫糜烂,就通过这三言两语暴露了出来。
(三)社会道德的衰落
在下层百姓生活困苦、统治阶级荒淫无度的同时,社会风气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应该是社会中道德品质较高的群体,然而罗大经却借杨长孺之口道出这样一番话:“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果不其然,在道德衰败的南宋中后期,连为官的士人也不能保有清廉的品性。在乙篇卷六“韩璜廉按”条,罗大经讲述了韩璜的“堕落史”。广东提刑韩璜奉命调查王鈇的贪赃不法,没想到却被王鈇引诱上钩:
王麾去伎乐,阴命诸娼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酒半,妾于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闻之心动,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见之,妾隔帘故邀其满引,至再至三,终不肯出,韩心益急。妾曰:“司谏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为妾舞一曲,即当出也。”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轿,诸娼扶掖而登,归船昏然酣寝。五更酒醒,觉衣衫拘绊,索烛览镜,羞愧无以自容。⑥
内心不坚定的韩璜最终被王鈇设计而无地自容,也没能完成调查的使命。
如果说韩璜尚有羞愧之心,那么南宋后期世人的道德则已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乙编卷一“妒妇喻”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张九成在绍兴做幕官,拒绝“供给钱”⑦;在馆中向皇帝进献书册有功,却不肯升职。张九成认为做幕官有俸禄足矣,哪里还用得着“供给”;进献书册已经被皇帝赏赐,哪里还用得着升官,这些都是本分之事。但人们竟然认为张九成这样做是沽名钓誉。对于这种道德风俗的败坏,罗大经进一步进行了分析和无情鞭挞:“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嗤笑刚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风,反相与嗤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嗤笑谦默者。”⑧在他看来,社会风气已经堕落到了一种可怕的地步。
(四)政治的黑暗腐朽
黑暗腐朽的现实政治也是罗大经经常描写的对象。在罗大经笔下,现实政治的黑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君子屡屡被小人诬陷,受到小人的迫害。秦桧当国时,就贬谪流放了一批直言劝谏的君子。《鹤林玉露》记载了许多因违逆秦桧遭到贬谪的贤臣,如张浚、胡铨、杨万里等,更有刚正不阿、不委曲求全的低层次官吏受到压制⑨,如甲篇·卷三“幸不幸”条中的王廷珪、甲篇·卷六“容南迁客”条中的高登等。罗大经生活的南宋后期更是如此,当时比较有名的是“江湖诗祸”。乙篇·卷四“诗祸”条记载,因为诗作受到当国者的厌恶,刘克庄、敖陶孙、曾极等人被并行贬斥,其中曾极还死在了贬所。
其二,直言奉公者少,阿谀狼狈者多。丙编卷二“大字成犬”条,对受权贵指使、无是非之心的梁成大给予了尖锐的指斥。监察御史梁成大为了迎合史弥远,不遗余力地上书抨击真德秀、魏了翁等正直之士。罗大经认为:“今夫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⑩罗大经又指出:“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亦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他认为,在八表同昏的南宋后期政坛,已经没有纯然正直的真谏官了。
其三,当权者的权势滔天。甲编卷二“进青鱼”条记载了“进青鱼”一事:秦桧的夫人经常出入宫中,与显仁太后闲谈。一次,显仁太后说到最近宫中的子鱼⑪个头太小,秦桧的夫人便应允道:“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原来宰相秦桧权势滔天,进献子鱼的官吏进献给秦桧家的子鱼竟然比皇宫的还大。“进青鱼”事件的背景是南宋初年,无独有偶,南宋后期也有这样一个权臣。丙编卷二“辛卯火”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⑫绍定四年,临安发生大火,就连皇家的太庙也没能幸免于难,然而唯独史弥远的丞相府得以保全。原来火灾发生之时,负责救火的殿前将军只救了丞相府,而没有顾上救太庙。这个小故事反映出奸相史弥远的权势已远超皇室。
(五)社会的动荡不安
罗大经主要生活于南宋后期,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在其笔下也有所反映。《鹤林玉露》中有数次叛乱场面的摹写,如甲编卷二“庐州之变”中提到的淮西军变,又如乙编卷三“白羊先生”中谈及的归正人陈应祥之乱。其中描写最为充分的应属甲编卷四“制置用武臣”条的李全之乱。
“制置用武臣”这篇文章一方面写李全的嚣张跋扈,及其对国家的危害:“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上下共以全为忧。”李全私造纸币,对南宋的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破坏,造成了江南地区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罗大经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反面人物李全的批评上,他还进一步指出,促成李全之乱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南宋朝廷用人不当。罗大经引用了时人乔行简的一封书信:
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处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⑬
结果正如乔行简所料,南宋朝廷用人不当,选派文臣许国统帅李全的忠义军。许国到山阳后,“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因而忠义军全军愤怒,囚而杀之。从罗大经对李全发动叛乱的描写可以看出,他既写出了野心家的跋扈贪虐,也能找出朝廷方面的原因,对社会的动荡不安进行了深度的思考。
二、《鹤林玉露》中的济世安邦之道
从《鹤林玉露》中展现给人们的罗大经这个理学家,不是长期以来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那副迂腐虚伪的面孔,而是一个清醒的忧国忧民的正直士大夫形象。⑭由于南宋后期下层百姓生活困苦、统治阶级生活奢靡、社会道德衰落、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动荡不安,所以罗大经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济世之道,试图以此疗救业已渐衰的世道人心。
(一)读书勤学
罗大经非常看重读书,他在《鹤林玉露》中屡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甲编卷五“读书”条,罗大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问博士李先“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李先回答“莫若书”。甲编卷五“荆公见濂溪”条写王安石少年时拜访周敦颐,三次入门却都被拒绝了。罗大经认为,如果王安石当时能得到周敦颐的教诲,就能消除心中的偏见,推行新法时也不会那么严苛,社稷苍生也就能有所依赖。乙编卷一的“论语”条写到,当时有人说山东人所读之书只有一部《论语》,赵普拜相后,宋太宗就此事询问赵普,赵普回答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⑮罗大经把《论语》这部书提到了较高的位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也由此而来。通过这几个故事,罗大经指出宋人读书问题的种种,却恰恰反映了他对读书这一活动的关注和重视。⑯在他看来,读书不仅能增长智慧,还能治理国家。
读书时所需要的态度应该是“勤”。“勤学”在《鹤林玉露》中被多次提到,甲编卷一的“手写九经”和“前辈勤学”、甲编卷二的“夜绩”、甲编卷三的“建茶”等条都有涉及。在“前辈勤学”中,罗大经从侧面描写了两位勤学的“前辈”——杨时和张九成。杨时的双肘不离案长达三十年,以此表现出他的勤学。张九成则是在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都立在窗下读书,留在窗下石头上的足迹至今犹存。在“手写九经”条,罗大经写到宋高宗“以万乘之尊、万机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烂然,终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宋高宗还亲手抄写《汉光武纪》,罗大经不禁赞叹其“圣学之勤如此”。
(二)重义轻利
义,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指物质利益、欲求。⑰罗大经反对只讲功利,不讲仁义。甲编卷三“利害”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登做尤溪县令,与乡老座谈。张登问“利”字以何字对,乡老皆曰“害”。然后罗大经借张登之口,指出“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字,只当以‘义’字对”⑱。罗大经认为以“利”治理国家,即使能得到一时之利,但终究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人们只关心自身的利益,便走上了邪门歪道:“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因此,罗大经提倡仁义道德。
从重义轻利出发,罗大经继而倡导节俭。在他描写的众多人物中,就有很多人平时生活节俭,如杨万里。罗大经还在乙编卷五“俭约”条专门论述了节俭,他先是列举了李若谷、苏轼、张九成、郑刚中等虽为官却生活节俭之人,然后总结出节俭的四个益处:一是可以养德,二是可以养寿,三是可以养神,四是可以养气。尤其是节俭可以使人不贪不淫,使人养成良好的品德,因而,罗大经又从节俭出发论及清廉。《鹤林玉露》中所描写的文士多具有清廉的品格,如杨万里、朱熹等人。
(三)伦理道德建设
作为一个理学家,罗大经最推崇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他希望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重振衰落的社会道德,这在《鹤林玉露》中有所体现。罗大经在丙编卷五“陆氏义门”条花费了大量笔墨,为我们讲述了陆氏义门,塑造了一个模范家族。首先是陆氏义门的管理制度:“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⑲其次是用饭制度:“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再次是接待宾客制度:“宾至,则掌宾者先见之,然后白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但随堂饭食,夜则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最后是礼仪制度:“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此外,陆九韶还编订了一套训词,每天早上击鼓三叠后由子弟一人歌唱,用以约束子弟们的言行举止。由于陆氏义门的门风谨严,还受到了南宋朝廷的旌表。
三、结语
下层百姓的困苦、统治阶级的奢靡、社会道德的衰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鹤林玉露》中主要的社会现实描写,这与罗大经生活的南宋后期的社会环境是相符的。面对污浊的社会,罗大经进而给出建议,即读书勤学、重义轻利、重视儒家立场的伦理道德建设。正所谓爱之深才会责之切,罗大经对南宋社会的种种批评,是建立在对国家的极度忠诚之上的。罗大经虽说是“清谈玉露繁”,但他仍“心怀天下难”,将人间疾苦诉诸笔端。
①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③④⑤⑥⑧⑩⑫⑬⑮⑱⑲〔宋〕罗大经著,孙雪霄校点:《鹤林玉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第80页,第16页,第203页,第139页,第78页,第169页,第164页,第42页,第81页,第32页,第196页。
⑦“供给钱”是朝廷支拨给各级统兵官基本军俸以外的职资,意在杜绝将帅擅差军兵回易等以肥己。见王云裳:《宋代军队经营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刑名与惩治手段》,《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⑨孙春霞:《〈鹤林玉露〉记人研究》,聊城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21页。
⑪浙江沿海一带对鲻鱼的称呼,色缁黑,肉嫩味鲜,粤人讹为子鱼。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⑭袁道露:《罗大经与宋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2页。
⑯王文雅:《利欲与道义:〈鹤林玉露〉中的世风之议》,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第77页。
⑰张立文:《朱熹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