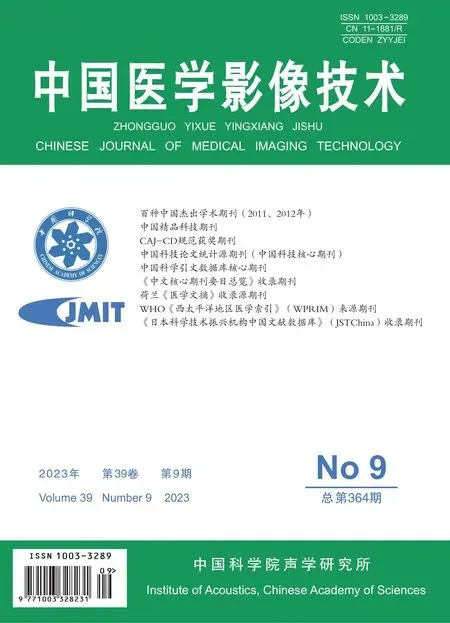腹膜后间隙分区用于判断腹膜后肿瘤来源
2023-09-27张延伟梁少华谢云香
毕 苗,张延伟,利 晞,方 颖,梁少华,谢云香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3;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影像科,4.治未病科,广东 广州 510378;3.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影像科,广东 广州 510260)
腹膜后肿瘤种类繁多[1-2]。腹膜后间隙一般分为肾旁前、肾周及肾旁后间隙,但对于肿瘤定性诊断价值不高。CT可初步判断肿瘤的位置、大小,对于定位肿瘤及定性含脂肪类肿瘤具有较高价值,但术前定性其他大部分肿瘤存在一定困难。本研究观察腹膜后间隙分区对判断腹膜后肿瘤来源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3年1月—2023年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及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术后病理诊断的109例单发腹膜后肿瘤患者,男63例、女46例,年龄6~91岁、平均(47.7±17.4)岁;主要症状包括腹部包块(n=44),腹痛、腹部不适(n=37),恶心呕吐、发热(n=10),腰部不适(n=6),体质量减轻(n=5),或经体检或CT发现(n=7);其中38例神经源性(29例神经鞘瘤、副神经节瘤及神经节细胞瘤各3例,2例神经内分泌癌,1例神经母细胞瘤)、62例间叶源性(27例脂肪肉瘤、2例脂肪瘤、1例脂肪母细胞瘤,8例平滑肌肉瘤、2例平滑肌瘤,12例淋巴瘤,卡斯尔曼病、囊性淋巴管瘤、海绵状淋巴管瘤各1例;海绵状血管瘤、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及血管外皮细胞瘤各1例;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2例,孤立性纤维性肿瘤及横纹肌肉瘤各1例)、7例胚胎源性(畸胎瘤4例,精原细胞瘤、中肾管囊肿及颗粒细胞瘤各1例)肿瘤,2例囊肿。
1.2 仪器与方法 采用Toshiba Aquilion 64排螺旋CT或Toshiba Aquilion One 320排CT机行腹部扫描,范围自胸骨剑突至耻骨联合水平。采集平扫图像,管电压120 kV,管电流25~350 mA,层厚5或1 mm、层间距5或1 mm;再以流率2.5或3.0 ml/s经静脉注射对比剂碘普罗胺(300 mgI/ml)或碘佛醇(350 mgI/ml)2.0 ml/kg体质量,延迟27~28、60 s采集动脉期及静脉期增强图像。采用标准算法重建图像,重建层厚及层间距均为5 mm。
1.3 肿瘤分区方法 器官分区法:以脊柱前缘水平线、双肾内侧缘垂直于脊柱前缘水平线所在线为分界线,将腹膜后间隙分为脊柱前区、脊柱旁区、肾周区3个区域(图1A)。若肿瘤较大,推压肾脏移位,则以移位的肾内缘为分界线。中心线分区法:以脊柱前缘水平线、腹腔左右侧垂直于脊柱前缘水平线的中心线为分界线,将腹膜后间隙分为中央前区、中央后区、外侧区。见图1B。

图1 腹膜后肿瘤分区方法 A.器官分区法,黄线为分界线,分为脊柱前区(绿色)、脊柱旁区(蓝色)、肾周区(红色); B.中心线分区法,黄线为分界线,分为中央前区(绿色)、中央后区(蓝色)、外侧区(红色)
由2名具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影像科医师共同分析CT图像,参考纵隔分区方法[3-4],以肿瘤最大长径与最大短径的交叉点为肿瘤中心点,参考冠状位及矢状位图像,分别以器官分区法及中心线分区法于相应轴位CT图像中确定肿瘤中心点所在区域,由另1名具有30年影像学诊断经验的主任医师进行复核。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6.0统计分析软件。以χ2检验比较计数资料。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基于器官分区法,不同来源腹膜后肿瘤在脊柱前区、脊柱旁区及肾周区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3.94,P<0.01)。上述3个区中,神经源性与非神经源性肿瘤、间叶与非间叶源性肿瘤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3.35、33.76,P均<0.01);81.58%(31/38)神经源性腹膜后肿瘤位于脊柱旁区,70.97%(44/62)间叶源性肿瘤分布于肾周区,57.14%(4/7)胚胎源性肿瘤分布于脊柱前区。见表1及图2、3。

表1 基于器官分区法及中心线分区法显示不同来源腹膜后肿瘤分布(例)

图2 患者男,65岁,腹膜后神经鞘瘤 A.腹部轴位平扫CT图显示,基于器官分区法,肿瘤中心在脊柱旁区; B.腹部轴位平扫CT显示,基于中心线分区法,肿瘤中心在中央后区; C.病理图(HE,×100) (黄线为分区线,红线为肿瘤最大长、短径,其交叉点代表肿瘤中心点)

图3 患者女,83岁,腹膜后畸胎瘤 A.腹部轴位静脉期CT显示,基于器官分区法,肿瘤中心位于肾周区; B.腹部轴位静脉期CT显示,基于中心线分区法,肿瘤中心位于中央前区; C.病理图(HE,×100) (黄线为分区线,红线为肿瘤最大长、短径,其交叉点代表肿瘤中心点)
基于中心线分区法,不同来源腹膜后肿瘤在中央前区、中央后区及外侧区分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68.07,P<0.01)。神经源性与非神经源性肿、间叶源性与非间叶源性肿瘤在上述3个区分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5.34、26.15,P均<0.01);76.32%(29/38)神经源性腹膜后肿瘤分布于中央后区,61.29%(38/62)间叶源性肿瘤分布于外侧区,71.43%(5/7)胚胎源性肿瘤分布于中央前区。见表1及图2、3。
3 讨论
腹膜后间隙为壁腹膜与腹横筋膜之间区域的总和,上至膈下、下达盆腔入口,除疏松结缔组织、脂肪、淋巴及神经组织外,还包含多个重要器官。一般而言,腹膜后肿瘤来源于神经组织、间叶组织、胚胎残存组织等,其内不包含来源于腹膜后脏器的肿瘤;虽然发生率低,恶性者仅占所有恶性肿瘤的0.2%以下[5],但因其位置深在、生长空间大,往往在体积巨大、压迫邻近器官出现临床症状时方被检出[6]。神经源性腹膜后肿瘤多位于脊柱旁,淋巴组织肿瘤多生长于大血管周围。腹膜后间隙形态不规则,范围大、不易分区,传统解剖学一般将其分为肾旁前、肾周及肾旁后间隙,均含大量脂肪组织,不适用于定性诊断腹膜后肿瘤。纵隔影像学分区方法之一系以器官为界,另一种则以定位线对器官进行分割[7]。本研究参考纵隔分区方法,分别以器官分区法及中心线分区法对腹膜后间隙进行分区,观察腹膜后肿瘤在各区的分布。
腹膜后肿瘤好发部位及性质常与其所在解剖部位的组织成分有关。本研究基于器官分区法将腹膜后间隙分为脊柱前、脊柱旁及肾周区,结果显示,不同来源腹膜后肿瘤在脊柱前区、脊柱旁区及肾周区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3例脊柱旁区肿瘤中,神经源性肿瘤占72.09%(31/43),高于非神经源性肿瘤(12/43,27.91%),与既往研究[8-9]相符,提示该区肿瘤以神经源性居多,与此处神经出入于椎间孔有关;51例肾周区肿瘤中,间叶源性肿瘤占86.27%(44/51),高于非间叶性肿瘤(7/51,13.73%);8例脊柱前区间叶源性肿瘤(3例淋巴瘤,2例脂肪肉瘤,脂肪瘤、血管外皮细胞瘤及囊性淋巴管瘤各1例)中,血管、淋巴来源肿瘤占62.50%(5/8),与该区主要由大血管及淋巴组织构成有关;7例胚胎源性肿瘤中,4例位于脊柱前区(4/7,57.14%),可能与胚胎发育过程生殖器官下降经过此区有关[10]。腹膜后间隙其他来源肿瘤较罕见[11-12]。器官分区法虽不切割器官、解剖关系明了,但神经源性肿瘤往往较大,可同时位于肾脏上、下区域,如以肾内缘延长线为标准,肿瘤中心点多位于肾周区;肾脏移位、跨越同侧椎体外缘时,如仍以患侧肾脏内缘为边界,则肾周区与脊柱旁区可存在重叠,影响临床定位肿瘤的准确性。
本研究基于中心线分区法,以双侧腹腔中线及椎体前缘水平线为界,将腹膜后间隙分为中央前区、中央后区及外侧区,脊柱前区、脊柱旁区范围较基于器官分区法有所扩大,且不受肾脏移位的影响。以此划分,29例神经源性肿瘤位于中央后区、8例间叶源性肿瘤位于脊柱前区,与基于器官分区法划分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心线分区法扩大了脊柱前区范围。基于中心线分区法,不同来源腹膜后肿瘤在中央前区、中央后区、外侧区的分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34例中央后区肿瘤中,29例为神经源性(29/34,85.29%),高于非神经源性肿瘤(5/34,14.71%);44例外侧区肿瘤中,38例为间叶源性肿瘤(38/44,86.36%),高于非间叶源性肿瘤(6/44,13.64%);19例中央前区间叶性肿瘤中,14例(14/19,73.68%)为血管、淋巴来源,包括淋巴瘤10例,海绵状淋巴管瘤、血管外皮细胞瘤、囊性淋巴管瘤及卡斯尔曼病各1例;7例胚胎源性肿瘤中,5例(5/7,71.43%)位于中央前区。
本研究2种分区法结果相似,表明2种方法均有助于判断腹膜后肿瘤来源;相比器官分区法,中心线分区法不受器官移位影响,更为简明实用。对于巨大腹膜后肿瘤,需结合临床及影像表现进行综合分析。
综上,腹膜后间隙分区对判断腹膜后肿瘤来源具有一定价值。但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未涉及腹膜后盆腔间隙,有待后续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