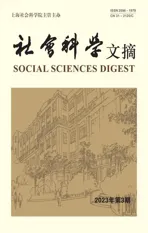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2023-09-23杨天宏
文/杨天宏
本文讨论历史研究中“形而上”的一面,在历史学者近乎一致标榜“实证”的今日,或不合时宜。之所以如此,并非作者固执一端,立异为高,而是希望在方法上执两用中,求实务虚。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
对“形上”或“务虚”的强调是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传统,溯其渊源,可达老庄。
道家哲学的核心命题是“道”,老子称道之为物,恍兮惚兮,有物有象,有精有真且有信。在老子那里,“道”是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它依托物象又高于物象。作为名词,“道”不同于动词的“道”即语言学意义上的“言说”。在道家创始人看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书开宗明义,三次辨“道”,揭示了“道”具有的“思想”和“言说”双重含义。按老子所言,“道”既内在又外化,乃万物之源,不能混同物象,不可言说及命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玄之又玄”,为言说之力所不能及。如果“道”可言及,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由此可见“道”在老子认知中的高度抽象性。
庄子哲学中也包含对“形上”的精神追求。但与老子不同,庄子注意到前人不怎么强调的“言”与“意”的区别,并注重抽象的“意”的表达。《庄子》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之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有学者认为,庄子寻觅的“得意忘言”之人,是“保持其内在意义而非外在形式的‘道’或逻各斯的容纳者”。这一将“逻各斯”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相提并论的认知,已意识到二者在追求超越物象上的精神共性。
在“言”与“意”的关系认知上,王弼较庄子更进一步。王弼是魏晋时期的“玄学”代表,认为“无”是“万物之所资”,主张“以无为本”。其与庄子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言”与“象”联系起来思考,认识到以“言”名“象”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试图以“意”实现联通与超越。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这一论说,充分体现了王弼以言尽意,将抽象的“意”置于具体“物象”之上的形上思考。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并无西方式研究“存在”的形而上学。此说不免偏颇。中国文化中很早就已出现“形上”与“形下”的认识范畴,并以“道”“器”对立的形式予以表述,确立起“道”高于“器”的认知等级观念。《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是卜辞,用于占卜吉凶,关注“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这固然与西方形而上学有别,但两者都强调抽象,内含对物象的超越。西方形而上学有“物理之后的学问”之定义,被看成“第一学术”。中国古代思想中也有这一元素。莱布尼兹曾说,他在中国文字中“看到一种脱离于历史之外的哲学语言的模式”。严复用被视为“道”的中国古典术语“形而上”缀以“学”对译西文表述中的“metaphysica”,看似牵强,实则信达。
在注重“形上”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人十分考究文章的虚实处置。《易经》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体现出将抽象的“尽意”而非穷尽笔墨“叙事”“状物”作为书写的终极追求。魏晋时期,追求超脱成为时尚,文学创作“虚”风盛行。对文学而言,对“虚”的讲究能激发想象,突破有形的文字表现手段,以无衬有,以虚托实,产生“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和认知效果。
作为古代文论的巅峰之作,《文心雕龙》对虚实关系的论述最为详尽,其《隐秀》篇有云:“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複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刘勰强调“複意”即言外之意,将“隐”视为文之“体”,强调“义主文外”,彰显对空灵虚无即形上精神的看重。
与哲学、文学比较,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务虚”成分更为浓重。
刘知幾作《史通通释》,曾自叙“指归”曰:“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他特别交代其“著书之义”,指出《史通》一书有与夺、有褒贬、有鉴戒、有讽刺,贯穿者深,网罗者密,商略者远。强调以往学者谈论经史多讳言前贤之失,此书反其道而行。“指归”具有的批判性,证明刘知幾对“形上”史论的看重。
近代学人继承了传统史学的务虚的传统。刘咸炘认为,史家职能为“纪事”,其要在“察势观风”。鉴于传统书志“止记有形之事,不能尽万端之虚风”,无以展示历史全貌,故刘咸炘主张治史者须重视“虚风”。
综上可知,“道器之辨”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重“道”轻“器”观念不变,充分说明传统文化对“形上”精神追求的重视。清季以降,中国史林风气几度翻转。随着西学东渐,科学主义盛行,加之政治干扰,学者一趋一避,重视形上思维、追求哲理抽象者日稀,“实证史学”,遂成时尚。然而,无论如何变及变如何,上列论述证明,标榜“实证”的学风并非源于中国悠久的主流文化与史学传统。
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近代中国“实证史学”来源安在?考镜源流,厥有两端:一是清代朴学,即乾嘉以来的考据学;二是被某些近代国人不恰当表述为“实证主义”的兰克史学。两大源头,前者出现时间相对晚近,亦非中国文化主流,对现代史学作用有限,真正对中国实证史学产生影响的是兰克及其弟子。尽管近年来史学理论界对兰克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有部分历史学者认知片面,未能跟进吸纳相关成果,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兰克史学的误读。
就历史方法而言,兰克确实将事实描述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他在《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序言中写道:“一直以来,历史被赋予评判过去、为了未来岁月指导当今世界的任务。本研究不奢望如此崇高的功能,它只想陈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虽然严格描述事实可能会限制我们,并且结果证明令人不愉快,但他无疑是最高法则。”兰克对后世最重要的影响是把史学建立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传播了考证史料及追寻历史真相的学风。也许正因为如此,克罗齐将兰克定位为“实证主义”历史学家。
不过,克罗齐的定位虽然把握了兰克史学的重要特征,却失之片面。因为兰克将历史提升到与哲学、文学等学科并立的现代学科地位,除了对“实证”的强调,还有对历史的精神层面认知即形上层面的重视。
从德国史学维度观察,兰克并不属于实证主义传统,他本人及其早期弟子都反对这一传统。在19世纪欧美史学界,实证主义特指英国文化史学家巴克尔代表的从历史中发现规律一类传统史学范式。兰克所属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追求历史中的个体性,与实证主义正相反。
就身份言,兰克虽是史学家,却是在擅长思辨的德国学术和人文环境濡染熏陶下成长,在史学撰述中不可能感受不到实证的局限。因而在将依靠史料寻求历史真相视为历史研究“最高原则”的同时,兰克一直努力寻求对史料的超越。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导言中,兰克宣称自己“运用了大量的档案文献”,但也意识到,如果仅以此为凭借进行研究,自己将“面临失去从整体上把握整个历史主题的危险”。
然而,由于兰克史学思想中的“实证”特征被人为放大,掩盖了他对历史的形上思考,兰克曾遭到黑格尔讥讽,说他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历史学家”。
也许是受到黑格尔批评并意识到历史研究离不开抽象的哲学思考,兰克明确了他对哲学及与哲学相关的宗教的认同。尽管因为历史学的特殊性,兰克与历史哲学家在方法上异趣,但观念上却与之相同,都重视形上思维。兰克曾谈论他人对自己的误解:“非常好笑的是,有人说我对哲学以及宗教兴趣缺缺。事实上,正是哲学和宗教因素,也只能是这些因素将我引入历史研究之中。”
兰克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形上思维,与他曾经的哲学训练有关。兰克早年在莱比锡大学就学,起初学的是古典语文学,后转习历史。在研习语文学期间,他对康德哲学发生浓厚兴趣,直接研读康德的著述。此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哲学和神学双重影响下,兰克异常重视主观意志与精神作用,强调研究主体的“自我主义”,认为“精神能立即产生出再生的力量”,“没有什么比这一点对我整理研究方面的思想更为重要的了”。
兰克的这一思想,与他对历史学的性质判断相关。他指出:历史学家既要博学,又要有文采,因为历史既是艺术也是科学。历史学的这一学科性质,决定了历史研究如同哲学一样,既要有批评性又要有知识性。没有能透视社会的人文与艺术眼光,没有严密的富有创建性的科学头脑,不可能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达成吻合。
从目的论立场观察,兰克理解的史学目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不可能将目光滞留在依据“客观”史料书写历史故事上。在兰克看来,历史首先是“依靠批判的理解,把真相与谬误区别开来”。但这只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更为繁难的任务是探究历史事件的因果,说明人类的意图,分析历史成败之由,“最后的结果是对世界有一个和谐的理解”,即“以设身处地的方式,移情地理解所有的一切”。如此繁复的任务,离开高度的抽象与深刻的批判,岂能完成?
作为史学家,兰克留下的史学论著点评,也体现出他对精神层面的看重。在兰克点评的历史著作中,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堪称不朽。兰克认为,这一作品之所以不朽,除了作者以其胆略直面教皇和教会、揭露诸侯的秘密、绝无谄媚迎合之迹外,主要原因在于能注意到当时政治生活中派别的错综复杂,意识到不对“普遍事态”进行考察就无法书写具体历史事实,在解释“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虚荣心和自私自利方面,表现出无愧于一个真正的天才和大师”。这一评论,体现出兰克对历史学家把握比思想更加内在的人类心理及精神活动的高度重视。
然而兰克毕竟是大师,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不轻下论断,这给人以注重事实重建忽略历史诠释的印象,但他一旦作出论断,便无可辩驳。英国史家古奇论述兰克的生平和著述,把他的《近代史家批判》定位为“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认为兰克批判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能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在兰克的著作中,人们较少看到主观的议论,然而“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
问题在于,兰克既将利用史料以寻求事实真相视为史学“最高原则”,又被视为开启了“史学的批判时代”,两者的关系如何协调?
马克思的一封信提供了打开困惑之门的锁钥。1864年9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兰克,说当时很多青年人追随兰克,兰克让他们参与德意志皇帝编年史的工作,要求他们只关注现象,死守客观,不让他们涉猎奇闻逸事背后的意义、重大事件的因果等,自己却掌控编年史中属于精神与智慧层面的存在。编写过程中,他的学生段尼格斯被视为“叛逆者”,因为他不满兰克对历史撰述中的“精神垄断”。
马克思对兰克的历史编纂所做工作的层次区分极具提示性。在马克思看来,兰克的历史撰述,存在作为基础工程的史料“编纂学”和解释历史事实的“思想观念”阐释两部分,他给学生的任务是前者,而把后者留给自己。这充分说明兰克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的重视。
像马克思这样区分历史研究层次的在当时并非特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数历史学家在理论上都认同唯心主义,严格区分历史学与科学,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当时,历史学家设定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历史的批判”。在巴勒克拉夫看来,通过将历史研究区分为两个阶段可以实现两者的结合:其一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其二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历史学家的“自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
不仅如此,巴勒克拉夫还敏锐观察到兰克史学中精神层面的突出地位,指出兰克的历史研究是要呈现每个时代特殊的精神,他不藐视有历史观点的史家,并非只知道让史料自己讲话。相反,兰克著作中的历史观点极为丰富并有一致性,它们都融入他的叙述中。其著作表达的方式与内容都透露着他的历史看法以及他所见到的历史特质与精神,这些观点与看法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原则——个体性的原则。巴勒克拉夫所言,道明了兰克史学的形上内涵。
然而何以兰克追求形上史学却给人留下“实证史学”印象?克罗齐曾就此作出分析。他注意到,虽然兰克“老是攻击哲学,尤其攻击黑格尔哲学,大大地有助于历史家们对哲学的不信任”,但他仍然信仰宗教、钟情哲学。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极富文采,善于表达,所以“能在礁石之间行驶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念或哲学信念”。克罗齐说得很含蓄,兰克是有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史家,其史学思想被误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暴露”他笃信并践行的宗教理想与哲学信念。
综上可知,中外史学传统均强调求实务虚,但在虚实关系上,则近乎一致讲求“道器之分”,将形上之“道”放在高于形下之“器”的位置。然而,由于我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学科分工形成板块区隔,当史学理论界的兰克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之时,仍有部分历史学者的认知未能跟进:言及兰克,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狭义理解的“实证”阶段,以为其高妙只在依据材料作史实重建;谈到中国传统史学,以为实证才是主流,强调搜集史料的功夫,忽略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这不仅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误读,也是对兰克史学的片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