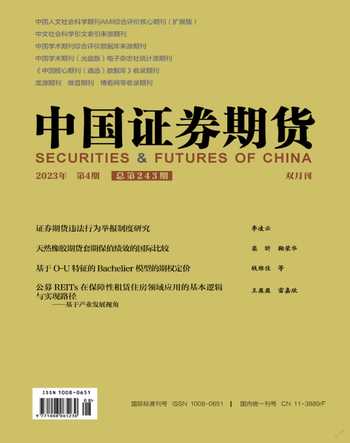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法教义学解析与反思
2023-09-19沈国勇王天龙
沈国勇 王天龙
摘 要:证券内幕交易主体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被二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但被二分的主体在诸多的规范中采用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导致实践中频繁出现法律适用难题。内幕交易主体方面的立法主要秉持信义义务理论,而执法与司法实践常常超越身份联系,逾越相关规定中“兜底条款”与“双重兜底条款”要求的同质性解释边界。基于身份联系的现行法规固然存在处罚漏洞,但法教义学视角下的监管进路应当是明确规范边界,包括证监会经授权制定成文规章、司法解释重新定义“非法获取人员”的概念,以及利用法律理论进行补漏。
关键词:内幕交易主体;身份联系;法教义学;监管进路
一、引言
从《刑法》和《证券法》对证券内幕交易主体二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到2012年最高院、最高检发布《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内幕交易解释》)对两类主体进行阐释,再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下称《资产重组办法》)等规章、文件对“知情人员”的范围进行扩充,我国的规则体系对内幕交易主体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但在现行法律规则如此繁多的情况下,内幕交易主体仍存在较大的逻辑缺陷——划分不周延、列举不全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与司法机关也常常因此在執法与司法实践中进退维谷,从而导致近年来学界对此的批判纷至沓来。而在诸多讨伐声中,也存在着部分学者认为如此二分“具有现实合理性”,这也能从2019年《证券法》的修改内容中窥得一二。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证券内幕交易的规则制定情况、理论纷争、法律适用困境等内容,并借法教义学的视角,以探寻内幕交易主体在我国规则体系中的改良路径及监管进路。
二、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则制定现状
《刑法》第180条第一款规定,内幕交易犯罪的主体分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第三款则规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可见,《刑法》未对内幕交易主体做出明确界定,而是采用“授权立法”的形式,授权“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界定。
2019年《证券法》(下称新《证券法》)第51条列举了八类具备特殊身份的“知情人员”,并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进行兜底。换言之,新《证券法》第51条的“兜底条款”又一次以“授权立法”的方式,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授以“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界定权”。
中国证券期货2023年8月
第4期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法教义学解析与反思
《资产重组办法》第41条、《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下称《内幕认定指引》)的第6条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下称《规范信披通知》)的第3条均对“知情人员”的范围做了一定的扩充,但后两份文件已分别被2020年10月30日的《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制度文件的决定》以及2022年1月5日证监会《关于废止4部证券期货制度文件的决定》废止。
《内幕交易解释》对内幕交易主体做出了细化解释,第1条将“知情人员”链接至2005年《证券法》(下称旧《证券法》)第74条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85条,《内幕交易解释》第2条则对“非法获取人员”进行了详细释义。
至此,在罗列了所有与内幕交易主体相关的规定后,不难发现,将“知情人员”与“非法获取人员”的规范含义相加,得到的合集并不能涵盖所有进行内幕交易的信息受领人。换言之,如此二分的内幕交易主体并不周延,存在一部分既不属于“知情人员”又不属于“非法获取人员”,但又实施了内幕交易的主体。该部分主体不能被纳入行政法规的兜底性规定,进而也不能被纳入《刑法》第180条的兜底条款,但实践中该部分主体不适格的人实施相关交易仍会被认定为违法甚至犯罪,相关条款存在“隐形扩张”。例如,李启红内幕交易案,被告人为一般而非具备监管或其他法定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不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知情人员”主体身份,但法院依旧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况下,以李启红知悉内幕信息并实施了内幕交易为由,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罪。又如,在倪鹤琴、曾云、魏薇内幕交易案中,“知情人员”倪鹤琴将信息泄露给曾云后,曾云又将信息泄露给其同事魏薇,如此一来,魏薇属于“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联络、接触的人员”,不在《内幕交易解释》规定的“非法获取人员”之列。但最终魏薇仍被判处构成内幕交易罪。
上述案例,体现出我国内幕交易规制实践中存在主体识别不清晰及法律适用不规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起源于存在漏洞的立法,还是归因于违背罪刑法定的司法?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法律存在疏漏,司法为了补漏而做出的隐形扩张,从而将对法益具有实质性侵害危险的交易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
然而笔者认为,在法益视角下讨论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的规范构造,属于立法论的范畴,易言之,是否要以法益侵害的角度划定内幕交易主体的外延,并不在司法与执法机关的职责范围内。
三、内幕交易主体的理论纷争及规范对应
(一)信义义务理论与规范对应
信义义务理论指的是构成内幕交易的前提不仅包括掌握内幕信息,还需要交易者违反了某种信义义务。这一理论的优势在于认定逻辑清晰,可以迅速将不相关主体排除,从而避免规制主体过于宽泛的问题。例如,出租车司机偶然知悉内幕信息并据此进行证券交易,倘若此类主体未被直接排除,则行为人需要自行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内幕信息是否属于自己分析得出的结果,这样的标准会导致法律的天平偏向于执法机关。然而,信义义务理论现今也遭受了较为猛烈的批判:其一,交易模式的变更和交易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传统信义义务理论在适用上逐渐显得左支右绌,以此为基础的理论不断派生,如“不正流用理论”“信息传递理论”,而理论的扩张动摇了标准的稳定性。其二,内幕交易行为在美国证券法中被置于“欺诈”框架下,因而难以摆脱信义义务之理论,而我国则未将内幕交易纳入“欺诈”之框架,没有证明信义关系存在之必要。
这一理论在我国立法中表现为新《证券法》第51条前5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均为公司的任职人员,属于传统的内部人,而第6项至第8项虽非公司内部职员,却因业务关联而具备“临时内部人”的特征。无论是传统内部人还是临时内部人,都对公司承担着诚信、忠实、注意、正直的信义义务。
(二)平等获取理论与规范对应
平等获取理论指的是参与市场交易的人应当具有平等获取市场信息的机会,从而禁止任何合法或不当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进行交易。该理论也存在一定优势:第一,平等获取理论以知悉并持有为标准,不以存在信赖关系为前提,能够避免遗漏部分不存在信赖关系的主体的规制。第二,内幕交易的主体认定在实践中存在扩张解释和任意解释的情况,以平等获取理论来认定内幕交易主体则可以避免这一点。
这一理论在新《证券法》《内幕认定指引》中均有所体现。新《证券法》第51条第9项规定“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受限于“兜底条款”狭窄的解释路径,新《证券法》只是为平等获取理论留下了实现的可能性。《内幕认定指引》第6条第5项规定“通过其他途经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为内幕交易人。结合该条前几项所述,无论是利用骗取、套取、偷听、监听或者私下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合法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均被纳入内幕交易的规制范围。由于《内幕认定指引》尚不属于部门规章,但却越权对上位法律进行解释,无疑会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换言之,《内幕认定指引》通过旧《证券法》“兜底条款”的授权,架空了旧《证券法》对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定,在任何人都能成为内幕交易主体的情况下,又何必多此一举进行主体划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幕认定指引》突破了法律解释的逻辑,给执法、司法和当事人守法带来了困难。
四、新《证券法》下内幕交易主体的适用困境
(一)基于身份联系的主体规范框架
从新《证券法》第50条和第51条来看,对内幕交易人的处罚应当被限制在授权边界内,而边界则在于是否具备身份联系。《证券法》第50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紧接着第51条列明了8类“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并授以证监会规定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权力。
在这两个条文“列举”加“兜底”的限定下,“知情人员”的范围得以确定——基于特定身份或职务的处罚范围。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规范体系下,旧《证券法》第74条圈定了“知情人员”的身份,体现出一种“身份中心主义”。新《证券法》第51条基于特定身份和职务关系确定的内幕交易处罚范围,与第50条中未设定范围的“非法获取人员”共同构成一种相对有限、特定的内幕交易查处模式,这并非一种涵盖任何涉及内幕交易的人的监管模式。从旧《证券法》第74条的6类人员到新《证券法》第51条的8项列举可以看到,新《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并非将所有人涵盖于内,而是想要通过更精细化的列举以限定“知情人员”的范围,新旧立法中始终不变的则是具有信义义务的身份或职务特征。
(二)超越身份联系的执法与司法实践
倘若完全在基于身份联系的规范框架下进行处罚,那么很多被处罚的人主体并不适格。例如夏雄伟内幕交易案,夏雄伟时任《证券时报》浙江站站长,在接听了精工科技证券事务代表邀请其采访公司的电话后,知悉了内幕信息。夏雄伟的新闻记者身份并不在旧《证券法》第74条规定之列,但证监会在《行政處罚决定书》中将其定性为“属于《证券法》第74条第(七)项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又如刘宝春内幕交易案,刘宝春作为非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国家公职人员,被法院认定为“属于《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然而刘宝春身为原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并不属于旧《证券法》第74条列举的6类人员;同时,由于其是受到南京市人民政府指派参加洽谈,是否属于“非法获取人员”也有待商榷。但最终一审法院以旧《证券法》第74条之“兜底条款”,将其纳入“内幕信息的知情人”的范畴。实践中还存在着此类情况:证监会出具“关于××涉嫌内幕交易案有关问题的认定函”,将不适格主体认定为“知情人员”,法院则怠于行使其独立审查之权责,直接采纳证监会在“认定函”中对违法主体的认定意见。此时,“认定函”成为内幕交易主体认定的唯一“法律依据”。
执法与司法机关如此笼统地定性,是对基于身份联系进行可预期推理的突破。作为《刑法》的前置性法律,《证券法》的“兜底条款”同时也驻守在行为入罪的大门前,因此就《证券法》的具体解释规则而言,应当同刑法中的“兜底条款”适用相同的解释规则——“恪守严格的解释立场,确立并严格遵守同质性解释规则”。这一解释规则不仅是刑事司法中的要求,对于对刑事案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行政处罚而言,同样应当恪守,“以‘认定函作为刑事案件中认定犯罪主体的法律依据”实在不妥。
事实上,早在1993年颁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下称《证券欺诈办法》)第6条就规定了“内幕人员”包括“由于工作联系而可能接触或获得内幕信息的新闻记者”以及“有管理权或者监督权的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即夏雄伟和刘宝春均属于《证券欺诈办法》规定的“内幕人员”。又根据2008年《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证券欺诈办法》因主要内容被“新的法律”所代替而被废止。此处“新的法律”指的是2005年《证券法》,然而根据“新的法律”,夏雄伟和刘宝春都不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但证监会和法院各自突破基于身份联系的类比推理预期,通过旧《证券法》第74条之“兜底条款”的路径,将二人定性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五、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则体系完善与监管进路
(一)规则体系中内幕交易主体的逻辑定位
研究内幕交易违法主体的范围,实质上就是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可罚性以及法理基础的解读。而研究的必要性则源于《证券法》等规定存在自有缺陷而致使执(司)法实践中产生认定障碍。
从内幕交易主体的规则体系来看:①《刑法》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内幕交易犯罪主体。②新旧《证券法》以明确列举加原则兜底的形式来确定内幕交易违法主体。③《资产重组办法》以列举的形式扩大了《证券法》圈定的“知情人员”的范围。④《内幕交易解释》在“知情人员”的界定上仍遵循《证券法》的路径,规定“知情人员”包括旧《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人员。⑤其他部门制度文件,如《内幕认定指引》(已废止)、《规范信披通知》(已废止),前者亦以列举加兜底为形式,后者则以详细列举的形式进行补充。可见,现有的证券法律、法规并没有很好地对内幕交易主体的典型类型和实质标准进行明确和阐释,导致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裁量权过大。
其中存在着内幕交易主体表述不统一的问题:①《刑法》规定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②《证券法》表述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③《规范信披通知》则设定为“内幕信息知情人”。④《内幕认定指引》甚至创设了“内幕人”的新概念。至于如此多样性的表述是有意为之——概念之间设定了细微差别,还是立法漏洞——制定时缺乏体系性考量,则无法从条文中推断得知,毕竟“内幕信息知情人”相较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而言,更像是一个规范性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内幕认定指引》和《规范信披通知》从效力级别来看,属于指导性制度文件,并非我国法律制定和规章制定意义上的法律法规,仅仅起到为证监会内部机构和人员提供指导的作用。《内幕认定指引》和《规范信披通知》的非法律位阶意味着运用于实在法的法教义学无法作业,而其又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创设性解释之效,造成了制度文件替代立法的局面。具体而言,《内幕认定指引》创设了从未出现在《证券法》中的“内幕人”这一新概念,而该概念涵括了具有信义义务的人员的“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因亲属关系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这与旧《证券法》第74条所列人员存在重大的理论基础差异——前者突破了后者需具备信义义务的范围圈定。上述两部文件定位于不具有法律规章地位的指导性文件,理应遵循严格的授权限制,却又常被司法机关援引以满足打击犯罪的需求,因而饱受诸多学者的诟病。
因此,内幕交易主体理应由法律法规予以界定,在涉及犯罪时,最多由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完善,证券会在此过程中应当在法律保留的范围之外、严格的授权范围以内进行规则的制定与解释。
(二)法教义学视角下内幕交易主体的监管进路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则构建极大地受到了美国经验的影响,将内幕交易主体二分为“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人员”正体现了美国信义义务理论在我国证券领域相关法律中的借鉴实践。但在具体的执法与司法实践过程中,“以身份标准划定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以手段标准圈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并行的二分法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从而导致部分具备身份条件的知情人未被纳入“知情人员”主体范围,如持股49%的公司股东;部分“不该获得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被认定为“非法获取人员”存在一定障碍,如与“非法获取人员”联络、接触而得知内幕信息的人。
对于此类漏洞,存在以下解决路径:①将符合身份条件但不在新《证券法》第51条前8项之列的知情人员列入“内幕信息的知情人”。②对“非法获取”进行扩大解释,使应当被规制的对象不被遗漏,避免执法和司法中的法律适用超出规范含义。③严格遵循合法行政、罪刑法定原则,对此类主体统统作主体不适格的处理,至少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因此在法教义学的视角下,我国内幕交易监管中存在三个维度的补正方向。
1证监会以成文规章扩展“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員”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照《证券法》的授权,以成文规章的形式对“知情人员”做出对象扩展的解释。《行政处罚法》第13条规定部门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范围内对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做出具体规定。且《立法法》第80条明确表明部门规章属于执行性立法而非创设性立法,因此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扩展解释,并未超出法教义学的作业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执行法律”的属性要求部门规章不得超越法律本身的含义,不应该是自主性立法,否则有僭越立法之嫌。至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能否利用法律授权,制定“通知”“指引”等类型的制度文件来扩大“知情人员”的范围,笔者认为,“通知”“指引”等文件并未对外公开且正式公布实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也不会以此为处罚依据,因而不应该认定其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进而,此类“通知”“指引”不宜被列入证监会依照法律授权而制定的、扩大“知情人员”范围的成文规章。
2以司法解释的路径重新定义“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
在“非法获取”的解释上,由于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未得到新《证券法》的授权来进行补充规定,因此只能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路径来解决该部分的主体缺漏问题。具言之,《内幕交易解释》在明确了“非法获取”涵括“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人员”“联络接触人员”纳入“非法获取”的范畴。但“身份列举式”的认定方式常常是挂一漏万。例如,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的主体就无法归入上述三种人员类型:内幕信息经知情人员A一手传递给非法获取人员B,第三人C又经与B接触后得知内幕信息并进行相关交易,此时第三人C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系“与非法获取人员联络、接触”而非“与知情人员联络、接触”,因此不属于《内幕交易解释》第二条所规定的“与知情人员联络、接触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
若需对此进行规制,需满足B属于“知情人员”之前提,而若要将B解释为“知情人员”,路径之一是不再区分“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人员”,明确任何人都不得不当使用内幕信息,但如此一来将涉及立法层面的改动,也即需对《刑法》第180条以及新《证券法》第50条、第51条进行修改,因此存在诸如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中的“非法”删去的立法建议。路径二则是在仍保留“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人员”二分的基础上,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内幕交易解释》第2条关于“非法获取人员”的范围修改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以外的信息受领人”,如此修改便能得到周延的二分结果。
3以“共同犯罪”与“共同违法”理论作为主体不适格对象的补充打击路径
对既不属于“知情人员”范围,又不符合“非法获取人员”条件的人,做出主体不适格的认定。这是由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律适用的“统一”优先于“正确”。“正确”固然是我们在法律适用中追求的最高目标,但这样的追求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且不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正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既有漏洞和滞后性带来的预期漏洞就导致法律适用的“正确”与“统一”之争频发。对于部分不符合内幕交易主体身份的人,虽然有判决将其认定为“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人员”,甚至也存在未在判决书中载明犯罪主体究竟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的情况,但在相关规则修改前,此类认定实属超越了条文的应有之义,是对“正确”的追求高于对“统一”的追求的体现。然而法教义学的逻辑出发点在于形式理性,即便法教义学不排斥价值判断,也不应将价值判断(“正确”)凌驾于形式理性(“统一”)之上。如此一来,对于不符合身份限制条件的主体,若是想通过规范判断纳入内幕交易规制的范围,只得“另辟蹊径”,借用“共同犯罪”和“共同违法”理论进行迂回认定。司法实践中亦有此类认定方式。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实施贪污行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据此,通过“共同犯罪”理论,可以顺理成章地将部分不符合规范身份的信息受领人纳入内幕交易规制的范围内。但这一路径仍不能完美解决内幕交易主体规制的漏洞:受限于“共同犯罪”的可罚性前提——只有在正犯已构成犯罪并具有可罚性的情况下,共犯才从属于正犯而成立并具有可罚性,部分内幕信息受领人并未与内幕信息泄露人共同实施内幕交易,从而无法通过“共同犯罪”的路径进行规制。例如,信息受领人从“非法获取人员”处获取内幕信息(该信息受领人不属于“非法获取人员”已在前文论述),而该“非法获取人员”并未实施内幕交易行为,在此种情境中,该“非法获取人员”并不构成内幕交易罪,进而无法以内幕交易罪的共犯对信息受领人进行规制。
六、结语
新《证券法》对内幕交易主体的范围进行了扩充,但仍无法从容应对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从法律、法规到司法解释,再到部门规章和制度性文件,内幕交易主体在我国的规则体系中始终存在着逻辑混乱的问题,在坚持适用同质性解释规则时,对部分具备处罚必要性的行为进行规制将难以突破“身份联系”的桎梏,从而使司法机关陷入为难的境地——要么进行超越法律文本的目的解释,使不符合主体要件的行为入罪,从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要么以形式判断优先于实质判断的标准,对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网开一面,从而违反法益侵害原则。
而在法教义学的视野下,法律解释只能是形式解释,且解释的最大射程不得超越语义边界。在《刑法》与《证券法》已经对内幕交易主体进行二分,但尚未对“非法获取人员”进行界定的前提下,监管的最佳进路是通过经《证券法》授权而制定的部门规章对“知情人员”的范围进行补充完善,使具备身份联系条件的主体被纳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的路径,将“非法获取人员”重构为“除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以外”的信息受领人,如此方能有效实现对内幕交易行为的阻却。至于其他如“共同犯罪”“共同违法”理论在此命题中的运用,虽然可以在司法解释尚未修改的阶段提供规制路径,但并无法完全化解现实与立法之间的龃龉。
参考文献
[1]汤君解释论视野下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主体的认定标准[J]法律方法,2019,28(3):347-357
[2]李激汉新《证券法》下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确定之构想[J]北方法学,2020,14(6):77-86
[3]曾洋证券内幕交易主体识别的理论基础及逻辑展开[J]中国法学,2014(2):158-182
[4]张淑芬,左坚卫新《证券法》下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的立法重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1):104-113
[5]齐萌证券内幕交易主体理论的检讨与选择[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8(6):99-101
[6]吕成龙谁在偷偷地看牌?——中国证监会內幕交易执法的窘境与规范检讨[J]清华法学,2017,11(4):157-176
[7]郝山,陶永祺,卫绮骐中国过于宽泛的内幕交易执法制度——法定授权和机构实践[J]交大法学,2014(2):71-84
[8]邢会强证券欺诈规制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9]夏中宝从“身份中心主义”到“信息中心主义”——内幕交易主体法律规制之变迁[J]金融服务法评论,2014,6(1):167-223
[10]刘宪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法教义学的再展开[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30(6):41-53
[11]刘宪权论内幕交易犯罪最新司法解释及法律适用[J]法学家,2012(5):39-51,176-177
[12]雷磊法教义学的方法[J]中国法律评论,2022(5):77-93
[13]张子学美国证监会监管失败的教训与启示[J]证券法苑,2009(1):114-146
[14]沈福俊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合法性分析[J]华东政法大學学报,2011(1):27-34
[15]王崇青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34-39
[16]陈兴良刑法教义学中的价值判断[J]清华法学,2022,16(6):5-22
[17]陳兴良共同犯罪论[J]现代法学,2001(3):48-57
Legal Dogmatic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 of Securities Insider Trading
SHEN Guoyong WANG Tianlong
(Shanghai JHH Law Firm,Shanghai 201199,China)
Abstract:The legal terms about the subject of securities insider trading are divided into“the insiders who has access to any insider information”and“the insiders who has unlawfully obtained any insider information”However,The divided nature of the subject in various regulations has led to frequent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Legislation concerning insider trading is primari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iduciary duty theory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practices often go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onnections and the homogeneous interpretation of“safety net provisions”and“double safety net provisions”as stipulatedAlthough there are penalty loopholes in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based on identity connection,the regulatory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dogmatic should be to clarify the normative boundaries,including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CSRC to formulate written rules,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of“the insiders who has unlawfully obtained any insider information”,and using legal theories to reduce legal loopholes
Key words:Subject of Insider Trading; Identity Connection; Legal Dogmatic; Approach to Regu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