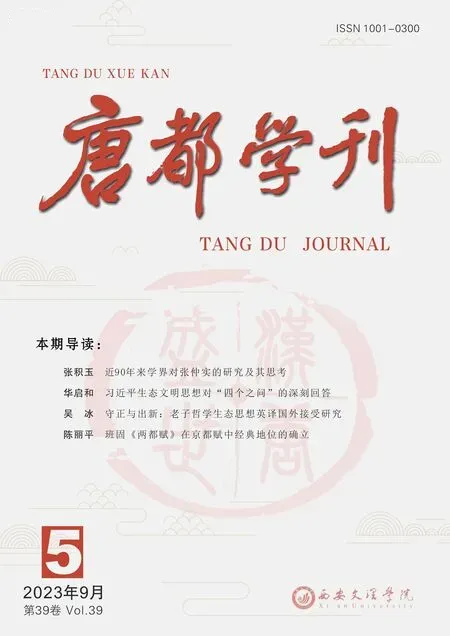略论早期儒家“性”范畴的特质
2023-09-18任鹏程
任鹏程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济南 250001)
“性”是早期儒家哲学中的核心范畴。甚至有学者指出:“‘性’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1]那么,在早期儒者看来,“性”有哪些特质和属性呢?本文着重讨论这一问题。
一、“性”与“生”
“性”是什么?考究字源发现,“性”字与“心”“生”两者密切相关。按照于省吾的说法,“心”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甲骨文心字作,正象人心脏的轮廓形”[2]。从甲骨文来看,“心”指的是人的血肉之心。从生理角度而言,心能够维持和延续生命的存活,正如朱熹所曰:“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3]心乃是生存之本,这是古人对“心”的基本认知。“生”之本义乃是指生命、生存,如《说文》曰:“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4]从《说文》看,“生”就像草木刚出土时候的样子。这种解说至少包含两层引申含义:一是指生命、生存这一事实;二是指生命生长的趋势及其走向。同时,“性”字在早期儒家文献中有时被写作“眚”,郭店儒简《性自命出》指出:“凡人唯(虽)又(有)眚(性)。”[5]虽然“眚”字不从“心”,但与“生”紧密相联,这更加印证了“性”与人的生命有关。
学者普遍认为,在早些时候“生”与“性”两个字是可以互用替换的,如徐灏说:“生,古性字,书传往往互用。《周礼·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读为性。《左传·昭公八年》,‘民力雕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言莫保其生也。”(1)转引自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杜子春将“生”读为“性”,表明在古代“性”与“生”二者的关系密切,阮元以为,“声亦意也”[6]。“性”指的就是生命或者说就是生之常态。傅斯年还从考据学角度说:“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皆用生字为之。至于生字之含义,在金文及《诗》《书》中,并无后人所谓‘性’之一义。而皆属于生之本义。”[7]在傅斯年看来,先秦时期的“性”字皆作“生”(生命)讲。生即是“性”的本义。这种人性观点就是儒家哲学史上的“生之谓性”。
综上,“性”字的本义即是“生”,它指人初生的自然状态。或者说,“性”为天然或者自然之义。从反面来说,人为、加工、炼造的东西都不属于“性”。这便是人性的基本义项。
二、“性”与“天”
“性”与生有关,那么什么东西能够生呢?古人给出的答案是“天”。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8]180“天”具备生生的意味,天没有任何言语和动作,四时的形成,万物的繁育都是天的功劳。天是万物的本原。儒家以为,人的德性亦是源自天。孔子云:“天生德于予”[8]98,认为“天”与“性”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8]79郭店儒简《性自命出》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9]136天是性的根源。孟子云:“天之生物也”[8]226,“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8]237也就是说,“性”乃初生者,其构成是“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是人天生所“固有”者[8]328。为了论证“四端”天生自然性,孟子列举了“孺子将入于井”[8]237的例子。荀子也持有这种立场。据《荀子·性恶》载:“凡性者,天之就也”[10]377“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10]377在荀子看来,天生的东西就是“性”,因而“性”即天然之物。不同于孟子的是,荀子以为眼睛可以观物,耳朵可以听音,等等,才是“性”。
“性”源自于天。先秦两汉之际的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易传》看来,能够生的东西就是天。《易传》明言:“天地养万物”[11]249,“天地之大德曰生”[11]606。“天”最大的品德就是生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11]6,万物在天化生之中获得本性。简言之,《易传》以为,“性”根源于天。《礼记》也说:“天之生物”[12]807,“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12]555,“天命之谓性”[12]798。意思是说,天能生物,同时给人以“性”。或者说,在《礼记》看来,天道在人便是“性”。
两汉儒家普遍站在宇宙论视角下讨论人性问题。在董仲舒看来,“天”是万物的根源,《春秋繁露》载:“万物非天不生”[13]410,“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13]34,“天之为人性命”[13]61。天生万物给人以性,这便是“天性”。据《白虎通义》载:“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14]216,“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14]93,人性是由天所赋的。然而,人性是万物之中最为尊贵的。人之所以是万物之中最高贵者,因为人天生含有五常之性。也就是说,人天生具有道德属性。扬雄则将人性视为玄的产物,而“玄”与“天”的含义具有一致性。“玄,浑行无穷正象天”[15]1,“天之肇降生民”[15]337,“一生一死,性命莹矣”[15]255。天生育万物,人最为高贵。东汉王充继承了这种观点,正如《论衡·祀义》载:“夫天者,体也”[16]206,“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16]142。王充认为,天是有形体的且具有物质属性,万物皆出自天,人性亦是如此。这便是“性命在本”[16]54。
综上,早期儒家以为,初生所具有的东西便是“性”,而能够生的东西便是天。所以,“性”即天性。
三、“性”与“气”
在古人看来,天之所以能够生,是因为气。“气”是生命体能够存在的最终依据,这是早期儒道两家的基本立场。庄子以为,气之聚散与生死存亡密切相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7],表明气是化生万物的材质。儒家也持这种立场,孟子以为,物质之气充满人的身体,“气,体之充也”[8]230。荀子甚至将“气”视为万物的本原,“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0]127也就是说,气是构成生命的质料,万物皆是气的产物。
气不但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且与人性有关。孔子将血气与人的道德相挂钩,发明出“戒”的工夫,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8]172“戒”是克制血气之弊的武器。郭店儒简《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9]136认为人性含有某些气。孟子将“性”视为致善之气,“浩然之气”即“(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8]231,浩然之气是仁义的本原,扩充壮大便是仁义。荀子与之相反,认为“人之情,欲是已”[10]298,“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10]375,“争则必乱,乱则穷矣”[10]117,“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10]329。情欲是构成人性的材料,属某种不良之气。人天生喜欢追逐利欲,容易致使情欲之气宣泄,引发混战走向禽兽之道。所以,荀子提出“治气养生”[10]14。就先秦儒家人性发展史来看,性含气。孔子并未对此作出善恶属性识别,孟、荀两位各执一端,或以为“性”是善气,或是恶气,各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
秦汉之际的《易传》《礼记》表现出将孟、荀二子综合的倾向。《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11]571,“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11]569。生生之物,开始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物质,它是物生存的开始,“与天地相似”即天生之以“性”。气就是构成人性的材质。然气有阴阳之分,且二者并非对等,如《易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1]108。《易传》将阳气视为尊贵的、善的东西,将阴气视为卑贱的、恶的东西,且认为阳气引发刚健之德,阴气容易逸于情欲。也就是说,《易传》是以阴阳论“性”之善恶。在《礼记》看来,“天地不合,万物不生”[12]759,“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12]555。天与人皆由气所构成,而人之气又源于天。而气则有积极的方面,亦有消极的方面,人身上的气亦如此,这便是“人利”和“人患”[12]310。其中,“人利”属于阳气作用的结果,而“人患”则阴气造成的。所以,人情自然兼具善恶之质。既然人情是人性的表现,推而论之,《礼记》的人性自然持善恶兼具说。总之,与先秦儒者相比较,秦汉之际的儒者普遍将阴阳二气视为构成人性的材质,并且开始呈现出以阴阳讨论人性或善或恶的倾向,这为两汉儒家阴阳性情说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两汉之际以“阴阳之气”讨论人性成了学界主流。董仲舒以阴阳二气定义人性,据《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载:“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13]296,认为天有阴阳二气,人身上也有这两气,且“阳气仁而阴气戾”[13]327,阳气使人仁爱,阴气使人贪戾,它们共同存在人性之中。《白虎通义·情性》延续了董仲舒的思想路线:“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14]381,并且引用《钩命诀》说:“阳气者仁,阴气者贪”[14]381,以为人禀阴阳之气而生,气有阴阳之别,故性情有善有恶。在扬雄哲学之中,“玄”被视为与“元气”相等同的范畴,以为“一阴一阳,然后生万物”[15]351,“阳气蕃息,物则益增,日宣而殖”[15]42,“阴气章强,阳气潜退,万物将亡”[15]144。玄以阴阳之气化生万物,人禀阴阳二气而生。其中,阳气是积极的东西,阴气是消极的东西,人性自然是善恶兼具,这便是他的性善恶混说。在元气自然论的基础上。王充以为,万物皆禀元气自然而生。《论衡》载:“人禀气而生”[16]48,“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16]81。意思是说,禀赋元气多的人就善,反之,禀赋元气少的人就恶。可见,王充认定,性之善恶取决于禀赋元气数量的多寡,性即气。
综上,“气”与道德密切相关,且逐步演变为构成人性的物质基础,性是天生的,它含有气。这似乎是早期儒家学人的另一种共识。
四、“性”与“材”
“性”与气相关,“性”即气,而气具备物理性特点,故“性”乃某种物质。
“性”即材,这是先秦两汉儒者共同的观点。孔子以为,“性”乃是材质,“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8]127,“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8]106。无论是矜持还是直率,抑或放荡或者愚笨、迟钝等等,这些都是人性之材的表现形式。郭店儒简《性自命出》指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9]136,“及其见于外,则物之取也”[9]136,“凡动性者,物也”[9]136。“性”是具有材质意义的气。然而,它是由不同种类的气所构成的,它们能够趋向善,亦能够趋向不善,而导致材质呈现不同的原因在于外物的刺激。故“性”即质料。孟子以为“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8]328,“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8]331人性之材料兼具两方面的含义,从静态的角度说,人性是一块好的材料,人天生具有善的资质、质地,这种材料便是人天生的善良品质;从动态的角度看,这种好的材料能够展现为某种能力,呈现为某种善的行为、积极的举止。所以,孟子提倡对材质进行养育、扩充。荀子也将人性视为一种材质,“性者,本始材朴也”[10]313,“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10]379。在荀子看来,“性”是原始的材料,它存在缺陷,需要对其加工和雕琢,这个过程便是教化。

两汉时期以材料论“性”的做法更加明显。董仲舒提出:“性者,天质之朴也”[13]313,“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13]291,“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若四时之条条然也。夫喜怒哀乐之止动也,此天之所为人性命者。临其时而欲发其应,亦天应也,与暖清寒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13]463。“性”是质朴之材,并且生来固有的,即阴阳二气。《白虎通义》云:“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14]381且引用纬书《孝经钩命诀》的解释说:“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14]381人性是由阴阳二气所构成的质料,其中“性”是积极的材料,而“情”则是消极的材料。所以人性是善恶相混的。扬雄汲取了这种观点,认为“一阴一阳,然后生万物”[15]351,“一生一死,性命莹矣”[15]255,“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19]性即气,气即物,所以性即物。王充以为,“阴阳之气,天地之气也”[16]732,“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16]877,“气若云烟”[16]776,“气若云雾”[16]999。阴阳之气即是天地之气,它们是人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气,是某种有形状的材料(类似云烟一样)。所以说,“性”乃是具有数量属性的物质、材质。
综上,“性”是具有物理性的材质,这便是“性”与“材”的关系。
五、“性”与“质”
“性”是某种材质。古人以为,材质具备“质”(属性)的特点。
“性”即性质,始于孟子。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8]369,“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8]293,“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8]237。人天生具有两面性,即“欲望”和“四端”。其中,欲望是人和禽兽所共有,而“四端”是人类所独具的。在孟子看来,“四端”具有普遍性,圣贤和小人皆具此物,“四端”是仁义之本,扩而充之便为仁义,同时仁义的本原与气有关,气是善良之气(如浩然之气)。也就是说,孟子首次对构成人性的材料(气)做了区分。荀子则以为,人性是一块坏材料,它是由情欲构成的,无论圣人还是小人,皆有情欲,且情欲无止境,也难以满足。《荀子·正名》曰:“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10]368荀子认为,情欲甚至成为生死之异的标识,只要是生物便会存有欲,反之,无欲者则不是生物。换言之,情欲具有规定性的意味。荀子以为,情欲的实质乃是人天生本有的致恶之气,所以强调“治气”[10]14。天生之气需要约束和寡淡,才能避免走向邪恶。
在《易传》看来,万物皆是阴阳交合而成,人性亦是如此。“成之者性也”[11]571,“性”是成之者,故它必然包括阴阳二气。《礼记》以为,万物皆是阴阳交合的产物,同时与其他物类相比,人身上又含有“五行之秀气”[12]311。到了两汉时期,学者普遍将人性视为具有规定性的物质。董仲舒提出:“性者,质也。……性之名不得离质。”[13]292“性”具有质的特点,脱离了质的属性不足以谈性,认为“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13]299。意思是说,具有质的属性的材质便是阴阳二气。《白虎通义·性情》载:“性者,生也”[14]381,“人禀阴阳气而生”[14]381,“魂,……少阳之气,……魄者,……此少阴之气”,而“精者,……太阴施化之气也。……神者,太阳之气也。”[14]389阴阳二气是人生存之本,即是“性”。王充以为,万物皆是元气化生,而元气中又有特殊类别,比较恶毒的事物是由毒气、太阳之气而生,《论衡》载:“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螫”[16]954,人是五常之气凝聚而成的,认为“(人)含五常之气也”[16]875,“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残则受仁之气泊,而怒则禀勇渥也。仁泊则戾而少慈;勇渥则猛而无义。而又和气不足,喜怒失时,计虑轻愚,妄行之人,罪故为恶。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酒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麹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麹蘖,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16]80。特别是圣人、祥瑞、嘉禾又是和气的产物。《论衡·感类》曰:“夫天地气和,即生圣人。”[16]812气乃是决定人、物属性的物质。
综上,人性决定人之生存,它是人之为人的决定者。儒家论“性”的这种意识自从孟子开启后,逐步成为儒家论“性”的主流以及学者论“性”的基本立场。
六、“性”“心”“情”“欲”与“命”
先秦两汉学者谈“性”的时候,还常常捎带“心”“情”“欲”与“命”等范畴。
首先,就“性”“情”和“欲”的关系看,在孔孟那里,“情”更多地是质实、真实义,指的是事物的实情、本来的面貌,“欲”则是指人的天生感官本能。《论语·子路》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8]142,“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8]191,“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8]70,“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8]70。《孟子·滕文公上》云:“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8]261,“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8]293,“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8]331“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8]328,“好色,人之所欲”[8]303,“养心莫善于寡欲”[8]374,等等。郭店儒简指出:“情生于性,……欲生于性,……爱生于性,……子生于性,……喜生于性,……恶生于性,……愠生于性,……惧生于性,……智生于性,……强生于性,……弱生于性。”[9]227人情有欲、爱、子、喜等多种,这些都是源自于人性的东西,即情生于“性”。荀子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10]369“性”是天生的东西,情是初生者的本质,而欲是人情的反映。这种关系模式深深影响了《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12]547,“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12]310。人性生来的状态是“静”(“未发”)的,这是人的天性。人出生之后便会受到外物的诱导,进而人性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它们是“性之欲”(“已发”),而“性之欲”有七种,比如好、恶、喜、怒等,它们都是天生的。这些“性之欲”要受到一定程度的节制,否则就容易导致天性的毁伤。所以《礼记》提倡“治人情”[12]317。到了两汉时期,情、“性”开始出现一种对立的模式,多数学者以为,“性”是属于正面的、积极的东西,而情则是负面的、消极的东西。董仲舒说:“生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13]299以阴阳论述性情,性情源自于天,天有阴阳之别,天“贵阳而贱阴”[13]324。所以,就会造成“性”阳而情阴。也就是说,阴气需要约束和节制,否则就会引起祸乱。这便是“节之而顺,止之而乱”[13]329。从阴阳之气的来源看,“天地之气,合而为一”[13]362。阴阳二气皆源自天,反映在人身上便是“性”、情。也就是说,“性”、情二者都是天的产物,它们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性情即天之性情。
其次,就“性”和“心”的关系看,孔子“治血气”[8]172的工夫便已经暗含了心、“性”关系的萌芽。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指出:“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9]136,“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9]136,“及其见于外,则物之取也”[9]136,“凡动性者,物也”[9]136,“物之势者之谓势”[9]136。心是人接受外物刺激的触发点,心受到外界刺激诱发性的展开,“性”的呈现便是情。而孟子将人天生固有的四种心(“四端”)视为人性,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8]237,从而开启了儒家以心言“性”的局面。荀子则认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10]267,“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10]379,“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10]375。心能够指导人的行为活动,但是它同时存在缺陷和弊病,即人心天生喜欢利欲,放纵人心便容易引发情欲,从而导致一系列的恶果。《礼记》以为,天受人以“性”,外物诱导人心,“性”便表现于外,这就是情。然而心有积极和消极两类,《礼记》载:“怵惕之心”[12]699,“肃敬之心”[12]344,“鄙心”[12]858,等等。人之好恶集结于心。所以,由心而发的情也有两方面内容,这便是“人利”和“人患”[12]310,即人性、人情兼具善恶之质。两汉的学者也大多数持这种立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身有情欲栣”[13]296,“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13]293。“栣”是心的功能,而心能够引导人身上气的走向,而性情本身即气,所以,心的功能表现为对“性”或气的统率。
最后,就“性”与“命”的关系看,孔子以为,“性”有时可视为“命”。《孔子家语·本命解》载:“一阳一阴,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于此也。”[20]郭店儒简有时将“命”视为原始生命,“有天有命,有命有性,是谓生”[9]207,生命是生存的发端,同时也是人性的起点。自从孟子开始,“性”和“命”两者才开始得以系统性探讨,孟子创造性地提出,人能够自身所把握的东西是性,而不能把握的东西是命。而荀子则说“制天命”[10]274。天命表现为天所给予人的东西,即人的感官、心知、形体、情感等,这些东西属于人天本有的,荀子将其称为“性”。但荀子以为,人天生具有恶端,而“制天命”更多体现的是对原始人性进行锻造。到了两汉时期,“命”开始更加倾向于原始生命、寿命、命运等义,且与气的关系更加紧密,《春秋繁露》曰:“人受命于天”[13]34,“命若从天气者”[13]317。“命”就是天之气在人身上的呈现。或者说,命含气。所以,《春秋繁露》倡导“气多而治”[13]452。爱护身体就是养气,也就是养命。后汉王充认为,“受命于天,禀气于元”[16]1011。命是禀气而成,命即气。“性命俱禀,同时并得。”[16]125命、性两者同时禀气而成,不存在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便是“用气为性、性成命定”[16]159。王充还认为,“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16]99,“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16]20。人的吉凶、福祸、富贵、贫贱都是“命”,并且它们是偶然而成的,而非天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性善的人或禀有凶命,性恶的人或禀有吉命,这便是“性与命异”[16]50。可见,儒家性命关系在王充这里变得错综复杂。
综上,就早期儒家哲学发展的历史看,“性”始终与“心”“情”“欲”“命”等范畴纠缠着,并且儒家人性论逐步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