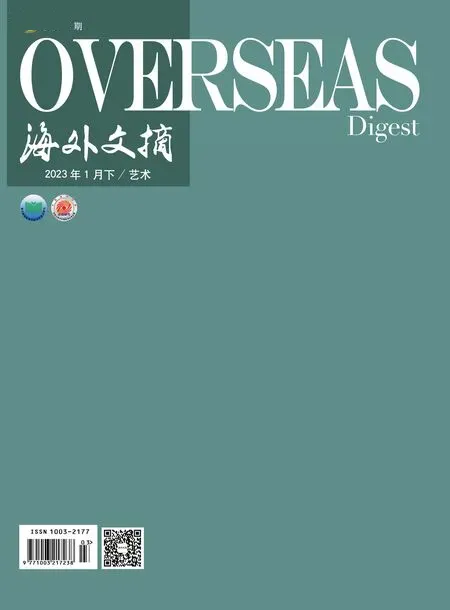《天平之甍》小说中的大唐形象
2023-09-16张迪
□张迪/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代表作家井上靖(1907-1991)因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创作了许多有关中国题材的小说。1957年出版的《天平之甍》是井上靖第一篇长篇历史小说,是代表其正式由流行作家转为历史小说作家的重要作品。小说以大唐为题材,主要讲述了作为遣唐使的日本留学僧们不远万里来到大唐,希望求取戒律师回日宣扬佛法的故事。
井上靖在小说中通过留学僧的眼睛,向读者展现了大唐的风土人情,描绘出他想象中的大唐形象。其实,所谓的大唐形象是作者受集体想象的制约而创造出的“想象中的大唐”,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认知。
研究小说中呈现的大唐形象为何,既有助于了解作家在作品中体现的个人认知,也能够进而窥视二战后日本的社会观念与民族意识。基于此,本文探究小说中呈现的大唐形象,分析作者如此创作的原因,分析井上靖在言说“他者”的同时是如何讲述“自我”的,以期为读者和学界深入了解该作品提供思路。
1 繁荣与衰败:矛盾又合理的大唐形象
《天平之甍》以遣唐留学僧的一员普照视角为主要视角,以天平四年(公元732年),日本圣武天皇决定派遣遣唐使第九次出使大唐为背景:经过慎重的选择后,朝廷决定派遣荣睿、普照、玄朗、戒融四位僧人渡唐求法并邀请德才兼备的传戒师前往日本实行戒律,完善日本的戒律,讲述了留学僧们为了能够将唐朝文化带回日本而作出巨大努力的故事,以此为背景,描写了不同留学僧在唐朝的遭遇及命运。
相比于初具国家规模的日本,当时的大唐,繁荣先进、气象万千,深深地吸引着渡唐的留学僧们,对大唐美好的想象支撑着他们克服对葬身大海的恐惧,坚定自己到唐的信念。初到洛阳的留学僧把所有自由的时间都花在观光名胜佛迹上,一边惊奇和赞叹于大唐的繁盛,一边感慨于自己国家的渺小贫穷。书上描写上元节花灯之夜:“……家家门口挂着灯笼,人人上街作彻夜之游。这期间洛阳的街衢每夜到处灯火,有吊甚多灯笼于屋轩的,有做巨大灯架或山棚把灯笼悬挂在上的。每个路口焚着火炬,在如白昼的灯火中,人们游行、唱歌、跳舞。[1]”而在初到大唐的留学僧们眼中,就连在大唐多年的日本同胞也沾染了大唐的气息,无论是气质还是行事风格都好像唐人一般。在唐十九载的玄昉本应对初来乍到的他们热情欢迎,却只是“一一询问初从日本来的年轻僧人的计划,并加以鼓励,然后在寺院内匆促地巡视了一番而去……”而另一位在唐盛名不亚于玄昉的吉备真备“由于长久的唐土生活,看起来不太像日本人,倒像唐人;肤色如唐人,连眼神亦如唐人从容大方”。留学僧们对在唐日本人的印象,实际体现了他们内心对唐人的想象,结识在唐同胞后产生的心理落差,也代表他们在接触唐人后产生的自卑与向往心理。
但大唐的无限繁华并没有迷失留学僧们的双眼,一向清醒的戒融就敏锐地发现了这强盛的国家下暗藏的衰败景象。戒融在与普照交流时说道:“来到大唐之后,首先看到的是饥饿的百姓,你不也看到了?在苏州时每日见到的就是饥饿的难民,真是看腻了。”饥荒让初到大唐的戒融直面了大唐的真实景象,认识到唐土上如同白云黄河般流动的难民人潮之中,也存在着佛陀的教训。而对于义渊门下的玄昉和行基,戒融是如此评价:“玄昉入唐后进入濮阳之寺,行基在日本走入庶民之中。玄昉学法相,行基给病者药物,为烦恼的人祷告,在没桥的地方造桥,在街头讲道。玄昉在异国学法相,究其奥义,由于才学出众,受留学国的天子赏赐紫袈裟。行基走动在乞丐、病人、烦恼的人之中,从这城到那镇,从这田庄到那村落,行走说法……所以我不知道谁伟大!”在戒融眼中,受唐朝天子赏赐的名僧固然伟大,但在日本为庶民讲法看病的行基也同样值得尊敬。戒融来到大唐后,发现唐朝繁荣外表下草民苦生的衰败景象时,并不感到气馁,反而能够从芸芸众生中悟属于自己的佛法。
这也体现了作家井上靖对中国的原始想象:就算是文化先驱的大唐也不全是一派繁荣的景象,其中也必然夹杂着荒凉的景象。这乍看矛盾的大唐形象却又无比合理,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无权无势的百姓在能目睹都市繁华的同时,又有面临饥荒的风险。同时,日本战后文学作家普遍将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割裂开来,对给自己带来文化制度的古老中国仰视崇敬,对近代中国的衰落俯视鄙夷[2]。井上靖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免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将初步形成的割裂的中国印象投射到小说创作中,小说中的大唐形象实际也是当时社会集体的想象物[3]。
2 混沌与清晰:觉醒的民族意识
《天平之甍》一书中虽对留学僧们在唐的生活均有描述,但对普照一人的着墨最多,从书中也最容易察觉到普照来唐后性格和行为的变化。在最初被选为留学僧时,天性冷漠的普照迟疑犹豫,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远渡大唐,毕竟在哪里都可以求学。而在得知去大唐是为了邀请传戒师来日,要促成此事必须要在唐待十几年才能与大师打好交情后,普照改变了自己对渡唐的态度。毕竟“既然可以那么长久地生活在那灿烂的大唐,乘上遣唐船冒险一番还算划得来”。“招请戒师有什么意义,他并不感兴趣,这十五六年间自己能学的经典数量才是重要问题”。由此可见,前期的普照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形象,虽有才学却没有为国奉献的打算,只有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才能打动他。
随着普照与其他留学僧的深入接触,普照也逐渐改变了自己处世的风格[4]。对于外表欺人傲慢的戒融,普照由最初的反感到理解他在众生中悟法的想法;对于在唐多年却一事无成的景云,普照给了他旁人没有的关注和对他葬身海底的缅怀;对于埋头抄经不见阳光的“奇怪”僧人业行,普照由最初的好奇到后来的主动帮助他运经抄经,甚至面对业行无端的责备毫不气愤;对于性情软弱却坦率的玄朗,普照由最初单纯的欣赏到最后为玄朗能连同妻儿一起回国而东奔西走;对于请戒师回日最为坚定的荣睿,普照由最初的无动于衷到后来被其精神打动,每一次普照对请鉴真渡日的事心生疑惑时,都被荣睿不屈的斗志打消,最后完成病死客乡的荣睿的心愿,成功帮助鉴真渡日。
可以说,这些留学僧对普照人格的完善和塑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书中另一位重点描述的高僧鉴真也对普照人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5]。在普照、荣睿最初邀人赴日传法时,与惧怕艰难海程的其他僧人不同,鉴真认定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是为了法。即使有淼漫沧海隔绝,生命何所惜,大家既然不去,那么我就去。”渡日前期坎坷颇多时,鉴真也是坚定地认为:“不必担心,好事多磨,渡日事一定相机完成本愿,唯前所准备舟船及物件不宜再用,以保安全。”必将能够实现渡日的愿望。在普照决定暂缓渡日计划时,鉴真只是说:“也好,可是随时可以再来。既然为了法,我东渡日本的决心不会改变。”不少僧人在渡日期间因病痛折磨而去世,除鉴真的弟子祥彦、思托外,其他僧人已对回避赴日表现得非常明显,普照不知鉴真是否也想放弃渡日,只知道“从那犹如日本武人、持有强烈意志的脸上,无法窥伺其藏在内心的意思”。第十次遣唐使返日时,渡日时机终于成熟,而此时的鉴真“两眼虽失明,却了无阴沉的感觉,原有严厉如古武士的风貌变得更为从容,使六十六岁的鉴真的容貌显得安静明亮”。由正面看来“虽然稳重,但仍是鉴真才有的那张意志力独特的脸孔”,此次也确实成功东渡传法。
混沌的普照只是以个人利益为驱使,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清醒的普照不再以自我获利为目标而生活,开始以国家利益为己任。这种由混沌到清醒的过程,也象征着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与日本前期强调“自由民权运动”的个人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同,明治政府制定了保留君主实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个人被纯粹视为是国家的附属品,把人民打造为忠于国家的真正“国民”形象。井上靖以鉴真东渡为小说后期的主线,通过塑造荣睿与鉴真坚定的形象,实现了普照的意识启蒙,映射到日本从近代时期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中。
3 他者与自我:对当代社会的反思
《天平之甍》中还有对物极必反,事物兴衰的讨论,这些对于大唐社会盛极一时却又必将衰落的论说,表现了井上靖作为他者在描述大唐形象时,所展现的自我心中的思考。小说中留学僧一行人刚到洛阳,普照就询问了荣睿对于大唐的感受,荣睿回答道:“我觉得这个国家目前正处于顶峰状态,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有百花盛开之感。此后学问、政治、文化各方面均恐有衰退的可能。趁此机会,我们要汲取能够汲取的东西,犹如蜜蜂采花粉。各国都有很多留学僧来这两大都城采花粉,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后面出场的宰相李林甫、出卖军船的刘巨麟等人的命运,也无一不是在暗示大唐衰退的结局。李林甫“性狡慧,口蜜腹剑”“出身于唐宗室,由下级官吏往上爬,勾结后宫而得玄宗宠幸,蹿升宰相,正是大权在握如日中天之时,是个玩弄权术,造成日后大唐帝国腐败之因的人物”。而留学僧在唐的天宝七年,大唐虽然过着太平的日子,却又有几件大事发生:天宝五年杨太真三十岁晋封贵妃;安禄山兼御史大夫,集玄宗宠信于一身;宰相李林甫受赐天下岁贡,大臣中冤死的人渐多,“表面上天下还算太平,但已开始酝酿着日后的大乱”。而普照和鉴真归日传法后,也的确传来了唐国大乱的消息。
井上靖在小说中特意描写的大唐衰落,也是想通过他者来警醒自我。一国的衰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离散的难民,受苦的百姓以及小人的上位中可以找到日后衰弱的迹象。连世人看来无比繁荣的大唐都能有一天走到衰落的地步,那其他国家又能如何?小说创作之时正值日本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日本汽车工业等制造业初步形成技术生产体系,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时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国民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上。1955年至197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每5年就会翻一番,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6%。井上靖清楚地观察到日本社会的变化,然而看着日益繁荣的街头市井,他并没有陷入盲目的喜悦中,反而将对现在社会高度发展的隐忧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旁观者的角度观诉说大唐的兴衰,同时也是审视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4 结语
《天平之甍》中展现的社会及人物形象是复杂多面的:强大繁盛的唐朝虽然繁华,却也有衰败阴暗的一面;普照从最初的个人主义到后期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盛极必反的历史教训不仅存在于中国唐朝,也能给现在的日本社会带来启示。当然井上靖想象中的大唐有个人经历的局限性,也受当时日本社会对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割裂而视的集体想象的制约。小说中的他者形象无疑是复杂的,是对自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作者对他者的态度也有既否定又肯定对立统一的一面。井上靖在呈现“他者”的大唐形象的同时,无一不在诉说着对“自我”的审视和反思。■
引用
[1] [日]井上靖.天平之甍[M].谢鲜声,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2] 郭雪妮.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乡恋”——以井上靖的长安书写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2(5):110-115.
[3] 池慧青,於国瑛.从芥川龙之介与井上靖的中国题材文学作品探究其中国观[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3(5):103-105.
[4] 李先瑞.谈近代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三种方法——以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99-102.
[5] 何志勇.“中日友好”主题下《天平之甍》的误读与误译——以楼适夷的两个译本为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19(1):9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