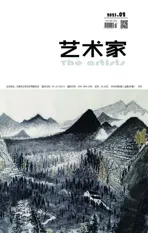张天翼《华威先生》的叙述人称与经典生成
2023-09-13张艳樱
□张艳樱
张天翼是中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大师,他以幽默含蓄、深刻犀利的笔触,描写了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社会千姿百态的众生相,接续了中国文学的讽刺传统。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不仅是张天翼的代表作,还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独特的小说结构;二是出色的讽刺艺术;三是无与伦比的真实性。这三点的形成又与“叙述人称”的使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叙述人称转换与小说结构
《华威先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作者并未采取传统小说“起因——经过——结果”的叙事结构,而是对情节进行了淡化处理,截取多个看似独立,实则有内在联系的场景,推动故事的发展。深入探究不难发现:小说中叙述人称的转换对其“片段性”的形成“功不可没”。小说每替换使用一种叙述人称,就形成新的片段。总的来说,小说叙述人称呈现出“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的变化。
(一)第一人称叙述
小说的第一个片段采用第一人称,记叙了华威先生对“我”说的三段话和“我”对华威先生的印象。华威先生为人谦逊,让“我”称他“威弟”或者“阿 威”;他工作忙碌,各式各样的会议挤占着他为数不多的时间,于是,他的包车总是在街头飞驰;他外表风雅,公文皮包、手杖、戒指和雪茄常伴于身。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在读者的心里初步建构起一个平易近人、儒雅风趣、为抗日工作疲于奔命的官僚形象。
(二)第三人称叙述
小说接下来的三个片段,均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在华威先生到难民救济会、通俗文艺研究会和文化界抗敌总会参加会议的三个场景中,“我”的形象都没有出现过,叙述者变成了一个近似全知全能的局外人,行使了观察“我”不在场的事件的特权,有的甚至是那些不可能为第三个人知道的事情,如华威先生和小胡子说的悄悄话: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我”在故事中的视域是有限的,显然,这些故事的内容不是“我”在场的时候发生的。也就是说,叙述者在叙述中将自己抽离出了“我”这个角色,以一个不肯露面的局外人的身份展开叙述。
在难民救济会上,华威先生的地位最高,会议得等他到了才能开始。可是,他偏偏坐在一个冷角落,似乎并不热衷于名利。实际上,他在暗中滥用自己的权力——不仅指定人员出任主席,还随意打断主席的汇报,凌驾于会议之上。在通俗文艺研究会上,他还未到场,会议就开始了,因此他有些不满。在文化界抗敌总会上,他全然换了一副脸面——他这次是“堆上笑容”“对每一个人点头”,还怕主席怪罪似的“伸了伸舌头”,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不难发现,在华威先生的心里有一个关于权力大小的等级序列,对待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他便拿出不同的态度。第三人称叙述能够全面捕捉华威先生的言行神态。
在以上三个第三人称叙述的场景中,虽然华威先生是见风使舵的,但不变的是,他对会议不上心、对工作不负责的态度。他总是迟到早退,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从来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不断兜售着“一个领导中心”的陈词滥调。从这三个场景可以看出,华威先生的形象和前文第一人称叙述部分中所展现的形象大相径庭。真实的华威先生不仅权欲熏心,爱摆架子,色厉内荏,而且不做实事,畏强凌弱。
(三)第一人称叙述
接下来,第五个场景的叙述又回到了第一人称,“我”的形象又一次显现了: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叙述者通过“我”与华威先生太太的对话,为华威先生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疲于领导抗日工作的官员。
(四)第三人称叙述
在“我”对谈话进行回顾之后,叙述者再次使用第三人称,又一次以近似全知全能的视角创作了一个新的片段。这一次,战时保婴会并没有邀请华威先生领导工作,可华威先生竟主动找上战时保婴会的负责人,先是隐晦地讨要领导权,又列举种种风险来威胁负责人,使自己成为战时保婴会的委员。这一次,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摧毁了上一场景中塑造的华威先生形象——华威先生并不是淡泊名利却不得不领导工作,而是权欲熏心,有想要攫取一切抗日活动领导权的强烈欲望。
(五)第一人称叙述
在最后一个场景中,叙述者再次回到了第一人称叙述,以“我”的见证的视角再次截取了华威先生的一个人生片段。和上一个场景一样,日本问题座谈会也没有邀请华威先生参加,可是,华威先生这次没能如上次一般占据上风。青年学生们毫不留情地揭开他“抗日”的幌子,直接向读者点明:“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华威先生“嘴唇在颤抖”“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与他对待战时保婴会的负责人时用“食指点点对方的胸脯”的气派判若两人。在最后这个场景中,叙述者借学生之口对华威先生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和前几个场景一起,较完整地展现了华威先生的形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叙述者不断转换叙述人称,书写多个不同的片段,每个片段又各有侧重,展现出华威先生不同的面目。叙述人称的每一次转换,不是确立华威先生的形象,就是摧毁先前所确立的形象,在不断的“确立”与“摧毁”中,华威先生的形象愈加丰富,小说的结构愈发完整,讽刺的意味更加鲜明。
二、叙述人称转换与讽刺艺术
讽刺可以是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通过外貌、动作、语言描写,赋予叙事对象以丑陋的外貌言行,如《阿Q 正传》中阿Q 被审问时的场景:“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阿Q 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乘势改为跪下了。”又如《围城》中刻画韩学愈的太太:“虽然相貌丑,红头发,满脸雀斑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而举止活泼得通了电似的”。无论是骨子里深深烙上奴性的阿Q,还是相貌极端丑陋的韩太太,鲁迅和钱锺书分别以一种带刺的笔调直截了当地对笔下的人物进行嘲弄。但讽刺不一定非要对叙述对象采取直观上的挖苦,亦可在表里不一的言行中使对象暴露本来面目,以讽刺他们不堪的灵魂。《华威先生》即是如此,张天翼并没有直接丑化华威先生,只是平静地叙写下华威先生的所作所为,使矛盾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达到讽刺的效果。
在第一个场景(第一人称叙述)中,华威先生对“我”说他的时间总是不够支配的,单单最近的,就有县长公余工作方案、集会、文化抗敌总会等会议等着他参加。而“我”对华威先生的印象,则是他的黄包车总是跑得顶快。此时,华威先生留给读者的印象是工作忙碌的抗日知识分子。然而,叙述者紧接着就跳出“我”的视域,运用第三人称,客观地叙述了华威先生工作的真实状态。每一场会议,华威先生都迟到早退,从来没有终席。不管参加什么会议,他的发言只有相同且空洞的两个要点——加紧工作和认定一个领导中心。即便有同志找他解决实际具体的问题,他不过是敷衍搪塞过去罢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内容较主观,第三人称叙述的内容较客观,前后内容显而易见的矛盾,使华威先生为自己所立的“人设”倒塌。
在第四个场景(第一人称叙述)中,通过华威先生太太的诉苦,叙述者为华威先生树立了一个不愿却又不得不领导抗日工作的形象。紧接其后,叙述者采用第三人称,记叙了华威先生是如何威逼他人获得领导权力的。即便华威先生夫妻二人用“苦恼”的说辞来掩盖,但华威先生拥有强烈领导欲的实质还是在他的言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不难发现,叙述人称的转换为人物性格矛盾的塑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这一组矛盾中,第一人称叙述那部分是华威先生的表象,第三人称叙述那部分是华威先生的真实面目,人称转换前后虚伪和真实的对立,将华威先生虚伪贪权的性格特征揭露得淋漓尽致。
《华威先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精简而锋利,这可以归功于《华威先生》中叙述人称的转换。《华威先生》叙述人称的转换如同作者为读者设置的指示器,叙述人称转换前后,不同视点制造了信息差,使华威先生的言行看起来漏洞百出,极具讽刺意味。
三、叙述人称转换与真实性
从1937 年到1938 年,抗日战争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时任湖南抗敌总会宣传委员会委员的张天翼对部分打着抗日幌子争权夺利、不做实事的国民党官僚十分不满。有论者指出:“张天翼加入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行列之后,一贯地强调文学要反映真实的社会人生。‘写真实’正是他在小说创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所在。”除了人物和题材的真实之外,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结合也增强了《华威先生》的真实性。
小说开篇这样写道:“拐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者,还是小说中的一个角色,照此来看,小说运用的叙述视角是“内聚焦”。但实际上,“我”在华威先生的故事中只是一个旁观者,和故事的发展几乎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小说运用的叙述视角更接近“外聚焦”。在读者看来,“我”是华威先生生活的见证者,是他身边的人。用第一人称“我”叙述,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使读者相信华威先生的形象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
《华威先生》中,无论是第一人称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都是站在故事外来叙述华威先生的。他不曾深入华威先生或其他人的内心,也不曾借“我”的身份发表自己对华威先生的看法,只是单纯地对场景进行描述,这就将叙述者的意图和情感隐藏在了冷隽的叙述中。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弥补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空间狭窄的弱点,有利于精准地找出矛盾,聚焦于华威先生表里不一的言行、态度,揭露掩盖在表面现象下的实质。
总的来说,《华威先生》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都有助于增强小说的真实性,不仅能使读者信任华威先生确有其人,还凭借对其言行举止的生动刻画使华威先生这一形象更具体、形象,富有真实感和讽刺意味。《华威先生》生动地绘写了华威先生这个“做戏的虚无党”的面目,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了真相,直击社会痛点和国民弱点,不仅有社会的真实性,还有历史的真实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讽刺名篇,有强大的生命力。
张天翼的作品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叙述人称,而是交替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华威先生》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交替使用是小说的显著特征,在故事结构的推进、讽刺效果的达成和真实性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塑造华威先生这一混迹于抗日文化阵营中不干实事、虚伪贪权、见风使舵的小官僚形象“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