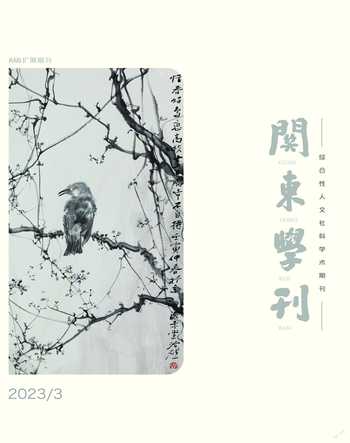臧克家关于丁力的佚简、题词辑考
2023-09-11刘竺岩



[摘 要]臧克家关于丁力的佚简、题词展现了二人晚年相近的文学观念,从中可见朦胧诗论争后反对一方的话语延续与诗歌流派建设构想。丁力去世前的三通佚简更能反映丁力遗作的创作与发表情况,相关诗作展示了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临终时的乐观心态与知行合一的豪迈诗风。臧克家、丁力晚年诗论的价值也在这些散佚文献中有所体现,即相关诗论与公木、贺敬之等“第一代”诗人的观点合流,在融合新旧体诗的同时推动了新格律诗的发展,也在精神诉求方面与朦胧诗论共同彰显了诗歌现代性的两个侧面。
[关键词]臧克家;丁力;佚简;题词;诗论
[基金项目]2022年度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中长期研究培育项目“新文学重要作家手泽研究”。
[作者简介]刘竺岩(1996-),男,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臧克家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臧克家致丁力的书信九通、在1998年丁力诗歌学术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一篇,以及致丁力之子丁慨然的书信一通。
丁慨然,诗人,丁力之子,原名丁楷,笔名丁慨然,又作丁楷然。致丁力书信数量在《全集》所有通信人中允称多者,其时间跨度自1962年7月至1987年7月,足见二人交游之密切。笔者近期在查阅“新诗民族化”的相关资料时,发现了臧克家致丁力的书信三通(其中一通有手稿影印件)、致丁力家属的书信一通、致丁慨然的书信一通、赠丁力的题词两件(有手稿影印件),以及赠丁力父子的书名题签若干。新见的书信与题词,查《臧克家全集》均未见收,当系散佚之作。尤其是书信,都写于1990年代,涉及对丁力的整体评价,不仅对《全集》有裨补之效,更为探究臧、丁交往及二者在文学思想上的亲缘关系有所助益。同时,臧克家是卓有成就的书家,本文重新披露数件不常见的臧克家手迹,无疑是有益的。
2023年是丁力逝世30周年,但关于他的研究论著至今并不多见。除各类作家辞书、方志外,唯古远清《中国当代诗论50家》(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潘颂德《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专章详细探讨丁力。但两书出版时,丁力尚在人世,正在不断发表关于诗的见解。当时既未“盖棺”,当然也就无法做出整体“论定”了。丁力逝世后,除回忆文章外,他也仅出现在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文学史叙述与少数期刊论文中。故而关于丁力的探讨始终未臻详尽。丁力在中国当代诗坛中并非无足轻重,老一辈诗人如臧克家、公木、贺敬之、邹荻帆等都对其推崇有加,无论其诗、其思,均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从被人忽视的文献中发掘丁力生平,进而考察臧、丁二人晚年诗论的价值,亦属本文的目的之一。
一、朦胧诗论争的余音
臧克家与丁力都是朦胧诗论争的主要参与者。前者是新诗研究者所熟知的,后者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形象较为单薄,应先做一简要介绍。丁力(1920—1993),湖北洪湖人,诗人、评论家、学者,1955—1957年任《文艺学习》评论组组长,1957—1964年就职于《诗刊》,历任编辑、编辑组长、编辑部主任,自此与臧克家成为密友。新时期以来辗转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兼任《诗探索》副主编。著有诗集多部、评论集《诗歌创作与欣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及诗评、学术论文多篇,主编有《毛泽东诗词大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清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93年丁力去世后,臧克家为他題词“人不在,业绩永存”,
丁楷然、蔡诗华编:《高大的银杏树——丁力研究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封四。并致信丁力家属,表达悼念之情,全信照录如下:
丁力同志家属同志们:
得到丁力同志逝世的消息,我很悲痛!丁力同志,与我几十年相交,情感深厚,志趣相合。他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好友;文坛上失去了一位老作家。丁力同志,是诗人,评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五十多年来,为文学事业,呕心沥血,丁力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文学方面,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刻苦努力,奋勇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赤胆忠心,令我钦佩。晚年,在病中,主编了《毛泽东诗词大辞典》,刚刚出书,他就去世了。人不在,业绩永存!希望家属同志继承丁力同志遗志,节哀珍重,为四化大业,作出贡献。
臧克家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臧克家:《丁力和丁力的诗》,丁楷然、蔡诗华编:《高大的银杏树——丁力研究纪念文集》,第550页。
信中,臧克家首先提及与丁力的友情。臧克家自1957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与丁力在该刊任职时期基本重合。时任《诗刊》编辑的白婉清曾回忆,臧克家多病,在编辑部工作“一天就出来几个小时,有时候会只能开一半”。故期刊编务很大程度上要靠编辑部主任来完成,“吕剑当时是编辑部主任。后来有沙鸥,1960年是丁力”。
连敏:《重返历史现场——吴家瑾、白婉清、郑苏伊、尹一之、闻山、王恩宇访谈》,《诗探索》2010年第3期。这说明,从1960到1964年底《诗刊》停刊,丁力一直以编辑部主任身份代臧克家行编务工作,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
除友情外,臧克家所谈的另一个重点是“志趣相合”。二者同为诗人,皆擅评论,这是容易理解的。但“奋勇与不正之风作斗争”之所指,显非友情、志趣所能概括。所谓“不正之风”及相关“斗争”,要从朦胧诗论争说起。1979年,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引入,拉开朦胧诗论争的帷幕。其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以“三崛起”站在朦胧诗人立场上;
“三崛起”指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与之相反的观点以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为首,臧克家、丁力等继之。在讨论中,臧克家《关于“朦胧诗”》与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足以概括他们的观点。臧克家书信中的“不正之风”即本出此文,他认为朦胧诗之病象有三:其一,“不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其二,“没有考虑文艺有社会功能”;其三,“晦涩”,“叫人不懂”。归结起来,是过于重视“学习外国”,从而有碍于“我们社会主义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民族形式”。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臧克家全集》第10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53页。丁力同样从晦涩难懂切入,将朦胧诗称为“古怪诗”,认为其病在于“反对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
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99-100页。归纳起来,在臧、丁的论述中,“晦涩”“不懂”“古怪”等是朦胧诗语言与形式上的问题表象,二人本质上站在现实主义与新诗民族化的立场上反对朦胧诗。相比于臧克家,丁力在这次论争中走在更前沿。他当时正在论争的核心场域《诗探索》杂志任副主编,与时任主编谢冕的观点南辕北辙。如霍俊明所论,《诗探索》的创刊号同时容纳了“探索”与“传统”两种声音,“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之间的诗学观念就有很大差异”。
霍俊明:《〈诗探索〉与“朦胧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足见这种对立的复杂性。那么臧克家重视与丁力“志趣相合”的原因就清晰可见了。
作为归来诗人,无论是臧克家、丁力还是与之观点相似的公刘、艾青,他们参与到论争中来,都带有两重目的。第一是意图在恢复“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秩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第二是任何论争都具有的共性,即在众声喧哗中掌握话语权。随着朦胧诗论争走向消歇,如洪子诚所概括的那样,“‘朦胧诗’影响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型期的地位”,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这些老一辈诗人不再出现在着眼于“新”的文学史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停止发声,事实上,他们正在不断重复并更新朦胧诗论争时期的话语。谢冕在《朦胧诗论争》的序言里总结得十分精当,“不是再无歧异,而是兴奋的中心已经转移”。
谢冕:《〈朦胧诗论争集〉序》,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第1页。这种“转移”在论争双方那里都有所体现。
朦胧诗的反对者们转向关于“国风”“乡土”的诗歌建设。臧克家早在《关于“朦胧诗”》中就提到“河北省承德办了个《国风》诗刊,他们提倡民歌体,就很受欢迎”。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臧克家全集》第10卷,第53页。他推崇的民歌体直接源自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即新诗要“精炼、大体整齐、押韵”,具体来说,须“运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句)而不流于松懈、散漫、啰嗦”。
臧克家:《精炼·大体整齐·押韵》,《臧克家全集》第10卷,第464-465页。在这个意义上,《王贵与李香香》《马凡陀的山歌》与《漳河水》是民歌体的范本。这在“第一代”诗人群体中近乎达成了共识。如公木倡导新诗向“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发展,其中“民族化”的要义就在于“向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公木:《中国新诗歌的发展道路——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丁力同样持此观点,他在遗作中将这个诗歌理想概括为“中国乡土诗”,其内涵是诗要具备“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国为乡土的乡土诗,即中国国风派诗”。
丁力:《“颁发中国城市诗优秀诗家荣誉证书”大会书面发言》,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亨辑·夏的诗》,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第6页。丁力去世后,这样共通的新诗觀也反映在臧克家致丁慨然关于创办诗歌集刊《新国风》的佚信中,具体如下:
慨然同志:
首先谢谢你两次寄来我给你爸爸的信复印件,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史料!
今天接到你12月10日信及有关材料,我嘱郑曼给你去电话,几次都未打通,现由她代笔写这封信。
你要我题写“新国风诗刊”名,写了几次都不满意。但因我体弱神衰,无力再写,就都寄上,请选用;如不合适,不用也行。
至于担任总顾问职,11月25日接到你上次信后,就嘱郑曼与你通过电话,说明我的近况,确实没有精力再承担了。五年多来,好几种病把我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行走须人扶持,无力思考问题,想写一篇短文都不可能了,从未参加过社会活动,每天要服多种药,才能控制病情。去年我出院时,协和医院大夫再三叮嘱我家属,要保护好我的身体,不能让我紧张、激动、过累。组织上还给我借来一套房子,使我能闭门谢客,安心养病。事实上,我能够保持目前的状况,已难能可贵了。几年来,不少来人、来信,要我担任社会职务,我都一一谢绝了。你了解我的病况后,一定会谅解我的。请你代向各位关心我的同志,说明我的病况,谢谢了!
握手!
郑曼问好!
克家
1999年12月15日
《诗坛泰斗臧克家的回信》,刘章、王恩宇、丁国成主编:《新国风·春》,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第1页。
所谓“新国风”,按照该刊同人的观点,是要“发扬当代诗歌的民间味、乡土风、亲切感、鼓动力”,提倡“具有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诗歌”,
《导言》,刘章、王恩宇、丁国成主编:《新国风·春》,第3页。这无疑与臧克家、丁力、公木等诗人的观点一脉相承。臧克家晚年多病,深为受邀作序、题签、担任顾问等社会事务所苦。此时他早已不堪重负,甚至不惜借屋别居,但面对“志趣相合”的诗人时,仍欣然为《新国风》数次题写刊名。可见已步入晚年的诗人仍极力尝试接续“十七年”,力图在风格层面上建构以“国风”为诗体的新诗流派。他在1990年代还为丁慨然的著述题写了“太阳魂”“中国新诗人成名作选”“中国城市文化”等书名,想必也与1983年题赠丁力“诗歌创作与欣赏”书名时一样,深怀“志趣相合”的鼓励之意。
朦胧诗的支持者们在论争后不久,就面临着“第三代”诗人的冲击,在“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激进话语中陷入迷茫。“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的抵抗主要表现在口语化方面,如李森所言,他们“面对的是‘朦胧诗’(包括‘朦胧诗’诗学中的现代主义修辞和英雄主义宏大抒情、主题抒情)‘书面语写作’模式”。
李森:《“口语诗”与百年“诗界革命”的“二元背反”诗学》,《南方文坛》2023年第2期。“第一代”诗人们也明显注意到了这种“口语—书面语—口语”的循环意味,但他们并不看重“第三代”诗的后现代特质,而是试图以“第一代”的观点解释“第二代”的衰落。如在另一篇遗作《破碎的“朦胧诗”到“朦胧诗”的破碎》中,丁力注意到“后朦胧诗”对朦胧诗的反拨,并看重其中的“通俗”,亦即“口语化”。但他对“口语化”的认识不在乎深度写作的消解,而是基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明朗清新”。他表示,“后朦胧诗也好,汪国真热也好,新乡土诗也好,现代诗也好,城市诗也好,总体都在矫正‘一桶浆糊’似的朦胧,加力避晦涩而趋清新”。丁力也敏锐地发现了“后朦胧诗”中的琐屑、庸常,但他仍以既有观点自圆其说,即“明朗的诗”未必“很深刻”,也不一定“回味无穷”。
丁力:《破碎的“朦胧诗”到“朦胧诗”的破碎》,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利辑·秋的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第123页。他的观点似乎是一种“误读”,但却如实体现了朦胧诗论争后三代诗人多元共存、在巨大差异中相互认知的独特詩歌生态。
二、丁力的晚年工作与遗诗
丁力于1983年患肺癌,术后有所恢复,仍积极投身到诗歌创作与评论工作之中。1993年3月,丁力癌症复发住院,当年6月23日凌晨逝世。依丁慨然的回忆,“父亲住院的3个月中,诗坛泰斗臧克家给他写了4封信”。
丁慨然:《银杏树老挺且直——记父亲丁力人生的最后5年》,《诗探索》1994年第4期。从时间与内容上看,其中三通书信即为本文讨论的臧克家致丁力书信,另一通暂未见,待考。这三通书信的内容当然以问候为主,但也与丁力的晚年工作及遗诗密切相关。原文抄录如下:
丁力老友:
得来函,知你因病住院。宋垒同志前几天来谈,没说到你入院的事,你身体底子壮,比称“壮夫”。你与疾病作长期斗争,想一定成为胜利者的。我已八十八岁了,外貌不老,但精神衰弱,一累即垮,会议不参加。找的人多。事情繁忙。
闻你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大辞典》已出版,我尚未见到。
克家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日
丁力老友:
上了年纪,几乎每夜作梦,梦见许许多多老朋友,21号(前夜)梦见你,健壮如牛,前天白天,心中想念你的身体情况,夜间就梦中与你欢聚了。也巧,你的来信今天收到了,你病中受折磨,我心里不好受,但你的乐观主义精神,使我钦佩,也感到慰安。你与病魔战斗了十年,我想你会成为胜利者的!
你的诗,不像是病人作的,豪迈之气,令人鼓舞,我立即打电话给丁国成同志,
丁国成,时任《诗刊》副主编。把这诗念给他听,他也说写得不错,我建议在《诗刊》上发表,他说应该这样。你听了一定很高兴!
我再过四个月多一点,就走上89岁之生命的途程了,体弱神衰,事情又甚多!
郑曼、小平、苏伊都想念你!
握手
克家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早
丁力老友:
你病中写诗,气势甚壮!愿你以坚强精神与病魔作斗争,成为最后胜利者!我出行为难,郑曼来看望你,祝你早日康复。
克家
九三年六月十三日
臧克家:《丁力和丁力的诗》,丁楷然、蔡诗华编:《高大的银杏树——丁力研究纪念文集》,第550-551页。极个别字词据手稿影印件校改。
在第一通信里,臧克家谈及丁力“身体底子壮”“与疾病长期作斗争”,即指1983年患癌及术后诸事。臧克家所言非虚,丁力与癌症作斗争,不仅局限于身体健康方面,作为诗人,诗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撑,也是他抗击疾病的精神武器。他在1983年手术后即作题为《与死神对话》的新诗,内有“我还有许多诗篇没有写,/我还有许多文章没有做”,“我像一株高大的银杏树,/根除了病虫害,/依然根深叶茂,/迎着流霞溢彩的时光,/任倔强的枝桠,/在天宇抒写崭新的春秋”等豪迈之语。
丁力:《与死神对话》,《丁力诗文选》(新诗卷),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第435-436页。在此后的十年间,丁力实现了这些愿望。他创作新旧体诗数十首,又承担了《唐诗今译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部分撰稿工作,创作热情高涨。在诗歌创作外,他还做了三件极耗精力的事。第一是前文谈及的,不断撰文延续并发展朦胧诗论争中的观点和话语,以倡导“民族化、群众化、当代化、多样化”的新诗发展道路,追求“清新、刚健、朴素、自然”的诗风。
丁力:《我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元辑·春的诗》,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第39页。第二是主编《毛泽东诗词大辞典》,这也是臧克家极为重视的工作。作为新时期以来毛泽东诗词的重要阐释者,臧克家的《毛泽东诗词鉴赏》《毛泽东诗词讲解》等著作堪称经典。丁力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大辞典》近乎穷尽式地纂辑毛泽东诗词研究论著,影响亦甚广。丁慨然曾评价丁力对该书的贡献,指出他“冒着暑热,几十次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去核查,复印资料。在与癌毒做斗争的同时,他以年迈之身,为《毛泽东诗词大辞典》的工作把关、献策,使这一工作臻于完善”,
丁慨然:《〈毛泽东诗词大辞典〉后记》,丁力主编:《毛泽东诗词大辞典》,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第1562页。其精神令人感佩。第三是着手编纂一部《著名作家、艺术家抗癌经验谈》,惜哉未果即病发,终使此书成为未竟事业。
在第二通信里,臧克家提到向《诗刊》推荐丁力病中所写的诗,对其中豪迈之气甚为嘉许。丁慨然回忆道:“(1993年)5月4日,父亲在病中吟诗,口占”,但未提及题目。紧接着又说,“5月27日10时半,丁国成来探视”,“并告诉《诗刊》要发他的《癸酉病中口占》”。
丁慨然:《银杏树老挺且直——记父亲丁力人生的最后5年》,《诗探索》1994年第4期。这个题目是丁力本人所起,还是臧克家或《诗刊》编辑代拟,已不得而知。诗歌发表出来,丁力已然作古。查1993年第8期《诗刊》,内有丁力《癸酉病中口占六首》,并标明“遗作”。录之如下:
一
仰卧病床何所思?东西南北任奔驰。依稀多少难忘事,尚有豪情似旧时。
二
一笑流光到九三,十年寿命岂新鲜!慨然吟得新诗罢,便续流光又十年。
三
我自去秋步履迟,中心感慨有谁知!等闲握得雕龙笔,且喜还能告一诗。
四
一怅平生累笔摇,诗文无数几篇豪;苍天若许延年月,会挽江河助大潮。
五
这瓶滴尽那瓶流,似此何时是个头!吾体不肥难贮水,谁身偏瘦却无油。
心怀故土诗思远,眼断南天笔意柔。闻道南方天又旱,争如将去润荒畴。
六
未知何事惹天烦,恶气横教久郁盘。将己付医春又夏,凭儿侍疾女还男。
遇邪火起三千丈,有病人图一万年。强坐于床呼扁鹊,来来为我下疑頑。
丁力:《癸酉病中口占六首》,《诗刊》1993年第8期。
确如臧克家所言,这些诗里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其中既有忆旧时不减当年的豪情,也有垂暮之年尚能为诗的喜悦。但这限于前三首,自第四首起,诗人开始感叹壮志未酬、力有不逮,怅惘之意渗透其间,与臧克家所言“不像是病人作的”出现矛盾。何以如此?要沿着第三通书信提供的线索考察。臧克家在与前信时隔逾二十日的第三通书信里说:“你病中写诗,气势甚壮。”与一位病人交流,臧克家自然不会反复纠缠于已妥善处理的作品,这说明丁力在这六首以后,又写了诗。查1994年《诗之国》创刊号,这个疑问有了答案。其中刊发了丁力遗诗共十六首,题为《癸酉病床口占》。其中前六首系《诗刊》所发,此外另有十首,当即臧克家所谓“气势甚壮”之作。第十四、十六首尤为雄壮,录之如下:
十四
莫谓疑顽老我身,此心依旧少年人!胡能迫得流光转,再使吟坛起异军。
十六
咳喘难平气已衰,回天失计复何哀。曾经癌变知生死,敢忘人间有去来。
诗笔南窗凭啸傲,声名海内任评猜。如来邀我谈玄理,潇洒西天走一回。
丁力:《癸酉病床口占》,刘燕及主编:《诗之国》(1),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丁力既有纂辑“抗癌经验谈”之意,对癌症想必了解较深。他在病发后似乎已意识到时日无多,到了总结之时。但这些自评诗绝无迟暮之感,内中满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此心依旧少年人”“再使吟坛起异军”正与丁力病中所言“战胜了癌症,还是要腾出手来,大写其诗的”遥相呼应。
丁慨然:《银杏树老挺且直——记父亲丁力人生的最后5年》,《诗探索》1994年第4期。“诗笔南窗凭啸傲,声名海内任评猜”两句,傲骨跃然纸上,足可看出丁力对其一生纵横诗坛、秉笔直书的自负之意。无论站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哪个立场,对丁力晚年诗学观怀有怎样的见解,他不断作诗、为文、组织文学活动,于一再探索中时时发展其观点,都足以令人尊敬。
至此,关于《诗刊》所载丁力诗“悲观”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诗之国》所刊十六首诗后有一“编者附记”,指出丁力遗诗改动处很多。
丁力:《癸酉病床口占》,刘燕及主编:《诗之国》(1),第160页。故而《诗刊》发表的六首诗是经过修改的版本,亦即臧克家收到的诗与《诗刊》所载有所区别。那么臧克家所见的版本是怎样的?丁慨然主编的诗歌集刊《中国诗宇宙》第二辑所披露的丁力遗诗,殆即初版本。其中第四首首句、次句作“心在诗文任笔摇,疑顽病我气犹豪”。
丁力:《癸酉病中口占》,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亨辑·夏的诗》,第9页。可见初版本气壮,《诗刊》本转入怅惘,作者开始对自身诗文价值产生怀疑。当然,对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不可能要求他一直满怀乐观心态。初版本中,第五首颈联原作“心怀故土忧思远,眼断南天浊泪流”,
丁力:《癸酉病中口占》,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亨辑·夏的诗》,第9页。其中满怀思乡之情。《诗刊》本改“忧思”为“诗思”,变“浊泪流”为“笔意柔”,思乡之切于此时化作从内心到笔端的柔情,可能是因为臧克家关于“豪迈之气”的鼓励,更可能是在缠绵病榻、自我总结后转乡愁为释然了。但无论如何,臧克家所言之“不像是病人作的”“豪迈之气,令人鼓舞”等评语是中肯的。豪迈之诗在遗诗中已逾半数,对即将走完一生的丁力来说,殊为难得。
三、臧克家与丁力晚年诗论的价值
朦胧诗与现代派小说相同步,是新时期文学摆脱“十七年”余绪,尝试文体重造、语言革新的重要表征。因此在文学史中,它们是文学代际变迁的突出反映,值得大书特书。故而对现代派小说、朦胧诗持反对意见的作家与学者,都容易被理解为陈旧、过时的。加上众多“第一代”诗人在晚年回归旧体诗,更会被看做在论争失利后“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文学现象显然比文学史叙述复杂得多,以上谈及的臧克家、丁力晚年诗论也自有其独特价值。
第一,这些诗论致力于弥合新旧体诗之间的鸿沟。臧克家晚年身体力行,创作并提倡旧体诗是众所周知的。他多次指出“新诗、旧诗,不应该是对立的”,“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臧克家:《新诗旧诗 互相学习》,《臧克家全集》第10卷,第85页。1980年代初的丁力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虽然赞成学习古典诗歌,但并不提倡写旧体诗。他早在1960年代就曾撰文质疑郭沫若提倡旧诗,到朦胧诗论争时,又将当时的诗派分为“古风派”和“洋风派”,指出前者“写旧体诗词,少数人写”,后者“照搬外国的,搞全盘西化”,
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诗歌创作与欣赏》,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4页。认为二者均不足取,应该提倡的是“国风派”,即解放体、民歌体诗。丁力:《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诗歌创作与欣赏》,第324页。这里,臧、丁二人有过分歧。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50家》中将丁力的观点概括为:“旧诗的内容再新,也还是旧诗;反过来有些新诗内容再陈旧,也是新诗范畴内出现的毛病。”
古远清:《中国当代诗论50家》,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323页。丁力曾致信作者,总体表示“此论公允”。
丁力:《丁力书信》,古远清编注:《当代作家书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7页。但到了1990年代,随着臧克家、丁力、公木等达成了关于“国风”“民族化”等的共识,新诗要与古典诗歌融合的观点被他们普遍认同,弥合新旧体诗裂隙的前提就随之产生了。臧克家此时仍在重复谈论旧体诗的优势,直到1999年还在不断为旧体诗集作序。丁力也在1993年“改口”,他表示,“臧克家同志讲新诗旧诗是‘并蒂莲’,双生的莲花,我赞成。一个诗人可以写新诗也可以写旧体,不必妄自菲薄”,“诗当然不能以体论优劣,关键是写好诗来”。他认为的“好诗”,就是具备“现实性、人民性、时代性”的诗,它们实现了“情与意的谐和统一”。
丁力:《“颁发中国城市诗优秀诗家荣誉证书”大会书面发言》,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亨辑·夏的诗》,第6页。丁力所言,当系发自肺腑,因为前文讨论的丁力遗诗,正是合乎格律的旧体诗,其中的悲天悯人之情及豪迈之气,确乎称得上“人民性”和“情与意的谐和统一”。
第二,这些诗论融入了新诗的另一脉——新格律诗,是促其发展壮大的一股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研究者将现代格律诗学追溯至饶孟侃《新诗的音节》与闻一多《诗的格律》,认为前者的意义在于重视节奏,即听觉,后者的意义在乎视觉,即“建筑美”补充了“音乐美”与“绘画美”。
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20世纪现代格律诗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69页。及至1950年代,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倡导现代格律诗,但却被认为与“群众化、民族化、民歌加古典”相冲突。
周仲器、周渡:《中国新格律诗探索史略》,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6-87页。进入新时期,在朦胧诗潮的冲击下,半格律诗、新格律诗、民歌体诗产生了合流趋势,最终统一于新格律诗一脉。如曾最激烈反对何其芳新格律诗理论的公木在1994年支持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即“雅园诗派”)成立,在“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的旗帜下,力图促使新旧体诗“合则双美”。在他的新格律诗理论体系中,臧克家那种“既近乎格律,又崇尚自由”的诗风是应该提倡的。
公木:《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首届年会开幕辞》,《现代格律诗坛》1995年第1期。公木的观点,其实正是对臧克家晚年诗论的高度总结。丁力同样如此,他写过“歌谣体詩和解放体诗,也写过旧体诗词,更写过半格律诗和口语化的自由体诗”,他将歌谣体、解放体、旧体诗词的优势概括为“容易上口,好记、能唱”,
丁力:《我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丁慨然主编:《中国诗宇宙·元辑·春的诗》,第39页。这为“国风派”所看重。尤其是丁力的解放体,在宋垒看来,殆即“从古典诗歌和民歌衍生出来的自由体”。
宋垒:《丁力与“解放体”》,丁楷然、蔡诗华编:《高大的银杏树——丁力研究纪念文集》,第335页。这说明,歌谣体、解放体新诗与旧体诗具有共通之处,它们可以共同成为新格律诗的有效资源。贺敬之也做出了相似的实践,他兼采词与新诗优长,大致按照格律,“自由地变换字数、灵活地运用长短句式,同时也不受篇幅长短的限制”,创制了“新古体词(曲)”,
贺敬之:《〈贺敬之诗书二集〉自序》,《心船歌集》,北京:线装书局,2011年,第47页。似亦应归于广义的新格律诗序列之中。可见臧克家、丁力的晚年诗论是“第一代”诗人集体转向的组成部分,最终推动新格律诗自成一派,至今仍不断发展。
第三,这些诗论与朦胧诗论其实有共通之处,它们都彰显了新时期初诗歌的现代性诉求。作为曾经的“论敌”,谢冕在回忆丁力时仍难掩赞美之意:“诗人时时刻刻和时代保持血肉联系,具有时代氛围、情调、品格,是非常可贵的。”
谢冕:《关于丁力》,《文化月刊》1998年第10期。丁力无疑把握住了新时期关于历史反思的时代氛围。他作于1970年代的数十首歌谣体、格律体、自由体诗,就在“含泪的笑”中近乎超前地把握住了反思的时代思潮。故而在结集为《俯首吟》出版时,臧克家为之题词,抄录如下:
感情真挚,字句朴素。敞开胸怀,坦露心腑。
题丁力诗友的《俯首吟》
臧克家
一九九〇年二月丁力:《俯首吟》,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扉页。
这种真挚的感情反映在丁力的诗论中,就是“诗要真”,即“真话不一定是好诗,但好诗一定要说真话”,“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感情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言不由衷。这种诗,读者是摇头的”。
丁力:《新、真、深、精》,《诗歌创作与欣赏》,第18页。臧克家也在《关于“朦胧诗”》中倡导诗歌站在时代前列、反映人民心声。
臧克家:《关于“朦胧诗”》,《臧克家全集》第10卷,第52页。那么,谢冕是怎样表述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开篇即指出,“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第9页。故而需要“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第12页。无论丁力、臧克家还是谢冕,都像他们的共同友人徐迟所论,要实践“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文艺。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所不同的是,臧克家与丁力的现代性诉求延续并发展着“十七年”诗论,是偏于社会一维的;谢冕的现代性诉求由社会而审美,亦即要与传统对立、与启蒙理性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关于“人”的危机对立、与逐渐成为“传统”或“权威”的自身相对立。
陈定家选编:《审美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孙绍振之“新的美学原则”当然亦属此列。但不论哪种现代性诉求,都是求新求变的,均指向崭新的精神需求。所以,因为朦胧诗人的“新”而忘记归来诗人的“新”,殊不足取。
总体来看,臧克家关于丁力的佚简、题词展现了两位诗人相近的文学观念,体现着朦胧诗论争结束后反对一方的话语延续与诗歌流派建设构想。丁力去世前的三通佚简更反映了丁力遗作的创作与发表情况,彰显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临终前的乐观心态与知行合一的豪迈诗风。从这些散佚文献出发,可以发掘出臧克家、丁力晚年诗论的价值,即在融合新旧体诗的同时推动了新格律诗的发展,也在精神诉求方面与朦胧诗论共同表达诗歌现代性诉求的两个侧面。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两代人的对立是普遍现象,无论现代派论争还是朦胧诗论争,都不应简单看做二元对立的两种话语。论争内部既有冲突,也不乏共通。论争的双方也非线性更迭、优胜劣汰的,他们仍在自身观点的发展中不断突破,产生一个个文学文化现象与事件,留下值得作为镜鉴的宝贵历史经验。
谨以此文纪念丁力先生逝世30周年,同时纪念即将到来的臧克家先生逝世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