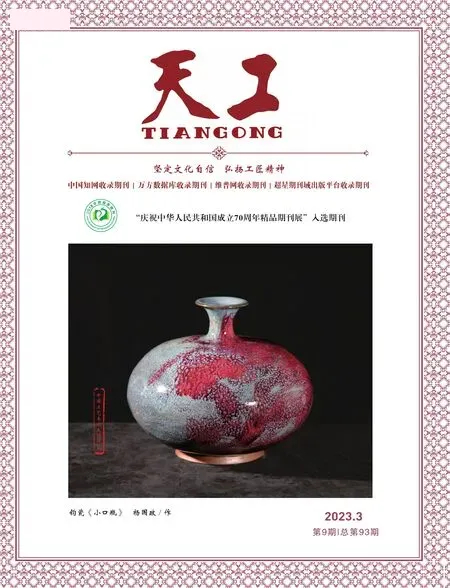科罗曼多漆屏的中国源流与外销发展探究
2023-09-08汤玉欣南京师范大学
汤玉欣 南京师范大学
科罗曼多漆屏是17—18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物品之一,但相关研究较之丝绸、瓷器等稍显薄弱。据统计,现今保存在世界各地的科罗曼多漆屏大约有250 件,主要收藏在法国、荷兰、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博物馆及画廊,少数收藏在我国的博物馆。
一、科罗曼多漆屏的中国源流
科罗曼多漆屏最初出现在欧洲大陆时,当地人并不清楚它的来源,只因从印度科罗曼多地区进口,而取名“科罗曼多漆屏”。“尽管对它们的装饰工艺有所了解,但是早期的艺术家并不知道它们有着中国血统。”有学者猜测,由于当时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多种限制,科罗曼多漆屏最初可能是通过走私的方式,从中国沿海地区运往印度。
科罗曼多漆屏的工艺手法在中国叫作“款彩”,由雕塑和彩绘两种工艺结合而成。 雕刻配以填色,是款彩工艺的特征之一。那么,科罗曼多漆屏源自中国何处?目前,说法层出不穷,福建、广东等地被提及次数较多,也有文章指出它来自中国北部或中部地区。笔者认为,可以从明清时期的漆艺大环境及工艺特征进行探讨。首先,漆器的制作通常需要气候湿润的环境,明清时期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是漆器制作的中心,扬州在这个时期发展了镶金、镶银、镶玉等技术,苏州发展了“雕漆”技法,徽州也以螺钿等工艺占据一席之地,江南地区有着较为成熟的漆器制作背景。根据扬州地方资料记录,“清代雕漆至乾隆而大盛……器物品种增多,并向大件发展,盘碗盒匣之外,还有屏风、宝座”。从今天流传的款彩屏风的数量和记录来看,款彩可能并非广泛流传的工艺技法。因此,其早期制作中心,或许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漆器工艺发达且气候湿润的江南地区。北京观复博物馆藏有一套康熙年间的花鸟屏风,是收藏家马未都从美国购得,在这套屏风的底部刻着一行字:“维扬姚某监雕填漆屏。”这里的“维扬”指的是扬州,“姚某”是监工,这位监工称这件屏风为“雕填漆屏”。这里的“雕填”同北方的“大刻灰”、南方的“款彩”同义。从地区漆工艺发展和藏品来看,尽管科罗曼多漆屏多是从广州等地传入海外,但是主要制作起源地很有可能是扬州、苏州、徽州等江南地区。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开放海禁后,福建沿海地区万商聚集,徽商在这一时期活动频繁,极有可能是他们将江南地区的款彩屏风销售给外商,而后传入欧洲。其次,通过对比分析款彩工艺,科罗曼多漆屏的发展离不开版画,它的制作过程与版画十分相似,其黑漆面的装饰底色也受到了版画黑白对比的影响。明代晚期,版画在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发展势头较好。据学者徐大珍推测,安徽博物院所藏的清代早期“汉宫春晓”款彩漆屏“从屏风漆工艺和用材分析,应是徽州漆工的作品”,将其与美国华盛顿福瑞尔艺术馆所藏的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汉宫春晓款彩屏风”进行对比,二者在图案、格局、人物、构图等方面基本吻合。至此,再一次验证了上文的推测:款彩漆屏的诞生与发展与江南地区的工艺有很大的关联性。
虽然款彩工艺的诞生地无法最终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扬州、徽州为主的江南地区或许是此类屏风的早期主要生产地,但也不排除其他地区先后制作的可能性。款彩漆屏的发展是多地工艺进步的见证,科罗曼多漆屏对欧洲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既离不开江南等地区工艺的发展,也依靠广东、福建等地的交易市场,同时更加得益于海上运输的保障。
二、科罗曼多漆屏的传播
(一)海上传播中的命名变化
科罗曼多漆屏的命名过程大体上是根据销售中转地而来,这类漆屏也被称作“班塔姆”(Bantam)或“万丹漆器”。“班塔姆”同科罗曼多一样,为地名,它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北部附近的古老香料贸易据点,17 世纪英国人在那里设有工厂,控制着印度科罗曼多海岸的设施。在《钱伯斯先生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词典(补充)》第一卷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班塔姆,印度版画的一种,雕刻在木头上……日本艺术家主要以黄金等金属为主,而班塔姆一般都是以颜色为主……”从资料来看,当时的研究学者并不清楚科罗曼多漆屏来源于我国,而将它描述为以颜色为主的、雕刻在木头上的“班塔姆”。“万丹”这一名称的由来,其实等同于“班塔姆”,如今的班塔姆虽然已成为废墟,但它的所在地位于万丹市的遗址附近。1950 年,班塔姆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为西爪哇省的一部分,并于2000 年成为独立的万丹省,因此“班塔姆”与“万丹”其实为同一地方不同时期的名称。后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班塔姆的港口被淤泥堵塞,船舶无法近距离停靠海岸,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总部转移到印度科罗曼多海岸的马德拉斯港口,又称金奈。与此同时,法国人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同一海岸的庞迪切里设立据点,由此,科罗曼多海岸成为当时我国款彩漆屏在印度的主要贸易地点,这类屏风的命名也由原来的“班塔姆”转变为“科罗曼多”。
(二)传播途径与线索
1498 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加马(Vasco da Gama,1469—1524)开辟了通往印度的航线,将包括欧洲、亚洲乃至新大陆在内的地区连接成海路。最初,漆器等商品是通过葡萄牙人销往欧洲的,我国的漆器主要由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欧洲。1608 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科罗曼多设立商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19 年和1622 年将这里当作据点。除了科罗曼多海岸,另一个重要的进出口地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西北部。科罗曼多漆屏主要是由居住在这里的我国商人和东南亚商人从国内沿海港口带到印度,之后与欧洲商人进行交易,运往欧洲大陆。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下令解除海禁,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被清政府开辟为外贸港口,并设立海关。从1670 年开始,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尝试直接与中国港口进行贸易,1672 年在台湾设有贸易站,后来在淘山、中山和广州也设置了贸易站。关于科罗曼多漆屏的外销记录,可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进货单中寻得线索。1697 年,伦敦分部要求从中国进口20 件12 屏的漆屏风,并要求屏风两边都是雕饰。同样,阿姆斯特丹发行的报纸Amsterdamse Courant刊登了当时商人进口物品的广告和物品目录,从物品目录可以看出,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 世纪后半期到18 世纪初每年都进口漆屏风。每年最少进口1 件,最多进口198 件,1687 年至1702 年大约进口500 件。也有记录显示,1696 年至1707 年间,有54 件漆屏风到达了伦敦。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官方记录没有包括走私的屏风,以及东印度公司员工个人进口的屏风,因此实际销往欧洲的屏风数量应该更多。
尽管以上的文件中并未明确指出“漆屏风”就是“科罗曼多漆屏”,但是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可以基本断定二者为同一物品。学者周功鑫认为,“可以断定当时输出的漆屏风大都是款彩屏风”;荷兰艺术史家杨·凡·坎彭(Jan van Capen)则更加肯定地认为,欧洲文献中说17 世纪的中国漆屏风,一定都是中国的科罗曼多漆屏。通过对国外博物馆中藏有的科罗曼多漆屏和我国款彩屏风的工艺进行对比,以及通过屏风背面的题字也可以确定17、18 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漆屏风就是科罗曼多漆屏。
三、科罗曼多漆屏的地域性发展
(一)装饰主题发展
科罗曼多漆屏的装饰主题,以人物为主,山水、花鸟等也有涉及。人物主题大多来源于家喻户晓的故事,比如《群仙庆寿图》《汉宫春晓图》等,这些故事常常被绘制成有叙事性的画面,而且出现频率较高。仅在现存的款彩漆屏中,就有多幅以《郭子仪祝寿图》为主题的屏风,它们在制作的细节、背面题词等方面稍有不同,如亚瑟·姆·赛克勒旧藏的清康熙年间的《郭子仪祝寿图十二扇屏》、美国电影明星霍华德·费德曼旧藏的《黑漆地款彩郭子仪祝寿十二扇大屏风》等。
后期,随着欧洲市场的需求量增大,屏风的人物主题也出现了符合销售市场的欧洲内容。在中国沿海等地制造的漆屏中,逐渐出现了欧洲人狩猎或行进的装饰场景。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欧洲人狩猎图》12 屏漆屏风描述的是欧洲人带着长矛和长枪猎杀老虎、鹿、兔子和鸟的场面。画面右侧有城墙,左侧的岸边停泊着船只,可能是在城外待命打猎。关于行进的主题,丹麦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关于欧洲行进列队图的科罗曼多漆屏,画面中心是一个骑着白象的人和一支举着龙旗帜的队伍,他们朝着岸边的船行进,船上的红旗上写着“荷兰朝贡”。西方学者Tristan Mostert 解释:这幅屏风的内容描述的是来中国朝贡的欧洲人。
(二)功能发展
首先,科罗曼多漆屏的原始功能是从屏风本身出发,通常作分割空间之用,相较于厚重的博古架,它的拆装和摆放更加方便。其次,由于漆屏制作精美和价格昂贵,它的装饰作用得到了更为广远的发展。17世纪,伴随着大量中国产品流入欧洲,欧洲兴起了一阵“中国风”,当时的欧洲流行将科罗曼多漆屏风用作壁饰。人们将漆屏的两面分开,整体的连幅挂在墙上,另一面的单幅切成小块单独装饰,这样装饰的空间被称作“漆器室”(lacquer room)或者“Chinese room”,通常用作陈列异国的工艺品,如瓷器、丝绸等。据资料记载,lacquer room 最早出现在17 世纪中期的荷兰,1654 年地方总督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Stadholder Frederik Hendrik of Orange)建造了一所海牙豪斯滕博斯宫(Huis ten Bosch),其中就有一间漆器室。之后1687 年建筑师尼科·德穆斯特辛(Nicodemus Tessin)又建造了两个漆器室。现在豪斯滕博斯宫已经不见踪影,但是在1677 年12 月13日,意大利旅行家博维诺兄弟访问了豪斯滕博斯宫并惊叹于它的异域风格,“它非常雄伟、豪华,完全用中国木制覆盖,用中国式彩绘”。此外,1695 年探险家威廉·蒙塔古(William Montague)也来到了这里,“房间的壁饰是由进口的柜子和抽屉柜的装饰分离而成的”。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漆器室的装饰几乎都是分割而成的科罗曼多漆屏。如今,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还可以看到漆器室,这里展出的房间原本是荷兰北部地方总督宫殿中的一间,据传是威廉·弗雷德里克(William Frederick)的配偶阿尔贝汀公主的房间。房间的墙面用漆屏风做装饰,两面相对的墙是同一幅《汉宫春晓图》12 屏漆屏风,其余的是《西湖十景图》漆屏风。在17 世纪,以科罗曼多漆屏为装饰原料进行“中国风”房间制作的现象,从荷兰蔓延至英国、奥地利、德国等地,英国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和伯格利之家(Burghley House)也有1690年左右制作漆器室的记录。
除了用作房间的墙饰外,科罗曼多漆屏也可以用作家具的制作,这使家具的形态更加多样化,一个12扇的漆屏可以用在多个家具的装饰上。18 世纪初,法国商人马尔尚·梅西尔(Marchand·Mercier)用漆屏风制作了各种样式的柜子,它的制作方法大致为:将漆屏风的两面切开,选择需要的部分,将它们切成3毫米以下的薄片,通过技术手段使它们弯曲后附着在柜子表面,最后在周围加上被称为“Ormulu”的边饰。
18 世纪中后期,科罗曼多漆屏的进口量开始减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价格的昂贵和替代品的出现。同时,漆屏风的高度下降,大约在180 厘米,屏数也由原来的12 屏居多转为4~6 屏。这可能是因为大型漆屏风用作房间壁饰的情况逐渐减少,用作家具制作的情况增多。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更多种类的工艺品销往欧洲,其中就包括壁纸等可以替代大型科罗曼多漆屏的用品。相比大型漆屏,壁纸的运输更加方便,价格也更低,与此同时,欧洲此时也研究出可以代替中国漆的原料。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科罗曼多漆屏的销量逐渐下降,以进口为主要来源的鼎盛时代也逐渐结束。
四、结束语
虽然科罗曼多漆屏属于“中国物”的进口时代逐渐黯淡,但是它所留下的“中国风”仍继续影响着整个欧洲,并渗透到各类本土风格和装饰中。明清时期,中国的款彩屏风由海路,经过印度洋来到欧洲。中国商人在持续向海外输送中国工艺的同时,也向本土手工匠人传递着新的信息。同时,科罗曼多漆屏在欧洲本土也衍生出新的功能用法,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新气象,后续的保护研究工作也在稳步进行。双方通过艺术与工艺进行文化交流,在吸收与消化中,不断形成多元化的风格,并产生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