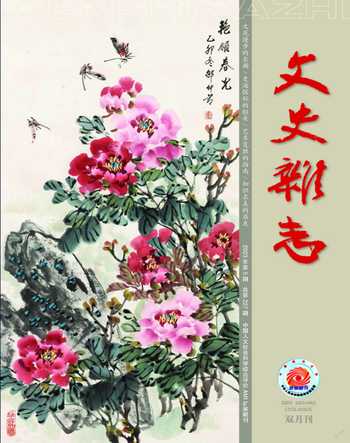百年古蜀神话研究概说(下)
2023-09-07周明
摘 要:百年来的古蜀神话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大体分作民国时期(包括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前后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时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时期、新世纪以来时期。这四个时期产生的论著和学术观点,充分地显示了以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为代表的巴蜀文化(或古蜀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在起源和面貌上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关键词: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古蜀神话研究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全国的神话研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学科建设的边缘化而陷于缓慢进行的阶段,只有极少一部分学者在坚守,其学术成果也是呈零星面世的状态。特别是在“文革”十年间,包括古蜀神话在内的整个神话研究都处于学术研究的停滞期,几乎没有发表和出版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不过,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受抗战时期巴蜀文化研究的启迪和影响,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研究传统仍在延续,古蜀神话的研究也因之得以延续。这种研究重点体现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研究和巴蜀民间文学研究两个方面,主要由生活在四川地区的学者主导完成。以吕子方、蒙文通、徐中舒、任乃强、邓少琴、袁珂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本土学者立足四川,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民间文学等角度深入地研究巴蜀本土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的相当部分涉及古蜀神话。
在巴蜀古代史(巴蜀考古)方面,四川学术界的学者们继承了抗战时期的学术传统,继续在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中巴蜀古史的可靠性、巴蜀遗物的辨认和断代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通过巴蜀地区神话色彩非常强烈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重塑巴蜀古代史,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带有强烈神话色彩的传世文献资料就成为历史学界和民间文学界共享的第一重证据。学者们力图通过传世文献资料来还原或透视巴蜀古史,客观上带动了古蜀神话的研究。
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巴蜀古代史的研究重点,是集中在《山海经》《蜀王本纪》《本蜀论》《蜀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与巴蜀有关的传世文献上,特别是集中在《蜀王本纪》《本蜀论》《蜀记》《华阳国志》等地方文献上。学者们力图通过对这些传世文献的梳理和研究,来探寻古代巴蜀史的各种问题。其中,吕子方先生写于1951年的《读〈山海经〉杂记》和蒙文通先生于1962年发表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二文,属于这一时期与古蜀神话研究关联最为紧密的研究论文。
对于记载远古神话最多的先秦典籍《山海经》,吕子方先生通过其山势和篇名南、西、北、东的记叙方式指出:“《山海经》以山为主,按左转的方向叙述,但不提东南西北,而是以南方为首位,从四川的招摇山谈起,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和线索。经文的第一卷《南山经》开宗明义就说:‘南山经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我认为一个人著书立说,总有一个重点,要是叙说地理地形,重点常常放在他所居住过的、最熟悉的地方。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就是所谓地方性或地方色彩。例如孔子是鲁国人,对鲁国情况最熟悉,他修《春秋》即以鲁国为主,取鲁国的材料最多。而《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都是按南西北东的次序排列,以南方开头,又首叙四川的山。大而言之,可以说这种排列法是南方作品的特征;小而言之,是古代蜀国作品的特征。(拙著未发表的《五天廷》一文,详细探讨了招摇山上应招摇星,是蜀国的山名。)”[30]
蒙文通先生赞同吕子方先生的说法。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多次引用吕子方先生的观点,同时通过《山海经》和《世本》所记古代帝王和神话人物的比较,认为“《山海经》是区别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的产物,代表着另外一个文化传统”[31],这个文化系统就是巴蜀文化系统。具体来说,蒙文通先生认为:“《五臧山经》不仅是以巴、蜀、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以其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32]除此之外,蒙文通先生还从水系考察入手,提出:“《海内经》不仅记载了岷江上游的小山小水,而且在《海內东经》还载‘白水出蜀,东南注江,这是《山海经》中唯一提到蜀的地方。此外,《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而其他部分却不见开明的记载,应当承认,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33]
吕、蒙两位先生对《山海经》产生地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其部分篇目出自蜀地的看法,拓宽了古蜀神话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古蜀神话的研究内容。
另一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研究中对一些流传甚广的古蜀神话进行了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在《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一文中对《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所载望帝故事时说:“望帝化为子规,是蜀人历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早已流传于中原。《说文》于嶲〔音髓〕字下云:‘嶲周,燕也……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汉魏时人称蜀人为叟,叟即嶲周的合音。后人或省称为嶲,又称为子嶲,即子规,因其为杜宇所化,又称为杜鹃或子鹃。杜宇化鹃本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许慎是经学家,‘淫其相妻不合于儒家伦常道德,所以称其‘惭,亡去。点金成铁,实在糟蹋了这个故事。李商隐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才是这个故事的正解。望帝禅让就是因为鳖令治水成功,民得陆处。说他如尧禅舜,这样解释也就可以使人满意了。但却要把惭愧德薄委国授之而去作为禅让的又一理由,这岂不是对禅让的谴责吗?”[34]
而博物馆学家邓少琴先生则从文献、文物、考古三方面结合对巴蜀史进行了大量地研究,提出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其在“文革”期间撰写的《蜀故新诠》一文侧重从个案入手进行考说,涉及不少古蜀神话,如该文“岷山是昆仑之伯仲”“蜀中传说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夏禹出自西羌石纽”“蚕丛氏之蜀”“杜宇之世蜀之振兴”“开明为蜀中治水前驱”“石棺椁与石笋”“石牛道之平治”“李冰治水”等小节,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古蜀史研究的力作,同时也是古蜀神话研究的重要成果。[35]
此外,这一时期值得重点关注的是,1960—1962年期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完成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华阳国志》作为世所公认的巴蜀地方志书,是晋代以前巴蜀古史资料的集大成者,其中大量保存了古蜀神话资料。任乃强先生在校补图注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学者的校注形式,在注释中采用了考说的方式进行,往往一条注释就是一篇短论,在很多涉及古蜀神话人物时的注释尤为详尽,如蚕丛、鱼凫、鳖灵、杜宇、开明等。[36]这种方式,对于读者深入了解《华阳国志》所记载内容及作者的学术观点,大有裨益。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袁珂先生为代表的典籍文献神话的搜集整理,在这一时期成绩最为显著。在袁珂先生的学术成果中,古蜀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
1950年,有感于茅盾先生所说“中国神话向来没有集成专书,并且散见于古书的,亦复非常零碎”[37]的现状,袁珂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神话整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这部简本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第一次将散见于文献典籍中的神话片段连缀起来,使之成为类似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的神话叙事系统,打破了国外关于“中国没有神话”的成见。该书一经面世,就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重视,短短几年间多次重印。后来,该书几经修订增幅,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神话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在《中国古代神话》第七章“鲧和禹治理洪水”第五节中,袁珂先生系统地梳理和介绍了“望帝化鹃”和“李冰治水”的神话,连带梳理和介绍了蚕丛、鱼凫、鳖灵、开明、五丁、二郎神等神话故事。可以说,这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第一次将古蜀神话进行系统地整理和推介,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古蜀神话的了解和重视。[38]
1963年,袁珂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神话故事新编》一书,其中有《含冤的望帝变做杜鹃鸟》《五丁力士拔蛇崩山》《李冰化龙计擒蛟龙》三篇涉及古蜀神话。[39]
1964年,以神话文献整理见长的袁珂先生逐漸把目光投向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他对四川中江地区搜集整理的《伏羲、伏羲,教人打鱼》《大禹治水除九妖十八怪》《杜宇变鸟》《五丁开山》等民间口传神话故事高度重视,并专门撰写了《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一文刊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上。袁先生在文中说道:“中江县并不是我们特地选择的一个搜集神话的地区,只不过是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方便,偶然进行搜集的,就已经有这么丰富了,推而至于全省全国,其蕴藏的丰富自然可想而知。这也是我们文学的瑰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40]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神话的现代传承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除此之外,袁珂先生还亲自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搜集整理了《李冰父子凿离堆》[41]《二郎擒孽龙》[42]等神话故事,并写下了大段的附记,较为详尽地记叙了蜀中二郎神话的流传和演变。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尽管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古蜀神话在内的巴蜀文化研究在整体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是还是有相当部分学者在艰难地前行。他们默默地从事研究工作并积累着能量,终于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推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三、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末的古蜀神话研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定。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至世纪末,伴随着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学术界也从十年动乱的沉寂中走出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在这一时期,原有的神话研究被激活,国外的各种神话学理论也陆续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使中国的神话研究出现了20世纪以来的第二次研究热潮。正如刘锡诚先生所说:“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从1978年起,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逐步把间断了十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43]
就古蜀神话研究而言,在第二次中国神话热的大背景下,自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和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话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一是神话作品的搜集整理。
在神话理论研究方面,有两个特点特别明显,一是老一辈学者积淀多年的学术成果得以出版面世并继续发挥余热,二是一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
从成果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古蜀神话研究仍是集中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和民族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两个方面。
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和民族史)研究方面,1979年4月,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从1981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先后编辑出版了一套“巴蜀史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徐中舒先生的《论巴蜀文化》、蒙文通先生的《巴蜀古史论述》、顾颉刚先生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任乃强先生的《四川上古史新探》、邓少琴先生的《巴蜀史迹探索》等。198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先生的《羌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尤中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史》,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汉骥先生的《冯汉骥考古论文集》。199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龚萌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继周先生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这些著作,大量采用蜀地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和口传资料,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角度对古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中不少地方都涉及对古蜀神话的研究,是我们今天研究古蜀神话的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川西考古发掘取得很多重要突破,尤其是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近千件,尤以大型青铜雕像和金杖、金面罩等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珍贵器物为奇特。[44]三星堆遗址大量文物的出土,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古蜀文化的高度关注。围绕三星堆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出土文物,学术界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主要成果“在于明确了古代巴、蜀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明确了巴、蜀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45]与此相应的是,古蜀神话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并进入不少学者的研究视野。
1983年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了全国首届《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山海经》所涉及的各种学术问题,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对《山海经》和古蜀神话的研究开始走进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阶段。
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袁珂先生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1982年,袁珂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发表《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一文,提出“广义神话”的观点,在全国神话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广义神话9个部分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古蜀神话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年,其《神话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中国神话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3年,《中国神话通论》由巴蜀书社出版。1996年,《袁珂神话论文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作中,古蜀神话被袁珂先生屡屡提及,并作为中国神话的重要案例被深入剖析。
老一辈学者之外,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巴蜀神话研究领域开始涌现。1996年,李诚的《巴蜀神话传说刍论》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一时期第一部以“巴蜀神话”为题撰写的学术著作,其中,古蜀神话的研究占了相当部分。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巴蜀神话”“古蜀神话”或蜀地少数民族神话为主的研究成果,如袁珂、岳珍的《简论巴蜀神话》[46],贾雯鹤的《巴蜀神话始源初探》[47],张启成的《古蜀杜宇神话传说新探》[48],萧崇素的《原始的探索童年的幻想——凉山彝族民间神话一瞥》[49],李子贤的《大凉山美姑县彝族神话与宗教民俗》[50],林忠亮的《试析羌族的古老神话》[51],李明的《羌族神话纵横谈》[52],李璞的《羌族神话与审美观念》[53],徐晓光、徐冰的《古羌神话与日本神话传说的比较》[54],佟锦华的《简析藏族神话》[55],李燕的《试论藏族神话中的自然历史观》[56]等等。
總体来说,由于这一时期“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的概念刚刚确立,相对来说,单纯的神话理论研究成果并不算多,很多相关研究都包含在“巴蜀文化”研究的大框架里了。
但是,在神话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这一时期的成果就相当可观了。这种搜集整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研究,它主要体现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含校译、校注、释文、整理重述等)和民间口传故事的搜集整理两大类。
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袁珂先生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古神话选释》;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山海经校注》,同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神话选译百题》;1984年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传说》;1985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山海经校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与周明合作);1998年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族神话辞典》;1991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海经全译》;1997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神话传奇》(与苟世祥合作);1999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上古神话》(与贾雯鹤合作)。这些著作基本上都属于古代文献中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成果,其中相当部分涉及巴蜀神话。尤其是《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一书专门列有“古蜀编”一章,它将散见于各类典籍中的古蜀神话资料遴选汇集并加以编排,形成较为系统的古蜀神话文献资料集,极大地方便了学界对古蜀神话的研究。
此外,刘琳先生于1984年在巴蜀书社出版了《华阳国志校注》,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古蜀神话资料的搜集和研究。
在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方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的编辑出版是这一时期古蜀神话搜集整理的突出成果。
1984年,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书,共计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多卷)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前后历时20余年。在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省政协主席冯元蔚等老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立即开展起来,古蜀神话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包含其中。当时,以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今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为主体的高校、科研机构、群众团体在各地进行采风、调查,搜集到不少神话故事。据统计,从1984年至1992年,四川全省先后参与民间文学普查的人员就达17500人,有160个县(区)铅印了资料集,26个县(区)出了油印资料集,21个地、市、州出版了铅印资料集,总计收录到民间故事16万余篇,其中就包含不少的神话故事。[57]这些神话故事被精选以后,先后收录到不同的故事集中,如谷德明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58],陶阳、钟秀主编的《中国神话》[59],陶立璠、李耀宗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60],侯光、何祥录编的《四川神话选》[61],孟燕、归秀文、林忠亮编的《羌族民间故事选》[62]等等。
总而言之,从改革开放到世纪末这段期间,国内的神话研究从少数学者的个体研究逐渐朝群体研究的趋势发展。就四川而言,在袁珂先生的带领下,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文化团体中涌现出不少对神话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使四川成为中国神话研究(包括古蜀神话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四、新世纪以来的古蜀神话研究
新世纪到来后的二十余年,中国神话学研究突破了单一的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而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趋势,各高校、科研院所及基层文化机构的神话研究者不断涌现,各种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版或发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神话研究新局面。特别是随着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和深入,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受到学术界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多学科的研究格局逐渐形成。
就古蜀地区而言,世纪初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相继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大量出现,引发学术界对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大背景下,古蜀神话作为古蜀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一大批学术成果随之产生。
论文方面,这一时期涉及古蜀神话研究的主要有:黄剑华《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63],李诚《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64],苏宁《试论三星堆神仙体系》[65],贾雯鹤《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66],罗建新《古蜀神话中的民族精神》[67],程熙《从神话考古看古蜀的历史文化内涵》[68],谢晋洋、胡美会《巴蜀神话的影响及研究价值》[69],王炎《大禹神话的现代解读》[70],叶舒宪《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与巴蜀神话历史》[71],易代娟《杜宇神话研究》[72],李沙《杜宇、鳖灵神话传说探析》[73],梁娟《从古蜀神话看古蜀人的原始信仰》[74],甘成英、毛晓红《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构筑李白瑰丽的浪漫诗境》[75],蔡从琴《杜宇神话的解构与阐释》[76],杨阳《从巴蜀神话看三星堆文化中鸟图腾崇拜》[77],邓经武《中国文化源头中的巴蜀神话》[78],李叶《蜀王神话的文化内涵探究》[79],何丹《杜宇神话的真相探究》[80],黄剑华《大禹的传说与西羌文化》[81],何中华《巴蜀神话的地理属性——以茅盾“北中南”神话地理分类来看》[82],王春宇《蜀地蚕神研究》[83],黄怡《探究巴蜀神话中的劳动内容及其价值意义》[84]等等。
著作方面,这一时期四川本土学者涉及古蜀神话研究的主要有:黄剑华《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书社2002年版)、《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巴蜀书社2003年版),周明《山海经集释》(巴蜀书社2019年版)、《路史笺注》(巴蜀书社2022年版),贾雯鹤《神话的文化解读》(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山海经〉专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李祥林《神话·民俗·性别·美学——中国文化的多面考察与深层识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女娲神话及信仰的考察和研究》(巴蜀书社2018年版),刘勤《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神信仰源流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等等。
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对古蜀神话的研究。它清晰地表明,四川的神话研究传统仍在传承、发扬。
2019年4月,继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成立之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神话研究的专门机构——神话研究院。神话研究院成立后,按照建院方案确立了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巴蜀神话研究”就是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神话研究院建院三年多来,其主办的《神话研究集刊》在每一集都專门开设了“巴蜀神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有关巴蜀神话研究的文稿,如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和史实探讨》,李祥林《西蜀‘漏天神话意象及其文化解读》,李殿元、蒲林德《阆中华胥神话传说简论》,周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四川卷〉概述》,李诚《神话与历史——略论杜宇》,徐学书《从古史传说看蚕丛氏蜀人与古蜀国和冉駹古国的关系》,谢天开《大禹神话与蚕桑文化探析》,宋峰《族群叙事理论视野下的巴蜀古代民族与神话》,陈云《大禹信仰及其祭祀活动源流》等,计二十余篇。
2021年,神话研究院与四川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拟在“十四五”期间推出一套“巴蜀神话研究丛书”。目前,相关组稿工作已经完成,第一批图书如黄剑华著《古蜀神话研究》、李诚著《古蜀神话传说试论》、周明编《巴蜀神话文献辑纂》已在2023年初正式出版。以后,神话研究院每年都将推出四至五本巴蜀神话研究专著,使整套丛书的总规模达到二十余种。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古蜀神话以其独特的发展历史、独特的民族构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增进我们对古蜀文明更深一步地了解和认识。
注释:
[30]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载《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见马昌仪:《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第442页。
[31][32][33]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1辑。
[34]徐中舒:《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创刊号)。
[35]邓少琴:《蜀故新诠》,载邓著《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详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7]茅盾:《中国神话研究》,载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38]参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2—238页。
[39]参见袁珂:《神话故事新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40]袁珂:《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民间文学》1964年第3期。另见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41]袁珂:《李冰父子凿离堆》,载张思勇主编《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109页。
[42]袁珂、王纯五搜集整理《二郎擒孽龙》(1963年),见张思勇主编《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7页。
[43]刘锡诚:《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序言》,载马昌仪选编《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版,第5页。
[44]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45]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3期。
[46]袁珂、岳珍:《简论巴蜀神话》,《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3期。
[47]贾雯鹤:《巴蜀神话始源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8]张启成:《古蜀杜宇神话传说新探》,《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49]萧崇素:《原始的探索童年的幻想——凉山彝族民間神话一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50]李子贤:《大凉山美姑县彝族神话与宗教民俗》,《楚雄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51]林忠亮:《试析羌族的古老神话》,《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52]李明:《羌族神话纵横谈》,《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53]李璞:《羌族神话与审美观念》,《文史杂志》1996年第2期。
[54]徐晓光、徐冰:《古羌神话与日本神话传说的比较》,《日本学刊》1994年第6期。
[55]佟锦华:《简析藏族神话》,《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56]李燕:《试论藏族神话中的自然历史观》,《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57]详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前言》(上),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17页。
[58]谷德明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59]陶阳、钟秀主编《中国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0]陶立璠、李耀宗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61]侯光、何祥录编《四川神话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62]孟燕、归秀文、林忠亮编《羌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63]黄剑华:《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4]李诚:《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一辑,巴蜀书社2003年版。
[65]苏宁:《试论三星堆神仙体系》,《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
[66]贾雯鹤:《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67]罗建新:《古蜀神话中的民族精神》,《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68]程熙:《从神话考古看古蜀的历史文化内涵》,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69]谢晋洋、胡美会:《巴蜀神话的影响及研究价值》,《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4期。
[70]王炎:《大禹神话的现代解读》,《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4期。
[71]叶舒宪:《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与巴蜀神话历史》,《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
[72]易代娟:《杜宇神话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73]李沙:《杜宇、鳖灵神话传说探析》,《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8期。
[74]梁娟:《从古蜀神话看古蜀人的原始信仰》,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75]甘成英、毛晓红:《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构筑李白瑰丽的浪漫诗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2期。
[76]蔡从琴:《杜宇神话的解构与阐释》,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7]杨阳:《从巴蜀神话看三星堆文化中鸟图腾崇拜》,《青年作家》2014年第12期。
[78]邓经武:《中国文化源头中的巴蜀神话》,《文史杂志》2016年第2期。
[79]李叶:《蜀王神话的文化内涵探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0]何丹:《杜宇神话的真相探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81]黄剑华:《大禹的传说与西羌文化》,《地方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
[82]何中华:《巴蜀神话的地理属性——以茅盾“北中南”神话地理分类来看》,《长江丛刊》2020年第26期。
[83]王春宇:《蜀地蚕神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84]黄怡:《探究巴蜀神话中的劳动内容及其价值意义》,《今古文创》2021年第27期。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神话研究集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