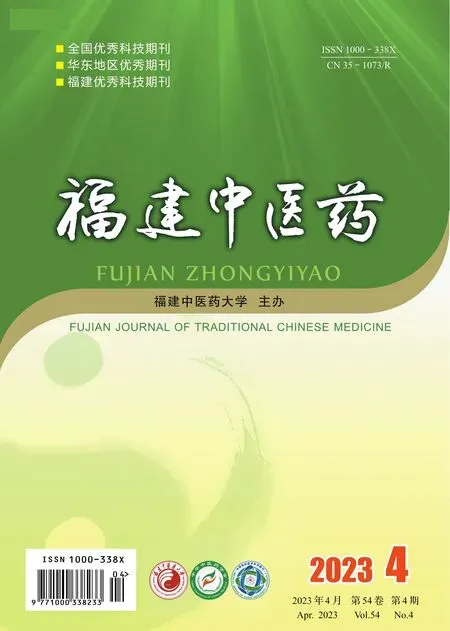严桂珍教授论治间质性肺病经验
2023-09-07叶燕燕黄依晴高丽丽指导严桂珍
叶燕燕,黄依晴,卢 峰,高丽丽 指导 严桂珍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 福州 350003)
间质性肺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是发生在肺间质内的一类疾病的总称,以肺间质炎症水肿和纤维化改变为特征,可致血氧交换功能降低和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表现为进行性呼吸困难、持续性干咳以及乏力等。ILD 起病隐匿,故早期容易被忽视或误诊,多数类型激素治疗有效,中位生存期约在3~5 年[1-2]。中西医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肺功能,延长患者生存期[3]。
严桂珍教授为福建省名中医、福建省第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50 余年。严桂珍教授常从虚、瘀、痰、热毒等方面辨证论治ILD,可明显缓解症状,改善或延缓其病程。现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根据ILD 临床表现,严桂珍教授认为本病属中医学中“肺痿”“肺痹”范畴,多因素体禀赋不足、久病体虚或失治误治,致肺气虚,甚至肺阳不足,致卫气不能御邪于外,当邪盛急病时,可进一步伤及肺络。正邪胜却,是本病急性发作与慢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病病机以肺脾气虚、肾阳不足为本,瘀血阻络、痰浊阻肺或痰热壅肺为标。
1.1 肺脾气虚,肾阳不足 肺气虚,肺金不足继而累及脾土,脾为后天之本,脾土虚则无法正常灌四旁,肺金失所养,故愈见不足;又因本病起病隐匿,多数病例有病程久、进行性加重特点,金水相生,肺病日久可累及肾;脾脏体阴而用阳,脾阳根于肾阳,脾虚日久亦可累及肾阳之气。肾为命门之火,既能助肺纳气,又能暖脾助运,故肺肾不足,升降失司,亦致咳喘不断。因此,严桂珍教授认为ILD 患者不仅表现为进行性胸闷,而且咳喘多是无力的。
1.2 瘀血阻络 《灵枢·本脏》曰:“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的通道,以经脉作为主干,与其分支的络脉共同沟通联系,输布气血以濡养脏腑、肢节等。《素问·经脉别论》曰:“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强调了肺助心行血、调节血液运行的重要作用。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虚则不能振奋营气,肺脉中血行迟缓,在细小的肺络之中易形成瘀滞。血瘀不仅是ILD病程进展中的病理产物,也是加重其病情的致病因素。一方面血瘀日久,脉络不通,气机升降失调,津液运化不利,聚而成痰,痰阻气滞于肺络,渐致痰瘀互结,积久蕴酿成毒,进一步损伤肺络;另一方面血为气之母,血瘀日久,导致新血化生不利则气无以濡养,故肺气虚更甚。
1.3 痰浊阻肺 ILD 多因无形之痰阻于肺络而难以排出,表现为干咳或伴少量白痰。从病理上看,肺间质、肺泡、淋巴管网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炎性反应[4]。由于肺泡上皮细胞对肺泡腔与间质的阻隔作用,在炎性反应过程中产生大量细胞因子、组织液、组织碎片等造成局部水液代谢障碍,常局限于肺间质,肺泡腔内一般无渗出或少量渗出,因此本病患者常表现为干咳。严桂珍教授认为:① 从气血津液角度上看,血不利则为水,血瘀而脉道不畅,可进一步影响津液化血,终致水病,水停于肺络形成无形之痰;② 从脏腑辨证角度上看,脾为生痰之源,居中央而灌四旁,肺为贮痰之器。脾虚则水津不布,肺虚则水道通调失常,聚之生痰,贮存于肺,阻于肺络,发为咳喘。
综上,痰浊、血瘀与气虚可相互影响。津液与营气入脉化血,痰、瘀二者为津血运行失常的病理产物,并与气的状态相关。一方面,气虚行迟,可致水液、血液滞涩,成瘀成痰;另一方面,痰与瘀又可进一步阻碍气机的运行。
1.4 痰热壅肺 严桂珍教授认为:肺脾气虚、肾阳不足与瘀痰阻络为ILD 的基础病机,故相较于健康人,ILD 患者正气不足,呼吸防御功能较弱,尤其是长期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常无力抗邪外出。当外邪急犯入肺,郁而化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热灼肺津,炼液成痰,痰与热交结而形成痰热壅肺之证。
2 遣方用药
结合ILD 本虚标实的病机特征,治疗时当标本兼治,但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有所侧重,急则重于治标,缓则重于治本。
2.1 健脾益肺、温阳纳气为主 ILD 本属气虚,尤其是阳虚不能进一步温化全身,这有别于感染性疾病与支气管痉挛,因此,严桂珍教授认为本病治疗宜用健脾益肺、温肾纳气之品,采用四君子汤加减益气健脾,可选用黄芪、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等健脾益气以绝水上之源。主要选用黄芪而非党参是因黄芪运脾利水化湿,为气虚水肿之要药,大剂量(30~50 g)黄芪在培土生金基础上,可起到利尿消肿、托毒生肌、排痰之功,进而减轻咳喘。《类证治裁·喘证》记载:“喘由外感者治肺,由内伤者治肾。”故用补骨脂丸加减温阳纳气,选用巴戟天、补骨脂等补肾温阳,纳气平喘。
2.2 重视活血通络 ① ILD 病变位于肺之络脉,治疗上严桂珍教授重视通达肺络,用药上采用取象比类之法,主张活血化瘀药要选用虫类药或外形形状尖细的中草药,旨在搜剔络中之邪,通以去其闭。虫类药可选用蜈蚣、地龙、全蝎等,其中蜈蚣用量5 g,地龙用量15~20 g,盖因虫多性钻剔而善走窜,活血化瘀力强。草木类药可选用红花、路路通之类,红花用量6~12 g,路路通用量15 g,因其外形尖细,可搜剔细小络脉之瘀血。② ILD 的血瘀包括血液瘀滞与络脉损伤2 种状态,因此必要时可予辛温通络或温补络虚之法。辛温通络首选桂枝,用量在6~9 g,盖因其性辛、甘温,入肺经,温通经脉,既可以温脾阳,助运水,又可以温肾阳,助膀胱气化。ILD 病位在肺之细小络脉,桂枝辛温温通以减轻瘀滞状态。温补络虚常用黄芪24~30 g、巴戟天或补骨脂10~15 g 健脾益肺,温阳纳气,以平衡人体整体与局部的气血阴阳状态。
2.3 清热解毒、化痰为辅 ILD 的缓解期与急性期都存在着邪毒的问题,邪毒即热毒或伴有痰毒,邪恋或邪盛皆可引起疾病的迁延,因此严桂珍教授主张运用清热解毒药,如蒲公英、鱼腥草、紫花地丁等,并结合症状辅以化痰药,如陈皮、半夏等。运用中应注意阴阳平衡,尤其是清热解毒药物性寒凉,可加重ILD 患者气虚、阳虚、痰瘀互结之象。因此,严桂珍教授提出固本培元以达阴平阳秘之法,即:强调处方在整体上寒性药与热性药需动态平衡,达到药性中正平和而无伤正气的目的。
病例介绍
患者林某,男,70 岁,有直肠癌根治术后、肺转移癌和过敏性鼻炎病史,于2017 年2 月17 日初诊。患者就诊时诉近4 个月反复咳嗽,咳痰,痰色白、质黏不易咳出,伴活动性气促,于外院确诊为双肺间质性肺炎。查肺功能提示:肺弥散功能重度下降,功能残气量、残气量正常,肺总量下降。辰下:稍活动后气促,偶有咳嗽,咳痰,痰色白,质黏,口干,饮后不减,纳少,小便调,大便偏稀,舌淡暗,苔黄稍腻,脉弦尺弱。西医诊断:间质性肺病;恶性肿瘤病史。中医诊断:肺痿,属痰热壅肺、气虚络瘀证。处方:党参30 g,黄芪40 g,炒白术12 g,薏苡仁30 g,菟丝子15 g,山茱萸15 g,路路通15 g,蜈蚣5 g,山慈菇9 g,姜半夏15 g,陈皮9 g,葶苈子9 g,炒紫苏子15 g,蒲公英30 g,重楼9 g,黄芩9 g,甘草3 g。共7 剂,每日1 剂,水煎服,分早晚温服。
2017 年2 月21 日二诊:气促稍缓解,活动后明显,口干,胃脘胀痛,二便调,舌淡暗,苔薄黄,脉弦尺弱。辨病辨证不变,在原方基础上去菟丝子、山茱萸、山慈菇、蜈蚣、葶苈子、黄芩、蒲公英、炒紫苏子、姜半夏、陈皮,加巴戟天15 g,地龙15 g,桂枝9 g,白芍9 g,鱼腥草30 g,野菊花15 g,玄参9 g,桔梗9 g,厚朴9 g,茯苓15 g。共7 剂,每日1 剂,水煎服,分早晚温服。
2017 年3 月21 日三诊:症状基本缓解,续上方继续调理治疗。
按:患者久病,肺、脾、肾不足,呼吸无力,故稍活动后气促;脾虚水液运化失常,聚液成痰,上贮于肺,发为咳嗽咳痰;气虚行迟,血液运行愈发滞涩,瘀血内生,故见舌暗而有痰;考虑余热未解且瘀久化热,故痰黏而苔黄稍腻。严桂珍教授谨守病机,辨证施药,在补益肺脾肾和活血通络的基础上,辅以清热化痰,排脓散结。一诊时以党参、黄芪、炒白术、薏苡仁益气健脾,兼利水或燥湿;菟丝子、山茱萸补益肾气;路路通、蜈蚣、山慈菇活血通络兼以散结;姜半夏、陈皮、葶苈子、炒紫苏子化痰定喘;蒲公英、重楼、黄芩清热化痰。诸药并用,共奏益气活血、清热化痰之功。二诊时,患者气促虽有缓解,但效果未达预期,考虑肾虚纳摄无权,久病治喘在于肾,故改菟丝子、山茱萸为温肾阳之力较强的巴戟天助纳气平喘;气促亦因有效运氧不足所致,即精微不足,因此除补肾温阳外,温通血脉也同样重要,单纯的活血药物无法通达久病的肢体末梢,所以改山慈菇、蜈蚣为通络平喘的地龙,并加用辛温通络之桂枝以改善局部瘀滞状态;患者口干、痰黏并伴有新发的胃脘疼痛,考虑为药物过寒伤脾所致,因此去除寒凉较甚的葶苈子、黄芩,改蒲公英为消痰痈的鱼腥草、野菊花,加用清热滋阴之玄参,佐以桔梗在宣肺利咽基础上升提药性;湿热之象明显且伴胃脘胀痛,因此去除姜半夏、陈皮,改为厚朴燥湿理气除满,茯苓健脾渗湿。诸药并用,共奏益气温阳、活血通络、清热化痰利咽之功。三诊时患者症状明显改善,取效满意。严桂珍教授在治疗过程中不仅兼顾患者体质,亦明辨疾病复杂的病机。本案患者虚实夹杂,治以养、通、清相结合,标本兼治,取得佳效。
3 体 会
目前ILD 病因难明,病情反复,年老体弱者尤甚,病情多呈进展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严桂珍教授治疗本病采用固护肺脾肾,重视化痰通络,辅以清热解毒的疗法,重在以养和通,以养固本,以通促畅,促进人体达到阴阳平衡的有机整体状态。治疗过程中尤为重视患者生活质量,强调纳好、寐安与二便调为治疗基本目标,以提高患者良好的治疗体验,减轻疾病所致心理负担,取得更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