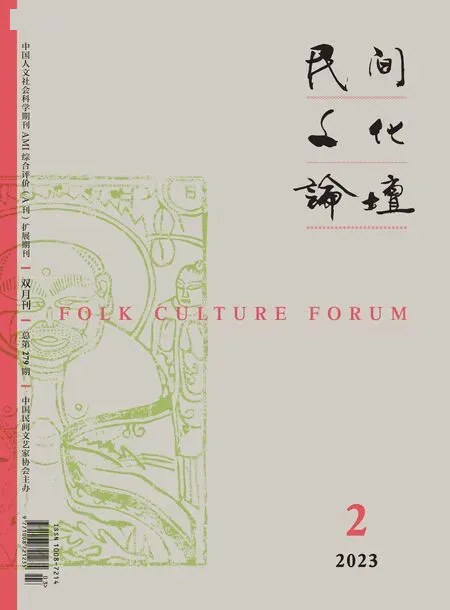广西风俗改良的近代与当下
2023-09-04黄洁
黄 洁
引言
政治经济的发展与近代新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带来了社会方式的变革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变化。左玉河透过研究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指出社会变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进性和缓慢性的过程。他看到了变动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同时,部分习俗的变革绝非政府的强制手段所能解决,民众日常习惯的势力也深厚强大。如民国时期推行新式婚丧礼仪、现代以后进行殡葬改革之际,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产生过一定的矛盾或冲突。①详见左玉河主编:《民国社会生活史》(上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7 章。他指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社会上层与下层民众这种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政府推行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移风易俗(如民国初期推行阳历与民间阴历并行)将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而中国社会习俗的变革和演进,正是在这种上下层的对峙与调适、新旧势力的冲突与妥协中进行的。①参见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 期。民国时期以来的移风易俗的经验,对当代中国也有借鉴意义。
这种近代社会生活史的视角与日本民俗学的传统异曲同工。柳田国男认为经历激烈变化的生活虽潜在地受到“往昔生活的束缚”,但“新的生活一定会留下新的痕迹”②参见[日]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篇(新装版)》,东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993年,第101、138 页。,这在他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的描述中可见一二。有贺喜左卫门也曾指出,民俗学成立之基础在于追究人们一直在变化的生活,把焦点聚焦在不断变动的生活动态,以考察其变化根源的意义。③参见有賀喜左衛門:《民俗学の本願》,载《有賀喜左衛門著作集〈第8 巻〉:民俗学·社会学方法論》,东京:未来社,1969年,第32 页。所以岩本通弥指出,民俗学必须追问现代的“日常”和至今为止的演变过程。④[日]岩本通弥:《日本の生活改善運動と民俗学-モダニゼーションと〈日常〉研究》,《日常と文化》,2019年第7 卷,第27 页。民俗学研究日常生活,终归是要服务于我们未来更好的日常生活。现在的、当下的民俗学研究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将来。与此相应,高丙中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提出关于日常生活的“未来的民俗学”。他指出,“民俗”在学术意识上与日常语言乃至社会意识里,都是属于“过去”的。但当大量的民俗项目被命名为“非遗代表作”,国家体制和社会公众都确认要保证其未来传承,民俗所内含的“未来”的意义也被完整地呈现,并成为一种中国事实,得到国家体制和社会人心的确认、承诺和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俗学不能继续在原先那种片面、割裂的时间意识中沿袭自己的研究传统。⑤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 期。特别是随着非遗概念等成为法定的公共文化,一些日常生活传承的文化需要通过体制的改变才能被容纳。而推动日常生活文化进入国家体制的过程与国家体制被重构的过程的同构,才是现代国家的正途。具体而言,民众能表达需求,国家体制对这些需求有所回应,也能在回应中进行调整,形成建设性的、可持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国家体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的关键所在。这些都要求民俗学者为了未来更好的日常生活,努力促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整体地位提升与细节不断完善。为此,本文尝试以广西为个案,梳理其移风易俗政策的近代与当下,探索面向未来的民俗学的可能性。
广西各民族自民国以来经历了政府推动的大量社会风俗改革活动。在近现代广西,从1930年代顺应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新桂系⑥相对于辛亥革命前后从1912年到1924年间,以陆荣廷、谭浩明为首的北洋军阀所代表的旧桂系,新桂系政府是指在1925年崛起的,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广西本地人为代表的南方军阀,属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因新桂系政府较早在广西开启了风俗改良之风而备受学界关注。之风俗改良的一系列政策,到1950年代改造社会生活领域的“移风易俗”政策,以及1980年代以来至当下顺应乡村发展、乡风文明化与城镇化热潮中掀起的“生活革命”, 政府对世居广西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改革一直持续着。既往研究对这些改良改革政策的施行引发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变迁进行了许多探讨。如廖杨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俗改良,将其视为近代壮族社会史的一环⑦参见廖杨:《辛亥革命与广西的风俗改良》,《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1 期。,方素梅援引方志材料讨论了1840年至1949年间当局针对壮族的婚嫁、丧葬、服饰及宗教迷信活动等社会风俗的政策①参见方素梅:《清及民国壮族社会风俗变迁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 期。方素梅:《近代壮族社会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65—268 页。,廖杨、付广华则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宗教问题的政策②参见廖杨、付广华:《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3 期。。近年来,广西民族史研究中,越来越多地重视民国以来特别是1930年代的近代改良风俗政策,但往往没有深入讨论具体内容,而着意于否定或批判政策本身。③参见谭肇毅:《民国时期新桂系的民族政策述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 期。付广华:《论新桂系政权的民族同化政策》,《桂海论丛》,2008年第5 期。王晓军:《边疆视域下新桂系时代广西的风俗改良》,《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2 期。刘雅琪:《民国初期瑶族的风俗改良——以广西兴安、龙胜瑶族地区为中心》,《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 期。雷云:《新桂系时期广西民族地区治理研究》,广西民族大学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李成生:《新桂系时期广西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改良述论》,《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3 期。如张声震、覃彩銮等人就当时掌握广西政权的新桂系所施行的同化政策,表明对他们将壮族等非汉民族的风俗习惯作为“陋俗”一事的批评态度。④参见张声震主编,覃彩銮编著:《壮族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1 页。同时,19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向来广受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但很少有研究系统而整体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风俗改良政策。冢田诚之依据《广西日报》的有关报道,探讨了革命时期的文化政策,尤其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移风易俗”政策的异同之处,为本文提供了一些数据整理和方法论上的参考。⑤参见塚田誠之:《広西における“改良風俗”政策について: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文化政策の一齣》,载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 : 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东京:風響社,2009年,第157—182 页。
“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自古以来,朝廷或政府始终将移风易俗视为治理国家、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及理所当然的责任。战后日本政府发起的生活改善运动及相关的各种计划,与民俗变迁之间的关系向来为日本民俗学界所重视。⑥代表如田中宣一:《生活改善諸運動と民俗の変化》,载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编:《昭和期山村の民俗変化》,东京:名著出版,1990年。田中宣一编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东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11年,第11 页。大門正克编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敗戦から1970年代》,东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年。伴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战时日本生活改善,与其说保护、保存当时的生活,不如说是一种改善、变革的公共意识。可以说政府的力量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风俗改良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有时甚至是使得民间传承发生断裂的关键因素。所以,本文主要围绕国家与民俗的关系⑦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导言。,对生活革命予以动态性的把握。基于“生活革命”视角,梳理民国以来,广西当局针对各族实行的风俗改良政策。特别是援用周星对“生活革命”概念的重申和补充,即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都市化促成了彻底的日常生活整体的革命性变化,包括日常起居与科技影响的层面等。⑧周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 期。通过对近代与当下主要政策内容与施行的今昔比较,进而概括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政策的潮流及生活革命的意义。
一、桂系政府的风俗改良与新生活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自1934年2 月发起了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为起点与主要内容的“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革新个人的日常生活来改造社会。⑨参见敖文蔚:《中国近现代社会与民政(1906—1949)》,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3—134 页。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着力推行新历改革、剪辫放足、衣食住行的改造、婚嫁与丧葬礼俗改革、节日纪念日体系改革等。⑩参见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 期。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也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山东邹平等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以清除落后而有害的习俗、引导民众走向现代的文明。①李红辉、梁生:《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人民论坛》,2010年第29 期。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也围绕反对宗教迷信、婚丧习俗、禁毒禁赌、放足剪发、普及卫生观念等涉及社会、民生层面的内容展开了移风易俗,以解决发展民生的问题。②参见刘果元、李国忠:《苏维埃时期移风易俗工作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 期。魏彩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的史实考察》,《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 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也在社会风俗的各个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旧风俗、提倡新文化的措施。
1932年,新桂系集团的重要宣传者梁上燕在《广西风俗习惯改良问题》中提到,没有存在价值的风俗习惯是封建势力,要创造“三民主义”的社会就必须消灭封建势力。他认为,比起推行近代的特种教育,盲信科举、土豪劣绅的存在才是当前应迫切予以禁止的事项。③参见梁上燕:《广西风俗习惯改良问题》,《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9 月16 日,第10 版。1934年,杨煊以“新文化”的标准,在《广西风俗概述》中描述当地的瑶苗女性,称她们污秽、拥有着古怪而可笑的身体。她们穿着银饰、裙装,行为粗鄙。且这些民族民众因长年居住在山中失掉了嗅觉,不知清洁卫生,干栏式住居是堆积垃圾污水之地。④参见杨煊:《广西风俗概述》,《广西政府公报》,1934年第8 期。直到1949年,仍有人认为苗瑶民相比侗壮人,更原始野蛮,用“猺”来描述当时的瑶人。这些居住于深山的瑶民被想象成是周身“长满长而密的毛”、未完全进化的族群,苗族的服饰都是“奇装异服”,且瑶族女性终年不洗头发而爬满虱虫,在男子面前袒胸露乳也不觉得羞耻。⑤参见《苗、傜、侗、奇装异服》,《广西日报》(桂林版),1949年7 月21 日。故有研究指出,由知识分子代表的这些身体想象和偏见构成了这一时期风俗改良运动普遍而“合理”的舆论基础⑥冯智明:《剪发易服的身体政治——红瑶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4 期。,也是改良的主要社会历史背景。
1926年5 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军阀在主政广西后,随即着手开展风俗改良活动,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如黄绍竑主政下的广西省政府于1926年7 月,通令全省各县捣毁寺庙偶像,以祛除迷信。1928年元旦,又通令全省实行分区禁赌办法,规定了除梧州、南宁、桂林、柳州、平乐、玉林、龙州、百色等8 个城市中划定区域准许开赌外,其余各县以及上述八县的乡间,禁绝赌博,但这些改革后因军阀混战而暂停。⑦参见黄绍竑:《五十回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136—137 页。新桂系的风俗改良活动至1930年代达到高潮。新桂系执政后,为加强民族融合,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施行了强制性改良。但同时也重视民族关系,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进步的观点和改革措施,如提倡各民族有不同族群的“种族”分类,禁止对少数民族用猺(瑶)、獞(壮)、狪(侗)等含有歧视因素的蔑称⑧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民俗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1 页。,在瑶民较多地区还建立国民党党部,吸收瑶民党员。
1931年,省政府颁布《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通令各市县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积极开展风俗改良运动。比如,在婚俗上,要求女子出嫁后常居夫家,禁绝不落夫家⑨结婚以后,女方仍在娘家居住,只有农忙和过年过节时才去夫家帮忙,直至女方生下第一个小孩以后才长在夫家居住的习俗。除壮族以外,侗族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也有类似婚俗。的婚俗、禁绝歌会歌墟。同时,崇尚节俭,严禁虚伪奢靡之习俗。⑩《广西各县市取缔婚丧生寿及陋俗规则》,《广西教育行政月刊》,1931年第6 期。此外,上述规则有不少条款涉及宗教信仰问题,如第3章第21 条即规定:丧家不准用地师、僧尼、道巫斋醮做亡,第5 章第34 条进一步规定,应革除游神拜佛送鬼、放花炮、中元节纸扎等迷信行为。⑪参见《广西通志·民俗志》,第427—428 页。各级政府致力于打倒神权、捣毁偶像,禁绝僧道地师营业,禁止制造纸人纸马等祭祀用品。使各城乡的寺宇寺产悉数充公,无所凭依而一蹶不振。①魏任重修,姜玉笙纂:《广西省三江县志》卷五 文化,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35年(1946年)铅印本,1975年,第517 页。这一系列措施与民国初年的城隍神像事件有关。②详见廖杨、付广华:《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当时,政府严格阻止城隍神像出游,招致不少民众反对,导致龚管带头部被飞石击伤。后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风俗改良运动,当时的南宁都督府派兵四处捣毁寺庙神像,致使僧侣散亡,经典焚烧殆尽,唯女尼姑得以幸免。一些县乡伴随着风俗改良政令行动起来,捣毁不少寺庙和神像。③参见莫炳奎纂:《广西省邕宁县志》卷四十 社会、宗教,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26年(1937年)铅印本,1975年,第1616 页。后来的新桂系政府也将“敬视鬼神,作偶像崇拜;建醮还愿,请僧道做法;迷信堪舆地师等”视为必须革除的陋俗。④参见亢真化、梁上燕:《改良风俗的实施》,桂林:民团周刊社,1938年,第16 页。在1932年广西民政厅出版的《广西民政视察报告汇编》中,还列举了童养媳、唱歌(歌墟歌会)、游惰、愚蛮、不卫生等需要予以纠正的陋习作为改革的对象。⑤参见广西省民政厅:《广西民政视察报告汇编》(民国廿一年度、上期),1933年。1933年4 月,桂系颁布《广西各县苗猺民编制通则》,用保甲制度取代少数民族传统的乡老、寨老、头人制度,首先在桂东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统一乡村编制,使苗瑶与汉人同一待遇。⑥参见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第95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0 页。同时,实行所谓的特种部族教育,以开化各族民众。
1933年7 月,省政府又修正、改订了同年2 月颁布的《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则》,从行政命令层面对广西各民族风俗作出全面的改良规定,涉及发型(如第37 条)、改装异服(如第27 和37 条)、婚俗(第6—8 条和第28—31 条和第34 条)、不落夫家(第32 条)、堕胎·溺女(第3 条)、祭神(第24—26 条)、巫觋·地师(第26 条)、葬礼(第10-18 条和第34 条)、生寿节庆(第19—23 条)等范围。⑦参见广西省政府:《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划》,《广西教育行政月刊》,1933年第2 卷第9 期,第58—62 页。具体规定办婚嫁、丧葬、生寿、节庆等事一律从简,严令禁止和取缔各种日常生活中的迷信、奢侈行为及其他一切陋规殊俗。如规定了婚俗的礼金金额、招待来宾的酒席所需金额、婚约、结婚年龄等细节;还列有对违反者的处罚规定(如警告、罚款甚至拘留等),包括对公务员违反者的处分等。除了重申对游神醮会、歌会歌圩和不落夫家的禁绝以外,将早婚、缠足、穿耳和染齿也纳入禁绝范围,且违者处以罚金。同时,不得穿耳束胸,不得留长发,鼓励购置国货、改装易服,以推崇戒奢从俭、移风易俗的朴素生活理念。但其中也包括应对1931年的规则草案引起民众不满而对改良内容做出的一些调整,如婚丧生寿礼金的规定有所放宽,丧家停柩在堂时间也由原来的“不得超过7 日”改为1 个月,有特殊原因可延长至3 个月;对违规参加歌圩、歌会者的罚金由禁止改为平时极力劝导,发现时即设法妥为解散,不听解散的,为首者罚金⑧参见王晓军:《边疆视域下新桂系时代广西的风俗改良》,《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2 期。,等等。针对信仰,在规则的第5 章“陋俗”中,第24 条规定:“不得迎神建醮,违者没收其所聚集及捐款,并处首事者20 元以上100 元以下罚金,其在场僧道之法衣法器没收之”;第25 条规定:“不得奉祀淫寺,及送鬼完愿,违者处5 元以上20 元以下之罚金”;第26 条规定:“不得操巫觋地师等业,违者处5 元以上20 元以下之罚金,再犯者加倍处罚”;等等。各地的民间信仰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佛道相关的寺院和庙宇等场所被充作学校,从业人员也很难维系旧业。如县志中提到,当时,贵县“黄冠辈多已别营生业”①欧卿义修,梁崇鼎等纂:《广西省贵县志》卷二 社会、宗教,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23年(1934年)铅印本,1967年,第313 页。,隆安县“道巫为之歇业”②刘振西等纂:《广西省隆安县志》卷三 地理考、社会、迷信,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23年(1934年)铅印本,1975年,第202 页。。又如,三江县拆毁偶像淫寺,二圣庙庙址建为卫生庙,三王庙易祀,其材料用于建学校。宜北县“今医务所成立,人心渐信用药品,不再如前之迷信鬼神”③李志监修,覃玉成纂:《广西省宜北县志》第二编 社会、迷信,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国26年(1937年)铅印本,1967年,第61 页。,风水择日和送鬼问仙之俗日渐减少。不过,即使在这样的重压下,各地仍有相应的抵制措施,有些驱疫禳灾的习俗仍未消减。
1933年,广西省政府颁布了《广西服装办法》《取缔市民服装办法》及其实行细则。以汉族的服饰为标准,对少数民族的“奇装异服”强行禁止,规定战时广西市民着装,应是“男子服装以中山学生装及普通长衫、短衫为标准,不许赤身露体及着不及膝之短裤”“女子常服以普通衣裙及长袍为标准,衣必掩腰,袖必过肘,裙裤均须过膝,不得袒胸露腿”。④详见广西省政府:《取缔市民服装办法》,《广西教育行政月刊》,1933年第2 卷第9 期,第63 页。广西社会上下形成“一色布衣”的风气并兴盛一时。根据1934年发布的《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省施政纪录》,当年度各县级发生违反改良风俗案件共52 件,其中陋俗45 件,大操大办生寿、丧葬、婚嫁各1 件,奇装异服4 件⑤参见广西省政府编辑室编:《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省施政纪录》,南宁:广西省政府出版,1935年3 月20 日,第133—136 页。,大致可见当时运动的效果。
新桂系以强制手段取缔违背规则者,如组织民团进行宣传和劝导,派民团在圩镇巡查,把守路口,检查行人,强制移风易俗;又如强迫少数民族剪发、按要求的服饰标准改装衣服等。如雷平县板价村一带,壮族女性穿着有异于标准的样式别具一格的裙子,被派到集市上的警兵认为怪异,便堵截铰剪。⑥参见方素梅:《清及民国壮族社会风俗变迁述论》。三江县顺应1930年代广西省内的趋势,1932年成立“改良风俗委员会”,制定了《三江县改良风俗委员会补充规则》,其中规定“苗瑶侗人之衣裙,应一律改用汉服,以资节省,而一观瞻”⑦魏任重修,姜玉笙纂:《广西省三江县志》卷二 改良风俗述略,第164、166 页。。各乡长、保长勒令女性改装,甚至有军警进寨抓人,拦截路口,威逼侗族等民族女性改变发式,或当场剪破她们的花裙,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当时,许多女性深受其害。如在龙胜,瑶民一下街就遭受辱骂,有被捆绑罚款,有反抗易容改装者,家财竟遭抢劫一空。⑧参见陈维刚、苏良辉:《龙胜瑶民起义》,载政协龙胜县委员会编印:《龙胜文史》(第四辑),1989年,第64—79 页。“一向瑶民赶圩,女子不穿短裤,近年政府对于其风俗习惯,严令改良,瑶人初不以为然,以后每逢街期,政府派兵守卡街口,举行检查,如发觉不穿短裤,除不许入街外,并施行鞭打;如此法令如山,瑶民始在裙内加出穿短裤,风俗为之一改。”⑨详见谢曼萍:《桂北傜区风光》,《中央日报》,1948年9 月28 日,第六版。有些地区,军警直接闯入家中,强迫妇女剪发改装,并没收民族饰品。这一系列政策引起各族民众强烈不满。因此,当时,龙胜龙脊寨老侯会庭等人被迫召集十三寨群众大会,宣布龙胜县改良风俗委员会禁令,强迫壮、瑶族群众改装易容,遭到与会者强烈反对。⑩参见黄钰:《龙脊壮族调查》,载覃乃昌主编:《壮侗语民族论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283 页。在此背景下,1932年底至1933年初,桂北地区爆发了声势较大的瑶民起义。起义参加者以龙胜县各地瑶民壮民为主,也包括了部分汉族。⑪参见南跃(黄钰):《一九三三年桂北瑶民起义》,《民族研究》,1959年第7 期,第42—48 页。起义大约坚持了一个多月后被新桂系镇压,当局为加强对瑶人的控制,杜绝民乱,制定了一系列善后政策。省政府视服饰差异为民乱的根源之一,所以令剪发改装,使汉瑶通婚而打成一片。①马炯:《兴全灌龙猺乱经过》,《政训旬刊》,1933年第21 期、1934年第22 期。1932年末,灌阳县第一次瑶民暴动后,新桂系推行“感化”并制定的善后八项,也包括了劝导剃发易服和兴学通婚。大规模起义发生后,又以宣传教育方式使全省瑶族归化。②谢祖莘:《绥靖兴全灌龙猺变始末》,广西省政府民政厅秘书处,1946年。其后,龙胜县平定瑶乱善后委员会成立,时任委员长的虞世熙认为必须办学校破除迷信并改易服装,使瑶民不再反叛。③虞世熙:《镇压龙胜瑶民起义纪略》,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8 辑)》,1988年,第209—218 页。经历“天罗地网”般的“勒令”与“训诫”之后,男性剪去长发、穿上汉服,女性不敢穿花衣花裙上街,这种状态大约维持到1940年代。2012年,笔者在三江县东北部侗寨调查春节习俗时,乡民大部分已改为简装,只结婚和重要节日时穿侗服,他们提到国民党时期的改装运动时仍记忆犹新。各村寨的守护神萨奶奶跟侗族女性一样喜欢穿侗族服饰,但过去不让穿花裙子时,萨奶奶就不喜欢在村中管寨保佑村民而离去,到1990年代以后才被供请回来继续守护乡民。在当地村寨周边的山谷中,至今仍有一些当年为避开国民党士兵巡查的“躲汉冲”,由此可知当年改装产生过的影响。
1936年5 月,广西省政府又颁布《广西乡村禁约》④《广西乡村禁约》,《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23 页。,以整顿乡规民约,要求各县乡村根据省政府颁布的规约制定新禁约,重申禁止和取缔的各种陋俗,改良内容涉及婚丧、祭祀、剪辫易服、节令习俗、娱乐生活、宗教迷信、文化教育等,几乎囊括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为响应新生活运动改革婚礼习俗的主张,同年7 月,省政府还推出《广西省政府集团结婚办法》,提倡婚礼婚俗的改革与新风。1937年,省政府出台新法规《广西省人民结婚须知》,对百姓结婚的仪式和程序进行明确规定,推行文明进步的新式婚制,其中包含集体结婚。⑤广西省政府:《广西省人民结婚须知》,参见李成生:《新桂系时期广西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载《广西地方志》,2012年第3 期,第49 页。最早举行集团婚礼的是邕宁县,随后便在全省境内渐成风气。《广西日报》上,集团婚礼广告不时见报。如1940 至1945年间,桂林市一共举办了9 届集团婚礼。⑥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桂林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43 页。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顺应国民党1938年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实行“增加生产、稳定物价、节约消费、调节金融”的政策,严加管束吃喝奢侈之风,1941年,省政府出台《取缔宴饮暂行办法》,采取强硬行政手段对社会上的吃喝应酬之风进行管制,试图推动“戒奢从俭”风气的转变。⑦广西省政府:《广西省取缔宴饮暂行办法》,《广西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1009 期,第1 页。1942年,省政府颁布《广西省禁赌办法》⑧广西省政府:《广西禁赌办法》,《广西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68 期,第10—12 页。,适用于境内处罚乡村赌博犯罪行为。1944年,内政部公布施行《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对境内民间社会崇拜神权迷信、缠足、蓄养婢女、童养媳、堕胎溺婴等被认定为封建作风的不良习俗予以查禁。
除了政府的风俗改革之外,少数民族内部的精英、寨老乡老也积极倡导并发起过一些改革。早在1917年,龙胜平等乡侗族举人石成山曾发起改良,要求少数民族进行改装并破除旧俗。当时,龙胜、兴安两县的红瑶寨老和知识分子成立了“改良会”,制定改良章程并立碑公布执行。风俗改良章程以乡约石牌的形式立于金坑和潘内两个村寨,包括潘内杨梅寨的《永古遵依》、金坑大寨的《永古遵依》和《兴龙两隘公立禁约》三块碑。⑨参见冯智明:《剪发易服的身体政治——红瑶身体装饰的文化表达研究之三》。据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收集的资料,当时提倡服饰改革的原因之一是瑶族女性的短裙。所以,上述乡规虽涉及服饰、婚嫁、丧葬、送礼等内容,服饰仍是改良的中心。一是弃“五彩”“以青为服”,以便衣青裙代替花衣、饰衣和花裙;还有禁“奢侈”银饰,如若不遵则罚钱。①详见《龙胜各族自治县潘内瑶族社会历史调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四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83 页。另外,社会内部改良和政府强制性改装还是有较大区别,当时知识分子的风俗改良未能禁绝妇女穿裙,虽然立了碑但民众不执行也就算了。
这一系列推动少数民族改良风俗习惯的政策和乡约后来多被指责为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的生活。随着社会变迁,有些地方的民族着装逐渐消失。据阮镜清1943年描述的那样,当时,虽苗人妇女的装饰尚保存古风,即黑及蓝色上衣,下衣为裤子或及膝的褶皱短裙,及耳环、项圈、指环、手镯等银饰,男子的服饰已几乎难见固有形式。②参见阮镜清:《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载《民俗》复刊号第2 卷第3、4 期,1943年,第21—33 页。
1930年代进行的改良风俗政策,强调是按三民主义精神,以科学至上、进化主义的思想为基础,将风俗区分为优劣,继而推行大规模的运动,旨在改革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鄙陋和恶劣的风俗习惯。③参见塚田誠之:《広西における“改良風俗”政策について: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文化政策の一齣》,第157—182 页。歌圩、不落夫家与迷信活动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在婚俗方面的改革往往与妇女解放相结合。当然,改革还包括卫生在内,在部分地区,人畜共居的干栏式住房也被作为改革对象。大部分政策和规则都伴随着劝告或罚金、禁止等举措,但在特定的民族地域施行时,因具体情况不同,现实效果也有所不同。特别是歌圩歌会习俗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后期,可以看到有些风俗改良活动,还逐渐与抗战运动相结合。
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领域的移风易俗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都带有移风易俗的性质。比如,提倡“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等。④人民出版社编辑:《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9、44 页。以火化为核心的殡葬制度改革,是新政府推动移风易俗的突出体现,对地方上的移风易俗影响很大。
1950年代,随着民族识别工作大规模展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关心有较大提高。宪法规定各民族平等,人人有保持和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这一时期,政府在少数民族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依次设置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国民党统治时期,少数民族将汉族视为“铁客”等,吓唬女性和儿童,传有“客进寨烂寨”“铁进袋烂袋”,形成了“苗瑶变婆”“苗汉结交产光”等谣谚⑤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侗族社会历史调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01—102 页。,民族关系相对紧张。1949年后,从语言上去除“苗仔”“瑶仔”“侗老”“壮古老”等称呼,民族间通婚也逐渐增多。随着民族平等和自由的呼声高涨,民族自治区的建设也不断完善,1951年8 月成立龙胜各族自治县,1952年12 月成立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融水苗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等,1956年又成立巴马瑶族自治县。同时,调整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围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诸问题也被认为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政策更注重提高生产力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如妨碍生产的风俗须依托当事人自觉改变。但对歌圩歌会,虽在浪费劳动时间上妨碍了生产,也不否定其自古是少数民族重视的习俗,要予以尊重,避免影响民族关系。⑥参见莫剑峰:《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处理民族风俗习惯有关的问题》,《广西日报》,1957年2 月23 日。是否妨碍生产成为评价风俗的一时标准。
除重视生产外,1950年代也开始出现乡村卫生相关的改良。如缺少厕所、村道上随处可见粪便,没有建厕造圈以收集粪尿作肥料等,因影响了生产而成为被改良的内容。为此,前期开始推行建造厕所和猪圈牛圈,以人粪尿液为肥料的政策①参见《把爱国卫生运动和积肥工作结合起来 很多乡村的农民已经做出很大的成绩》,《广西日报》,1952年8 月17 日。,因符合提高生产的实际需要,到后期逐渐普及广西各地乡村②参加《百花社僮族社员户户建厨圈猪》,《广西日报》,1958年1 月21 日。。有些地区则改变了传统的人畜共居的干栏式住居在一楼饲养家畜、二楼住人的习俗,将猪圈牛圈等分开建造。③参见《田阳那道绿机两屯群众 实行人畜分居》,《广西日报》,1953年1 月16 日。《以革命干劲改变千年陋习 天等奋战五昼夜实现人畜分居》,《广西日报》,1958年6 月10 日。《讲究卫生 减少疾病 平果都安各族人民改善居住条件》,《广西日报》,1958年6 月29 日。可见这些卫生相关的改良举措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生产服务的。
1957年,省政府开始介入改良歌圩歌会等影响劳动生产的习俗。当时认为,尽管山歌本身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需要给予充分尊重,但在歌圩中,也存在由其派生出来的旧社会的缺点,即少数已婚者谎称未婚而参加唱山歌,破坏他人夫妻感情,伤害了良好习俗,甚至引起械斗;且青年歌圩持续半月乃至20 天之久,妨碍了公社的劳动生产;不同村落之间的对歌引起矛盾、大吃大喝的浪费问题也需避免。所以,需要引导歌圩活动向优美、健康的方向发展。④参见李金光:《引导“歌圩”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广西日报》,1957年3 月28 日。除制约歌圩,还使其“为政治和宣传服务”。1958年,在《唱支山歌给党听》流行后,各地兴起以民歌、山歌宣传政治之风。同年5 月9 日,《广西日报》上刊登了《山歌:有力的宣传工具》一文,提到做什么事情都要唱歌,农民通过歌唱赞美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农村成立俱乐部后,进行政策的宣传、通知、广播等,也广泛使用歌曲,为政治和生产服务。此后,各地歌圩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以歌颂党和领袖,歌颂新社会、新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先进的生产经验。青年男女在恋爱歌中歌唱“新婚姻法”、婚姻自由。⑤详见广西僮族文学史编辑室,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广西僮族文学》(初稿),南宁: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5—68 页。1958年以后,政府开始对民间风俗区分好坏优劣,认为有些民族风俗习惯不适合社会主义和民族发展繁荣、影响生产,应该干涉。如壮族不建厕造圈的习惯,部分苗瑶地区为举行盛大的婚礼或祭神“还愿”而杀死耕牛的习俗。⑥参见方人:《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同化问题》,《广西日报》,1958年5 月2 日。推崇良俗是春节间为农业生产养精蓄锐,恶俗是迷信浪费和赌博等,大力倡导以文艺晚会宣传党的政策,引导健康、正确的方向。⑦参见丘如仑:《节前谈习俗》,《广西日报》,1963年1 月24 日。
1950年,国务院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及“改人、改戏、改制”政策,自1950年11 月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戏曲改革运动,旨在挖掘整理民族民间艺术遗产,使文学艺术沿着有领导的健康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1951年3 月,广西即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并先后在柳州、桂林、梧州设立分会;4 月1 日又创办《广西戏曲》周报,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全省戏曲改革运动。当时,组织艺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三反五反、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等运动,各剧团将宣传内容编成演唱材料,上街宣传。⑧详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文化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2—153 页。总体而言,在政府指导下,各种文艺活动原本不固定地点举办的歌圩活动,改为在公共场合;原来男女恋爱的山歌,也实际转为用普通话唱歌颂和宣传党的政策的红色歌曲,劳动妇女也被动员广泛参与其中。
伴随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否定迷信的活动也被放在较为重要的位置。1950年,宾阳县的道士礼仪被批判为迷信。①参见《迷信害人大,赶快破除它》,《广西日报》,1950年12 月8 日。三江县的少数民族生病后会“求神拜鬼”,认为生死由命,这些也被认为是迷信思想和宿命论。针对这些“迷信”活动,政府采取了不强制禁止,而是在提高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慢慢改革的方法。②参见《兴安土改覆查队员赵如昌黄榜金等违反民族政策》,《广西日报》,1953年3 月21 日。这种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关于婚姻习俗的改革进入法律层面。1950年4月,广西地区也颁布了婚姻法,废止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干涉虐待妇女、子女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提倡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此后,1952—1953年间,大力推动婚姻法的贯彻落实。首当其冲的是被视为“封建陋习”的不落夫家的改革。③参见《革除“长住娘家”封建陋习制止了妇女集体自杀 福建惠安开展已婚妇女“回夫家”运动》,《广西日报》,1953年2 月12 日。不过,这时的改革并非强制禁止或间接叫停,而是提倡在婚姻法的自主原则下,由男女双方自我思考处理。④参见《省妇联贯彻婚姻法农村调查组工作总结(续完)》,《广西日报》,1953年2 月5 日。1956年,田阳县不给不落夫家的女性发放工分,乡政府也不给她们发放粮食购买证,更拒绝她们参加生产。此后,尽管不落夫家被视为是无价值、应改变的风习,但其形成也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根源,简单处理或强令革除只会招致不满,甚至造成悲剧,应从群众的自觉出发耐心说教才能逐渐改变。故主张反对借助行政手段强制改革风俗的方式。⑤参见《不落夫家不给工分》,《广西日报》,1956年8 月8 日。因此,继续进行婚俗改革时也与其他风俗一样,以尊重个人意愿和自觉为主。
1950—1960年代,强调尊重各族民众风习的区政府,仍没有放弃推行改装的政策。各民族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提升,但差异和歧视问题仍然存在。最主要的表现集中在对待服饰的态度上。1957年,桂林市有瑶族干部开始呼吁成立瑶族自治县,但被说成地方民族主义受到打压。瑶民当时仍不大敢穿瑶族传统服饰,也不敢说瑶族语言,服饰在不少地方逐步失传。⑥参见莫模林:《瑶族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浅析》,载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社科文萃:2019年桂林市社科学术年会论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2020年,第297—298 页。但相比民国时期强制各族民众改装,1955—1957年,为满足少数民族对首饰的需要,首饰业生产了大量的耳环、手镯、银针等供应山区;196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商务局拨款七千两白银给首饰组加工少数民族的各种装饰品。“文革”期间,各族多不穿本民族服饰,而穿上大众服装。
尽管经历了多次改装易服的规定,大多数苗瑶侗族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自身的服饰。1950年代以后,融水苗族男子穿汉装的越来越多,即使是重大节日场合穿民族服饰者也寥寥无几;融水苗族女子的盛装比男装保存较好,几乎女孩子人人有苗装,年长者穿日常苗服。年轻女性也多穿汉装,只有出嫁、入葬或重大节日才穿民族服饰。但有些民族则对民族服装比较坚持,1970年代,外出当兵退伍回家的白裤瑶青年回到乡镇所在地时,仍必须脱下军装,换上白裤瑶传统服饰才能回村。南丹水族男女也对改装很抵触,拒绝改穿紧身衣、汉服、旗袍等。龙脊的壮族直到1980年代前,女性夏天上山劳动仍穿祖先的传统服饰白上衣。⑦参见玉时阶、玉璐:《广西世居民族服饰文化》,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10—111 页。在三江县侗族人的记忆中,50—60年代仍有将侗族服饰改为汉装的改装指示;70年代以后,侗族服装有了较大的变化,女性除中老年仍穿无领无扣对襟衣外,青年平时很少穿民族服装或百褶裙,劳动、赶圩都穿裤子。男性中青年日常服装与当地汉族趋同,逢年过节才穿民族传统服饰。苗族男青年也开始穿起中山装、国防装、青年装、休闲装或西装等,只有老年人才继续穿民族传统服装。水族、仫佬族等也改汉服,只有部分老人还穿民族服装。①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旅游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通过多次改装运动的经历,仅有较少的六七十岁的老年女性会在平日里穿民族服饰。②参见兼重努:《トン:民族一体化の動きと民族内部の多様性》,载末成道男·曾士才編:《東アジア》(講座世界の先住民族—ファースト·ピープルズの現在),东京:明石書店,2005年,第333—351 页。
进入1950年代后,广西区政府比以往更着力于殡葬改革。民国以来只是批判奢侈传统的葬式而推进卫生经济的葬式。1949年,广西各地实行殡葬改革,红白喜事从俭。尤其是自1956年开始,政府推行全面的殡葬改革,提倡以火葬取代土葬,以简单追悼会取代繁琐的传统葬式。包括废除葬礼中迷信内容并简化葬式、推进火葬、在贫瘠地区建设公墓等内容。1978年后,广西各地相继推行以火葬为主的殡葬改革。③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1979—2005 社会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150—152 页。各地殡仪馆在承办收殓、停灵、埋葬、筑墓、造碑、举办追悼会的同时,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逐步取代丧主对死者的拜祭、做道场、看风水、择吉日等传统习俗,节省开支,减轻了民众负担,逐步形成新社会风尚。
概而言之,1950年代的移风易俗对迷信和婚姻的改革等,虽沿袭1930年代的风俗改良,但主要集中于之前不甚彻底的不落夫家和迷信活动等方面。不同之处在于移风易俗的方法,不是政府勒令强制改革而是以民众觉悟、自发性为基础。一方面,推行自治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文化,肯定了民国以来被禁止的歌圩为民族文化特征;另一方面,重视生产,将妨碍生产的习俗作为改良对象。
三、1980年代以来的“生活革命”
1978年以后,政府再次重视与民族文化和风俗有关的政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或风俗习惯唤起了观光客对边境旅游的兴趣,作为观光资源的价值也开始受到关注。和1950年代有很大不同,1980年以后,民族风情旅游在包括广西在内的西南地区兴盛起来。1987年以来,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除历来受重视的婚丧与迷信的移风易俗以外,近年还增加了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话题④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2 月20 日。。
近几十年来,移风易俗作为推动广西社会建设的手段之一,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等国家治理的方针政策都涉及移风易俗。广西新农村建设中,提出了要带头发展经济、帮助群众致富、关心困难群众、移风易俗、参与公益事业、维护社会稳定、参与基层组织建设等意见。⑤周健:《关于广西新农村建设经验、问题与对策的调查与研究》,葛忠兴主编:《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10 页。广西乡村振兴战略中,也强调了移风易俗在乡村治理、保障乡风文明、推动传统乡风向现代文明乡风转变、培育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的意义。⑥贺祖斌等:《广西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生态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6—19 页。2019年,广西民政事业在发展规划中,提到社会救助在脱贫中的意义,养老服务改革及文明节俭治丧、节地生态安葬、文明低碳扫墓等殡葬改革的重要性。⑦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83—285 页。乡村振兴战略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四个方面提出乡风文明建设的要求;甚至强调移风易俗是保持乡土味道和乡村风貌,留住乡愁的重要途径之一。①贺祖斌,林春逸等:《广西乡村振兴战略与实践·文化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第7—8 页。当下移风易俗的目的、侧重点和方式,都与历来的改良有所不同,但内容上几乎一以贯之。如婚俗、丧葬、杂神信仰等经过反复移易依然顽强存在的风习仍是当下重要的移易对象。文明乡风以移风易俗、倡导新风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为重点。随着乡村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带来的民众日常生活的全面改善以及城镇型新生活方式的普及,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建设和民众参与的移风易俗,在当地掀起了一系列“生活革命”。这时期的改革内容涉及甚广,以下以传统文化的复活、民族关系的变化、乡村卫生与养老、寨改工程与乡风文明、殡葬改革等分别进行梳理。
1980年代是传统文化的复活期。广西各少数民族多拥有本民族传统的村寨组织,如侗族的寨老制和习惯法、苗族的鼓词、瑶族的理词等。寨老组织变身为老年人协会或老年人组织,在处理家庭和婚姻矛盾、土地山林纠纷时,寨老仍使用传统习惯法进行调节,借助巫师和寨老的传统教育,鼓励民众自觉自愿移风易俗。又如服装问题,伍新福在《苗族文化史》中谈到,他1980年代在融水一带实地考察苗族,年轻女性平时服装已与汉族没区别,多穿着从市场买回来的衣服和鞋帽,但节庆时仍多着传统民族服饰,但很少银饰。这代表了当时区内各县苗族的普遍状况。②伍新福:《苗族文化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198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化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建设思路,服饰等物质文化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发展出符合现代生活理念的文化交流、旅游休闲等功能。同时,融水县通过举办各种苗族节会,使服饰文化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推动了苗族传统服饰向现代化方向发展。③尹红:《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 期。1990年,桂林的恭城成立瑶族自治县,成为广西最年轻的瑶族自治县。当时,县庆组成游行队伍,县直机关和各乡镇主动从外地购置经过改良的瑶族服饰,大多被认为没有本地特色。此后,县民族局为举办庆祝活动而要求制作瑶族服饰,新制作的服饰使用的材质、花边纹饰、制作工艺都与传统样式有很大差别。近年,自治县推行瑶族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瑶族文化得到很大重视。行政机关、行业窗口推行瑶族服饰,瑶人穿民族服饰不再是令人羞耻的事了。④参见莫模林:《瑶族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浅析》,载桂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隆斌主编:《社科文萃》,沈阳:沈阳出版社,2020年,第297—298 页。
近年来,三江县侗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及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契机是三江县开始将民族风情作为旅游资源进行民族旅游开发。位于林溪乡的程阳侗寨的传统木结构建筑永济桥,1982年被指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程阳八寨2008年被指定为国家4A 级景区。2000年以后三江县对民间工艺、手工艺品进行再评价,加大保护。2007年,文体局把侗族刺绣申请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与县民族局合作在次年国庆节举办民族手工艺制作大赛,由当地女性将纺线和织布展演给游客看。2008年,县政府公布包含16 个项目的第一批非遗名录,其中14 个项目与侗族文化有关。不过,高涨的民族旅游业对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进行了区分。对于游客而言,似乎侗族等少数民族制作的手工艺品才有纪念价值,汉族族群的手工艺品受到了打击。比如,因为无人光顾,六甲人不再卖自己的手工艺品,而本地侗族开始将六甲人小孩的帽子和布鞋类手工艺品卖给游客;林溪侗族的绣花鞋比富禄客家的绣花鞋卖得好,大概也是这个原因。⑤参见金裕美:《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民族族群的多样性——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汉族和他们的手工艺品为例》,载寸云激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5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646—647 页。
这时期乡村卫生与养老福利保障受到更高的重视。1999年开始,政府注重完善农村医疗卫生设施以解决乡村缺医缺药看病难问题,并重视农村安全卫生用水和卫生厕所的改造。2006年底,针对广西农村普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差情况,政府作出实施“城乡清洁工程”的决策。主要内容有4 点:一是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落后的人居环境;二是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清洁大行动,创造整洁、优美、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三是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引导农民讲究卫生、移风易俗、摈弃陋习,推进乡风文明;四是树立一批文明卫生村镇先进典型,打造品牌示范效应。①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办:《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有力抓手:开展“城乡清洁工程”创建活动的探索、成效和经验》,中央文明办调研组,河北省文明办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调研报告文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0—181 页。1999年,推出“2000-2005年广西农村小康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05年所有乡镇都应建有敬老院,有条件的村镇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引导农民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公益事多办、鬼事不办,以创建“文明户文明村”。②参见《2000—2005年广西农村小康行动计划研究》,载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决策咨询研究成果选编 3》,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93 页。这些变革都是为了乡风文明而展开的。
2013年,在第一次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会议中提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根据《“美丽广西”乡村建设重大活动规划纲要(2013—2020)》,注重提升清洁、生态、宜居和幸福乡村,分4 阶段8年完成。其中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是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农村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设施建设、乡村美化建设、培育乡村新行为、新习惯、新风尚等6 个方面。最后一点即强调引导民众移风易俗,改变生活习惯,通过订立村规民约,营造文明、整洁、卫生的乡村环境。其他解读也涉及绿化美化乡村生活环境、饮用水安全和道路设施建设等。③参见彭清华:《在“美丽广西 生态乡村”活动电视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广西日报》,2014年11 月15 日。同年5 月14 日起,《广西日报》开设专栏“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系列谈,在全区14 个市,每个市选择1 个乡村进行清洁乡村活动的持续跟踪报道。④参见《乘势而进 再接再厉 提升效果》,《广西日报》,2013年10 月17 日。《武鸣县开展“清洁乡村”活动:“八个一”绘就美丽画卷》,《广西日报》,2013年12 月16 日。《聚人人之力成整治新声势》,《广西日报》,2014年3 月19 日。《三访南宁市西乡塘区忠良村:五彩画卷显魅力》,《广西日报》,2014年9 月24 日。其后,2016年1 月29 日,区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洁条例》,集中针对因地制宜建设乡村卫生厕所、垃圾和污水处理等乡村清洁设施,配备符合要求的卫生保洁专用设施设备;支持乡村建设沼气池等设施,处置乡村垃圾、畜禽养殖废粪便、农作物秸秆等生产、生活废弃物。⑤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清洁条例》,《广西日报》,2016年2 月1 日。近年来,区内乡村各家各户动手清扫垃圾并进行集中整理分类,清洁房屋工作,整治环境卫生,改善村庄面貌,清洁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关注民生的全方位乡村改革下,特别是用电、自来水、炉灶、卫生厕所等在乡村普及,都带有生活革命的意义。从2008年起,区政府为解决少数民族村寨连片木质结构房屋火灾隐患问题,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条件,拨出专款约3 亿元,用3年时间实施“4+1”村寨防火改造工程,即寨改、电改、水改、灶改加房改。⑥电改是村寨及木板室内电线路的用电规范和防火整改。水改是加强人畜饮水,建立消防用水管道、消防池等设施。灶改是将木板房内火塘改造为不易引起火灾的厨灶,将灶从木造二楼搬到砖造一楼。还有将木板房改为砖混结构房的房改。市、县也拨出相应资金组织实施。寨改主要是对集中连片50 户以上的木板房村寨开设防火线(一般为12 米以上),分割成30 户以下,使大寨化小,有利于防火救灾。“村容整洁”问题被视为新农村建设最薄弱的环节,四改也是为了解决农村柴火垛、厕所等问题。包括开辟防火隔离带、建设消防水池、改造火塘和旧电气线路、道路建设等在内的防火综合改造工程至2012年竣工,据统计,改造地区重大火灾事故下降了70%,整体改善了人炊、交通及村庄环境。①《中国民族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民族年鉴 2013》(总第19 期),《中国民族年鉴》编辑部,2013年,第677 页。至2013年,广西累计完成投资12.8 亿元,共完成4 市14 个县区1933 个村寨的防火改造任务。②《广西6年投12.8 亿改造资金 1933 个村寨建“防火墙”》,《当代生活报》,2014年3 月23 日。
关于殡葬改革与葬式的移风易俗。早在1966年,南宁市火葬场建成使用后,广西开始实施由政府指导和管理、以科学的方法和仪式处理遗体、安慰丧主及其亲友的特殊殡葬服务。1978年后,广西各地相继推行以火葬为主的殡葬改革。如灵川县于1986年在鸟笼铺北、桂黄公路西侧建立面积20 亩的公墓场,积极宣传和推行火葬。③参见灵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灵川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2 月,第681 页。1980年代后期,针对民间仍然存在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有些县市在自愿情况下,积极争取家族长、寨老、巫师等当地有影响人物的支持,或利用民间组织形式,或以其他方式代替操办酒席等新方式,改革婚丧习俗,取得一定成效。如1988年前田阳县一些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现象愈演愈烈,耗费大量资财,1989年县里成立红白事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全县红白喜事改革。全县15 个乡成立了红白喜事改革指导委员会,在153 个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广播、墙报等积极开展移风易俗,树文明新风的宣传,至1990年初,全县已有540 起红事从简办理。④参见王燕:《破婚丧陋习、树文明新风,田阳县抓红白事改革取得成效》,《广西日报》,1990年2 月2 日。此外,还推行以播放电影代替酒宴的方式,如富川县瑶族乡自1990年以来改变了过去大办酒席的做法,办婚丧事的主人家邀请县里的电影放映队到家门口或村里空地上放映一两场电影,受到其他村民欢迎。⑤何小洪等:《瑶乡新俗——礼仪电影》,《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 月31 日。
1994年3 月,区政府颁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殡葬管理办法》,积极推进殡葬改革,破除封建迷信的丧葬陋俗,文明节俭办丧事。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后,传统葬式得到复苏,个别地区乡村又兴起大操大办丧葬仪式的风气。⑥参见谢之雄主编:《广西年鉴 1995》,南宁:广西年鉴社,第625—626 页。其后,政府大力推行火葬的宣传工作,并强化殡葬行政管理。1996年4 月,为纪念倡导火葬40 周年,宣传殡葬改革,《广西日报》刊登了殡葬改革专版,广西电视台也作了专题访谈。⑦参见许家康主编:《广西年鉴 1997》,南宁:广西年鉴社,第393 页。到2005年,全区设有殡仪馆、公墓和殡葬管理单位等殡仪服务机构56个。⑧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1979-2005 社会卷》,第150—152 页。2000年以来,众多媒体纷纷提倡绿色文明公益性葬式。⑨参见《再难也要做的事》,《广西政法报》,2001年3 月23 日。《移风易俗 文明扫墓》,《贵港日报》,2008年4 月3日。《太和花园清明防火压力重——有关部门呼吁市民移风易俗文明拜祭》,《梧州日报》,2009年4 月4 日。《春节上坟烧纸引发山火——消防部门希望人们移风易俗,文明祭奠》,《桂林晚报》,2010年2 月20 日。《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殡葬新风》,《柳州晚报》,2010年11 月29 日。《移风易俗,用“添绿”来送出祝福 广西各地举行新春植树“团拜”》,《南国早报》,2012年1 月30 日。2013年以来的殡葬改革,进一步推崇厚养薄葬,绿色殡葬。南宁、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平乐等各市县出台了面向不同群众减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为主要内容的惠民政策。同时,推行节地生态安葬,各地鼓励引导花坛葬、海葬、草坪葬、墙壁葬、骨灰堂室内格位葬等方式。2018年,区又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村镇创建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在百县千镇万村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推进乡村移风易俗,现已有94%的建制村建立了“一约四会”,即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协会、道德评议会,由村里有威望德行者担任会长,监督和约束村民,依托这些民间组织,规范了各村镇民众的丧葬行为,深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①参见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202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4—235 页。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后,为了响应疫情防控,除补贴殡葬外,殡葬服务机构也逐步开通网上祭扫服务。2020年,实行清明祭扫防控,全区殡葬服务机构推出免费敬赠鲜花、挂黄丝带、擦拭墓碑、代客祭扫等形式,甚至开展“云祭扫”提供免费网络祭扫服务,弥补群众因疫情不能到现场祭扫的遗憾。清明节当天,全区各殡仪馆、公墓同时开展代祭扫公益活动并同步视频直播。②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广西多措并举综合推进殡葬改革移风易俗》,中国政府网(新闻中心之地方动态),http://www.mca.gov.cn/article/xw/dfdt/202005/20200500027310.shtml,发布日期:2020年5 月7 日;浏览日期:2022年10 月8 日。
1980年代以后,各地民众努力恢复的风俗,很多是在过去的风俗改良或移风易俗政策中被强制中断,或已经消失的民俗。人们所谓过去的、传统的形态,其实与当下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看见的样式和形态有许多不同。除此之外,还有政策引导或民众自发形成的层出不穷的新习俗和“新生”乡村文明。村寨改革在广西各村寨中受到普遍的接受,特别是用电、用水、卫生厕所的普及。卫生整洁的乡村环境,殡葬改革从简易葬式到多元生态葬式,从去除迷信到文明祭扫再到云祭扫,与科学技术革命关联的城镇新型生活等,也在慢慢从市镇渗透到乡村。笔者认为,因为是相对而言自发自由的革新方式,才使得当下民众自我选择的移风易俗,更有了“生活革命”的意义。
四、讨论
广西的风俗改革,可以说从近代一直延续到当下。然而,却很难说是连贯发展至今的历史过程。
从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风俗改良的具体举措和实施状况来看,各阶段的政策其实有所联系又存在差异。在看待风俗习惯的基准上,1930年代的风俗改良,当局是以儒教思想为准区分良俗和恶俗,对后者予以禁止废除,特别是对婚姻习俗与信仰活动,这与1950年代的移风易俗有共通之处。1950年代的文化政策也区分良善之俗与陋劣之俗,但标准不再只是以儒教为主导,而将中心落在劳动生产上。在此标准下,不直接影响生产的风习受到尊重,并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延续,妨碍生产的风习或其中一部分内容成为迫切需要被改革的对象。相比之下,1980年代后则以符合健康文明乡风为基础,有更丰富的要求,在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平等自由的同时,也鼓励和引导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传统有异的新式风俗;在城镇化背景下的旅游开发和乡村建设等活动推动下,民众也获得了更多自主自由参与的可能性。
在社会生活方式和风俗改革的方法上,1930年代新桂系政府的风俗改良针对迷信活动、改装、婚丧生寿、歌圩歌会等习俗的一系列改良都是强制的。1950年代以后的移风易俗,除了早婚、不落夫家和红白喜事的奢侈作风等所谓带有封建色彩习俗的改革外,表面上都不加以强制,而依托民众自觉。同时,到1950年代后期,基于尊重民族文化的原则,政策相对弹性,唱山歌耽误生产及男女情爱的部分被视为应改良的内容,也出现了采用山歌来歌颂政权宣传政策等引导习俗为政治所用的情况。整体而言,前两个阶段的政策存在不少沿袭相承的内容,如对不落夫家的婚俗与迷信活动,进行了反复的改革,也有过中断和调整。改革开放后,随着各族村寨组织的复活,传统文化复兴的力量也得到恢复,过去被强制废止或勒令改革的服饰和迷信活动及其他风习也获得一线生机,有些甚至出现新样貌新风俗。当下的移风易俗几乎成为从乡村发展到城镇化战略各项战略均绕不开的话题,更加鼓励相关主体自觉自愿的方式。
可以说,当下目之所及的广西地区的民俗文化和民众的社会生活,实际上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俗改良,国家与民俗、国家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特别是民国以来的勒令禁绝与“文革”期间的强制中断后变化至今的结果。在所谓“传统文化”的消失、断裂与复活的同时,顺应城镇化和科技发展,当下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社会生活领域及新动向、新风俗,如旅游开发下的民俗体验活动,疫情下的云祭扫云服务等。这些经历了“消失”再复活的传统与依托多样手段产生的新风俗互动下的日常生活的整体,不仅有国家主体的政策,也有民众的参与与推动、传媒手段和科技手段的配合,更体现了当下“生活革命”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只看到“民”和“俗”,而看不到近代中国语境中操控着民众生活的风俗改良或移风易俗的有形或无形之手,我们或许不能真正理解民俗学所要抵达的生活世界的真谛。
高丙中在讨论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时曾指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既成性、未完成性与开放性、自在性与反思性、理所当然性等特点。所以在移风易俗时,充分认知“日常”与“生活”的内在紧张关系,也要超越其既承、自在的格局。①参见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主流政治表述没有贬低普通人的说法,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实践上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而类似20 世纪初的非遗保护运动那样的社会改革,给了普通人为了推动日常生活正当化的机会,民众互动、地方政府对民间组织、民间文化的认可、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代表内容给予了国家遗产的地位,传统的与未来的、国家的与民间的、意识形态与老百姓的喜闻乐见不仅互不冲突,且相互融洽,也为民俗学者积极参与其中提供了议题和可能性。对学科本身,1980年代以后,“民俗生活”概念的提出,将民俗学研究从过去的遗留物取向拉到“当下”。而非遗保护的理念与实践让“过去”与“未来”相反相成的制度机制被建立起来。今后论述日常生活时应意识到未来维度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和公共生活中,倡导以完成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的理论建设,推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政治经济活动中等整个体制中的优先这一社会改革的目标。针对移风易俗这一关系国家体制与民间社会、社会生活改革与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话题,有必要结合中国社会或社会参与的文化实践、公共政策实践已经走通的道路,把日常生活纳入进来,并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予以呈现与诠释,从而建立起日常生活的完整时间意识,继而超越朝向过去的民俗学,将视线放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并持续进行的生活革命。
在承认社会文化延续性的基础上,中国民众“当下”正在经验的日常生活,可以说都是在先辈“过去”的决策或政策、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抵抗与认同的一系列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在变化不变之间不断调整、发展至今的,这些构成了移风易俗的过程。而外部的媒体媒介、近代技术的进步影响(催化或推动)了这种移风易俗的进程。正如过去的决策和政策会对当下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当下的选择,也势必会影响下一辈、下一代人的日常生活。回到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中,政府在推行带有移风易俗性质的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措或社会变革时,须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在剧烈的对峙与冲突之后,政府与民众相互妥协与调适,才是社会进步之正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