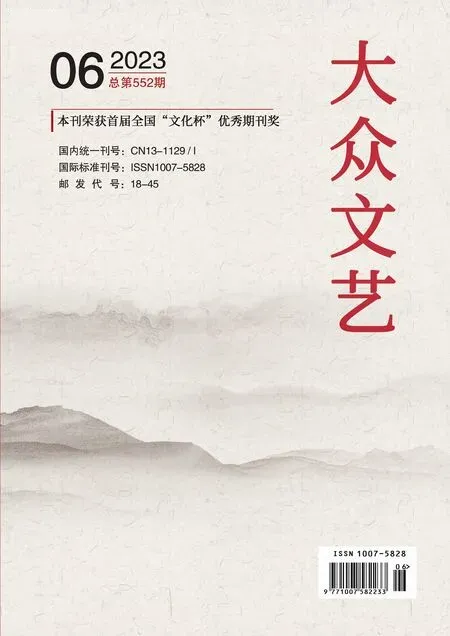“慈悲”观视域下的唐窟观音形象及其再创作*
2023-09-02李颖
李 颖
(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从前秦十六国、北朝至元朝,经历代兴建的敦煌莫高窟,以佛像、经变、佛教史迹、佛教故事和供养人等,向人们传述丰富的佛教文化,折射出历史、政治、文化的流变,融汇了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的敦煌石窟,更成为艺术家无限向往的“朝圣之地”。
作为敦煌石窟艺术形象之一的观音,自东晋时期传入我国,千余年来经历代高僧大德的弘扬,帝王卿相的推崇、饱学鸿儒的提倡,已深入人心,为百姓所熟知,成为滋养人们精神世界和抚慰现实困境的重要载体,大量宗教古籍、经论及其哲理奥义,也正是被赋予鲜活、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逐渐与儒、道文化共同汇入到中华文化深邃的长河之中。
一、观音名称的由来
“观音”一词可追溯至叙利亚摩尼教的阿拉姆语:Kаriа。早在公元3至4世纪的中亚,摩尼教、佛教等宗教已在这一地区逐步流传,各宗教之间相互影响,Kаriа与佛教梵语融合产生Аvаlоkitеśvаrа,其含义“可观宇宙,并全知,一呼,即刻救苦救难”[1]。在我国本土,观音最早的译名为:光世音,唐太宗时期定名为“观世音”,因避讳唐太宗的名字“李世民”,将“观世音”的世字去掉,成为“观音”。
观音,后来又作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光世音菩萨等,从字面解释就是“观察(世间民众的)声音”的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观音容貌慈祥,体态端庄,常持净瓶杨柳,寓意给予世间众生清凉,消除疾苦。净瓶和杨柳与佛教早期僧团生活有关,净瓶是盥手的器具,杨柳用作刷牙清洁,逐步演化代表观音无量的智慧和神通的法器。当人们遇到灾难时,只要念“观音”名号,观音便挥扬柳枝、倾洒甘露施以救度。在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观音被尊为上首菩萨,位居各大菩萨之首,与大势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身边的胁侍菩萨,并称“西方三圣”。最早的观音,都是健壮、留胡须的男身像,直到中国宋朝时期,才出现体态丰腴、婀娜的女身像。据《妙法莲华经》记载“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2]观音菩萨在众多佛教菩萨形象中最为人所崇奉,影响也最大。
二、“虽善无征”的观音形象
(一)“法身无体,以悲为体”的观音形象
观音不似佛教的释迦牟尼生平确切可考,借《红楼梦》里一句“虽善无征”形容观音虽慈悲,但形象却不固定具体最为贴切。省庵法师也有:观音在我们心中,与我们不二,无须取相之说。而憨山大师则认为“法身无体,以悲为体”是观音形象的根本,无论哪种解释“悲”均为观音形象的核心。“悲”原意为痛苦,由痛苦而生悲情。观音之“悲”是悲悯众生,拔除痛苦,“悲”与慈爱众生,给予快乐的“慈”相辅相成。佛教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能超越自身而感同身受他人之疾苦,是一种超然的悲悯,并从对世间人兽、顽石、草木等不可数的,一切有情众生的友善仁爱,体现着终极的平等和慈爱。为此,观音会有三十三种不同的化生,如敦煌盛唐时期所建45窟南壁绘制的观音经变画,观音应声化现为三十三种不同世俗人物,体现有求必应、救苦救难的场面。除了此之外,观音也会幻化成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圣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准胝观音等不同形象应声救苦。形形色色的观音形象,为雕塑、绘画、舞蹈等艺术形象的再创造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丰富的构想。
(二)“关照世俗,对应母性”的观音形象
宋元时期,从原有古印度形象狰狞、狞厉的男像转为世俗气息极浓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民间传说妙善公主和马郎妇故事激发下,也得力于民间艺术家的创造,上接西王母传说和无生老母信仰,各类娘娘、老母、妈祖、神化的村姑,一众女神涌现形成壮丽的女性神信仰潮流。女神之首的观音以其亲和、柔美,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的气质彻底征服和感召了大众,改变了人们的精神情趣。观音“世俗”化并非对其的贬义,而是指观音形象深入民间。与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内心世界相对应,观音如同满足所有孩子愿望的魅力十足且慈爱的母亲,永远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对于一种外来文化,老百姓总会基于现实的需求,对其进行选择和适度的发挥,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身的文化传统,在现实中不断去改造和同化它。
此外,历史的演进使男性的社会分工权重增强,威严强势的“父权”在两性关系中虽占据主导优势,但较难成为人们倾诉意愿的对象,女性自我意识逐步弱化,转而家庭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主渠道,因此所谓“积善人家、香火继嗣”成为女性自我身份归属认同的关键,因此,民间“送子观音”在世俗强大宏愿的推力下应运而生,作为母性形象存在的观音就此得以彰显。
在经典文学《西游记》中不难窥见百姓对诸神的态度,孙悟空上天入地对谁都瞧不上眼,唯独在慈祥的观音菩萨面前收敛起狞厉乖张,诉委屈、搬救兵、讨主意,俯首帖耳、乖巧可人起来,只因观音面对众生不离不弃,每每前去开化和搭救,乃至对待各路妖魔也是怜爱备至,即使化作各色面目在人间作恶的精怪妖孽,她也只是一概收回循循善诱、教化了事,慈眉善目的观音,肌肤光滑圆润,纤纤玉指抚摇翠绿欲滴的柳叶,未施以教化已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很难将其与留有胡须、威猛彪悍的印度男性相联系,这慈母般怜惜众生的观音又怎能不被民众所喜爱和抬高。
(三)“赋彩于形,鲜活于世”的观音形象
在宗教场域之外人的世俗生活中,观音被赋予了诸多职能,江南多省视观音催子旺子,福延子嗣之能,福建顺德地区人们将“生仔”衍生出“生菜(财)”之意[3],在观音借库还库日向其祈祷财运亨通,连原本龙王降雨的活儿,也因百姓的偏爱嫁接到观音身上。其中,民间灯彩歌舞节目【观音坐莲】就是流传在江西石城县琴江镇一带,表现观音治水、施雨于人间的慈悲善举,借以祈求保佑来年风调雨顺。它以多人和彩灯组成丈尺的高台,造型独特,在莲花彩灯间一朵鲜艳欲滴的花蕊,衬托着亭亭玉立少女装扮的观音娘娘。歌舞表演的形式,内容分为“巡天”“入凡”“洒露”三个部分。“巡天”是表现浩海烟云(由爆竹烟火造成效果)、雾涛滚滚中观音在高高的灯台上挥云帚,众花仙簇拥着巡天而行。“入凡”是表现波涛汹涌,浊浪排天,观音率六位荷花仙女同二十四个花神组成洪水巨浪搏斗的情景,观音踏浪将洪水收入净瓶。“洒露”是表现骄阳似火,万物枯黄,田土龟裂,酷热炙人,六天将赤膊求雨,观音娘娘挥动柳枝,洒下甘露,滋润万物,普度众生。造型富丽堂皇,气势磅礴。莲台旁有六位天将推着莲台,步伐稳重徐徐前进。台前花神手持莲花灯簇拥,象征着一年二十四个节令,如花似锦。三位饰演天将的男子,手执高于莲台的宝伞、日月伞、灯柱,紧随在莲台左右及后方,整个灯队色彩斑斓,场面壮观无比,令人目不暇接。
由此可见,历经与中国文化交融,渗透百姓精神意识,慈悲救难的观音形象已然是深入民心,并赋予了鲜活的再创造。
(四)“艺术重构,再造升华”的观音形象
艺术重构的观音形象,笔者根据舞蹈身体语言学理论大体将其分为三种构成形态:其一,基于宗教意义和信仰意图的原生观音形象;其二,基于信仰和民俗生活需要,在民间产生的自发创造力催生出的次生观音形象;其三,超越狭义主观信仰和民俗事相,基于审美经验,经由艺术的重组加工、再创造的再生观音形象。
宗教对于大多数人是一种看不见、虚无缥缈的事物,人们需要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将其转化为现实,使自身与信仰对象间产生实实在在的联系。观音形象,意涵了救世主的神圣信仰,如何救世?是一个现实问题,称念其名号可获救助,诵读其经文或称颂咒语均可得不可思议之妙处,这些较之有着千手千眼或怀托溜光水滑胖娃娃的观音原生形象对于普罗大众,由于其是可被具体把握的形象,与世人具体祈祷诉求直接对应,更易建立沟通与互动,这类原生形象是直接的、实在的、可依的和具体化的,有助于与信仰者之间产生紧密的关系。
原生观音自东晋南北朝时期来到中国,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的普遍规律,似乎并不适合观音在中国的传播路径,观音一经出现可谓受到中国民众强烈回应。究其原因,中国人自古崇拜上天,效法天地,在天人感应中首先确立的是道德性。此外,中国人也崇拜道德高尚的圣人,圣人是否胜勇无边能救助苦难并不重要,圣人给予普罗大众是一种道德和教化。崇拜神仙的思想也相当普遍,各路神仙也是自唐之后才具有了救助世人的功能,此前的神仙多以长生不老、逍遥自在为“人设”目标。而祖先崇拜是依靠血缘关系在宗法治下维系的关系,祖先崇拜中也少见任何神威救助功能。鬼神崇拜、自然神崇拜更是在观音信仰前缺乏威力。观音形象一经来到中国,于世人观念中它统摄一切而且神力无边,在上述一切崇拜的现象中脱颖而出,是一种平等的、威猛的、智慧的、慈悲的、亲和的形象,它突破了中国本土信仰形象功能狭窄的弊端成为人们心中的保护神。隋唐之前观音多为神灵保佑,隋唐后拓展为智慧觉悟、净土接引、咒语加持、福德积累等多种信仰形态,佛教理论、经典依据研究并行,与其他信仰相互激荡,支撑推进这一信仰到了全新高度,也为次生观音形象的产生积累了强大的民众力量。
信仰是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精神或天赋。观音形象随着观音信仰不断的演变成为融入中国人民俗生活的一部分,彰显出民族群体慈悲、友善、和谐的禀赋,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自发创造力不断被加以塑造。在此前讨论的男像到女像演变中,这股力量使异域情调更贴合现实的地气儿,在各地节庆民俗艺术活动中,如:民间灯彩歌舞节目【观音坐莲】中这股力量催生出次生观音形象最夺目的,结构缜密、形式完整的新式样。然而这一类型的观音形象仍然不可脱离虔诚信仰基础,在与民俗生活的融入中以娱神、娱人、自娱的样貌活泼泼的生长于民间,成为今天我们追根溯源观音形象,艺术的再造观音形象不可或缺的、鲜活的动态参照。
再生观音形象超越狭义主观信仰和民俗事相,它是群体或个体的审美经验,是独特的,可被感知和被共鸣的,经由艺术化的重组、加工、再创造呈现于当下的艺术舞台,作用于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借鉴壁画原貌的基础上,予以舞蹈姿态的重组和舞韵、舞律的变化,是当代敦煌题材舞蹈创作中动作源发掘的重要方式,除经变画中的飞天、天宫乐舞中的反弹琵琶舞伎外,艺术家关注较多的当属具观音。敦煌初唐第57窟又名“美人窟”为观音原型创作的独舞《敦煌彩塑》是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系列的舞蹈。1980年在全国首届舞蹈比赛中荣获创作二等奖,表演一等奖。肃穆幽静的中心台位,青烟缭绕,一缕定点柔光勾勒出神态端庄、静雅、曲线婀娜的观音形象,大幕缓缓开启之时,犹如打开斑斑驳驳、尘封千年的石窟大门,随着委婉清雅的乐曲,塑像活起来了,她不甘孤寂,向往凡心尘世、一步一步走出洞壁,领略人间烟火。她游历山丘溪水,对一草一木、一花一蕊都备感亲切;她光顾湖光山色,对青枝茂叶、飞鸟啼鸣更是情意绵绵;她急步人群之间,对凡人笑语、喧闹如潮的景象惊喜不止,目不暇接。面对如此沁人心脾的繁多新异,作者创编了一组错步凌空跳跃,一串连续高速旋转的舞蹈语言和高难技巧,淋漓尽致地把特定的内心情感倾诉无余,将作品的意蕴、舞蹈的意指顿时推向了高潮。然而,对人间的向往无论多么炽热,它毕竟是向往,不甘孤寂的彩绘终归没有回天之力,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定位,无奈地回返于深深的洞窟。
围绕敦煌众多形象的艺术再创造作品层出不穷,直至2005年央视春晚中以唐窟三十三种变相的观音为原型创作的《千手观音》可谓将观音形象发挥到了极致[4]。抛开张继刚娴熟的舞技和高科技声光电运用,只就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及普遍的“群众基础”,以及千百年来凝聚起的巨大慈悲感召力,在形象塑造上获得成功已是必然。无声而静穆的壁画形象,在限制的手臂动作的不断重组叠加下,极尽细腻、美妙,赋予观音形象以生命的浪漫和活力,将观音广化众生的博大胸怀与人们追求和谐、理想的精神境界相呼应,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手数量的多寡,意在体现观音的慈悲,以无量之眼关照无量众生,以无量之手帮助无量众生。舞蹈动作正是以手做文章,以极度夸张的创作手法使“千手”的形象,比壁画原型更加瑰丽,目不暇接的视觉影像强化了博大、万能、奇异和神圣的美感。
舞蹈创编层次布局严密,动中有静,静中有舞,通过创作人起、行、顿、止的舞台空间流动安排,仿若表现出慈悲观音犹如悉达多游历四方城,体悟人间的千百种疾苦,欲与世人同甘苦的形象,传递出质朴无华和不同凡俗的神情,显示出耐人回味的清新的艺术活力。更可贵的是作品渗透了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将茫茫大漠深处沉寂千年的彩绘塑像演化成活,一帧桢、一幅幅丰姿异态款款舞出石窟,呈现于当下的艺术舞台,使其不再孤寂。
观音固有的祥和、端庄、缄默无言的形象深入人心,编者保留了此观音形象的重要特征,使观众感到舞台形象真实可信,然而打破常规以聋哑演员塑造观音形象的思路,更使得观音的无言与演员的沉默相得益彰,此举并非创作的投机或噱头,而是体现出万物皆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主体的存在,关怀生命,敬畏生命,是佛教慈悲的思想基础,舞蹈中演员完美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这一文化精神内涵。聋哑舞者鲜活的生命融入美、创造美、表现美,与我们无差别、平等的展现与奉献,从而完成了常人都不易达到的艺术境界,不禁令人惊叹和敬畏。
结语
两千年前,由印度、尼泊尔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在敦煌这片神奇戈壁里扎根,不禁让人感叹华夏文明的恢宏与胸襟的广阔,吸纳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又以其独特的方式不断更迭完善,创造出更璀璨的文化广播四方。笔者从观音的历史渊源说开,进而对成功的观音题材的舞蹈作品进行分析,并非宣扬“人人礼佛、家家拜佛”,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他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大美无言的境界,从而启迪智慧与人生。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艺术作品的品质高低,不仅在于编者纯熟的编创技术与手法,更考验编者对将要塑造的对象,具有的文化底蕴的深度剖析,融入编者独特的艺术视角。因此,我们不断地再出发、重返敦煌,感受河西走廊上儒、释、道及其他宗教文化不断交汇浸润后的成像,其地域性、宗教性、艺术性鲜明而夺目。同时,不同文明展现出彼此的豁达胸襟和包容精神,它们打破守成与封闭,互相尊重与认同进而交流促进,这是基于时代永恒的精神动力,在新的人文环境与时代条件下不断创新使敦煌艺术焕发新的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