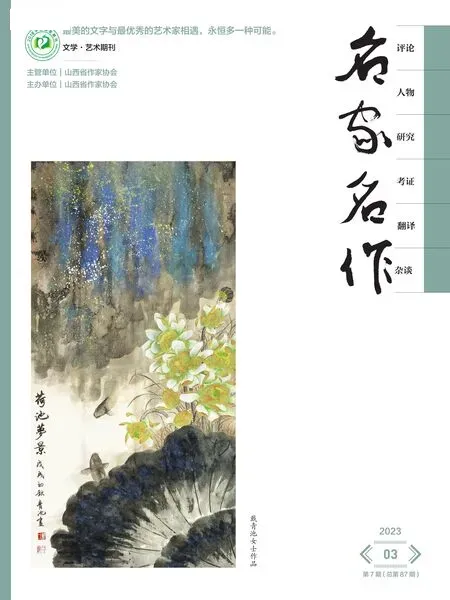齐梁之际文学政治体的形成及特征
——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2023-09-01张然婷
张然婷
“竟陵八友”是活跃于齐梁时代的一个士族文人集团。学界以往对该集团及其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层面,缺乏对其政治性的深入分析[1]。本文旨在探究南朝“文学政治体”的发展形态,关注两对君臣关系:一是萧子良与王融,他们的结合标志着文学政治体的诞生,也反映了其早期并不完善的模式构建;二是萧衍与沈约,两人的合作推动了文学政治体的成熟化——该制度最终促成了梁朝代齐的大业,也推动着南朝政治进一步走向中央集权。
一、萧子良与王融:文学政治体的诞生
关于“竟陵八友”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书·武帝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2]可以说,如果没有萧子良自发“开西邸、招文学”的行为,则以竟陵王之封地命名的精英团体,“竟陵八友”,便不会存在。《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载:“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3]所谓“才学”,与《梁书·武帝纪》中的“文学”一样,指的正是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文人。他们“游集”在竟陵王府邸,并不只为文学交流,更是一种政治站队。与晋宋不同的是,齐梁时代重文之风盛行,社会从贵族到寒门皆以善文为荣,“文学入仕”成为一条日趋流行的从政之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齐梁以来皇权政治有意识的回归。
东晋时代,侨姓士族掌握政权与兵权,形成了以王、庾、桓、谢为代表的门阀势力。南渡初期的琅琊王氏家族一手扶持晋元帝司马睿即位,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声势之大,甚至到了皇帝“命导升御床共坐”的地步[4]。颍川庾氏以外戚身份显贵,在晋明帝崩逝后迅速把控权柄,史载“太后临朝,政事一决于亮”[4]。谯国桓氏依仗军功起家,经略荆州,通过桓温三次北伐积攒威望,成功解决徐、豫二州之难,得以遥控建康,实现了“政在桓氏,祭在寡人”的政治格局。陈郡谢氏虽行事更为低调,但其全盛时期,谢安掌握政权、谢玄掌握军权,依旧把皇权笼覆于阴影之中。
然而,田余庆指出,东晋时期门阀政治乃“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其存在是过渡性的,待时机成熟后,以帝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仍将主宰历史舞台[5]。这一过程自淝水之战胜利后以晋武帝司马曜领头推进,桓楚政权瓦解后,又被刘宋一朝承袭,具体表现为寒人受到提拔并渐渐接触机要,而士族虽然依旧维系着极高的社会声望,却逐渐远离了政治与军事的核心。至齐梁时,先前以事功立家的阀阅世家完成了向“文化贵族”的转型[6]。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家族,莫过于“竟陵八友”中谢脁所属的陈郡谢氏与王融所属的琅琊王氏[7]。王氏一族在南齐,虽有王俭以佐命齐高帝萧道成开国之功而位列宰执,但史载其人“弱年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并尚经学”[8],常以“江左风流宰相”自况,足见其亦有好文之特点。王俭之后,王氏闻名者如王融、王筠、王籍等一众齐梁人物,俱以文学著称。
南朝时期,中央集权稳步提高,对士族而言,意味着政治地位不断削弱。东晋门阀全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受到打压的士族在社会风气的推动下纷纷转向文学出仕[9],继而出现了“竟陵八友”这样“才学游集”于皇室成员之间的文学集团。他们多利用文学手段,依附于皇权与宗室,从而参与政治活动,发挥影响力。
王融和竟陵王萧子良的例子是文学政治体谋求利益的一个典型。《南齐书·王融传》载:“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3]但王融对自己的定位远不只是一介文士。就《齐传》所录,王融弱冠之年举秀才,事晋安王于豫州,官南中郎行参军。“坐公事免”是王融人生的转折点,尽管关于事件详情的记载已缺失,但由此而知,王融仕途的第一个低谷期是免官自豫州返回建康。王融一心从政,很快“启世祖求自试”,以此踏上人生重要的一步——“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柏俊才在《王融生平仕履考》中指出,王融入竟陵王西邸一事发生在齐武帝永明五年丁卯(公元487 年),是较为合理的推论[10]。这就促使王融在永明年间从晋安王门下转投竟陵王府邸,从中可以看出,这并非只是竟陵王之“善立胜事”与重“文教”,更可能是王融在审时度势之下,有意识地对萧子良的政治投资。因为在齐武帝诸子中,竟陵王萧子良颇受荣宠,拥有十分明显的政治优势。萧子良之显赫地位能为门客提供良好的政治前途。
以文学为媒入竟陵王邸后,王融的确获利颇丰。《魏虏列传》载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 年),“遗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世祖发扬、徐州民丁,广设召募”[3],与《王融传》“会虏动”时间相合,可知王融得竟陵王所募,拜宁朔将军、军主便发生在此时。《齐传》又言,“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3],其体现了萧子良在政治与军事双方面对王融的重用,致使王融得以“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3],甚至召集了江西数百楚人为自己所用。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王融与竟陵王间的政治纽带与利益联结。《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有录, 南齐草创之际,刘宋车骑大将军沈攸之起兵反抗,萧子良同父亲萧赜驻盆城,受封的官职正是宁朔将军[3]。宁朔将军作为萧子良的第一个仕途名衔,对其有特殊意义,而萧子良“板融宁朔将军”的行为,在王融看来他与竟陵王已成为政治盟友。他“自恃人地”,认为自己在三十岁以前能位列宰辅,甚至公然道:“车前无八驺卒,何得称为丈夫!”[3]结合其“倾意宾客,劳问周款”的行为,可见他有拥萧子良为帝之意。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 年),齐武帝萧赜疾笃暂绝,王融“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11],欲立子良。王融的谋划既无缜密的事先安排,也无充分的临场把握,甚至缺乏和萧子良的有效沟通,可以说是一场一厢情愿的造反活动,因此不出所料地走向了失败。按《南齐书·王融传》录:“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3]王融政变不成后的感叹令人玩味。“公误我”一词仿佛暗示着王融与萧子良间存在某种政治约定,而致使王融大计落空的原因是萧子良的“背约”。其中尤以“误”字的情感色彩最为浓烈。《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中有“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之说[12],和王融此处之“误”所蕴藏的情绪表达较为类似;只怕在事情败露后,王融的内心也生出了萧子良“不足与图大事”的感受。一个“误”字,既展现了事态的严重性,又揭露了王融主观上的愤懑不平。
然如《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所载,“子良素仁厚,不乐事务”[3],可知萧子良本人并无篡位的野心。在武帝“遗诏使子良辅政”的关键时刻,他推脱不受,甘居萧鸾之后。皇孙萧昭业即位后,萧子良备受猜忌,在忧惧中郁郁病逝,年仅三十五岁。王融与萧子良交好,若知其无称帝之心,何以冒险谋划扶持萧子良上位?事败又为何认为萧子良在武帝之死前后的消极表现“误”了他们的约定?
竟陵王是王融仕途前程的最终依仗。只有辅佐萧子良称帝,王融才有机会以从龙之功成为宰执。“竟陵八友”文学交游的光鲜形象只是其外表,其内核是围绕萧子良形成的一个“文学政治体”。王融与萧子良 “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是这个团体内党附子良一众中最重要的人物。身为西邸集团一员,王融试图通过有意识地推举萧子良上位,实现个人利益(“三十内为公辅”)。而萧子良的不配合就成了对其此前一系列效忠行为的“背叛”。萧子良在这一点上没有与王融达成共识,二人的政治诉求出现了明显分歧。萧、王对时局的模糊判断,最终导致二人的凄惨下场——萧子良蒙冤受忌而终,王融因策划谋逆“诏于狱赐死”[3]。
可以说,萧、王“谋逆”是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文学政治体在初登历史舞台时进行的一场以失败收场的政治行动。它反映了文学政治体的内在缺陷,即当集团内皇室核心成员与重要士族人物之间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此前建立的联结将迅速走向崩溃。而萧子良死后,西邸文学集团看似瓦解,“竟陵八友”诸余者却心照不宣地围绕萧衍建立了新的核心,这是因为洞悉时局者如沈约、范云早就察觉到了萧衍的能力和野心。比起萧子良,萧衍显然是更合适的领班人选。在此背景下,文学政治体经历初次挫败后,很快以萧衍为中心重新凝聚了起来,并最终完成了代齐建梁的壮举。
二、萧衍与沈约、范云:文学政治体的成熟
若认为萧子良与王融时代的“竟陵八友”是文学政治体不完备的萌芽阶段,那么萧衍与沈约时期的“竟陵八友”则反映了文学政治体的成熟阶段。按《梁书·沈约传》言,“高祖在西邸,与(沈)约游旧”[2]。结合《武帝纪》对“竟陵八友”的记载,可知沈约和萧衍曾同附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彼此有所往来。二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竟陵八友”作为一个以文学为招牌的精英集团,成员之间更是多有诗歌唱和,可奇怪的是,沈约与萧衍却无任何酬唱的诗篇,实在罕见[10]。这表明沈约与萧衍在文学层面二人的风格与主张多有相对之处。《南齐书·陆厥传》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 ‘永明体’”[3]。可见,“八友”之中,沈约与谢脁、王融在诗歌创作上尤为相投,因并崇“四声八病”而多有文学交流与切磋。王融死后,沈约甚至亲作《伤王融》以悼:“途艰行易跌,命舛志难逢。折风落迅羽,流恨满青松。”相比之下,萧衍对沈约的“四声”说却显得不以为然。《沈约传》载:“(沈约)又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萧衍)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2]。
文学喜好的不同似乎在暗示沈约和萧衍的关系不甚亲近,可这与《梁传》中“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的记载相悖。对此极有可能是,沈、萧之交不在于文学,而在于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竟陵八友”以文学为皮、政治为骨的特点。沈、萧的政治往来始于竟陵王邸。永明十一年(公元493 年),齐武帝病笃,竟陵王萧子良以西邸人物为重,召萧衍、范云等为帐内军主[8]。沈约虽不在此列,但从萧子良死后其被排挤出京的情况来看,他在武帝去世前后仍属萧子良集团的一员[8]。与王融一心扶持萧子良不同,萧衍在关键时刻与萧子良划清关系,转向皇太孙萧昭业,通过依附权臣萧鸾,逐渐获得重用,被授雍州刺史的显官。沈约为了摆脱“萧子良党羽”的阴影,最终选择如萧衍一样倒向萧鸾。在萧鸾帐下,沈约与萧衍的政治利益自早年竟陵王府后,又一次发生了交叠。
萧鸾即位,愈发猜忌,其子萧宝卷行事更可谓荒唐,于内听信“刀敕”群小,于外杀伐有功之臣,如萧衍的胞兄萧懿曾平定裴叔业与崔慧景的叛乱,却被赐死。在齐祚飘摇的环境下,经略雍州的萧衍成了沈约投注的对象。除沈约外,“竟陵八友”中的范云与任昉也纷纷转向萧衍。其中尤以范云为代表[8]。至此,“竟陵八友”的初代首脑萧子良虽死,但“竟陵八友”之文学政治体的内核延续下来——成员们审时度势,以政治利益为驱动力,团结在萧衍的身边形成了新的士族政治集团。
萧衍在讨伐东昏侯的过程中,沈约、范云等身为文士,虽不像曹景宗和韦睿在具体战事上做出了实质贡献,但平定建康城之后,沈、范的作用开始凸显。萧衍勋业已成,沈约率先站出来建言萧衍行换代之举:“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已终,莫不云明公其人也。谶云 ‘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茍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2]可以说,沈约的主动造势,对萧衍极其重要。《沈约传》中载萧衍召范云议事,范云对其即位同样表示支持,萧衍于是说“智者乃尔暗同”[2]。这里用“智者”一词,传达了萧衍对沈、范二人的认可,于是沈、范在萧衍处的亲信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最终超越一众武将,成为萧衍口中真正佐其建梁的人:“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2]
萧、沈、范的结合使文学政治体的模式进入了成熟阶段。三者都是“竟陵八友”的成员,都有早年交游的事迹,但最终将他们联结起来的不是文学,而是政治。萧子良与王融的失败是因为二人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可萧衍、沈约和范云却在利益诉求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即代齐建梁。萧衍需要利用沈、范的名望为自己的篡位造势,缔造禅代正统性,最终实现个人成就帝业的抱负;而沈、范的目的则一如沈约在劝进言里说的那样——“攀龙附凤”——渴望通过参与新王朝创立的方式,以从龙之功成为开国元老。
天监元年(公元502 年),梁武帝萧衍受禅。官爵上,范云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二年(公元503 年),范云任尚书右仆射,位至宰辅。待遇上,范云因“佐命功”封霄城县侯,邑千户。《梁书·范云传》载,“(范云)尝侍宴,高祖谓临川王宏、鄱阳王恢曰:‘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2]。沈约于天监元年获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后授尚书仆射。丁母忧归朝,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不久拜尚书令,行太子少傅,位列梁朝十八班品中第十六班,为一时显宦。待遇上,沈约于武帝受禅后封建昌县侯,邑千户。其母谢氏拜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2]。
由上可知,范云与沈约都凭“竟陵八友”这一文学政治体收获了丰厚利益。天监二年(公元503 年),范云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以善终。同属该政治集团的沈约虽较长寿,但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为梁武帝萧衍所忌,忧惧而亡。沈约的命运说明,齐梁时期的文学政治体尽管拥有华美的诗歌外衣做饰,却终究摆脱不了中央集权体系下君主对其所谓“政治野心”的猜忌与构陷。
三、对萧沈关系的另一种解读:文学政治体下的皇权政治
萧衍对沈约的不满或从早期便已开始。《梁书·沈约传》中录,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沈、范二人同为萧衍所重,沈约为与范云争功,使手段在萧衍面前出头:“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高祖初无所改。”[2]范云有顷而至,萧衍对他说:“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2]明看是夸赞之语,但萧衍未必没有识破沈约的伎俩,故“才智纵横”一词用于此处,意存反讽,有忌惮提防的含义。
沈约的文学成就冠绝当时,为一代词宗,本人也自负才高,与萧衍多生过节:“先此,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2]与上述先范云一步见萧衍的举动一样,沈约锋芒毕露、不善藏拙。就栗事而言,沈约所展露的“才胜武帝一筹”并非最严重的问题,更甚者是沈约私下指点皇帝的行为本身对萧衍想要构建的集权君王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君臣关系不睦的铺垫下,真正致沈约于死地的导火索是颇有宗教色彩的“夜梦齐和帝”之事。《梁书·沈约传》载,“(沈约)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2]。按《资治通鉴》所录,萧衍即位后,欲封齐和帝萧宝融为巴陵王,沈约提出杀萧宝融以绝后患,得到了萧衍的认可[11]。萧宝融因沈约而被“摺杀”,沈约又梦见萧宝融“剑断其舌”,这个故事暗含“因果相报”的佛教色彩。可见,沈约全程见证了梁武帝最大的隐私,知晓其登基称帝的野心,也参与了其对南齐皇室的清算。
然而,沈约说“禅代不由己出”,便是将上述篡位过程中不光彩的一面转移到萧衍的身上。这不仅暗示了杀害齐和帝的决定乃出自萧衍自身巩固皇权的需要;还直截了当地戳破了禅代传说,表明代齐并非群臣苦谏的结果,而是萧衍个人的想法。这与萧衍想要打造的君王形象背道而驰——无论是萧衍登基前的言志诗歌《直石头》[13],还是登基后创作的《孝思赋》[14],都有意描绘萧衍的“谦退”之意,与其后期意图构建的“菩萨皇帝”头衔相合;而沈约之举,却实实在在地驳斥了萧衍一手缔造的“圣贤”之态,将其为达目的处心积虑的一面暴露无遗,从而形成了对皇权威严的公然挑战,以及对梁室皇权正统性的威胁。
在此背景下,同属一个文学政治体、曾共同开创梁朝的萧衍与沈约关系迅速疏远,最终走向破裂。萧衍“及闻奏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2]。派遣宫内宦官谴责重臣一事,表面看来并不算严厉制裁,实则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于沈约这样一位既有政治地位又有家族名望的士族领袖而言,言语羞辱是对其社会形象的摧毁。类似事件在东吴也有发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孙)权累谴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而卒”[12],与南朝梁沈约之死情况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陆逊与沈约在各自政权内俱居显职,二人都是当朝士族人物的代表。他们的去世都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皇权与士族间的矛盾。但与东吴时期士族阶级全面崛起并压制皇权的历史大势不同的是,沈约之死却体现了皇权政治的回归:齐梁时代全面“文士”化的士族通过加入文学政治体的方式主动依附于皇族,以此进行政治活动、实现政治诉求。而一旦士族人物的行为触及了皇权的逆鳞、违背了集权君主的话术体系,那该士族个体乃至其家族都会受到来自皇权的主动清算。这种清算可以是彻底的,如沈约之死;也可能不彻底,如吴均因编撰《齐春秋》见罪于梁武帝,仅仅遭到免职。但无论彻底与否,皇权的地位乃至政权的稳定,都不会如东吴时那样,因对一家士族的清算而动摇。这是因为齐梁士族在文学政治体的影响下逐渐沦为皇权的点缀,不复拥有东吴后期陆凯与陆抗、东晋早期王导与王敦那样的政治军事重要性。皇权已从门阀阴影下走出,重归于神圣稳固,皇权政治的残酷便在这一环境下展露无遗。
四、结语
文学政治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诞生于南齐,以竟陵王萧子良与王融的关系为早期代表;又在齐梁嬗代之际,通过萧衍与沈约的结合,逐渐发展成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为魏晋南北朝诸帝之最。在其漫长的统治岁月里,文学与政治的连接愈发紧密,这种“文学为皮、政治为骨”的士族团体逐渐走向极盛。利益体以“文学集团”为单位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在梁朝具有普遍性。不仅梁武帝本人热衷于打造“文学兴国”的形象[9],其诸子也纷纷效仿,最为代表的是以昭明太子萧统为核心的东宫集团[15],萧统去世后围绕继太子萧纲形成的二代东宫集团[16],以及湘东王萧绎领导的西府集团[17]。
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文学政治体”是南梁皇权为中央集权做出的重要努力,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其根源来自晋末与刘宋时代皇权回归的大趋势,而其形成至顶峰的历史进程,又有意识地推动南朝皇权进一步达到独尊的地步。尽管遭遇了萧子良与王融的失败政变,文学政治体的模式被萧衍与沈约继承,并最终缔造了梁朝代齐的大业。萧衍也利用文学政治体完成了真正的中央集权——梁武一代,重要士族的命运几乎都与君王个人好恶密切相关,沈约之死的例子更是直接彰显了集权君主话术体系的苛刻。
需指出的是,文学政治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结构的一种变态,是在“九品中正制”问题频频而“科举制”尚未诞生的过渡阶段,一种专为中央集权而打造的特殊产物。它在齐梁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昙花一现,随着侯景之乱爆发,文学政治体这一模式迅速走向衰败,体现出其不稳定性。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学政治体虽具备外观上的美感,却存在结构性弊病。在成熟的科举制度诞生之前,文学与政治的过度融合是危险的。太平时期,它的危害尚可停留在行政效率低下、世风腐化的层面[18],而一旦遭受如侯景之乱这样的外部冲击,文学政治体的脆弱便会被无限放大——受到“文学立家”的氛围影响,而全面“文士化”的南朝士族阶层疏于武略,面对剧烈的外部冲击,表现得如同一盘散沙。从这个角度出发,以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史官对南梁亡国的反思颇有雾里看花的意味[19]。与其说梁朝宫廷文学的发展导致了灭亡的结局,不妨说是具有齐梁特色的“文学政治体”这种不成熟的制度使文学错误地涉入政治领域,加速了南梁的衰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