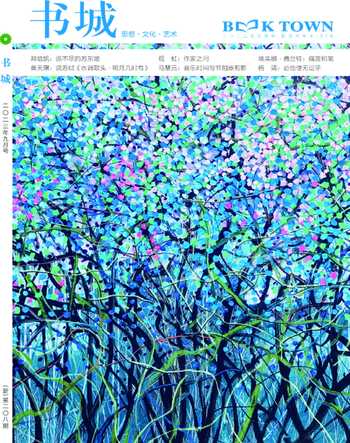出落个红闺人俊雅
2023-09-01郭梅
郭梅
题记:汤显祖的《牡丹亭》为女性的爱情婚姻自由而呐喊,二百五十多年后的女曲家吴藻则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女性权利,其独幕剧《乔影》以主人公女扮男装饮酒读骚为酒杯,浇作者内心之块垒。
一
明清时期,“童心说”“性灵说”等思潮风起云涌,女性文学繁荣,一些才女产生了如男子般可以自由抒怀的念头,其中就有吴藻。
吴藻(1799-1862),字蘋香,号玉岑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活跃于道光年间的浙江文坛,诗词曲皆能,而以词曲最工,其杂剧《乔影》享有盛誉。
与多数出身书香世家的闺秀作家不同的是,吴藻出生在嘉道年间的一个商贾之家,后来嫁的也是商人。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花帘词”条记载:“蘋香父、夫俱业贾,两家无一读书者,而独呈翘秀,真夙世书仙也。”
《乔影》是吴藻年轻时创作的一部独幕杂剧,作者借谢絮才之口尽情地吐露胸中的“高情”和“奇气”,渴望冲破现实对女性角色的束缚:“百炼钢成绕指柔,男儿壮志女儿愁。今朝并入伤心曲,一洗人间粉黛愁。我谢絮才,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敢夸紫石镌文,却喜黄衫说剑。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咳!这也是束缚形骸,只索自悲自叹罢了。但是仔细想来,幻化由天,主持在我,因此日前描成小影一幅,改作男儿衣履,名为《饮酒读骚图》。敢云绝代之佳人,窃诩风流之名士。”剧中只有一个人物,情节性并不强,像很多优秀明清杂剧作品一样接近抒情诗,是作者的内心独白。谢絮才显然正是吴藻本人的自我投影,正如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花帘词”条所记:“(吴藻)又尝作饮酒读骚长曲一套,因绘为图,己作文士装束,盖寓速变男儿之意。”
“饮酒读骚”出自《世说新语·任诞》王恭之语:“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饮酒”向来被作为名士风流以及排遣苦闷的表现方式,而“读骚”则往往寄寓着命运不遇的悲感。吴藻在《乔影》中写谢絮才“眼空当世,志轶尘凡,高情不逐梨花,奇气可吞云梦”,但在现实中却有志不得伸,有才不得用,故而自以为“像这憔悴江潭,行吟泽畔,我谢絮才此时与他也差不多儿”。这种情绪郁积之深,就化作了主人公的心灵独白:“我想灵均,神归天上,名落人间,更有个招魂弟子,泪洒江南。只这死后的风光,可也不小。我谢絮才将来湮没无闻,这点小魂灵飘飘渺渺,究不知作何光景。”而其对声名的看重与追求,也直接来自《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其生命意识的高扬和内心活动的郁勃,显然是相通的。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女性要求施展抱负的呼声也纳入了个性解放思潮的主旋律,她们中的大部分仍主要着眼于将拥有与男性同样的条件当作自身解放的最终目标,对男性也受到压抑的事实缺乏客观及敏锐的感知。而吴藻在《乔影》里所抒发的“高情”和“奇气”却并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它向往完全的自由,反抗施诸女性的所有束缚,涵盖面和批判力较其他女性的要求更显宽广和强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为女性呼唤自由的同时,吴藻还进一步认识到了即使是男性想充分施展才能,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在现实生活中也很艰难,所以她得到了当时广大男性文人的共鸣和激赏。如齐彦槐诗曰:“毕竟小青无侠气,挑灯闲看《牡丹亭》。”许乃榖更是为《饮酒读骚图》题辞云:“我欲散发凌九州,狂饮一写三闾忧。我欲长江变美酒,六合人人杯在手。世人大笑谓我痴,不信闺阁先得之。”
二
女扮男装历来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题材,尽管这类作品都带有提升女性价值的含义,但其意旨及表现却各有不同。木兰替父从军和英台易妆读书,虽然一个慷慨激昂,一个缠绵悱恻,最后恢复女儿妆重返闺阁却是一样的。明显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是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也符合一般观众关注故事情节的观赏心理。而明清时代出现了另一类作品,虽仍可置于这一框架之中,却产生了不少根本性的变化,即当作品中的主人公穿上男装时,那件衣服已经内在于她们,成为她们生命意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她们往往从心理上已把自己当成了男子。与此相应,这类作品也就基本不以情节的跌宕起伏争胜,而是注重琐碎的生活叙述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在明清戏剧史上,《乔影》之前有叶小纨的《鸳鸯梦》、王筠的《繁华梦》等,《乔影》之后则有何珮珠的《梨花梦》等。尽管这些作品都有特定的思想倾向,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吴藻在《乔影》中所表现出的意向更为鲜明,因为她的“名士情结”在其全部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不仅表现在叙述性的虚构作品之中,也表现在直陈性的抒情作品之中。
有意思的是,吴藻的这种“名士情结”和改变社会性别的心曲,甚至体现在《乔影》中对美人名士的向往:“似这等开樽把卷,颇可消愁,怎生再得几个舞袖歌喉,风裙月扇,岂不更是文人韵事?”—红袖添香,轻歌曼舞,诗酒流连,吴藻在这里表现的是最典型的名士习气。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这种感情在其笔下并非仅见于《乔影》,比如《花帘词》中就有一阕《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
珊珊琐骨,似碧城仙侣。一笑相逢澹忘语。镇拈花倚竹,翠袖生寒空谷里、想見个侬幽绪。
兰釭低照影,赌酒评诗,便唱江南断肠句。一样扫眉才,偏我轻狂,要消受、玉人心许。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
瘦影珊珊堪怜,玉手相携温馨,赌酒论诗,浅吟低唱,美人名士互相爱慕,惺惺相惜,索性就“买个红船,载卿同去”,这是最典型的男性文人做派。由此也可看到,吴藻虽是女性,但当她幻化为男性,即以文人或名士自居时,显然也不假思索地沿用了男性文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魏晋风骨,清士名流,是后世文人回望历史时,万分艳羡的风度。魏晋时期文人饮酒作乐,清谈成风,即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尽管身处乱世,但名士们寄情山水,疏狂傲物,活得自我且放达。这样的风气不仅存在于当时的男性文人之中,女性亦不甘示弱。东晋时的谢道韫出身于士族之家,自幼便以“咏絮之才”名世,长于诗文,又具捷智。谢道韫的丈夫是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一次,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清谈斗智,辞理将屈,谢道韫便坐到青绫屏障后继续献之前议,舌战群儒,众宾客不能折屈之。谢道韫风致翩然,谢安称她有“雅人深致”,时人评论她神情散朗,有林下气度。
吴藻将《乔影》中的主角命名为“谢絮才”,自不免有追慕谢道韫之意。魏晋时社会风气相对开放,文人好以名士自居。吴藻将笔下主人公谢絮才的自画小影命名为《饮酒读骚图》,又在剧首写道:“敢云绝代之佳人,窃诩风流之名士。”很明显是心摹手追,忍不住将魏晋风流移植到了剧中。
木兰从军和英台易装的故事本身都只是民间传说,经好事者整理改编后,无不充满了戏剧和传奇的色彩,主人公身上的那件男子外衣只是一时之需,最终还是要穿回旧时女儿装的。这类作品以情节的离奇取胜,符合观者猎奇的心态,显然超离了生活,并不具备真实性。明清时期女性作品中涉及男扮女装的尤多,如陶贞怀的《天雨花》、陈端生的《再生缘》等几部弹词作品对于此题材把握得较为成熟,将矛盾冲突着眼于男子身份所带来的自由与利益之争,而不再仅局限于男女之情与女性重新改回红妆的艰难。类似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这类女性作品已试着将“女扮男装”作为一个引子,以书写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和女性被迫幽居闺中的不满与不甘。这些女子本身才华不逊于男子,却由于性别连尝试的机会都不能享有,情何以堪?尤其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处境困窘,又没有依靠的女性,她们碍于女性身份,不能凭借自身才华赚取生活所需,就很自然地会厌恶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在作品中抒发不满和抨击现实。不过,这些女性文人将女性意识反映到作品中,多多少少会设置一个或几个触动女性意识萌发的关键因素,比如,陈端生《再生缘》里的孟丽君是为了保全名节,为夫报仇,在逃婚的过程中渐渐体味到闺房之外的风景大好,生而为男子的权利是那样的诱人,于是,她起了不愿脱下相貂重返妆楼的念头—这是当时较普遍的渐进式的女性的思想觉悟。不过,年仅二十余岁的吴藻却没有完全效仿这些文坛女前贤,而是一改此前拖沓、迂回的“思想斗争”,在其独幕杂剧《乔影》中直接以犀利大胆的动作和言辞表现了她的女性解放思想。
《乔影》是吴藻早年之作,在体裁和篇幅等方面就与陈端生等前人有明显区别—既非小说,亦非传奇、弹词,而是一个独幕杂剧。全剧不过一千余字,写女子谢絮才不满自己的性别,改换衣装,扮作书生,在书斋赏玩自描的男装小像,即《饮酒读骚图》。她在赏画饮酒、放浪形骸、尽情抒怀之际,却突然感怀身世,悲从中来。沦落到如此境地,只因为自己生而为女子。她读《离骚》之际又想到三闾大夫报国无门,在江畔行吟的孤寂与萧瑟,对比自沈亦是明珠湮没,怀才不遇。但屈原的诗文千古流芳,死后还有弟子为其招魂。而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却受制于女性身份,只能锁于深闺,不能为国效力,更没有机会名留青史。黯然神伤之际,谢絮才只得收拾起画卷酒具,默默下场。全剧就此落幕。
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在《乔影》中,吴藻之所以将主人公命名为谢絮才,除了追慕谢道韫的林下之风、名士风范以外,应该还包含了另一层深意,那就是谢道韫与她有同病相怜的一面—她们的婚姻都不如意。据《世说新语·贤媛》记载:“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悦。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弟兄,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东晋时很多所谓的名士往往醉生梦死,沉湎于清谈却不正视现实,王凝之就是此中之最—他在任会稽太守时,孙恩造反叛变,而作为太守的王凝之却只知道焚香拜佛,求神仙保佑免遭涂炭。谢道韫劝夫不果,只能亲自招募士兵,组建军队进行反抗。当孙恩叛军兵临城下时,王凝之仓皇出逃,在城门口被叛军所杀。反倒是一介女流的谢道韫镇定自若,指挥军队顽强抗敌,可惜寡不敌众,全家惨遭灭门—唯独谢道韫,连孙恩也不得不折服于她的胆识与谋略,不敢加害,命人将她送回故乡。
吴藻的丈夫是商人,有道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吴藻虽衣食无忧,自我感觉却无异于笼中的金丝鸟,在精神上无法得到最亲密伴侣的理解,让她十分痛苦,满腔幽愤只能诉诸笔端:“怕凄凉人被桃花笑,怎不淹煎命似梨花小,(絮才!絮才!)重把画图痴叫。秀格如卿,除我更谁同调?!”
正如严迪昌所言:“女性的觉醒,大抵始自于婚姻问题,但仅止步于此,觉醒尚难有深度。吴藻的女性自觉,可贵的是对人生、对社会、对男女地位之别以及命运遭际的某些问题,都有初步的朦胧的思考,从而成为这种思索和悟解觉醒长途中值得珍视的一环。”(严迪昌编选《金元明清词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在古代,对于有经济来源的男性来说,爱情是生活中的美好点缀,更何况男性若是婚姻不谐,大可以有三妻四妾来“弥补”,但对女性来说,婚姻之路完全是一条单行线,上车的刹那就已无法退票或得到额外的补偿。吴藻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情不投意不合的婚姻在她生命中所造成的悲剧与遗憾,她力求摆脱这无语、喑哑的人生,却只能在纸上狂放而已,尤其是[北雁儿落带得胜令]:“我待趁烟波泛画棹,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这支著名的曲子借用历史上诸多奇人异士的想象和传说,一气甩出长达十句的排比以及一连串典故,以李太白、王子乔、刘禹锡等历史上著名的俊逸神仙、洒脱文士自喻,气势磅礴,表现出一种绝对的自豪与自信,无半点寻常小女子的忸怩作态,表达了那种渴望发展个性、展现才华、向往极致自由的迫切心情,从中可以看出吴藻渴望自由的急切和其本人不输于旁人的豪迈俊逸。只是,对比她当时羁绊闺中的窘境,愈发可见她忧郁烦躁的心态。她甚至还在剧中的[收江南北]曲里写道:“只少个伴添香红袖呵相对坐春宵,少不得忍寒半臂一齐抛,定忘却黛螺十斛旧曾调。把乌阑细钞,更红牙漫敲,才显得美人名士最魂销。”在表示不惜以买醉麻痹自己的同时,却不忘倩美人来揾英雄泪,而这,就是吴藻思想局限的表现了—她想要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想通过红颜陪侍来实现,而浑然忘却了那位女子的自由平等又如何体现呢?!
年轻时的吴藻还真的曾换上男装,与男性文人一起饮酒赋诗,甚至走马章台。前文提过,吴藻亦逢场作戏,甚至还写了《洞仙歌·赠吴门青林校书》。这首词写得风流婉转,甚至有几分轻佻的味道,可以说完全具备男性文人的立场和角度—“一样扫眉才,偏我轻狂,要消受、玉人心许”,分明就是酸腐书生赢得美人心后扬扬得意的嘴脸。而当她写到“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买个红船,载卿同去”时,吴藻已然忘记了自己的性别,陶醉在了被美人钦慕的良好感觉中。不过单就词作而言,这首词倒也不落俗套—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男性以女性的筆调来填写的哀怨之词,少有女性以男性的口吻来调笑嬉闹,况且吴藻笔力刚柔并济,不输等闲。
窃以为,这首词恰恰与《乔影》相互佐证了谢絮才即吴藻本人的化身。但吴藻不免也陷入了矫枉过正的误区—她想获得与男性文人平等的地位,但却又不知从何处入手解决,只能随男性之波而逐流,以男性流连勾栏的方式来表现和证明自己的才华,而且还要借妓女的钦慕赏识来抬升自己的地位。可以说,这是吴藻作品在追求女性自由解放的同时,暴露出的思想性局限。
正如吴藻在定场诗中所说:“百炼钢成绕指柔,男儿壮志女儿愁。今朝并入伤心曲,一洗人间粉黛羞。”这个剧本以饱酣淋漓的笔墨和豪放奔涌的情怀,抒写出人间不平,呼喊出女儿心愿,在当时便引起了轰动,“被之管弦,一时广为传唱,几如有水井处,必歌柳词矣”(《杭郡诗》三辑)。据目前所知,该剧是女曲家剧作中少数从案头走向剧场的例子之一,演出时人们“传观尽道奇女子”(许乃毂《乔影》题辞),而且“雏伶亦解声泪俱,不屑情柔态绮靡”(同上),其振聋发聩可见一斑。
三
吴藻的同乡前辈陈端生的代表作《再生缘》和《乔影》一样,以女扮男装为情节绾合的核心。六十万字的弹词《再生缘》也是一部赞扬女性才能的作品,该书叙写已由父母许婚皇甫少华的女子孟丽君因不愿改嫁刘奎璧,女扮男装逃婚而走,通过科举考试中了状元,身居高位,不仅举荐未婚夫皇甫少华出征立功,还为皇甫一家平反了冤狱,为朝廷铲除了奸佞。但当封侯后的皇甫少华意欲迎娶孟丽君时,她却选择了回避,竭尽全力保全自己并非男儿身的秘密,以避免回到桎梏甚多的家庭之中—她强调“宰臣官俸巍巍在,自身可养自身来”,为官做宰不仅可以谋生,而且能为国效力,她愿意一辈子不露女儿身。
值得再提一笔的是,陈端生是陈文述的族姐,而陈文述正是对吴藻创作影响甚大的老师。有这么一层关系再加上吴藻本人的勤奋好学,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吴藻很可能是陈端生的读者,并深受陈端生思想的影响。而当我们将陈端生与吴藻的身世及作品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这两位杰出的女性还真是有着相当多的可比之处。
首先,二人皆是因婚姻不幸开始思考女性的人生意义的。吴藻嫁与了不懂风情的商人,夫妻感情不谐;而陈端生的丈夫则被卷入科场舞弊案而下狱,从此鸿雁两分开。
陈端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家中有三姐妹,端生居长,自幼饱读诗书,除了早夭的二妹外,端生与妹妹长生都长于创作。除了《再生缘》,她还有《绘影阁诗集》(已佚),而长生则有《绘影阁初稿》。她们的母亲汪氏非常支持女儿的创作活动,如陈端生在《再生缘》中言道:“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吴藻所望尘莫及的。陈端生的少女时代生活富足,母亲慈爱,姐妹和睦,没什么烦心事,因此《再生缘》的前十六卷都是在她出阁之前完成的—她从十八岁开始写作,二十岁时已经完成了十六卷。如此勤奋且高产的作家,即便在当今亦属罕见。不过,创作《再生缘》对陈端生来说本意只是娱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闺中游戏罢了,没有像吴藻那般在作品中直面现实,情感激荡。陈端生本意也“不愿付刊经俗眼”,所以前十六卷的文字虽然在情节上诡谲跌宕,但相对吴藻的《乔影》而言,就有点寡淡无味了。相比谢絮才的饮酒读骚、直白疾呼,孟丽君的当众撕本则多少有点恃宠而骄、无理取闹,不甚高明。孟丽君自第三回换上男装逃婚,一袭男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一种掩护,实际上从内心而言,她还是一个遵守纲常的女性,其逃婚的初衷本身就是为了不嫁二夫以保贞节,并非出于真心相爱—她和父母选择的未婚夫未曾谋面,哪来的爱情呢?更遑论陈端生在《再生缘》的开头便已设定了“三美同归”的结局。后来母亲去世、丈夫科场作弊、女儿早夭等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陈端生的生活每况愈下,不仅无暇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使陈端生认识到这个社会对于女性是多么的苛求与不公平。丈夫系狱发配带累了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催熟了陈端生的女性独立思想。陈端生满腹的才华没有用武之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怀才不遇呢?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主人公孟丽君重归那喑哑无声的女性世界中去了。但这又毕竟与她从小受到的教育相悖,因此,《再生缘》终究未能成为完璧。
与陈端生不同,吴藻生于商贾之家,所受到的束缚没有书香之家那般严苛,再加上吴藻与陈端生相差了近五十岁,时代的变迁亦是造就她俩思想不同的一个原因。
相对陈端生笔下的众人将抗争的焦点聚集于孟丽君是否要放弃宰相之职这一具体目标,《乔影》中的谢絮才所抗争的或追求的目标就有点语焉不明了。不过从“敢云绝代之佳人,窃诩风流之名士”这两句中可以略窥一二—
明清时期虽有众多女性的觉醒,并发出要自由要解放的呼声,但大部分女性的追求仍主要着眼于在某一具体的方面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最普遍的即如孟丽君,身居高位,才学权势不逊于男性,以拥有与男性同样的地位、权力甚至金钱当作自身解放的最终目标。所以在这些作品中,女主人公乔装成男性,多的是女性夺取功名利禄如同探囊取物般容易的描写,且轻易便能博得统治者的欢心,跃上权力的顶峰。殊不知在封建时代,即便是男性想博得一官半职,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可女性对男性也受到压抑的事实似乎明显缺乏认知,而吴藻在《乔影》里所抒发的“高情”和“奇气”,涵盖面和批判力较其他女性的要求更显宽广和强烈。
换言之,虽然陈端生和吴藻都在控诉女性命运的不公,但陈端生显得更优柔,吴藻则分明有着壮士断腕的果断。郭沫若在《〈再生缘〉和它的作者陈端生》一文中曾指出:“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条件的。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总之,孟丽君是以封建之伦理来抵抗强加于自身的不公命运,狡猾而隐晦,虽不乏聪明之处,但多少有点显得犹疑而欠果敢。而且,在《再生缘》中,劝说孟丽君改回红妆的人比比皆是,不仅有男性,如皇甫少华、孟家父子等,还有不少女性,如她的母亲,还有“妻子”苏映雪,等等,所以孟丽君孤立无援之时也曾暂时妥协,说明陈端生自己的思想也曾动摇。这也就是说,孟丽君是不自觉、不得已才着男装,初时陈端生也一直以孟丽君情归皇甫少华为行文的最终目的。但吴藻在《乔影》里则借谢絮才之口直接发出女性解放的呐喊,这从主人公出场便着巾服便可见一斑。显然,这是吴藻深思熟慮的结果,有着绝不妥协的决绝和果敢。作为文坛后辈,在思想性上,窃以为,吴藻显然胜过了陈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