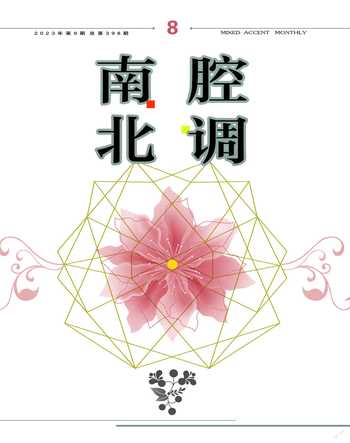“双线叙事”下的乡村困境与希望
2023-08-31郭一谨
郭一谨
摘 要:小说《宝水》主要围绕着明暗两条叙事线索展开,明线主要叙述宝水村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建设乡村旅游业的全过程,暗线则深入主人公地青萍隐秘、曲折的私人情感。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相互交织,一方面反映了当下乡村发展背后的某种精神痼疾与困境,另一方面又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新生蜕变与希望。
关键词:乔叶;《宝水》;双线叙事;困境;希望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问世不久,就先后登上了多个文学好书榜,颇受读者青睐。作为一位“70后”作家,乔叶此次落笔生根在新山乡,并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展现了中国现代化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也唤醒了无数人心里那份丰饶细腻的情感。
小说依照春、夏、秋、冬的时序衍移,聚焦于中原大地上宝水这个村落,以女主人公地青萍重返乡村治疗“失眠症”为线索,讲述宝水村成功从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化旅游业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的故事。小说透过“归乡者”青萍的目光和思考,写出了当下乡村背后的沉疴痼疾、精神困境,并以朴素的笔调,在生动琐碎的家常中娓娓道出新时代乡村的新生蜕变、绵延不息。
一、一明一暗的双线交织
《宝水》有着独特的叙事手法,不是由单一的明线牵引着读者,而是有明暗两条叙事線索。明线紧紧围绕着宝水村展开,讲述宝水村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完成乡村转型的故事,主人公青萍正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见证者、推动者。与此同时展开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青萍的“病”,作品展现了她的原乡记忆的“隐痛”留存以及重返乡土的“疗愈”过程。明暗双线交织贯穿全篇,共同推动着故事的发生与发展。
小说开篇即介绍了中年丧夫的主人公青萍因长期受到严重“失眠症”困扰,提前从“象城”报社退休,为休养身心,便应老朋友老原之邀,来到其老家宝水村协助经营由原家老宅改成的旅游民宿,开始在宝水村一年的生活。小说便由此借着青萍的眼睛和心灵,体察着宝水方方面面的肌理层次。宝水村民在乡村建设专家“孟胡子”、乡村干部刘大英、秀梅等人的引导、带动下发展乡村旅游业,从“孟胡子”来村里设计图纸、进行局部改造,到青萍替老原接管民宿,筹建“村史馆”等工作,人物在明面上直接介入宝水村的变革成为小说的明线。
在宝水村的乡村旅游业由“乱”到“治”的发展过程中,各家有各家的“生意经”。在乡村转型经历“阵痛”之时,村民们纷纷献言献策,积极解决激增的客流导致的有关堵车和停车、生活垃圾的处理、公共卫生服务等问题,大家做好食品安全与保障,和游客打好交道,做到既保障服务又保持盈利。与此同时,宝水这个当下的新农村,也已然进入短视频时代,青萍和村里的“三梅”共同经营的抖音账号“宝水有青梅”将富有特色的乡村生态,通过互联网媒介平台呈现在更多的远方客户面前,宝水村成功地从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
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小说的暗线从故事的开头就“埋”上了:
“若是明天出门,我今晚八点就会吞下安眠药,洗漱完毕,兢兢业业地上床卧着,像母鸡孵蛋似的,巴望着能顺利地孵出一点儿毛茸茸的睡意。能睡着一会儿算是运气好,睡不着就是分内。”[1]
小说的暗线正是由青萍严重的“失眠症”所勾连起的一系列隐秘、曲折的私人情感。青萍由奶奶一手带大,童年生长于和宝水村同属怀川县的福田庄,十几岁时随父母来到“象城”读书。奶奶和福田庄对她而言,既意味着温暖、亲密、自由的童年经历,又构成自卑敏感的少女在都市目光的打量下最想洗去的乡村印记。青萍的奶奶爱“维人”,也擅长“维人”,在福田庄的语境里,“维人”,意指“对各种人脉资源的经营缮护”[2]。从她记事起,甚至在父亲出生之前,奶奶“维人”的长绳就已经开始编织,依靠着奶奶“维人”,小门小户的地家在福田庄支撑起相对稳固的地位,也保留住了起码的体面。奶奶一辈子所遵循的农村伦理与处事法则,以剪不断的人情往来的方式,牵缚着在“象城”工作的父亲,困扰着城市出身的母亲,最终酿成了家庭的悲剧——父亲在帮福田庄七娘的儿子借体面的红色“桑塔纳”婚车的途中发生车祸,意外丧生。在青萍看来,来自福田庄的所有麻烦都寄生在奶奶身上,福田庄等于奶奶,奶奶就等于福田庄。多年来,村里人无数次托在“象城”工作的父亲帮忙办事,而奶奶的满口答应、从不拒绝,让青萍感到愤怒。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奶奶非要给父亲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并把他拖进深渊、陷阱里。父亲的死,更是直接导致青萍与奶奶之间难以消除的情感裂痕,而老家福田庄也成为她最深刻和最疼痛的记忆。在城市核心家庭惧怕的“人情线”里所包含着的付出、压力与束缚之下,奶奶的“维人”被误解为一种为了维系自家在村里的面子、地位、虚荣心与实际利益的“私心”。即便青萍在“象城”结婚之后,这种城乡之间的冲突与纠葛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也未在平淡的婚姻生活中得以抚平,且伴随着丈夫的去世更加难以愈合。对乡村生活既眷恋又怨恨、既怀念又恐惧、既亲近又疏离的复杂情感,以严重的失眠、多梦的精神病症长久地折磨着她。
在小说的暗线叙事上,青萍的“病”以及微妙的情感变化并非以顺叙展开,而是作为记忆或梦境的“碎片”穿插在宝水四时流转、晨昏相继的日常生活里。她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宝水村里,与村民朝夕相处,变成宝水乡村式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式的“乡村农民”。青萍在参与宝水村事务、和村民共同经营民宿的过程中,不得不切实地解决农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甚至大小摩擦,因而需要不断地调动其从奶奶、父亲和福田庄村民那里所获得的乡村生活的经验与知识。她能从宝水的“老祖槐”联想到小时候自家院子里的槐树,从跛腿的光辉身上看到自己叔叔的影子,从要强得令人心疼的小女孩曹灿身上突然照见童年的自己……在陪九奶睡觉时,能突然从她身上嗅到自己奶奶那种熟悉的、令人安宁的气息,“仿佛在这一刻,穿越到了福田庄的老宅,穿越到了小时候”[3]。更重要的是,青萍在宝水所体味的乡村生活,混合着温厚与无奈、情理与计算的人情世故,最终构成她理解奶奶为何如此重视地缘、亲缘的传统乡村情感根据。在宝水,她遇到了大英,遇到了秀梅、青梅、雪梅,更遇到了九奶——这位年轻时和自己奶奶有过交情的老人。也是在和九奶相处的日子里,她才彻底地认识了奶奶,明白了奶奶为何热衷于“维人”,最后她也成为奶奶——为宝水村的人情琐事忙碌着。“我在宝水村做到这些分外之事,在本质上好像就是对福田庄的弥补性移情。”[4]她曾经在福田庄所抗拒的一切,在宝水却逐渐自然而然地接受着、包容着。她重新回到了真实的乡村结构内部,理解了乡村世界的行为逻辑,进而也重构了“人与我”“城与乡”之间的关系。
二、难以言传的沉疴痼疾
一直以来,“乡村”作为一个积淀着种种社会问题的庞大群体,许多作家纷纷把目光投注到这个难以回避的社会群落中,乔叶也是如此。她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通过“我”的视角讲述隐忍、勤劳却深受中国男权主导文化压抑钳制的奶奶的一生;长篇小说《拆楼记》的叙述者“我”带着城市知识分子的目光审视乡村的落后与愚昧,并怀着一颗悲悯之心看到了乡村背后的生存困境。
《宝水》延续着这一话语,小说以主人公青萍的视角,展现她原乡记忆的隐痛以及这背后所暗藏的种种乡村困境、沉疴痼疾。青萍奶奶的“维人”,从表面上看是传统乡村生活中维系邻里关系的纽带,实际上折射出的却是乡村背后的某种生存艰难。青萍的爷爷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从了军,奶奶一边勤谨恭敬地侍奉着公婆,同时又提心吊胆地盼候着爷爷。在那个年代,奶奶作为乡村生活中的弱势存在,不是被人摘走刚刚变红的枣子,就是被偷走垛得整整齐齐的柴火,日子过得如履薄冰,却没有实力扑上去与对方撕个高低。新中国成立后,本以为很快就可以过上安生日子,爷爷却不幸在解放大西南的战争中牺牲,从此奶奶成为“光荣烈属”,独自抚养着年幼的父亲和刚刚出生的叔叔,正是因为得到了邻里乡亲们的不断帮扶,日子才渐渐好了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奶奶的“维人”是乡村底层最无奈的生存之道。而当父亲大学毕业,在“象城”立定脚跟后,奶奶更是抓住这个出息了的长子继续她的“维人”,一件一件地给村里人办事,这也是在进行道义上的人情回报。
在福田庄,“最会讲理”的奶奶正是凭借着在家长里短中宽解人心的本领和在“象城”工作的父亲对邻里乡亲源源不断地帮扶“维住了人”,使得地家成功处于村里的“上层”。“人情似锯,你来我去。”[5]这是她的嘴边话。奶奶看重的是“你来我去”里的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这是乡村生活的基本伦理要求,既是回馈与报偿,也是预支和交换,更是相互依靠、信任、包容的共同体生活。对于奶奶和福田庄来说,重点是“你来我去”,然而对于青萍的小家庭而言,重点却是“人情似锯”。“被锯”,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疼痛。即便父亲已经接受过大学教育,也无法摆脱这种强大的旧式乡村伦理。他被来自福田庄的各种复杂人情线捆扎着,陷入泥潭似的深网,在以奶奶为中心的传统乡村生活逻辑的要求下一件件地给村里人办事,甚至最终丧失性命。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父亲的死却是他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是“自杀”:早年间青萍叔叔结婚时,父亲主动借来一辆“破天荒”的吉普车当婚车,由此便在村里开了头,“找婚车”便成为村民心中父亲能办到的重大事件之一。起初只是吉普车,后来发展成小轿车,最后甚至挑起了颜色,必须要红色的小轿车。在青萍看来,如果当年叔叔结婚时父亲没有借那辆吉普车,便不会有之后的帮七娘的儿子借红色“桑塔纳”,他做的这些也许是为了讨奶奶欢心,也许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许两者兼有之。但他已经死了,一切都不得而知。
在小说的叙述上,父亲、奶奶、福田庄,构成青萍隐秘、疼痛的原乡记忆,她曾经拼命从福田庄逃离到“象城”,在城市中漂泊,追求着事业、金钱、欲望,但无论她多么努力地融入,其外在和心灵都无法彻底地与故乡割裂,都被深深打上了原乡的隐痛烙印。一次偶然的机会,青萍来到宝水生活,并在田间劳动中不断地进行旧日回溯,在植物菜蔬里平复了内心的伤痛。在一年四季的更替中,她联结起上自老人九奶、下到青年香梅等农村女性的历史记忆和生命经验,也见证了宝水的绵延不息与新生蜕变。但与此同时,随着青萍一步步深入村民生活,宝水村的“暗面”也借着她的眼睛和心灵凸显了出来。
宝水村主任兼支书刘大英性格直率泼辣,表面上看大大咧咧没有城府,实际上凡事拿捏得当,进退有余。然而,大英强悍干练又聪慧狡黠,却承受着女儿娇娇“怕见生人”的癔症带来的难言之痛。娇娇的病来自早年间进城打工时遭到侵犯后难以愈合的精神重创。村里孩子没上过多少学,心思又简单,到城里打工多不适应,精神病便成了近年来周围村庄里最常见的病症。美丽风情的香梅长期遭受着丈夫七成的家暴,但她没有选择大众化的妇女保护渠道,而是以青萍难以想象的方式秘密谋划、反戈一击。她先是私会初恋男友,后是设局致七成摔伤腿脚,趁机对他大打出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6],香梅选择了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而非知识分子式的维权,维系着他们之间恐怖的、平衡式的婚姻。
小说看似笔调温和,实际上触及乡村的某些共性、重大的问题,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留守儿童的困境、家暴等。小说包含着乡村生活的种种真实质感,同时也迂回地呈现出农村的另一个“切面”。《宝水》在叙事双线的互相交织、牵制下折射出当代乡村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沉疴痼疾,无论是福田庄的奶奶、父亲,还是宝水村的娇娇、香梅,都反映出乡村背后的某种生存艰难和精神病态。乔叶以真实但不尖锐的方式揭露乡村存在的切实问题,在她的笔下,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精神困境的存在地。
三、生生不息的乡土希望
“乡村”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重要表现领域之一,文学史上也诞生了诸多表现农村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比如《故乡》《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近年来“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无疑需要以文化作为支撑,才能使社会各界在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和整合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农村文化建设”[7]。时移世异,如何用文学形式反映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审美价值,开拓出文艺新境界,是新时代文学从业者需要探讨的课题。
与《最慢的是活着》《拆楼记》等作品不同,《宝水》的出色之处就在于乔叶在批判乡村沉疴的同时,更有着对乡村空间温情的怀恋以及对乡村发展的忧思和展望。小说没有从概念、观念出发,而是实实在在地潜入农村生活深处,写活了人物,写足了细节,呈现出新山乡生存与振兴的时代故事与当代乡村建设发展的可能路径。
初到宝水,青萍并不愿意真正进入乡村内部,因为父亲间接死于“人情”,所以她對乡村的“人情”社会充满了偏见,她只想当一个宝水村的“旁观者”,不过度介入宝水人的生活,又不过于冷漠。起初她庆幸自己是个“外人”,然而宝水村的四季变化与自然风光,抚慰着她的心灵,也缓缓地改变着她的想法,渐渐地她也时常觉得自己在“里子”里了。在乡村里“悠”着,和村民一起“扯云话”“挖茵陈”“吃懒龙”“数九肉”“打艾草”,听九奶讲她和老原爷爷的情感往事,了解她对心上人坚贞的守望和践诺,包括九奶最后的离世和“喜丧”,这些日常的村事和乡间生活、传统的风俗与民间文化,都在改变着她的故乡记忆,并在潜移默化中疗愈着她。“对于青萍而言,故乡福田庄承载了她的创伤记忆,如同一个噩梦般的存在。宝水则是一剂良药,带给青萍宝贵的治愈感。青萍年少时,不理解村里人为何值得她奶奶付出,而她十几岁时的困惑,直至四十几岁时才在宝水村得到了解答。”[8]通过在宝水的疗愈,一个原本对生活心灰意冷的中年女人,最终和比认识丈夫还早、给自己介绍过对象的老朋友老原在九奶“你俩好了没有”的牵线下“身不由己”,成为恋人。至此,青萍完全成为乡人眼中“宝水村的女人”,真正地在“里子”里了。
在小說的文本铺陈中,作者用四季更替的方式讲述着宝水的故事,不厌其烦地书写着乡村的自然风景与风土人情。在宝水,招呼客人到自家吃饭不用四碟八碗,就是添碗水添双筷子的事;谁家杀只鸡,杀只鹅,都会叫上邻居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前来支教的研究生周宁和肖瑞为村里的孩子开办“性教育”知识讲座;谁家有困难需要帮忙,能搭把手的事就绝不冷漠——正如九奶所言:“人在人里,水在水里。活这一辈子,哪能只顾自己。”[9]这句话道尽了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情感和联系。
作为“美丽乡村示范项目”的宝水村,新绿初萌,春花初绽,水清路畅,屋舍整洁。宝水村民在“孟胡子”、大英等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通过民宿民居、高效农业、户外拓展、旅游经济等各种途径,优化了农村环境,提升了服务意识,不仅让村民拥有了更加幸福的居家生活,也让游客获得了更加美好的乡村体验。宝水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发展突飞猛进,希望的种子在宝水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当然,旧的乡村文化伦理道德、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和新时代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每天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纠葛、矛盾与冲突。散漫的生活习惯、利己主义、追逐华丽装饰的心思与崇尚自然、淳朴、清洁、爽朗、高效、有序的乡村建设的冲撞、抵抗与缠绕,都在宝水时时发生。青萍、大英、 “孟胡子”、杨镇长、王主任、老原等人都参与到了这项事业中。除此之外,青萍还负责筹建宝水村“村史馆”等工作,这些都让她真实见证了新时代城乡之间的流动、互动、碰撞与融合,感受到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艰难、曲折和复杂。
在《宝水》中,作者几乎完全摒弃了“阳春白雪”式的辞藻,而是选择大量使用河南方言土语,比如处理人际关系叫“维人”、聊天叫“扯云话”、喜欢叫“景”、夸人出色叫“卓”……这些土话作为乔叶“独特的母语”,更带着淳朴、温度与感情。这些方言的介入,大大激活了小说的动感,也使得小说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显得更加“接地气”。乔叶的老家在河南焦作,因此她把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作为小说写作的核心,在《宝水》中,乔叶给郑州另起了一个名字叫“象城”,老家焦作叫“予城”。“予”是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宝水》中的叙事角度就是第一人称“我”,而“象”和“予”合在一起,就是“豫”。如乔叶所言:“我‘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宝水》里的这些地名。人到中年,离家乡越来越远,而写作却有回归迹象,故乡的根一直跟随着我。”[10] 为了写好《宝水》,乔叶经历了长期的“跑村”和“泡村”,走进真实的乡村生活现场,深入乡村生活内部,和村民生活在一起,如此才写出了乡村振兴的艰难和复杂,以及在这艰难性与复杂性中产生或成长的各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结 语
生活的“宝水”是天然的恩赐。小说名字“宝水”一语双关,既是村名,也包含了生活是创作的宝贵源泉的含义。乔叶经历了长时间的“跑村”和“泡村”,积累了大量鲜活有趣的素材,由此才写出了新农村建设、新山乡振兴的出色之作。与此同时,“水象征着特别宝贵的民间力量,就像宝水村民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可以爆发出很多智慧和努力,很像山间的泉水,可能特别细小,但是汇聚起来就能成江成河。”[11]
《宝水》通过一明一暗的双线叙事,写出了当下乡村的困境与希望。乡村固然是某种精神困境、沉疴痼疾的存在地,但小说也借着地方风情、文旅资源丰盈了失落的乡土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被荒废了的农村重新恢复活力,吸引着更多青年人回到农村发展,这既寄托了乔叶对中国新农村发展的期望,也开启了一种乡村新书写的可能。
参考文献:
[1][2][3][4][5][6][9]乔叶.宝水[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6,189,278,345,195,350,417.
[7]饶曙光,兰健华.共同体作为方法:乡村振兴主题电影的高质量发展路径[J].长江文艺评论,2021(03).
[8]顾学文,沃佳.“新乡土小说”系列访谈︱乔叶:“巨变”原是在生活中点滴发生的[N].解放日报, 2023-02-25(05).
[10]张帅.乔叶:虚构写作 抵达现实[N].大公报,2023-04-03(B1).
[11]李喆.乔叶:诚实地去倾听,朴素地去写[N].北京青年报,2023-01-09(B01).
作者单位: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