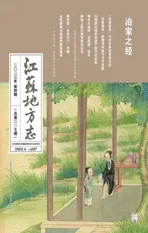《治家格言》与中华传统家训文化
2023-08-29周晓光
◎周晓光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朱用纯(1627—1698),字致一,号柏庐,明末清初苏州府昆山县人。《清史稿》有传。据相关传记资料记载,朱氏“覃精理学,凡六经四子,濂、洛、关、闽诸书,及明儒薛、胡、高、顾之论说,辨析毫厘,知行并进,而一以主敬为程”[1],其基本学术倾向偏于程朱理学一派。明亡隐居不仕,教授生徒以养家,凡“来学者,授以小学、近思录。仿白鹿洞规,设讲约,从者皆兴起”[2]。在明清鼎革之际,是一位颇有影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氏著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春秋五传酌解》《困衡录》《愧讷集》《毋欺录》《治家格言》等,其中《治家格言》流传极广,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经典之作。
一、《治家格言》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典型代表
家训起源甚早,一般认为西周初年文王、武王的王室家训发其端,而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诫伯禽》,则是最早的家训名篇之一。在数千年的演化、发展过程中,家训“由个别到一般、由贫乏到丰富、从分散到系统、从浅表到深层”[3],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主旨鲜明的中华传统家训文化。按照学界的认识,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精髓是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等。[4]《治家格言》正是体现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精髓的典型作品。
关于道德人格,《治家格言》主张“居身务期质朴”,也就是要求做人必须涵养淳朴的品格,为此《治家格言》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如对待富贵与贫穷,《治家格言》说:“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在朱柏庐看来,嫌贫爱富是一种可耻的道德人格,当予以摒弃。对待钱财,《治家格言》强调“勿贪意外之财”“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嫁娶要重人品而轻财物。见到“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朱柏庐认为,幸灾乐祸的心态并非磊落的道德人格。此外,在待人接物、临事处置、居家睦邻、积德行善等方面,《治家格言》也都基于磊落光明的道德人格要求,一一训诫,树立规矩,体现了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本质要求。朱柏庐后来撰写了另一部家训《劝言》,被视为《治家格言》的姊妹篇,它进一步细化了《治家格言》的规范和要求,两者在思想上高度一致。《劝言》对道德人格还有进一步阐释和要求。如称“积德之事,人皆谓惟富贵,然后其力可为。抑知富贵者,积德之报。必待富贵而后积德,则富贵何日可得?积德之事,何日可为?惟于不富不贵之时,能力行善,此其事为尤难,其功为尤倍也。盖德亦是天性中所备,无事外求,积德亦随在可为,不必有待”[5]。对于道德人格,朱柏庐提出了“德”本于人的天性,无论富贵与否,积德之事“随在可为,不必有待”的看法。

朱柏庐画像
关于教子方法,《治家格言》认为“训子要有义方”,而“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所谓“义方”,就是立身行事的规矩和法度,从教导子孙读书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有基本遵循。《劝言》之《读书篇》对此进一步发挥道:“读书须先论其人,次论其法。所谓法者,不但记其章句,而当求其义理。所谓人者,不但中举人进士要读书,做好人尤要读书。”朱柏庐认为,教导子孙读书,其重当在明了圣贤之书中的“义理”,懂得“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的道理。[6]这里体现了朱氏之家教,高度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关于读书目的和功业理想,《治家格言》言:“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也就是说,子孙读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应科举求功名,而更重要的是见贤思齐,成为一个具有圣贤之品格的“好人”。对于功业理想,朱柏庐训诫子孙:“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就是要以天下国家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治家格言》说:“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即使在完纳税课后囊中并无分文,但仍要以履行了对朝廷的“义务”为至乐之事,这是朱柏庐也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所提倡的家国情怀。
为人处世中,《治家格言》提倡拥有淡泊的襟怀。“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不争讼、不多言,方是处事之道。朱柏庐还训诫子孙:“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愬,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要求子孙遇事当淡泊处之,“守分安命,顺时听天”。《治家格言》所倡导的这种淡泊人生,也正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核心要义之一。至于如何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治家格言》亦有反复训导,如“宴客切勿留连”“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等等,皆符合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主旨。因此,从总体来看,《治家格言》体现了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精髓,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典型代表。
二、《治家格言》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践行指南
中华传统家训文化博大精深,具有系统的学理体系。无论是针对家庭的家约、家风、家规、家法、家诫等,还是面向宗族的族规、族谕、宗约、祠规、祠约等,都具有丰富的内容,涉及立德树人、纲常人伦、人格塑造、处事之道、行为规范等方面。动辄数十上百条的训诫,在传统家训中并不鲜见。如元代郑太和的《郑氏规范》多达168 则,凡冠婚丧祭、衣服饮食、日常行止、待人接物等,无所不包。历代之家训,大多重视将天理人伦原则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事之中,告诫家人和族人如何立身处事、如何践行文化传统。比如孔子第十世孙孔臧告诫其子孔琳:“徒学知之,未如多履而行之。”[7]既要为学,更要践行。《清史稿》在朱柏庐本传中,言朱氏“其学确守程朱,知行并进”[2],赞誉其是一位崇尚理论认知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学者。朱柏庐在《毋欺录》中曾表示:“下学而上达,上达即在下学中……学之必不可不进于上达,而教之必不可不主于下学也。”[8]因此其《治家格言》,尤为强调于日常具体行为规范要求中,彰显中华传统家训文化内涵,体现了鲜明的实践性。
比如,《治家格言》开篇即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这里,朱柏庐将一天的规律作息和家庭卫生环境的维护,视为治家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传统家训文化中,这是被反复强调的基本要求。先秦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于《弟子职》篇中言:“少者之事,夜寐蚤作……凡拚之道,实水于盘,攘臂袂及肘,堂上则播洒,室中握手。”要求弟子作息规律,甚至还提及了打扫房间的方法。北宋学者苏洵撰有《安乐铭》,其中反复提到“贫富俱当早起,一日之计在寅”“门户向晚早闭”“洒扫厅堂前后,拂拭桌凳灰尘”“吩咐厨中女眷,碗碟擦净洗新”。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训蒙绝句·小学》中也提及“洒扫庭堂职是供”。朱柏庐《治家格言》开篇之言,实际上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具体践行训诫。再如《治家格言》中的名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乃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珍视物力之精髓要义的具体表达。宋代江端友在《家训》中曾说:“凡饮食知所从来,五谷则人牛稼穑之艰难,天地风雨之顺成,变生作熟,皆不容易。”清初张履祥《示儿》篇中有“稼穑艰难,自幼固当知之”句,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又如,中华传统家训文化尤重节俭风尚,南北朝源贺《遗令敕诸子》要求诸子“毋奢越”;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主张“施而不奢,俭而不吝”,意思是花钱而不奢侈,节省而不吝啬。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诫江夏王义恭书》要求“供用奉身,皆有节度”,虽显为贵族,也当以节俭为大。唐代柳玭的《柳氏家训》训诫家人要“以勤俭为法”。苏洵的《安乐铭》提倡“省使俭用过世,粗衣淡饭为主”。宋代名臣司马光曾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的《训子孙文》一再告诫后人“有德者皆由俭来”,而“俭,德之共”“侈,恶之大也”,将节俭视为有德品格之重要表现。宋人赵鼎《家训笔录》称:“古今遗法子弟,固有成书,其详不可概举。惟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明末清初人傅山撰有《十六字格言》,其中一字为“俭”,傅氏称:“一切饭食衣服,不饥不寒,足矣。”可见,节俭在中华传统家训文化中,作为治家的基本法则而被广泛提倡。那么,如何践行这一传统家训文化的治家法则呢?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将其落实到了具体要求上,提出“自奉必须俭约”“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勿贪口腹而恣杀牲禽”,尤其是“莫饮过量之酒”。过量饮酒,在传统家训文化中是一再被告诫有违节俭原则的。早在汉代,有严光者说“嗜酒者,穷馁之始也”。三国时,王肃有《家诫》称:“夫酒所以行礼、养性命、为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而唐代王梵志的《世训格言诗》亦言“饮酒妨生计”。因此,在践行节俭家训文化时,《治家格言》强调了饮酒不可过量浪费。
此外,提倡读书始终是中华家训文化的主题之一。《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无论是明君帝王,还是平民百姓,勤学都是基本要求。北宋欧阳修《家诫二则》反复告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道理。明朝吴麟征《家诫要言》说:“多读书则气清,气清则神正,神正则吉祥出焉,自天祐之。读书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闲,邪闲则过恶作焉,忧患及之。”阐释了读书的重要性。《治家格言》秉承家训文化倡导读书的传统,训诫子弟“经书不可不读”。慎言在中华家训文化中也是屡屡被提及。如北宋苏洵《安乐铭》言:“但凡与人说话,腹中先要思忖。不干己事休说,不当言处莫论。……言语不可轻发。”南宋袁采《袁氏世范》说:“言语简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慎言于人于己,都是明智之举。明朝庞尚鹏《庞氏家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凡饮食不知节,言语不知谨,皆自贼其身,夫谁咎?”强调谨言慎行,为处事之要。明朝高攀龙《高氏家训》反复叮嘱“言语最要谨慎”“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明末清初人傅山在《十六字格言》中说:“默,此字只要谨言。古人戒此,多有成言矣。”朱柏庐《治家格言》同样训诫子孙:“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也是秉持了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要义。
传统家训文化言“恶事虽有千万,第一首数奸淫。我不淫人妻女,妻女亦不淫人”[9],《治家格言》则训诫:“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传统家训文化称“好讼甘刑求胜,怀仇斗力为能。纵然幸免夹打,奴颜屈膝公庭”[9],《治家格言》则曰:“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传统家训文化有“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10]之说,《治家格言》则要求“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传统家训文化反对嫌贫爱富,说“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长厚有识君子,必不然也。”[11]《治家格言》则直言不能因“见富贵而生谄容”,也不能“见贫穷而作骄态”。如此等等,中华传统家训文化之核心要义,《治家格言》均一一提出具体实践途径和做法。因此,该书其实是人们践行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一部指南书。
三、《治家格言》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播典范
记载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家训类文献,历史上并不在少数。翟博主编的《中国家训经典》收录了上起周朝,下迄明清之家训273篇(部)。赵振《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则著录了传统家训233篇(部),并记录了历代家训专著存目160 篇(部)、历代亡佚家训专著266 篇(部)。南宋时还首次出现了古代家训总集—刘清之的《戒子通录》,仅此一书即收录先秦至两宋的家训171篇,“凡为父母、为子侄、为兄弟、为夫妇之道具是”[12]。不过这些数量巨大的家训文献大多存于个人文集、谱牒、方志、类书中,而如《颜氏家训》等以单行本传播的较少。即使像《戒子通录》等广受好评的家训著述,传播并不广泛,影响也甚为有限。元人崔栋称:“刘清之所辑《戒子通录》一编,皆古者明君良臣、慈父淑母教诫子弟,理明意切,读之能使为人臣、为子弟者油然起忠孝之心。惜此本传之者寡。”[13]《四库全书总目》亦言:“自宋以来,史志及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文渊阁书目》载有二册,亦无卷数。”[14]可见尽管传统家训文化的著述数量丰硕,而家训传播则以家族内部相传为主,范围和影响受到较大局限。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治家格言》自问世后,受到了广泛关注,流传迅捷,风靡一时,成为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播典范。戴翊清在《治家格言绎义》的序中称:“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久传海内,妇孺皆知。”其时“江淮以南皆悬之壁,称《朱子家训》。”[15]文献学家张舜徽也指出:“昔在明末,有朱柏庐撰《治家格言》,举凡修身齐家、匹夫匹妇可行之事,皆言之甚悉。其后盛传于世,几乎家喻户晓。”[16]乾隆三十年(1765),《治家格言》还被译为满文,在八旗子弟中流行。甚至该家训还曾传播至日本等海外地区。[17]《治家格言》成为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传统家训文献之一。
那么,《治家格言》何以成为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播典范?
首先,《治家格言》的核心内容高度契合中国儒家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深得民众之信服。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伦理法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涉及了国家政治生活关系和家庭伦理生活关系,而“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关乎人与人、个人与群体及国家的关系,还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晚明及清初鼎革之际,与历史上“天崩地坼”的时代类似,传统社会中儒家的主流价值观受到冲击,按照朱柏庐的说法:“今举世之人,汲汲津津,所事者惟功利,所尚者惟富贵。其于人之所以为人,三纲五常之道,莫之或讲也。”[18]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精英期待回归长期浸润的伦理观念和伦理秩序,对《治家格言》这样一部意在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的家训,自然奉若佳典。清人郑光祖说:“世传《朱子家训》是明季朱柏庐《治家格言》,语虽浅近,意却精深,与孔孟之书实无歧异,学者读而守之,亦可寡过。”[19]《治家格言》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强调“为官心存君国”“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在父子关系上,称“训子要有义方”“薄父母,不成人子”;在夫妻关系上,告诫“妻妾切忌艳妆”“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这些训诫,其实是儒家伦理“三纲”的具体反映。而500 余字的各条具体规范要求,体现的也是“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实质。中国儒家文化“三纲五常”的主流价值观,以当今时代的视角来看,其中不乏糟粕;但它契合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人生理念,被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推崇和接受,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治家格言》以工整的排比对仗展示通俗易懂的文字,这种表现形式深得民众之喜爱。关于朱柏庐之文章,其好友杨无咎曾说:“柏庐雅不欲以诗文自鸣,而其所作咸有法度,修辞立诚,非专工词藻者所能及也。”[20]高度评价了朱柏庐作为一个文人的创作水平。有学者评论道:“朱用纯的散文或文章,亦自有较高的成就……从内容上看,朱氏文章同其为人一样,无论是倡导气节、关注修身,还是怀人感旧、谈诗论文,多为言之有物、有感而发之作,而少无病呻吟、敷衍应酬之篇。需要拈出一说的,即便是他那些为数甚夥的纯粹道德劝勉之文,亦因文如其人和其业,而毫无造作虚伪之痕,充满感染震动之力。”[21]对朱柏庐之文学成就评价甚高。就《治家格言》来说,文章一是辞藻华美,对仗工整,体现了形式之美;二是文字浅白,通俗易懂,体现了表达之力;三是韵律和谐,朗朗上口,体现了遣词之才。一篇内涵丰富、警句迭出、文采斐然的家训,自然得到民众之喜爱和传播。

《江苏好家训》书影
再次,《治家格言》多样的传播方式,深得民众之喜闻乐见。《治家格言》问世后,其传播方式主要包括:一是抄录流传。抄录者中,既有普通的民众,也不乏名宦达官。如林则徐曾在江苏任职,途经昆山时亲笔抄录了《朱夫子治家格言》。[22]据学者对相关资料的整理,抄录《治家格言》的名家还包括了晚清重臣李鸿章、清末实业家黄自元、书法家魏戫、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清末民初著名社会活动家郑孝胥等,其中不少墨迹因人因字而显,成为名家墨宝广为流传。[23]而传抄的内容,或是整篇抄录,如上述名家的作品;或是录出警句,如山东巡抚程含章每任一地,必自书“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悬挂于大厅。抄录成为《治家格言》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二是刊刻流传。得益于明清时期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同时由于《治家格言》“其言质,愚智胥能通晓;其事迩,贵贱尽可遵行”[24],市场前景广阔,因此问世后,被坊间反复刊刻,形成了诸多版本。甚至有地方官员也组织刊刻活动,如清代名臣陈宏谋任职地方时,“刊发《朱子治家格言》万余本,分发各学”[25],以此教化民众。刊刻流传成为《治家格言》大规模传播的重要渠道。三是注疏传播。《治家格言》问世不久,朱柏庐弟子顾易即著《朱子家训演证》,阐释其意。其后出现的注疏、句解、演绎类的著述不胜枚举,如曹显伟《治家格言类证》、戴翊清《治家格言绎义》、朱凤鸣《朱子家训衍义》、金国均《朱子家训试帖》、杨继游《朱子家训格言诗》、五洲译书局《绘图注解朱子治家格言》、上海广益书局《绘图改良治家格言》等等。这些著述的出现和流传,对《治家格言》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治家格言》还广泛出现在碑刻、木雕、书法作品等载体上,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总之,《治家格言》成为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播典范,是传播内容、形式与方式有机融合的产物,它奠定了《治家格言》在中华传统家训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朱柏庐是晚明清初一位平民思想家、教育家,其《治家格言》既是中华传统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口,更是了解民众日常伦理生活的样本。开展对朱柏庐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治家格言》的价值和内涵,也有助于展示这位平民思想家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