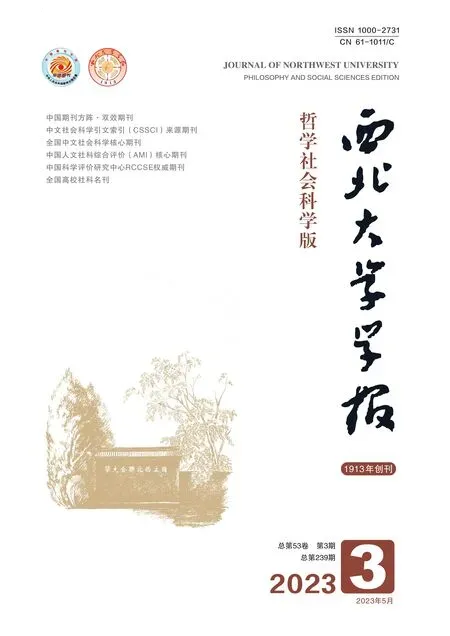视觉共同体与欧洲中国风中的“女托邦”
2023-08-26王大桥何琪萱
王大桥,何琪萱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风依托大量中国物品的传播,最先开启于古罗马时期(1)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波斯和印度就有贸易往来,然而,直到公元前1世纪初期,中国才真正开始直接参与世界贸易,穿越亚洲大陆后抵达地中海沿岸,最终将丝绸和瓷器传入古罗马。参见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随着中欧贸易交通的便利与进口规模的扩大,逐渐席卷整个欧洲。中国风在一般意义上通常被视作装饰艺术,是欧洲传统艺术的附庸和补充,对其研究也主要从艺术形式层面展开。但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中国风容纳且包含异质性的视觉经验和审美理念,特别是女性主体参与到中国风跨地域的审美表意实践中。她们的审美趣味和情感经验深刻影响中国风的艺术表达方式,形成一种包含意义增值的视觉经验,参与欧洲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理想、情感倾向与生活经验的生产建构。中国风孕育并粘连着女性视觉感知经验的变化与生成,梳理、考察与分析中国风所沉淀的本民族审美经验的再生产过程,指向了中欧审美经验中观看方式及其视觉经验的流变机制和特殊性。中国风中的视觉元素及其所携带的一种感觉方式、经验意义与情感想象为欧洲女性共享,以“女托邦”的形态,形成了一种以女性审美经验和生活趣味为主导的视觉共同体。
一、东风西渐中的视觉经验与女性的审美认同
中国物品是欧洲认识和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中国风的传入最先改变古罗马上层阶级女性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其后参与女性生活经验并塑造其审美趣味。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与高昂的运输成本,丝绸成为古罗马时期的奢侈品,由拥有较多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宫廷贵族独享。丝绸最早用于王室的盛典仪式,男性君主用昂贵的丝绸布代替亚麻布来铺设罗马广场的遮阳篷[1]16,通过展示财富和品味在宫廷中获得其他成员的认可,以达到彰显其优越社会地位的目的。丝绸作为奢侈品的区隔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阶级上,还集中表现在性别向度中。相比贵族男性视丝绸为贵族社会等级的标志,女性则更多关注其审美价值。中国丝绸涌入罗马前,女性通常穿着动物皮毛、植物纤维制成的服饰或希腊本土生产的斯科岛丝绸,后者的材质较中国丝绸更为粗糙,随着罗马进口中国丝绸数量的增加,希腊本土的丝绸逐渐退出罗马奢侈品市场[2]65。由于中国蚕丝易上色的特殊材质,丝绸通常呈现紫色、红色和蓝色等鲜艳色泽,加之技法精巧的中国传统刺绣[3]63,为欧洲女性带来陌异的视觉体验。
中国丝绸重塑与改写了罗马女性的视觉经验,并逐渐淡去其作为舶来品的身份,开始融入和渗透至本土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感受中。欧洲将中国丝绸拆洗,重新制作成薄若无物的布料。在罗马贸易市场中,丝绸轻盈、半透明的材质带给罗马贵妇强烈的视觉冲击,她们在对丝绸细腻材质的感受中生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在以女性主导的审美消费中,中国丝绸被运用于家庭装饰中,室内布置开始出现丝绸面料制作的窗帘和衬垫,随后逐渐演变为女性服饰[4]16,并以丝绸丝带和阳伞作为配饰。女性在公共场合贴身穿着薄如蝉翼的丝绸衣物有悖于当时的保守观念,但风月女子则带动了这一流行风尚,借以充分凸显自身的身体曲线。清柔的丝绸长裙甚至能透出她们的肉体肤色,在遮盖身体的同时也展现身体。在对其透明度进行调整之后的改良式丝绸材质中[5]28,这一审美风尚逐渐为普通女性所接受,丝绸飘逸的视觉特质保留下来,用以表现女性身体的婉约和柔美特质[1]29-31。由于丝绸在穿戴方面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在保守的罗马人看来,丝绸等轻质柔滑的面料太过女性化,不适合作为男装的制作材料。”[1]23丝绸所代表的性别差异甚至上升到社会法制的层面,罗马政府一度颁布禁止男性穿着丝绸衣物的社会禁令。
价格高昂的中国丝绸通常仅供罗马贵妇消费,她们的审美趣味浸透着本阶级的习俗,“习俗塑造着人的经验和行为,制约和规定着人‘看待’世界‘经验’世界的方式。”[6]136特定的文化产品为不同阶层的女性群体所认同,昂贵的丝绸与罗马上流阶级女性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起来。除重视丝绸面料本身外,她们还关注金线刺绣和特殊颜色等附加层面的审美价值。通常经过裁剪和刺绣的丝绸服饰价格不菲,而采用昂贵染料和金丝刺绣的长裙价格则更为高昂。另外,服饰颜色在古罗马承担着文化分层的区隔功能,紫红色作为个人权威与地位的标志曾为皇室所垄断[7]151-152,随着罗马刮起爱好丝绸的风潮,紫红色丝绸服饰逐渐为贵族女性所享用和穿着。由于彩色染料的稀有性,紫红色丝绸成本价格近乎纯白色的丝绸的十二倍,而普通阶层的妇女则根本无法承担这一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奢侈品(2)根据公元301年迪奥克莱斯皇帝颁布的《最高价格法》显示,在罗马帝国每磅纯白色丝绸的价格高达2 000赛斯特斯,而同等重量的紫色丝绸则近24万赛斯特斯。参见拉乌尔·麦克劳林克:《罗马帝国与丝绸之路》,周云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在上流阶级范围内,贵族女性经由丝绸,将自身身份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趣味和其他阶层的女性区别,实现了审美层面的交流与认同。通过穿着奢华的丝绸服饰,贵族女性强调了自身所属阶层趣味的合法性,精美的中国织物构成了她们公共集体性的视觉经验。正如尤卡·格罗瑙(Jukka Gronow)所言:“时尚能团结某一社会阶层内部人员,同时又在阶级之间划出分界线。”[8]113中国丝绸融入本土的审美习俗,成为区隔身份的标志性符号,由此建立起来的视觉共同体同样具有排斥其他阶层女性的特质。
在上行下效的流行机制的逐步带动下, 不同阶层的女性逐渐在家庭生活的私密空间中使用大量中国物品, 女性影响下的日常用品生产与市场消费趋向成为中国审美风尚的先声。 14世纪以降, 中国传统的瓷器、 漆器和玉器等日常器物经由中亚和西亚等国家传播至意大利[9]16-17, 成为宫廷贵族阶层女性珍贵的室内陈设, 贵族女性开辟专用的橱柜, 甚至建立瓷器室专门展示中国奢侈品。 17世纪中叶瓷器摆脱了附属装饰的地位, 成为衬托整个房间装潢的主角(3)奥利弗·英培(Oliver Impey)认为, 自1660年伊始瓷器开始成为整个房间装饰的主角。 这一时期中国瓷器作为装饰性物品为皇室贵族女性所展示, 并通常以堆砌的效果陈列。 17世纪里斯本的桑托斯宫是早期瓷器厅中最典范的一例, 桑托斯宫共安装260件青花瓷, 瓷器被永久性固定在木架上。 此后, 蒙特斯潘诺夫人的特列安农瓷宫、 玛丽女王的汉普顿宫以及德国王后索菲·夏洛特的夏腾堡等宫室陆续设立。 参见甘雪莉:《中国外销瓷》, 张关林译,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87-92页;Oliver Impey,Chinoiserie:The Impact of Oriental Styles on Western Art and Decoration,New York: Charles Seribner’s sons, 1977.。新奇的异域商品不断冲击着欧洲女性视觉经验, 她们对中国风物品的审美消费欲求大大提升。随着欧洲进口中国物品的扩大, 对中国器物的喜爱渐成风尚, 欧洲“中国风”自此形成。 物品价格的下降使中国风审美趣味开始突破传统社会阶级的区隔,原本宫廷范围内的审美风尚逐步为普通富裕家庭所接受, 瓷器更是从供人欣赏的装饰品演变为日常餐具的一部分。 最早专供欧洲市场的克拉克瓷中包括大量碗、 盘子、 茶具及盐、 醋调味料瓶等实用器型, 早期贵族通常使用价格高昂的银器作为餐具, 中等阶层的家庭则更多使用白镴餐具。 由于白镴的质地无法添加任何纹饰,随着瓷器的大规模涌入, 更具有审美价值的瓷器受到欧洲女性的喜爱[10]298-301。
在传统的审美文化视域下,女性被局限于家庭事务内,通常与味觉这一低级的感官范畴相关。考斯梅尔认为:“食物领域强调的是家庭化和女性化,其不仅表达在象征层面,还直接体现在字面意义上,因为家庭生活中的女性承担准备食物的任务。”[11]9518世纪,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剧增,荷兰和英国掀起“饮茶风”。酒和咖啡通常出现于男性构筑的公共空间中,咖啡屋成为精英男性群体谈论政治话题的重要场所,而饮茶活动则主要在家庭空间内开展,由女主人和女仆主持并参与[12]178-183。中国的饮茶习俗融入欧洲女性的日常经验中,在英国贵族女性群体中形成“下午茶”的审美仪式,饮茶风尚的兴起带动瓷器茶具和茶服等物品的消费和使用,这些物品在女性日常经验与无意识的观看过程中变得熟悉。中国物品上的视觉图案作为传达意义和信息的视觉符码,在潜移默化中参与改变了欧洲女性的视觉经验和情感结构。
随着中国物品的域外流通,欧洲女性在集体观看和欣赏中国器物的视觉图像时,与中国女性共享视觉符码及其意义的表达。花卉与动物作为中国艺术中的经典母题,经由瓷器等物质载体传播至欧洲,并在欧洲形成一种欣赏花鸟纹饰的审美趣味,“欧洲人也欣赏花草图案之美,中国瓷器外销欧洲,也开始了花卉图案的交流”[13]137。花卉是物质媒介中的常见图案,前身来源于希腊和罗马的玫瑰、棕榈和藤蔓纹饰,因娇柔、美丽等审美特质与女性形成譬喻,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阴性符码,为各地女性观者所广泛接受。随着全球贸易的拓展,缠枝花卉经由中亚传到中国,来自欧洲的异域花卉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莲花和牡丹等花卉[14]63-75,其在宗教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后,渗入到与女性密切相关的装饰艺术与日常生活中,在丝绸、银器和瓷器等视觉媒介中得以表达。中国视觉图像所承载的情感与意义粘连着女性的集体想象,认同“依赖于一套广泛界定族群的群体象征”[15]130,欧洲女性在观看日常用品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和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花卉纹饰。中国花卉与本土莨苕涡卷的组合呈现出奇异和美丽的视觉特质,展现了她们区别于男性的视觉经验,这一审美趣味同样符合欧洲女性的审美期待。
女性在共享一种视觉符码和意义的过程中形成审美认同。缠枝花卉和凤鸟主题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与女性具有天然的亲缘性,其折射中华民族的性别文化观念,蕴含中国女性个体切身的日常经验与审美感受。在中国“花卉指向女性的甜蜜和美丽特征,并通常指涉女性的少女时代,艺术作品致力于建构和强化女性和花卉之间的关联”[16]43。在中国早期文化阴/阳二元观念中,朱雀和凤凰作为与女性相关的阴性视觉语汇,直接代表皇后;牡丹花卉则直接与唐朝女皇武则天统治时期的个人偏好有关,成为高雅华贵的象征。花纹装饰基于不同的审美经验投射出相异的审美意义,花鸟纹饰逐渐被赋予浪漫、奇丽的审美特质,其背后深层的政治象征、文化内涵和神话色彩逐渐淡去,正如霍尔所言,视觉形象“永远不会最终确定,而是始终受制于变动”[17]32。在欧洲女性自身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的介入中, 中国经典视觉形象在跨文明圈的交流中获得可流通、 可共享的普遍审美意涵: 花卉硕大的花蕾和舒展的叶饰, 飞鸟娇小的体态、 伸展的翅膀和细长的尾部羽毛为女性所捕捉和经验, 花鸟图案在跨文化传播中融入不同文化群体的女性经验与情感中, 共通的视觉符码成为文化认同的载体, 为中欧视觉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向度。
中国风物品以直观的感性视觉符码脱离抽象艺术形式与复杂的文化背景,因此较少受到艺术学院及其制度体系的喜爱。高雅艺术通常由男性趣味主导,男性精英群体旨在捍卫与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无涉的艺术形式,中国风作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装饰艺术被排挤到欧洲艺术正典之外。在诸多视觉形象中,欧洲女性偏爱表现中国女性的图像,柯律格指出除载有女性人物的各种器皿外,欧洲女性还钟爱女性人物立体雕像,“一般来说,女性形象很受欢迎,因为她们描绘了东方的异域风情和服饰风格”[18]48。中国景德镇和德化专门制作女性佛像与普通人物造像,新奇的人物造型为欧洲女性接受和喜爱,女性造型逐渐成为欧洲客户特别定制的样式[19]105,191-194。在人物造像方面,中国古代女性的柳叶眉、花瓣唇妆和带有中国传统纹饰的长袍带来了异质性的审美感受。其中遮蔽身体性征的宽松长袍成为与欧洲女性日常生活相关的晨袍、睡袍和茶服,这种直筒版型服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女性对沙漏型服饰的追求,松动了视腰线为表现女性魅力之唯一方式的西方传统审美观念。女性服饰的变化蕴含着她们的审美偏好和内心情感,中国女性服饰松动了欧洲女性既有的日常生活经验。
此外,中国风不限于直观静态视觉图像,同时还展现于公共的文化空间中,彭丽君认为“一个人有意识地参与到更大的集体中,能更强有力也更有效地形塑其认同”[20]152。中国审美风尚除通过装饰艺术媒介传播外,还通过戏剧以及狂欢节等得以充分展现。由于希腊与罗马的传统戏剧将女性的腿视为贞洁的象征不允许展示,所以剧中女性角色通常由男性扮演。遮盖女性禁忌部位的中国长袍和长裤为欧洲女性演员的出演提供重要契机,巴黎戏剧中女性人物服饰遵循中国习俗,裙子无鲸骨架,也没有低胸衣领[21]129,女演员通过穿着中国服饰参与到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中。中国风舞台主要基于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视觉表征,呈现神秘和奇幻的美学风格,欧洲非常喜爱使用中国风布景,甚至“中国服饰和宝塔等中国视觉元素被用于欧洲古典主义戏剧题材中”[22]122。剧场提供了一个共享视觉经验的公共空间,沉浸在中国风舞台布景中女性的视觉经验被充分调动,女性观者则在注视女演员异域服饰与中国风舞台布景时,形成一种全新的集体视觉经验,经由强烈的视觉刺激想象中国女性的情感经验和生活场景,体验他者文化的在场性。中国风在欧洲各地形成不同的视觉风格和表达方式,其中意大利将中国风格融入到本土狂欢的审美习俗中。作为一种民间娱乐形式,狂欢节将广泛的社会阶级卷入其中,松动了既有的观看秩序。中国风不再作为宫廷贵族所专属的视觉经验,各个阶层女性通过穿着长袍具身地参与到中国风化妆舞会中,甚至下层阶级女性也能通过公共娱乐的形式接触意大利宫廷的中国风审美趣味,在效仿贵族审美趣味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这一时期翻译和出版的中国图像文本为意大利狂欢节提供视觉依据,女性运用中国传统服饰和皇室使用的华盖道具充分参与其中,想象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感受,意大利女性在广泛的参与中塑造各个阶级个体间的情感认同。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通的过程中,中欧女性审美习俗和情感经验得以共享,逐渐生成了女性群体间自发的审美认同。中国传统视觉形象成为超越阶级、民族和文化隔阂的视觉表达,最终塑造了基于情感与审美认同的女性视觉共同体。
二、中国风的流行与女性视觉共同体的形成
17世纪前,中国物品数量稀少且仅供少数宫廷贵族所有,无法形成大众化的审美风尚[21]48。基于异质的审美习俗和审美观念,中国传统视觉表达不可避免地发生审美变形。早期意大利的仿制实践主要在陶器中得以体现,其以玻璃和陶器模仿中国瓷器的材料,吸收和挪用中国经典视觉纹饰。但这一时期的仿制实践主要满足公爵阶层的审美需求,只能被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23]21-23。随着大量中国商品涌入,欧洲逐渐形成追求中国物品和艺术的大规模审美风尚,各个阶层消费者产生对仿制品的需求,模仿中国物品与视觉元素的风潮出现。中国风在法国得到皇家认可并融入本土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中,“这些物品在融入法国环境时才受到欣赏,在原始的中国材料、图案等主题中添加奇异的趣味,这正是异国情调的定义”[24]160。相比欧洲其他国家,法国钟情于在中国外销器皿上镶嵌金属附件,中国传统器具在法国审美习俗与审美趣味的影响下器型发生改变[25]43-54。贵族阶级女性热衷追求价格昂贵的新奇物品,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审美品味,为迎合其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出现了大量香薰、化妆盒和粉盒等女性专用器皿。在中国器物与欧洲本土材质的有机结合中,中国传统媒介外观和视觉形象逐渐去地域化、脱语境化,现藏法国赛弗勒国家艺术瓷器馆的香薰由中国德化窑瓷器改装,法国工匠将两杯上下扣合,顶部、底部和中间镶嵌青铜附件,杯底和杯口分别装饰莨苕叶和镂空花叶[26]129。器物开始适应欧洲女性的视觉习惯与审美经验,颠覆和改造了中国器物原本的实用功能,一种全新的视觉外观和视觉形象诞生。
政权更迭为宫廷审美趣味流变提供契机, 原本男性化的巴洛克风格被女性化的洛可可风格所替代, 中国风的传入为洛可可审美风格的形成提供重要视觉元素。 宫廷女性以个人审美偏好引导所处时代的艺术风格, 法国洛可可流行风尚一定程度上由蓬帕杜夫人的个人的审美趣味所引导, 作家兼艺术评论家龚古尔兄弟将其称之为“洛可可之皇后和倡导者”[27]41。 为迎合女性受众的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中国外销瓷器不再只出口青花瓷, 肇始于康熙时期的五彩和粉彩瓷器开始涌入欧洲[28]46, 中国瓷器清丽的色彩满足皇室女性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想象。 孔雀绿釉瓷器带给女性愉悦的视觉体验,为蓬帕杜夫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等欧洲宫廷女性喜爱和收藏(4)蓬帕杜夫人钟爱中国青瓷和孔雀绿釉瓷器,据统计其共收藏青瓷74件,占总收藏数量的三分之一。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同样喜爱孔雀绿釉瓷器,她收藏的孔雀绿瓷器套件现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参见上海博物馆编译:《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色彩丰富的中国瓷器重塑了欧洲女性的视觉经验,推动了法国本土彩色软瓷的生产。法国赛弗勒瓷器厂为迎合女性大主顾的审美趣味,创作具有新奇趣味艺术品,在效仿中国瓷器的色彩的过程中,将本土典型的洛可可视觉风格融入其中。与巴洛克风格强调庄严宏伟的黑色、锰紫色与铁红色不同,洛可可风格通常运用剔透的深蓝色、浓郁的绿色、明快的天蓝色与柔和的浅黄色表达,轻快明亮的色彩体现女性独特的审美旨趣,其中“蓬帕杜玫瑰”是贵族女性个人视觉经验和审美趣味的重要表征,胭脂玫瑰粉色软瓷显现出娇美、柔弱的女性特质。
在与中国审美风格的交流和碰撞中,一种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全新风格出现,中国原本的审美意义逐渐变化,最终呈现出奇异、新颖甚至怪诞的美学特征。这种全新的美学风格集中表现在本土羊毛壁挂中,由于尺寸较大,挂毯能更清楚地展现中国风绘画的细节。为投合女性赞助者和消费者的审美想象,具有女性特质的视觉元素在中国挂毯中反复出现。画面中鸟类以纤细的羽毛与轻盈的体态为特征,装饰于宫殿周围两侧。宫廷服饰则通常采用粉色、淡绿色与浅黄色等与真实中国服饰无关的色彩,阳伞旨在烘托中国宫廷女性闲适的生活方式和愉悦的内心情感[29]108-111。视觉表征中阴性特质的建构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维度相关,中国风视觉图像作为他者反映自我的镜像,折射出欧洲眼中中国形象的变迁,欧洲对中国图像的视觉表征透视着自身的价值判断。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权威视觉形象逐渐去合法化,洛可可中国风艺术形象受其影响,将早期合法的中国视觉图像作加改造,试图塑造女性化的、没有威胁的中国形象。
洛可可中国风旨在建构殊异的中国女性形象的视觉表征,女性形象的改变与不同地域的审美理念和创作方法有关。欧洲传统绘画中隐含“看”的政治,传统艺术与美学预设了男性为绘画观者的标准,而女性身体则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性别思维在隐秘的层面上运作,埃德蒙·伯克视女性身体曲线为审美理想的论述是欧洲传统美学的微观缩影。在根植于欧洲传统审美理念的中国风绘画创作中,女性形象刻画呈现出与中国相异的审美旨趣,画中女性袒露的服装和奔放的姿态与中国女性的实际形象相差甚远。从创作方法来看,中国风画家挪用和转化了中国传统的美人图,布歇“不仅吸收欧洲出版的插图书籍,其创作显然直接受到中国木刻版画的影响”[30]599。其充分借鉴中国宫廷画家焦秉贞的美人画,焦秉贞的绘画受西洋再现技法的影响,通常借用线性透视的视觉语言来描绘视觉场景,但由于中国传统的水墨工具和工笔画技法更适用于“写意”的视觉表达模式,焦秉贞的绘画通常展现女性的情绪和情感。布歇沿袭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绘画传统,以素描和油画技法来重新改造中国风壁挂的图案样本,表现以丰满的肉感为视觉特征的中国女性身体。其中油画作为光影与色彩的技术,要求表现审美对象的面部的立体轮廓。画面中抽象的东方元素与具象的西方细节结合,中国女性的头部主要表现为卷发或宝塔形的帽子,马德琳·嘉丽(Madeline Jarry)指出壁挂中“欧洲女性形象与亚洲人毫无相似之处”[31]21。在跨域审美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中, 殊异性视觉元素丰富了原本中国女性视觉形象的单一形态, 形成具有审美差异的视觉空间, 诸多异质性视觉元素的参与, 为存有差异的视觉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可能。
伴随洛可可审美趣味对私人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强调,欧洲室内的宏大装饰逐渐演变为个人室内装饰。女性消费者的参与,冲击了欧洲社会中男性主导下的禁欲观念和伦理观念,原本由男性主导恢宏大气、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巴洛克风格转变为轻松愉快的洛可可风格,注重以日常生活美学为主的家庭室内的小装饰品出现,通常呈现为精致小巧的视觉外观。中国物品由展示优雅品味转变为个人生活的舒适体验,正如阿苏利所言,良好的审美品味从公共领域逐步进入私人领域,“它的存在不再是为了宫廷人士提供一个展示技艺的场地,而是为了展现符合一种生活方式的属性并提供审美的享受。”[32]47中国风仿制物品数量的增加与价格的下降,使曾经的奢侈品逐渐为中产阶级所观看和享用,成为与女性相关的室内装饰风格,“奢侈成为家内事务,女人们开始在家庭范围内对它发挥影响”[33]131。中产阶级女性的审美选择彰显了与传统贵族截然不同的物质文化品味,浸透着自身独特的审美判断与内心情感。与主张禁欲主义和工作伦理的中产阶级男性不同,女性引导一种以感官愉悦为主的消费方式和生活理念,她们关注异域物品中视觉上的多样性和由此获得的审美愉悦感。
中产阶级女性特殊的审美需求深刻影响了欧洲中国风仿制实践,多元化、个性化和现代化的中国风物品诞生。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重新开始崇尚古典主义审美趣味,英国的设计风格开始表现出新古典主义与中式元素叠合的特殊审美趣味,逐渐偏离色彩明丽的装饰风格,为更简约的审美趣味替代[21]220-222。这种简约的视觉风格符合中产阶级女性独特的审美诉求,她们“所需要的奢侈品与过度奢华无关,它们是知识、便捷性和个人选择能力的体现”[34]267。英国瓷器在模仿荷兰代夫特瓷器和中国陶器的同时,结合希腊文物的审美风格,形成清新淡雅的审美趣味。骨质瓷和奶油色陶器突破了原有中国风风格的藩篱,其中韦奇伍德设计的奶油色的陶器被称为“女王的器物”,其洁白的视觉外观与中产阶级女性的趣味吻合。由东方漆器改造的女士书桌、梳妆台和奇彭代尔家具,作为文明与文雅的文化空间,成为受中产阶级女性喜爱的现代化家具[34]2-3。中国风作为一种流动的审美趣味,基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中呈现出完全相异的视觉风格,在物品参与和融入当地视觉经验与审美习俗的过程中,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得以实现。
中产阶级女性作为中国风审美观念的具身实践者,结合自身的视觉习惯和审美趣味,在私人领域中对中国风视觉元素进行重新诠释和改造,良好的审美品味通过家庭内部装饰得以诠释和展示。她们在房间布置时通常考虑房屋整体的视觉风格,以新古典主义为内核的亚当风格为女性家庭设计提供灵感,这一风格强调轻盈的质感,亚洲亚麻和棉花制品的视觉图案丰富了亚当风格的视觉内涵,被充分运用到壁纸的设计中[34]291-292。传统中国壁纸的视觉元素通常由花卉与动物构成,审美意义根植于本土历史与文化中,喙中衔珠的鹦鹉在中国文化与审美语境中代表观音的伴鸟,鹤在中国被视为仙禽,与长寿的审美意涵相关,通常配以八卦图传递道家复杂的宇宙观信息。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审美元素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动,各种中国自然鸟类均演变为单一的热带鸟造像,被古典主义所吸收和挪用[10]192。生命之鸟、生命之树和生命之花等视觉图像,其“设计灵感借鉴于17世纪中叶进口到英国的印度棉布”[35]121。中产阶级女性不仅基于自身审美判断和感觉经验布置房间,还通过剪切和粘贴印度风格墙纸或印刷品的方式重新排列视觉元素[36]128-131,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欧洲古典美学的连贯性要求,她们的审美实践注入对中国审美趣味的情感和想象,丰富和拓展了中国风视觉经验的表征方式。
中国风物品经由上行下效的流行机制从贵族迁转至中产阶级,在标准化生产的推动下,甚至传播至社会底层阶级[34]145-150。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与纸张价格的下降,商家开始以想象中的中国场景与中国人物作为广告图像,兜售异国情调想象[12]169-172,各个阶级的女性消费者在看广告时将奇异中国形象整合到自身的情感结构中。齐美尔认为时尚潮流背后隐含性因素,基于女性心理需求中的模仿性和竞争性因素,在上层阶级达成新奇性和独特性的追求后,下层阶级开始效仿相同的风格。女仆、交际花和女工等与上流阶层与奢侈物品密切接触的群体最先成为欲求主体[37]22。18世纪末,亚洲奢侈品中印度棉布和瓷器被大规模进口和仿制,根据女性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形成多样化和个性化审美风格,相对廉价的白棉布服饰呈现多层活褶的审美外观,与上流阶级钟爱的丝绸服饰相似[34]52。不同材质和品质的中国风物品迎合不同社会等级的女性消费群体的审美需求,相比价格昂贵的彩色釉瓷,社会底层的欧洲女性倾向于购买更便宜的青花瓷,因为通常价格低廉的瓷胎和着色较为粗糙。中国风物品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空间,消费主义的兴起为原本被排除在视觉共同体之外的女性群体提供观看机会,重新配置可见与不可见性。虽然不同质地的商品带给女性差异化审美感知,但不同阶层的欧洲女性仍然借由中国风物质媒介分享可共通的视觉经验,据此形成朗西埃意义上容纳差异的“歧感”共同体。
三、“女托邦”与她们的审美观念
中欧长期以来处于相互隔绝的地理位置,彼此局限于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各个国家和民族间依赖自身特有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通过共通的文化符号和观念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趣味和情感结构。欧洲自身具备一套评判和鉴赏艺术的标准,而中国以承载民族文化和审美情感的物品为依托将差异化审美理念传播至欧洲,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洲本土视觉经验和审美风格。女性视觉图像作为中国艺术主题之一,透视出中国深层的审美理念与女性真实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情感。相比欧洲根植于古希腊的再现审美观念,中国将“气韵生动”和“传神”视为终极审美追求,女性人物服饰飘逸的腰带和生动的皱褶显现出内在的气息和节律。中国传统绘画中通常不表现孤立的女性人物,在中国语境中“人的形象是贫乏的,必须强加给他形式……人总不被单独放置”[38]78。女性与其他诸多视觉元素包括男性和孩童角色、庭院和花园以及叙事情节共存和互动,构成整体的视觉表达。在物品域外流通的过程中,生动的中国女性人物刻画吸引欧洲女性群体。
中国传统艺术通常以美人画和仕女画概括整个女性题材绘画,正如巫鸿所言,这种方式“以相对狭隘的画科观念置换了女性题材绘画的多维和复杂”[39]3。宽泛的指认遮蔽了绘画内部的差异和女性复杂的情感表现。中国瓷器承载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的情感记忆与审美理想,其丰富的视觉表征不仅涵盖世俗世界中不同阶层和地域的女性形象,还容纳理想世界中神话与虚构艺术中女性形象的表达,折射出复杂的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相比强调女性道德教化的母婴图、表现底层女性的耕织图和被欧洲称作“伊美莎斯”的纤弱女性图像[40]165-168,138,145,突破传统性别身份陈规与表达女性人物情感和欲望的视觉图像,投合了欧洲女性的审美情趣,为她们消费、传播和观看。在戏剧和小说插图的影响下,明代以降的女性视觉形象开始革新,挣脱儒家的道德规范和男性的审美标准,从政治、道德象征和视觉观赏的对象转化为审美和欲望主体,呈现全新审美旨趣。明代女性人物画跳出传统仕女图和美人画的经典程式,作为强调情感和欲望的历史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提供女性人物自主表达感情的契机,衍生于小说和戏剧的全新绘画创作出理想的女性形象。明代商业化社会的兴起为女性接受教育提供了机会,江南地区女性首次以读者的身份出现,这一时期“受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她们互相影响与社会相互间作用的机会充分增多,创造了一个过去不曾存在的阅读批评群体”[41]31。伴随儒家秩序中二元等级制度界限的模糊和松动,江南文化圈的精英阶级女性借助儒家男权秩序裂隙,开始跻身于原本专属男性精英的生存空间,基于阅读与批评形成亲密的女性共同体。女性读者大量涉猎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关涉爱、激情和浪漫的文类吸引闺阁中的女性,女性阅读批评群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催生迎合女性审美趣味的文本,浪漫爱情故事所设想的男女平等理想以及承载这一理想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传统戏剧和小说中被遮蔽的女性角色得以凸显。符合女性的审美旨趣的世俗化和感官化的情感出现,情感作为一个重塑的概念,其表达普遍哲学式和抽象化的情感审美维度逐渐淡化,开始与婚姻、恋爱等具体经验相关的情感范畴相关。小说和戏剧插图中的女性图像通过木刻版技术大量复制,工匠将其挪用至瓷器表面后,更广泛的女性群体采用直接观看图画的方式欣赏为女性而创立的题材。
作为符合女性情感诉求的视觉表达,展现戏剧和小说中爱情题材的瓷器受到欧洲女性的青睐,相比男性化的政治和军事题材,表达爱情的主题隐含着女性的观看位置。中国戏剧最早借由物质媒介传播,柯玫瑰(Rose Kerr)指出“在康熙时期,许多剧本的版画插图被仿制到瓷器上,《西厢记》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题材。”[40]59早在明代嘉靖年间,绘制西厢题材场景的瓷器即已出现,主要以当时的木刻版画为原型创作,这一题材于康熙时期达到数量和种类的巅峰,借由青花、五彩与粉彩瓷器反复演绎,并为荷兰代夫特瓷器大量仿制。[26]269部分瓷器采用连环画的方式以故事为线索从上到下展开布局,将完整的戏剧内容浓缩在器物表面,戏剧的情感张力和瓷器的曲形表面引导女性反复转动瓷器观看,另外一些瓷器图像侧重表现局部的视觉场景。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着重描绘女性尊贵与威严的形象,戏剧插图作为低级审美趣味与高雅的文人画形成分野,旨在通过描绘香艳的氛围,激发女性观者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欧洲女性以沉浸式的观看方式参与到戏剧故事中,而非凝神静观式的赏析。视觉图像中的女性均位于画面中心位置,她们的内心活动与情感欲望构成了内在的女性视角,欧洲女性观者在观看过程中开始关注自身的情感和欲望。
中国瓷器与室内陈设和布置密切相关,女性长期以来被认为缺乏鉴赏高雅艺术的知识,并被排挤在主流视觉经验之外。布尔迪厄认为,“艺术作品只对掌握一种编码的人产生意义并引起他的兴趣,艺术作品是按照这种编码被编码的”[42]3。相比抽象的植物花卉图案,直白的人物形象与生动的叙事情节更能引起女性的兴趣,来自小说和戏剧插图的爱情图像通常透露出含蓄的色情意味。这些图像与欧洲古典主义美学范式中抽离感性人物身体的裸体形象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旨趣,相比欧洲将美抽象为一种纯粹的审美理念,中国倾向于在具体经验层面中呈现美,图像中的色情描写通常与真实可感的生活场景相连。中国的色情意涵主要通过更为隐晦的方式呈现,高居翰指出侵入女性私人空间是中国表现色情的重要维度[43]245。各国博物馆提供大量可视化证据,表明女性图像中关于墙头、窗户和内室的描绘。表现局部视觉场景的西厢瓷器通常展示张生跳墙和男女主角私会的色情图像(5)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收藏多件清代西厢瓷器,其中一件瓷器展现戏曲《西厢记》中的高潮片段,描绘男女主人公在内室中的色情场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有描绘“隔墙吟联”“红娘请宴”“月下佳期”“回音喜慰”四幅场景的中国外销碗类瓷器,展现男女主角的内心欲望。此外,中国首都博物馆藏有二十余件西厢故事清朝外销瓷器,表现张生跳墙和男女主角私会的情景。参见柯玫瑰:《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院馆藏清代瓷器》,秦蘅译,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上海博物馆编译.《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184页;胡雁溪,曹俭:《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231页。,外销欧洲的康熙五彩《牡丹亭》人物图盘,取自杜丽娘与梦中创造的男性欲望客体的亲密画面[40]138。在挪用木版画视觉图像的过程中,工匠将图像改造得更富感官与欲望意味,男女主人公私密化身体接触的视觉场景富有挑逗性。与古典哲学和美学中纯粹愉悦的审美观念不同,欧洲艺术充斥大量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与欲望投射为指归的女性裸体描写。欧洲女性群体私下相互传阅和观看色情图像相比欧洲直露的身体描摹,隐晦的色情表达更能满足这一时期欧洲女性相对保守的审美观念。
这些高度理想化的审美形象为女性读者接受,表达了中国女性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深层情感与欲望,与真实的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差异,欧洲女性对遥远的中国投注浪漫化想象,在观看图像的过程中,重新编织了自身的视觉经验。视觉图像中的审美理想影响了欧洲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视觉经验形塑并构建了女性的自我形象,理想和想象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的公共话语中。一种以女性为主的审美想象空间,即“女托邦”[44]159形成,通过公共的、集体的观看经验,形成超越时间、空间和世俗藩篱的女性共同体,女性主体自身创造了一种基于文学艺术纽带的亲密关系。英国和法国女性试图扩展和重新配置古典乌托邦模式,视爱情小说为男性权力之外的自由领域,重新思考和怀疑男权话语体系和男性审美观念对女性特质的定义,“女性被赋予的仁慈、持家、性感、多愁善感与善于交际等特质,在文本中得以强化、挑战和改写”[45]2。欧洲女性开始探索基于自身情感和身体欲望的独特文学作品,出现了摆脱男性话语陈规的审美表意实践。
欧洲男性作者通常将女性视为自身欲望投注的客体,忽视和否定女性主体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在欧洲早期现代写作中,数量可观的女性视角文本开始聚焦于女性之间的友谊和情感,男性不在场的“女托邦”空间形成。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致力于论证中国物品与女性文学空间的关系,认为上流阶层女性同时作为早期中国奢侈品的观看群体和浪漫主义小说阅读群体,两者基于共有的审美风格形成“共鸣”空间,阅读和观看的经验得以相互强化[46]58-68。这一视角为欧洲女性作家群体的审美实践提供一个可能性阐释向度,直接的视觉经验为欧洲女性主体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图像中含蓄的色情表达为女作家表达女性友谊和情感作品提供灵感,由于女性之间亲密和色情的主题存在限制,17世纪晚期欧洲女作家群体的诗歌通常采用隐晦的色情表达。异域情调也为英国女作家提供了可行的表达空间,东方作为欧洲为自身建构的他者形象,被视为性幻想的场所,中国瓷器中的色情意象印证和强化了中国物品和感官享乐的关联。欧洲女作家将被禁止欲望和审美理想投射到异域空间和东方人物中,为作家的审美创作和审美想象提供了可能。“女托邦”关乎女性的真实的感觉、情感和欲望,是一种介于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女性审美共同体。中国图像中相对封闭的女性闺阁空间不仅为文学文本中的欧洲女性欲望表达创设情境,现实中以教育和养老为导向的“女托邦”社区也据此生成。
四、结 语
中国风在中外审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推动着一种以女性经验及意义生产为主导的视觉共同体的形成,其溢出传统西方美学的性别陈规与男性视角凝视,孕育着粘连女性生活趣味与情感倾向的女托邦审美空间。相比男性对纯正的、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捍卫,女性的审美趣味以更加宽容的姿态,吸收、借鉴和再创造中国的视觉图像,在不同审美经验的交融中,欧洲视觉图像的审美意义不断增值与再生产。从女性视角观测中国风的生产流变,推动了异质性视觉经验的形成,同时颠覆了传统男性主导的审美空间,进而打破了审美经验内部的均质与统一化趋向,最终以“女托邦”的形态构筑一种全新的视觉共同体。因为想象具有公共效力,可以“为行动者与旁观者创造相遇的空间,从根本上说,也是伦理个体自我塑形的空间”[47]38。作为美学意义上的共同体,从不同个体深层的感性基底形成审美认同和情感共鸣,以共享共通的视觉经验,超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隔阂,在原有政治、文化和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