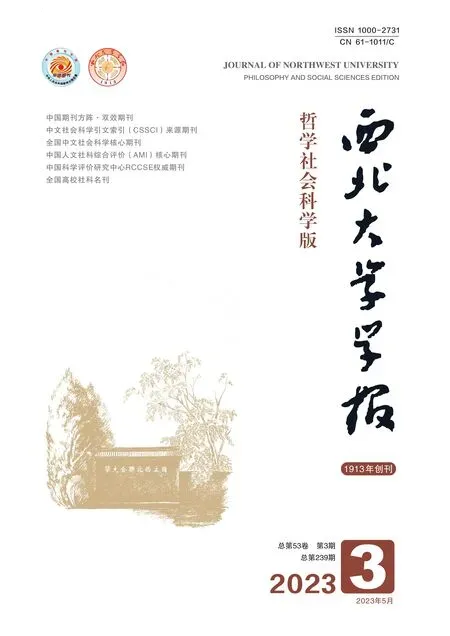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
2023-08-26王雨萧
王雨萧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纵观历史,庄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人,他能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1]962,其境界之高,常人很难企及。而在生死的问题上,庄子也有着死生一体、安死顺生、以死为乐等超凡脱俗的观念。本文将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对《庄子》(1)本文着重从整体上研究庄子学派的生死观,所言庄子皆指代《庄子》一书。除特殊说明,所引《庄子》原文皆依据[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生死观的“变”与“不变”进行剖析。
一、庄子哲学中生死变化的理论依据
分析庄子哲学中的生死问题,首先要从庄子哲学中生死变化的理论依据谈起。在庄子思想中,“生”与“死”的产生及变化源于“道”与“气”的作用。但是这两者对于生死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又有所区别。其中,“道”之得失是导致生死的根本原因,而“气”之聚散是生死变化的直接原因和实质体现。“道”使世间出现生与死,“气”使世间产生生死之变化。
(一)道: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庄子对于生死的论述与“道”是分不开的,很多学者指出“他更注重从道的立场考察人的死亡问题”[2],“庄子的生死哲学只是浅表层次,庄子是通过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来揭示‘道’的本质、作用以及世界万物的产生”[3]。“道”作为道家的最高范畴,以往的学者对其多有研究。《庄子》一书对于“道”最经典的论述见于《庄子·大宗师》: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1]225
道是万物存在之本源和根本:它真实存在,无虚无妄,但无形状大小;可以直观感知,而难以用言语把握;它是万物之根本,但它本身则以自身为根本。同时,它的存在,空间上遍在,时间上无限。根据这种描述,道往往被视作与西方哲学中“实体”相当的一个概念,中国学者因此多以“实体”(又译为“本体”)来称呼道。不过,中国哲学的思考路径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实体性、本质主义思维,因此,以“实体”或“本体”来反向格义中国哲学中的道,显然是行不通的。
就中国哲学语境来说,道作为万物之本源和本根,虽然具有与“实体”相似的特性,但从根本上来说,道并非实体,而是指称万物之生化,所谓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之过程,这样的道也被称为“造化”或“造化者”,《庄子·大宗师》言子来将死,子梨往问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1]238子来则以大冶喻造化,言:“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1]239“造化”即造而化之,正是指万物之生化而言。由于人亦处于生化发展之中,而化之所向对于人来说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才会出现“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的疑问。不过,庄子以大冶喻造化,又以“造化者”称之,这种拟人化的修辞一方面易于揭示万物在生化过程的被动性、“被抛性”,另一方面却极易导致歧义,以为造化或者道就如同上帝一般的造物者,从而导向对道的“实体”化理解。同样,庄子亦以“生生者”指称道,“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1]231。作为杀生、生生之作用的道本身是不死不生的,有生有死者只有具体事物,庄子所谓:“道无终始,物有死生”[1]520。然而,道亦只是“生生”,即生化流行之过程,以“生生者”指称“道”,只是为了从言语上指称道之生化作用,而非将道看作一个上帝般的实体。这一点也体现在庄子所言之“物物者非物”[1]672中,“物物者”显指道而言,但由于“物物而不物于物”[1]593,所以物物者又非物,即不是实体之存在者。虽然物物者(道)不是实体,但“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1]662。就是说,道非物,但又不离于物,道物之际,乃没有分际的分际,我们以“即物而非物”称之。但道如何能即物而非物呢?究其实,道即万物之生化,道的生化作用就体现在万物生化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才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1]909作为万物之所由的道不是别的,就是万物之生化本身,所由者生化而已。由于一切万物皆处于生化发展之中,故道“即一切物而非一切物”,为万物之本源本根。对道的一切不可道之道,皆落实到对生化的讨论上来,而生死则是生化之一环。
在道家哲学中,生死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之生死指有机生命体的存活和死亡。而从广义上讲,由于一切万物皆处于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事物皆有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因此,生死往往指代一切万物之存在和消亡,也即《庄子·齐物论》所言之成与毁,体现出道家的大生命视野。无论是狭义上有机生命体之生死存亡还是广义上万物之生成与毁灭,皆为万物生化的环节之一,因此都属于大化流行。生死之化一方面体现出道,是道之存在的显现,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道对于生死之化的作用。从生死之化体现出道而言,生死之化乃物理之自然,有生必有死。从道对于生死之化的作用而言,道为杀生者、生生者,似乎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1]909。但实际上,道对于万物之作用乃无作用之作用,即“自然”,也就是老子所言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失道和逆道之所以会导向灭亡和失败,乃是由于其自身失去生化之理,违背生化自然之态势。得道、顺道亦并非得到外在于自身的道的神秘作用,而是事物自身之发展合乎生化自然之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为生死之根本。
(二)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道作为万物之生化过程进一步落实为气化流行。生死就体现在气化流行的聚与散之中。因此气之聚散是万物生死变化的直接原因和实质体现。
中国哲学中的“气”具有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所言质料的意义,是构成万物的最基本成分,或言始基。不过“气”在这里并不能仅仅从唯物主义所言之物质的角度予以理解。毋宁说,“气”本身兼具物质与精神的含义。这一点在《庄子》中有鲜明的体现,如《庄子·逍遥游》中之“云气”、《庄子·齐物论》中之“噫气”、《庄子·至乐》中之“形气”等皆具有自然界物质之气的含义。而《庄子·在宥》中之“血气”、《庄子·天地》中之“神气”、《庄子·刻意》中之“邪气”、《庄子·盗跖》中之“志气”等皆具有精神之气的含义。在《庄子》中,正是由于气兼具物质与精神的含义,所以才能既构成物质事物,又构成精神存在,而成为万物生化之始基、质料。
道气关系实际上即气化流行之过程与流行之气的关系。气之流行体现为道,单纯言气则只见概念上的气,道则无处显现。从根本上说,原本就不存在静态的、不动的气。气总是处于运化之中,故有气之运化流行,则有道之显现。气有聚散、隐显之不同存在状态,而道一皆统之,此即“道通为一”[1]68之义。进一步来说,“道通为一”并非仅停留在抽象的思辨之中,而是体现在“通天下一气”的存在论命题中。《庄子·知北游》通过对生死变化的讨论具体阐释了这一命题: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1]647
庄子认为,人之生,实则为气之聚而有形的状态,死则为气之散而无形的状态。无论生还是死,无论神奇还是臭腐,从根本上看,皆为气之存在。“道通为一”是从形式上来说,万物皆处于生化之中,不离生化,但具体落实为质料上的“通天下一气”,这就从气的角度将万物之生死皆归于气之聚散。
讨论生死总是涉及具体某物之生死,生总是“我”的生,死总是“我”的死。人们因此执着于生死,把生死看成属于一己之“我”的生死。然而庄子同样从气化流行出发,否定了这种“生死我属”的常识,认为生死并非是某一人(物)之生死,而是属于自然大化,其言: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1]652
《庄子·知北游》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委”。对于“委”字,司马彪称:“委,积也。”郭象、成玄英亦解“委”为积聚。俞樾对此提出反驳:“司马云,‘委,积也。’于义未合。《国策·齐策》:‘愿委之于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传》:‘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属也。’天地之委形,谓天地所付属之形也。”[1]736俞樾之说为确。“委”即托付、寄托之义。身体之形成并不在我而在天地,是天地寄托于我的结果,它仍然归属天地;生命和性命之所存亦不在我而在天地,是天地和顺之气托付于我的结果。成玄英疏:“委,结聚也。夫天地阴阳,结聚刚柔和顺之气,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死生聚散,皆不由汝,是知汝身岂汝有邪?”[1]736其将“委”解为“结聚”虽与此语境不合,但他正确地看到气之聚散形成“我”之身形性命。这一事实决定了“我”之“身形性命”乃大化流行的结果,非“我”所能决定。既然非“我”所能决定,那么身形性命,生死都不能说是属于我的。由此,生命之于我不再具有本己性,生也就没有执著的必要,而死也不再是神秘和可怖的现象,生死皆为大化流行中的自然现象。这一“气化生死”论构成了庄子讨论“生死之变”与“死生无变”的理论基础。
二、庄子哲学中的“生死之变”
《庄子》一书对于生死之变有许多讨论,本节主要从“死生往复”与“死生自然”两个方面予以展开。
(一)死生往复:相反无端,莫知其穷
庄子对生死的讨论不仅在于认为生死变化是通达而顺畅的,其别具一格之处主要在于生死相反无端、往复无穷的观念。《庄子·田子方》借老子之口称:“生有所乎萌, 死有所乎归, 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1]630《庄子·寓言》称: “万物皆种也, 以不同形相禅, 始卒若环, 莫得其伦, 是谓天均。 天均者天倪也。”[1]833万物都像种子一样, 产生于它之前的一物, 再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变为另一物, 其生死变化, 就像沿着圆环而行, 无法察窥其始与终的边际。 庄子将万物这样的变化状态比喻为“天均”或“天倪”。
庄子也将死生存亡等变化比作昼夜交替:
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1]625
庄子以“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来说明万物生死存亡的状态,万物的死生之变化就如同日出日落,人必须顺遂自然之变化而“日徂”,这才是“知命”后的明智做法。又如“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1]195、“死生为昼夜”[1]548、“死生终始将为昼夜”[1]631,都阐明了死生就像昼夜交替,人无法窥探其始终。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使自己在万千世界的变化中保持安然平和之态。
究其原因,这种死生往复的存在方式乃气化流行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无端的性质:“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1]562。宣颖称:“二气合,则生物形;散于此者,为生于彼之始。”[4]130散于此而生于彼,气的变化本身是相反无端,没有穷尽的,生死亦然。
(二)死生自然:善吾生者,善吾死也
庄子对于人生愁苦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愁苦这种状态是伴随着人的出生而产生的,《至乐》篇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1]541这种对生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庄子对死的看法,正是因为庄子意识到了生命的愁苦和短暂,因而多论及死。在谈到生死问题时,《大宗师》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221
庄子认为造化赋予个体生命其实是“劳我以生”,这种表述与“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表述是一致的,表明庄子认为辛劳与愁苦是人生的本然之貌。“佚”通“逸”,《广雅》称:“佚乐也。”在通向死亡的生命过程中,庄子认为由年轻变老是一个逐渐轻松、逐渐安逸的过程。而在生命终结之时,个体顺遂自然变化而死则是一种休息。从“息我以死”能够看出,庄子认为死就同“寐”一样,只是自我的休息。这里的“息”与之前的“劳”和“佚”相比可以说是一种更本真的状态。“劳”则不免被外界所影响,无法真正为自我而活;“佚”虽然使人逐渐轻松,但仍受限于外界,不免活在压力之下;“息”在这里反而是一种自我独成一体的状态。庄子对于造化使人死亡这种作用没有一点点怨恨和不满,反而认为这是一种“善”。如果说生是造化给予的一种善和“大德”,那么死同样体现了造化之善(生劳死息)。造化一方面“善吾生”,另一方面又“善吾死”,“吾”只需要顺遂自然的变化就可以了,生与死皆为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死亡与其他千变万化的现象一样,皆为自然现象,“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1]415;“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1]962等都体现了庄子哲学中生死的自然性。正是这种自然性消解了死亡的神秘性,此诚如杨国荣所言:“通过把死还原为一种自然现象,庄子也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死的神秘性。”[5]210
“自然的”同时意味着普遍的、必然的、绝对的。“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1]658天地间变化出生命,由生命又变化出死亡。万物在生之时都展现出勃勃生机,在死之时也都顺遂变化而死,无一例外。因此,庄子认为不能强求那些在变化中已消失的东西,庄子用“求马于唐肆”[1]627的比喻指出,强求那些在变化中消失的东西就像在空荡荡的商铺中想要买马,是不可取的。
三、庄子哲学中的“死生无变”
生死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但在《庄子》一书中,又存在很多论述死生同一的文本,最直观的表述见于《庄子·德充符》“以死生为一条”[1]189、《庄子·天地》“万物一府,死生同状”[1]368及《庄子·齐物论》“死生无变于己”[1]91等。本节主要考察庄子“死生同一”的理论认识和“死生无变”的生命态度。
(一)死生同一: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死生同”不是抹杀生死差异的简单等同,在庄子哲学中,生死的同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存在论的层面,二者皆为大化流行之一环。二是在存在者层面,二者共同组成具体事物存在之整体。这两个层面都是对庄子“齐物论”的展开。
从存在论的层面来说,生与死表现为气化流行过程中聚与散、显与隐。不仅如此,事物之生死和其它存在特征如大小、美丑等皆为一气流行之不同显现。因此,如果“以道观之”,也就是从大化流行的视角看待万物之差异,那么这些差异便都在道的视域下被泯除。《庄子·齐物论》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1]68
大小、美丑,固然与事物存在本身相关,却也与人之主观感受相关,特别是当人们以一己之主观意见为准来判别事物之存在时,必然产生可不可、然不然等是非之分。不唯如是,如果人们执著于事物外在之存在形式,一旦事物出现变化时,必然产生成与毁,也即广义之生死的执见。在庄子看来,这些执见不仅导致是非之分,产生儒墨之争,更重要的是,人们执着于己见,使内心终不得平静,不得逍遥。庄子正是有见于此,才断然放弃了以这种常俗之见“观物”的视角,而从道的层面观之。所谓“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就指明了常俗之见不堪用,而只能寓诸事物之“庸”,而“庸”非平常之用,它指向的是存在论层面的“通”。“道通为一”正是从存在论层面将生与死打通起来而无隔碍。“道通为一”更具体地落实在“气通为一”上,这也就是上文所言之“通天下一气耳”。[1]647根据陈少明的说法,庄子“齐物三义”分别为齐“物论”、齐万物、齐物我,而齐物我,“说到底就是能够‘齐生死’”[6]97。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齐“物论”、齐万物最终是为了齐生死,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大化流行的宇宙观。
从存在者的层面看,生死虽异,但俱为事物之一体,是事物完整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庄子将生死比作身体,其言:“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1]235他认为死生本为一体,其中“无”是头颅、“生”是脊骨、“死”是尾骨。《庚桑楚》对这一比喻亦有提及: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为友。是三者虽异,公族也。[1]706
“古之人”是庄子哲学中的理想人格之一,“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的“至”作“至极”解,是说古之人的智慧达到了最高层级,其具体所指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未始有物”表明这种最高层级的智慧没有物我之分,世界浑然一体。既然没有物我之分,就没有主客、人我之对待,没有分别差异。自然也没有生死之分。不过,这种境界并不容易达到,如褚伯秀所言:“禀质为人,既形而下,欲复乎‘未始有物’,不亦难乎?”[7]745这种境界实正是“齐物论”所要证成者。
次一等的境界为“有物矣,将以生为丧也,以死为反也”。这一层级境界已经产生分别,因而有物我、生死之分。但这种境界仍高于常人,成玄英疏:“丧,失也。流俗之人,以生为得,以死为丧。今欲反于迷情,故以生为丧,以其无也;以死为反,反于空寂;虽未尽于至妙,犹齐于死生。”[3]798常人总是乐生恶死,以生为得,以死为丧。但这一境界之人能够与常人拉开距离,以生为丧,以死为反,表现出对生死的超越之见。而这种超越之见正是走向“齐生死”的必要环节。
再次一等的境界认为“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认识到生死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且生命短暂。持该生死观的人,虽然尚不具备最高层级的智慧,甚至也还尚未达到次一等级的智慧,但仍高于常人,是庄子所能够接受的最低限度。“以无有为首,以生为体,以死为尻”之要义在于把生死看作完整生命过程的必不可少的一环。常俗之人乐生恶死,进而产生执生怖死的情绪。而如果能够把生死看成一体,看成万物生化的必要和必然的过程,那么生死就不是截然相分之二物,而是一体之物。“知有无死生之一守”就是知道有无生死一体,这同样是达成“齐物论”的重要步骤。因此,对于这样的人,庄子才“与之为友”,引为同道(2)孙明君在《庄子“畸人”说及其天命观》中将庄子的“死生一体”思想分为生苦死乐、平静面对生死、不知生死三个境界。但这种划分并不妥当。生苦死乐和不知生死侧重对生死的认识,平静面对生死则侧重面对生死的实践方式,它可以是前两种境界之表现而非境界本身。参见孙明君:《庄子“畸人”说及其天命观》,载《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2期。。
庄子不仅通过直接的、肯定式的论断阐释了死生一体的观点,也通过否定和疑问的方式阐释了死生不是对待的:“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体。”[1]672死生不是势不两立的,生不会妨碍死的自然作用,不会使死的东西复生,死也不会妨碍生的自然作用,使生的东西莫名死去。生死本为一体,无所对待。
(二)死生无变:死生虽大,无变于己
按照通常的观点,由生到死的转变是一种从有到无、从存在到不存在的转变,郭象称“人虽日变,然死生之变,变之大者也”[8]104,对于一切有生命的个体而言,死亡是“变之大者”,生命中的一切变化——无论是形体的改变还是境遇的转折,都不会像死亡一样如此剧烈和突然。庄子并不反对这种认识,但他认为,人们只要能转变认识,达到“齐物”之智,以死生为一条,即使如死生这样的巨变也不能影响我们的内在精神,所谓“死生无变于己”[1]91。庄子哲学语境下的至人、真人、圣人和神人之所以有别于常人,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生死的看法与常人不同。
对于真人面对生死的态度,庄子认为“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1]762。成玄英疏:“夫处生而言,即以生为得;若据死而语,便以生为丧。死生既其无定,得失的在谁边?噫,未可知也!是已混死生, 一得丧, 故谓之真人矣。”[3]860站在生之人的角度看, 生为得, 死为失; 然站在死之人的角度看, 则死为得, 生为失。 实际上, 无得无丧, 无生无死。 既然对生死持这样一种观点, 人生其他的变化就更不值得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转折, 因此庄子又称“古之真人, 不知说生,不知恶死”[1]210。“不知说生, 不知恶死”, 说明真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常人之情感, 而这正是至人“死生无变于己”的前提。 这里的“死生无变于己”和《天下》篇所说的“外死生”是一个意思, 如王明称: “所谓‘外死生’, 就是《齐物论》说的‘死生无变于己’, 认为死和生并无利害好坏的分别”[9],段德智称: “把‘外生死’看作体认大道的先决条件”[1]。 至人正因为对于“死生”这个变化之最大者都能够有这般置之度外的心境, 所以对于其他的任何变化都更加无视和坦然,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能够不被外在的利害所伤。
论及圣人,庄子认为圣人眼中的死具有“物化”的特点。对于何为“物化”,《齐物论》称: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106
《刻意》篇说:
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1]480
所谓“物化”即事物处于大化流行过程中的转化。庄周梦为蝴蝶是人与蝶即不同事物之间的转化,而生死则是同一事物不同存在状态之间的转化。在庄子的生死观中,个人存在总是有限的,而道的存在却是无限的。相应地,存在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执于一己之生死属于有限性之存在,而与道相合、顺应自然大化则是超出有限,走向无限之存在。圣人作为与道相合之人,他的生存方式就真切地体现了顺应自然大化,超越有限,走向无限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可谓“死生无变于己”的极致表现。
四、庄子哲学的“养生”与“顺死”
“死生同一”的认识和“死生无变于己”的生命态度落实到生活实践中表现为“养生”和“顺死”的生死观。
(一)养生而不执生
庄子的生死观从根本上说表达了一种“重生”(3)《庄子·让王》载:“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的态度。“养生”“全生”因此是庄子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庄子之养生全生并不刻意追求生命之长生不死,而只是实现“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1]205,使生命达到一种自然长寿的健康和谐状态,这一点体现出道家与神仙家之分殊。因此,庄子对于养生持“养生而不执生”的态度。
庄子为何会有这样一种“养生而不执生”的思想呢?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庄子充分认识到人生的愁苦,认为执着于生本来就是一种错误。《齐物论》说: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1]56
劳碌无成、困苦受累的人生是悲哀的,如果一直过这样的人生,即使长寿也丝毫无益。庄子追求养生是因为能够通过修养的方式使自己努力减少人生愁苦,相反,一味地追求长生不死在庄子看来更添人生之愁苦:“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1]541林希逸称:“惛惛,老而不聪明也”[10]277,这种对不死的追求使人即便活着都充满了忧患和苦恼,恰恰背离了生命的原貌。
第二,庄子对“养神”与“养形”进行了区分,从而阐发“养生而不执生”的态度。对于“养形”和“养形之人”,《庄子·刻意》称:
吹呴呼吸, 吐故纳新, 熊经鸟申, 为寿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 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1]476
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馀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1]560
庄子虽然肯定“养形”是必要的,但是庄子认为“养形之人”和“导引之士”并不值得称颂。正如杨国荣指出:“对《庄子》而言,这种‘道引之士,养形之人’的行为方式与‘刻意尚行’者同属一类,他们仅重外表、有意为之,尚未达到‘天地之道’。”[11]如果只知道“养形”,一味地将养形作为存养生命之方,反而会对生命有所伤害,其原因在于“养形果不足以存生”[1]560。养形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资源为前提,但是物质资源非常丰富最终却没有得以养形的人也不在少数。世人都认为保养形体是保存生命的重要方式,但是实际上“养之弥厚,则死地弥至”[3]630,“厚养其形,弥速其死”[3]630。实际上,与养形相比,庄子更重视养神。在论及“养神之道”时,庄子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1]483“养神”作为重要的体道方式和治身之术,实质是保持内心的纯朴、宁静、恬淡,它已经脱离了对“形”“身”是否死亡的关注,不再追求身体的不朽和寿命的不死,而是能够因循自然,内心虚静,凝守精神。
第三,庄子所持的生死齐一的态度其重要表现就是寿夭齐一。成玄英疏“万物一府,死生同状”[1]368之时就提到了寿夭亦无变于己的观点:“死生无变于己,况穷通寿夭之间乎!”[3]416在庄子看来生与死不仅仅是没有差别的,长寿与短命也没有差别。又如《庄子·知北游》称:“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1]657长寿与短命相差多少呢?其实不过是片刻之间而已。在面对寿夭的情感态度上,庄子也因此而持“不乐寿,不哀夭”[1]368这样一种哀乐不入的情感态度。
(二)顺死而不恶死
当生命中还没有死亡的威胁出现时,庄子主张顺遂自然的造化,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方面不要自取死亡,另一方面也不要苛求长寿。但是当死亡的到来已然迫近之时,庄子主张顺遂自然的造化,直面死亡。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顺死而不恶死”。此“不恶死”不仅仅是指庄子对死亡没有像常人一样的厌恶之情,它还包括了庄子由之而具备的“不哀死”“不畏死”的通达态度。
庄子“顺死而不恶死”的态度首先源于死后状态的未知性。庄子用“丽之姬”的故事抛出了对悦生恶死的质疑:“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1]98吕惠卿称:“以丽姬观之,则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蕲生?又何知生之可悦,死之可恶乎?”[7]69陈碧虚称:“一生之内悲喜莫知,生死之际安可轻议?”[7]70如果生者祈求生,那么死者会不会也祈求死呢?这当然是一种反讽,但他表达的是庄子对于常识之见的反对,即死不值得厌恶。
其次,庄子“顺死而不恶死”的态度还源于他对“生之偶然、死之必然、生死自然”的体认。庄子认为死亡只是自然变化过程的环节之一,是必然事件,无人可以幸免。庄子在《养生主》提到“遁天之刑”与“帝之县解”[1]119的概念也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关于“遁天之刑”,郭象解为:“感物大深,不止于当,遁天者也。将驰骛于忧乐之境,虽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3]134人如果不能明白死亡是天理之必然,这就是“遁天之刑”,妄图逃避天道的刑罚。但是实际上天道之刑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必然的,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1]144,因此“遁天之刑”实际上是愚蠢而无用的做法。与此相反的概念即“帝之县解”,庄子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1]119情感之哀乐变化,源于患得患失之心。如果能够做到安时而处顺,哀乐就不会产生,天地对自我的倒悬也就得以解除。
最后,庄子“顺死而不恶死”的态度根源于他的齐物论思想。庄子将这种齐生死的理论落实到实际态度中,对面临死亡的态度进行重构,主张“不知说生,不知恶死”[1]210,并且主要偏重于对“不知恶死”的强调。庄子多次对死亡进行正面论述的用意也均在于此,都是为了通过正面的甚至具有强烈褒义的描述来阐明“不知恶死”的鲜明态度,而并非是真的以死为乐。这种“不恶死”的态度还反映在其丧葬观中,《庄子·列御寇》称: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齎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1]933
在庄子看来,死本身就是与自然同化,因此葬与不葬并没有什么不同。庄子这种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但这正是庄子在行动上对“死生同一”“死生无变于己”的明证,是庄子对顺遂生死最切己的体认。
五、结 语
本文从“生死之理”“生死之变”“死生无变”“养生顺死”四个方面分析了庄子生死观中的“变”与“不变”。其中,“生死之理”是庄子看待生死问题的理论依据。道作为万物之生化本身,与万物是“即物而非物”的关系,道就体现在万物生化之中,气则是万物生化之始基与质料。生死从根本上说只是气化流行过程中之聚散。这种道气论为庄子论述生死之“变”与“不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变”是从生死的客观存在所作的论述,生与死循环无端,自然而然。“不变”则是庄子根据其“齐物”思想所形成之新的生命认识,以生死一体的认识为基础,才会具有“死生无变于己”的达观态度。这一达观态度要求人们在现实中采取“养生而不执生”“顺死而不恶死”的生命态度与实践方式。以上共同构成了庄子的生死观。
总的来说,庄子对生死的论述,其系统性、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罕有其匹者。而从其影响之所及来看,庄子的生死观,对《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等道家典籍,对魏晋士人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生活方式,皆有重要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庄子》从南北朝开始,受到道教的重视,经过历代道教徒如成玄英、褚伯秀、陈碧虚、陆西星等对《庄子》的注解,庄子的生死观完全融入道教之中,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