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系事
2023-08-24徐叶香
徐叶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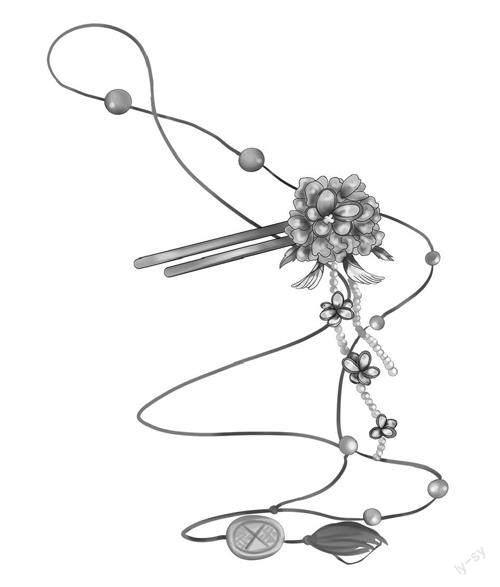

“记”是中国古代一种常见的文体,大约萌芽于两汉,发展于唐宋,至明清逐渐定型。唐代,记体文开始发展,偏重于记事的基本功能;宋代,随着理学的兴盛,记体文中的议论色彩渐趋浓厚,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明代,理学逐渐跌落神坛,社会的重情倾向加重,作家的情感亦渗入到创作之中,记体文中常常流露出作家的真情实感。归有光的记体文是明代的代表之一。本文在追溯记体文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归有光的记体文创作特色,研究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并探究其创作对“记”这一文体发展的影响。
一、记体文的发展
“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发展起来,大约在唐以后。查阅唐代以前的文学著作得知,“记”一般作为其他体裁的附属而存在。萧统的《昭明文选》是现存较早的诗文选集,其中有“奏记”一类,所收文章偏重奏书性质,“奏”的特征更为明显。刘勰的《文心雕龙》列“书记”一类,其下又细分为“谱籍簿录”“方术古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共24种。由此可知,此时的“记”应是指记下的文字,还未形成一种独立的文体。
南宋真德秀认为,“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明人吴讷认为,“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认为,“揚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综合以上各家的论说,古人认为记体文在内容上以“善叙事为主”,在形式上应有“记之名”,这是“记”的文体特点。徐师曾认为扬雄的《蜀记》是一篇典型的记体文,惋惜《文选》未列其类,说明记体文在东汉时已经有人创作,只是并不为人重视。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作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封禅泰山之时,也是现今可见的最早的游记。这篇游记内容完整,详细记叙了封禅的整个过程,其创作时间要早于杨雄的《蜀记》,证明了记体文在两汉时期已经萌芽。
徐师曾认为“记”这一文体“盛自唐始”,应当是正确的。北宋初年,李昉等人所编的《文苑英华》首次将“记”列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收录了306篇文章。宋人姚铉在《文苑英华》的基础上编著了《唐文粹》,在“记”类选录了87篇唐人创作的记体文。这说明,唐代的记体文创作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且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名篇佳作,其文体特征已基本显现。在姚铉所选的记文中,所记叙的对象涉及古迹、陵庙、浮屠、府署、堂楼亭阁、书画故物等,内容十分丰富,同时也非常细致,可见唐人大大开拓了“记”的题材范围。在记体文的发展过程中,韩愈和柳宗元的贡献十分突出,两人的记文甚至被后人视为“记”体之正宗。茅坤评价韩愈的《燕喜亭记》,“淋漓指画之态,是得记文正体,而结局处特高。欧公文大略有得于此”(郭预衡《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
宋代的记体文与唐代相比,文章的议论色彩更为浓厚。陈师道曾在《后山诗话》中写道:“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这句话点明了宋代记体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偏重议论。“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议论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指出了韩、柳的创作对宋代记体文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宋代的记文以议论为主,一方面是韩、柳记体文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宋代理学的发展相关。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兴盛,作家在创作时有意地融入议论,阐发大义,由此也造成了向议论的转变。例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其中却充满理趣。
记体文经由唐宋的大力发展之后,在题材内容、创作手法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其形式已基本确定,完成了向独立文体的转变。明清时期,记体文的发展基本遵循唐宋时期已经形成的记体文创作范式,可发展的空间减少,作家在创作时难出前人窠臼,但依然尝试在内容或手法上进行突破。明代,随着理学的影响逐渐削弱,新兴商业发展,社会的重情倾向加重,文人进行文学创作时开始关注小我,抒发个人情感,代表文人有归有光、徐渭等。清代,记体文创作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亦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例如,桐城派重视义理、辞章、考据,其记体文创作亦带有考据的特色,姚鼐的《登泰山记》便是其中的代表。经过明清文人的再一次发展,记体文已正式定型。
二、归有光的记体文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明代中期文人,主要活跃于嘉靖、隆庆时期的文坛。归有光崇慕上古两汉,通经博古,一生创作丰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有《震川先生集》40卷,收录文章共300余篇,其中“记”类占3卷,共计57篇。记文内容涉及居室楼阁、寺庙祠堂、图画,以及人事杂记等,其中居室楼阁占大多数。在这些记文中,归有光虽写建筑,实际上常常借这些建筑称赞所居之人的高洁品性或者由一二小事生发出亲情、友情之善。
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评价,“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赞赏了归有光的文章对于情感的把握自然真切,无须文辞修饰便能使人读之有感。这一点在归有光居室楼阁类的记文中表现明显,其中的代表有《项脊轩记》《思子亭记》《世美堂后记》。项脊轩是归有光的读书之处,虽然只容一人居,却承载了诸多美好回忆。“儿寒乎?欲食乎?”(《项脊轩记》)归有光以平常之语句写出母亲的拳拳爱子之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项脊轩记》)归有光借枇杷树之繁茂写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嘉靖二十七年,归有光的长子去世,他在第二年筑思子亭,期盼能唤儿归来,“徘徊四望,长天寥廓,极目于云烟杳霭之间,当必有一日见吾儿翩然来归者”(《思子亭记》)。深沉的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除了对亲情的描写感人至深,归有光对友情的刻画亦细腻无声。《见村楼记》在记叙见村楼的过程中,引出了归有光本人与亡友李中丞、方思曾过去的深厚友情,“延实之楼,即方氏之故庐,予能无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来省墓,及岁时出郊嬉游,经行术径,皆可指也”。往昔的记忆历历在目,然而物是人非,只余下孤寂的回忆,悲怆的心绪从字里行间溢出。《野鹤轩壁记》写与友人相会之事,“烈风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号,可念也”。寥寥数语写出这次相会的特殊经历。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归有光巧妙地将它们融入作品之中,由事及情,情感真挚自然。
王世贞在《归太仆赞》中评价了归有光,“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世名家矣”。归有光借建筑来称赞屋主人品性的作品,大有学习韩愈《燕喜亭记》及欧阳修《醉翁亭记》之风。《卅有堂记》写沈大中不为物之有无所累的豁达人生态度,《自生堂记》写友人盛徵伯学医救人之高义,《卧石亭记》称赞徐君之仁人孝子之心,《本庵记》赞赏杨伯厚的孝悌之道。这些记文大多应他人之邀约而作,但是文辞朴实,不见阿谀之色,对他人的赞赏亦出自真心实意。
在人事杂记部分,归有光也不吝表达自己的观点,关注现实,关心民生。《光禄署丞孟君浚河记》记载了孟绍曾捐资浚河一事,归有光借此反讽地方官员无所作为,“孟君居一乡,能兴其乡之水利;则夫受司牧之寄者,独可以辞其责耶?”《唐行镇免役夫记》写太守方侯感于民众劳役之苦,下令免除服役,百姓感念其德,特请为之作记,归有光于结尾处发起诘问,“彼不之恤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常熟县赵段圩堤记》中亦发出“天下之事,其在人为之耶!”的感叹。以上的文章虽以记叙功德为旨,但归有光不止于描写他人的善行,而是联系现实,批判地方官员不恤民意、不担其责的不作为态度,在声声反问中流露出个人的忧虑与愤慨。
他在《沈次谷先生诗序》中谈及“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虽然论述的是诗歌创作,但从其记文的创作情况来看,对于情感的重视已经渗入文章创作中。归有光将真挚的亲情、友情融入屋舍楼阁类的记文中,让本是冰冷的建筑物因人物的活动而增添了温度,同时也增强了记文的感染力,呈现出语淡情深的语言特色,读之亲切有味。在人事杂记类的记文中,归有光着眼于现实存在的弊病,书写民众的艰难,揭露官吏的失职,愤慨的情绪糅杂其中。这些情绪都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或是对亲友的怀念,或是对名士的敬重,或是对官吏的鞭挞,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归有光。这种将情感融入创作中的手法,也让其记文呈现出事中有情、以情系事的特色。
三、特色成因及价值
记体文历经了唐宋的两次大发展,至明代,记体文的创作模式已基本定型。前人对记体文的探索已十分完善,留给明代文人探索的空间并不多,在这一背景下,明人要想打破因袭,创造新变,也有一定的困难。归有光以情系事的记文特色的形成,与其文学取向和人生遭际有关。
明代,复古运动迭起。“前七子”和“后七子”推崇秦汉古文,他们强调“文必秦汉”。归有光反对“后七子”雕琢的文风,认为“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他在《庄氏二子字说》中认为“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今之时则然矣”,批判时文过于浮华。从这些言论中,可见归有光更喜欢不事雕琢的朴实文风。在文学取向上,归有光属于唐宋派,对唐宋文人亦多加推崇,但其记体文并没有专尚议论的气息,反而是议论和抒情皆有。一方面,理学发展至明代,其影响力已大幅度减弱,以议论为文的风气不再盛行,归有光本人也并非理学家,他在进行记文创作时不会好为议论。另一方面,归有光的记体文有学习韩愈、欧阳修之风,影响了其最终的记文创作。
少年时的归有光便慨然有志于古人。他仰慕两汉遗风,渴望走上仕途后能得到重用,却八次落第,直到老年才上任长兴县令。纵观归有光的一生,身为布衣之士的经历几乎占据他的整个人生,他的文章大部分创作于为官之前。曾国藩言:“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曾国藩文集》)曾国藩指出了归有光的文章境界不足。归有光本人也感慨“尝以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为恨事”(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因此,他的散文题材较狭窄,多从日常交友、身边琐事处着笔。受限于此,归有光的记文内容亦多从身边之事写起,挖掘细腻的情感;或是着眼于时事,引发感慨。
明代,记文的创作数量十分可观。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文海》收录记文60卷500余篇,其题材涉及居室、纪事、游览等共15类。归有光的文章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其中蕴藏的细腻情感,读之令人深受触动。明代中后期,随着“性灵”之说和心学的流行,社会的重情倾向加重,文人积极地抒发内心情感,与之相比,归有光的文章亦显得清新可感。唐代的记体文偏重记事,宋代的记体文议论色彩浓厚,及至明代,转而重视抒发个人情感,记体文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创造出了新的成果,归有光的记体文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