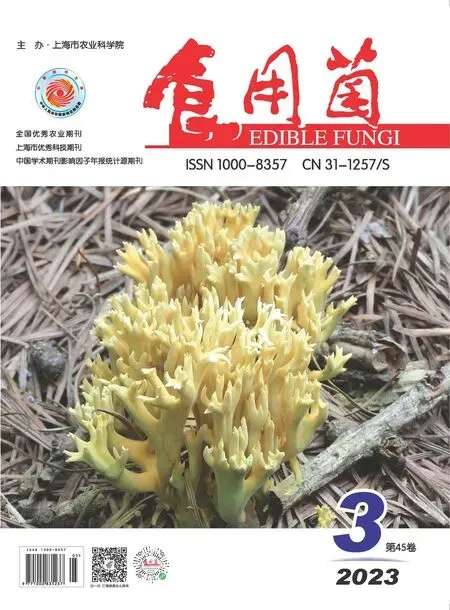桑黄活性成分研究及行业发展分析
2023-08-22谢存一周禹佳张疏雨柴林山朱万芹李剑梅
谢存一 周禹佳 张疏雨 柴林山 朱万芹 李剑梅
(1辽宁省微生物科学研究院,辽宁 朝阳 122000;2贵州大学农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桑黄是一类珍稀食药两用真菌。桑黄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被记作“桑耳”,作为传统中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但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期才逐渐受到关注[1]。桑黄因主要寄生于桑树上而得名,但杨树、白桦等树干上也发现生长不同种类的桑黄[2]。桑黄的人工栽培技术逐渐成熟,其活性成分及产品开发得以逐步推进。桑黄的生物活性成分因其来源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桑树桑黄的多糖、总三萜及黄酮含量相对较高[2]。桑黄毒副作用小、治疗效果好,作为药材开发潜力大、市场前景广阔[3]。
1 桑黄活性物质研究
1.1 多糖类
多糖是由单糖分子通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一类高分子聚合物,其生物活性价值较高,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保健品等领域[2,4],具有抗菌消炎、抑制肿瘤等功效[5]。桑黄多糖以水溶性多糖为主[6],且以桑树桑黄、杨树桑黄以及鲍姆桑黄多糖的研究居多。桑树桑黄因人工栽培困难,主要研究其发酵液、菌丝胞内多糖[7-8],杨树桑黄子实体栽培技术较完善,其多糖提取、活性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多[8]。
桑黄子实体多糖、发酵液多糖的提取方法有溶剂(热水、稀酸、稀碱)浸提法、超声提取法、微波提取法、酶提取法、盐提取法、三相分离提取法、低温低压法等[5,9]。李彦颖等[10]总结了近年来多糖提取工艺的研究结果,得出多糖的提取率为1.52%~10.6%。桑黄多糖的分离纯化常采取离子交换层析结合凝胶分子筛层析的方式[10]。桑黄多糖结构多由杂多糖构成,单糖组分有甘露醇、果糖、葡萄糖、阿拉伯糖、木糖、半乳糖、鼠李糖、岩藻糖及核糖等[10-12]。贾建波等[13]分析两种β 型吡喃桑黄多糖结构,其中HHM由葡萄糖组成,HLM 由葡萄糖及半乳糖组成。CHENG 等[14]分离出的桑树桑黄胞外多糖SSEPS2 由D-甘露糖组成;葛青等[15]分离出的多糖PBF6、LIU等[16]分离出的多糖PRG 由葡萄糖组成。GE 等[17]从桑黄子实体中提取到甘露聚糖,主链1→6 甘露糖,支链1→3 葡萄糖;MA 等[18]分离得到桑黄菌丝胞外多糖SHP-2,主链→4)-β-甘露糖-(1→4)-α-阿拉伯糖-(1→3,4)-α-葡萄糖(1→3,4)-α-葡萄糖-(1→3,4)-α-葡萄糖-(1→3,4)-α-葡萄糖-(1→3,4)-α-葡萄糖-(1→6)-α-半乳糖-(1→4)-β-甘露糖-(1→,侧链有四个α-D-葡萄糖-(1→及一个α-D-甘露糖-(1→。另有研究表明相对分子量大于5×104,以β-(1→3)-D-葡聚糖为主链、周围随机分布β-(1→6)连接的葡糖基的多糖类成分更可能具有较高的抑癌活性[19]。
桑黄多糖的药理作用研究表明,其具有抑制肿瘤作用,能够刺激机体产生淋巴T 细胞及B 细胞,激活巨噬细胞,增强其免疫反应,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20-21]。LIU 等[22]体外肿瘤细胞试验证实,在其有丝分裂的G0∕G1 及S 时期,鲍姆桑黄多糖PPB 通过阻碍细胞分裂抑制胃癌细胞、宫颈癌细胞的增殖,同时促进巨噬细胞增殖,增强吞噬活性,具有较强的调节免疫功能。鉴于化学疗法对人体产生的毒副作用及单一疗法的局限性,化疗药物组合桑黄多糖治疗肿瘤或产生更有益的作用[10]。桑黄多糖还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对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DPPH·)及2,2’-联氨-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二胺盐自由基(ABTS+·)清除率分别高达88.83%、73.54%[23];桑黄子实体多糖生物活性较强,而菌丝体多糖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活性[24]。除此之外,桑黄多糖还具有一定抗糖尿病的作用,HOU 等[25]、CHENG 等[14]、ZHANG 等[26]、FENG等[27]研究发现桑黄多糖可抑制葡萄糖扩散、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糖水平。桑黄多糖还具有其他功效,ZHANG 等[26]的小鼠试验发现鲍姆桑黄子实体多糖具有保肝作用;李金凤等[28]发现桑黄多糖对大鼠的胶原诱导性关节炎有一定的治疗作用;郭俊平等[29]的试验表明,灌胃桑黄多糖的小鼠具有抗疲劳、耐毒、耐缺氧特点。
1.2 多酚类
多酚是一类含有多元酚结构的具有高抗氧化活性的天然化合物,包括黄酮、花青素、酚酸等。桑黄子实体中含有标志性的酚类物质有hispolon、鞣花酸、γ-紫罗兰亚基乙酸等[11]。闫国卿[30]研究发现,桑黄P.igniariuson含有的多酚类物质包括hypholo⁃min B、hispidin、hispolon 及bis-noryangonin;昝立峰[31]用甲醇分离自F.ellipsoidead子实体的多酚类物质inonotusin B 的抗氧化活性最强。HSIEH 等[32]研究表明,桑黄多酚类化合物hispolon 对鼻咽癌细胞的增殖有一定抑制作用。黄酮也是桑黄标志性的活性物质之一,主要为二氢黄酮类、黄烷类等[33]。唐琳[19]在五种桑黄中共检测出10 种黄酮类化合物,2 种为二氢黄酮(异樱花素、圣草酚),2 种为黄烷醇类(儿茶素、表阿夫儿茶精),2 种为黄酮类(黄芩素、川陈皮素)以及4 种为黄酮醇类(3,7-二氧-甲基槲皮素、槲皮素、橘皮素、3,5,6,7,8,3′,4′-七甲氧基黄酮),其中3,7-二氧-甲基槲皮素在五种桑黄中含量均较高。程鑫颖等[34]从瓦宁木层孔菌子实体中分离出3种黄酮类化合物(7-甲氧基二氢莰非素、二氢莰非素、樱花亭)及2 种多酚类化合物[4-(3,4-二羟苯基)-3-丁烯-2-酮、hispolon],这5 种化合物清除自由基能力与其浓度呈现一定依赖性。桑黄体外总抗氧化活性与其总黄酮含量呈现极显著相关性[35]。桑树桑黄含黄酮类5.12%,高于杨树桑黄及松树桑黄等[11,36],野生桑黄的黄酮含量明显高于人工栽培的桑黄[2,37]。黄罗丹等[38]用乙酸乙酯萃取、纯化桑黄发酵液中的总黄酮,发现其对小鼠肝癌细胞HepG-2 有抑制作用,且效用与剂量呈现正相关关系。
1.3 萜类、甾体类
目前对桑黄萜类物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萜类[2]。三萜类化合物可视为由六个异戊二烯单位聚合而成,主要前体有鲨烯、羊毛甾醇[39]。三萜类物质在免疫调节、抑制肿瘤、抗菌消炎等方面有积极作用[2]。袁红艳[40]从桑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到7 种三萜类化合物,分别为齐墩果烷型[3-乙酰氧基齐墩果酸、3β-羟基-20α-甲基齐墩果-13(18)烯-29-甲酸],环阿屯烷型(3-羟甲基-4α,14α,20R-三甲基-9,19-环-24-乙烯基-5α-胆甾烷),羽扇豆烷型(羽扇豆醇、23-羟基白桦酸、白桦脂醇、1β,3β,11α-三羟基羽扇豆醇);并验证一些具有羧基、齐墩果烯类、羽扇豆烷型的三萜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何策等[41]采用优化工艺提取桑黄总三萜,得率为12.32%;同时发现桑黄总三萜对DPPH·及ABTS+·均有较高的清除率,IC50 为0.304 mg∕L、0.520 mg∕mL。刘增才等[42]研究暴马桑黄菌株DL101三萜合成的分子机理,发现基因SbGPS在三萜合成途径中的重要作用。黄静[43]优化桑黄液体发酵工艺后获得菌丝体三萜为236.8 mg∕mL。谢江宁等[44]分析桑黄P.igniarius总三萜的功效,发现其能抑制脑胶质瘤细胞U251 的增殖。桑黄甾体类化合物的相关药理作用报道较少,孙德立等[45]从P.baumii子实体中提取的甾类化合物有抗炎及抗肿瘤功效。WANG 等[46]分离获得的羊毛甾类三萜可有效抑制由脂多糖(LPS)诱导的体外巨噬细胞(小鼠)产生一氧化氮(NO)。
1.4 呋喃及吡喃酮类
桑黄子实体中含有呋喃及吡喃酮类化合物[11,47]。王钦博等[48]分离纯化P.baumii的吡喃酮类化合物inoscavin A。CHEN 等[49]研究表明,桑黄子实体中的菲林呋喃A 与菲林呋喃B 存在抗互补活性。LEE 等[50]从桑黄中提取苯乙烯基吡喃酮(黄色粉末),发现其自由基清除能力较强,且能抑制芬顿(fenton)反应所引起的DNA 超螺旋断裂。胡小斌[51]研究发现,桑黄中提取的5-羟甲基-2-糠醛有抗糖尿病的作用。研究者发现,桑黄的子实体中吡喃酮为主要的多酚色素,并且分离出分子式为C13H10O5的β-分泌素牛奶树碱抑制剂[52]。
2 行业发展分析
2.1 桑黄产品
近年来市场上不断出现以桑黄为原料的保健产品,如桑黄酒、桑黄口服液、桑黄袋泡茶等。基于桑黄多糖的保健功效,邵伟等[53]以多糖含量为指标优化茶饮料的发酵工艺,结果菌丝多糖体积质量达0.064 g∕100 mL;傅海庆[54]研制的桑黄口服液能显著提高小鼠免疫功能;刘福胜[55]研制的桑黄多糖胶囊具有提高小鼠的抗衰老能力及保护肝脏功能。李雪等[56]用桑黄发酵液、酸奶,开发出具有桑黄口味的风味酸奶。洪文龙等[57]结合桑黄与灵芝的保健功效,以黄酮含量为指标,优化工艺后袋泡茶制作的冲泡液中黄酮体积质量达(12.95±0.23)mg∕L。上述研究为桑黄产品的深加工,桑黄销售市场拓展具有指导意义。
全国各地纷纷制定桑黄作为药材的质量标准。湖北省于2009 年收录野生忍冬木层孔菌Phellinus lonicerinus,并颁布了桑黄药材地方标准;其后山东省、安徽省、吉林省、甘肃省、浙江省等陆续制定了人工栽培的瓦尼桑黄Sanghuangporus vaninii、桑黄纤孔菌属真菌鲍姆纤孔菌Sanghuangporous baumii、粗毛纤孔菌Inonotus hispidus等桑黄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相关药材质量标准[1]。
2.2 行业发展前景及制约因素
近年来,桑黄功效及药用价值的研究正逐渐深入,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初步探索阶段,例如对桑黄的抗肿瘤功效研究缺乏临床实际疗效的数据支撑,其治疗与保健效果没有明确指标,须尽快制定其量化标准,建立临床试验评估体系,更好地为开发保健产品及药品提供指导[1]。另外,多数省份尚缺乏桑黄应用行业规范、地方标准,产品准入规范及质量标准等,且已经颁布的桑黄药材质量规范及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也存在对桑黄活性成分要求不一的问题[1,58]。
多年来桑黄作为传统药材在民间被广泛应用[59],但尚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药典》),其研究、种植、产业转化仍未深度融合[1]。《药典》中明确药材水分、灰分含量是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其会影响浸出物含量测定及药材性状检测结果。《陕西省地方标准DB61∕T 11586—2018》《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9 年版)规定了桑黄水分、灰分含量范围[58],但标准不统一。活性成分、指标性成分不明确或含量低的药材,无精确定量方法,需测定其浸出物含量。目前鲜有桑黄浸出物含量测定的研究[58]。农药残留、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检测均证实桑黄作为药材的安全性,但因其生长周期较长,应全程动态检测,保证用药安全[58,60]。除此之外,桑黄活性成分质量标准评价体系、炮制工艺标准的缺乏均是制约桑黄进入《药典》的重要原因[58]。长城等[58]提出开展桑黄标准化栽培、尽快建立国家级质量标准、根据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筛选入药种类、将DNA条码列入桑黄标准等建议。
拉丁学名命名混乱是影响桑黄产品申报、制约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韩国等一直将P.linteus作为桑黄统一拉丁学名,其产品也被认可为食品、药材等进入市场[1]。长期以来,我国桑黄的学名各异,包括针裂蹄Phellinus linteus[61]、裂蹄针层孔菌[62]、火木层孔菌Phellinus igniarius[63]等,同时桑黄的基源物种说法也仍存在争议[58]。目前经分子序列分析创建新桑黄孔菌属,其模式种命名为Sang⁃huangporus sanghuang[64]。杨焱等[1]建议将目前人工栽培的不同种类桑黄统称为“桑黄”,对不同种属进行细化鉴定分类;同时建议在药材产品申报及标准制定时,统一应用最新的拉丁学名及中文名称。基于杨树桑黄成熟的人工栽培技术,为保证道地性及市场资源的持续利用,长城等[58]建议将其作为质量标准中的桑黄来源之一。
3 展望
桑黄作为一类珍贵的食药用菌,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及保健功效,在抗菌消炎、抑制肿瘤、降血糖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桑黄活性成分包括多糖类、多酚类、甾体类及萜类、呋喃及吡喃酮类等,这些活性物质的提取、分离纯化,以及相应的化学结构、药理作用被广泛研究。目前桑黄保健类食品及药材类产品的开发受到重视,市场需求量上升。未来应加强桑黄临床试验研究、制定完善相关标准、推进桑黄进入药典进程、统一学名认定、优化人工栽培技术,进一步加强桑黄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