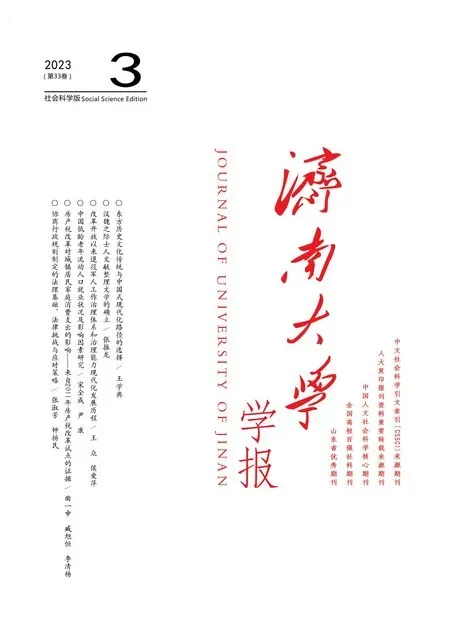阿来和张翎小说时空建构下的民族文化解读
2023-08-21张堂会
孙 欢,张堂会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少数民族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由于历史积淀、风俗文化以及异质场域等影响,阿来和张翎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所展示的文学景观理应“源流多异,风貌互殊”①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然而,如果以时空建构的视角去解读,时空书写下的叙事呈现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特点,时空的转换,时空的跳跃与衔接,人物形象的显露与隐匿都不露声色地传递着民族文化的情怀;可以发现更多的民族文化包容与融合的共同体理念,个人与民族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现代民族精神。对两位作家小说中民族文化的解读有助于挖掘少数民族文学与新移民文学中异质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更好地把握跨领域文学书写的文化表达,更进一步理解异质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命运与共的包容与融合理念。这种横向对比是对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对两种文学分支的再认识,为更多跨文化领域的文本解读提供创新性的研究示例。
一、故土:时空建构的根基
时空从来不具有独立存在属性,更多的时候是“诸多层面的复合”,人们对于地域的感知融合着“情感、记忆和历史、文化”的复杂情绪①丹珍草:《差异空间的叙事:文学地理视野下的〈尘埃落定〉》,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不论是离乡还是出国,这种离散状态使原乡处在地理意义上的相隔状态,而故土的情感像符码一样印在作家心中。物理空间的疏远并不能引起心理空间的冷漠与淡忘,相反故土情怀越来越浓。阿来书写的物理空间是地处雪山与峡谷之间的藏族村落,而张翎表达的是江南的乡镇与大洋彼岸之间交错的物理空间。藏族机村村庄和江南小城温州是风情异样的地理空间,这种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景观。如果穿越时空的表层,洞悉时空的复杂性,可以发现两位作家描绘的故土在情感诉求上的一致性与交融性。
故乡存在于作家的记忆之中,因此,故乡的时空建构源自回忆和想象。阿来《机村史诗》《云中记》等作品围绕藏族村庄的物理空间进行叙事,在回忆和想象中书写藏族村庄的历史与现状。机村的“机”在藏语里是“根”的意思,乡村就是他的根。然而,故土情怀的深层体验无非是背井离乡、海外飘泊所产生的对故土的眷念。张翎曾写过“童年、故土、母语”仿佛是“生命密码”,永远融入血液中,“无法剥离”②[加]张翎:《废墟曾经辉煌》,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其初期作品“江南三部曲”即《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以及后来的小说《阵痛》《流年物语》《劳燕》,都呈现了南方故土气息和荣辱与共的家国情怀。它们依存于记忆空间中重塑故乡的心理空间,增添了地理场域里故土的依恋。人物的记忆与作家的记忆双重呼应,形成交织着人物情感的立体式空间布局;与其说是文本人物回归故土,不如说是作家重温故土的乡愁。因此,张翎说故乡是“随身的行囊”,不论在哪里,“每一种离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回归。”③[加]张翎:《望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5页。
当现代化建设影响故乡的物理空间时,怀乡记忆不可避免地被冲击,而作家能够较为平和地处理人物在命运波折中的心理构建,接受并赞同故土的进步,表达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前进。譬如机村原有的物理空间构建有石头寨楼、庄稼地、打麦场、磨坊、村后的山坡和森林等,而机村现代化的物理空间可见公路、隧道、种树的公司、民俗博物馆、觉尔郎景区等。每一个物理场地在时间线上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新时期以来乡村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文本中故事情节发展的枢纽由广场向酒吧的公共空间转变,显露出新的时代气息。这种变换不是建立在对立冲突的基础上,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张翎笔下交错的跨国物理空间加剧了故乡变化带来的心理触动,文本人物在海外生活数月或数年回国往往会被国内的改变而震撼。譬如《交错的彼岸》中蕙宁旅居海外十年后回到故乡,发现飞云江岸边的 “陌生”景致,“高楼、汽车”取代了三轮车、艄公等童年记忆中的景象④[加]张翎:《交错的彼岸》,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378页。。为了适应异文化的冲击,移民会发生一些认知上的改变,对祖国的态度会和在国内时有所不同,但不变的是归属感,甚至会变得更加爱国。至此,故土似故土又非故土;变的是故土的时空,不变的是故土的情怀、故土的文化和对家国的依恋。当然,阿来和张翎的家乡空间构建方式略有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讲,阿来建构的故土是由一到多、由封闭转为开放的物理空间以及社会空间;而张翎的故土叙事却是基于现实与过往、江南与北美之间不断交替更迭的空间转换。虽是如此,地理空间上的漂泊成就了文化上的归乡,而心理空间的回忆、思念、感悟等情感体验造就了作者对故土、家国、民族的文化再思考。
二、历史:时空建构的灵魂
当作品对历史的表达不再局限于时间维度以“凝固时间、保存记忆、探究往昔”的形式出现时,在特定时间下“某一个空间内”发生的事便具有了现实场域的灵魂⑤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60页。。两位作者将笔触伸向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进行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与心理空间的重构。通过不同的视野复原或重构回归历史现场,展现了时空变迁伴随着历史文化的深思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当空间叙事介入历史长河,地理空间或合或分,心理空间或紧或疏,与虚构的过往世界拼接融合可以消除时间的隔膜感;但有时心理空间因为异地异质的不适宜反而会进入另一种荒漠。于是,探究历史循环的真相或者寻求心理空间的疗愈显得格外重要,它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使过去得以向前良性的发展。
阿来的《格萨尔王》《尘埃落定》《瞻对》是对藏族历史一脉传承的寻迹之作。《格萨尔王》所展现的高原史诗形态从属于“江河源文明”,是“长江黄河的源头”产生的文明形态①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第63页。,主人公弘扬正义的主题思想贯穿于整部史诗,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作为传唱千年的民族史诗,它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与民族精神凝聚和传承的直观见证,涵养出深厚的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意识。在《瞻对》中,作者以“两百年”康巴的历史为载体,构建了时空交错的藏民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融合。而《尘埃落定》则以民国时期藏族各土司之间的恩怨展开叙述,以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怀角度把握历史深处的文化秘密。嘉绒部族历史的书写只是时空建构平台的一种载体,对历史未来的深切呼唤才是意图所在。随着解放军进剿国民党残部的隆隆炮声,一个旧的世界终于尘埃落定;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文明终将战胜野蛮走向新时代,形成包容与融合的民族文化。
张翎的历史书写有时会脱离其熟知的时空,然而,最终还是绕不开落叶归根的乡思文化。《金山》采用时空跳跃的技巧讲述了百年华人的海外奋斗史,在时间和空间上交错地呈现达到了缩短百年时光流转的效果,突出了社会和文化空间巨变产生的情感体验。而来自“陌生的朝代,陌生的土地,陌生的风土人情”的《睡吧,芙洛,睡吧》见证了淘金时代华人女性不屈不挠的他乡奋斗的血泪故事②[加]张翎:《睡吧,芙洛,睡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正如列斐伏尔和福柯认为的那样,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表征,是种族、性别、阶级的权力关系网络”③杨傲霜:《20世纪初英国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14页。,巴克维尔小镇的街头和街尾代表着两种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而芙洛和丹尼的爱情是连接两种迥异空间的桥梁。勤劳的中国女人芙洛使两个族裔有了沟通;她的豪情与柔情,勤劳与智慧,无畏命运悲舛的精神征服了全镇人民。她死的时候,全镇的人给她立了一块墓碑“睡吧,芙洛,睡吧”。据此,主人公芙洛朴实、善良的形象散发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感召力与包容性。《劳燕》采用多层叙事的框架,跨越时空限制,以三个幽魂的对话回顾了在日军侵略背景下乡村女孩阿燕的凄惨命运,以独特的视角叙述了中西方不同文化的情感表达与思考。三个男人的生前约定在死后得以实现,自此揭开了七十多年前,一个平凡的乡村女子在不平凡的时代无声抗争生活的故事。主人公阿燕本来带有中国传统乡土的文化基因,但在不同文化的激荡和融合之下,她没有依附于任何一种文化,而是慢慢地将这些不同的文化融合发展。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她坚强地生存了下来变成了强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和人性的光辉感染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而阿燕的故事又与当时中国自身命运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独特民族品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包容与融合的多元文化。
三、形象:时空建构的内涵
不论是地理空间的定位,还是时间空间的延展,小说最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人物的活动,时空建构才会生动形象,叙事才有活力和意义,文化内涵才更丰满和真实。从时空建构的角度解读文本,可以得出比较典型的两类形象,即母亲形象和他人形象。母亲形象在崇尚孝道文化的中华民族属于社会文化的“主体”体现者的位置,并对应着故乡和母国乃至民族的精神形象。形象学研究的他人形象是作家以自身观察为出发点对外来文化的具象记录,是对一种文化形象乃至自我形象的塑造;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中,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对外来文化的认知以及重新构建自我的过程。
无论东西方文化,母亲形象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孕育其形象的母体文化的深刻内涵。阿来的小说惯于设置缺失父亲的主人公,其背后是默默的坚韧的母亲形象书写,譬如《格拉长大》和《随风飘散》中柔弱的疯傻母亲桑丹,尽管她的经历凄惨,但她多次护子的行为体现出母亲的本能。无独有偶,张翎的小说也刻画了韧性的母亲形象,譬如《余震》中小灯的母亲李元妮,那个一夜之间经历丧夫、“丧女”、儿子独臂、家园毁尽的她,二十六岁一夜愁白了头。“天灾平等地击倒了每一个人”,但是他们“站起来的方式,却是千姿百态的”①[加]张翎:《余震》,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李元妮在灾后用瘦弱的身体支撑起破碎的家庭,坚守着老宅,坚守着对小灯的纪念。《阵痛》中描述母女三代在波荡起伏的岁月中隐忍与坚守,无论经历了何种苦痛,仍对生活报以希望②[加]张翎:《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页。。至此,在天灾人祸面前,母亲的坚强形象与舐犊之情互相融合。
两位作家对他人形象的塑造截然不同,其中一个是关于村庄以外的外来人,另一个是中华民族以外的民族。符号互动论把自我与他人之间做了一个动态的定位,即“人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而这种互动是“基于一定的意义阐释与理解之上”,并“处于不停的互动与变化过程中”的状态③李金云:《主体 语言 他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页。。阿来的作品蕴含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情感体验,其中村民是主体,村庄以外的一切人或物是被“凝视”的客体。文本中蕴含了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理念,而渴望民族繁荣昌盛的共同体意识正是作者传递出的新时代民族发展愿景。譬如进入机村的汉人正是机村现代化启蒙的先行军,如机村的外乡小学老师、《守灵夜》中的章老师、《云中记》中的外地幼儿园老师等都为村庄带来了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张翎的文学创作竭力在中西文化中寻找平衡,以历史为背景,文化冲突为表象,以期获得共性表达。作者通过《金山》异国人物形象的书写表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了解的愿景。她在小说中还塑造了较多的对中国文化痴迷的他人形象,如《望月》的牙口、《交错的彼岸》的彼得、《邮购新娘》的保罗等。作者站在一定的高度远远地审视着中西文化并思考全球化形势下这两种文化的沟通。因此,作者并没有刻意地去渲染本民族文化的神秘以迎合西方对东方的想象。《邮购新娘》的约翰受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的影响来到了中国,建立恩典红房学堂,并爱上了中国姑娘邢银好,而他的孙子保罗一直希望去中国寻找爷爷的生活印记。这其实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新审视,是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认同,这切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流融合,彰显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华夏民族的文明胸襟与文化自信。
四、结语
阿来和张翎基于故土文化的根基在时空交错的构建下以开放的文化胸襟和视角融入了自己跨越民族、国家的生存体验,投射了个人的精神价值和民族文化,并将空间原型扩展为叙事框架,借助深厚的历史文化拼接历史碎片凝聚灵魂,以丰富的人物形象呼应故土情结和言说自我。这种跨越时空的异质文化书写,突显了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的渴望,以及对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思索。是以,两位作家对时空触感的书写实践蕴含着极具丰富的文化意向表达,为跨越多民族文化、东西文明乃至世界多样性文明的时空探索提供了阐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