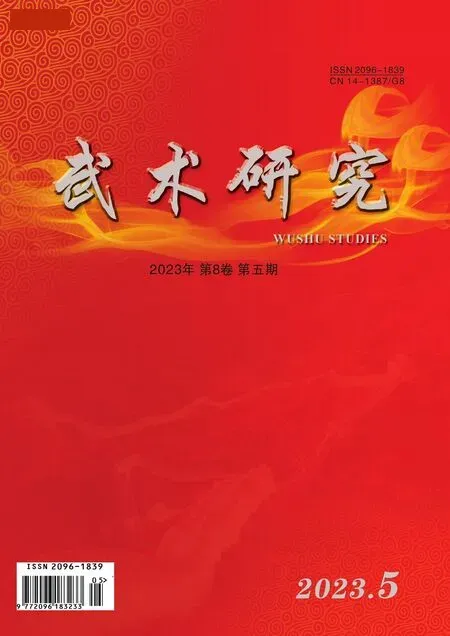武术兵道(短兵)服饰的谛视与完璧:向“黑”色回归的无色之美
2023-08-17牟萧羽
牟萧羽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武术散打、自由搏击和综合格斗等竞技格斗类项目是现代搏击的组成部分,众多竞技格斗类项目中西方的拳击、日本的柔道和泰国的泰拳等,受当下时代背景的影响,开始在世界体育竞技舞台崭露头角。[1]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便有中国兵道(短兵)、日本剑道以及西洋击剑项目。现代剑道起源于日本,深受中国古代剑术及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土情况加以创新,最终形成特有的日本剑道。剑道服饰更是以中国唐代风格为基础,同时根据其具有民族特色的武士服饰及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服饰后凝练成现在的剑道服饰。[2-4]西洋击剑根据欧洲骑士精神以及现代竞赛规则的要求下,采用电子科技技术与传统结合的风格,率先踏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因此,目前来看只有中国兵道(短兵)还处在发展的新阶段。[5-6]作为炎黄子孙的传承之子,理应担起赓续重任,将其发扬光大、传承后世。
1 武术兵道(短兵)现实的发展处境
武术兵道(短兵)是我国民族传统武术竞技对抗项目之一,戴小平曾对短兵格斗给出定义:“是通过两人相较、相击、相搏和相对抗的形式,进行竞技而比较剑刀武艺的形式,包含有中国数千年相延续而产生与发展的精妙的刀剑法。”[6]“兵”即可看作是手持的武器也可认为是战场上的士兵,它是与军事、战火相关的统称字。《说文解字》中写道:“兵,械也。”按照其观点,上“斤”下“廾”,廾(两手)持斤、并力之皃(貌),强调“兵”是会意字,本意为武器。关于“短兵”一词,出现甚早。2019 年,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武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25 年)》中强调,要求建立完善的国家武术重点项目目录,并将短兵运动列为重点发展项目对象之一,这使近些年关注并加入武术兵道(短兵)项目的群众基数逐渐增多,武术兵道(短兵)是我国竞技对抗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当今国家及社会双重肯定发展的背景下,无疑是最好的发展时机。
1.1 武术兵道(短兵)服饰设计的偏轨
在中国世代延续的审美形象中,大多以黑与白为众多基色的表象,这主要因为“黑”与“白”是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矛盾且互相融合的双极色,体现在视觉追求上更多是中国浓韵内敛且幽邃的自然美。我国对短兵护具的研发起步尚晚,且略显不足,当下,短兵以武术散打和剑道等项目的护具服饰为参照。然而现有的散打服饰设计主要倾向于便于竞赛的相关工作,缺乏在民族文化气息上的考究,在审美及认知层面尚有提升的空间。[7,8]在民间,武术兵道(短兵)的相关服饰形式更未形成统一。仅在《武术兵道规则2022版(确定版)》中有规定护具的相关内容,包括:护头、护甲、护手 (手套)、护裆(阴)、护腿、护臂和兵道鞋,并将软皮革、海绵、帆布和硬牛皮条作为护具主要材料,主体为黑色基调。虽然护具结构齐全稳健,但并未融入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民族元素,整体来看稍显疲软,隐约有散打、跆拳道甚至欧洲重甲护具的影子。虽然贴合于国际化道路,但笔者认为,武术兵道(短兵)当下更适合稳健的路线,稳扎稳打的同时,逐渐在未来扩大发展,拉长战线。多一点中国元素,多一点不同的地域特色(如,不同地区在不影响竞赛公平性的前提下,以不同的参赛着装和器械外貌等形式参加比赛),把握中国有利优势“多点开花”彰显与其他项目的差异性,展现项目特色更是重中之重。在多元素的糅合下,打造现代的“华山论剑”。武术兵道(短兵)服饰代表着项目形象,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短兵格斗开发的专业水平及审美标准。
1.2 武术兵道(短兵)的文化优势
短兵服装的设计在质量层面上应满足以下几类要求:首先,必须适应日常训练,又与比赛时的穿着大相径庭;第二,在材质上,应无闷热感、吸汗、耐磨、易洁和防破等功能;最后,在设计层面,应饱含中国元素,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甚至不同队伍,可设计不同款式。如,融入华夏图腾符号,东北地区以虎、雷和兽为主;西南地区以云、鸟和羽等风格理念为主;不拘泥于固有模板,突出我国众多民族与悠久历史的优势特色,强化民族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的长久发展。
中国兵道(短兵)服饰护具应更多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基调,结合西方展现人体美的设计风格,充分发扬兵道(短兵)项目的差异优势。中国兵道(短兵)的理念优势在于其项目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百兵之长于一身,是当代中国器械搏斗的代表。因此其服饰上的设计,必然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可加入中国古代士兵贴身的甲胄元素,在服饰护具中传承武术文化,展现出华夏历史的磅礴气概,作为中华几千年军事体系中的开山泰斗,甲胄是传统军艺的重要代表之一,从不同朝代遗留至今且保留完整的甲胄中,就有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色彩”,装饰上有:祥云、龙纹、护心镜、火炎等;颜色上更丰富多样:朱黑、墨蓝、黑漆等;款式也千姿百态:虎头、鱼鳞、狻猊等。只有尊重先辈的优秀传统文化,才可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9-11]
中国兵道(短兵)还应遵守中国服饰文化中的服饰颜色等级制度。服饰从初始之期,就有着标识的功能。如,各部落之间的相似,以及之后社会中不同年龄和性别角色的服饰不同。最经典的莫过于古时的加冠与插簪。后来随着不同朝代君王的统治调整,这种等级秩序被不断改变,服饰的实用功能渐渐被政治功能取代,审美沦为功利的奴隶,服饰被纳入与之不和谐的体系中。中国服饰文化的“级”,表面上来看是社会等级的划分,维系血缘的枢纽和衡量家族成员亲近的量尺,深层次更是对天地秩序的效仿,这种观念具体反映在形制上。传说在尧舜时代有“十二章”,即服饰上有十二种图案。《尚书·益被》上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肪、献、希、肃,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由于实物现已无法考察,因此当下对这些图案的理解各不相同,参照孔安国的说法,一种图案分别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堆)、藻(水草)、火、粉、米、肪(斧形)、献(了厂形),天子的服装用十二种图案,诸侯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士用藻火两种。在图案的使用上,上可以兼下,而下不能兼上,等级界限非常分明。这些图案中,不仅将日月星辰和花鸟草木等自然事物搬在服饰上,而且这些事物还有各自的象征意义。旧、“月”“星辰”代表天,“山”在古人心目中被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为皇帝是天子,所以这四种图案专供皇帝使用,天子通过登天之道(山)而达到同天,(日月星辰)的交流和融合,从而达到“天人合一”。“龙”象征着王权,“华虫”近于凤,只有天子和三公诸侯才能使用这两种图案。“肪”据说是以斧形象征决断。“献”以获相背之形象征善恶分明,“粉”“米”代表食禄丰厚,“藻”有文饰,“火”焰向上,士以上才能用。而选用十二种图案,也是象征着“天人合一”:天之大数,不过十二,若为十三,无所法象。皇帝既然被称为“天子”,说明他同“天”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是上通天意、下察民情的中介,所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最直接、最明显地表现在其衣着服饰上。表现在图案上,便是以十二种图案为其代表,这些图案除了表现天象(日月星辰)和与天相通的途径(山)外,还表现在古人观念中认为十二乃是“天数”,所以在数量上也要符合“天数”,以便祈福于上天,获得上天的保佑,使人的日常行为符合天理,严守天数,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目的。只有追本溯源地了解华夏文明和服饰文化,才更有助于武术兵道(短兵)项目的推广。
2 武术兵道(短兵)服饰中的设计完璧
无论是武术兵道抑或是普通的服饰都离不开面料、色彩和造型三个重要元素。色彩作为其中最具感染力的语言,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递服饰的文化与风格,体现了人们的审美感受与审美愿向,同时也影响了服饰价值与质量。汉斯·霍夫曼曾经说过:“色彩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表现力量。”
黑色在色彩学中被称之为“无彩色”即无色彩中性色,是重要场合和节日的首选。长久以来,黑色盛装早已成为优雅色彩的传统代言词,因为黑色系的服装是通过放弃绚丽多彩的豪华与张扬,从而才更随性地将黑色的优雅与高贵显露出来,它用黑色来揭示无色的㤞寂之美,表现服装的艺术价值,彰显生命的意义。所以黑色是有没有风险的优雅。
2.1 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优势
服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同时也是折射出同期社会文明下审美文化和多元意识形态的有力写照。随着人类文明地不断演变。人们对黑色的概念早已不只停留在单一的色彩层面。中国如此,兵道亦是如此,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许多颜色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文化内涵和特殊意味。在我国古代,就有古人把黑色涂抹于身体并从事相关巫术和祭祀等活动,以此向上苍祈求安详和天命。通过这些方式,逐渐发展为古代人尚黑的色彩倾向,并不断上升为一种独特的中国特色审美情趣。[12]
色彩是了解事物的大门,其本身其实并无正邪与尊卑之分,能够唤起人们无意识地自我联想。色彩引发的心理主观反映,源于客观世界的自我经验。这些经验每个人都经常察觉,并逐渐成为自我审美认知。笔者认为大多的信息、符号和评价认知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得出的,而颜色的象征性也源于这一切,其大多是流传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传统和风俗文化,这些色彩符号的信息经验是心理抽象化的产物,因此,心理映像与色彩效果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出于现实中某些复杂因素的影响,色彩在特定的环境下被强行赋予不同的特定意义。
在中国古代尤其受到五行色彩学说和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深层次地在审美等层面上得以体现,黑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民族感,这不仅表现在古往今来人们对服饰颜色的选择,还表现在传统技艺以及各种艺术和文学作品中。虽然自夏朝以后崇黑浪潮渐退,但到了秦朝又重新开始盛行如,秦汉时期以“天玄地黄”的中国传统色彩观念为基准,开发制作的中国漆器,其黑色与朱色相搭配的“鬼斧神工”下隐含了中国人崇尚与自然共生的和谐情感观念。同期秦始皇又根据五行学说,以十月(亥月,亥月属水)朔为岁首。服饰与旌旗都以黑色为尊,臣民以黑色为重,其中庶民用黑色头巾裹头,称为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方今水德之时,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并在之后数朝沿用流传。如,汉代帝王同样推行尚黑之风,《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六《霄游宫》记载:“汉成帝号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缔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更有诞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黑陶以及在此之后通过不断继承而来的北宋时期的磁州窑、汉唐壁画、帛画、琉璃瓦等都是以黑的色彩为源头。《小尔雅》载:“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古代贵族或官员常用服色之一。同样,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与黑色产生不解之缘的例子,如,《说文解字》中:“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亦有《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等。我国《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服饰卷》中有记载,黑色在我国至少30 多个少数民族中是不可或缺的主流色调,并且众多少数民族至今仍传承穿着黑色服饰的传统风俗。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面对同一事物时,人们对于客观主要持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认知态度、功利态度和审美态度,分别对应的是三种属性:知识、价值和审美,同时也说明了三种人类学基础,事物的物理性、事物的可用性以及事物的形象性”。举例来说,一棵树,植物学家来看它生长的结构与成分;商人来看会是它在市场中的价值;艺术家来看则是享受它带来的美感。因此,对于同一事物,主要看其在观察者眼中,具有何种程度的相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武术兵道(短兵)项目服饰功能的呈现,离不开人的审美态度。
2.2 武术兵道(短兵)中的黑色点缀
黑色不会与其他相搭配组合的颜色产生让人感到不适或不恰的反和谐感,因其具有广泛的调和与适应能力。它常常与相配的任何色彩呈“互助”趋势,从而有助于不同事物的风格展示。这种深邃的宽容魅力使黑色更具吸引力。从哲学视阈分析,“无”等于“空”。空灵的“无心”容纳百川,是美感诞生的初始。因此,笔者认为保持物象间的距离,保证“空”的绝缘,使二者不沾不滞,更有助于兵道服饰意义上的诞生。同时,黑色的“无”色之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大和为美”的审美观不谋而合。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色,老子认为黑色是一切色彩的初始亦是止熄,因此黑色深得道家之喜爱。也正是这种唯黑论更加幽韵地体现空灵奥妙的中国传统内涵。[13]
在兵道服饰的色彩运用过程中,应该注重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等的文化差异,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色彩在优良与善恶评价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色彩在不同观念下夹杂而生的多层次象征意义,可以为众多问题的思考提供相应的临界参照价值。只有对一种色彩拥有深厚广泛的了解与研究的人,才能区分五彩斑斓的黑与纯净的黑运用在何物上更有意义。
黑色具有一定的消极性,若要变消极为积极,瞬时让人眼前一亮,则需要适当的点缀如,武术兵道的服饰对于体态和外形不够好的人,往往会显得过于沉闷和压抑。那么随着不同的年龄、人群、性别分别加上不同颜色的点缀或亮色涂抹、翻边,则会增添不少意蕴,又或者在墨黑中加一点蓝的甘蓝黑、极浅的烟黑色到炭灰,再到深邃的天鹅绒黑等,就像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般,绵延不绝、此起彼伏、和谐而富有节奏。因此,不避讳黑色的消极因素,反而在其中加入能引起质变的对比搭配,意外地赏心悦目,这本身也是黑色特有的一种“性格”。正如,李以泰在他的《黑白艺术学》中所说:“大块黑中有一小块白,这白会变得犹如白玉般的珍贵,而大块的白中有一小块黑,这黑也会变得更加光彩照人”。[14,15]
时至今日,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多元发展,缭乱的色彩让新时代的“绘者”们目不暇接。黑色作为经由历史岁月沉淀,经久不衰的经典之色,有着其独特的味道。黑色作为百搭之色、调和之色更符合我国“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多边发展理念。难以调和的颜色一旦与黑色搭配,嵌入黑色的深邃或是纯净,就会立马变得和谐起来,甚至别具特色。武术兵道若想在这座竞争激烈的历史“比武台”中巍然屹立,应注意到与黑色相关的经典性意义是其他任何所谓精彩绝伦、妙笔生花的“颜色”都无法替代。
3 结语
服饰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早期物化形式的标志,是人类具象符号的开端,它以穿着方式、服饰外貌、搭配饰物为外在表现形式,反映着不同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及制度形态等内在流动的痕迹。因此,服饰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更在其中渗透着各个时代人类的观念意向,同时也是社会人民三观及民族精神的外显转化。从物质与精神的双向层面上来看,服饰文化在表现国家、社会、民族发展的同时,还具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价值。中国的服饰文化,凝练中国哲学的深厚意蕴,体现着中华人民伟大的物质文化创造力,即“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观念,从而使中国服饰文化远超过基础的实用功利阶段,成为民族精神以及政治社会秩序的具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