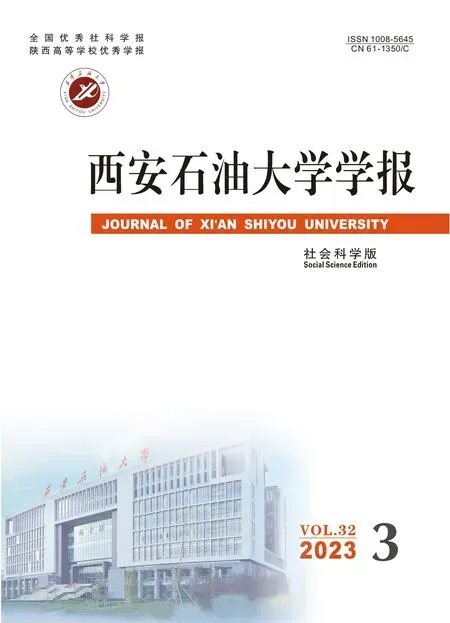论西部文学乡村话语的现代性建构
——以王选《最后一个村庄》为中心
2023-08-15梁增凯
梁增凯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0 引 言
《最后一个村庄》是甘肃青年作家王选的新作,整本书由28个故事构成,共同诉说了“最后一个乡村”麦村的消逝。小说对人物故事的言说满载着现代文明与旧文明之间的二元冲突,象征着旧文明的故乡麦村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被逐渐瓦解,这一方面寄托着作者对不可追回的故乡的惜别,另一方面也承载了作者对势不可挡的现代性的反思。小说从叙事、形式和主题等多个方面展现出作者自觉的文体意识,并以此构建出作者西部文学书写的乡村现代话语。
1 “颓废”的现代性
王选用28个故事建构了一个逐渐被现代文明侵蚀瓦解的麦村,旧的传统行将就木却迟迟不去,终于伴随着最后一个麦村人的离开并不精彩地落下帷幕。整本小说的叙事都散布着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气质,作者把麦村最后的辙乱旗靡一一呈现,这似乎是为旧文明书写的时代挽歌,却与现代性相去甚远。王德威认为现代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颓废”的话语建构中迂回而生的:“所谓‘颓废’(decadence)包括却并不止于该字眼鄙薄的意涵——一个过熟文明的腐败与解体,以及其腐败与解体之虚伪甚至病态的表现……‘新’意又将从何而生?颓废即是将正常异常化,并且暗暗地预设在所有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中。”[1]32在王德威这里,看似颓废的没落书写成为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现代性武器,能把旧文明中的伦理道德秩序置于陌生化地位进而将其击碎。在小说中,麦村的28个家庭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毫无招架之力,村民或逃离村庄去城市里寻找出路,或斡旋于旧传统的瓦解之中,更有甚者在孤独绝望里期盼着死亡的召唤。作者极力描绘村民面对现代文明的无力感,就是其言说现代性之不可抗拒的方式,进而传达出小说本身的启蒙特征;但另一方面,作者恐怕也难以认同行将解体的旧文明为“腐败的”和“病态的”的说法,小说字里行间都传达着他对故乡村庄的怀念与追忆,作者也毫不吝惜笔墨来描绘旧文明的淳朴与真挚,对他而言,或许故乡麦村只是因为脚步太慢而被这个时代遗弃,却不会因其“腐败”和“病态”而被剪除。
“颓废”的现代性书写是作者乡村现代话语建构的一种文体自觉,借由这种颓废书写的总体基调,小说呈现出大量现代文明与旧文明之间二元冲突的样貌,这些冲突首先体现在“从前-现在”的时间对立上,进而体现在作者随时间而变的叙事方式上。
先说前者。时间维度的乡村现代话语建构体现着作者“颓废”现代性书写的文体自觉。李欧梵把“现代性”表述为一种时间体认方式:“在这个新的时间表里,‘今’和‘古’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新的重点落在‘今’上,‘今’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将和过去断裂,并接续上一个辉煌的‘未来’。”[2]53-54在李欧梵这里,对时间维度的现代性认识似乎体现着一种社会达尔文的进化概念,但其言说更传达着一种通过时间切割而形成的“古”“今”二元对立关系,倾覆旧时间的现代性掌握着价值标准的制高点,又通过其存在的合理地位指涉着文明进化的光辉未来。小说呈现了多种形式的时间对立,这些对立首先体现于小说故事的时间结构,其次是故事言说的时间线索,最后是叙事语言的用词自觉。
首先,小说的28个故事在时间逻辑上体现为由从前到现在的编排顺序,并以自己现身的第11个故事《骑马要骑花点点》为界限,把从人口中听说的故事过渡到“我”所知所见的故事叙述当中,此时“从前/现在”的时间冲突转化为“虚构/非虚构”的叙述冲突,把传闻中现代性的破坏力拉到现实当中,将现代性书写提到更高的感受维度,从而使现代性获得亲临感和压迫感。其次,故事言说的时间线索和叙事语言运用是共同完成的,作者依靠大量的时间转换词语来安排故事的时间倒错,从而使故事叙述在时间冲突中获得张力。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时间词,“x年前”“x年后”“后来”等等贯穿于小说叙事,其中又以“多年以后”一词的出现频率最高。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通过大量时间词汇的使用,作者打破了故事的线性时间逻辑,把不同时间的故事并置起来看,使得“从前/现在”的时间冲突转化为事件或状况的冲突,更能够突显出现代文明对麦村人的冲击,形成更强的叙事张力。在《燕儿燕儿吱吱》中,一个“四十多年前”把读者拉回青年赵世杰在麦村当农民的情境中,进而回到现实,当已然是城里人的赵世杰宣称“城市,让生活更糟糕”[3]121的时候,人物高傲的性情变质,使得新旧文明的冲突在乡村颓废书写的时间维度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作者还通过文字游戏为小说创造出一种“未来感”。在《日头日头晒我着》中他说:“耕田,1960年生,六十六岁。”[3]36如此算来,如今至少是2026年了,可书籍出版时间为2021年,可知作者有意通过文字时间游戏来呈现一种现代性表达。
再看后者。按照时间逻辑编排的28个故事,在整体结构上呈现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间分区,不同分区的故事叙述有着不同的叙事方式和风格。孔帕尼翁从莫利尼埃的观点出发,认为“它(风格)一直与内容的形式(说理衔接)和表达的形式(形象及文本分布)相关。如此一来,便是主题(内容之形式)中有风格,风格(表达之形式)中有主题了。”[4]178作者面对不同的叙事内容转换着“如何写”的叙事方式,并通过将故事叙述和内容指涉相统一,体现出其自觉的文体意识。全书以第11个和第24个故事为界限,将叙事时间区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部分,又以“说书人”模式、参与式讲述和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来与之对应,然而三种分区和三个讲述模式却共同诉说着一个行将就木的麦村的“颓废”主题。
从叙事学角度看,“我”是全书的同故事叙述者,一方面作为故事的讲述(复述)者,另一方面又是小说故事中的人物,“我”通过不同讲述方式把28个故事分区,又作为线索把28个故事串联起来。第一,在前10个故事中,“我”还是小孩子,只能通过“听说”的方式得知故事内容,读者或通过“我”转述,或通过一种在场的形式和“我”共同聆听他人讲述。《彩凤开花在三月里》中,讲述人“我”说“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可那时“我”可能还未出生,所以并未在故事中出现,那么“我”的讲述只能是转述;《喝喊一声绑帐外》中描述赵贵子夸张的擤鼻子动作后,“开始了他情绪激昂的讲述”,而此时,读者和“我”一同到场听起故事来。对故事来源几经倒手的说明,强调出故事时间上的遥远和不可靠,由此给麦村人物的故事套上一层缥缈的神话外衣。第二,从第11个故事起,“我”开始描述自己的所见所知,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大多是“我”的同侪友人,“我”或参与或感受着他们的生活,这样的叙述把故事拉到读者面前,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因此,当现代文明冲击着阳刚、康辉等人的生活时,“我”能带领读者对“现代性”做出最直接的感性判断。第三,从第24个故事起,无论是从故事的叙述方式、故事的荒诞性还是故事的叙事元素来看,小说都打破了现实主义的去真实呈现世界的讲述方式,进而以一种荒诞的、意识流的或者泛神论的叙述方式来呈现麦村人的故事。于是,村民看见过世的“赵贵子在核桃树下飘起来”;槽头里的驴说了人话,揭发了赵拜天和草红上床的事;赵平梦游去过所有离开了麦村的人家,玉珍为了寻梦游的赵平困在了山神的梦里……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都以过去式的姿态叙述出来,却无一不指向未来,满载着作者对麦村或者旧文明未来的思考。三种叙事模式把故事上的线性时间切割开,一方面借由麦村落幕的颓废叙事来展现作者的现代性思考,另一方面,这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本身就以其现代性特征来呼应其内容表达。
小说的颓废叙事中孕育着萌发的现代性特征,麦村人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无力招架,作为“他者”被公开处刑,旧的文明传统被置于陌生化地位,接受着现代文明的审判。作者以“颓废现代性”为主题基点,从时间维度和叙事模式两个层面来建构乡村现代话语,展现出其现代性书写中自觉的文体意识。从另一个方面看,小说叙事在时间上的对立所创造的并置结构以及由叙事模式的切割所呈现的多层时间结构,呈现出作者现代性书写的空间样貌,因此也呼唤着一种叙事结构的空间诗学阐发。
2 现代性与空间叙事
小说从时间对立和叙事模式的转换两个维度共同诉说着故乡麦村正在落幕的颓废主题,并从中体现出作者对现代性的思考及其自觉的文体意识。作者在故事叙述中对“过去/现在”时间的对立分割和重组,以及面对不同时间分区所转换的叙事模式,创造出大量并置的空间样貌。在近年文艺理论空间转向的背景下,作者在小说中所呈现的空间叙事也应是其现代性书写的尝试之一。从结构形式上看,全书呈现出一种“主题-并置”的空间样貌;从空间诗学角度看,作者借“城市-乡村”对立的地理空间书写来隐喻现代文明与旧文明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权力关系对抗。
2.1 “主题-并置”的空间叙事结构
《最后一个村庄》作为一个由28个小故事组成的叙事文本,应该被定位为一本松散的小说集,还是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呢?龙迪勇认为此类文本应为完整的叙事作品,并将其结构方式命名为“主题-并置”叙事。何为“主题-并置”叙事?龙迪勇认为:“其构成文本的所有故事或情节线索都是围绕着一个确定的主题或观念展开的……从内容或思想层面,我们可以把这类叙事模式称之为主题或观念叙事;从形式或结构层面,由于它们总是由多个“子叙事”并置而成,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并置叙事。”[5]27进而“子叙事”是统一于“主题”这个相当于总空间的“场所”,所以主题-并置叙事就是空间叙事。在《最后一个村庄》里,28个故事共同言说着麦村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瓦解的“颓废”主题,从思想层面看,全书的“颓废”主题一以贯之;从形式上看,28个故事作为小说的“子叙事”各自独立,又共同承担着主题言说的责任。由此看来,《最后一个村庄》在形式上是一种主题-并置的空间叙事结构,但是深入文本细部,又会发现小说中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并置形式。
首先,小说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主题-并置形式,在作为“子叙事”的故事和“颓废”主题之间增加了一个时间分层,从而形成了“主题-分区-子叙事”的三层叙事结构。28个故事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逻辑,但是却存在一定的时间分区。从第11个故事起,由于“我”的成年,故事获取方式逐渐由听说向在场转移,故事讲述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从第11个故事起,小说内部出现了“从前/现在”的时间分区,“子叙事”也在不同分区内部以不同的叙事模式讲述着麦村的没落故事。如果从故事的时间指涉上看,小说从第24个故事开始以泛神倾向的荒诞叙事言说未来,于是小说整体则呈现出“从前/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分区,时间分区和子叙事各自之间都呈现出一种并置关系的空间样貌。
其次,故事讲述前的词曲引用与故事之间的并置关系。每个故事开始之前,作者都有一段词曲引用,这些词曲包括儿歌、山歌、民歌、童谣和秦腔等形式,这些歌谣和戏曲的选择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它们与故事也存在一层对应关系:“让歌谣和我所写的故事融为一体,或者说,你读完了一个故事,回头再看开头的歌谣,发现这首歌谣,已经把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结局包含在里面了。”[6]小说中的歌谣和戏曲如同“楔子”,与故事共同传达着相同的主题且相互指涉,一起构成文本叙事。《最后一个村庄》中词曲楔子与故事是一种并置关系,呈现出彼此独立又统一于主题叙事的空间样貌。此外,歌谣和戏曲的运用也体现出作者故事叙述的文体自觉,承载着家园文化的歌谣和戏曲的频繁出场,一方面传达出作者对不可追回之故乡记忆的惜别,另一方面又隐含着新旧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
最后,时间倒错的叙事手段使得故事情节处于并置关系之中,这也体现出作者现代性书写的叙事自觉。时间倒错指的是通过打破故事的线性时间逻辑,重新排列情节的先后顺序。书中的时间倒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同一故事不同时间情节的空间并置;二是同时发生情节的空间并置。先看前者。同故事的时间倒错安排是当代小说常见的叙事手法,前文提到的《燕儿燕儿吱吱》中,赵世杰四十年的前后变化由一个时间词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两种时空并置的样貌。《星宿星宿挤眼哩》中展现出更加成熟巧妙的时间倒错而成的时空并置结构。作者通过“我”念法院判决书,把赵虎皮在赵贵子家耍酒疯并杀害马彩菊的场景还原出来,其中杀戮的血腥场景则省去现场描述转而以法院书文的客观文字代替。在时间上,赵虎皮杀人发生在前,念法院判决在后,但是通过时间倒错叙事的手段,把“当时”和“当下”两个时空场景并置起来,共同完成了还原赵虎皮杀人的叙事任务,打斗场面的血腥和法院公文的冷静形成激烈的时间和情感冲突,场景切换一如电影蒙太奇叙事,充满现代感。再看后者。同时空情节并置以《喝喊一声绑帐外》最为典型。豹子以一敌十的打斗场面与秦腔《斩单童》在同一处所同时进行,台上“喝喊一声绑帐外”的唱腔一起,台下豹子的打斗也开始了。于是一句台上秦腔唱词,一段豹子台下打斗的场面描写,二者交替进行,伴随着台下看戏者的不断叫好声,秦腔表演、豹子打斗、作者叙事三者都达到了高潮。作者通过看、打、写的交融制造了强烈的叙事冲突,其所依靠的就是空间并置的叙事模式,实则不难看出这段描写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农场竞卖场景在叙事方式上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追求写作思路的现代性尝试和运用空间叙事时自觉的文体意识。
作者在全书的结构安排和故事的叙事结构两方面匠心独运,创造出大量的文本空间样貌,从形式上展现出小说结构的现代性特征,以及作者叙事言说的自觉的文体意识。文本外在形式的空间建构指向内容和主题,于是要进一步思考文本内容中的空间建构是如何能够触及乡村现代话语建构之现代性内核的。
2.2 “城-乡”对抗的空间诗学分析
作者在小说中建构出麦村这个地理空间,并以“村庄概况”作为小说叙述的开始,来增强小说的非虚构感和现实感。麦村作为“我”的故乡,是作者地理空间建构和叙事言说的起点。此外,作者又将我国西部传统文明中的道德伦理、乡俗礼仪、生产方式等文化要素移植到麦村,使麦村的存在获得一种人文地理的赋义,于是麦村不仅被建构成一个可知可感的乡村地理空间,还因此获得了一种符号学意义,它在叙事中既表现为麦村的自我指涉,又可作为我国西部落后乡村的一种广泛虚指。另一方面,作者还建构了一个与乡村地理空间相对的城市地理空间,来作为与旧文明形成二元对立关系的现代文明的表征。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并非一定步调一致,但在小说中,兰州等城市地理空间一方面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瓦解旧传统的现代文明意义,于是小说中的城市地理空间建构兼具着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在小说的28个故事里,城市空间在文本叙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也暗含着现代文明对乡村旧文明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的文明力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乡村空间的文化传统逐渐瓦解,最终随着最后一个麦村人的离开同乡村一起被倾覆。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呈现出一种二元冲突的权力对立格局,此时文本中的空间建构脱离了地理意义的束缚而获得形而上色彩。空间并非不言自明,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是生产的结果,它超越了事物存在的容器属性而体现为一组关系:“空间作为一种产品,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一种事物或物体——而是指一组关系。”[7]前言22两种空间内部各有一套自洽的经济、文明的话语形式,二者以人的行动为界限相互关联又相互冲突着。小说把言说的重点放在了麦村旧文明逐渐瓦解的“颓废”言说上,而瓦解麦村传统文明的,正是日渐茁壮的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一方面,现代文明为乡村人开辟了生活的出路,也满足了其现代生活的欲望。《玉米地里的高粱花》中,阳刚和杨翠儿的自由恋爱需要在城市里才能实现,而在乡村里没什么机会做的烙猪油盒成了他们在城里谋生的手段;《奇哉怪哉》中赵闰生的女儿嫁得城中“贵婿”,自己也跟着发了财,获得了十足的快感;《云朝西》里赵天依靠学习落户城市,摆脱了身不由己的旧家庭……另一方面,现代文明也为一部分人造成了生活困扰甚至敲响丧钟。《古今古,打老虎》中赵平赵安两兄弟在城市中富裕起来,可当失去了乡村里老人的纽带二人却逐渐反目;《二月二晴》中随着儿孙的进城,贵禄老汉成为空巢老人,在孤独中选择自吊而死……《最后一个村庄》里,更多的是描绘麦村人面对现代文明的无力感,从第11个故事开始,现代文明逐渐消解着麦村传统文明中的家庭伦理、孝悌礼仪、婚俗……或许城市文明为落后的乡村人打开了一条幸福大门,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文明冲击,更多的乡村人表现出的是不适感和无可奈何,在守旧与迎新的斡旋中,麦村人消失在麦村。
麦村的年轻人离开乡村去城市谋求出路,老人或随儿女而去或老死家中,在城市扑面而来的现代化中,乡村人失去了旧时的生活节奏,只得在现代旋风中打转。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力量最终彻底击碎旧的乡村文明,乡村空间也在这个过程中随之瓦解。从麦村人的故事结局中可以看到,现代力量并不一定能够引导乡村人走向圆满结局,而在湍急的现代洪流中,人亦不能停下脚步。《正月里的冻冰立春消》中,赵善财的两个身份都在现代文明中被消解:主管婚丧大事的身份在年轻人摆脱乡村后丧失,赤脚医生的身份被城里的医院所瓦解。“一种遗弃感,让他七十多岁的光阴,日渐窘迫和黯淡”[3]84,被“遗弃”可能就是脚步慢于时代之人的命运,旧的乡村文明与乡村空间一同在颓废中黯淡,但另一方面,城市空间伴随现代文明却正冉冉发亮。
3 现代性的启蒙:异质的性别身份隐喻
小说颓废叙事的精神内核指向旧文明落幕后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文明对乡村传统的瓦解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从开端到倾覆的过程。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文化的此消彼长,旧的文明被拖下神坛从神性向世俗性过渡,而此世俗性具备三个特征:世俗化的公共空间、信仰及其实践的衰落、形成新语境。[8]27旧的文化传统“去神化”的开端必然会经历一个异质过程。作者以其自觉的文体意识,在小说开篇的故事中以人物性别身份的异质建构,来隐喻旧的文明传统的异质开端,以及现代文明的悄然而至。
小说的第一个故事《粉红衫儿青丝帕》讲的是海明娃的去世。海明娃何其人也?他有两个本领:一是绣鞋垫,二是打山歌。他是村里唯一一个会绣鞋垫的男人,女人见了都“恨老天把自己生得心笨手粗”;他会打山歌,村里男女都不会,没他社火集会办不起来。海明娃不爱和男人们在一块,“就喜欢钻进女人堆里”,虽然他女人缘好,却一直打光棍儿。作者给予作为男性的海明娃更多的女性特质,使得海明娃成为一个被阉割的男性身份。罗兰·巴特认为:“象征领域不在生物学的性别,而在阉割:在阉割/被阉割、主动/被动的领域。”[9]106巴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人物的性别身份(而非生物性别)的主动建构,从而理解小说人物的关系,而且每一个人物的性别特征都有其象征指向。故事中海明娃作为男权中心文明的男性角色,失去了雄伟、粗犷的男性特质而被气质阉割,这本身就象征着男权中心的旧文明已然失去旧日的权威地位。海明娃跟女人扎堆,又死于女人的玩笑,这也就意味着海明娃所代表的旧文化传统的下场。而作者并非没有为海明娃被阉割的男性身份做一次补全的尝试,海明娃在集市与名叫妹妹的女性相遇相爱,可最终二人却没能走到一起,因为海明娃被女人们抛着玩时捏碎了蛋,摔折了腰。这也就象征着旧文明卷土重来的尝试最终破产,现代文明的到来势不可挡。
在第二个故事《魇子魇脖子》中,作者又塑造了一个与海明娃相对的、极具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赵翠叶。与海明娃被阉割的形象不同,赵翠叶承担着一个“主动”的“阉割手”的身份建构,她被赋予了强势的男性气质。首先,赵翠叶结婚不出嫁,而是挑上门女婿;其次,家庭中男性能力的不足,“反而让她变成了一个男人。她耕地、撒籽、施肥、锄草、收割、驮运、打碾、晾晒、粜卖。偶尔,太苦太累,她窝一肚子气,没处撒,也会把马猴揍一顿。”[3]17马猴就是她的上门丈夫。赵翠叶身上所体现的男性气质,也是旧文明异质的表现,当女人成为乡村家庭的顶梁柱,她就担负起了传统文明的主流话语,而马猴则只能承担一个唯唯诺诺的外村闯入者身份。此外,文中对马猴的描写为赵翠叶“男气”的女性身份建构起到了衬托作用:他站直了不如扁担高,瘦,说话叽里咕噜说不清。但就是这样的男性形象却借着现代文明的东风翻身做了主人——马猴去城里搞拉煤生意发了财。此时,马猴“闯入者”身份中的潜力与赵翠叶依靠农事吃饭的乡村传统文明特质区分开来:“麦村人老实、胆小、笨拙,稍微做点手脚,就心虚、腿抖”[3]20,而马猴“艺高人胆大”,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也就是投机倒把。可以看出,旧的文明传统中力量、淳朴、厚道等这些特质成为乡村人发财的拖累,已然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而马猴依靠投机倒把却赚得盆满钵满。虽然现代性与投机倒把并不一定直接关联,但是,在两种文明话语的激烈对峙中,原地踏步只能被时代所落下。赵翠叶及其象征的旧文明传统,只能成为麦村最后的守望者,等待现代文明的冲击。
小说打头的这两个故事都将目光聚焦于异质的性别身份的书写,这体现出作者乡村现代话语建构的文体自觉。人物异质的性别身份一方面造成其不可避免的苦难结局,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村文明现状的隐喻,指向一个及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文明未来。实则小说中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村中,人物的性别身份和性别地位发生逆转的例子还有很多,尤其以男女家庭伦理秩序的变异最为明显。《菜籽开花渗金黄》中,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渗入,村里人逐渐都进城谋求出路,赵望祖的老婆李粉香也不例外。李粉香在城里由端盘子发展为经营一家理发店,可她却并未告知留守麦村看管儿女的丈夫,“李粉香也不会给他说这些,觉得说了也毫无用处。她多少从心眼里有点瞧不起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3]220此时,往日男权中心文明下的女性李粉香,在城市文明的加持下从思想和地位上双重压制住了丈夫,这段婚姻也只能以离婚草草而终。李粉香作为现代文明既得利益者,与其说与赵望祖离婚,不如说是与旧的乡村传统割离,城市现代文明在这场新旧文明对峙中轻易获胜。作者对李粉香女性身份地位改变的言说,并没借用过多的性别修辞来增强人物主体的异质特征,而是从事件过程出发,来描绘文明对峙中此消彼长的能量势头,因此故事少了一些隐喻意义而更加突出其现实感。
小说中的故事全部指向一个颓废主题,通过描绘麦村人不同的惨淡收场来隐喻旧文明的大厦将倾。小说开头的两个故事就是作者对旧文明开始溃烂的寓言,正如王德威所言:“颓废即是将正常异常化,并且暗暗地预设在所有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中”,海明娃和赵翠叶性别身份的异质建构,正是作者打破旧文明常态并将其陌生化的现代性书写的体现。
4 余 论
《最后一个村庄》是作者直面我国西部农村现代转型问题而撰写的小说,小说一方面以颓废叙事展现着旧文明的土崩瓦解及让位于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承载着作者诚挚的故乡家园情感,并通过每一个麦村离去的背影与故乡惜别。小说第28个故事《去博物馆看故乡》中,“我”的故乡麦村已然成为历史,只能通过建造博物馆的形式将其保存,现代文明是击垮乡村文明的外来力量,最后又只能依靠现代文明的经济方式来把故乡保留下来,以供“我”和后代参观追忆。实则后代已然对“故乡”失去概念,当孩子询问什么是故乡时,“我只能搪塞给他一个世故而含糊的答案:故乡,就是回不去的地方。”[3]381“故乡”之所以难已解释,是因为此刻故乡已经由一个感受的集合转变为冷冰冰的概念,可故乡永远是“个人的”,如何用知识的方式去传递一段感性经验呢?所以,当“我”故地重游,“我只能以一个游客的身份,看到我们暗淡的过往”[3]392,故乡只能是回不去的地方。
作者在小说中寄寓了浓厚的追思情感,对望回不去的故乡大有兰波“生活在别处”的存在主义反思,但作者并未止步于追忆与叹惜,而是走得更远。小说在颓废叙事中重现了大量的传统文明内容,作为故乡的历史记忆保存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瓦解的故乡文明期待着一次现代性的转型和重构,而这些存留的历史文明则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养料。王选认为这本书有三个意义:一是缅怀故土,二是保存记忆,三是照亮未来。[6]小说中的歌谣和戏曲承载着故土文明中的文化记忆,西部传统的婚丧礼仪、伦理道德也通过大量的故事情节保存了下来。西部乡村在20世纪末经历着大量人口流失等“症状”,农村留守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这是农村现代化改革必须要经历的阵痛。王选说看见了“最后一个乡村”, 乡土重建才会行以致远。在国家精准扶贫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下,一个现代的西部农村景象或已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