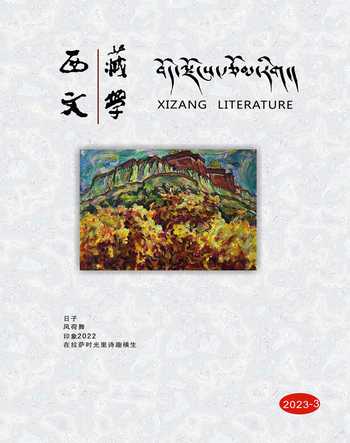墨脱往事(外一篇)
2023-08-09张祖文
张祖文
父亲和生产队长
父亲是从我读大学那年开始干生产队长的,前前后后一共干了23年。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是我们那个家族,上上下下几十号人中,唯一带“长”的一个人。
父亲干生产队长那年,刚好上一任队长生病,是痨病,走路都喘气,没办法,只好让贤。但老队长虽然病了,却不想完全放手,便找到了父亲,并向村里推荐了父亲。
之所以推荐父亲,主要是因为父亲老实,还不识几个字。那时的农村,也没多少事干。老队长的算盘,是找个人在前面跑跑腿,而队里的大盘小事,还是他说了算。因为他吃定了父亲什么都不会干,他说的自然也就不会遭到反对。而且,生产队长的活,都是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几乎没有收入,稍微能干的人,随便在外面馆子洗几天碗,都顶得上队长一年的“工资”了,所以,也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干。
记得当时父亲的确也犯了嘀咕,认为自己干不下来。但架不住我当时已经考上了大学,还是第一届要交学费的大学,家里因为这事几乎被掏空了,一听说干队长还有“工资”,也就动 心了。
但其实所谓的“工资”,只是村里发给各个队长的茶水费而已,而且每月只有区区的5 块钱!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還有老队长在背后指点,自己也就跑跑腿,应该不会太辛苦,在父亲的心里想的,这5块钱几乎就相当于白捡了。所以父亲就走马上任了。
没想到,这一干居然就是23年!
刚开始时,父亲连生产队基本的表格都不会做。老队长开始还耐心指导,后来却也烦了,常常借故推托。在面对权力时,人可能就是这样,刚丢弃时,也许有点舍不得,还想发挥发挥余热,时间久了,就会真的觉得那东西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不再是自己的了,这时再干,就会没有任何动力。
父亲便只能找我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姑父来帮忙。姑父说有文化,其实也没有比父亲多读几天书,只是因为一直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干会计,多少比父亲懂一点,业务上熟一点,所以两人便经常在忙完地里的活后,加班加点干生产队那点事。
时间久了,父亲对手面上的事情倒已基本上能应付了,但生产队虽说是社会组织架构中最小的细胞构成,却毕竟有几十户好几百号人,邻里之间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远非平常人所能想象,父亲后面业余的大部分时间,便都耗在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各种纷争之中。好在父亲是个老实人,解决问题从来没有什么私心,大都处理得不偏不倚,便没有惹到什么大麻烦。当然也有一些当时有怨言的,但时间久了,也会发现父亲是真的在秉公办事,也就没什么话说了。
没想到没什么文化的父亲,倒把一个生产队搞得不错,谈不上风生水起,但至少没出什么事。要知道在农村,即使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是翻天覆地。农民的素质这些年是有所提高,但农民的秉性改变并不是十分明显。面对任何侵犯自己“领地”的行为,很多时候都会做出明显过激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一个土生土长而且左右逢源的人,真是很难摆平的。
没文化的父亲居然干稳了生产队长,这让我一个有文化的叔就有了些不服气。
那个叔是改革开放前的高中生。虽然那时的学生主要还是搞生产,没学到什么真正的文化,但因为整个村子都没几个,所以仍然很是金贵。叔高中一毕业,父亲就从家里扛了几麻袋花生,通过他一个在公社供销社当主任的姑父,找到乡里中学校长,将叔送进学校当了代课老师。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使是代课,也是吃公家饭了,比普通农民当然是强上了千百倍,会引很多人羡慕的。叔也因为这羡慕,一去学校后就有了些张狂,自恃高中学历,不太服学校管教,后来更因为与校长起争执,直接在校长的床上拉了几堆屎!为人师表,做出这等粗鄙行径,这还了得!叔当即就被学校开除,又成了农民 一个。
好在后来改革开放,打工机会多了,叔便携家带口,外出打工。在广东,他帮了一个老板很多年。我开始不知道叔在那里是干什么,后来才得知是专门用死猪肉做香肠、腊肉,那些肉臭了烂了都无所谓,甚至是生蛆了都可以,反正加上大把大把的香料,就什么味都遮住了。叔每年都会回老家,每次回家都会给我们讲他在工厂的事情。这导致我现在对外面卖的什么腊味都完全不放心,甚至是一见了就会有想吐的感觉。
叔在外面漂泊了几十年,也没挣到什么钱,后来那老板的厂还是倒闭了,没办法,只好又回到了老家。
一回家,叔动的第一个心思,就是父亲的那个队长职位。虽说那时生产队已改为了社,队长也改为了社长,愿意干的人还是很少,但叔却不这么认为。
那时我已经到西藏上班了,很少回家。父亲在电话里说,叔一回了老家,就往村里跑,频繁和几个村领导联系,还动不动就请他们到家里喝酒吃饭。
我听了,便对父亲说,他是想当村长吗?
父亲说,当村长肯定要找乡里啊。
哦,就队长?那不是想你的位子吗?我便对父亲说,反正你们是亲兄弟,不是外人,叔又的确比你有文化,那你还不如让给他算了。
听了我的话,父亲却不言语。
我以为父亲是舍不得这队长的位置。毕竟,干了十几年了,我每次回家,明显感觉到父亲身上好像真的有了一些“官架子”,说话做事和我以前记忆中的样子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差别。比如说话,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就会端着,不轻易发言,更不会轻易表态。父亲的这些变化,我是真看在了眼里。一方面觉得他可爱,另一方面又为他担心,害怕他对那个生产队长的名号越来越恋栈,变成一个“官迷”。好在父亲后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也就不再担心。只是劝他,毕竟年龄越来越大了,生产队长的活也越来越繁琐,能放手就放手,别累着自己了。
但父亲却对我的建议不置可否。
一次回家,村里正在换届,十几个队长也要重新选举,我便又劝父亲,反正我都工作这么多年了,家里也不缺他干队长的那点钱,不如激流勇退,让叔干算了。
父亲却沉默了良久,才叹了口气,说,就是我不干,他也搞不成的。
我有点吃惊,不明所以。
父亲却说,你叔不踏实,野心太大了,人家不会相信他的。
我回家那段时间,看叔很忙,经常往队员家里跑,一看就明白去干什么了,有时手里还会拎着一些花生萝卜之类东西,跑得很勤,还不避讳,好像志在必得。
我想問父亲为什么也不去跑跑,但想本来就觉得父亲辛苦,不干了也是好事儿,也就没再言语。
没想到的是,选举结果出来,父亲得的票居然高居第一,叔的票却是倒数第一。
父亲便又连任了队长。
后来,又选举了几届,父亲都顺利当选。听说叔一直在进行各种活动,却始终没能选上。
前几年,基层开始搞合村并镇,原有的生产队也合并扩大。村里提了要求,如果合并后还干队长的,工资可以翻一倍多,不再干了的,可以一次性补偿两年工资。父亲一听,马上向村里申请,主动不干了。私下里父亲对我说,能一次性领两年工资,有啥不好呢?合村后,生产队人口翻了一倍,事情也会多很多,应付不过来了。而且现在干队长,动不动就要用微信什么的,他智能手机都不怎么会用,再干实在有点吃力。说到这里,父亲长叹一口气,说,老了,不适应时 代啰。
父亲就这样彻彻底底退了下来。
退下来时,父亲的工资已经是500块一个月了。从最初的5块到500块,父亲真的是走过了一个时代。
墨脱往事
那一年去墨脱,也就是那个全国最后才通公路的县,给我最震撼的不是那里的美景,而是旱蚂蝗。
去墨脱之前,除了知道那里海拔低,只有800米,还没通公路之外,其余的真是一无所知。随行的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去。我们是以调研的名义去的。一到墨脱,发现这里森林覆盖率极高,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既然是调研,当然要城里乡下乱跑,以体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不,在下乡到老百姓家里的路上,就要徒步穿越无数密林中的蜿蜒小径。奇怪的是,我们来调研的都穿得很随意,只有那个带队的本地人,却穿得是严严实实,而且不仅头上带了一顶帽子,还用一条毛巾把脸和脖子都捂得密不透风。我有点不明所以,想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穿扮,也太妖娆太滑稽了,一看到他,就老想笑。但觉得这也许是别人的习惯,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跟着走,强忍着,尽量不去看他。
我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森林中行走,难免有些兴奋,便边走边说,加之作为工作人员,身上还带了一些大部队调研需要的东西,有点负荷,所以不一会儿就热了。时间久了,就开始出汗,而且越出越多,终于大汗淋漓。
我边走边擦汗。虽然汗多,却对身边的美景很是激动。但突然地,我却觉得怪怪的,因为自己的腿不知怎么的,有点痒,好像有蚂蚁在爬一样。开始还没怎么注意,只是挠挠,但后来越来越痒,还明显觉得裤子上浸出了什么东西,湿漉漉的。
在高原上我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秋裤,所以,这是两条裤子。虽然汗出得多,也明显感觉到因为出汗,而导致秋裤也贴在了腿上,但汗再怎么多,也不至于把外面那条裤子也浸透了呀。而且那浸出的东西一看颜色就很深!我猛然觉得不对劲,马上弯腰,卷起裤脚,扯起秋裤的 卷口!
这一扯可不得了!只见一团团黑乎乎、圆滚滚的东西,一下子掉了下来!
我的心一紧!整个人都僵住了!要知道,我是农村出身的,当然知道那从自己腿上掉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蚂蝗!
而且确定无疑!
我老家四川的水田里,以前到处都是这玩意儿。也因为这东西,我一直不敢下水。没想到,在蚂蝗的天堂四川我都能避开的东西,在这里却给碰上了!
只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一直在密林中,根本没下过水田,这怎么就遇上了蚂蝗?
可当时已经顾不上想这么多了!因为恐惧,我整个人马上就动不了了,看着在地上蠕动的那几团让自己心惊肉跳的东西,全身僵硬了,一瞬间时间停滞,连呼吸都没有了!恍若隔世之后,才颤抖着双手,撸起了裤腿!
这一看吓坏了,只见整个腿都是鲜血直流!
而且,还有好几个还在冒血的孔!
除此之外,有好几条正在充血的蚂蝗尾巴,正在使劲往腿里钻!
我对蚂蝗的恐惧立即上来了!整个人如被抽了骨头一般,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全身 无力!
我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同行的人见我如此,都围了上来!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一看,便都马上卷起了各自的裤子!
这一看全都惊恐大叫起来,只见一条条已经吸满了血的蚂蝗也从他们的裤子里滚了出来!所有人都一阵阵惊呼!
这时那带队的见大家惊慌失措的样子,才说,哦,不好意思,出来时忘了给你们说了,我们这里蚂蝗多!你看我这记性!边说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很是遗憾的样子。
可我们谁都顾不上他说的了,都在手忙脚乱地对付自己身上的蚂蝗!一个女生手忙脚乱地拍着自己的腿,上蹿下跳的,尖叫连连,已经完全失控了!一看就是比我还要害怕。另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却一手拍着自己的腿,一手抓住一条正往腿肉里钻的蚂蝗尾巴,大声说,你再钻吧!老子一定要把你扯出来!话音未落,蚂蝗却断了!一截留在了他的手上,另一截却还在 肉里!
带队的见大家这惊恐的样子,连忙说,各位领导,我们现在不必太慌,还是先走出这林子!之后,钻到大家身体里的蚂蝗只要吃饱了,就会自己掉出来的!大家最紧要的,还是像我一样,尽量把自己包严实一点。因为这蚂蝗都在树上,它们会顺着汗味,落在人的头上,再经过头发,经过脖子,进入人体,所以,先把头包一下,让它们钻不进去,就会好多了!
又是一阵手忙脚乱!我连忙把自己的外套脱下,包住了头,把袖臂拴了起来,紧紧遮住了大半张脸,只留了两个眼睛。看身边的人,也大都如此!
然后,一群人如惊弓之鸟,加速往前走!说实话,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在调研的时候,这么迫切地希望快点到老百姓的家里!虽然一想到蚂蝗就会全身发软,但为了尽快避开它们,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硬生生快了起来,真是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不知快了多少!
这次在墨脱的经历,可谓是惊心动魄!只记得到老百姓家里时,我虚脱得都有点怀疑人生,整个人完全散架了,只觉得三魂脱了五窍,我早已不是我了!
这真是令人永世难忘的经历。现在想起墨脱,都不是它那美丽的景,而是那让我毛骨悚然,一条条悬挂在树叶上,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旱蚂蝗。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