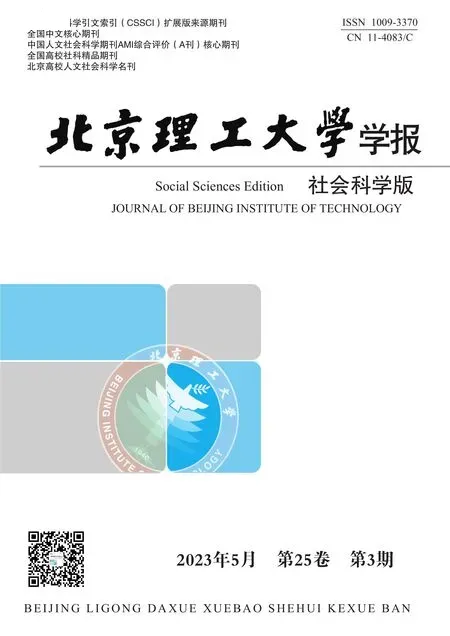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危险性质
2023-08-08李金明
李金明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国涉及正当防卫的刑事案件中,仅约 0.5%的案件被认定为正当防卫(无罪)①笔者对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所有涉及正当防卫的刑事案件判决书进行检索分析,发现1996 年1 月1 日至2019 年12 月31 日,全国涉及正当防卫的刑事案件共有18 768 件24 329 人,被各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正当防卫宣告被告人无罪的仅有104 件133 人,约占涉防卫刑案总数的0.554 %、总人数的0.547 % 。, 凸显司法机关对防卫标准的把握过于严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理论与实务界对理解和认定作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不法侵害存在误解②有关不法侵害的争议问题十分广泛,例如“不法”是何种含义?这涉及客观不法论与主观不法论之争;“侵害”的形式是仅仅包括作为还是也包括不作为?“侵害”是仅限于攻击性、破坏性的暴力侵害,还是也包括平和方式的侵害?“侵害”的法益是仅限于公民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私法益还是也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公法益。本文仅仅探讨不法侵害的性质问题。。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是正当防卫成立的前提条件。从行为的角度分析,不法侵害究竟是指实害行为(即对他人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结果的行为),还是指危险行为(未对他人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结果但是具有造成侵害结果可能性的行为)?或者既包括实害行为也包括危险行为?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否存在。例如,在王某华故意伤害一案③该案的基本情况是:2018 年7 月31 日14 时许,被告人王某华的儿子王某2 爬上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郑某家门旁的一棵龙眼树上摘龙眼,郑某看到后不让王某2 摘,双方均认为该龙眼树是自家的,二人因此发生争执,随后王某华赶到并加入争执。郑某的儿子王某1 见状,便骑电动车将王某华撞倒,王某华随后与王某1 互殴,王某2 见状拿起一把铁铲打王某1。在打斗过程中,王某华看到郑某拿起一根木棍相威胁,遂从郑某手中抢走木棍,并持木棍击打郑某,致郑某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及左顶部头皮挫伤伴肿胀。经鉴定,郑某所受损伤构成轻伤一级;郑某左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遗留左腕关节功能障碍,评定为十级伤残。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华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实施不法侵害的人所采取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本案中,虽然案发时郑某持木棍对王某华造成一定的威胁,但郑某当时并未对王某华实施不法侵害行为,且王某华在已夺过郑某手中木棍的情况下,仍持该木棍击打郑某,王某华的行为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正当性和紧迫性。王某华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仍持木棍对他人实施伤害行为,并造成他人轻伤的结果,综上,王某华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王某华关于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王某华的辩护人关于王某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2018〕琼0105 刑初429 号判决书,审理法院: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中,当郑某手持木棍对王进行威胁时,王夺过木棍将郑某打成轻伤。辩护人认为郑某持棍威胁的行为属于不法侵害,王的反击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而法院认为郑某持棍威胁的行为不是不法侵害,从而王的反击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法官与辩护人对不法侵害的理解不同:辩护人认为危险行为属于不法侵害,法官则持否定意见。对不法侵害的不同理解也会影响对正当防卫时间条件的判断。在昆山反杀案中,关于刘某的侵害行为是否属于“正在进行”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于某明抢到砍刀后,刘某的侵害行为已经结束,不属于正在进行。但也有观点认为,于某明抢到砍刀后,刘某立刻上前争夺,侵害行为并没有停止①该案的基本情况是:2018 年8 月27 日21 时30 分许,于某明骑自行车在江苏省昆山市震川路正常行驶,刘某醉酒驾驶小轿车(经检测,血液酒精含量87 毫克/100 毫升),向右强行闯入非机动车道,与于某明险些碰擦。刘某的一名同车人员下车与于某明争执,经同行人员劝解返回时,刘某突然下车,上前推搡、踢打于某明。虽经劝解,刘某仍持续追打,并从轿车内取出一把砍刀(系管制刀具),连续用刀面击打于某明颈部、腰部、腿部。刘某在击打过程中将砍刀甩脱,于某明抢到砍刀,刘某上前争夺,在争夺中于某明捅刺刘某的腹部、臀部,砍击其右胸、左肩、左肘。刘某受伤后跑向轿车,于某明继续追砍2 刀均未砍中,其中1 刀砍中轿车。刘某跑离轿车,于某明返回轿车,将车内刘某的手机取出放入自己口袋。民警到达现场后,于某明将手机和砍刀交给处警民警(于某明称,拿走刘某的手机是为了防止对方打电话召集人员报复)。刘某逃离后,倒在附近绿化带内,后经送医抢救无效,因腹部大静脉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于当日死亡。于某明经人身检查,见左颈部条形挫伤1 处、左胸季肋部条形挫伤1 处。检例第47 号,https://www.spp.gov.cn/spp/jczdal/201 812/t20181219_40292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18 日。。前一观点认为于某明抢到砍刀后,刘某的侵害行为已经结束, 是因为此前刘某用刀面击打于某明颈部等身体部位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已经结束。该观点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后一观点认为于某明抢到砍刀后,刘某的侵害行为并没有停止, 是因为其认为不法侵害包括危险行为,刘某的实害行为虽然已经结束,但他在于某明抢到砍刀后立刻上前夺刀,表明刘某对于某明的人身伤害危险并没有结束。对不法侵害的不同理解会影响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判断。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中国通说采用的是以必需说与基本相适应说为基础的折中说,认为原则上应以排除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在手段、强度、后果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1-2]。根据折中说,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时,需要对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进行比较,考察二者在手段、强度、后果等方面是否存在明显失衡。此时,如果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就会把不法侵害人造成的实际侵害结果与防卫人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进行比较,往往得出防卫过当的结论;如果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危险行为,则会把不法侵害人可能造成的侵害结果(侵害危险)与防卫人实际造成的损害结果(防卫结果)进行比较,往往得出正当防卫的结论。以昆山反杀案为例,于某明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有意见提出,于某明本人所受损伤较小,但防卫行为却造成了刘某死亡的后果,二者对比不相适应,于某明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②检例第47 号,https://www.spp.gov.cn/spp/jczdal/201 812/t20181219_40292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18 日。。显然,该观点将不法侵害理解成实害行为,将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实际造成的挫伤结果与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实际造成的死亡结果进行比较,得出防卫过当的结论③实务中有不少司法人员在防卫过当的判断中,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例如在叶某朝故意杀人案中,被告人叶某朝因向王某追索餐费遭到寻衅报复,当王某持刀砍向叶的左臂和头部、郑某用凳子砸向叶的头部时,叶持刀还击刺死了王、郑二人。关于本案能否适用特殊防卫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不能适用,理由是被告人受到的是轻伤,说明王某、郑某的侵害行为没有达到严重危及叶某朝的人身安全的程度。该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误以为不法侵害就是侵害人对防卫人所造成的实际侵害结果,本案中就表现为王、郑二人对叶造成的轻伤结果。将此轻伤结果与被告人给对方造成的死亡结果相比较,当然会得出防卫过当的结论。但是,如后所述,不法侵害属于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所以应当考察不法侵害行为可能对防卫人造成何种侵害后果(即危险),而非仅仅考察侵害行为实际对防卫人造成了何种后果。本案中,由于两名侵害人用刀和凳子攻击叶的要害部位(头部),所以,应当认定该侵害行为具有致叶某朝伤亡的可能性,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应当适用特殊防卫的规定。防卫人仅受到轻伤,正是防卫行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才出现的减轻效果,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侵害行为不严重的结论。[3]27-28。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实害行为也包括危险行为,对于危险行为同样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刘某的行为因具有危险性而属于“行凶”的前提下,于某明采取防卫行为致其死亡,依法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于某明本人是否受伤或伤情轻重,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没有影响④检例第47 号。。该观点将不法侵害理解为既包括实害行为也包括危险行为,从而得出不同结论。对不法侵害性质的理解分歧,会导致对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不法侵害的性质:实害行为还是危险行为?
理解不法侵害的性质,在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大体上包括实害行为说、危险行为说、实害或危险行为说三种主张。实害行为说认为“侵害”是客观上会给社会带来某种物质危害后果的行为[4]。有学者从词源意义上分析,认为“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5]。该说强调不法行为对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的结果。危险行为说认为所谓“侵害”是指对于“他人的权利”(法益)带来侵害的危险[6]。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侵害,是指可能造成实害的行为,是一种可能造成实害的预测[7]。该说主张作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仅仅是一种可能给他人法益造成实害危险的行为,而非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实害或危险行为说,认为所谓“侵害”是指对他人的权利造成实害或者危险[8-9],或者是对法益具有侵害或者威胁的行为[10]。按照实害或危险行为说,不法行为无论是对法益造成实害结果还是仅仅带来一种危险状态,都属于不法侵害,都可以成为正当防卫的对象。
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应指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
(一)基于法律救济体系的分析
只有将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置于整个法律救济体系当中予以整体考察,才能得出妥当的解释结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为了解决这些冲突,必然需要一套纠纷解决机制。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解决纠纷和冲突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公力救济是指权利人通过法定程序请求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对其权利进行保护的一种方式。典型的公力救济有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11]。典型的私力救济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救行为。社会救济是指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一定的社会力量来防止和排除侵害,以保护和补偿公民合法权利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它介于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主要借助社会力量来保护、补偿或纠正受到侵害的合法权利[12]。典型的社会救济有调解和仲裁。刑法正当防卫制度主要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制度相关,而与社会救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本文主要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角度来探讨。
从历史来看,私力救济的出现早于公力救济。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没有国家和法律,私力救济是解决人们纠纷的唯一方式。 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出现,私力救济逐渐被公力救济取代和限制。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而相互交错的过程[13]。人们一般认为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公力救济占居主导地位,而私力救济则起补充或辅助作用。当权利即将或已经受到不法侵害时,只有在通过法律程序、依靠国家机关不可能或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法律才例外地允许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侵犯者或其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施加强力影响,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简言之,私力救济是公力救济不济时的一种救济方法。
根据救济行使时间的不同,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可划分为事前救济、事中救济和事后救济①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 条第1 项规定,对扬言杀人者予以行政拘留,从而避免一起杀人案,这就属于事前公力救济;小偷正在实施盗窃行为时被警察当场抓获,属于事中公力救济;抢劫犯实施完抢劫行为后被法院判刑,属于事后公力救济。。就私力救济而言,事前私力救济是指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之前,权利人依法采取措施以防止其权利受到侵犯的行为。例如中国民法典规定的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际违约行为发生之前,允许受害人解除合同或者中止履行合同,以保护自身利益,对防止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或者在侵害结果发生后难以得到公力救济具有重大意义。事中私力救济是指合法权益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或者其他危险时,权利人或第三人当场采取必要手段,制止不法侵害或者排除现实危险,从而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中国刑法第20 条、第21 条规定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事后私力救济是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因公力救济的滞后性导致权利无法得到及时有效保护,权利人采取必要手段恢复其权益的行为[14]。例如自救行为中,盗窃案的被害人在盗窃犯携带赃物逃离现场后,又从盗窃犯手中夺回财物的,属于事后私力救济[15]。
事前救济、事中救济和事后救济中各自对应的不法侵害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在事前救济中,不法侵害行为还没有真正开始实施,最多处于预备阶段。例如甲扬言早晚有一天要杀掉乙并开始准备杀人工具,乙得知情况后立即报警,公安机关依法对甲行政拘留,经过思想教育,甲放弃了杀乙的计划。这是典型的事前公力救济。在事前救济的情形下,不法侵害一般表现为预备行为,有的甚至只是犯意的表示,不法侵害尚未进入着手实行阶段。此时的行为虽然也是违法的,但是其对法益的侵犯程度轻微,仅仅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的、抽象的危险②事前侵害中的不法侵害对法益形成的危险是不确定的,因为人具有自由意志,在侵害人真正着手实行侵害行为之前,完全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例如甲扬言杀乙之后,因害怕承担刑事责任而主动放弃杀人计划。又因为事前侵害中的不法侵害至多处于预备阶段,其对法益所产生的危险并非属于具体的紧迫的危险,而是仅仅属于抽象的危险。。事前救济所对应的不法侵害行为属于抽象的危险行为,事前救济所起的作用是预防不法侵害。而在事后救济中,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法行为对法益既可能造成实际侵害结果(简称“实害结果”),例如犯罪既遂;也可能没有造成实害结果,例如犯罪未遂。因而,事后救济所对应的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实害行为,也包括危险行为。不过,此处的危险是指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而非不确定的、抽象的危险①在杀人未遂案件中,杀人犯的开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但由于枪法太差而未能击中要害,被害人受到轻伤。杀人犯的开枪行为对被害人的生命法益所造成的危险属于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这与杀人的预备行为(例如为杀人而买枪)对他人生命法益造成的不确定的、抽象的危险是不一样的,二者存在程度上的差别。。 事后救济所起的作用既可能表现为挽回损失,例如盗窃案件的被害人通过自救行为挽回了财产损失;也可能仅仅表现为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而无法挽回损失,例如人民法院依法对杀害他人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但是被害人的生命却无法挽回。而事中救济介于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之间,其发挥的作用既不是预防不法侵害,也不是事后惩罚和挽回损失,而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制止该侵害行为。因此,事中救济所对应的不法侵害只能是正在进行中的侵害行为,该侵害行为既要处于已经开始(如果尚未开始,就属于事前救济的范围),又要处于尚未结束(如果已经结束,则属于事后救济的范围),显然,这样的侵害行为只能是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而不包括已经造成实害结果的侵害行为和不确定的、抽象的危险行为。由于正当防卫属于事中私力救济,所以,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只能是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
总之,从法律救济体系来看,事前救济的功能是预防侵害,与之对应的不法侵害是不确定的、抽象的危险行为;事后救济的功能是挽回损失或惩罚,与之对应的不法侵害是实害行为或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事中救济的功能是制止侵害,与之对应的不法侵害是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作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不法“侵害”,理应是指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而不包括实害行为。
(二)基于刑法条文规定的分析
中国刑法第20 条和第21 条分别规定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据此,正当防卫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采取的防卫措施,紧急避险是对正在发生的“危险”所采取的避险方法。毫无疑问,从救济行使的时间来看,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属于事中私力救济。因此,从体系解释方法的要求出发,对二者所救济事态的性质应当做出相同解释,即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也应当解释为“危险”②正当防卫中的这种危险是指人的不法行为对法益所造成的确定的、紧迫的危险;紧急避险中的危险并不限于人的不法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危险,其危险来源相当广泛,既包括人的行为,也包括动物、自然灾害、疾病等带来的危险。,而非“实害”。
另外,从新旧刑法的对比来看,刑法学界一般认为,与1979 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揭示了正当防卫的本质,即在法条中明确表述正当防卫是“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所谓“制止”不法侵害,就是指防卫行为迫使不法侵害停止,没有发生侵害法益的实际后果。如果已经发生了侵害法益的实际结果,就不属于“制止”不法侵害。从侵害者一方来看,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仅仅对法益形成了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在尚未对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结果的情况下即被防卫人阻止。因此,作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应指(紧迫的)危险行为,而不包括实害行为③不法侵害仅指危险行为而不包括实害行为,并不意味着不法侵害在事实上没有对法益造成任何实害结果。例如甲持刀杀乙时遇到了乙的强烈反抗,导致甲未能杀死乙,但是造成了乙轻伤害的结果。此案中,作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是甲的杀人行为,而不是事实上导致乙轻伤结果的伤害行为;就杀人行为而言,虽然甲没有造成乙的死亡结果发生,但是却有致乙死亡的紧迫危险。就乙的防卫行为而言,其所制止的不法侵害就是甲正在实施的具有导致乙死亡危险的杀人行为,甲的杀人危险行为就是乙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正是由于乙的防卫行为有效制止了甲的杀人行为,才导致乙仅仅受到了轻伤结果,该轻伤结果正是乙正当防卫所带来的效果,如果没有乙的有效防卫,甲就会造成乙的死亡结果。。
中国刑法第20 条第3 款的规定也足以证明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是指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根据该款规定,防卫行为可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伤亡的前提条件是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法条术语采用的是“危及”而非“危害”。在汉语中,“危害”是指损害、破坏的意思,而“危及”是指威胁到的意思④《汉语大辞典》对“危害”和“危及”的解释。http://www.hydcd.com/cd/htm_a/3365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18 日。。显然,“危及”人身安全是指行为威胁到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对他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危险状态;而“危害”人身安全是指行为损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对他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实际侵害结果。在此,立法者选用“危及”而非“危害”一词,表明了其对不法侵害的要求是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的鲜明立场。刑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立法者认识到只有对严重威胁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防卫才有意义,而对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暴力犯罪,则已完全丧失了防卫的必要性。因此,对该款规定中的“危及”一词应当解释为“威胁”或者“给……带来危险”,而不能解释为“给……造成危害结果”。
(三)基于防卫实践需要的分析
一个良好的制度必然是照顾现实需要的制度。法律设立正当防卫制度的初衷是支持和鼓励公民在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能够挺身而出,积极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因此,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必然要反映防卫实践的现实需要。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鼓励公民大胆行使正当防卫权的作用。在现实发生的防卫案件中,不法侵害人往往有备而来,在案件起因上占据主动地位;而防卫者往往毫无准备,处于被动地位。从防卫人的角度来说,当不法侵害人已经着手实施侵害行为,对他人的法益造成紧迫的危险状态,但还没出现实际侵害结果时,应当是采取防卫措施的最佳时机。此时,允许防卫者对侵害者予以反击,可以有效地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从而实现正当防卫的效果。如果等到不法侵害已经对他人(包括防卫者和第三人)的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结果时才允许防卫,要么会出现防卫者难以甚至无法实施防卫行为的局面(例如不法侵害导致防卫者重伤时,防卫者难以进行有效防卫;不法侵害导致防卫者死亡时,防卫者无法实施防卫行为);要么会使防卫行为变得毫无意义(例如不法侵害导致第三人死亡时,防卫者即使采取反击措施也无法挽回他人的生命)。现实发生的大量的正当防卫案件都能说明这一点。从正当防卫的实际需要出发,只有将不法侵害解释为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才是合理的。
二、实害行为理论的表现及其谬误
在当前的理论与实务中,实害行为说的理论流传甚广,从而对司法实务正确认定正当防卫产生消极影响,也误导正当防卫理论的发展方向。
(一)实害行为说在实务上的表现及问题分析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的现象,从而引发一些不良倾向的出现:一是会导致只有不法侵害造成实际侵害后果才能实施防卫行为,从而严重束缚了防卫人的手脚,致使其无法有效实施防卫行为;二是可能助长不法侵害人的嚣张气焰,让其感到只要还没有造成实害结果,防卫人就不能防卫,导致正向不正让步;三是导致司法人员在认定防卫限度时将防卫结果与侵害结果进行简单比较,将本应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错误地认定为防卫过当,致使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的认定率极低,挫伤了公民行使防卫权的积极性。
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司法机关对不法侵害的不当解释①至于司法机关为何会将不法侵害解释为包括实害行为,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背景如何,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是重要原因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有关正当防卫的指导案例评析意见中明确指出,不法侵害行为包括实害行为②https://www.sohu.com/a/408 318 538_120 387 323?_trans_=000014_bdss_dkwcdz12zn,检例第47 号:于海明正当防卫案。。
实践中,许多司法机关正是由于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所以,才将实害行为作为防卫前提和防卫对象,并将其作为确定防卫限度的重要依据。实务中广泛存在的将防卫人实际遭受的侵害结果与不法侵害人实际所受的损害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得出防卫过当结论的根源正在于此。例如在广受争议的于欢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于2017 年5 月28 日就于某故意伤害案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介绍了检察机关对不法侵害的认定,认为从防卫起因看,本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按时间顺序可分三个阶段:一是2016 年4 月1 日赵某荣等人非法侵入于某家住宅、4 月13 日擅自将于某住宅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大公司堆放,吴某占将苏某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二是2016 年4 月14 日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为,限制、剥夺于某和苏某霞人身自由,实施辱骂、脱裤暴露下体在苏某霞面前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于某、苏某霞人格尊严的行为,采取揪抓于某头发等行为侵害于某人身权利,在源大公司办公楼门厅前烧烤饮酒,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到于某持刀捅刺之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某、苏某霞离开接待室,强迫于某坐下,并将于某推搡至接待室东南角。检察机关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具有持续性且不断升级,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行为。面对这些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于某为制止这些不法侵害,反击正在实施不法侵害的加害人,完全具有正当防卫的前提①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1 705/t20170528_19172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 年11 月18 日。。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检察机关认定的不法侵害范围比较宽泛,既包括案发当天侵害者实施的非法拘禁、侮辱、殴打等行为,也包括案发前实施的非法侵入住宅、侮辱等行为。事实上,除了案发当天侵害者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一直持续到于某采取防卫措施以外,其他侵害行为包括4 月1 日赵某荣等人的非法侵入住宅、4 月13 日搬运物品至公司堆放和将苏某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4 月14 日辱骂和脱裤侮辱于某母亲等行为已经结束,在于欢实施防卫行为以前均已造成实际侵害结果,而非仍然处于持续状态中的危险行为。例如,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已经对于某及其母亲的生活安宁造成破坏、脱裤侮辱于某母亲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实际侵害,而且这些行为在于某采取防卫措施以前已经实施完毕,已无法通过私力救济予以挽回,不可能再通过实施防卫行为予以制止。因此,不应当将这些实害行为视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将实害行为视为不法侵害,所以,有关负责人在分析该案的防卫限度时指出,于某使用致命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后果,(但其本人)身上伤情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程度,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①。在此,司法人员显然是将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与不法侵害行为造成的侵害结果进行比较,而不是将防卫结果与不法侵害行为的危险进行比较,自然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由于不法侵害是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所以,作为正当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只能包括实施防卫行为当时实际存在的对法益形成紧迫危险的行为,而不包括已经对法益造成侵害结果且无持续危险的行为;与此相联系,在判断防卫限度时,应当将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与不法侵害行为当时对法益形成的紧迫危险进行比较,而非将防卫结果与侵害结果进行比较。
具体到于欢案件,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应当仅限于某实施防卫行为时客观存在的非法拘禁以及殴打行为;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时,应当将于某防卫行为造成的死伤结果与侵害者当时实施非法拘禁和殴打行为时可能造成的侵害结果(即危险)进行比较,而不是将防卫造成的死伤结果与防卫者实际遭受的未达到轻微伤程度的伤情进行比较。所以,司法机关关注的重点首先应当是4 月14 日22 时22 分,于某、苏某霞欲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某浩等人究竟对于某和苏某霞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于某和苏某霞的人身权利产生了什么样的危险?如果于某当时没有采取防卫措施的话,他和母亲苏某霞可能遭受什么样的侵害结果?一句话,防卫人面临的不法侵害的危险是什么?这是司法机关办理正当防卫案件首先要查明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办案机关并未将工作重点放在查明不法侵害的危险问题上面,而把查案重点放在实害行为和实害结果上面,导致无法准确判断防卫人当时面临的危险究竟是生命危险还是人身自由被继续剥夺等其他危险。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被告人于某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与杜某浩、郭某刚、程某贺、严某军等人发生冲突,被告人于某持尖刀将杜某浩、程某贺、严某军、郭某刚捅伤。”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6〕鲁15 刑初33 号。问题是“被阻止”“发生冲突”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例如对方是采取什么手段阻止于某离开的?是用杀死、伤害还是其他方法威胁的?并不清楚。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于某、苏某霞欲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杜某浩等人阻拦,并强迫于某坐下,于某拒绝。杜某浩等人卡于某项部,将于某推拉至接待室东南角。于某持刃长15.3 厘米的单刃尖刀,警告杜某浩等人不要靠近。杜某浩出言挑衅并逼近于某,于某遂捅刺杜某浩腹部一刀,又捅刺围逼在其身边的程某贺胸部、严某军腹部、郭某刚背部各一刀。”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7〕鲁刑终151 号。从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看,比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更为具体,增加了杜某浩等人卡于某脖子、出言挑衅和围逼等细节,但是卡脖子的力度究竟有多大、围逼时有无使用工具等并不清楚。如果卡脖子的力度足以致命或者围逼时使用致命工具,就会给于某造成生命危险。那么,在判断于某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时,就应当将侵害方对于某造成的生命危险与于某给侵害方造成的死伤结果进行比较,就会得出于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的结论。
(二)实害行为说在理论上的表现及其问题分析
实害行为说在刑法理论上的表现主要是所谓持续侵害的“累积升高”理论。有学者认为,持续侵害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持续进行的不法侵害,它由两要素组成,即事实上累积的侵害危险及社会公众(包括防卫人)对该危险的感受;对其危害性要进行“累积升高”评价。当不法侵害是由多人的多个违法犯罪行为结合而成且持续实施时,应该综合地、整体地判断这一连串行为最终累积起来并“层升”的危害总量,确定防卫行为的一瞬间,防卫人遭受的不法侵害的“质”和“量”,进而确定其可以适用何种强度的防卫,最终准确判断其防卫是否过当。以特殊防卫中“行凶”的认定为例,当多人持续对被害人实施多种侵害进行折磨,尤其当公权力行使者离开,被害人精神彻底崩溃时,即便侵害人实施强度有限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累积的“行凶”[16]。“累积升高”理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将实害行为作为防卫前提,违反了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宗旨。按照该理论,只要不法侵害是由多个违法犯罪行为组合而成,无论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是否造成实际侵害结果,都允许对其正当防卫。但是实际上,由多个违法犯罪行为组合而成的一连串持续侵害行为,其违法犯罪的形态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可能有的是既遂、有的是中止、也有的可能是未遂。对于构成犯罪既遂且已实行终了的实害行为,由于已经无法再制止不法侵害,丧失了防卫的必要性,所以,不应当主张对之正当防卫。例如,在于欢案中,不法侵害者案发前(2016 年4 月1 日、13 日)实施的非法侵入住宅、侮辱等行为早已完成,实害结果也已发生;即使案发当天,在于某实施防卫行为前,侵害者的侮辱、强制猥亵等行为也已实施完毕,对被害者的人格尊严、性羞耻心等人身权利已造成实际侵害结果。这些实害结果不可能再通过所谓的“防卫”行为加以挽回,因此,不应成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如前所述,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既然实害结果已经发生,已经不可能通过私力救济予以挽回,就失去了正当防卫的意义。此外,对于构成犯罪中止或犯罪未遂的侵害行为,同样不属于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因为无论是已经中止或者未遂的侵害行为,都已经停止了对法益的侵害,原本对法益形成的危险已经消灭,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不应对之正当防卫。只有在防卫时刻现实存在的对法益形成紧迫危险的不法行为,才是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
二是该理论主张多个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累积升高,混淆了正当防卫与刑罚、其他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众所周知,刑罚和其他法律制裁手段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某人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实施多个违法犯罪行为,当然可以对这些行为合并处罚或者数罪并罚,违法犯罪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刑罚或其他法律制裁力度的增强,这是罪刑关系的必然要求。但是正当防卫并非刑罚或其他法律制裁手段,它不具有处罚的性质,只是法律赋予公民在紧急情况下的一项私力救济措施。虽然从效果上分析,正当防卫也具有威慑违法犯罪分子的作用,但是这只是该制度的反射效果,就好比复仇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威慑违法犯罪分子的作用一样,但是并不能说复仇就是法律所允许的惩罚手段。从性质上分析,正当防卫是法律规定的事中私力救济手段,它具有私权性质,只能针对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来进行。而对不符合防卫前提条件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并不允许对其进行正当防卫。“累积升高”理论主张对多个违法犯罪行为组合而成的侵害行为进行整体判断,累积其危害总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防卫的强度。显然,这是将正当防卫看作了刑罚或其他法律制裁,按照罪刑均衡或者比例原则的要求,象法官根据犯罪行为的数量和社会危害性大小量刑一样,依据不法侵害行为的数量和危害总量来确定正当防卫的强度。这就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制度之间的界限,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不法侵害人甲在杀死被害人乙以后,又紧接着对乙的尸体进行侮辱,一直旁观整个侵害过程的乙的儿子丙此时再也忍无可忍,冲上前去用刀将甲砍死。按照“累积升高”理论,丙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因为甲的不法侵害由两个行为组成:一个是故意杀人行为,另一个是侮辱尸体行为,在确定防卫强度时,应当对这两个行为整体判断,累积危害总量,必然得出丙杀死甲完全符合防卫限度的结论。 但是,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当丙用刀砍甲时,甲的杀人行为已经完成,被害人乙已经死亡,乙的生命已经无可挽救,此时,甲的不法侵害仅表现为侮辱尸体,而非杀人行为,正在进行的侮辱尸体行为才是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丙将侮辱尸体的甲砍死,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
三是该理论主张判断正当防卫的标准是社会公众(包括防卫人)对危险的主观感受,过于主观化,可能导致认定的随意性。在三阶层犯罪理论体系下,正当防卫属于违法阻却事由,违法性判断的客观性必然要求正当防卫的判断应当坚持客观标准,而不是主观标准。而“累积升高”理论主张由社会公众和防卫人依据其对危险的自身感受,来判断不法侵害的大小,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侵害和其他不可控的因素,被害人精神彻底崩溃时,即便侵害人实施了强度有限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行凶”,进而主张对其实施无限防卫权。这样一来,防卫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并非取决于客观上存在的不法侵害情况,而是完全取决于防卫人的主观感受:如果防卫人意志十分脆弱,精神容易崩溃,那么其行为就是正当防卫;反之,如果其意志非常坚定,抗压能力强大,那么其同样的行为则构成防卫过当。显然,这样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
三、危险的程度
作为正当防卫前提条件的不法侵害应指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问题是该危险究竟属于何种程度的危险?以故意犯罪的发展过程为例①以不法侵害的主观方面为标准,可以将不法侵害行为划分为故意不法侵害和过失不法侵害;故意不法侵害可以细分为故意犯罪和故意违法行为,过失不法侵害也可细分为过失犯罪和过失违法行为。刑法中关于故意犯罪形态的规定,例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既遂、犯罪中止,充分说明犯罪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法益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这也可以用来说明故意违法行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法益的危害程度是存在区别的。而过失犯罪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形态的问题。。 故意犯罪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②另有学者将故意犯罪的发展过程分为 6 个阶段:决意、阴谋、预备、着手实行、完成行为、发生结果。[17]295-297:一是预备阶段,从行为人开始实施犯罪预备行为时为起点,到行为人完成预备行为且尚未着手犯罪实行行为时为终点;二是实行阶段,从行为人着手犯罪实行行为时为起点,到犯罪既遂为终点[1]140。这两个阶段中的行为虽然都是犯罪行为,但是其对法益造成的危险程度不同:犯罪预备行为是为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其对法益所形成的危险性较小,属于抽象的危险;犯罪实行行为则是着手实施能够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其对法益所形成的危险性较大,属于具体的危险。不法侵害中的危险属于其中的哪种危险呢?另外,根据理论通说,犯罪既遂以后,例如小偷得手以后被发现,在逃跑途中被害人或第三人使用强力追回财产的,或者非法侵入住宅、非法拘禁他人以后,被害人或第三人使用暴力反抗的,属于正当防卫。这就必然产生这样的问题:犯罪既遂以后是否还存在不法侵害的危险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来考察。
根据中国刑法,正当防卫只能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来进行。所谓“正在进行”,是指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并且尚未结束。关于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如何认定,中国刑法理论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进入现场说,主张以不法侵害者进入侵害现场为标准;二是着手说,主张以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行为标准;三是直接面临说,认为应以合法权益已直接面临侵害的危险时为标准;四是综合说,认为一般情况下以着手为标准,特殊情况以直接面临为标准[18]。如何评价这些观点,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以及正当防卫的性质。首先,从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目的来看,无疑是在公权力不在场的情况下,要让防卫人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免受不法侵害。“有效保护”是确立正当防卫制度的一项核心要求。如果一项制度处处给防卫人设置障碍,导致其无法有效保护合法权益,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以着手说为例,该说主张只有当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时,才允许实施正当防卫。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越接近侵害的完成阶段(既遂),防卫人的防卫行为就越难以达到防卫目的。在持枪杀人案件中,中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当杀人犯瞄准被害人时就是杀人的着手[19]。问题在于,当杀人犯已经持枪瞄准被害人时,防卫人往往已经来不及或者很难再进行有效防卫。按照着手说,往往会错过有效防卫的最佳时间。有学者提出“有效理论”,主张只要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已经到达防卫人最后的有效的防卫时间点,换言之,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无法有效保护自己或第三人,就应允许采取防卫行为[20]。根据“有效理论”,防卫人最后有效的防卫时间就是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这对解决防卫的有效性问题十分有利;另一方面,“有效理论”对于不法侵害开始时间的认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过于提前。不法侵害人正在预谋或者只是处于犯罪预备阶段,按照“有效理论”也可被视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从而允许行使防卫权。这样就过分扩张了正当防卫的范围。对于一个有计划的侵害行为的事前预防,无论如何仍属权力机关的任务①Jakobs(Fn.5),12∕22。[21]。这就需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即正当防卫的性质。从法律属性来分析,正当防卫属于事中私力救济措施;根据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主导与补充关系的原理,只有当公力救济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时,法律才例外地允许公民行使正当防卫权。当不法侵害还处于预谋或者预备阶段的前期时,完全可以求助公力救济来预防不法侵害的发生,在此阶段就不应当允许采取私力救济性质的防卫措施;当不法侵害进入预备阶段的后期,尤其是接近着手实行时,一般而言就来不及求助公力救济了,而此时对于防卫者来讲,应当是防卫时间,防卫人往往只需采取较轻手段即可制止不法侵害;当不法侵害进入着手实行阶段以后,就更不可能求助公力救济了,此时对于防卫者来讲,并非最佳防卫时间,防卫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要想有效制止不法侵害,往往需要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所谓的“下狠手”)才能奏效;当不法侵害人完成实行行为,达到犯罪既遂以后,往往也无须私力救济了,一般不允许采取防卫措施②当然也有例外,对于继续犯和状态犯,即使犯罪既遂以后也允许采取防卫措施。按照通说,财产犯罪既遂以后,如果侵害人在现场或逃跑途中被抓获并被受害人采用强制手段追回财产的,对受害人的行为也可认定为正当防卫。。
综合考虑正当防卫的有效性要求以及事中私力救济的性质,将不法侵害或者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间③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就是正当防卫的开始时间,在此意义上说,二者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定位于“预备的最后阶段”或者“接近着手的预备阶段”较为妥当④Roxin(Fn.6), §15,Rn.24。[22-23]。“正确的界限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对于正在发生的攻击,人们除了未遂之外,仅仅允许算上直接地位于未遂阶段开始之前的那个狭长的预备结束阶段。”[24]甲乙二人正在商谈谋杀丙的计划时,被丁无意中听到,于是,丁暗中观察二人的行动。次日,甲乙二人共同到某黑市上购买两把枪支,然后各持一把枪支前往丙的家中,打算找到丙后共同开枪将丙打死。假设防卫人丁可以任意选择防卫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是法律所允许的正当防卫呢?按照“预备的最后阶段”理论,当甲乙二人商谈谋杀丙的计划时,属于预谋阶段;当甲乙共同买枪时,属于预备阶段的前期;当二人持枪前往丙的家中时属于预备阶段的后期;甲乙二人找到丙并开始掏枪时,属于预备的最后阶段;瞄准射击时,属于着手实行阶段;导致丙死亡时属于犯罪既遂。根据“预备的最后阶段”理论,只有当甲乙二人出于杀丙的故意找到丙并开始掏枪时,才属于预备的最后阶段。此时,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允许防卫人立即采取防卫措施进行反击。
总之,以“预备的最后阶段”为标准来认定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具有合理性,它兼顾了防卫的有效性和事中私力救济性。而其他学说由于各自存在不同缺陷而难以被实际采用:进入现场说并不一定意味着不法侵害进入了预备的最后阶段;着手说容易导致开始防卫的时间过于延迟,难以起到保护合法权益的效果;直接面临说与着手说没有明显区别,因为合法权益已直接面临侵害的危险,就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经着手,同样会导致开始防卫的时间过于延迟;综合说是着手说与直接面临说的折中,同样不具有合理性。
不法侵害开始于预备的最后阶段,持续发展到着手并进入到实行阶段。与此相对应,不法侵害的危险就包括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和实行阶段的危险。其中,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属于抽象的缓和的危险⑤危险的程度具有相对性:就不法侵害的危险性而言,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它的比较对象是谁。如果与预备阶段前期的不法侵害相比较,其危险性程度则更高,属于具体的紧迫的危险;但如果与实行阶段的不法侵害相比较,其危险性程度则更低,属于抽象的缓和的危险。,其对法益的危险程度介于预备阶段前期与着手实行之间的危险;实行阶段的危险属于具体的紧迫的危险,其对法益的危险性程度高于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区分这两种不同程度危险的意义在于对于合理认定正当防卫的限度具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防卫人在面临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时,只需采取较轻暴力即可制止不法侵害;当面临实行阶段的危险时,防卫人往往需要采取严重暴力方可制止不法侵害。前述案例中,甲乙二人出于杀丙的故意找到丙并开始掏枪时,丁只需开枪击中其手腕即可制止二人的杀人行为;但如果甲乙二人已经举枪瞄准丙甚至开始扣动扳机的时候,丁要想有效制止二人的杀人行为,往往需要击中要害、将甲乙二人杀死才能奏效。不法侵害对法益所造成的危险性程度越高,制止不法侵害所需要的防卫力度也就相应越大。
关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中国刑法理论上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结果形成说,认为危害结果实际形成即意味侵害结束[25];二是侵害制止说,认为侵害被制止时,不法侵害即告结束[26]; 三是危险排除说,主张排除不法侵害的客观危险就是结束时间[27]; 四是折中说,认为侵害结束无统一标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28]。不法侵害结束时间的认定取决于如何看待不法侵害的性质。既然不法侵害属于危险行为,其对法益造成的危险是防卫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不法侵害的开始时间就是危险的开始时间(即前述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开始时间),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危险消灭的时间就是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所以,判断不法侵害的结束时间应当采用危险排除说,即从实质上看,当不法侵害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客观危险已经消灭或者危险不复存在时,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已经结束,防卫行为即应停止。从表现形式来说,危险消灭通常表现为五种情况:侵害行为实施完毕且已造成危害结果、不法侵害者自动中止了侵害行为、侵害者已经被制服、侵害者已经逃离现场以及侵害者丧失了侵害能力。其他几种学说均因未能揭示危险消灭的本质而不宜采用:结果形成说有混淆犯罪既遂标准与正当防卫结束时间标准之间界限的嫌疑①犯罪形态与正当防卫是两种不同的刑法制度:刑法规定犯罪既遂、未遂、预备和中止这四种形态是基于合理追究刑事责任的需要,根据犯罪行为客观危害大小的不同和犯罪人主观恶性的不同,所规定的区别对待的责任追究制度;而刑法规定正当防卫则是出于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需要,兼顾防卫人和侵害人双方利益,所规定的一项正当化事由。因此,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理应与犯罪形态的认定标准相区分,不能把犯罪未遂中着手的认定标准直接拿来作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开始时间的认定标准,也不应把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错误地拿来当作不法侵害结束时间的认定标准。否则,就混淆了犯罪形态和正当防卫两种不同的制度。,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出现时达到了犯罪既遂形态,例如杀人犯已将被害人杀死,此时就失去了挽救法益的机会,不能再行使防卫权,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例如后述的继续犯和状态犯),不法侵害虽然已经既遂,但是仍然存在挽救法益的余地时,即应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允许被侵害者或第三人行使防卫权;而且该说仅能说明危险转化为实害结果时危险不复存在这一种情形,而不能说明侵害者自动中止、侵害者被制服等其他情形。侵害制止说仅能说明不法侵害者已经被制服这一种情形,而无法涵盖侵害结果已经形成、侵害人自动中止等其他情形;折中说并未提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与不法侵害结束时间之认定有关的争议问题是,当不法侵害已经既遂,但是侵害行为并未完全结束时,不法侵害行为的危险性应当如何认定?这主要涉及继续犯和状态犯两种情况。
继续犯(又称持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行为终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例如非法拘禁罪是典型的继续犯[1]180。在继续犯的情况下,犯罪已经既遂,但是犯罪行为并未完全结束,因而被害人的法益仍然处于侵害者的持续侵犯之中。刑法理论一致认为只要侵害行为仍在持续,不法侵害就没有结束,被害人有权实施防卫,对此没有异议。有疑问的是如何认定继续犯中的不法侵害?简言之,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究竟是指已经过去的实害行为,还是指即将来临的危险行为?抑或是二者均包括在内?根据本文的观点,不法侵害的性质是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所以,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仅指危险行为。就继续犯而言,不法侵害的范围应当仅限于防卫行为实施时,侵害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等法益进一步扩大侵害的危险,而不包括防卫行为实施前已经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例如,在于欢案中,杜某浩等人对于某及其母亲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属于继续犯,时间从2016 年4 月14 日16 时许开始,到当天22 时22 分左右于欢捅刀子后结束。问题是本案中的不法侵害究竟是何种行为?是捅刀子以前发生的非法拘禁行为,还是此后可能发生的新的非法拘禁行为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新的危险。根据危险行为理论,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应当指的是后者。因为正当防卫的性质是事中私力救济措施,其实质是制止不法侵害,对于采取防卫手段前已经发生的法益侵害结果(例如人身自由被剥夺6 小时),已经无法挽回,通过防卫措施可以挽救的只是那些已面临紧迫危险但是尚未发生实害结果的正处于危险状态中的法益。所以,对于继续犯而言,防卫行为可以制止的不法侵害,仅仅是可能发生的新的非法拘禁行为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新的危险。至于采取防卫手段前已经发生的拘禁后果及其他实害结果,不属于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就于欢案而言,于欢捅刀子所制止的不法侵害只限于防止此后可能持续进行的非法拘禁行为,以及侵害人可能改采的更严重的法益侵害手段[21]97。于欢捅刀子以前已经发生实害结果的非法拘禁、侮辱、强制猥亵、殴打等侵害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由于继续犯的特点是实行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存在,所以,作为继续犯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必然属于实行行为,而非预备行为。与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行为相比较,实行阶段的危险属于高度的、具体的、紧迫的危险;与制止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行为相比较,制止实行阶段的危险行为就需要更强的防卫力度,从而对其防卫限度的把握则较为宽松。
状态犯是指犯罪既遂以后,实行行为所造成的不法状态处于持续之中的犯罪形态[1]181。例如在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者实施完盗窃、抢劫等行为后,就非法地占有了他人财物,这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状态处于持续之中,但是盗窃、抢劫等行为已经结束。状态犯与继续犯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不法状态发生于实行行为结束之后,且只有不法状态的继续,没有实行行为的继续;而后者的实行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理论和实务界讨论的问题是:不法侵害者取得财物以后,正要离开或已经离开现场时被发现并受到追捕,追捕者使用暴力手段夺回财物的,如何处理?在国外存在着正当防卫论与自救行为论两种观点的争论,但是中国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在财产侵害(状态犯)的情况下,行为虽然已经既遂(结束),但是不法侵害状态仍然存在,在现场还来得及挽回损失的,应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19]264。对追捕者暴力夺回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的结论没有异议,但是对其理由则应持怀疑态度。如果认为被追捕者的侵财行为已经既遂(结束),就说明实害结果已经发生,而状态犯的特点是实行行为并不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正当防卫所针对的不法侵害就必然是实害行为,而不是危险行为。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制止不法侵害,防止其由紧迫的侵害危险转变为实害结果。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只能是危险行为,不能是实害行为。在追捕者夺回财物的场合,侵害者虽然已经取得财物,但并不意味着其侵财行为就已经既遂。以盗窃罪为例,盗窃既遂的认定标准,在刑法理论上主要有六种学说①这六种学说是接触说、转移说、控制说、移动说、失控说、失控加控制说。[1]500。 其中,通说是“失控说”,认为应以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作为既遂的标准。按照“失控说”,当小偷盗取他人财物,正要离开时被主人发现并追赶,此时,虽然小偷在物理上持有了他人财物,但是由于主人的追赶,随时有可能夺回该财物,导致小偷并未真正控制该物品,主人也没有完全丧失对财物的控制;换句话说,在追捕过程中,小偷对所盗财物的持有并未达到稳定的状态,主人并未完全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因此,在小偷将被盗物品转移至安全场所之前,主人使用暴力追回被盗财物的,对盗窃罪而言,属于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既遂。既然是犯罪未遂,就意味着该盗窃行为仍然处于犯罪的实行阶段,其对他人财产法益造成了接近实害结果的紧迫危险。由于接近实害结果的发生,该危险程度要比一般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更大,与此相对应,对接近实害结果的危险行为的防卫力度也要相应增强,从而对其防卫限度的把握则应更为宽松。
总之,从发展过程来看,不法侵害的危险大致包括四种形式: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实行阶段的危险、既遂以后的危险(继续犯)和接近实害结果的危险(状态犯);从危险程度来看,这四种形式的危险大小呈现逐步升级的趋势:预备最后阶段的危险性最小,实行阶段的一般侵害危险(包括继续犯的危险)程度较高,接近实害结果的危险程度最高;从防卫的限度条件来看,就同一种不法侵害而言,防卫所需的力度会随着侵害危险的逐级提升而增强:制止预备最后阶段的侵害危险所需的防卫力度最小,制止实行阶段的一般侵害危险所需的防卫力度较大,制止接近实害结果的侵害危险所需的防卫力度最大。
四、结论
准确理解不法侵害的性质对于正确认定正当防卫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无论是司法实务界还是刑法理论界,都普遍存在将不法侵害理解为实害行为的倾向,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对防卫标准的把握过于严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积极性。实害行为理论将不法侵害解释为实害行为,违反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宗旨,混淆正当防卫与刑罚及其他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其主观化的判断标准可能导致认定的随意性。应当予以纠正。从整个法律救济体系、中国刑法条文的规定以及防卫实践的需要出发,可以合理地推导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应指确定的、紧迫的危险行为而非实害行为的结论。同时,不法侵害的危险存在从低到高的程度上的差异,这对正确认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具有重要影响。